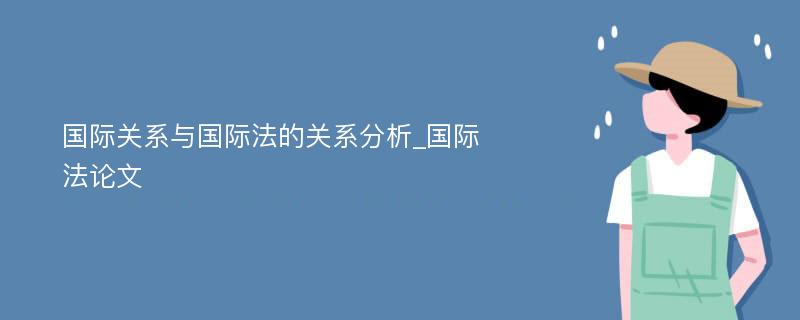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关联性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联性论文,国际法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国际关系是指主权国家之间的一切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关系,也包括文化、科技和法律方面的关系;既包括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间的关系。而狭义国际关系仅指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官方政治外交关系,即国际政治关系。(注:李兴:“‘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概念辨析”,《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2期。)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国际关系日益呈现出地域上的全球性,内容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互动性,层次上的复合性以及变迁的有序性等特征。国际法是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以及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注:卢松:“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传统国际法仅认同对狭义国际关系的调整与规制,但在当今国际关系呈纵横扩展的情况下,国际法本身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这一窠臼,日益关注其他层面复杂的社会关系。
国际关系属于国际社会事实层面的内容,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等属性;而国际法则属于其价值层面的内容,带有反映性和主观性。因此,它们之间既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联,又含有现实的矛盾,并不能预期二者达致完全和谐的关系状态。故此,承认关联并解析二者的矛盾才是推进其良性互动的根本。笔者试图就此做些探讨。
二元互动
国际关系的发展促成了国际社会的产生,构筑了国际法赖以发轫并勃兴的社会基础,使得国际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得以在对国际关系的调整与规制中实现;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国际关系的运行也需要有一个国际法律体系来进行有效协调。综观国际关系演进与国际法嬗变的历史,我们似可对二者的互动作四方面的归纳。
首先,国际关系催生了国际法。从法哲学观之,法归根到底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深嵌于社会母体之中,是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注:田成有:《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应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法因社会关系的调整而起,法的价值因其对社会关系的规制而得以实现,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了法存在的社会基础。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个共同体(主要是国家)及其成员间发生交互活动,形成交往关系,从而将原有的国内社会关系扩展至世界范围,形成了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性权威的社会系统,而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内在的秩序要求与其行为主体对利益与权力的本能追逐之间的矛盾又催生了一系列国际性规则。因此,国际法不应被看成是一种脱离权力和社会过程的机械的法条和规则,而应被视为在一个考虑政治及其它变量(variables)的背景中试图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者所作能动反应的结果,(注:See David H.Ott,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Modern World,Pitman Publisher,1998,p.10.)其产生和发展也有特定的社会基础: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彼此进行交往与协作,从而形成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注:梁西:“论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在现实中,奴隶制时期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和国家间关系只具雏形,但各国统治阶级已经开始以条约、和约的形式规定边界、战争及使节等原则,国际法渊源于此并对初具雏形的国家间关系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弥兵会盟”等制度对当时诸侯间战和关系的影响便是佐证。14世纪以后,国际法终于走上历史前台。其标志就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交替阶段爆发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全欧性国际战争,也是中世纪国际关系转入近代国际关系的契机。(注:杨泽伟:《宏观国际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1页。)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而告终,和约规定的国家主权原则、以国际会议方式解决争端、对违反规范者实施集体制裁以及常驻外交使节制度等,构成了近代国际法的基本脉络,是国际法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一个实际的国际社会的存在,而且标志着一种对国际行为产生直接约束力的国际法的存在。(注:黄德明:“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江汉论坛》,2000年第6期。)
其次,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运行产生规制性作用。基于一般法的作用方式,笔者将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规制性作用归纳为以下三点:提供制度架构以设定国际关系运行模式,规范具体国际行为,建立价值标准并进行价值评判。
国际法是基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状态而产生,并为维护这一基础的存在与发展而提供一定的制度架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设定特定的行为模式。这一作用方式不仅依赖成文的国际性法律,更多的是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准则、规则和程序而实现的。(注:刘杰:“论国际关系中的法理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2期。)譬如,二战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其否决权制度最初设定了美苏主导下的世界和平安全决策权的分配、行使以及制衡的模式,从而奠定了两极格局的制度基础,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美苏之外第三国的外交抉择并对冷战期间国际关系的演进铺设了预期的轨道。
如果说前种方式更多的是基于国际关系宏观层面和事物发展的可预期性,那么规范具体国际行为的方式则是在事物发展的现实性基础上更为普遍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微观层面,如,《南极条约》的缔结之于南极共同开发;WTO争端解决机制之于国际贸易纠纷;国际法院对“洛克比空难”的法律裁决之于利比亚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等都体现了这一行为方式。
国际法建立价值标准并据以评判国际事件的是非曲直,则体现了国际法对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直接涉及各国的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但长远看来却关乎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要求各国都承担相同的控制排放量义务,这显然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注:卢松:“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公约最终所采用了“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有效构建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都认可的控制排放义务的价值标准,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短期经济利益与人类环境大计的考虑,对各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与谅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再次,国际关系的发展丰富了国际法的内涵。国际关系的演进不断推动着国际法的嬗变,这一积极效应在当代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二战后,国际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权国家数量迅速增加,非国家行为主体也日益活跃;国家间关系从“高级政治”领域逐步扩展到“低级政治”领域,扩展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全球市民社会的勃兴成为一股新的力量,不断挑战着国家权威体制下的世界秩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化的共生、竞争逐渐摆脱“软要素”的地位;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遇到了有力挑战,和平与发展的呼声响彻全球……国际关系的多维化、多元化已经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与此同时,国际法的发展也相映成章。海洋法、空间法、国际经济法等新的法律部门层出不穷;WTO争端解决机制等程序性国际法也不断推陈出新;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网络和形形色色的国际司法、仲裁机构蓬勃发展,根植于丰厚的国际关系现实土壤,国际法发展进入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最后,国际法的完善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相对国内民主而言,国际关系的民主是一种更高级有序的民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注:引自胡锦涛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5/28/content-891128.htm)这些都是其题中应有之意。而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核就是主权平等和权力制衡,不断完善的国际法充当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助推器。
其一,国际法为国际关系民主比进程提供制度保障。民主与法制总是相辅相成,国际法以全球化框架下的民主价值为指南,通过建立一整套有关国际决策、执行、监督、制衡的原则制度,来达致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合理化解民主化体制建构对主权的不利影响,保障主权平等,以此来促进和保障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谅解》(简称DSU)第26条第2款确立了“消极协商一致”的表决原则,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民主化的促进堪称国际法推进决策架构民主化的典范(注:“消极协商一致”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其基本含义是:在就贸易争端设立专家小组、通过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报告、授权报复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除非协商一致反对该项请求或报告,否则就被DSB接受或通过,这样就有助于防止败诉方遭受胜诉方的准单方面报复,不仅使以往常见的败诉方阻挠争端解决进程的情况几乎不复存在,有助于争端的迅捷解决,而且平衡了当事方在争端解决中的发言权,充分尊重了争端当事方各自的主权。参见余敏友、左海聪、黄志雄:《WTO争端解决机制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1页。)。
其二,国际法的发展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奠定必要的组织基础。民主总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现代国际社会已日益呈现出组织化的结构趋势。大量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不断涌现,整个国际社会正在形成一个系统的组织网络。(注: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9页。)而国际组织本身就是作为国际法动态载体与机制形态而存在的,以联合国为核心、构筑于国际法基础上的各种政治性和专业性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司法仲裁机构,不仅在其内部权力与治理结构上体现了民主化要求,将各自的成员国纳入一定的民主机制内,而且还通过会议协商、斡旋、调停与建议、倡导等方式支持着全球性的民主步伐,业已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奠定了较为完备的组织基础。
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间关系的规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国际法既是国际关系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着国际关系,国际社会不断推动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的嬗变同国际关系的演进相辅相成。(注: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现实矛盾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情况:特定时代失衡的秩序呼唤理性的法律规制,却往往又以自身的无序运转推倒了法制的架构。这反映了国际关系这一国际社会事实层面内容与国际法这一价值层面内容在互动中的矛盾。下面笔者就对主体、内容以及价值取向三方面存在的矛盾试作分析。
1、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多元化vs国际法主体绝对化
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经历了由一元到多元的发展历程,即由以前的单一主权国家行为主体,逐步发展为国家与非国家两大类行为主体。
就国家行为主体而言,主权国家构成了整个国际社会运行的基础,既是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又是国际法律秩序的根基所在。而历史上殖民地里争取独立的民族建立的独立运动政治实体(如民族解放组织)因其具有一定的参与国际关系、享受国际法权利与承担国际法义务的能力,也是一种准国家的或过渡性的国际法主体。(注: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非国家行为主体(non-state actors)主要是一些国际组织。19世纪中叶多边国际会议作为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最早雏形应运而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现代国际组织。(注:此处专指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states organization)。)国际组织独立参与特定的国际关系,在其职权范围内具有国际法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而国际组织是现代国际法主体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注: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5页。)
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关于以上两类行为主体的规定性是一致的,但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社会情势的变迁,二者的吻合开始出现裂痕,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日趋多元化与国际法主体的绝对化构成一对显著矛盾,突出表现在对跨国公司和个人主体地位的界定上。
从一般法理上讲,跨国公司只是一个法人实体联合体,其所从事的主要是跨越国界的赢利活动。但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相互作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其跨越国界的经营行为事实上对东道国乃至母国的内外行为产生着极大的影响。1973年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智利阿连德政府被颠覆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就是显著例证。(注:智利左派于1970年大选获胜,该公司为避免其在智利的分公司及资产被没收即策动并支持智利国内由皮诺切特领导的反对派对抗政府,最终推翻了民选政府,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此外,跨国公司在逃避税收、转移就业、输出环境公害、跨国腐败中对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国际经济法的角度看,跨国公司是参与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但在这个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与多元文化相关联的时代,单纯依靠国际经济法只能规制和调节跨国公司所参与的国际经济关系,其出于赢利性目的而参与政治性国际关系(例如干涉东道国内政、跨国腐败等)时则成为国际法管辖的“真空地带”。
对个人主体的界定也是如此。“个人的行为对于发生在宏观政治范畴内的国际事件的进展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注:[美]威廉·奥尔森等:《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一些人主张个人(特别是精英人物)也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例如行为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一书中就专辟一章论述精英的权力,参见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88-97页。),因此个人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逐渐提升,但传统国际法一直否认其国际法主体资格。正如菲德罗斯所说:“国际社会原先只是抓住了一些国家和其他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将对个人生活关系的规定付诸各国。但是……不能先验地得出结论说国际社会剥夺了对个人生活关系的规定。相反,国际法学必须认识这个事实:国际社会已逐渐对这些关系的类别自行予以规定。”(注:[奥]菲德罗斯:《国际法》(上册),李浩培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页。)目前,个人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和承担义务已是不争的事实。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而直接规定公民应享有的各项权利;个人在某些领域也享有程序权利,如根据1969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一个特别委员会被授权听取个人针对其国家的诉讼;(注:[美]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余逊达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而个人能够直接承受国际法上的义务这一规则早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中就明白无误地确立了。(注:汪自勇:“对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反思”,《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因此,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是一个是否承认而不是是否存在的问题。现时的情况是,“主张个人具有排它的国际人格的理论家虽然还少,而承认于国家之外赋予个人以法律上有限的国际人格的学者则愈来愈多”。(注:转自引周鲠生:《国际法》第66页。)
此外,在国家不能或不愿涉足的领域,各种非政府组织(NGO)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战前夕全世界大约有170个非政府组织;至1940年,这个数目增加到500个;而20世纪90年代初时非政府组织剧增至约4600个。(注:See Charles W.Kegley.Jr,Eugen R.Wittkopf,World Politics:Trend and Transformation,St Martin's Press,1993,p.155.)非政府组织提倡和动员公共支持;提供知识、技术和非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还可以充当可供选择的沟通渠道、创造弥合政治分歧所必需的信任关系;更重要的是,非政府组织正帮助确立公共政策的议程——指明或确立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注:See Jessic T.Mathews:Power Shift,Foreign Affairs,Volume76,No.1 January/February 1997,p.58.)这些都彰显出非政府组织在日渐凸现的全球市民社会中业已成为重要的变革力量。其出于公益性目的而参与国际关系时则成为国际法管辖的又一个“真空地带”。那么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又如何界定呢?李浩培先生曾对国际法主体作过这样的概括:“国际法主体是其行动直接由国际法加以规定因而其权利义务从国际法发生的那些实体。”(注:黄炳坤主编:《当代国际法》,香港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33页。)这一界定非常灵活,它绕开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参加者的定势要求,直接以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判断何为国际法主体,既包括了传统的主权国家主体,又能容纳二战后的国际组织,同时也不排除直接由国际法所调整的某些特别关于个人的法律关系中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注:汪自勇:“对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反思”,《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对于跨国公司和非政府国际组织而言,这一界定同样适用。跨国公司及其他事实上的国际关系参与者都无一例外地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主体,其与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广义国际关系的一部分,直接依照有关国际法的规定,它们事实上与传统国际法主体之间业已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国际法律关系,跨国公司、个人以及其他国际关系参与者应同样具有广义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2、国际关系内容的复杂性vs国际法功能的有限性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与互动。战后世界经济的空前发展集中体现于生产跨国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经济一体比加深了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态势,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趋势加强。(注:See Dennis Pirages:Global Ecopolitics-the New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uxburv Press.1978,p.5.)199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讨论当时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该组织中的成员国地位问题时,明确裁定该国已不复存在,终止其成员国资格并认定波黑等五个加盟共和国为其在该组织中的财产和债务继承者。这一决定与其说是裁定一个主权国家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不如说是决定和宣告一个主权国家是否存在。(注: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除了这种对主权的“硬碰撞”之外,世界经济变动所引起的对主权的“软侵蚀”也是屡见不鲜的。作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重要成果的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所含各项协定,就触及了关税、出口限制等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国内政策的排他领地。正是在这种“软硬兼施”之下,“主权的黑盒子”开始变得透明起来(注:See Anne-Marie etc,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Dual Agenda,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7,1993,p.207.)。相应地,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也相伴而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改往日“革命外交”和“意识形态外交”的路线,强调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这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与此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也随着市场制度、贸易和金融准则以及西式民主政制在全球的扩张而跃过国界大肆传播渗透,试图取得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准则的地位,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则面临被同化、被湮灭的危险。(注:杨泽伟:《国际法析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由此,民族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激荡也对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变迁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融合与互动的大背景下,对某一个具体的国际问题而言,已经很难区分到底是国际经济问题还是国际政治问题了,而且其中往往掺杂着政局稳定等国内因素。虽然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以及其他具体国际关系范畴各自的演进不断催生新的国际法部门,但在这种融合互动的大背景下,传统的部门国际法的单一功能发挥就日益显出不足。例如历时十余年才出炉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为保护并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而制定,但其所涉及的领海区分问题、临海国与内陆国海洋经济利益差异问题、发达国家在履约上的强势地位问题(注:美国里根政府1982年12月以本国从事海底采矿的私营公司利益受损为由否决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重新协商有关条款,于1994年补充达成一项协定以照顾美国的利益,这就是发达国家在国际法制定及履行方面强势地位的真实写照。)却远非一部公约所能解决。正是国际法自身和诸多外在的因素使得国际关系内容的复杂性与国际法功能的相对限制性构成又一对难解的矛盾。
其一,国际法自身的因素。国际法所建立的不是以统治权为基础的法律秩序,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超越当事者的最高权威,因此,国际法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效力较弱的法(weak law)(注: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此外,部门国际法的日趋专业化固然有助于涵盖尽可能多的领域,以充分发挥规制功能,但现实的困境是,条块分割过细导致各种部门法资源难以协调起来去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现实。
其二,国际政治的干预。如王铁崖先生所言,国际政治关系是国家之间最活跃的关系,由于国际社会受到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制约,国际政治给国际法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美国及其盟国对伊拉克在1990年夏入侵科威特作出了暴力性的反应,这被视为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这一国际法律制度框架内的“正义之举”,而美国自己却在距此不到9个月前(即1989年夏)入侵了巴拿马。仅数月之隔,国际法却屈从于强权政治,《联合国宪章》最终没有敌过“自由女神”的“权杖”。
3、国际关系价值趋向上的普世化vs国际法的“国家间”狭隘性
国际法建立于平等主权国家的协调意志之上这一特点,决定了它是由体现平等主权国家协调意志的规则所组成的体系,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它可能具有这样的缺陷,即在体现和维护人类基本道德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方面能力比较弱。在很多情况下,人类基本道德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是与各国的道德和国家利益一致的,因而可以通过国际法的规则体现出来并得到保障。但并不尽然,传统国际法在这方面表现更为明显。20世纪前后的国际法无力约束列强的扩张和侵略并防止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平与人权等人类基本道德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才会被践踏无遗;(注:王曦:“论现代国际法中‘对一切,义务的概念”,《珞珈法学论坛》(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人类共有的自然环境也因为国际机制约束不力而成为狭隘的国家利益之争的牺牲品。国际法这一缺陷除了源于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本身所反映的“国家间”意志协调性与面对全球问题应运而生的国际关系价值趋向普世化的矛盾。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新科技革命产生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诸如人口爆炸和老龄化、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恐怖主义等等,就其范围而言是跨越国界的、关系到整个人类利益的,就其严重程度而言是危及整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注:俞正梁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205页。)如何在现有的国家体制下发挥国际法的积极作用,以谋求国际关系普世性价值的实现,已日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全球问题的蔓延和加剧推动着国际社会携手加强国际合作,主权国家政府主导的国际合作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以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市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也逐步走上了历史前台,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非政府国际组织以本集团利益或全人类利益为终极关怀,作为“人民代表制的基本形式”(注: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语,俞正梁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在超国家层面和跨国家层面发挥作用,已经对现行的主权国家权威体制提出挑战,构建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法律体系也因此受到冲击。例如,1999年底,新一轮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在美国西雅图举行,但是因为会场外的劳工组织抗议、生态环保组织反对及其他NGO的阻挠而无果而终。
在二战后提交国际法院的第一桩案件——1946年科孚海峡案中,国际法院指出阿尔巴尼亚炮击通过科孚海峡的英国军舰前,没有基于“普遍的、广为承认的原则”(general and well-recognized principles)而履行通告的国际义务,其所指的这些原则即“人道主义的考虑、海上交通自由原则和国家不得故意准许其领土被用来从事违背其他国家的权利的行为”(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编:《国际公法案例评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8-80页。),其中,人道主义原则是一项适用没有例外情况的绝对原则。故而,国际法院最后判决阿尔巴尼亚做出赔偿。从国际法院的上述原则依据可以看出,现代国际法学界已经认识到了国际法的这种缺陷,它不仅谋求平衡单个国家之间的权利,而且努力平衡单个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利益,以求对整个无政府体系中规范各国间关系的秩序和稳定问题作出回应。国际法院裁决的尽管遇到公正与否的质疑,而且始终没有被执行,但它无疑既照顾了当事国各自的主权,又兼顾了人类基本道德准则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应该说较好地体现了国际关系的普世性价值追求。这一案例告诉我们,力图把横向的主权国家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对等要求与纵向的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协调性有机结合起来,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协调中介
今日世界全球化日益加深,超越国界的世界经济发展,逐步走向组织化、民主化的国际政治社会以及相互激荡的多元文化,共同推动现代国际关系逐步迈出“威斯特伐利亚体制”,新的运转模式呼之欲出,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互动与矛盾也更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置身如此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树立一种广义的国际观。从语言学角度讲,汉语中的“际”和英语中的“inter”都是“之间”的意思,基于过去单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构建国际社会的事实,传统国际观认为“国际”就是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就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法就是指国家间的法。这一观念适用于过去的国际社会,但已经与现在的世界经济社会情势不相符合,这也是以上三对矛盾产生的观念层面的原因。为此,我们提出应以广义国际观替代传统的狭义国际观,即“国际”应被界定为构建于主权国家、国际组织、民间及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关联基础上的复合、立体的秩序框架。广义的国际法更应区别于传统的国际公法,应为反映国家意志的协凋并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限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注:黄进:“宏观国际法学论”,《法学评论》,1984年第2期。)它更多的是一个体系,而不是一个部门法,其特点在于针对具体国际问题,通过对各种国际法律规范进行综合研究以提供“一个丰富的规则库藏,人们在处理案件时可以从中吸取适用的法律而不必担心是应该适用公法还是私法”(注:P.Jessup,Transnational Law,Yale University Press,1956,p.15-16.),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事实上,国际现实中的很多问题都需要从广义国际观的角度来分析处理,例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了联合国对伊进行经济制裁,这既涉及针对侵略事件的国际政治斗争,又与经济性质的制裁相关联;既与伊科等当事国有关,又涉及联合国、欧美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主体;既内含着国际公法中的一些传统问题,又因实施制裁而殃及欧美银行中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存款,从而影响了国际金融秩序。于是有关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纷纷出面,努力解决因这些复合因素而造成的混淆公共与私人界限这一问题。(注:[美]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余逊达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另外,为了应对一体化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巨大影响,欧盟在劳工、农产品销售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规定了不同于传统国际法的宽松的法律适用制度,打破了国际法与国内法以及国际法诸部门之间的界限,创立了独具一格的“欧盟法”体系,这也是依广义国际观念应对国际现实的经典案例。
其次,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作为独立于主权国家及国家间治理体制之外的新治理模式,理应受到高度重视。全球治理就是试图在全球层次、区域层次和次区域层次上,通过改革重建一套全新、更有效的管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注:乔卫兵:“全球治理及其制度化”,《欧洲研究》,2002年第6期。)它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民主化要求与发展趋势,是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全球市民社会三方面力量在全球政治领域博弈的结果。一方面它要求主权国家积极改变自己的传统角色,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并造福于全人类;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国际组织治理的加强对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周延召、谢晓娟:“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但与此同时,现阶段国家主权的不可超越性又制约着全球治理的发展与扩张,全球治理仍然必须构建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因此,顺应全球治理趋势进行主权的重构以及实现民族国家体制在全球化时代的自我扬弃,也已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课题。
最后,基于以上观念与实践层面的认识,作为人类世界智慧所凝结的国际关系学科和国际法学科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应相互借鉴。没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事实解析与预测,国际法研究就会缺乏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而陷入“法律无边”的荒谬,因此研究国际法必须注重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必须以实证精神为指南;同样,没有国际法的规范研究提供制度框架和价值评判,国际关系研究就会出现无序与混乱,“法律虚无主义”就会滋生,(注:李谋盛:“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法学评论》,1984年第2期。)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也必须掌握基本的法律分析方法和价值评判原则。这种借鉴并不会混淆应有的学科界限,有学者甚至主张“国际法律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际法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方面,国际法学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部门”。(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它对于以更扎实的社会科学底蕴、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国际风云变幻,是不无裨益的。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的演进与国际法的嬗变是一个二元并进、相辅相成的历史进程。秉承广义国际理念以夯实这一进程的价值基础,推进全球治理以协调二者相形相进的实践步伐,从而使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在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上协调运作,毫无疑问将更好地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