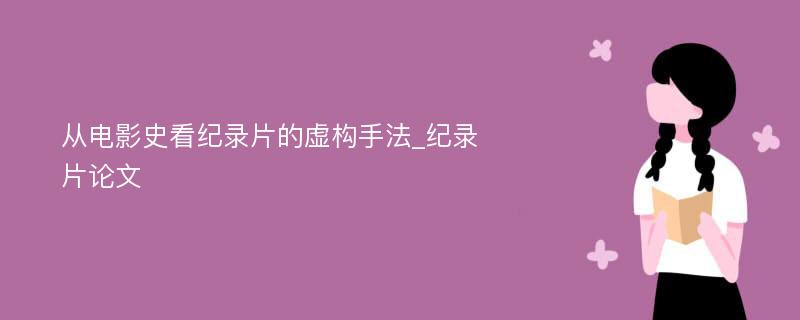
从电影史看纪录片的虚构手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录片论文,手段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我国纪录片呈现产业化、国际化的趋势,尤其是最近两年一批纪录片取得了既卖座又叫好的收益。与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纪录片就是纪实手法的刻板印象不同,这些新纪录片大量使用虚构手法,引发了学界业界关于纪录片真实与虚构关系的又一次争论。
关于纪录片是否可以采用虚构方式,虚构与真实是否对立等问题,在电影史上有过多次争论,出现过“每部电影都是一部纪录片”[1],“每一部电影都是虚构的”[2]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电影理论家认为“非虚构是纪录片最后一道防线,失去了它,纪录片同故事片就分不清界限”[3],另一些则认为“纪录片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达到真实”[4]。
在本文中,笔者回到纪录片发展历史中找寻虚构与真实关系的答案。本文通过历史分析力图证明,纪录片从来都不仅仅是纪实,虚构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并不专属于剧情片。纪实与虚构都是纪录片的表现手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掘本质真实。
一、世界纪录片发展史:虚构——非虚构——再虚构
世界纪录电影的演进史是顺着“虚构——非虚构——再虚构”的轨迹不断发展的。
(一)虚构与纪实的源头:电影滥觞时代的两种传统
如果把纪录片发展史放在整个电影理论发展的大框架下理解,那么纪录片发展过程中虚构与非虚构之争最早应该追溯到电影的滥觞时代。在电影诞生初期,就出现了以卢米埃尔兄弟为代表的“对现实进行再现”,和以乔治·梅里埃为代表的“对现实进行表现”两种不同倾向。
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咖啡厅里放映了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工厂大门》,电影艺术从此诞生。在卢米埃尔兄弟对电影的早期实践中,他们招募摄影师,到世界各地拍摄了大量新闻片、旅行片,这些影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现实进行描摹”,通过固定的单镜头拍摄对现实生活场景进行还原,纪录眼前的景象。
早期创作者乔治·梅里埃在电影拍摄实践中却走向了与卢米埃尔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卢米埃尔兄弟的影片是纪实的,无意将电影发展成为一种叙事艺术。但梅里埃却认为影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非虚构”的纪实工具,而且也是可以借助“虚构”的戏剧化方式进行电影叙事的新型艺术载体。他通过“停机再拍”、“二次曝光”等摄影特技获得艺术特效,强调主观表达,并通过对早期蒙太奇的探索,开拓影片的叙事功能。与卢米埃尔的纪实题材不同,梅里埃关注幻想题材,拍摄了大量的魔术片、神话故事片、科幻片。
卢米埃尔兄弟开创的“对现实进行再现”和梅里埃开创的“对现实进行表现”是电影两种不同表现手段的源头。前者力求还原生活的表象,强调未经处理过的客观真实;后者则注重表现对现实的主观体验,关注内心现实。在后续的发展中,偏向“再现”的电影越来越追求自然、强调作者的自我隐没,避免主观处理;而偏向“表现”的电影则不断探索对现实素材做个性化的处理。但是这两种风格倾向并非前者是纪录片,后者是剧情片,而只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在电影艺术的发展中同时存在于纪录片和剧情片之中。
(二)虚构与纪实的此消彼长:纪录电影的风格流变
1920年代,约翰·格里尔逊第一次提出“纪录片”这个名字,同时将其定义为“对现实进行创造性的处理”,纪录片从此独立成形。在电影滥觞时期的这两种传统之下,纪录电影发展出了两种极端:一种是对现实的临摹,一种是对现实的安排。纪录电影史便在这两个极点之间形成和演变。[5]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传统同时存在,此消彼长。
1.20世纪20年代:虚构与纪实混沌共存
20世纪20年代,纪录片创作呈现虚构与纪实混沌融合的状态。格里尔逊的定义确立了“真实”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对于如何抵达真实的手段,这一时期并未作出特别限定,虚构和纪实共同存在于早期纪录片的表达之中。
“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北方的纳努克》的创作实践被认为是“对现实进行描摹”,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中看到虚构的作用。首先,《北方的纳努克》借助了虚构搬演的方法来展现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影片拍摄时期,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已经受到了现代文明的侵蚀,为了还原古老文明,拍摄过程中弗拉哈迪必须排除现代文明的干扰,这就意味着卢米埃尔式完全不经处理的临摹是难以完成的。弗拉哈迪最终选择让纳努克一家搬演当年祖先们的生活方式,片中在冰天雪地捕杀海象、建造冰屋等场景都是人为搬演的,展示了“未受现代文明污染和腐化的纯洁的野蛮人”形象。其次,《北方的纳努克》虚构手法的运用还表现在叙事结构的主观建构上,尤其是通过机位调度、景别变换和后期剪辑,拍摄者不断改变观众的视点,将剧情片的叙事运用到纪录片中,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虽然《北方的纳努克》中弗拉哈迪将剧情片的虚构手法与表现真实场景的纪录片结合,但在搬演架构下呈现的事实核心却仍然是真实的。
作为20世纪20年代英国纪录电影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约翰·格里尔逊强调“对现实进行安排”,他“视电影为讲坛”,突出纪录片的宣教功能。他在作品《漂网渔船》和领导的英国纪录片运动都倡导“画面+解说+音乐”的“上帝之声”式的直接说教,影像完全被画外解说建构起来,配以音乐的烘托,这种操作具有明显的人为安排。
2.20世纪50—60年代:虚构与纪实界线明晰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美国“直接电影”和法国“真实电影”的提出,纪录片虚构与纪实的界线逐渐明晰。
“直接电影”是一种观察式的记录,强调冷静旁观生活的现象,利用同期声,不使用画外解说,无操纵式剪辑,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让其义自现。直接电影产生于二战后,传播的宣教功能逐渐淡化,电影界对格里尔逊直接说教的纪录片产生了质疑。同时,电影美学理论发展出现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倡导纪实美学。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德鲁小组提出“直接电影”的创作理念,质疑和反叛20世纪40年代以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格里尔逊传统,反对逻辑和说服力是由解说而非影像本身表达出来的,提倡在场“直觉的感性”。梅索斯兄弟和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在德鲁的创作理念基础上,开展直接电影的创作实践,拍摄了《推销员》《芭蕾》等一批直接电影。在他们的影片中,为了将主观参与降到最小,他们很少与被摄主体交谈,决不操纵剪辑,也不可以营造画面,力图呈现生活的本真。
与此同时,在1960年代的法国,在法国新浪潮运动和吉加·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的共同影响下,出现了以让·鲁什为代表的“真实电影”。真实电影与直接电影一样,反对格里尔逊“上帝之声”式的宣教操纵。但对于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二者却存在分歧。与“直接电影”的冷峻观察不同,“真实电影”是一种参与式的记录,延续维尔托夫的理念,主张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互动,并在互动中展现被拍摄者的内心现实,以折射出深刻的社会真实现象。直接电影力图排除摄影机、隐没拍摄者;而真实电影不但承认摄影机的影响,而且把它当作启发内心真实的重要手段。在让·鲁什的《夏日纪事》中,拍摄者走上街头,对行人随机提问“你幸福吗”,通过问答的互动,被拍摄对象往往给出个性化、难以预测的答案,这样观众在摄影机的带领下,走进了被摄主体的内心世界。真实电影超越了直接电影呈现的表层真实,通过作者介入,引导观众一起进入更深层的真实。
通过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对纪实美学的提倡和发展,格里尔逊传统中预先准备的脚本、画外音和配乐被认为是对真实的抹煞。至此,20世纪40年代以前虚构与纪实的混沌状态开始逐渐明晰,虚构和纪实走向分离。直接电影将纪实发展到了一个极端,他们认为漂亮的画面和清晰的声道都是对“真实”的一种美化,其实是走向了虚假和欺骗。他们认为在冷静观察中捕捉现实,比漂亮的形式更重要,在拍摄实践中十分反感画外音,没有声源的音乐被排斥在外。他们拍摄的影片片比较低,为了抓拍现实,画面晃动模糊,忽明忽暗,声音噪杂不均匀……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对格里尔逊风格的反对和对纪实风格的提倡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从此以后,“非虚构电影”在众多情境下成了纪录电影的代名词。
3.20世纪80—90年代,纪实与虚构复归融合
20世纪80—90年代,纪录片创作逐渐脱离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的纪实风格,进入了纪实与虚构复归融合的“新虚构时代”。与纪录片诞生初期对虚构搬演的采用不同,20世纪上半叶的“虚构”是一种无意识、被动不自觉的虚构,而这一时期的“虚构”,是有意识、主动积极的虚构。
这一时期的历史环境进一步影响了纪录片理论和创作实践。一方面,科技进步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使得人们开始质疑“真实”。另一方面,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在倡导纪实风格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甚至连“直接电影大将彭尼贝克都说直接电影过于依赖所谓的‘美妙瞬间’,造成许多无谓的浪费与沉闷枯燥。”[6]创作者发现许多关键场景,按照直接电影的限定,一旦错过就无法弥补,纪实风格的限制最终损失了“真实”。同时,将纪录片定义为“非虚构的电影”,概念上的限制逐渐成为纪录片探索的桎梏。结果,这一时期的纪录片越来越小众化,从二十年代弗拉哈迪的票房大卖变成五六十年代逐渐被影院拒绝,到七八十年代进入发展迟缓期。纪录电影史学家埃里克·巴尔诺在《世界纪录电影史》里用“缓慢的运动”概括这一时期的纪录电影,并指出导致前进迟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常常被指责是有“倾向性”的,纪录片的拍摄者不断被嘱咐要“客观”,但是这种嘱咐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哪部纪录片是无倾向的,拍摄中总是面临无穷无尽的选择,不管承不承认,每一种选择其实都带有主观动机。[7]“非虚构”限制了纪录片的发展,促使电影人对什么是纪录片开始了新的思索。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理论界的讨论中开始出现淡化叙事电影和纪录电影界限的倾向。创作实践中,纪录片导演也逐渐尝试突破纪录片非虚构的边界。1987年,埃洛尔·莫里斯拍摄犯罪纪录片《细细的蓝线》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这部作品是对直接电影的反叛,影片“有意识的人为化”,对犯罪过程进行故事片一般的搬演,在剪辑上慢镜头的使用、对特写的突出、强调镜头组接的节奏感,不断重复的主题音乐……在影片的结构上,完全按照作者意识进行建构,运用“罗生门式”的方法,通过各种人物的辩词展开一种推理的真实,对谁是真凶具有强烈的自我判断和主观倾向。莫里斯认为:“直接电影的总体思路对电影制作造成了极大损害,对纪录片制作的危害尤其突出,因为它鼓吹了这种虚假的、形而上学的说法:即风格保障真实。”[8]同样采用虚构风格的还有克罗德·朗兹曼的纪录片《浩劫》,这部关于希特勒种族屠杀的影片需要大量回顾历史,而朗兹曼没有选择将犹太人大屠杀的影像资料进行简单堆积,而是通过对经历者的采访重新“再现”历史。朗兹曼认为:“不存在只是简单地复制时间或呆板地记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纯粹纪录片,为了讲述真实,绝对需要创造,需要将时间复活。”[9]他毫不避讳地将自己的手法称作“现实的虚构”,并认为“这种虚构是富有创造性的,显示了非凡的威力,将现实与想象的边界完全融为一体”[10]。
基于对这种创作实践的分析,1993年,美国学者林达·威廉姆斯提出了“新纪录电影理论”,肯定纪录片中的虚构手法,认为“纪录片不是故事片,也不应该混同于故事片,但纪录片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揭示真实”[11]。与格里尔逊的虚构不同,后者目的是政论宣教,而威廉姆斯倡导的虚构是对深度现实的挖掘。他认为:“对真实和虚构采取过分简单化的两分法,是我们在思考纪录电影真是问题时遇到的根本困难。选择不是在两个完全分离的关于真实和虚构的体制之间进行,而是存在于为接近相对真实所采取的虚构策略中。”[12]
通过梳理世界纪录电影的演进脉络可以发现,纪录片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超越既有形式的历史,纪录片工作者的“兴趣和热情在于不断打破电影的原有限制,发现新的可能性和未尝试的制作形式”,纪实与虚构两种手法的融合使用给纪录片本身不断注入发展的活力。
二、中国纪录片创作实践
从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实践来看,尽管略微滞后于世界纪录电影的发展,但同样经历了“虚构——非虚构——再虚构”的演进过程。
(一)1905—1991年:混杂纪实复现与虚构表意
1905至1991年的新闻纪录电影时期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都采用格里尔逊的“画面+解说+音乐”的固定模式,强调解说词的宣教功能,压制了影像的表意功能,既有主观化的虚构表意,又有纪实复现。
1.改革开放以前:形象化的政论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建国初期的中国纪录电影受苏联模式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国情影响,强调纪录片的新闻性、宣传性,认为“电影是形象化的政论”,采用“画面+解说+音乐”的固定模式。1953年成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将办厂方针确立为“形象化的党报”,强调政治利益,形成了“新闻简报”风格。
2.改革开放以后到1991年:专题片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政治思潮涌动活跃,20世纪80年代,随着《话说长江》等的热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专题片”。虽然与改革开放前的政论片相比,弱化宣传性,强调文艺性。但是,从纪录片的表现手法上,仍然继承了“画面+解说+音乐”的模式,画面被解说和音乐操纵,影像的纪录功能被轻视。在《话说长江》中树立了陈铎、虹云两位主持人,画面内容完全被两位主持人朗诵的解说词建构。
(二)1991—1995年:转向纪实风格
1991—1995年是纪实风格的转向时期,这种转向一是源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的纪实美学随电影译著引入中国,与中国30年代就有的现实主义传统一同影响了这一时期纪录电影的发展。再加上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电视业出现重大转变,电视语态从俯视变为平视,从宣传变为新闻。《东方时空》开播的“生活空间”(后改版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栏目化的纪录片样态,强调关注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题材。在内外双重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纪录电影抛弃虚构,转向纪实。
这种转变的开端是1988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合作拍摄的纪录片《望长城》,该片一反新闻纪录电影时期宣教、政论的风格,接受西方纪实风格,强调现场同期声、镜头跟拍和创作者主体意识的淡化,一时间掀起了中国纪录电影的纪实风潮:反对虚构手法和主体意识,强调纯客观,甚至无解说、无音乐、无剪辑的极致自然。这种纪实美学打破了“画面+解说+音乐”的固定模式,实现了纪实的复归,并将客观独立、冷静呈现等观念引入中国纪录片创作实践。
但纪实风格的发展出现了单一化、绝对化倾向,过度强调纪实风格,把虚构表意等同为虚假,摒弃剪辑、音乐和解说词,不顾画面质量,甚至发展为弱化叙事。纪实风格的引入本来是为了突破宣教模式的禁锢,但最后这种对禁锢的突破反过来却变成了一种新的禁锢,造成了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纪录片形式粗糙单一、内容边缘化、缺乏观众意识等弊端。“那个时候一想起纪录片,大家想到的就是对一个人的跟踪,镜头摇晃,节奏缓慢,大段的长镜头,大段不紧不慢的访谈或对话,解说词声调不高,冷静而有距离。”[13]观众心目中关于纪录片“黑乎乎、摇晃晃、不好看的”的刻板印象,成为1995年、1996年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低迷的重要原因。
(三)1995年以后:虚构的策略化运用
1995年以后,中国纪录片创作进入了多元化探索时期。虚构作为一种叙事策略重新被关注。
如同纪实风格是受到国外影响发生转变一样,中国纪录片的“再虚构”很大程度也是西方经验引进的结果。一方面“新纪录电影”理念传入中国,引发了关于纪录片“真实”的新探讨。另一方面,以1995年《故宫》为代表的一批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与探索频道、BBC合作,国外纪录频道的商业化运作手段和重视市场的创作理念正好与当时我国影视产业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契合。随着对收视率的逐渐重视,需要把纪录片拍得好看,让纪录片讲故事,借助虚构手段的新纪录片逐渐突破原有的纪实边界。演员扮演、情境再现、三维动画等虚构手法被大量用于纪录片创作,传统纪录片的非虚构边界逐渐被打破。《圆明园》中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现场重构,以历史图片资料为模版,利用CG技术重新生成建构了三维动态的圆明园的“真实”场景,在93分钟的影片中数字特技生成的画面达35分钟。《大唐西游记》被称为“手绘动画纪录片”,在210分钟的总时长当中,手绘特效画面占到了120分钟之多。[14]《敦煌》为了将零散破碎的历史汇聚,保持叙事的完整性,虚构了一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舞伎“程佛儿”作为线索串联叙事。《迷徒》邀请《潜伏》《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专业演员扮演郑蕴侠,进行剧情化的叙事处理。《英与白》和《幼儿园》引入主观干预,表现表层真实下的内心现实。通过对现实生活冷静的记录、某一角度的观察以及后期的组织重构,透射出主体性思考,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三、反思电影史:纪录片的本质与表现手段
纪录片的本质是真实,而虚构和纪实都只是表现真实的手段。“真实”与“虚构和纪实”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真实”是本质层面,“虚构和纪实”是手段层面。
真实是纪录片的本质和生命。英国纪录片学派创始人约翰·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可见真实性是纪录片区别于剧情片的核心特质。但是,什么是真实?纪实不等于真实。手段纪实不一定能反映本质真实,一些深度真实也无法用纪实手段反映。
真实不是仅仅对现实进行客观的映照式表达。绝对的客观真实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即便是在“真实电影”的全盛时期,也无法做到“绝对真实”。这是因为“真实”在从创作到放映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多重选择和假定。导演从生活的原始现实真实中提取素材,完成了第一次选择。其选择过程必然受到创作者的主观理念的影响。在创作过程中,除导演的选择之外,真实还会经过摄影、剪辑的选择加工,这是第二重选择。在传播过程中,观众受个人、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进行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理解,是第三重选择。因此,认为把纪实手段发挥到极致就一定比虚构手段更能还原真实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就算“直接电影”真的做到反映“绝对真实”也只是浅层的真实,而不是完全的真实。因为真实具有多层次性。纪录片的真实不是哲学上的客观真实,而是经历了多重选择加工的真实,是心理意义的真实。“从心理层面看,真实是一种被生活经验认同的心理感受,即真实感,只要符合观众的生活经验,那么这就是真实的。”[15]
如果将真实的层次细分为当下的表层真实、历史真实和心理真实,会发现被认为是“真实”代名词的“纪实”手法,在呼唤“真实”强调不做主观化处理的时候,其实恰恰丧失了“真实”。纪实手法在表现真实上出现了断点,这是纪录电影引入虚构手法的根本原因。“真实电影”以捕捉眼前正在发生的现实为宗旨,缺乏历史的参照和深度。纪录现实不等于表现真实,捕捉事物的现象不等于揭示事物的本质,捕捉到了局部真实不等于抓住了总体真实。[16]因此,在表现历史真实和心理真实时,需要将虚构手法纳入其中。首先,在历史类纪录片中,为了接续历史,弥合因不在场而造成的时空断点,需要引入情景再现、场景搬演、人物扮演等虚构手段,西方电影史上,《浩劫》中对已经发生的大屠杀历史的重新排演,中国电影史上,《圆明园》中的情境再现和使用专业演员扮演郎世宁就属于用虚构展现历史真实。第二,在文化思辨类纪录片中,为了弥合抽象的思维断点,需要创作者主观对思辨推理过程进行重构,采用主观设问、情景重现、虚构搬演等虚构手段。例如《细细的蓝线》采用“罗生门”式的表现手法,《科伦拜恩的保龄》用作者判断重构现实,通过影像推理,得出校园枪击案背后的真实原因。第三,在心理情绪类纪录片中,导演怀有无法直接拍摄到的主观感受,于是选择、摄取有承载能力的现实影像,经过局部安排、后期重构表现自己的情绪,弥合了主体感受的断点,[17]如张以庆的《英与白》通过对影像的后期重构,表现无法言说的孤独和绝望的等待。
通过对纪录电影发展史的梳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虚构手段的目的是为了接续纪实手法无法弥合的影像叙事断点,采用事件搬演、演员扮演、情境重现等虚构手段拍摄的纪录片,与采用“墙上苍蝇”式冷静如铁的纪实手法直接呈现的纪录片一样,都是抵达真实的手段。
四、结语:纪录电影,一个开放的概念
纵观中外纪录片发展历史可以得出三个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
首先,真实是纪录片追求的本质属性,纪实和虚构是抵达真实的两种不同手段。从纪录片诞生之日起,它的表现手段就不是只有纪实一种的。美国学者托马斯在描述“虚构”这条线索在纪录片中的发展时说:“纪实和虚构是相互渗透相互转移的,用重构的手法或戏剧的描述表现真实事件的观念和电影本身一样古老。”[18]虚构在纪录片的发展演进中,从未被排除在外。从弗拉哈迪的搬演到格里尔逊的人为打造,从真实电影的主观参与再到新纪录电影用虚构方式表现深度真实,虚构与纪实经历了混沌融合到逐渐分离,再到复归融合的过程。“伴随着纪录片对‘真实’内涵属性的追索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发展,在艺术实现手段上则表现出由纪录摹写到重构扮演等虚构策略的不断加强,纪录片在向更深层面对真实进行追索探询的过程中,其手段呈现的却是向虚构的不断拓展。”[19]
其次,理论是为实践在做着注解。纪录片创作是一个开放的实践,纪录片的理论定义也是随着时间不断发展。手段为目的服务,为了探寻多层次的更完整的真实,纪录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边界不断扩展,甚至可以说随着纪实与虚构手段的融合,纪录片与剧情片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纪实和虚构,作为手法,同时适用于纪录片和剧情片。故事片《人咬狗》、《女巫布莱尔》是在虚构内容中渗入非虚构元素;而近十年出现的《敦煌》、《故宫》等新纪录片则是在非虚构类内容中渗入虚构元素。正如单万里在《纪录电影文献》序言中写道的那样:“不论纪录片还是故事片都有一个共同名字,那就是‘电影’。纪录与虚构分别代表着电影的两个极点,已往人们过分强调一分为二的作用,却忽略了‘合二为一’的功能。纪录与虚构,如同分别朝着地球的南北极航行的两艘航船,在达到极点之后开始贯通两极,朝着各自方向演进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开始出现合流的趋势。”[20]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研究纪录片发展史,讨论纪录片的本质定义和边界问题,都是为了给当代创作提供经验的参考,为当代问题提供历史的解答。如果陷入概念的桎梏,被人为建构的理论束缚实践的创造力,就会出现打破束缚的突破反过来成了新的束缚。借用美国纪录片研究学者比尔·尼克尔斯在《纪录片导论》的一句话:“与为纪录片或者非纪录片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适当定义的努力相比,我们更亟需要做的事情是:观察纪录片发展与演进过程中实验和创新的实例。”[21]突破既有框架是电影艺术创新发展和产业差异化竞争的必然要求,从既有束缚中解放出来会发现虚构,同纪实一样,是抵达真实的一种手段。通过虚构与纪实的融合,纪录片与剧情片的边界将趋于模糊,而影像的力量却会不断增强。
标签:纪录片论文; 电影史论文; 北方的纳努克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真实电影论文; 纪录电影论文; 法国电影论文; 艺术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