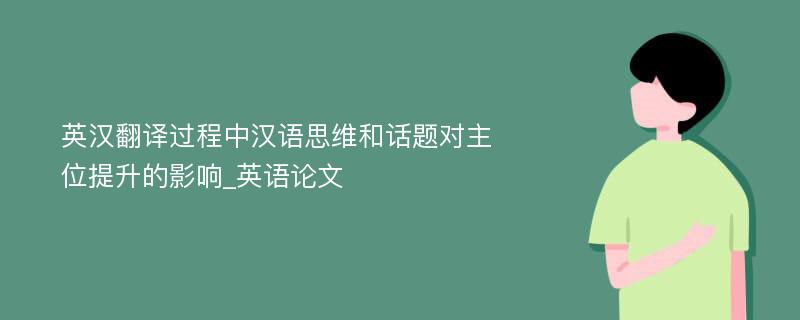
汉语思维与话题对英汉互译过程中主位推进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英汉论文,过程中论文,思维论文,互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英语是一种注重主语(subject-prominent)的语言,它的基本形式构架是主谓一致。在通常情况下,除标记性主位以外,在Halliday的语篇分析模型中,主、述位和主谓结构具有极高的相关性,主位和述位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语法中主语和谓语间的区别相同(Baker,1992:123)。可见,英语的主位大部分情况下和主语重合。但作为信息起始点,主位并不一定涉及话题。
汉语传统的语法受西方语法的影响,认为汉语属于主谓结构的语言。但最近几十年来,语言学家提出了不同看法。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Chao,1968:69)指出:“汉语句子中主语和谓语的语法意义是主题(topic)和述题(comment),而不是动作者(actor)和动作(action)。”Charles N.Li和S.A.Thompson在其著作Subject and Topic一书中提出,英语属于注重主语(简称SP)的语言,而汉语则属于注重主题(简称TP)的语言,也是话题(也称为主题)突出(topic-prominent)的语言。申小龙(1990:223)提出了汉语中普遍存在的主题一评论句的概念,即“先提出我们想要说明的一个话题,它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词组,甚至是一个句子的形式,总之是一个要说明的‘板块’,然后对这个话题加以评论”。汉语的主语和谓语不一定具有英语中那种严格的形式关系。汉语中不具备明确的形式结构特征,只以意合形式组合在一起,以话题为中心辅以评论的小句大量存在。汉语中既有与英语相近的主语+谓语,也有不同于英语的话题+评论。正如Baker(1992:139)所提出的,对于译者来说,除了要知晓某一特定主、述位结构在源语和目的语中不同的标记强度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利用目的语中的现有结构资源恰如其分地对源语语序进行转换,使其具有和在源语中类似的表达效果和功能。刘宓庆教授(1999:6,14)也指出:“所谓翻译的实质,就是语际意义转换”,“翻译时应摆脱形式约束,实行变通,双语转换才有可能……”换句话说,在英汉翻译中,要处理好两种语言间的主位、述位转换问题,就是要处理好英汉两种语言中主语+谓语和话题+评论的适当转换问题。
在主题突出的语言里,一个子句的话题总是位于句首,这与Halliday模式的主位是一致的。如果句首是为主位保留的,话题总是位于句首的,主位与话题就是同一件事Baker(1992:142),翻译也就比较简单了,只要把原文的主位转换为话题。Baker(1992:144)认为:“还没有人论述在注重主题语言里的主位与主题的关系。”不管她的这一个观点是否正确(事实上,有些学者如彭维宣(2000)、向明友(1997)已有论著和论文),至少可以说明这是个研究领域。我们这里关心的是英语原文里的主位推进结构是否能完全在译文里体现出来。如果不能,是什么因素引起这种错位?在一般情况下,英语严格地遵循SV结构的要求,而汉语遵循主题—评论的结构。汉语主题前置处于主位位置是普遍的语言现象,相当一部分是无标记的。要注意源语和目的语在这方面的特点,不可呆板地用目的语主位、述位结构套源语的主位、述位结构,过分追求形式的对等。对原文和译文的语言结构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帮助译者进一步了解不同的语言对相同事物的表达方式,从而译出合适的译文。由于汉语是话题突出的语言,往往需要在译文中重新安排主位,确立话题,实现英汉语言等效转换。
汉语小句中的主位衔接功能则不如英语明显。主题常常只是为小句设立一种叙述的框架(Chafe,1976:51)。对于印欧语系的语言来讲,或许可以直接套用有关理论模式对某一语言的主位结构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规律进行观察和对比。不同语系间的差异较大时,英语的主位推进模式在译文中不能表现出来。Baker(1992:127)注意到英语的主位推进模式在阿拉伯译文里不能体现出来,一个原因就是阿拉伯语里很少用独立的代词,阿拉伯语里的动词本身包含人、单复数和性别,因此,一个英语语篇的主位是人或人称代词,而在阿拉伯语的译文中是动词变成主位。
语篇分析中将句子按其线性顺序切分为主位(theme,T)和述位(rheme,R)两部分。主位一般只含有已知信息(given information),述位往往是新信息(new information),是交际的重心所在。在语篇中,主位、述位层层推进形成主位推进模式(thematic progression)。国内外语言学家曾提出较多的模式,胡壮麟(1994:144)对它们进行了概括,认为有最基本的三种模式:(1)Tl—T2,第一句的主位继续成为第二句的主位;(2)R1—T2,前句述位的某个内容发展成为第二句的主位;(3)T1+R1=T2,第一句主位和述位的内容一起产生下一句的主位。下面我们将讨论英语句子中主位、述位的结构转换为主题—评论的结构。例如:
(1)Studies/serve for delight,for ornament,for ability.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is in privateness; for ornament,/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is in the 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第一句由主位和带有三个信息点的述位构成。第一句里三个述位中的信息点分别担任第二句话中的已知信息,即主位,从而引出三个实际上并列的新主位—述位结构,是上述第二种模式,其译文亦是如此。王佐良先生的译文为: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译文十分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信息结构。也就是说,主位、述位结构(用/划分)一致,主位与汉语的话题对等一致,译文衔接紧密,语义连贯。
英语主位也可与译文主位不一致。认知是语言表达的基础,由于汉民族与英民族的思维有同也有异,思维体现在语言上,体现在汉语分句和句群的话题与英语相比有同也有异。例如,汉语语序中时序象似度与英语相比要高些,这样英汉两种语序或主位就可能不对应。例如:
(2)I shall answer his letter/when I have a moment to spare.
译文:有空/我就给他回信。
英语原文一般译成汉语中自然的时间顺序。
下面我们准备从汉语思维几个方面与汉语话题推进模式讨论翻译时主位推进模式的转换。
二、汉语流散型句段与多话题句
(3)Once a group of Chinese was visiting the home of an American.As they were shown around the house,they commented,"You have a very nice home.It' s so beautiful." The hostess smiled with obvious pleasure and replied in good American fashion "Thank you",which caused surprise among some of her Chinese guests.
译文:有一次,几个中国人到一位美国人家里去作客。主人引他们参观自己的住所。中国客人说:“你们的房子多好啊。真漂亮。”主人听了十分高兴,按美国习惯笑着回答“谢谢”。有些中国客人对她的回答感到意外。
这段英文与汉语来自《语言与文化》,其中一位作者邓炎昌教授生于美国,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回到中国,另一作者是著名语言学家刘润清。书的前半部分用很地道的英语写成,后半部分为汉语。如果比较英语与汉语对应的句子,可以了解汉英句子表达方面的异同。这段英文第一句主语为a group of Chinese,第二句主语they,前后两句主语保持一致,用they来衔接。而汉语第一句主语是“几个中国人”,第二句主语“主人”,也就是说,第二句主语与英文主语不一致。另外,英语句中的which caused surprise among some of her Chinese guests对应的汉语句子主语为“有些中国客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语语篇呈典型的直线性,语篇信息有序地相互衔接着,每个句子的内容顺其自然地过渡到下一个句子,主位推进构成信息延伸与传递的途径。这段英文的第二句重复前句的主位,即第一句的主位继续成为第二句的主位,可用T1—T2表示,是第一种基本模式。句子中的which可看作是T2,前句中的主位和述语内容一起产生一个新的主位,即T1+R1—T2。而译成汉语时,由于语言结构不同,汉语突出人,各个小句的主题交替使用“中国客人”和“主人”,他们是这个语段的中心人物,出现的频率大于英文里的主位,构成这段的话题(彭宣维,2000:56),形成平行相关的主题。下面我们把英语的主位推进模式与汉语的主题推进模式分别列出,可以更加看出它们的差异。
英语:T1—Rl,T2(=T1)—R2,T3(=R1)—R3,T4(=T3+R3)—R4
汉语:t1—c1,t2——c2,t3(=t1)—c3,t4(=t2)—c4,t5(=t1)—c5(t=话题,c=评论)
在组织语段方面,汉语的语段呈现流散型,而英语则呈现聚集型。中国文化往往表现为一种心理视点动态延展的时间型构造。例如,中国画的构图从不把视点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而是采用移动透视的表现手法。《清明上河图》中的拱桥一段即是采用了这样的动态构图法,既画桥上,又画桥下,既画屋内,又画屋外,内容异常丰富。这种可以使人“步步走、面面观”的移动透视法也同样反映在汉语的语段组织方面,即语段流散型铺排而体现动态延展的特性。例如:
(4)A peasant and his family were working in a little field beneath the singing larks.The father,the mother,and four children were there putting fresh earth around sprouting potato stalks.They were very happy.It was a good thing to work there in the little field beneath the singing larks.(The Letters of Liam O'Flaherty)
译文:有个农民一家人正在一小块地里干活,头顶上就有云雀在歌唱。地里有父亲、母亲和四个孩子。他们在往绽出新芽的土豆秧周围培上新土。他们十分愉快。()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倾听顶上云雀的歌唱,真是乐在其中。(马义禄译)
可以看出,在英语语段里,保持a peasant and his family在各句中的主位和主语位置,是一种平行展开的主位模式,即T1(划线部分)—R1,T1—R2,T1—R3。而汉语语段呈流散型铺排。译文第一小句“有个农民一家人”与英文中的主位一致,但第二小句及第二句的主位是“头顶上”和“地里”,这是两个新话题,表明叙述的视角有所变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空间图景,第三句的主位回到“他们”,而第四句的主位也是“他们”,但是原句的主位却是it。显然,译者如果用原文的主位推进组织译文,就会遇到一定的难度。事实上,汉语中常常有这种流散型的句段。例如:
(5)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约是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檐下一个小铺盖。她仍然头上扎上白头绳,()白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朝花夕拾》)
实际上,用汉语话题结构解释比较容易,这是以地点话题组织的句子(堂前一桌上一檐下)。整段内容围绕话题“她”展开,每个短句的主位除了两次为“她”外,主题变化比较频繁。我们可以通过对比译文看出两种语言思维的差异,译文始终以she为主位,也就是用篇章的主要参与者组织句子,而汉语里地点的主位处理为状语,处于句末。
译文:But one autumn,after two New Years had passed since this good news of Xianglin's Wife,she once more crossed the threshold of my uncle's house,placing her round bulb -shaped basket on the table and her small bedding-roll under the eaves.As before,she had a whit mourning band round her hair and was wearing a black skirt,blue jacket,and pale green do dice.…(杨宪益、戴乃迭译)
三、整体性思维与话题和主位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汉语的语序就是例证之一,操汉语的人习惯上先提整体后提部分。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要注意话题与意义的连贯性。例如:
(6)填入下面横线上的两句话与上下文衔接最恰当的项是(1997年高考语文卷第8题):
泰山的南天门又叫三天门,创建于元代,至今已有六百余年________为“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阶崇万级俯临千嶂奇观。”
A.元代石刻“天门铭”在门外西侧,一副石刻对联在门的两旁,
B.门外西侧有元代石刻“天门铭”,门两旁有石刻对联一副,
C.元代石刻“天门铭”在门外西侧,门两旁有石刻对联一副,
D.门外西侧有元代石刻“天门铭”,一副石刻对联在门的两旁,
保持篇章结构的连贯性涉及到三个环节:话题、语序及语言运用。在一段语义连贯的话语中,各句之间都保持直线的联系,并尽可能始终围绕一个共同话题。就上述例子而言,不难看出其话题是介绍泰山南天门。比较所给的四个选项,只有B项能够始终保持话题不变。“南天门”与“门外”、“门两旁”遵守从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的顺序,因此保持了话题和意义的连贯性。而其他三项由于不恰当地改变了其中一个主语或两个主语,从而改变了话题,使语段变得不连贯。
(7)I paused to contemplate a tomb on which lay the effigy of a knight in complete armor.A large buckler was on one arm; the hands/were pressed together in supplication upon the breast; the face/was almost covered by the morion; the legs/were crossed in token of the warrior' s having been engaged in the holy war.
译文:我走到一座坟前,立住脚步深思起来。坟上躺卧着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雕像;他一臂挽盾,两手/一起紧按在胸前作祈祷状;脸孔/差不多全给头盔掩盖住了;两腿/交叉,表示此骑士曾经参加圣战。(夏济安译)
译文围绕着话题骑士雕像展开,“一臂”、“两手”、“脸孔”、“两腿”形成话题链,语序与原文并不相同。原文第一句述位中的complete armor与第二句的主位buckler可以看作是集与元素的关系(就像年year与February的关系一样)(徐盛桓,1996:24-27),第二句的a large buckler相对后面的述位是已知信息,因此第一句的述位complete armor成为第二句的主位a large buckler,即T1—R1,T2(=R1)—R2,而第二句中的述位arm又成为后面短句中的主位,因为arm与hands关系密切,是元素与元素的关系。原句是第二种线性推进模式T2(=R1)—R2。
如果译文亦步亦趋地改译为“盾挽在一臂”,就打破了汉语话题的一致连贯。译文的短句都是同一话题—评论结构,主位都是身体的一个部分,是已知的信息,句子推进模式为第一种模式T1—R1,与英文原句并不一致。英语句子似乎强调视线从一个部分自然地转向另一部分,而汉语语段强调整体与部分有序的排列,话题连贯。
(8)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削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这段话中心话题是祥林嫂的改变,从头发、脸色到神色、眼睛,由外到内,由宏观到微观,按顺序映出祥林嫂的变化。句子的顺序完全和作者的思维活动同步,也反映了汉民族话题统率的思维特点。作者为了使思路清晰可见,还特意使用了两个分号,标明表达的层次。接着从她的生活状况表现她的变化,一是随手带的碗,表明她已经无家可归,而且没有东西吃,二是使用的竹竿,层次清晰地介绍了祥林嫂生活的悲苦和贫穷。句子的组合顺序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是有路的。”请看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文:
Of all the people I had seen during this visit to Luzhen,none had changed so much as she had.Her hair,streaked with grey five years before,was now completely white,making her appear much older than one around forty.Her sallow,dark-tinged face that looked as if it had been carved out of wood was fearfully wasted and had lost the grief-stricken expression it had borne before.The only sign of life about her was the occasional flicker of her eyes.In one hand she had a bamboo basket containing a chipped,empty bowl; in the other,a bamboo pole,taller than herself,that was split at the bottom.She had clearly become a beggar pure and simple.
虽然译文没有保留原文的推进模式,但读起来很流畅。looked as if it had been carved out of wood…and had lost the grief-stricken expression已说明了她毫无生命的迹象,所以用the only sign of life about her衔接反而自然。原文都是同一话题—评论结构,主位都是身体的一个部分,强调整体与部分有序的排列,话题连贯。句子推进模式为第一种模式,而英译文与原文并不一致,似乎强调视线从一个部分自然地转向另一部分,是第二种线性推进T2(=R1)—R2。
四、以物或抽象概念作主语
习惯于本体思维的中国人在描述或记录动作或事件发生或演变的过程时,观察或叙述的视点往往落在动作的发出者,强调动作发出者的感受,并以其作为句子的主语,因此,汉语中主动语态使用频繁。而习惯于客体思维的西方人却常把观察或叙述的视点放在行为、动作的结果或承受者上,并以此作为句子的主语。汉语句子的主语话题通常是人或物,人类语言前置的倾向实际上反映了话题/主位(topic/theme)前置的倾向。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是一种人本文化,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汉语属于重主题的语言,讲话人首先想到具体的主题人(我、你、他或人们等),再说其所作所为。汉族人受传统的哲学思想影响,重视人的主体意识,因此主语位置上多为人,句子主位也往往是人,人常是话题。另外,汉语的一段话语中有用同一个主语(尤其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贯穿下来的习惯,是加强话语内部连贯的有力手段。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以自然为本位。西方哲学主张人物分立,主客分明,强调客观,重视理性。思维的目标往往指向外界,比较偏重于对客体的研究和观察,探索外部客观世界对人的影响,因而句子常以物或抽象概念作主语,强调主语物的重要性,强调事实,强调物对人的作用。英语中非人称的一切事物无论是具体的、抽象的、意念的、心理的,都可以用来作主语。无灵主语可以说是英语句式的闪光点。英译汉时常常不按照原文的主位、述位推进模式进行翻译,行文符合汉语的习惯。例如:
(9)An episode of humor or kindness/touches and amuses him here and there;
译文:他/不时地会碰上一两件事,()/或是幽默得逗人发笑,()/或是显得出人心忠厚的一面,()/使人感动。(杨必译)
以抽象事物作主语,在句子中也是主位,以人作宾语。汉语译文把这种主宾关系颠倒过来,以人作为主位,形成话题。
(10)秋宝一周纪念的时候,这家热闹地排了一天的酒筵,客人也到了三四十,有的送衣服,有的送面,有的送银制的狮子,给婴儿挂在胸前的,有的送镀金的寿星老头儿,给孩子钉在帽上的,许多礼物,都在客人底袖子里带来了。(《为奴隶的母亲》)
译文:On Qiu Bao's first birthday,the celebration lasted the whole day.About forty guests attended the party.The birthday presents they bought included baby's clothes,noodles,a silver pendant in the shape of lion's head to be worn on the baby's chest and a gold-plated image of the God of Longevity to be sewn on to the baby's bonnet.(张培基译)
在汉语语段里,观察或叙述的视点往往在动作的参与者或发出者,并且相互呼应(如“这家”、“客人”,而且“客人”与“有的”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译文则把视点主要放在与birthday相关的内容上,围绕birthday presents展开。在汉语的语义场周岁酒筵里,出现同一语段的词汇有“客人”、“礼物”,构成被激发的已知信息,在语段里是连贯的。About forty guests attended the party.中,旧信息(guests)+新信息(attended)+旧信息(the party),而the party相对于about forty guests是比较旧的信息,因为the party与前面的the celebration意思相同,作者认为改为The party were attended by about forty guests.更符合英语行文习惯,这样前面三句的主位基本相同,都不涉及人,能更加连贯些。
五、对偶性思维与话题对应
一般认为,英语主题结构中的主题均为有标记主题,而汉语的主题(或话题)相当一部分是无标记的(unmarked)(金积令,1991),但有的语言学者并不认同(许文龙,2004:64)。Baker(1992:134)认为,前置的宾语在汉语里比英语的标记性要小。例如:
(11)“We know what you have done,”(said Zhou En-lai).
译文:“您做过些什么,我们是知道的。”
这句话很简单,是周总理对一个外国专家讲的话,反映了周总理朴实的作风。如果译成“我们知道您的贡献”或者“我们知道您的功绩”,都显得过于花哨。如果译成“我们知道您做过些什么”,又显得过于平淡。周总理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很有分量,译文译得恰如其分,语气重心在“我们是知道的”。原文中的宾语“您做过些什么”(what you have done)成为话题,“我们是知道的”是评述,是信息焦点。话题“您做过些什么”位于句首,作为宾语它不在常位上,而且后面有个停顿,起到了强调作用。
(12)a.I admire his learning,but I despise his character.
b.His learning I admire,but his character I despise.
a,b所陈述的事实是相同的,但是语序却不一样。a是正常语序,其主题是对主语的态度作一般性的客观陈述,而b宾语前置于主位,强调宾语成分所包含的信息。句a既可以翻译成“我佩服他的学识,但鄙视他的人格。”也可以译为“他的学识,我佩服;他的人格,我鄙视。”而b只能是后面一种选择。由此可见,可以用话题对应结构,把宾语前置作为主位,话题的对比使信息突出,适度提升句子的语气。
中国古代把整个世界看作是阴阳二气交感运动的哲学思想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汉民族的生存方式,形成对偶性思维。这种母语思维的对偶性原则也非常深刻地影响了叙述文体和抒情文体。张今教授指出,汉语的一个特点就是四字结构。四字结构符合周易逻辑中的四象格局。周易逻辑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词语结构自然也不能不受到周易逻辑的阴阳模式和四象模式的深刻影响(张今,2005:182)。两个句子就是一个句群,两个阴阳就是一个四象,而四象是稳定的结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偶句符合四象格局。汉语的对偶、对仗句中是T1—R1,T2—R2模式。英语中也有这类句式,但数量很少,一般出现在antithesis修辞手法及一些谚语中,如Once bitten,twice shy.(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Man proposes,God dispose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
冯胜利(1992)曾从汉语构词学的角度论证了“韵律乃骈偶之母”、“奇偶乃汉语之魂”两个母语构词、构句的语言根源。启功也曾把骈偶看作是汉语的“基因”。他们的研究成果证明了汉语的表达优势在相当程度上与汉语和谐的语音、整齐对称的语感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偶式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借助整齐对称的形式、谐调匀称的音节,使意义相似、相对或相连的两个部分形式对照,让它们互相补充,互相映衬。对偶句或排比句在表面句法结构上具有比较强的粘连性(许余龙,2000:207)。句子本身是一种形合手段,帮助意义的凝集,令人读后感到意义鲜明,印象深刻。
(13)……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
译文:…and (the Chinese) advocated that "all nations live side by side in perfect harmony".The Chinese held that "one should be as inclusive as the ocean,which is vast because it admits hundreds of rivers" and called for drawing upon the strength of others.
“吸纳百家优长”与“兼集八方精义”是一个意思,也不必都译出,译文综合了两句的意思。
(14)Perhaps the reader,whom I cannot help .considering as my guest in the Old Manse and entitled to all courtesy in the way of sight-showing,….
译文:本文的读者,我应该待之以上宾之礼。古屋的一切,我应该尽量让他参观,……
译文的结构与原文很不相同,译者安排两个话题,形成话题对映,后面一句中的“我应该”与前面一句述题中的“我应该”相对应,是述题的反复使用。
(15)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nor long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A.Lincoln)
译文:a.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话,世人不会太注意,也不会长久记住;但勇士们曾经在这里创造的业绩,他们将永志不忘。
b.我们在这里说了些什么,世人将不大注意,也不会长久记住;但勇士们在这里做了些什么,他们将永志不忘。(田乃钊译)
这两个译文是话题—评述结构,划线部分是话题对比,使信息突出,“今天”与“曾经”、“我们”与“勇士们”形成对比。而述语部分是意义对比。宾语不在原来的位置上,而是放在句首作为主位,形成一种强调。b中划线部分的话题比a的划线部分更加自然、有力。虽然上面的译文符合四象格局,但还不是对偶,如果把它们修改一下,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c.我们在这里说了些什么,世人将不大注意,也不会长久记住;但勇士们在这里做了些什么,他们将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汉语的音韵美和节奏美缘于它的工整和对仗。两个意思相近的词经常并列使用,如“小心谨慎”、“正直诚实”、“生动有趣”、“阴谋诡计”。这种对称结构含有冗余的成分,形成显性重复,极富感染力。c中的“铭记在心”与“永志不忘”就是同义反复。再看一些译文:
d.我们在这里说些什么,世人不会注意,也不会长期记住,但是英雄们的行动却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英语世界》1984年第1期)
e.世人不会太注意,也不会长久记住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话,但他们将永远记住勇士们曾经在这里创造的业绩。
f.全世界将很少注意到、也不会长期地记起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但全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张培基译)
g.世界人不太会注意、也不会长久纪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但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做的事。(许渊冲译)
这几个译文的感染力远不如译文c。
六、结语
事实上,汉语中的句群、语段都有一个总的主题成分,可将一些看似松散的小句或句子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从而达到“形散而神不散”(形式松散而语义关系紧密)的组织效果。这正是曹逢甫(1997)所说的,汉语是语段取向的语言,而英语等欧洲语言是句子取向的语言。Chafe(1976:50)在分析了一些汉语话题结构句及其英语译文后得出结论:Chinese seems to express the information in these cases in a way that does not coincide with anything available in English.In other words,there is no packaging device in English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Chinese topic device,and hence no fully adequate translation.
翻译的过程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同时也涉及不同文化与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我们从英汉语言中主位和话题之间的联系和转换的必要性中就可以看出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及语言人群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异。这种相应小句结构的不对等以及英汉语言所暗含的思维方式的异同决定了译者在翻译中必须依据具体需要以及原文表达的语言力度和特定的语篇功能进行适当的结构调整,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提高其可接受性。本文只对英汉互译中主位和主题的关系和转换进行尝试性的探讨,通过原文和译文间的比较可以发现,英语和汉语主位之间的关系和常用语言结构并非完全一致,译者不能拘泥于原文的小句和篇章结构来生搬硬套,而要依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行文规范来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