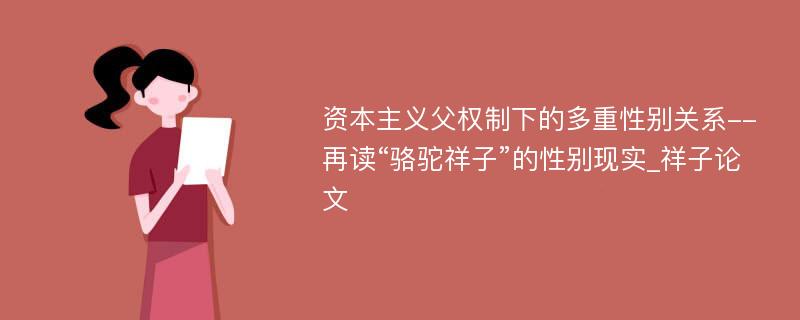
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多重性别关系——重读《骆驼祥子》的性别化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父权制论文,性别论文,资本主义论文,骆驼论文,祥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论:反观《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
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比较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页5-6)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页222)①
《骆驼祥子》(以下简称《祥子》)的叙事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正式浮现出来,对祥子做了上述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祥子》的批评,多数把这两部分当作《祥子》意指化的有力证据,以便对《祥子》中的“再现”进行现实主义的解读:北平的洋车夫祥子试图以个人的力气和精神对付社会的重重矛盾而逐渐跌落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生,这体现了在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的混乱中个人主义话语对平凡民众所拥有的吸引力和陷阱;而历时地看,《祥子》的再现成功地继承着“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所着力的国民性批判,北平和祥子之间的否定性互动就象征着现代中国及其子民之间的普遍结构。
可是,鉴于《祥子》最终没有完成的意指化过程,笔者认为,上述的现实主义解读策略应该是处理《祥子》这一文本的初步印象,或者至多是接近它的一个切入点,而不该是一个终点。否则,这种批评不能回避专用《祥子》来把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的特殊性和延续性正当化的嫌疑。以现实主义为名的上述批评中最可疑的地方之一,也是笔者通过本论文要介入的地方在于,把《祥子》一书还原为由一位(男性)主人翁祥子及其社会环境所组成的二元对立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只有祥子获得主体的位置,与之相对的社会环境往往被认为是作为国家单位的中国。由此而生的“祥子对中国”这个定式中,“祥子”和“中国”这两项几乎压倒了这一文本中值得深思的诸多脉络,尤其是依靠男性个体与他的国家关系的观点就无从把握男性和女性之间真正社会性的多种生活层面。
尽管有如此的偏向和制约,这种读解模式到今天还在广泛流传。其重要的原因确实是,它既是在这篇小说里主导叙事的一位叙事者所明确指出的解读方向,也符合于作家老舍所承认的创作意图。②在这种读解中不假反省地被再生产的是,将作品里的叙事者看成作家的文学性替身,并将作家当作作品意义的来源的传统读法。另外一个有力原因可以说来自“文本内部”,即《祥子》的叙事者利用自由间接引语的方法,着力把祥子的内心变化为客观世界的声音不断地讲给读者听,③以鼓励读者把《祥子》的现实理解为祥子一人的现实。
还有第三个原因是,对《祥子》的读解和批评向来不得不受到对《狂人日记》或《阿Q正传》等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批评规范的影响。的确,《祥子》与这些“长辈”文本形成紧密的关系网,使相互间的文学史意义更加丰富。可需要注意的是,祥子在《祥子》里的分量和作用不能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或《阿Q正传》里的阿Q等同起来,因为与这些先行文本相比,《祥子》这一文本所包含的意指化线索,往一个特殊的方向发展得更多,分化得更细致。比如,将《阿Q正传》(英文题目为“The True Story of Ah Q”)解读为围绕阿Q及其环境的叙事是相当恰当的,因为《阿Q正传》中的人物们,虽然开始时仿佛代表了各个说话位置,却很快融合成一个整体性环境,压迫得阿Q临死也难以抗拒。但在《祥子》里,除了祥子以外,却至少有两个人物跟他一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并且始终跟他解除不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距离和隔膜。
“她们”就是虎妞和小福子。她们各自出于对女性身份相似而有别的自觉,或者说出于对自己作为女性所处的各自不同的社会位置的自觉,都以坚强的意志介入祥子的生活,与他进行戏剧性的互动,直到以意义深远的死亡而告终。所以,一旦意识到她们共同的主体位置,将《祥子》仅仅当作“祥子的(真实)故事”④显得不合适。进而,我们对她们的处境理解得越深,便越能看清楚祥子作为一个男性所处的位置的相对性,也越能重新注目这三个不同的位置之间展开的悲剧性关系网。因此,是不是可以设想,通过正视她们与他的关系,能够把《祥子》从现成的现实主义语境里拿出来重新脉络化,或者说干脆建构新的(被掩盖的)一种现实?为此,笔者提议,要围绕着“性别”(gender)这一现在充分普及却仍需检讨的角度去进入《祥子》这一著名的文本。
夹在“现实主义”和“女性文学”两者间的“性别”
“性别一词是指,围绕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关系和实践。女性主义学者以性别为核心分析概念,对性别关系在社会性互动和身份认同中以及在如经济、家族、政治和法律体系等的结构性、制度性领域里的各种表现方式进行了详细检讨。她/他们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与对女性性和男性性的界定一样,因继续被建构、被再生产、被争论而发生变化。这样,对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相关的作为先天因素的女性性和男性性这些概念进行挑战。”⑤既然这么理解“性别”一词,就可以看到,《祥子》通过祥子、虎妞、小福子三者的矛盾,比任何文本都更强烈地暗示着,我们所经历的和所能想象的一切现实总是被性别化的。因为矛盾中的他/她们显示,在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下,性别关系是按照阶级/阶层而不断分化的,而且这些分化中的各个男性和女性们的不同利益关系以他/她们身体为媒介实践出来。
从《祥子》里的三位家长开始吧。曹先生是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家之长,全权主外。家庭这一“私领域”则由曹太太担任,但正是因为她从属于曹先生,所以曹先生不可避免地成为曹宅的唯一权威。刘四爷则是个中产阶级商人阶层的一家之长。他是人和厂的主人,而其女儿虎妞一边负担家事,一边到位于刘四爷的房间和自己的房间之间的“柜房”(页48)上班。最后的是个下层阶级贫困阶层的一家之长二强子。他为了糊口,把女儿小福子卖给了一个军人,用她的身价开始做买卖,不久赔本。小福子回家以后,二强子默认她在门内卖身养家。
简言之,虎妞和小福子都在门内从事除了家事以外的劳动,创造不可轻视的经济利润。如叙事者和刘四爷所承认,人和厂的形成和维持一直少不了虎妞的劳动。小福子的劳动更是不可缺少,因为在她所属的下层阶级当中,家长的收入太少,养家一定要有女性家人的经济活动。其实,她们对家庭经济的担任不能说是例外,而应被看成是在她们各自所处的社会位置当中相当典型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两位女性所创造的经济利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归属于各自的一家之长,却以她们混淆了男女之间的“自然”界限,即“内/外”的界限为由,她们的家长们都会责备她们。以上就是虎妞和小福子试图通过结婚这种交易来摆脱的状况。⑥
至于祥子,他现在是下层阶级的未婚男性体力劳动者,也是未来的一家之长。其实,他当作目标的“自由,独立”的生活就意味着成为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的一家之长。为此,他选择拉车,其很大的动机在于,他认为这是一种适合男子汉的活儿。有趣的是,祥子最愿意的既稳定又经济的雇佣方式是“入住”拉包车,也就是住在雇主家里,陪着雇主上下班,陪着他的太太和孩子来往,还要做些家务。正是通过入住拉包车,他与杨先生、曹先生或夏先生等各种中产阶级的男性们见面,临时成为他们家庭的一部分。而这些中产阶级的“公/私”领域的维持和繁荣,便建立在像祥子一样的下层阶级对其服务之上。曹先生的家庭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更为有趣,也相当反讽的是,祥子被此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味儿”(页59)深深吸引,把它当作他要通过拉车建立的家庭的榜样。当然,到时候,他由于“文化资本”的缺乏不会像曹先生那样教人,而是像刘四爷一样从事个体经营来养活自己的家庭。
以上对《祥子》的性别化现实的简单分析,显然不是现成的现实主义批评以其认识论框架曾经解读过的或要解读的现实。现在,笔者要用这一节剩下的篇幅说明,《祥子》的性别化现实,也很难被80年代后期以来一向对文学批评中的男权中心主义提出挑战的女性主义批评视野所观察到。
简单来讲,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中,以女性主义为名的批评大部分是“女性文学”研究,其意思是由女作家生产而(或者“所以”)含有对女性现实洞见的文学。举《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的例子,它是在对1949年之前的九位女作家的文学文本解读中,读出与“五四”以来以特定的方式被现代化的父权制话语——“这样一种既要女人觉醒又要女人沉睡的话语”⑦——作斗争的女性意识,并把它细致地辨析出来的第一本专题著作,到现在还被誉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研究。笔者欣然认同这一评价,只不过认为,我们应该记住这本著作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应该记起今天的我们有了更广阔的眼界来回味这一“从女性主义视点所做的研究”。⑧
这个视点是什么?笔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像任何话语一样,所谓女性主义总是以有质的差异的复数而存在。而且由于女性分明是弱势群体,但绝不是少数群体,所以各个女性主义流脉与现成的种种话语和世界观形成复杂关系,相互间也存在不少分歧。因此,“女性主义视点”这类字眼,若不被很长的理论性术语所限制,就很容易选择如下非生产性的二分法的一个项:“女性主义者希望的是什么?是希望消除女性这一范畴,把性差的意义减到最低,从而以我们本质上与男性一样为前提来主张我们的权利?还是希望主张女性的身份,以我们作为女性的共同点为根据来肯定女性的文化,并组织我们自身?”⑨
如果说到70年代的社会主义话语以及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话语里的有关女性的讨论选择了第一项,那么可以说,如“女作家们的眼睛”和“女人的视点”⑩等的字眼所表明,《浮出历史地表》选择的,或者至少它所生发的解读效果是第二项,即女性的差异——父权制之下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差异。1989年当年,这样标示性别差异来重新建立“女性文学”这一老范畴的尝试,应该是有力的智力挑战。但这样的“女性文学”研究的正当性,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到质疑,原因在于把“女性”这一还原性的概念当作建立“女性文学”的第一根据。正是因为“女性”。一词就意味着作为女性而生活,所以女作家们的观点和对各种女性们的文学再现的交叉和积累,很可能使得“女性”这一概念丰富起来,甚至动摇起来,但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场域里的女性主义批评走过来的路,大体与此相反。
90年代女性写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脉络被称为“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个人化写作”被视为“女性写作”的主要形态,既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同时也是注重女性差异的女性文学探索的必然延伸。从80年代中期提出“女性文学”,到80年代后期注重反叛父权制社会的“女性真相”,都在指向一种经验化、本质化的女性想像和认知。(11)
依笔者看,“女性”这一概念延伸为把“个人化”、“私人化”,或甚至与这些词等同的状况是,在以男为公、以女为私的有待反省的前提下,将“女性”一词当作“不是男性”,甚至“从属男性”的理解方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种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局限大概如下:首先,把父权制当作一个无历史性的独立结构,各个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互动也被还原为一种零和(zero-sum)结构,即有权力和无权力。从而,不容易通过文学批评把女性们再现为“主体”(12),反过来也不容易切实地理解各个男性位置的复杂性,因为虽能说父权制一般保证男性对女性的普遍优势,但并不能断定一切男性都从父权制中得到同类均匀的利益。这三点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而也许,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有所变化的,只是把女性一项的内涵从男性的社会性受害者改变为男性的美学性他者。
既然意识到了如上的局限性,我们理应在文学文本面前,开放“女性对父权制环境”这种先验的框架,而探寻父权制里性别关系和实践的具体分化及其变形。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所谓女性主义批评与其努力寻找似乎逼真再现女性的处境、自我或内面的文学文本,不如努力发掘叙述多姿多彩、富有意义的性别关系的文本。而我们正在读的《祥子》不正是这种文本吗?
倚仗对“女性文学”的女性主义批评却很难发现这一点,因为它一向束缚于这一假定:女性的现实区别于男性的现实,而且只有女性作家才能再现它(其另一面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众所周知,这种女性主义批评所批判的主流男权批评是现实主义批评,而这一点对《祥子》不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它主要是通过现实主义批评而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的最优秀作品之一。女性主义批评尖锐地意识到“关于谁和为谁生产知识”这一问题,是很正当的,但在落实这种意识的时候,它一般拒绝将如《祥子》等(带着)现实主义经典(标签的)文学文本当作积极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女性文学”研究自觉参考现实主义文本,大都是为了把“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对立起来。
这种批评惯性有必要重新反顾如下事实:第一,文学文本的建构总是向着包括作家的经验和意识在内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网络敞开,而且在每个意识形态性文本里都存在种种裂痕,能让拥有不同期待视野的读者从中迎接不同的问题。第二,长话短说,现实主义批评和“女性文学”研究之间的这种主观性纠葛,有待被问题化,因为它本身就与现代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性别意识形态相仿。第三,这两种批评方法反正都是在认识论上遵循了类似的循环型二元结构的本质化话语,也是不言而喻的。两套批评话语使用得越普遍,性别问题就越留在死角。所以有理由期待,本论文以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多重性别关系的观点重新解读《祥子》,有助于打破这两大批评之间维持多年的僵局,掀开新的批评对话的空间。
重读《骆驼祥子》的性别化现实
祥子把自己的力气和人力车当成最起码的生产手段,试图爬上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梯子,成为个体经营者、中产阶级的一家之长。他想先靠拉车在人流物资汇聚的北平立住脚后,再娶一个“一清二白的姑娘”(页53、204)。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祥子显示了与其他同行们不同的勤快和良好的道德。他不赌,不嫖,也不好吃懒做,都是为了保护他劳动力的源泉——身体。不过,《祥子》给我们的最基本的启示就是,身体既是劳动力的源泉也是性征(sexuality)的媒介。而这种身体的复合性,祥子通过虎妞的“侵犯”才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
[虎妞与祥子]《祥子》的叙事者对虎妞的评价本来还是肯定的,将她描写成一个朴素、聪明、善于理财的准男性。但是一旦祥子与虎妞发生性关系以后,评价虎妞的基准就转为“女人”。而当这个女人构成祥子的欲望指向的中产阶级性别意识形态中的一项时,如要做祥子孩子的妈妈,她就被叙述为太“丑,老”(页53);她“厉害”(同前)——她在男人们的厂子里争权斗利;她“不要脸”(同前)——她“引诱”(页58)了祥子,让他失贞,还以假怀孕要求结婚。叙事者强调,祥子没有丝毫非分之想,是虎妞引诱了他。而有点惊异的是笔者接触的以往的研究中,多数都原封不动地接受了这种引诱说。非要说虎妞引诱了祥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引诱的原因在哪儿?
王德威恰当地指出,虎妞的身体不过是一个暂时替代品,用来代替祥子因被杨宅解雇而失去的未来的人力车。(13)但他忽视了一个事实,这就是那天的性关系对虎妞来说也是一种工具。尽管叙事者对虎妞的陈述充满恶意,我们通过虎妞的一贯言行可以猜测,她其实很久以来就希望找回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这个身体向来是为其家长刘四爷服务的。
现在刘四爷的家产,做个中产阶级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但他从前属于与祥子差不多的社会底层,通过“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页34)等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才经营起现在拥有数十辆洋车的人和厂。正因如此,他才和曹先生一起成为祥子最敬畏的两个人。
但如前所述,我们不得忽略,如果没有虎妞的作用,现在的刘四爷及其人和厂就成立不了。问题是她在人和厂做的事却只被认为是“打内”,而不被看成是正式的劳动:“刘四爷打外,虎妞打内,父女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页35,本论文暂且不提家务劳动问题。)(14)由此出现了虎妞的两种不满:第一,刘四爷利用虎妞创造和维持的经济力,得以充分地发挥自己作为男性的性征,反之虎妞因为被要求只作能干的劳动者而被迫压制自己的性征:“说真的,虎妞是这么有用,他实在不愿她出嫁”(页43);第二,因为虎妞不是刘四爷的儿子,她投入在人和厂的多年间的劳力以及经营厂子的不凡的能力,在社会上和在经济上无法得到应有的承认。
能同时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与老实、有性魅力又不得不让虎妞掌控的男人结婚。祥子像是满足这些条件的人,所以虎妞早就选定了他并趁机付诸实施。虎妞的打算是跟祥子结婚后,让他作为刘四爷家的“儿子”(页116)“稳稳当当的能把爸爸的事业拿过来”(页145),从而虎妞自己从准男性劳动者的角色中摆脱出来,成为呆在家里而享受“女性”生活的太太。为此,她才有计划地促成和祥子的结婚。也许,虎妞以这样的方式图谋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不像祥子一样去拉车,是在允许的条件下“最合理”地发挥了主体性的,犹如有一位女诗人曾经带点讽刺性地写道:“对我们(女性——笔者注)大部分人来说,与男性权力结合是共享权力的最可行的方法。男性权力再不足道或再堕落,如果不能与其中任何一种结合,就意味着我们将得不到保护,极易受到伤害。”(15)
另一方面,从虎妞屋里出来的祥子,发现了作为性征媒介的身体可以胜过自己劳动的意志而受到冲击(页54),但解释这一惊讶的发现的根据只有他追求的中产阶级的性别意识形态。按照它,虎妞则是个“破货”(页53),早已失去了成为自己未来家庭的主妇的资格。还有,这不只是虎妞的错,刘四爷没有好好管理其女儿的身体也在责难逃。最终,和虎妞的事儿,作为自己身体的完整性被刘氏父女玩弄和破坏的一桩耻辱经历,刻印在了祥子心里。尽管如此,虎妞还是如愿以偿地与祥子结了婚。这是因为虎妞非常清楚祥子的意愿是什么。虎妞让祥子认识到,在她身上可以得到他所要的两件东西:一件是妻子和孩子(祥子把虎妞怀的孩子一直看成像小马儿一样的儿子);另一件就是买人力车的钱。听到虎妞怀孕的消息之后,祥子便认为结婚是不可避免的。而婚后,祥子拿虎妞给的钱买了第二辆人力车。
问题是虎妞的钱是很有限的。虎妞并没有与祥子一起降到底层社会的念头,想着在结婚带过来的五百块钱都用光之前,与刘四爷和解,回到他手底下。但虎妞将这个计划告诉祥子时,他却说不回人和厂住。这里包含着父权制很重要的一点:父权制不仅包含着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同时也意味着在一个组织之内/间男性们要有高低序列,或者支配和被支配之分。祥子这么回答是因为他不愿意被吸收到刘四爷家供奉他作为一家之长。同样的原理,为了自己能成为一家之长,他不会拒绝丈人的帮助。他为了从心理上准备虎妞和刘四爷的和好,在人和厂前转悠。可是在虎妞将祥子的这一面说出来时,祥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反应。
现在,她自己这么说出来!自己的车,自己的钱,无缘无故的丢掉,而今被压在老婆的几块钱底下;吃饭都得顺脊梁骨下去!他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一直到她翻了白眼!把一切都掐死,而后自己抹了脖子。他们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死;大家不用想活着!(页136)
上文毫无保留地展示了,祥子的本来以中产阶级性别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良心和良知多么容易动摇变质。把上文与祥子遭受两大不幸——失去洋车和买洋车的钱后只知道埋怨命运——作个比较吧。前者正是在与让祥子感到自己作为男子,或者“人”被理解的一名同事和曹先生同行的路上发生的,而后者是因着无规矩的军队和腐败的侦缉队这些准国家机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制度化)而起的。祥子对他们不敢反抗,却因虎妞的一句话就翻了脸。这表明,与真正剥削自己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男性代理人相比,向一个似乎侵犯了自己男性性的女性问罪要更容易。
但虎妞也聪明地懂得,自己的钱能使祥子的这种性别意识形态失利。于是她不怕与祥子吵架,要求他一起分担家务,并向他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性征。对此,文中的叙事者嘲笑“他完全变成了她的玩艺儿”(页140),并控诉虎妞的性欲到使祥子的劳动力消耗殆尽,甚至到威胁他生命的地步。换言之,《祥子》里女性在性征上的主动比包括剥削式的劳动契约在内的任何事还要更具破坏性。
可是,祥子和虎妞的家庭遭到流产的关键原因,并不来自虎妞,而来自于刘四爷。刘四爷没有虎妞,无法经营人和厂,但又不想把祥子当成儿子将人和厂传给他,所以索性选择了把厂子卖掉换成现金而离开。虎妞和刘四爷的亲情关系在当时社会有关性别的理财规则面前,就这么简单地结束了,而虎妞做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女性的愿望也随之落空,使她变得十分沮丧。
祥子呢?据叙事者的报告,祥子“实在有点可惜……倒没有十分为它思索”(页149)。但从刘四爷离开,祥子中产阶级一家之长的梦想的物质基础也随之消失的时候起,叙事者对虎妞的“恶行”的揭露就层出不穷,这应该当成偶然来看待吗?会不会祥子不需要没有刘四爷的虎妞,所以要从祥子那儿除掉虎妞的理由突然增加?
第17章中刘四爷的失踪与虎妞在经济上、性上利用小福子的消息一起传来,而这一利用因其发生在一个叫虎妞的“母夜叉”(页134)和笑貌像白兔子一样娇憨的小福子之间,就被描写得比《祥子》里的其他关系更不正常,毒辣而扣人心弦。加上第18章中虎妞真的怀孕时,她干脆变成一个不能控制自身的疯人。疯人虎妞当然没有成为母亲的资格,疯人的儿子也就成为难以让人接受的存在。最终,虎妞“带着个死孩子,断了气。”(页177)
刘禾稳妥地指出:“她难产而死——一种非常女性化的死法——也许是对她的反讽式惩罚,因为她违背了这个社会的性别规范。”(16)可叙事者的评价里也有值得倾听的部分:“在这杂院里,小孩的生与母亲的死已被大家习惯的并为一谈。可是虎妞比别人都更多着些危险,……她的优越正是她的祸患。”(页174)也许叙事者的意图在于将虎妞的死归咎于她自己,不过他说“她的优越正是她的祸患”是很合理。她的优越就在于,她一直有把握自己能够应用父权制的文法,通过把刘四爷和祥子联结起来为自己营造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
最后,我们在此还需注目《祥子》里随怀孕而来的性别关系的变化。虎妞原本是一个拥有独立的谋生能力和意志的女性。但自从她怀上了孩子,就开始依赖祥子,祥子则站在了家长的位置上,一个人背负家庭经济的重担。从这儿开始,祥子的家庭每况愈下,与此成比例的是虎妞的疯狂程度也越来越严重。但如果去掉叙事中恶意夸张的成分,那么这也可说是一个被仅有的两个男性亲属置之不管的、在陌生的环境中自已经受初产的孕妇身上会发生的身体和精神反应。
进而,将此看作发狂,其实也是把有关阶级/阶层的前提隐藏起来的结果,因为也许只有像曹宅那样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产妇,才会得到丈夫雇佣的女仆人和奶妈等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照料而“维持常态”。但是虎妞呢,不管在结婚之前或之后,距离其他女性的合作和帮助都很远。虎妞未婚时一直过着准男性生活,而在婚后只与在她眼里自己从未享受过的女性形象的化身小福子成为了朋友,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上,像虎妞和小福子的母亲们一样,贫民阶层女性的生活始终充斥着不断的分娩、过度的劳动、营养失调和丈夫的暴力等不利因素,从而很难充当帮助没有经验女性的曼托(mentor)的角色。结果,虎妞随着产期的临近而陷入一生中最无力的状况,却只能把自己的身体委托给对它一无所知的男性权威,如祥子和“顶着一位虾蟆大仙的”(页175)巫婆,任他们摆弄。《祥子》里没有任何一种场面是人的身体被如此地嘲弄和异化。虎妞临死前,巫婆趁着祥子打盹儿溜走,醒过来的祥子“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页177)。虎妞在分娩不妙时的喊声痛苦地提醒我们,她在从刘四爷那里收回对身体的主权,又在与祥子的结婚关系中看管它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自己:“她把一切的神佛都喊到了,并且许下多少誓愿,都没有用。最后,她嗓子已哑,只低唤着“妈哟!妈哟!”(页174)
女性间沟通的缺乏,在有关另一个重要女性小福子的叙事中也同样出现。这和祥子每逢难处就得到同性曼托们的劝告完全形成对比。刘四爷、曹先生、小马儿的祖父正是那些曼托,虎妞和高妈等准男性们也是如此。无可否认,这样的差异成为将祥子和虎妞/小福子各自引向生与死的原因中的重要部分。如何评价这样区别化叙事也是我们在《祥子》里值得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小福子与祥子]祥子办完虎妞的丧事回到家里,忽然发觉到自己对小福子的爱,让人感到有点意外。但我们不久就会搞清楚,因为小福子是虎妞的镜像,虎妞当祥子的妻子越不合适,小福子就越合适。这种镜像关系的两个女性所呈现出的共同状况是:资本主义父权制之下,如果家长需要或愿意的话,女性的身体就容易被迫成为他增值资本的直接生产手段。而不同之处是:虎妞丑陋的外貌与刘四爷的经济手腕结合起来造就了中性化劳动者虎妞,而拥有美丽外貌的小福子由于二强子经济上的无能成为了性商品,“就被人挑到市上去卖掉”(页156)。
这“市上”买卖的是下层人的身体。而这市场总是明显地性别化了。例如,小福子的身体和祥子的身体虽然都被转让给过军人,但军人用祥子的身体作为劳动工具,而用小福子的身体作为男性身体的消费对象。祥子在军队感到被侮辱而愤慨,其原因是,虽然他的力气和他的人力车一样都属于他自己,军队却不支付他报酬。可是,小福子的身价总归二强子,而小福子连对此质疑的余地都没有,因为他就是小福子身体的主人。
正是因为如此,小福子虽与祥子同属一个阶级,却能与中产阶级的虎妞走到一起。祥子希望靠来自自己结实的身体自立起家,而她们却只希望加在自己身体上的父权制的权力减弱。而且这个方法就是,通过结婚将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转移到一个新的家长那里,他要有一定水平的经济能力和良心,不至于过分滥用或出卖她们身体(所以这个新的家长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与中产阶级的家长是重叠的)。
虎妞和小福子对保存在父权制下渐渐枯竭的自己的身体的渴望,与祥子在资本主义的下层生活中对保存自己劳动力的渴望,一样地迫切,或更为迫切。所以她们都主动提议跟祥子结婚。她们每逢祥子的中产阶级家长的梦想受到打击时就接近他,暗示自己能满足祥子的需要。虎妞在祥子失去了买车的机会的时候(页51),小福子则在祥子失去孩子的时候(页179),出现在他眼前。在此,重要的是,她们的求婚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她们的女性身体展开时才能有效。这是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被祥子当作女人看待,才有了成为祥子家女人的资格。
他的口不大爱说话,见了她(小福子——笔者注),他愿意随便的说;有她听着,他的话才不至于白说;她的一点头,或一笑,都是最美满的回答,使他觉得真是成了“家”。(页180)
虎妞与小福子的镜像关系在小福子与祥子婚姻失败的场面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尽管虎妞的身体没有成为祥子这一男性性征的追求对象,但因她的身体连接着刘四爷的钱和祥子孩子的缘故,所以虎妞和祥子的家庭得以暂时成立。与此相反,小福子的性魅力使祥子想象了一下两个人的家庭,但小福子的父亲二强子的存在让他在下一个瞬间就抛弃了这一想象(页180-1)。可是,这儿也有一点需要细究。按叙事者的话,祥子是因为无法抚养在经济方面无能为力的小福子的两个弟弟和二强子而放弃与她结婚的。这样的说明听起来顺理成章,但小福子如果选择从二强子的家中脱离的话——就像刘四爷断绝和虎妞的关系,或者像跟小福子同居的军人毫不理睬二强子一样,小福子和祥子不也完全可以不要其他负担来开始新的生活吗?
隐藏在这里的问题是小福子并没有被赋予订立契约的主体资格。《祥子》里的现实不允许女性拥有所有权,因而她们实际上根本就不能成为任何产生所有权的契约(结婚就是一种)的当事者。《祥子》有力地显示,在这样的条件下,结婚只不过是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围绕对一个女性身体的所有权签订的契约而已。祥子放弃小福子,是因为他知道二强子因为经济的缘故不会调整或转让对小福子身体的所有权。相反,刘四爷却以同类的理由将对虎妞的所有权完全让给祥子了事,从而让他遭受挫折。祥子所向往的中产阶级家庭,如果没有像刘四爷这样的外援,单靠自己的力气是难以达到的目标。这样看来,祥子的委屈和失败根本上都与父权制有关。父权制使祥子继续抱着当一家之长的梦想,同时也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权又使他的梦想落空。这两面性就是祥子这头“骆驼”背上驮负的“双峰”(页20),使他不堪重负最终倒下。
把《骆驼祥子》作为新的批评资源
在这一节里,笔者想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观点来重新追问现实主义批评和“女性文学”研究,并建议把《祥子》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资源。
笔者在第一、二节里指出,现实主义批评和“女性文学”研究,都倾向于依据同一结构的解读框架来固定文学文本所再现的内容及其意义。与此同时,它们没有感到详细检讨每个文本所带来的不同效果的必要性,因为其框架总是发源于对所谓世界的特定诠释,对文学的形成和作用这一问题也已有了明确的答案。结果,这两种批评都强化了同时标记作者生平和狭义的社会—政治史的编年型文学史。文学史应该澄清的根本问题是文学在不同的阅读语境当中作为文学被接受的理由、价值,这正是所谓的“文学性”。而在编年型文学史中,那只能作为作者通过文学作品对当代世界做出的一些类型的反应。但如果文学性不仅仅如此,而将其理解为,由处于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读者通过读解文本不断对话而生成的流动性概念的话,又会怎样呢?那样的话,关键并不在于作品和作家所指示的内容及其意义,而在于读者顺着文本进行的意指化过程(signifying procese)而得到的启示和生发的质问或疑惑,也就是说是文本的阅读效果。沿着这种思路,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推断出,不论是“个人对一国之社会”还是“女性相对于父权制社会”,都是预先限制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
所以本论文采取了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多重性别关系这一视角来解读《祥子》,以便证明,《祥子》这一文本里面的紧张关系,能够不断鼓励读者积极介入《祥子》这一叙事组成体,并使读者发掘其中等待读者追究的种种思考资源。这种紧张是指,《祥子》的叙事者集中陈述着一名人力车夫在资本主义中下层社会中的挣扎和没落故事,但我们通过钻进这一叙事的前后、表里之间的裂痕可以构建的是十分具体化、整体化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性别关系网。而这种构建关系网的工作越发展,越能具备有违甚至超越叙事者的主观及其叙事表层指示的现实感。如今,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这种效果就是《祥子》的再现性叙事所拥有的批判性力量,所以也正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在此文本中值得再评价的部分。这一点,现在我们通过解读《祥子》的结尾部分来确认一下。
祥子决定“仗着狠心维持个人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页181)而离开了小福子。这就意味着,祥子追求向上的“个人自由”要以对于受父权之苦的周边女性熟视无睹为前提。但是尽管祥子回到了老本行努力圆梦,但由于缺少她们的协作和照顾,他的生活都一天天不如以前,几乎到了放弃梦想的地步。
只有与刘四爷和曹先生再次相逢,祥子才能旧梦重燃。首先,祥子偶然遇见刘四爷,但拒绝告知他的“唯一的亲人”(页197)虎妞的葬址,以此来痛快地惩罚不给自己的家庭提供经济基础的刘四爷。然后他才决定去找他心中的两个人,曹先生与小福子:“顺着曹先生的主意去作事,而后再有小福子的帮助;他打外,她打内,必能成功”(页199)。果然,曹先生承诺会重新雇佣祥子,如果曹夫人不反对也会一起雇佣小福子,这给了祥子新的希望。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次曹夫人可以正式发表意见的场面,但我们终于没能听见她的声音,因为祥子哪儿也找不到小福子。原来是,他得助于周围的男性曼托们,对自己作为男性的现在和未来有了足够的了解,却对同一阶级女性的“命运”竟然无暇顾及,所以他自己在北平漂浮,却放心地以为小福子会始终呆在原地。而这一知识空白又由曼托之一,小马儿的祖父来填补了。根据他的指点,祥子访到白房子,才打听到了小福子自杀的消息。
什么也没有了,连小福子也入了土!他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他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她已作了吊死鬼!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还用想什么呢,还用希望什么呢?(页210)
仅用祥子的看法来解释小福子之死的这一场面,决定性地表露出视野的狭隘性和盲目性。因为读者此前通过虎妞、小福子和祥子之间的一连串事件,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在性别化的现实下,男性和女性即便说处于同一外部物质条件下,也很难拥有同样的需求和欲望,更不能共享同一身份和利益关系。所以,读者看到上面祥子的自圆其说后,自然意识到祥子的愚钝犹如阿Q般令人寒心。那么,小福子之死的真正理由是什么?紧接上文的下面这段话中所描述的祥子作为人力车夫的“自我废功”给读者提供了线索。
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糊糊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懒,他狡猾,……他并不后悔;假若他也有后悔的时候,他是后悔当初他干吗那么要强,那么谨慎,那么老实。……对什么事他也不想用力,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页210-2)
小福子一死,祥子要通过拉车实现的家庭之梦又一次成为泡影。祥子失望之余,决定放弃卖力气。但无论怎么失望,或绝望,他都没有理由去死。因为对他来说,身体的第一意义总是劳动力的根源,受剥削的也是这个意义上的身体。所以他只要通过自己消费自己的力气去找回对自己身体的主权就可以了。可是,让小福子感到绝望的自己的身体不仅是劳动力来源的场所,更是所有阶层男性得以随意滥用的场所。换言之,小福子的身体这一物质存在本身就构成资本主义父权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她为结束自己的不幸而唯一能做的就是结束自己身体的生命。
在祥子卖了阮明而感到一丝内疚的场面中,我们还可以发现祥子到此时为止仍是行为和思维的主体。但小福子的死亡却只是极其虚无。小福子吊死的“树林里到晚上一点事儿也没有,她不出来唬吓人”(页209)。不但如此,唯一记住她的人——祥子为了悼念她(不如说借这个名目),竟加入到害死她的队伍中成为其中一员,让读者啼笑皆非:“几乎每次喝醉他必到小福子吊死的树林里去落泪;哭完,他就在白房子里住下。”(页211)
据悉,对祥子产生自我认同的有些读者,向老舍质问过祥子如此没落而希望又在哪里的问题。我们也不得不提出类似的疑问。祥子直到最后也只知道怜悯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理解缠绕小福子等周边女性们的生存条件及其与自己的密切关系,对这样的他来说,有什么理由要寄予希望呢?这个问题或许显得有些轻率,却是作为批判理论的现实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都不可回避的,因为这总是衔接着“新主体”的问题。资本主义父权制性别化的现实下,不选择祥子的路(屈膝为奴,成为麻木不仁的代理人),也不走小福子的路(自暴自弃,死了以后什么痕迹都不留),而能够安排新的人生的主体又会是谁,又怎么才能形成的?《祥子》的叙事最后所介绍的一个另类的女性形象(她恰恰是告知小福子之死的声音的主人)更引导读者必然地这么质问自己。
“白面口袋”这个外号来自她那两个大奶。……可是,她的出名还不仅因为这一对异常的大乳房。她是这里的唯一的自由人。她自己甘心上这儿来混。她嫁过五次,男人都不久便像瘪臭虫似的死去,所以她停止了嫁人,而来到这里享受。因为她自由,所以她敢说话。想探听点白房子里面的事,非找她不可。……自然打听事儿也得给“茶钱”,所以她的生意比别人好,也比别人轻松。(17)
我们已经看到了小福子和虎妞以父权制为轴是一面镜子的正反面。而今,白面口袋可以说成是小福子的镜像,也是虎妞的镜像。根据叙事者的形容,白面口袋的身体作为她性征的媒介,在家庭的篱笆内使得五个家长死亡,但自从她干脆进入白房子后,则给以多数男性快乐。而且她的身体在性买卖中完全被对象化,但她却享受自由地释放性征、自由地说话的生活,同时把这些活动当作谋生法子来愉快地劳动,所以她自己好像并没有被异化的感觉。白面口袋与祥子也处于面对面的关系。《祥子》里“自由”一词只属于祥子和白面口袋这两个人。祥子的自由来源于资本主义父权制并可在其制度下永远延期,而相反,白面口袋的自由却起初受到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排除,而后经过这制度内的调整后就得以实现。而我们应该记住的是,祥子未完成的自由与白面口袋完成的自由终究都只为维护资本主义父权制服务。伴随白面口袋的出现,《祥子》几经周折的叙事最终完成了由祥子、虎妞、小福子和她组成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方形封闭回路。
因此,笔者不肯承认《祥子》里存在任何新主体的雏形。(18)但重要的是,不要把这个不承认的感觉用“对20世纪前期中国现实的切实反映”,或者用“老舍这个男性知识分子想象的局限性”等“惯用句子”来取而代之。应该怀着对《祥子》文本所引发的包括新主体的问题在内的种种启发和疑问,全方位地探索有关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其他文学叙事,并和《祥子》进行越来越丰富的对话。对《祥子》进行文学批评不正是为了探寻让读者走上这种探讨和对话之路的叙事效果吗?进而,难道这种批评的介入本身不是已经在撰写新式的文学史了吗?如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本来作用在于,将文学文本中的潜力尽可能向读者释放出来、由读者来把握的话,上述提议应该引起深思。
注释:
①《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引自此书的正文部分,不再另注,只在文中标出页数。
②金容沃、崔玲爱:《骆驼祥子》第2卷,首尔:原木1986年版,第579-580页。
③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5-157页。
④对《祥子》的现实主义批评大部分就停留在这么一个模式当中。它们将祥子放到中心地位,然后将虎妞和小福子作为刻薄刁蛮的恶妇(或压迫者)和君子好逑的淑女(或受害者)对立起来,引导读者把祥子看成包括前者的在场和后者的缺席在内的恶劣环境的牺牲品。可是,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从虎妞和小福子的观点来看,祥子正是她们越挣扎就越让她们筋疲力尽的环境的一部分。
⑤Evely Nakano Glenn,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Mothering:A Thematic Overview",Glenn,Chang and Forcey eds.,Mothering:Ideology,Experience,and Agency,New York:Routledge,1994,p.3.
⑥在《祥子》里,除此之外,她们好像没拥有别的“交易”方法。不可否认,鉴于虎妞和小福子的状况,这么一个“再现”可以说颇具盖然性,但是这种再现是在什么程度上正当的,尚值得商讨。
⑦⑧⑩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第41页,第260页,第42、2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Glenn,p.22.
(11)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第五章,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10页。
(12)这里的主体同时意味着(自认为)自主思考和行动的自我,以及被制度性实践或意识形态呼唤的代理人。
(13)David Der-wei Wang,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151.
(14)其实,经营这种家庭和作坊不分的“家族企业”,是现代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中公认的一条致富之路。这企业属于一家之长,而他在动员家人,尤其是在动员妻子和未婚女儿来经营企业时,不需要支付报酬或可以支付最少的报酬来利用她们的劳动力。其效果是抑制家庭消费,以在促进家庭内资本积蓄的同时,抑制社会通货膨胀。
(15)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再也没有母亲》(Of Woman Born的韩译本),首尔:平民社1995年版,第84页。
(16)刘禾,同上书,第169页。
(17)老舍:《骆驼祥子》,上海:人间书屋民国廿九年版,第288页。如果只是要传达小福子死亡的消息的话,像白面口袋这样显眼的人物根本没有必要出现,她的登场反而会影响作品的统一性。也许因为如此,笔者现在从《祥子》的初版中引用的形容“白面口袋”的部分(除了第一个句子之外),在5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的各种《祥子》版本中都被省略掉了(关于《祥子》的版本,可参见金容沃、崔玲爱共著的《骆驼祥子》第1卷,第234-239页)。围绕《祥子》的版本而进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有关阮明部分的省略和《祥子》主题及其社会—政治上的含义关系上,而据笔者所知,有关“白面口袋”的部分被省略却一直没有受到关注。
(18)有关这一点,[德]凯茜《试论老舍作品中的女性描写》一文中曾得到论述,但在理论立场和论证细节上与本论文相去甚远。见曾广灿等编:《老舍与二十世纪——’99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