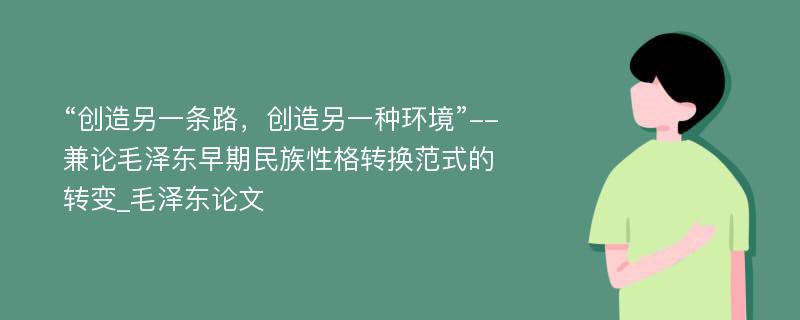
“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兼论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范式之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性论文,范式论文,早年论文,另辟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8年7月,毛泽东告别“修学储能”的学生时代,带着自1910年以来积淀的改造国民性的思索,开始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对象化、具体化和实践化。然而,残酷的现实不允许他实现多年的乌托邦式的“人皆圣贤”的国民性改造梦想。十月革命胜利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他在情愿和不情愿、自觉和不自觉的矛盾冲突中亦步亦趋的选择马克思主义,逐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国民性改造问题,促使他实现国民性改造范式的转换。
一、范式及国民性改造范式
“范式”(Paradig)一词最初是由美国人库恩提出,用于解决科学发展的模式问题,是一个作为描述整个科学结构的概念。范式包含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哲学观点、公认的科学成就,方法论准则、规定、习惯、乃至于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实验仪器等等,具有极其复杂的内涵。他提出范式这一个概念并不是为了说明那些纷繁复杂的具体内容,最为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新的模式对旧模式的反动,即范式的转换。按照库恩的观点,一个范式的变换似乎是一种危机,不再保持一种无声的和几乎看不到的规则,取代沉默不然的是实际上在做的对原来范式的质询。后来,范式作为一个概念引入各学科。笔者也把“范式”概念引入国民性改造领域以说明旧范式的危机以及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否定。
国民性改造范式是指国民性改造的整体结构模式,包含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理论基础、国民性批判、改造目标、改造途径以及已有的国民性改造理论、改造成就等等内涵。近代中国的国民性改造起初并无统一的范式,只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感到中国的人心风俗亟待改变,才能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直到严复、梁启超等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上升到成为占支配地位,并使整个晚清社会在他们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引导下,形成势不可挡的近代第一次国民性改造思潮,国民性改造范式才随之产生。早年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产生及发展正是对这种范式的承继。但随着他对国民性改造的深入探讨与实践,他逐渐对梁启超范式的信任发生了怀疑,危机显现,引发范式转换。
虽然,从1918年至192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得到壮大,这为毛泽东国民性改造范式转换提供了阶级基础;毛泽东在“驱张”和为实现“湖南共和国”的努力化为乌有后,他心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破灭,信念的改变成为他国民性改造范式转变的主观条件;而且,十月革命胜利所带给中国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希望曙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迅即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重新解读和建构近代国民性改造理论,使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朝立无产阶级新人阶段迈进,给求索中的毛泽东以思想启迪。到1920年底或1921年初,当他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标志他国民性改造范式转换的完成。这种转换主要表现在理论基础、批判重心、改造目标和改造方法的转变上。
二、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的理论基础之转变
近代国民性改造旧范式的理论基础是严复、梁启超等人从西方引介的英雄创世之唯心史观、庸俗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和合理利己主义,他们试图用这种理念去改造中国人卑劣的国民性,由于总是强化少数英雄人物的个人作用而激不起民众的共鸣,国民性改造成果自然就收效甚微,旧国民性改造范式的理论危机凸现。毛泽东通过对改造国民性的思索和实践,意识到国民性改造旧范式中理论基础与改造中国国民性现实之背离,在旧范式理论下的国民性改造,使国人从“家族”束缚中挣脱出来的个人,立即又陷入了民族、国家的桎梏之中,并未达到树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新民的国民性改造目标,质疑由此产生。
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离开湖南去北京,他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并在李手下做一名助理员,在这里他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过的书刊,见到许多过去从未见过的人物,接触到过去许多从来接触到的新思想,这为他探寻新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如此艰辛求索中,他抛弃了曾被他质疑的旧国民性改造范式的理论基础,使国民性改造范式的理论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其一,实现从二元论到唯物论的转变。最早体现这种转变的是他1919年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的“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问题提得响亮,答得明白,表明他注意到人类物质生活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意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同恩格斯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必须首先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1] 相契合,到1921年1月在致蔡和森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2] 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其二,由圣贤创世到群众史观的转变。此前,从他留下的早期文本材料看,圣贤创世观很明显。由于在五四运动中他看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人民群众在他心中的位置愈来愈重要,他在《释疑》中说:“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3] 群众史观初现端倪。其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毛泽东的发言及主张,表明他已实现由进化论向阶级论的根本转变。
三、国民性批判重心之转移
近代国民性改造旧范式中国民性批判一般都是把国民作为一个整体笼统地加以批判,而1918年以后的毛泽东对国民劣性批判则表现出批判重心的转移。该转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前人较少触及或被忽略的国民劣性的深入批判;二是突出并大力挞伐统治阶级的劣性,进而批判旧制度。
对前人较少触及或被忽略的国民劣性的深入批判又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对国民迷信心态的批判。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中国文化传统是神秘主义的传播媒介,通过它内化为社会心理,传统中国人,无论是上层统治者、思想精英还是下层民众都具较浓重的迷信心态,晚清启蒙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迷信家,因而,他们较少批判国民的迷信心态。毛泽东则对此着力批判,他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中说:“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4] 其二是对国人“大一统心态”的批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王朝,虽然天不佑秦,仅至二世被汉取代,但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被历代统治者所效法,“大一统”在获得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后化为社会心理,得到社会认同。毛泽东当时“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而“主张‘湖南共和国’的”,“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5],并认为这是导致中国“一盘散沙”的根源,他说,“推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6]。这种批判虽显牵强,但有它的历史背景,毛泽东当时主要是为了论证阻碍各省自治的不仅仅在各省督军,也在国人“大一统”的社会心理,阻碍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这也许正是他要竭力批判国人“大一统”心态的真正原因。其三是深入批判国人的旧思维方式。“中国人没有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有小的细胞才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各个才有团体”[7],在致罗学瓒的信中批判了国人四种逻辑错误:“四种迷,说得透澈,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以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8]。其四是对女子弱国民性进行批判。通观中国历史,女子处在社会最底层,精神的压抑和肉体的折磨,使她们身心呈现出许多弱国民性,他认为:“盖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做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陬。于不得幸福之外,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9]
更为重要的是批判重心转移的第二个方面:突出并大力挞伐统治阶级劣性,进而批判旧制度。在近代国民性改造旧范式中,国民性批判一般只笼统地对国民劣性加以批判,很少把它区分为普通民众和统治者,因而把那些专属统治者的劣性强加到民众身上,加大了国民劣性程度的估计,而把被统治者的一些优良品性,如俭朴,吃苦耐劳等,又遍及于一些恶劣的统治者,没能真实地反映国民性状况。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他在对一般国民劣根性批判后,改变他原先对国民性的判断,他说:“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10],“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我觉得湖南人确有几种可爱的特性,坚苦,奋发,勇敢,团结心,都是…”[11]。在对劳动群众国民性重新判断后,便突出剥削阶级恶劣品性。他在《卡尔和溥仪》中,批判了统治者的官本位心态:“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没有不再想做官。心理上观念的习惯性,本来如此”,因此,他预言“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以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12] 在《原来是他》的短评中,批判了为官者仗势欺人的丑恶嘴脸,“车夫拉了一个整天,拉昏了,不识时宜的拉着乱跑。忽然背上飞到几个重拳,连忙叫‘哎哟,了不得!’接着眼泪也下来了。本预备着吵嘴,一看,原来是他!就不敢说,拉着车飞也似的跑了。”[13] 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淋漓尽致地剥开统治者的恶劣品性,他说:“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至于湖南一省而言,造乱者,少数之武人。”[14] 这与他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对当权者“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的判断,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
由此,毛泽东便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旧制度,他说:“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15]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中,指出封建经济制度是造成国民愚弱的重要原因,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分析它对农民、工人、女子、学生、教师等群体的不良影响。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蔓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痼疾的暴露,毛泽东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痛陈资本主义制度使“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
四、国民性改造目标的时代切换
在近代国民性改造旧范式中,改造目标是造就资产阶级新民,由于民族危机的压力,又烙上了浓重的民族主义印记。毛泽东在梁氏范式目标模式的基础上,虽贴上个性解放的标签,建构出自己的具资产阶级性质的圣贤豪杰目标,即发达个性;身心并完,得大本大源,卓励敢死的新国民[16]。但该目标的历史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它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实现起来异常困难。况且,毛泽东所确立的资产阶级新民目标,就他本意言之,并不是一个终极的价值目标,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超越的对象,从而创造出更加完美的高于资产阶级新民的理想国民。另外,毛泽东确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目标,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子,是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使然。一旦有比资产旷级新民更高的目标,他必然会及时修正自己的目标追求,寻找新的航向,切换国民性改造的目标模式。
实际上,在驱张期间,毛泽东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1920年2月致陶斯咏的信中提到:“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17] 很显然,他在这里称“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是有别于“发达个性”、“身心并完”、“实现自我”目标的,开始由个体向团体飞跃,而“勇猛精进”与新民学会的“革新学术”相比,其战斗性明显增强,体现了目标切换的初步轮廓,但不清晰。当然,突破中见继承,“高尚纯粹”仍然是前一阶,段圣贤豪杰理想人格的再现。到1920年7月毛泽东终于“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有一枝正在盛开的既优于中国传统又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的小花”,这正是他求索多年而不得的目标,于是,他的目标转换有了现实基础。1920年11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他彻底放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朝着理想目标迈出坚定的步伐,于11月25日这一天之内,在痛苦与沉思中连续发给向警予、罗璈阶、李思安等人七封信,决定另辟蹊径,从头做起,把“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目标具体化。他在致向警予的信中说:“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决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8] 在致罗璈阶的信中说:“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 由此可见,他把“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的目标具体化为“刻苦励志的‘人’”了,这种“人”就是以共同信守的主义为基础的同志团体.如果说在这些信中他没明指“主义”是什么,而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就非常明了了:“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用。”[20] 由此,毛泽东的新人目标便浮出水面,无产阶级新人清晰可见了,完成了国民性改造目标的时代转换。
五、国民性改造方法的彻底转换
在近代国民性改造旧范式中,采用的方法是温吞水式的改良的方法,即通过先觉者用成熟的思想观念去启迪昏睡中的国人,国民应召自觉改造而成理想国民。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在探求国民性改造方法上,正是顺着梁启超等人的思路,在具体途径上做深入的思考和拓展,虽然在某些方面有超越梁启超之处,如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去变换全国之思想,使人人有哲学见解,依自己主张行事,比起梁“淬厉其本所有而新之”,“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略显可行性;又如创办新民学会,培养更多“大气量人”,通过层层向外扩展的方式去改造国民性,比起梁只通过《新民丛报》去摇旗呐喊,其现实基础更坚实;通过创办夜校去开启目不识丁的工人农民之智,比梁只注重国民教育显得更实在等。但是,毛泽东此前总体上同梁启超一样,也是想通过先觉者去启迪国民,使国民由“小人”转变成圣贤豪杰,没有突破梁氏范式改造方法的束缚,而惧怕暴力革命的手段,正如他所说“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21]。李大钊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从思想道德变迁和经济关系变革的角度剖析了近代国民性改造的经济缘由,提出“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提出“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22] 的国民性主张。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成为李大钊手下的一名临时职员。这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经济缘由的剖析,使得毛泽东拓宽了仅从精神上改造国民性的思路,开始注意用经济利益这根红线把民众联合起来,通过改造社会经济结构来改造国民性。
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他痛定思痛,决定另辟道路,另起炉灶。他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注重领会其精神实质,并用来研究和解决国民性改造的实际问题。毛泽东第一次读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他第二次北京之行。他后来回忆道:“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3] 这一段话表明,毛泽东自那以后,开始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因为这时他已认识到温和改良的如“倡学”方法或无政府主义方法无益于国民性改造,他说,“‘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因此,“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24]。再说,“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抵抗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它,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哪有回心向善之望”,[25] 所以,教育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无政府主义也同样如此,“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26] 因此,只有在变革社会经济结构中激发出国民推翻强权统治的热情才能改造其麻木、冷漠的劣性;在阶级斗争中培养国人的纪律性、团结协作精神以克服其懒散,无公德心,无国家观念等劣性;用阶级斗争的持久性和残酷性以改造其无恒心,自卑性等等,通过革命斗争培养出祛除劣根性的无产阶级新人,才能实现国民性的彻底改造,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27] 基此,至1920年底或1921年初,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方法也实现了根本转变。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之范式转变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历程,揭示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浓缩并再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的艰辛探索。
标签:毛泽东论文; 范式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梁启超论文; 东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