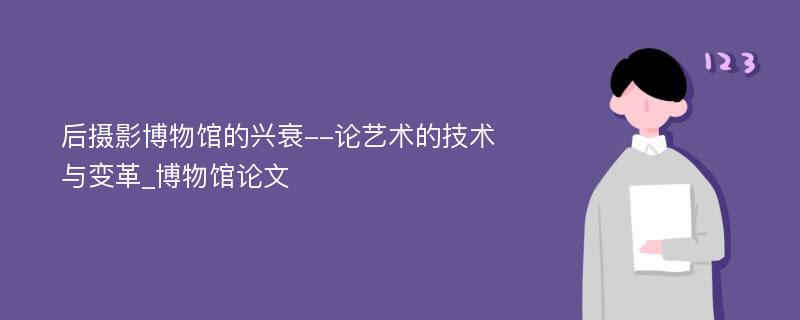
后摄影博物馆的兴起与衰落:论艺术的技术与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物馆论文,艺术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53(2008)05-0116-06
哈斯克尔笔下艺术家的高低座次
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的著作《艺术中的重新发现:论英法两国的趣味、风尚和收藏》(Rediscoveries in Arts:Some Aspects of Taste,Fashion,and Collecting in England and France,1976),以两个历代艺术大师济济一堂的场面作为开篇。第一幅是保罗·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从1837年开始,为巴黎美术学院(Ecole des Beaux Arts)的半圆形壁龛绘制的巨幅壁画。第二幅便是伦敦的阿尔伯特纪念碑(the Albert Memorial)浮雕底座上汇集的一批绘画大师。亨利·休·阿姆斯泰德(Henry Huge Armstead)创作了这组浮雕,而纪念碑则是1864年前后设计的。
哈斯克尔指出:这两件作品着手创作的时间相距大约17年,不过对于谁能名列重要艺术家之列,已经有了变化。1837年时,一群不朽之士曾经的聚会,在阿姆斯泰德着手创作之前已经被彻底地颠覆了。
哈斯克尔没有提到,而我要在这里强调的一点则是:两组群像中德拉罗什绘于巴黎的那一组,恰恰是在摄影出现之前绘制的。第二组,就是阿姆斯泰德雕刻的那组浮雕,恰恰作于摄影对西方文化可能产生进一步影响的大约15年之后。而与此同时,摄影已然改变了展示、复制、分析和评鉴艺术的方法。
艺术家—发明家
摄影的出现通常被当作技术的进步。事实上,艺术家们积极地参与到了摄影的发展改进中来。早期摄影术的发明者们——法国的达盖尔(Daguerre)和英国的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都是艺术家,尽管塔尔博特起初从事的是科学、语言学和数学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碘化银纸照相法”(Calotype)和他在执著地改进这种新方法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艺术才华,如今较之声名显赫的达盖尔,反倒得到了摄影史家们更高的评价。
塞缪尔·F.B.莫尔斯(Samuel F.B.Morse)是最早将达盖尔摄影法介绍到美国的人之一,他也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美国知名画家。当然,他也因发明电报和“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而举世闻名。
摄影的发明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反响。那时候,摄影带来的巨大而直接的轰动,远在如今出现的万维网之上。1839年8月19日,达盖尔的成果得以在法兰西科学院(the Institut de France)公之于众,当日,演说慷慨、排场铺陈、盛况空前,着意要让这一天载入史册。①在随后的几年里,单单是替月亮拍摄的“首张照片”,就接连出现了成百上千张。
不到10年,摄影技术便已传遍全球。一夜之间,各种拍摄、冲印和复制相片的方法争相涌现,每一种都各有所长,包括延时和短时曝光。这其中就包括塔尔博特的“碘化银纸照相法”(即后来的talbotype)、“硝棉胶玻璃负体系”和达盖尔照相法。
摄影文化的传奇与真相
摄影对于艺术和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而且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理解。我们对摄影,尤其是对艺术与摄影之间关系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带有一层传奇色彩。
有一个关于摄影的传奇故事是这么说的: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这种原本既卑微又遭误解的方法获得认可,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而最终它又在20世纪晚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摄影的地位——这几乎一直是各种美学争端的焦点——在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一直变化不断。摄影的声望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时有高低,部分地受制于其他几股文化潮流。
较之后来,19世纪的时候,批评家和鉴赏家们更可能看重照片的价值。早期的摄影图像——特别是达盖尔照相法——难以复制,且不易制成大量副本。因而许多照片就和用传统方式绘制的图像一样,不仅独一无二,而且更加稀少。影印法常被当作是一种自动绘图法。②
然而,1855年巴黎“万国博览会”(the Exposition Universelle)上,尽管呼声很高,但官方仍将摄影剔除在各大美术展览之外。结果,摄影作品只好将就着在工业展厅中展出了。但是3年之后,当卡米耶·西尔维(Camille Silvy)在苏格兰摄影协会(the Photography Society)举办的年度展览上展出他的《河景》(the River Scene)时,《爱丁堡晚报》(The Edinburgh Evening Courant)评论道:“这位新艺术家的画面让人无法视而不见。那水、那叶、那人、那远景、那天空,都那么完美无瑕。”另外一位评论家在《苏格兰人报》(Daily Scotsman)上写道:“倘若这幅照片未加修饰、取自自然,那么它就是一件艺术佳作,堪与凡·德·内尔(Van der Neer)或其他知名画手的任何一幅描绘相同景致的画作一较高下。”③
还有一种反复出现在19世纪艺术史中的假设,它认为摄影在艺术作品的创作、构图和装裱上,产生了某些形式上的影响。然而,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在摄影出现之前,西方绘画就已经酷似摄影了。实际上,许多精密的摄影装置可以保证相机镜头拍摄出来的照片能符合线性透视这种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理想。④
摄影的力量
有两件事给那些最早看到照片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一便是它们可以毫发毕肖地把细节表现出来。
1839年,就在法兰西科学院对外公布达盖尔的成果之前,莫尔斯拜访了他。莫尔斯惊叹于达盖尔取得的成果,在家书中写道:
你们无法想象那细节刻画得多么精美。油画和铜版画都无法企及。打个比方,朝马路另一边望去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远处的广告牌和那上边的线条文字,但单凭肉眼却看不清这些细小的标记。借助放大镜,这上边的每一个字母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楼房墙面上和马路人行道上的裂纹也都历历在目。⑤
著名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yon Humboldt)也为达盖尔拍摄的图像那面面俱到、超乎想象的精确而折服。冯·洪堡惊呼:“人们能在照片里看到那么一扇小小的天窗,上面碎了一块玻璃,用纸张糊了起来。”⑥
除了这些细微之处外,照片还能够捕捉到的另外一样东西,便是真实世界,这实在令人叫绝。照片不受制于任何主观的干预,似乎还能够圆满地记录下任何一个时刻,使之永远留存。
相反,较之于摄影不加修饰地表现实际情况,艺术仿佛尽是在虚构。面对着记录了历史瞬间的照片,正统的历史画上——法国学院派眼中最高级别的艺术形式——展示的宏大的寓言故事和事件则开始显得可笑而又落伍。
摄影图像真实可信,这种观念虽说有些落伍,却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写道:“即便如照片般惟妙惟肖,绘画从来就不过是表现对事物的理解,而照片也从来就不仅仅是做到对正光源(即物体反射的光波)而已——那是其对象物身上残留的东西,这在绘画中是没有的。”⑦而此前,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已经指出:“照片成了印证历史事件的证据标准。”⑧
这两项令人赞叹而又独一无二的特点——无穷无尽的细节以及无懈可击的真实感——对于两种艺术形式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两者的地位和声望一落千丈,很快便淡出了艺术史。
尽管在权威看来,肖像细密画从来就不是什么高级艺术,但是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初期,它一直是一种流行而又时髦的肖像艺术,尤其是在巴黎这样富庶的大都市里。“达盖尔银版法”几乎一夜之间便将其赶尽杀绝,倒不是因为肖像照片价格更低廉——刚开始可一点也不便宜——而是因为它们取代了肖像细密画的三大主要优势:精巧的细节、真实的写照和社会地位。
纳德尔(Nadar)之类的摄影师们不断承接业务,因此,到19世纪50年代,肖像照片被广泛地运用于时装集上。这些做法对于提升摄影的整体地位而言是大有助益的。正如罗森(Rosen)和策那(Zemer)谈到的那样,在19世纪中期,“许多艺术家和评论家一开始故作清高,瞧不起这项新发明……到最后,还是想要几张他们母亲的照片的。”⑨
摄影发明之后,另一种日渐衰弱的艺术形式是可反复复制的雕版画。自文艺复兴以来,手工刻印的雕版画被用来制作油画和其他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实际上,自打印刷术发明以来便是如此。除了摹本之外,印刷品成了在各地之间传播构图和艺术观念的主要手段。
传统上,精美的雕版复制品本身就被看做是颇有成就的艺术品。那些版画上既有原画者的名字,也有雕刻者的名字。鉴赏家们则热衷于收集这些价格不菲的印刷品。19世纪初期,许多版画收藏家们幻想着:随着原作的不断老化,雕版印刷复制品最终将会取代它们。⑩
然而,随着摄影的到来,复制版画的市场日渐萧条。它们的价值和地位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当然,原因在于现在艺术品可以被翻拍了。此后,照片将在艺术的研究、传播以及鉴赏等方面扮演一个核心和决定性的角色。
摄影与新兴的艺术博物馆
摄影发明之后,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已然成为传播图像的主要方式——不论是数量上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所有图像。著名的纪念碑和艺术品都成了最受摄影师追捧的题材。(11)
在英国,包括罗杰·芬顿(Roger Fenton)、菲利普·亨利·德拉莫特(Philip Henry Delamotte)、约瑟夫·坎德尔(Joseph Cundall)、阿伦德尔协会(The Arundel Society)以及威廉·塔尔伯特(William Talbot)本人在内的前辈摄影师和摄影作品出版商们,执著于艺术品摄影实验,并且力图把摄影作为复制艺术图像的手段,以使艺术作品更加广为人知。1852年成立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Fratelli Alinari公司,通过它与各大艺术博物馆和诸如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这样的艺术史家的接触,很快蜚声国际,这两位都热衷于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摄影方法。
Allinari是第一家替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绘于阿雷佐(Arezzo)的那些壁画拍摄照片的公司,这些照片,还有竞争对手们拍摄的那些,传遍了欧洲和北美。(12)
最终,摄影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博物馆——后摄影博物馆(post-photographic museum)的出现。在现代文化当中,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范例,它既包容了对艺术博物馆的旧有看法,而且还改变了这种看法。时至今日,我们几乎忘记了曾经有那么一座前摄影博物馆(pre-photographic museum)。但是,正是借助于后摄影博物馆,摄影不仅影响了在它发明之后产生的艺术,而且还影响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整部艺术史。
前摄影博物馆——剑桥的阿什莫利(the Ashmolean)、卢浮宫(the Louvre)、乌菲兹(the Uffizi)、伦敦国家画廊(the National Gallery)、普拉多美术馆(the Prado)、梵蒂冈画廊群(the Vatican Galleries)、埃米尔塔什博物馆(the Hermitage)、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威尼斯学院(the Accademia)、米兰的the Pinacoeca di Brera,以及类似的机构,几乎都分布在欧洲——它们都是在由个人收藏家、学术团体、历代王朝先前收藏的原作藏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些“珍品陈列室”和“皇家藏品”常常被安置于昔日的宫苑、宗教建筑和经改建的政府办公楼内,它们鲜明地反映了某个地区画派的风格或者当地的审美趣味,而不是意在展现艺术的整体面貌。
在拿破仑时代,不少这类的藏品又被有条不紊地重新整合,像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那样,成了公众性的国立博物馆,来自各大教堂、修道院的艺术品还有拿破仑时代以前从王公贵族家中没收的藏品在这里汇聚一堂。从19世纪开始,来自欧洲各国殖民地和各次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品纷纷汇入这些国有藏品之列,展现了帝国实力和大国威严。(13)
后摄影博物馆也像摄影那样,开始尽数网罗一切。它们的建立不是为了安放现有的艺术品,而是搜罗一批具有“教育”功能的藏品。
南肯辛顿博物馆
19世纪后半叶,通过摄影来理解艺术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大量艺术品照片传遍了世界各地——有的是单幅印刷品,有的是立体幻灯片,有的是廉价彩色石印复制品,它们被装裱一新,成百上千的家庭、公共场所和教室里,都挂有这样的图片。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图片出现在书籍报刊中。此外,摄影还促成了一种新型的专业艺术博物馆的诞生,这本身必将转变向公众展示和阐释艺术的方式。
这种后摄影艺术博物馆的原型便是南肯辛顿博物馆,即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接下来特别是在美国,许多此类博物馆便是发端于此。在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主张之下,南肯辛顿博物馆得以建立,建馆的想法始于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展会上搜罗了来自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展品——把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和工业产品聚集在一起展出,成为全民的盛会,它正是这种“世界大展”式的展览方式的起源。
南肯辛顿博物馆心怀两大目标:提高公众的品位,特别是英国制造业企业家的品位,还有就是通过艺术杰作的道德感召力,使社会蓬勃向上。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收藏有价值的艺术品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当没有原作或者原作过于昂贵时,照片、石膏模型和其他复制品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南肯辛顿博物馆的特色在于:它把照片、模型、复制品和原作四种类型全都摆在公共展厅展出。
从教育功能上来说,在南肯辛顿博物馆以及其他各地的这类博物馆里,较之原作,照片复制品的价值差别不大。在这些方面,特别是从低廉的价格这一点上来看,照片更有优势。
南肯辛顿博物馆的首任馆长亨利·科尔(Henry Cole)痴迷于如今所谓的“新图像技术”,相信它们潜在的教育艺术。到1856年,科尔已经拥有了一批可观的藏品,包括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伦(Julia Margaret Cameron)的作品,还有许多采用不同的图像印刷法印制的图片。(14)科尔对摄影的理解与支持,还有在博物馆管理过程中对摄影的运用,得到了他那位颇具影响力的副手——艺术家理查德·雷德格雷夫(Richard Redgrave)和另一位艺术家约翰·查尔斯·罗宾逊(John Charles Robinson)的支持,罗宾逊是南肯辛顿艺术收藏部的负责人,在博物馆购藏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科尔任命查尔斯·瑟斯顿·汤普森(Charles Thurston Thompson)为博物馆的摄影师。汤普森的职责涉及方方面面。1864年,当著名的拉斐尔草图(the Raphael Cartoons)被借至该馆时,汤普森拍摄了照片。为推广艺术名作而组建起来的阿伦德尔协会出版并发行了汤普森的照片。
汤普森还为一些模型在博物馆中展出的艺术品拍摄了照片。例如,1866年他被派往西班牙圣地亚哥(Santiago),去拍摄12世纪晚期建造的圣地亚哥主教堂的门廊。这些照片被用以补充观众举办的模型展。就像替拉斐尔草图拍摄的照片那样,它们也是由阿伦德尔协会出版发行的。由于中世纪建造的这座门廊被隐藏在后来建造的教堂西立面之后,在汤普森拍摄之前,它几乎不为人知。事实上,阿伦德尔协会出版的这些图片为它赢得了在中世纪艺术史上的地位。(15)
不过,较之于此,摄影的影响还要深远得多。1855年,汤普森赶赴图卢兹(Toulouse)拍摄朱尔·松列奇(Jules Sonlage)的749件藏品,其中许多都源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这是已知的最早使用摄影来充实博物馆收购方案的实例。这些照片被一一编目,还被安排在马尔博罗展厅(Marlboro house)中展出,为的是获取政府的支持,以便购置藏品。(16)先通过照片来评估有意向购买的藏品,然后再校验原作,从此往后,后摄影博物馆一直沿用此法。
一旦购得了原作,南肯辛顿博物馆便巧妙地运用摄影和博物馆的印刷目录,奠定了安德烈亚和卢卡·德拉·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还有乔万尼·皮萨诺(Giovanni Pisano)等人在艺术史上的声望。博物馆向公众出售藏品照片,并且选出其中一些,送至地区性艺术院校进行交流。(17)这些做法成绩斐然,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期,照片已经供不应求了。(18)
后摄影博物馆的成功
至少在伦敦,前摄影时代的博物馆要适应这种新手段还有重重困难,这一点很重要。19世纪40年代之际,地处逼仄陈旧角落里的大英博物馆,既想摆脱自己那“精英人士的珍品馆”形象,(19)又打算把数目日增的藏品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推而广之。摄影——就像南肯辛顿博物馆即将证明的那样——是有能力满足这两个目的的重要工具。
那时候,摄影早已风靡伦敦和各地,尽管在大英博物馆里对它时有提及,而且早在1843年,塔尔伯特本人便着手开始了试验,但是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理事们才设立了摄影工作室。南肯辛顿博物馆在这项当时颇为新颖的技术上占据了领先的地位,恰恰在这时候,大英博物馆才开始对此有所回应。
为了管理新的工作室,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们任命罗杰·芬顿为博物馆的首任专职摄影师。芬顿之前是位律师,他是当时最杰出、最有影响的摄影师之一。1855年,在王室的资助之下,他受命如实记录克里米亚战争。他在那里拍摄的战斗图片现在成了他最知名的作品,它们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组战地照片。
芬顿是早期最为活跃的摄影倡导者和实验者之一。他还是伦敦摄影协会,即现在的皇家摄影协会的首任荣誉干事,并且在法国的同类研究团体中出任该协会的代表。
不过,1859年,芬顿在大英博物馆中扮演的这一开创性的角色就这样匆匆地、不愉快地结束了。理事们理解不了摄影的重要意义,而且又不愿投资于此,认为芬顿不过是个“临时的技工,能做的只是些有限的小事”。(20)最终,伦敦的博物馆摄影这一行掌控在了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工作室手中,而且直到1927年,大英博物馆才雇人接续这项工作。(21)同样,伦敦的国家画廊直到20世纪才拥有专职摄影师。(22)
在北美,由于绝大多数艺术博物馆都是在摄影发明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所以盛行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起来的大多数博物馆——包括波士顿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华盛顿特区的康克兰美术馆(the Corcoran Gallery)——都有意把自己打造成科尔的南肯辛顿那样的博物馆。多数博物馆都把摄影纳入到了规划之中。
比如,1869年,查尔斯·卡拉汉·珀金斯(Charles Callahan Perkins)曾提议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建立一座秉承南肯辛顿特质的艺术博物馆”。这座新馆便是波士顿美术馆
珀金斯写道:“因为它是以教育为目的的,而且不时会有财政上的困难”,新博物馆的藏品就必须是既能迅速筹集,价格又比较低廉的。“艺术原作数量稀少、价格不菲,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而上佳的绘画摹本,也和原作一样数量有限、价格昂贵,所以,我们局限于购置用石膏以及类似材料摹制的建筑构件、雕塑、钱币、珠宝、徽章、铭文、翻拍的18世纪前绘画大师的画稿照片,较之原件,它们毫不逊色,而且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23)
渐渐地,摄影开始影响博物馆对待艺术以及向公众展示艺术的方法了。19世纪初期,公众所见的艺术作品几乎没有破损明显、残缺不全的。残破的希腊罗马雕塑总会被修补完整,这些有时候是由阿尔波特·托瓦尔森(Albert Thorvaldsen)那样的著名新古典主义雕塑家制作的,有时候则来自一大批零零碎碎的雕塑残片。油画上的破损处总会被重新描绘,掩盖起来,或者迎合时尚,把画面裁小或放大,以适应新的展览。
到20世纪初,至少在艺术博物馆里,这些做法早已不复存在了。一门新兴的科学的艺术“保护”学科,迅速地取代了艺术修复。而经过专门培训的艺术保护新手们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便是摄影——不仅包括传统摄影,还有X光片、红外线和紫外线照片——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的摄影手段丰富充实了后摄影博物馆的美学观,这种观点是要尽可能地去除先前修复的东西,只留下有助于理解作品的最初状态,并且有助于保护它不致遭到进一步毁坏的部分。博物馆展出的艺术品不仅残缺不全,往往还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如今,这些都被看做是证明藏品年代、独创性和真伪的重要标志。
因此,即便后摄影博物馆以原作代替照片和其他复制品来布置展厅,摄影的直接影响仍然左右着展示的方式。颇为讽刺的是,照片巩固了原作本身的重要性和价值,以至于主管们非原作不可。在波士顿美术馆以及不远处位于哈佛大学校园里的福格艺术博物馆(the Fogg Art Museum)这些“革新性”机构的展厅里,原先具有“教育意义”的照片和石膏仿制品渐渐消失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摄影、购藏、保护、出版和发行这一系列复杂的环节,成了后现代摄影博物馆固定的运作体系,而且还成了所有艺术博物馆的榜样。19世纪五六十年代间,由科尔打造起来的教育和传播体系本身就成了现代教育性艺术博物馆的基本模式。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和教学凭借的主要是照片和印刷书籍,随着它的不断发展,摄影成了理解、阐释和评鉴艺术的主要手段。
新的高低座次
最后,再回到哈斯克尔就德拉罗什和阿姆斯泰德各自的艺术经典而作的比较上来。人们很容易注意到的是,阿姆斯泰德省略的那几位德拉罗什名人堂里的艺术家——包括乔尔乔涅(Giorgione)、凡·代克(Van Dyke),以及除伦勃朗以外的所有荷兰画家——他们的作品不能用黑白照片很好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阿尔伯特纪念碑上的新来者,包括安格尔和卡拉奇兄弟,他们的作品用这种方法可以表现得更好。
不过,阿尔伯特纪念碑上真正的变化在于新近对杰出的意大利大师们的重视——换言之,就是那些作品被翻拍、收藏,并且经后摄影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支持者出版发行的画家。(24)因此,在后摄影时代,跃居艺术顶峰的是那些通过照片而广为人知的画家和作品。
本雅明(Benjamin)在《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一文中——该文声名显赫,俨然已是一则经典——指责摄影复制品缺乏原作的“光晕”(aura),即“它在时空中的存在,它在自己恰好出现的地方那独一无二的存在”。于是他总结说:“这个机器复制的时代所丧失的便是艺术品的光晕。”(25)
早在19世纪90年代,本雅明尚未成年之际,摄影的地位就已经改变了。当时工艺美术运动大行其道。机器制成品曾因为无可挑剔的完美而备受推崇,如今只好让位于热衷手工制品的新趣味。像照片那样,机器制成品的文化价值已经降低了。工厂产品粗陋,而工匠制品质优。
实际上,在艺术的光晕这个问题上,本雅明完全颠倒了因果。恰恰是机器复制品——照片——赋予原作以光晕,就像机器成就了“手工制品”,消极成就了“积极”,数字技术使其潜在的对手“模拟”技术重获新生。
在摄影出现之前,无所谓是否“手工原作”,因为没有什么机器翻拍的原作照片。正如我们已经见证的那样,恰恰是复制品赋予了原作以地位和重要性。一件艺术品被复制得越多——而且复制品生硬呆板,生气尽失——原作就会越发重要。
艺术家们首先认识到摄影给那些受其庇护、一再被复制的作品带来的变化。像米莱(Millet)的《播种者》和《晚祷》之类的油画作品,被大量复制成戈培尔(Goupil)照相平版印刷品,这些画很快便跃居为宗教文化遗产。
“昨天,我和艾美莉亚(Amelia)一道去参观了米莱的展览,”1887年,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o)在给儿子卢西恩(Lucien)的信中写道:
人真多啊……我撞见了Hyacinthe Pozier,他和我打了招呼,说他刚刚经历了深深的震撼,他泪流满面,我们还以为是他的哪位亲人过世了……根本就不是,《晚祷》,米莱的这幅油画使他情绪激动。这张画算得上是画家最糟糕的画了,如今花50万法郎也买不到,对那些把它团团围住的附庸风雅之辈来说,就是有如此强烈的道德感染力:他们在画跟前争先恐后、拳打脚踢!这是毫不夸张的事实……这不禁使人对人性产生了悲观的看法;愚不可及的多愁善感,不禁使人想起18世纪的格瑞兹(Greuze)风潮……真是无知!真叫人伤心。(26)
反过来,很少被复制的艺术品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未经拍摄、未加发表的艺术品,前途未卜。实际上,在后摄影博物馆的光晕笼罩之下,未经拍摄的作品根本谈不上存在与否。在摄影发明之后的这段艺术史中,发现并且出版这样的作品差不多就是一种再创造了。
S.N.贝尔曼(S.N.Behrman)在那部描写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商约瑟夫·杜维恩(Joseph Duveen)勋爵的传记中,记录了杜维恩为讨好自己那些拥有百万身家的藏品买家,向他们奉送根据对方的藏品打造的制作考究、插图精美的图录。“有一年圣诞节,”贝尔曼写道,“杜维恩替克雷斯(Kress)准备了一册装帧华丽的书,叫做《塞缪尔·H.克雷斯德绘画、雕塑及其他藏品》(The Collection of Paintings,Sculptures,etc.of Samuel H.Kress)。书本相当沉重,不易搬动。尽管如此,它的题目却多有夸张不足之处,因为该书收录的只是杜维恩卖给克雷斯的藏品的来龙去脉和图片复制品,忽略了克雷斯从别处收购的大批藏品。因为对杜维恩来说,那些购自其他商户之手的藏品是不存在的。”(27)
在后摄影时代里,印刷的艺术书籍已经取代了阿尔伯特纪念碑基座那样壮观的展示方式。这些书籍展现给世界的是一批受专家们推崇,认为“重要”的作品和艺术家,而书中的插图则构成了正统的艺术经验。自19世纪末以来,几乎所有关于艺术的本质和意义的论断都是直接通过摄影这种方式,或者在摄影的影响下形成的。
无以计数的照相复制品不仅远远没有减少艺术品的“光晕”,反而为之增光添彩,最终使博物馆从摄影出现之前存放艺术品的帝国库房和珍玩室,变成面向大众的场所,与后摄影展馆相得益彰。即便是后摄影博物馆那雄伟、承载着象征意义的建筑,也反映了艺术从稀世珍品向具有宗教般强大力量的圣物的转变过程——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这股照片复制的力量。
后摄影霸权的衰弱
如今,我们已经步入了后互联网艺术博物馆时代。以前,艺术史学家们会说:“我的书本里没有,幻灯库里也没有,所以它肯定不重要。”现在,他们的学生会说:“在网上没有,肯定就不存在。”
不知不觉中,价格低廉的数码影像出现了,万维网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两项技术可以简单便捷地修改、发布并且传播图像,这一切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落后的后摄影霸权。这同时改变了摄影的真实性。当图像处理软件价格便宜、使用方便,而且经过加工处理的图像十分常见的时候,照片就再也不能作为可视真相的标准了。
如今,博物馆认识到:替自己的藏品拍摄的那些照片从来就没有客观地展现艺术品,它们其实就是特定美学观的产物,小心翼翼地适应着摄影师及其雇主的口味和观念。实际上,博物馆中的照片是对艺术品的阐释,它们就像所有的艺术史文献那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通过“隐藏的相机:摄影文献和公共博物馆”这样的展览,主管们向公众传达了这些看法。(28)
以前,由于精品艺术博物馆的打造和藏品的结集出版耗资巨大、过程复杂,所以与艺术相关的资料便被束之高阁,只局限在博物馆、艺术学者和高级出版商这个独享特权的圈子中。而如今,只要可以连接上时新的计算机网络,任何人都可以获得那些资料。(29)在万维网上,任何人都能当一回博物馆主管或者艺术史家,提出自己对艺术内涵的独到见解,从博物馆网站还有成百上千其他网络资源上借用图片,还可以用与计算机相连的廉价设备扫描图片。
如今,大多数艺术博物馆都有自己的网站,但是,它们仍然有必要直接回应这些技术变革问题,调整展示和解读艺术品的基本方针。尽管大量与艺术相关的材料都被转换成了电子资源,博物馆用数字摄影来解读和评鉴艺术品的做法,如果不能说完全相同,那么也与19世纪末的时候利用“模拟”图片异曲同工。艺术博物馆推出的在线资源和其他数字出版物仍然酷似印刷目录和展览手册,只不过增加了些许技术上的改良,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新兴的博物馆网站不过是后互联网博物馆的雏形。就像150年前遭遇摄影时那样,艺术博物馆全方位地步入了崭新的电子世界,正朝着新颖、留待定论的方向前进。就像摄影出现的时候那样,数字技术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艺术手段,一种解读和发布艺术作品的新方法,并且还是对艺术本身发起的特殊挑战。不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拟时空中,新的南肯辛顿博物馆或许已经在着手筹划,因为显然博物馆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已经终结,而另一个时代才刚刚开始。
*本文译自:Peter Walsh,Rise and Fall of the Post-photographic Museum:Techn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t,in Theorizing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A Critical Discourse,Fiona Cameron and Sarah Kenderdine(eds),Cambridge Ma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7。
注释:
①见Michel Frizot,Photographic Developments,收入 M.Frizot 编A New History of Photography,Cologne:Koeneman,1998,p23。
②同①。
③见Malcolm Baker和Brenda Richardson编,AGrand Design:The Art of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New York:Harry N.Abrams and The Baltimore Museum of Art,1997,p139。
④见Charles Rosen和Henri Zerner著,Romanticism and Realism:The Mythology of Nineteenth Century Art,New York:Viking Press,1984,p99,p110。
⑤同①,p28。
⑥同⑤。
⑦Susan Sontag,On Photograph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2,p350。
⑧Walter Benjamin,The Works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收录在H.Arendt主编的Illuminations当中,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p226。
⑨Charles Rosen and Henry Zerner,Romanticism and Realism:The Mythology of Nineteenth-Century Art,New York:Viking Press,1984,p99。
⑩关于复制版画原先的地位、衰落,以及最终的消失,详情可参考Marjore B.Cohn,Francis Calley Gray and Art Collecting for 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1)艺术品摄影图片的早期的历史,可以参考Anthony Hamber,The Photography of the Visual Arts,1839-1880,1989,第一、二、三以及第四部分。
(12)见Heilbrun,Around the World:Explorers,Travelers and Tourists,收入M.Frizot编A New History of Photography ,Cologne:Koeneman,1998,p156。
(13)在帝国主义分崩离析后的欧洲,这些藏品酿成了政治问题。荷兰把自己在殖民时期收藏的大部分艺术品归还给了印度尼西亚,而希腊则仍在为收回长期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尔金大理石(Elgin Marbles)而不断努力。这类藏品的帝国主义本质,已经在就艺术博物馆展开的批判性研究中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14)同③,p137-138。另见John Physick,Photography and the Southern Kensington Museum,London: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1975。
(15)同③,p129-130。
(16)同③,p153。
(17)同③,p139。
(18)见Christopher Date和Anthony Hamber著,The Origins of Photography at the British Museum,1839-1860,收入History of Photography,1990,14,no.4 (October-December),p309。
(19)同(18)。
(20)同(18),p322。
(21)同(20)。
(22)同(11)。
(23)见Walter Muir Whitehill,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A Centennial History,Cambridge,Mass.:Havard University,1970,p9-10。
(24)Francis Haskell,Rediscoveries in Art:Some Aspects of Taste,Fashion,and Collecting in England and Fra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p17-18。
(25)Walter Benjamin,The Works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收录在H.Arendt主编的Illuminations当中,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p220-221。
(26)Camille Pissarro,Letters to His Son Lucien,John Rewald和Lucien Pissarro编,第三版修订版,Mamaroneck,N.Y.:Paul P.Appel,1972,p110-111。当然,米莱的素描不为公众所知晓,而戈培尔复制的《晚祷》销路很好。在好几次讲座当中,我采用自己多年前在卢浮宫拍摄的一张照片来说明光晕产生的过程。照片上展现了保护《蒙娜丽莎》的昏暗玻璃柜前那争先恐后的巨大人流,而对《岩间圣母》及悬挂于其周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却视而不见。我也曾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尽管卢浮宫是世界上参观率最高的主要几家博物馆之一,但它也是其中观众最稀疏的展馆之一,原因在于:巨大的人流专注于那三件被反复复制的作品,而忽略了其余的作品。
(27)S.N.Behrman,Duveen,New York:Random House,1952,p99-100。
(28)例如,可以参考Born 1998,其中探讨了1997年在伦敦举办的这次展览。自1990年以来,类似的展览已先后在美国的博物馆中举办,其中包括波士顿美术馆。
(29)关于新技术如何打破知识权威,详情可参考拙著《衰弱的典型:网络、专家以及信息霸权》(That Withered Paradigm:The Web,the Expert,and the Information Hegemony),收入Henry Jenkins和David Thorburn编Democracy and New Media,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