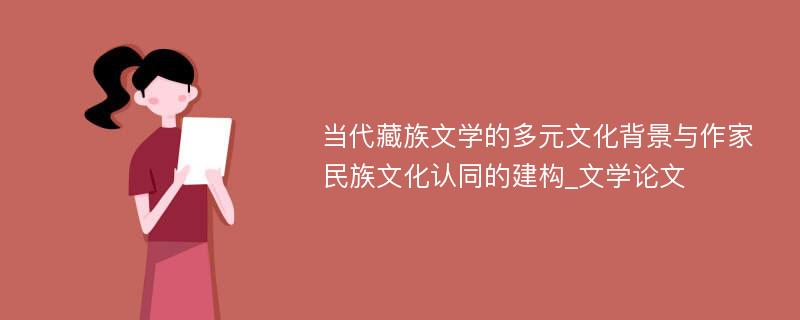
当代藏族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与作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民族文化论文,文化背景论文,当代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04)06-0029-04
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表达,蕴藉着深沉的民族记忆,体现出鲜明的民族 文化特性。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作家的多元文化背景对其创作的影响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这些变化是以近二十年来民族文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少作品和作家受到 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引起的。其中显见的一个例子是,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获茅 盾文学奖,并成为唯一入选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的当代精典。《中华读书报》(200 3年9月4日)有消息介绍说,“据了解‘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几乎囊括了中外现当代 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有鲁迅、老舍、冰心、茅盾、巴金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 作,有杨绛先生的译著《堂吉诃德》,已故诗人陈敬容先生的译著《巴黎圣母院》、朱 生豪先生的译著《哈姆雷特》等。而阿来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则成了唯 一入选的当代经典。”藏族作家阿来与鲁迅、巴金、茅盾以及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被 置于世界经典作家的行列里,我们不得不思考,阿来以及当代藏族作家的书写何以在多 元文化背景中展开?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藏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族文学步入了她的当代发展 阶段。建国之初,藏族文学中涌动着“忆苦”“感恩”的热潮,“讴歌新生活”“融入 社会主义大家庭”成为藏族文学的基本主题。这一时期活跃在藏族文坛的大多是民主改 革后成长起来的一批藏族作家,如饶阶巴桑、意西泽仁、嘎藏才旦、益西单增、降边嘉 措、格桑多杰、班觉等人,大都经历了旧社会的苦难,他们的创作成为西藏历史的见证 。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中高原人生的写照。概括地说,新中国第一代藏族作家的创作书写 的是社会制度转型带来的新生,他们还无暇顾及传统文化的优劣,他们面对的文化背景 相对单纯。扎西达娃、阿来、央金、色波等则是民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藏族作家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步入文坛,他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直面传统和未来。面对时代的 跨越和改革开放时期国际舞台上“中国形象”塑造的需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热 潮涌动,当代藏族作家开始对自己安身立命的民族文化进行反思,从民族精神的提升、 民族发展的高度思考藏族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并在各种文化面前,适时适度地调整自身 的心态,重塑自己的文化身份,藏族文学从民族本土土壤中滋生了强烈的现代意识,并 试图与世界格局下各种现代意识平等对话。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当代中国语境里的现 代性概念歧义丛生,现代性的历史发展在中国特别在藏区是以现代化为主要动力,以现 代化为主要关怀,这样的现代性诉求实质保留了前现代的胎记,从社会生活的一般面貌 到思想文化的演变,到个人身份认同,都可见到一些传统的、天人合一式的价值与规范 。藏族文学的当代发展必然体现出社会现代性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 上崛起的高原魔幻现实主义,成为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并不偶然,它不仅仅是西方文化 的接受体或派生物,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藏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痛切反思和重新书写。藏 族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对于整个中国主流文化而言,带有边缘性,阿来、扎西达娃等 藏族作家对西方非主流文化作家的关注,除其写作技巧的可资借鉴外,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的语境成为观照民族作家创作的重要参照,作 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创作更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正如阿来所 说:“因为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的非主流特性自然而然让我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做出独特、真实的表达。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也给了我很多的经验。比如辛格与莫瑞森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何讲述有关鬼魂的故事。例如,从菲利普罗斯和艾里森那里看到他们如何表达文化与人格的失语症。我想,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来说明文学如何用交互式影响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不同国度、不同个体身上发生作用。”[1]
加勒比黑人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说过这样的话:“文化 身份就是固定的本质,那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内在的 、历史未给它打上任何根本标记的某种普遍和超验精神。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我 们可以最终绝对回归的固定源头。当然,它也不是纯粹的幻形。它是某物……它有历史 ……过去对我们说话。但过去已不再是简单的、实际的过去,因为我们与它的关系,就 好像是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一样,总是已经是‘破裂之后’的关系。它总是由记忆、幻想 、叙事和神话建构的。”[2]借用霍尔的观点看,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不能再继续沿着 过去“本质性”的文化身份去重构民族文化身份。阿来等藏族作家在建构自己的文化身 份时,至少应考虑四种“在场”关系:即“藏族原初文化的在场”、“汉文化的在场” 、“中国的在场”、“世界的在场”。
“藏族原初文化的在场”:即中国境内的藏族不仅聚集在原住地青藏高原,由于中国 历史上的战争、迁徙和商业贸易交流,使整体性的未被异化的本原性(原初性)藏族文化 在与其他民族的杂居融合和历史征战中遭到破坏,在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等地亦有 散居的藏族群落,他们告别了自己的原初文化,具有整体性的原生态的藏族文化只存在 于藏民族的神话、民间故事、风俗风情等各个方面,逐渐成为一种隐性的、不自知的存 在,族群中的每个成员只能在日常生活事象中部分地感受到原初民族文化地隐性存在。 这种隐性存在的民族文化是藏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民族文学得以枝繁叶茂的根,当代藏 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应不断挖掘和表现藏民族的文化之魂。
“汉文化的在场”:契丹人在公元10世纪就把生活在中原的中国人称为汉族,《辽史 ·百官志序》说“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朱熹《通鉴纲目》“奉 蜀国为正统,以魏、吴为僭越”,汉为正统的认识广泛存在于中国文化中。汉文化成为 显性的、实在的存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文化常常代表着权力的主导方,构成了 对藏族等少数族群过度言说的文化“霸权”,历史上中国境内地域沙文主义的氛围曾经 是浓厚的,中原地区的住民曾把“蛮”、“夷”、“狄”、“戎”等颇不雅驯的称谓赠 给了自己的周遭族群。因之,汉文化在大多数历史阶段作为主流文化往往对少数族群文 化造成某种抑制。
“中国的在场”:中国的在场是古老的在场。在中国长期管辖的疆域内除了儒教文化 外,尚有伊斯兰教文化、喇嘛教文化、萨满教文化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各民族交往 的历史已上演了上千年之久,这些不同文化在历史上既有过融合也有过冲突,自近代以 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所以“中国的在场 ”是一个等待着中华各族群去开拓、重构的“新世界”。是当代藏族作家施展抱负的大 舞台。
“世界的在场”,就是“全球在场”:全球化已成为21世纪无法回避的世界潮流。全 球化不仅仅意味着同一,更裹挟着冲突。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 后世界上最大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儒教文化之间 的冲突。一切差异性和多样性相互切磋、杂交,以“一种综合动力跨越一整套文化形式 批判地占用主导文化的主符码的各种因素,将其混合起来,肢解给定的符号,重新阐述 其意义。”[2]
上述四个在场交错缠绕,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成为当 代藏族作家面对的文化大语境,对当代藏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产生不容忽视的影 响。这些在场关系既是当代藏族作家进行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动因,也说明了民族文化 身份建构的艰巨性、相对性和复杂性。
藏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建构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口号,首先遭遇的就是如何看待本民族的 传统文化的问题。“……身份决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 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 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 现。[2]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与民族文学特质两者本身就是同一性质问题的不同角度的 评说。面对这重重在场关系,当代藏族作家如何通过文学实践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成为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简单回顾二十年来藏族文学创作和批评,我们就不难发现, 在评说藏族文学时,人们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文学创作的“民族性 ”问题,对“民族性”作少数民族意义上的藏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的理解,还是作“ 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性”的理解?以阿来为例,《尘埃落定》在世纪末文坛上掀 起的浪潮至今未完全消退,各种评论文章纷至沓来,许多评论者多把目光聚焦在作品中 的宗教体验、藏民族历史、神秘文化以及作者对汉语的自如轻灵地运用。不难看出,这 些论说,仍然囿于对文本作藏民族文学“民族性”阐释上,可是阿来对此并不以为然。 他说,他欣赏评论界把这部作品称作“寓言式小说”的评价,他要面对现实中权利对生 命的制约,对掌权者和无权者的影响以至权利如何从“潜在的暗力”上升为“戏剧化的 冲突”乃至“血与火的拼争”之类的问题。他才选择了麦其世家所处的地域、时代和土 司制度以作为能反映普遍的个别。他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如果要揭示“一 般”的话,不妨找个小的地方来描写,而麦其世家身处的土司制度中,土司们把自己看 成“国王”一般。“土司是一种外来语,在我们的语言中,和这个词对应的词是‘嘉尔 波’,是古代对帝王的称呼,所以麦其土司不会用领地这样的词汇,而说‘国家’。” 从阿来自己的阐释,我们有理由相信,阿来所言说的文学“民族性”并不囿于藏民族文 学,而是通过藏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彰显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性”。鉴于此,我不同 意有藏族评论者所持的“藏族文学最广大的读者是藏民族,藏族文学最终的裁判,也是 藏民族”的观点。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当代文坛的轰动以及最终摘取茅盾文学奖就是 最好的证明。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以藏民族题材写作的非藏民族作家马丽华、 马原等的创作情形:这部分作家作为异文化者,他们感念西藏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他们在藏生活的经历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对西藏的感情,常使他们不是用肉眼去感受西 藏,而是用心灵,用心灵之笔去书写。毋庸讳言,作为异文化者,他们更多的是从日常 事象去感知藏民族生活,他们常常感到一种无所适从的困惑。看到年轻人舍弃一切去印 度朝圣,去布达拉宫,去山洞修行这样的事项之后,便不知不觉中产生这样的疑虑:“ 如果没有来世呢?”他们不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异文化者身份去盲目欣赏,这种创作 心理上的转换,与其说是汉民族文化身份所决定的,毋宁说是“中华民族”意义上的“ 民族性”的表现。马丽华们的转换体现了基于“中华民族”意义上的现代性诉求,和本 土作家扎西达娃等通过文学书写传达的现代意识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面对世界全 球化和本土化的共存趋势,藏族文化的民族性成为一个有待重新检验的存在,扎西达娃 的创作已触及到这一深层问题,但是,这一问题绝非一个藏族作家可以单独解决的。许 多优秀的文学工作者已经发现,“民族性”固然是民族文化(文学)生存延续发展的基础 ,但世界性、共同性、现代性的或缺不唯是民族文化(文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障碍 。也会窒息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文学)更应在世界文化格局中自我认 可、自我建构。扎西达娃们不断寻找表现“民族性”、“民族魂”的突破口,在拉美作 家那里受到了启发,和内地作家的“寻根”热潮相呼应,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和 对荒诞的热衷,不是扎西达娃的目的(当时的评论大多从扎西达娃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的模仿上言说)。恰恰相反,扎西达娃执著的是对藏民族文化之魂的追求,系在皮绳扣 上的是一颗痴韧、狂放、善良、瑰丽、渴求幸福、向往自由而又沉重、苦涩蒙昧愚钝等 令人钦敬又令人心酸、充满活力又积淀惰性的高原民族灵魂,(《西藏,系在皮绳扣上 的魂》)这一形象富有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一系列作品中扎西达娃有意无意地 将自己的内心矛盾传染给了其笔下的人们,并将其永远悬置在追寻“民族性”的“途中 ”。《泛音》中次巴、旦郎对民族“音乐魂”的追寻又一次强化了这一象征意义。次巴 并不看重外在的诸如穿藏族服饰、唱藏曲就能代表真正的藏族音乐,藏族音乐如同藏族 的祖先的声音,在当今的西藏显然早已不复存在,但却隐匿在藏民族生活的本身,成为 一种无形的存在。如果扎西达娃、阿来们仅以这种表达来进行现代与传统、民族性与现 代性的诉求,那么免过于平板。他们深知一个民族不能墨守一个静止不动的传统并生存 下去,藏族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如何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对这个传统 是维护还是重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化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为当代藏族人 乃至中国人不可磨灭的主体记忆的一部分,藏族文化现代性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 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某种均衡发展?还是对自己的文化精神进行通切反省和重新书写? 阿来坦言,“我很反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写的《 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的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是全 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并不是哪个民族的专利。每个民族在观念上有所区别,但绝非冰 炭不容,而是有相当的共同性。这便是我们地球上生活的主体——人类。[3]
当然,我们可以把阿来这段表白看成他追求的至高境界。不论是扎西达娃还是阿来, 追求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必然要面对前文所述的几种在场。藏民族原初民族 文化的不完整性的隐性在场必然成为当代藏族作家殚精竭虑表现的重心,文化本身是一 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它有自己的基因、要素、结构、能量和生命链。藏族文化作为独立 的系统,决定了它不是被动的受器,而是具有选择、同化和创造内力的能动主体。当代 藏族作家并不一味去抵抗那些外在的、显性的他者文化,而是把其中的部分因素纳入到 本民族的文化中,在和其他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磨合过程中从他者文化汲取有益的 营养,化为自己的血肉,进而使自己得到充实、丰富,甚至积极的变革。历史上,尽管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可以强行在藏区实行某种制度(农奴制度、土司制度等),对发展近现 代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民主改革以来当代藏区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方面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现代化。21世纪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但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意味着同一性、共生性,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将出现愈来愈多的文化认同,但认同并不预示着不同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文化核心、文化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成员心灵中深入骨髓、体现着民族特征的东西,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又包括信仰和价值取向。事实上,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所遭遇的文化危机及文化身份建构的焦虑,主要是价值观念层面的问题,是精神文化深层的问题。一方面,当代藏族作家已清醒认识到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建构民族文化身份必须面对许多复杂敏感的问题,有必要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对文学的“民族性”进行反思,对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反思等,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要充分认识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复杂性、艰巨性。正是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当代藏族作家在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时,只有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转化、重构和创新的热情还不够,还应该考虑上述几种“在场”关系,扩展视域,在中华文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写作,在这一点上,藏族作家阿来乐于承认自己通过汉语受到的汉语文学的滋养,以及世界文学的滋养。但同时又指出其创作的《尘埃落定》应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视野中去审视。应该说阿来正是厘清了当下文化语境,认识到全球化并不是与民族化对立,全球化关照下的民族化才是充满活力的民族化。当代藏族文学应该既是藏民族的,也是中华民族的,还是世界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为傻子二少爷等一系列文学形象的塑造打好恰当的底色。
面对多元文化背景,当代藏族作家任重道远。既要大力挖掘民族文化中适宜于发展完 美人性的要素,通过民族文学,展示民族文化精魂,又要在重建中国文学、塑造“文化 中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既要信心百倍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又要增强本土认同;既 要借全球化话题和语境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又要利用本民族资源保持民族的审美经验传 统,以开创性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我认为,扎西达娃、阿来等优秀的藏族作家用他 们的创作比较好地实践了他们的追求。他们不约而同的在本民族的灾难与个人的精神磨 难之间,在共同的压力和个人独特的生命感受之间,在异域异民族文学的启迪和本民族 的现实境遇之间,找到了一条通往历史、传统和未来的路径。对于现实的观察和感受、 对历史的思考与反省更加丰富起来,凸显出较强的主体意识,从而使藏族当代文学成为 当代中华民族文学大观园里一株奇葩,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收稿日期:2043-06-22
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藏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作家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多元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尘埃落定论文; 阿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