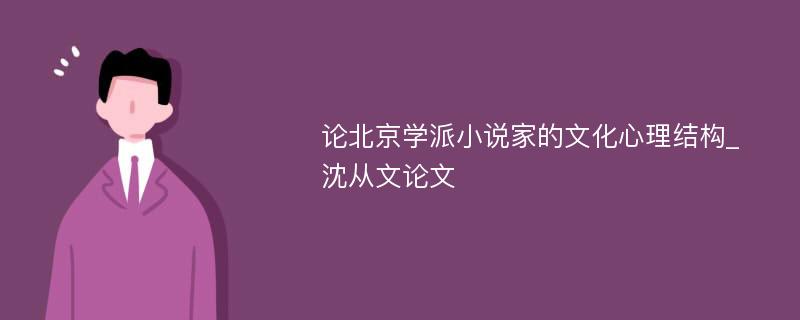
论京派小说家的文化心理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小说家论文,结构论文,心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2—0148—05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都接受过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现代中国中西方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和调和是极其复杂的,也决定了知识分子价值观念和历史观念上的矛盾和紊乱。在这个过去与现在、本土与外来文化各种层面、不同体系的互相渗透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往往存在着传统的因子,本能地抗拒着对异质文化的全面横移。即使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激进的反传统文化者,在心灵深处都保留了对传统文化的依恋情感。具体到京派作家,这个问题就更为明显。传统文化对京派作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检讨某一具体的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及其在现代的处境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它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有生命的东西,表现在该文化涵育下的绝大多数个人的思想行为之中,也表现在他们的集体生活之中”(注: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本文拟以京派小说家为个案,分析、探讨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及其人文理想的种种表现方式,以求更完整地把握京派小说的复杂性和它对传统文化的承继关系。
一
京派作家虽然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个性思潮和民主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但他们对传统文化大多有一种直接或间接的精神牵连,这不能不联系到他们的出身背景和生活道路。像凌叔华、林徽因都是大家闺秀,出身名门望族,自幼受到正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即使在她们长大后接受现代文明浸染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传统东方女性的矜持。朱光潜生于安徽桐城,深受桐城派文学的影响,接受过传统教育模式的严格训练,而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更和传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沈从文是由湘西保留的楚文化的环境下哺育的,“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注:沈从文.长庚〔A〕.沈从文文集〔C〕.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尽管沈从文不具有其他京派作家那样的家庭背景和文化熏陶,没有系统地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但后来他依靠顽强自学,对传统文化具备了较高的鉴赏力。汪曾祺的精神命脉中融入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染,他曾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希望寄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糅在一起。”(注:汪曾祺,施叙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J 〕.上海文学,1988,(4).)这种审美方式正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 而京派小说家的重要代表废名对传统文化的接受最为明显,但同时也最为复杂。最了解他的周作人回忆说:“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本国的杜甫、李商隐、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在这一时期我觉得他的思想最是圆满。……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跌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己。”(注:周作人.药店杂文·怀废名〔A〕.)这些都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京派小说家在心灵深处与传统文化一种割不断的依恋情感。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特征。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内倾性格,有其内在的力量,“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和道家的‘自足’等精神上面,佛教的‘依自不依他’也加强了这种意识。若以内与外相对而言,中国人一般总是重内过于重外。这种内倾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曾显露了不少不合时宜的弊端,但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而不断却也是受这种内在的韧力之赐”(注: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这种内倾的表现就是中庸、和谐、 节制的文化心态。京派小说家的文化性格多通达、从容、中和,较少激烈的态度,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世俗化的审美倾向,很少反映尖锐的时局冲突,而且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具有一种雍容、悠然的处世方式。像汪曾祺的《戴车匠》、《鸡鸭名家》,沈从文的《三三》、《边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的人物多半持有一种淡泊的生活态度,他们更看重的是其自身的德性化追求,追求自身的完善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陈聋子、渡船老人等大都经历过生活的风浪,但他们早已忘却了对生活的非分之想,只求在极自然的状态下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尤其是汪曾祺的小说,更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在一种温婉、恬淡的文化心态背景下,把自己的心完全沉浸到民族的衣食住行之中,其中的人物大多具有重义轻利、乐天知命、爱众爱人的传统人文主义理想,如小说《异秉》中的一段描写:
“每天必到的两个客人早已来了,……他们已经聊了半天,换了几次题目。他们唏嘘感叹,啧啧慕响,讥刺的鼻音里有酸味,鄙夷时披披嘴,混和一种猥亵的刺激,舒放的快感,他们哗然大笑。这个小店里洋溢感情,如风如水,如店中货物气味。”
小说中的这种生命既不庄严也不浪漫,但正是在这种舒缓的叙述风度中,呈现出一种朴素、自然的生命本色,这难道不是中国传统伦理观照下的依恋情感吗?
京派小说中的这种儒家人文理想还表现在对伦理道德层面的思考和把握。儒家一方面强调“为仁由己”,即个人的价值自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伦秩序,要求控制自我的欲望和遵从道德规范,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即是一例。京派小说在对伦理的挖掘中,更多地表现出了挖掘者本身固有的传统伦理制约,突出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尤其是像林徽因、凌叔华这类知识女性,虽然受到了“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鼓舞,有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愿望,但一旦问题落到诸如伦理道德时,难免顾虑重重,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观便流露出来。京派小说在反映爱情、婚姻等涉及两性关系和家庭秩序时,大多写得矜持、节制,同当时文坛盛行的这类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鲁迅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评论凌叔华的小说时便有一番十分中肯的意见:“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A〕.)如她的《酒后》写一个女性倾慕来她家做客的青年男子,要求丈夫允许她吻一下这个客人,但当丈夫同意她的要求后,她却没有了这个勇气,传统的伦理观终于压倒了心中的欲望,这正是儒家人文理想的重要实质。其他的京派小说家,即使像沈从文这样有着独特生命观的作家,在描写爱情时大都适可而止,较少放纵的情欲。这虽然避免了诸如张资平、叶灵风等海派作家那种赤裸裸的情欲描写和肮脏的色情文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又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对时代精神特征的深入揭示,它在个性解放的表现上就远不如郁达夫、冯沅君、汪静之等人的热烈、大胆,因而影响也就小得多,极大地限制了其切入人性、切入生命的深度,导致以“道德化”削弱了现代意识,这是京派小说所付出的一个沉重代价。
二
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融合了儒、释、道精神,形成了一套既稳固又开放的体系,使其内在的精神底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效用。其中的“入世”和“出世”便是这种文化性格的两面,既对立又统一,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往往构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处世的人生哲学。京派小说家同样有“入世”和“出世”所组成的双重人格。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已经和“五四”时代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他们所面临的世界,正是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而日渐式微,但新的人文理想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没有先驱者的那种沉重的心理负荷。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缺乏执著、明确的政治理想和忧患意识。恰恰相反,京派小说家仍然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入世精神,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表示了强烈的关心和担忧,对国民党政治上的独裁、专制严重不满。例如沈从文在国民党实施文化专制政策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禁书问题》等含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章,介入了当时的中国现实。针对当时的人性堕落等负面因素,沈从文也忧心忡忡,大声疾呼,这都是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面,他把自己的文学作品看成是拯救民族灵魂的良药,“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注:沈从文.废邮存底·元旦日致《文艺》读者〔A 〕.沈从文文集〔C〕.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忧患之情跃然而出。萧乾、废名、林徽因、凌叔华等人也并没有真的超然于社会现实之外,他们的眼光仍然深情地注视着民族的危亡局势和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从他们的作品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就拿隐逸气最为浓厚的废名来说,他在20年代的小说创作也还反映了社会现实,正如周作人所说:“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是现实。”(注: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A〕.)废名早期的小说对普通人民满怀挚爱之情, 对农村落后的现实亦有较真切的揭示,到了抗战时期,他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表现了很强的民族气节。至于沈从文在《长河》中所表达的对当局者民族歧视的不满,对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担忧,都无不表明他对这个民族的拳拳之心,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的作品并没有什么主张,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心。京派小说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到了一个契合点,其入世的精神代表了知识分子从此岸到彼岸的不懈追求和自我超越,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弘毅进取,才使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其悲怆和苍凉。
京派小说家出世的一面甚至比入世的色彩还要浓重一些,在他们内心深处仍保留了对传统的避世、隐逸等的欣赏和留恋,尽管京派小说家对社会、对人生都背负了很强的责任感,在“五四”的光照下满怀信心地走向社会。但严峻的社会现实给他们重重一击,放眼望去,中国仍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们所期望的人权、自由、平等都成了泡影,从而感到茫然和失落。对京派小说家有着较大影响的周作人就走着一条从叛徒到隐士的道路,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双重心态,有人评论说:“周先生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周先生十余年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二百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注:胡伟希等.十字街头与塔〔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周作人的这种情状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实境遇, 也是他们在政治高压下保持自己超然独立和精神自我放逐的必然选择。京派小说家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他们的力量还太弱小,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社会的乾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性格中“出世”的一面便占了上风,与剧变的现实日渐疏离。废名在20年代后期受周作人退隐思想影响甚深,对禅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终于“悟道”,整日隐居,周作人回忆说:“从意见的异同上说,废名君似很赞同我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话,他现在隐居于西郊农家,但谈到这些问题他的思想似乎比我更为激烈。”(注:周作人.永日集·桃园·跋〔A〕.)沈从文抱恨说:“一个写小说的算什么,想过许多,写了许多,其实连自己也救济不了,尽是些世上他所没有的东西。”(注:沈从文.一周间写过五个人的信摘录〔Z〕.)他的创作视角转向了湘西那古朴、 单纯的农村社会,旋律中交织着老庄崇尚宁静、自然的人生哲学,少了那种仗剑侠义的青春热血和愤世嫉俗。后来他干脆放弃了文学,转到中国古代文物、服饰研究,在一种恬淡的心态下来平衡着人生的苦闷,正应和了周作人的一段话:“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说闲话。”(注: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A〕.)李健吾自嘲艺术对人生的无关痛痒:“你捧出艺术,仿佛端着一盘点心,想做一番慈善事业。你会出乎意外遇见的尽是摇头摆手,然后从他们绝望的瞳仁,你照见自己也是肤黄肌瘦。”(注:李健吾.艺术家〔A 〕.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京派小说家千方百计地寻找着心灵的避难所,在沉闷的现实中以“出世”的退守方式继续维系着传统士大夫的高洁人格和艺术信仰,在其小说中也投下了浓重的影子。像废名的不少小说,都流露出很重的隐逸思想,读他的小说最好是在树阴下,恍然与现实隔绝:“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象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有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A〕.)废名曾计划用十年之力写的小说《桥》,几乎难以嗅到人间烟火,小说中的人物都安然自乐,他们所信仰的是紫云阁的尼姑所传授的返璞归真的哲学。在幽静的自然中寻觅顿悟,大有古代文人超然尘外的庄禅人格。汪曾祺小说与废名有相似之处,作品中的主人公对现实缺少直面人生的态度,神情散淡,随遇而安,这正是得道后的人生境界,他后来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更是渗透了庄禅哲学。京派小说的“入”与“出”的文化属性,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与矛盾心态,他们既渴望建功立业,又要保持精神自由;既想关注人生,又茫然不知所措;既想超越传统,步入现代,又难以割断精神上的牵连。总之,雄心勃勃的政治理想与避世者的洒脱、从容,和谐地得到统一,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性格和复杂心理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材料。
以上从文化心理方面论证了京派小说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今天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接触、碰撞、沟通更加频繁,面对着种种相同的社会、文化危机,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紧迫课题。京派小说家在此方面的探索或许不无益处,他们着力寻找着一种融合了各种文化体系的价值系统,单就这一点而言,就足以证明其对于重新建构人文理想的真诚。
〔收稿日期〕1999—04—16
标签:沈从文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周作人论文; 汪曾祺论文; 废名论文; 凌叔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