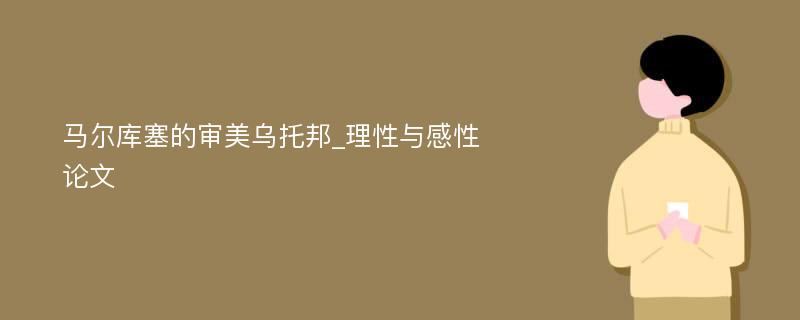
马尔库塞的审美乌托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马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马尔库塞是个异类。他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吸收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并以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重铸,以此构建自己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马尔库塞极其重视文学艺术的政治功能,可是,他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将文学艺术与革命相关联。在他看来,文学艺术的革命性并不取决于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也不取决于作家有否介入现实,相反地在于审美形式,在于作者、读者与现实的疏离,并通过与现实的疏离来实现感性解放,培植新感性,以此反抗现实对人的异化,反抗不合理的现实。
马尔库塞是在改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深刻理解人的生命存在与社会文明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上,来展开美学思考的。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社会文明是相抵触的。文明进步的先决条件就是克制、延迟本能的满足,并把力比多转移到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和表现中去,因此,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的生命本能持续受压抑的历史。
马尔库塞重新阐释了弗洛伊德的文明观,他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发掘出隐含着的社会学内容和批判的政治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观点无疑是有重大价值的,但是,他只是一般性地阐述了压抑理论,而没有深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中做具体分析,因此,也就没有对一般文明要求的现实原则与特定文明形式所要求的现实原则即操作原则做出区分,没有对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做出区分。在马尔库塞看来,一般文明要求的现实原则是以“缺乏”作为依据的。由于生产力低下、物质供应不足所造成的贫困和克服贫困所需的劳动,这就要求限制和延缓本能的满足。这种压抑是必须的,是基本压抑。而针对具体的社会形态来看,对人和自然的统治方式决定了现实原则的各种历史模式,它通过一系列社会机构、社会关系、法律及价值标准来实施压抑性控制,并且为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引进了附加的压抑即额外压抑。①额外压抑的提出,既预示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又很好地解释了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实境况。正是存在这种额外压抑,即便在富裕的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人类仍然没有摆脱社会压抑,相反地,社会控制却被组织得更为严密、更加彻底了。
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是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它不是由暴力,而是由技术来实施全面统治的。技术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社会管理、生产活动、生活活动、日常消费,凡是人的现实活动领域都无法摆脱技术的掌控。技术逻辑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逻辑。
“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②马尔库塞指出,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于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如今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包含在商品中。生产的组织、商品的享用,以及种种服务和娱乐,这一切所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并将个体与社会整体紧紧维系在一起,加强了“一体化”的过程,以致人们在讲自己的语言时,也讲他们的主人、赞助商和广告商的语言。同时,高层文化也被“俗化”了,它与现实的“间距”被弥合,文化中心变成了商业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并且这种思想灌输不再是宣传,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由此塑造了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塑造了单向度的人。人甚至降格为“人力资本”和“欲望机器”。“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它设计出一种历史总体——一个‘世界’。”③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外部世界和人的思想方式及行为模式的变化,它还通过人的需求体系的变化进而改变着人的本能结构,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似乎已经无法逃脱这种被异化的命运。“人的第二自然就如此阻碍任何变革,这种变革原本能够摧毁人对市场的依赖,甚至是人被商品所淹没和异化的状况。”④当人的现存世界,无论日常生活、政治谋划、生产活动、文化娱乐、话语交流,或者思维方式,都已经无可挽回地被同化、一体化,当人无可奈何地失却自身的自由并失却对自由的意识、对异化存在的抗争的时候,马尔库塞就不能不寄希望于文学艺术,他另辟生路,在远离尘嚣的虚构世界构建审美乌托邦,以此反抗现实。
在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中,文学艺术是作为现实对立面被建构起来的,它处在与现实相异在的虚构世界,是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拒绝和控诉,是对人的异化存在的抗争。
马尔库塞深入阐发了席勒的“美导向自由”的观点,进而指出:“人只是在摆脱了内外、身心的一切压制时,只是在不受任何规律和需要压制时,才是自由的。但这样的压制却是现实。因此,严格地说,自由乃是摆脱现存现实的自由,因为人只是在‘现实失去了其重要性’,其必然性也变得无关紧要的时候才是自由的。”⑤现实世界是不自由的世界,是充满着强制性法则的受压抑的世界,它为秩序、需求和必然性所制约;而文学艺术则是想象的世界,是虚构的世界,在这个与现实相异在的世界里,现实秩序失去了权威性,必然性失去了重要性,需求也因缺乏真实对象不再时刻促逼着人,当人处身这个没有外在束缚和压制的世界,人也就终于获得了自由的存在。因此,正是文学艺术所构建的审美乌托邦,为人保留了一片飞地,一个伊甸园,珍存着对业已失去的自由、和谐的记忆,因而也珍存着对不自由、受压抑的现实的反抗。
马尔库塞认为,文学艺术的质料和素材是来自现实的东西,文学艺术和现存社会共同分享这些质料和素材,无论它们被如何加以改造重铸,都依然是在给定的质料、素材基础上的变换;也正因为它们是现存社会共同分享的,文学艺术才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才能对现存现实做出抗议。“艺术就是现存存在物的一部分;而且也只有作为现实存在物的一部分,它才能对抗现实存在物。”⑥但是,在文学艺术中,质料和素材都脱离了它的直接现实性,成为某种与现实有着质的差异的东西,成为“另一现实”,即“异在世界”的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借助于审美形式,将自己与现存现实分隔开来,从现实的时间之流中超脱出来,升华为另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想象的异在世界。“只要这部作品是艺术,它就不是现实的东西,也就是说,小说不是报纸上的故事,艺术里安宁的生活并非活生生的生活,甚至流行艺术中的真实罐头盒,也不再是超级市场的东西了。艺术本身所具的形式,不仅与致力于去取消把艺术当成‘第二级现实’的努力对峙着,而且与把创造性想象力的真理改换为‘第一级现实’的努力也对峙着。”⑦文学艺术既非实存的现象世界,也非隐身于现象背后的所谓理式或本质,它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存在,是非现实的虚构世界,是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和升华。就在这超越现实的升华过程中,文学艺术终于摆脱现实束缚而获得了自律性,并成为人得以自由生存、人的生命本性得以解放的世界。
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这种悖论式关系恰恰最为有效地包孕着政治潜能。一方面,文学艺术源于社会现实,甚至它的审美形式以及艺术自律都是社会历史现象,是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成果。同时,文学艺术给予人的苦难以安慰,给予情感以净化,使冲突得以和解,似乎在客观上肯定着现存现实。然而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超越了社会历史的竞技场。由于这种超越,这种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使人摆脱现实原则的制约、摆脱功能性生存而成为自由的主体,也使文学艺术世界超脱现实的无尽过程而成为另一个不同于现存现实的虚构的异在世界,为人提供了全新的经验。它让人以新的面貌和方式来感受新的世界和经验,从中发现真理,转而批判社会现实、控诉社会现实。文学艺术只有潜入到社会历史之中,并且也只有通过审美形式实现审美升华,超脱现实世界,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其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因此,马尔库塞说:“艺术作品的结构,就是由肯定现实存在与控诉现实存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艺术意识形态与艺术真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⑧
马尔库塞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又对其进行了根本性改造。在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视野中,文学通过形式的陌生化来增加感知难度、延长感知时间,从而将人们惯常的“识别”活动转换为“感觉”活动,唤醒并更新被生活磨钝了的感觉,重新感知被日常经验遮蔽了的事物,让事物的感性特征充分展现出来,使“石头变得更像石头”。
与这种认识论的思想方法不同,马尔库塞是从存在论出发来看待审美形式的。马尔库塞认为,现实并非确定不变的客观对象,文学艺术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打开人的心灵的窗子,更新人的感觉,让人看到同一对象的不同容颜。审美形式对于人的意义是更为根本的,它不仅仅是更新人的感觉,更不是为了增加阻力、延长感觉时间,文学艺术通过审美形式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生存状态,让文学艺术和人从现实世界超升出来,从现实压抑中解放出来,让人的感性、想象和理性以日常所未曾有过的崭新方式得以敞开。审美形式是一种“异化”力量,它通过对被异化的现实和人的异化存在的异化,赋予世界和人以新的存在。因此,“文学艺术本质上是异化,因为它维系和保护着矛盾,即四分五裂的世界中的不幸意识,被击败的可能性,落空了的期望,被背弃的允诺。由于它揭示了人和自然在现实中受压抑和排斥的向度,因而曾是合理的认知力量……虚构的作品叫出了事实的名称,事实的王国因此便土崩瓦解;因为虚构之物推翻了日常经验并揭示了其残缺不全和虚假之处。但艺术只有作为否定力量才能拥有这种魔力。只有当形象是拒绝和驳斥已确立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时,它才能讲述自己的语言。”⑨文学艺术借助于审美形式、借助于虚构而获得新的秩序,一种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吻合的感性秩序,因此它所培植和蕴蓄的力量正是与异化现实相对抗的生命的力量,是拒绝和驳斥已确立的现实秩序的力量,是揭露并推翻日常虚假经验的力量。
马尔库塞和萨特一样,都十分看重文学艺术的政治批判功能,而且对文学艺术的审美形式、虚构本性和审美自律及其对人性的解放作用也有着相近的看法;但是,对于文学艺术政治潜能的具体认识,两人又有着明显差异。萨特虽然没有忽视文学艺术形式,但他更强调以作品题材的现实化来介入现实,批判现实;而马尔库塞则更注重审美形式。在马尔库塞看来,作家在作品中直接表现革命和批判现实,相反地,是缺乏真正的革命性的,因为作家本人就处身现实之中,受到意识形态的掌控,他的呐喊、叫嚣、反抗,只是在既成的理性框架中、在意识形态的牢笼中蹦来跳去,根本无法对现实作出有力批判,无法给予既定现实以致命打击,很快就被重新接纳并窒息于现实的沉寂中了。事实上,即使在政治内容完全缺乏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只有诗歌存在的地方,都可能存在具有革命性的文学艺术。政治在具有革命潜能的文学艺术中是可以缺席的,诸如兰波的诗歌、库尔贝的绘画,它们并没有表现政治性内容,却以其审美形式与现实决裂,因此也就抗拒了不合理的现实。是审美形式造就文学艺术与现实相疏离和相异在,而这种疏离和异在的程度,就构成文学艺术的解放价值。所以,马尔库塞说:“艺术不能为革命越俎代庖,它只有通过把政治内容在艺术中变成元政治的东西,也就是说,让政治内容受制于作为艺术内在必然性的审美形式时,艺术才能表现出革命。所有革命的目标——自由和安宁的世界——都出现在完全是非政治的媒介中,都受制于美和和谐的规律。”⑩
文学艺术有自己的语言,而且也只能以自己的语言形式去揭示现实。对审美形式的重视,使得马尔库塞甚至主张应该从“介入的文学”中摆脱出来,从实际生活和生产过程的王国挣脱出来,以审美形式赋予文学艺术不妥协的、自律的性质。马尔库塞和萨特都看到文学艺术的审美形式、虚构本性、审美自律对人性的解放和滋养,但是萨特出于对现实斗争的热忱却急急乎让人去介入现实,从事批判的事业了;马尔库塞同样对现实斗争充满激情,可是,现实政治斗争的挫折,现代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同化和异化,使得他更为关注革命主体本身,转而去思考文学艺术究竟是如何让人获得真正的主体性、如何培植人的新感性的。在他看来,唯独具有新感性的人才昭示着人类未来的希望。个体感官的解放是普遍解放的起点。
在全面异化的现代发达工业社会,工具理性成为组织整个社会的核心,人的感性则因长期压抑而被扭曲、变得麻木、死气沉沉的了,人已经被压铸成单向度的人。这些丧失生命力和主体性的人是无能力承担解放的任务的。
改造社会,首先要改造人本身,要恢复人性的丰富性,要重塑人的感性,为此,马尔库塞提出了“新感性”。“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11)人的新感性的获得是社会解放的前提,自由的社会必须植根于崭新的本能需求之中。在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中,新感性恰恰成为了连接文学艺术与社会革命的关键所在。
马尔库塞所说的新感性是与理性相和谐的。在康德美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尔库塞进一步作了阐发。他认为,人的想象力依赖于提供经验材料的感觉,并将这些感觉材料和感官对象及关系加以转化,创造出想象的自由王国。因而,想象的自由受制于感性秩序,不仅受制于感性的纯形式,而且受制于感性经验内容。从有机体结构的另一极看,想象力还受制于人的理性。即便关于崭新世界或崭新的生活方式的最大胆的想象,也仍然是由概念指导的,仍然遵循代代相传的、精织于思维发展中的逻辑历史。感性和理性都被纳入到想象力的构想之中。感官的世界是一个历史的世界,而理性是对历史世界在概念上的把握和解释。想象成为沟通感性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的中介,想象力变成生产性的,社会的重建找到了自己的向导。
文学艺术中的感性之所以是新感性,还在于生命本能被开拓了,它由性欲成长为爱欲。马尔库塞认为,人的性欲本能原先是多形态的,只是受到文明的长期压制才被逐渐限制在种族繁衍的实用功能和有限部位。当文学艺术为人提供了想象的自由王国,当压制不复存在,性欲就重新得到拓展而成为多形态的丰富的爱欲。爱欲是一种接受性,它倾向跟对象融合一体,因此攻击性只能成为从属性的了。“艺术作品从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中,产生出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这些理性和感性公开对抗那些滋生在统治的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和感性。”(12)
新感性是马尔库塞就文学艺术活动提出的卓越见解,但是,他的解释仍然沿袭了传统美学关于理性与感性相和谐的现成结论。想象力固然可以沟通感性与理性,而问题在于,当感性受制于理性,当想象接受了概念的指导,感性是否还能是自由的、不受压抑的?那种与感性相融合的理性又是一种怎样的理性?阿瑞提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感性与理性的融合。他将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活动视为原发过程(即无意识过程)和继发过程(即意识过程)的特殊结合,并称之为第三级过程。“第三级过程用特殊的机制与方式把精神和物质这两种世界混合起来,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把理性和非理性这两种世界混合起来。创造的精神并不拒绝这种原始的(抑或古老的、陈旧的、脱离常规的)心理活动,而是以一种似乎是‘魔术’般的综合把它与正常的逻辑过程结合在一起,从而出现新的、预想不到的而又合人心意的情景。”(13)阿瑞提也阐述了文学艺术活动中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关系,而他同样没有说明这种“魔术”般的综合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其实,马尔库塞所看重的文学艺术的异在性,恰恰可以很有说服力地阐明感性与理性的崭新关系。从人类生成历史来看,感性生命是人的根柢,理性是为维护、协调感性生命而发展起来的,它只能是服务于人的感性生命。感性生命是“主人”,理性则是服务于感性生命的“仆人”。可是,由于感性的盲目性,更由于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理性张目,理性终于赢得权威地位,并反过来遏制、乃至窒息感性生命。唯有文学艺术是个特殊领域。作为一个非现实的想象的异在世界,操作原则或现实法则在此丧失了它存在的合法依据。文学艺术的虚构世界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这里不存在外在的法则,不存在凝固的秩序,于是,人的感性生命自由地展开了自身,这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世界只遵循生命自身的法则,只遵循感性的秩序。正因如此,理性的权威地位被褫夺了,它重新降身为“仆人”。
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关系颠倒,也不是复归原始。当感性生命重获自由,重新成为“主人”,它就不仅改变了受压抑、被异化的状态,转而开拓自己的疆土、增强自己的力度,向感性生命的全方位、多形态展开了,向一切与生命相关联的对象、向整个世界展开了,性欲也随之转变成为遍及人类和自然并意图与其融合一体的爱欲。理性不再固执于僵死的条文和法则或机械的逻辑和规范,作为感性个体的“公仆”,它必须转化为理性智慧,成为追随感性生命、服务感性生命、协调感性生命的新理性——理性智慧。在文学艺术的虚构世界中,生命本能中的攻击性也因失去真实对象而丧失了野蛮力量和嚣张气焰,它被接纳到爱欲之中,从属于爱欲,成为人的接受性和创造性的一种动力。理性只有彻底放弃中心地位,转换统治者的角色,改变刻板威严的面目,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仆”,成为理性智慧,才能和感性生命相和谐。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感性和理性的融合,感性也因此成为包容着理性、融汇了理性智慧的新感性。文学艺术借道于跟现实相异在的虚构世界,为人类持存、积蓄、培植着新感性,持存、积蓄、培植着一种与现实相对抗并欲求改革现实的力量。
马尔库塞天才地预见到文学艺术的虚构世界与新感性的关联,却囿于现成结论,未能深入揭示其中的内在机制。
在评论萨特存在主义思想时,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萨特所说的“自由选择”,脱离了人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处境。他说,假如一种哲学借助其对人或自由的存在本体论的分析,能够把被迫害的犹太人和刽子手屠刀下的牺牲品证明为完全自由的,证明为依然是其自己承担责任的选择的主人,那么,这些哲学思想就堕落到纯属意识形态的水平上。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可以为迫害者和刽子手提供最得心应手的辩解。“在死亡与奴役之间的自由选择既不是自由,也不是选择,因为两种出路都毁灭了欲求着自由的‘人的现实’”。(14)
马尔库塞的批评是合理的,他自己则力图将人和人的感性置于特定社会的历史境况中做具体分析,阐明它们被异化的社会历史事实。就如科尔纳所说:“在现象学中,历史、社会及社会变革的唯物主义理论之缺席,促使马尔库塞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因此提供了现象学所缺漏的‘具体哲学’的核心内容。”(15)然而,当马尔库塞转而从文学艺术的异在世界来思考人和新感性,那位被羽化了的“普遍的人”和被“还原”了的感性是否仍然保有其历史内涵呢?
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跟现实相异在,并持存着反抗现实的感性力量,其审美形式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尔库塞说:“所谓‘审美形式’,是指和谐、节奏、对比诸性质的总体,它使得作品成为一个自足的整体,具有自身的结构和秩序(风格)。艺术作品正是借助这些性质,才改变着现实中支配一切的秩序。不错,这个改变是‘幻象的’,但是,这种幻象却能表现着那些不同于占支配地位的言论世界的意义和功能内涵。语词、声音、图像,从另一个维度上,为行将达到的和解,‘悬置’、剥夺着现存现实的存在权利。”(16)
马尔库塞笔下的审美形式是和谐、节奏、对比、声调、旋律、色彩、结构、形状、文体、语体等总体,但又不仅仅是诸形式要素的总体,它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
任何物质对象都有其自身的时空形式,这些时空形式既申明对象自己是具有特定形态的特定客体,将自己与其他对象区别开来,却又仍然让自己依存于现实时空连续体之中;审美形式则完全不同,它独具一种力量,能够让文学艺术作品从现实时空连续体中超脱出来,置身于非现实的虚构世界,获得自律性。这是一种“专制的力量”。审美形式之所以能赋予文学艺术以异在性和反抗现实的权力,就取决于这种专制力量。它剥夺现实质料的现实性,悬置它们的现实关系和现实权利,推翻它们的现实秩序,并按照审美秩序,即感性秩序对它们进行改造重塑。
在《结构主义诗学》中,卡勒说:“文学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与一般的交流有明显的不同;它的形式和虚构属性决定了它的奇特、力量、组织结构以及与一般口语不同的永久性。”(17)卡勒认为,文学形式暗示了特定的阐释程式,基本上确定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契合,这样,阅读前的期待就会发生作用,将各成分“归化”,纳入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将文本作为文学来阅读,作为虚构的文字来阅读。审美形式的专制作用仿佛卡勒所说的“归化”。作品以其形式标志引起阅读欣赏的期待,改变欣赏者与文本间日常的实用关系,建立起非现实、非实用关系,并将文本建构为一个想象的虚构世界。在这关系转化的过程中,原先所有的质料,如语词、音响、线条、素材等等,都不能不发生质的变化而被纳入审美视野,使它们成为审美世界中不可替代的成分,也可以说,因审美专制而归化了。
从表面上看,文学艺术形式与阐释程式的关系似乎是约定俗成的,欣赏者只需从特定文本形式出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把文本当做文学艺术作品来欣赏,譬如“字条诗”。但从深层原因来看,审美形式之所以具有专制力量,正在于它即生命的形式。
就如康德把审美形式视为自由的象征,视为人类实存的方式和自然宇宙的存在方式,马尔库塞则认为,“审美形式是感性形式,是由感性秩序构成的。”(18)文学艺术的节奏是生命的节奏,它的旋律是生命的旋律,它的色彩是生命的辉光,它或柔美或壮观或华丽或朴拙或挺拔或畸曲或奋激或凄厉的形式,都展现着生命多姿多彩的形态,而非仅仅作为外观模仿的技巧的形式。正是这种审美形式与人的生命相合拍、相共鸣,它与人一见如故,顷刻间就吸引人跃入生命的新境界,一个生命得以自由活动并展示着生命本真存在的新世界,而这个世界只能是跟生命饱受压抑的现实世界相异在的虚构世界。生命的创造本能、生命活动无限丰富的形态,赋予文学艺术以不息的创造新形式的动力,也决定着文学艺术形式创新的基本走向。那些简单的形式模仿或者对新异技巧的玩弄,当它背离生命活动之形式,最终不能不受到生命活动的矫正,或为生命所摒弃。
“形式是艺术本身的现实,是艺术自身。”(19)在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中,审美形式具有极为重要的核心价值。这一点,引起不少学者的非议。杰拉尔德·格拉夫说:“形式主义把经验陌生化,不是为了揭示幕帷后面的某些真实,而是为了使我们再也不要希望遇到真实。正是马尔库塞对审美陌生化这一概念的这种用法,使他得以把他的康德的形式主义同某种超现实主义调和起来。”(20)这种将马尔库塞与形式主义相等同的做法显然是偏颇的。
在马尔库塞看来,审美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它是生命本身,因而也就是文学艺术本身。审美形式区分了文学艺术活动与其他实践活动,区分了生命本真存在的世界与非本真存在的世界,文学艺术正是借助于审美形式,才超越了现存的现实世界、超越了被异化的境遇,才成为跟现实作对、反抗现实的作品。审美形式按照感性秩序把来自现实的质料和素材加以重组,颠覆了现实秩序,重建感性生命的秩序。因此,审美形式在否定的同时又在肯定着,即使形式表现着无序、狂乱和苦难,它仍然是对无序、狂乱、苦难的把握和否定,同时是对自由的生命的肯定。文学艺术凭借审美形式让人遭遇了生命的真实,一个充满着生命欲求、不息的创造潜能,和敞开了心扉时时准备迎迓新世界的崭新的感性生命。
审美形式具有双重性格:商品化与抵制商品化。审美形式作为一种形式,总是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朦胧的知觉、矛盾纠葛的经验和运动变幻的情感,给它以形态,给它以界限、框架,使它成为一个客体,并赋予它可衡量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文学艺术作品因此同其他产品一样可以用于流通交换了,它因被赋型而沦为商品。文学艺术被赋型之后,具备了无限的可复制性,而这种可复制性又快速推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进程。当代“反艺术”的兴盛,就起因于反抗这种作为现实形式的“商品的”形式。可是,审美形式又非一般的形式,它有着专制的力量。凭借这种专制力量,文学艺术超越了现实,它被携入非现实的虚构世界而具有了自律性。文学艺术就借助审美形式所获取的自律性来抵制商品化过程。
审美形式赋予文学艺术以无限魅力,它令作品敞开自身来吸引、接纳欣赏者,它让欣赏者进入一种生命自由活动且不断创造着的境域。每一次欣赏都是一次新的经历,一次新的创造,文学艺术作品也因此成为唯一的,它绝不重复自己,并且永远只能是未完成的、不能被固定的。从这个角度看,文学艺术的价值是无法确定的,它以生命的真实和自由来抵制外在物质形式的囚禁,抵制商品化,并对抗整个商品社会。
马尔库塞进一步引申了本雅明对艺术可复制性的论述,他说,有一种与所有复制性的东西对立的存在,这就是艺术品的氛围,即艺术作品在其中被创造并对之诉说的、规定了艺术作品的功能和意义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情境。一旦艺术作品脱离了那个不能再重复和不能再挽回的历史时刻,它“原初”的真实就被歪曲了,或被修正了:它获得了另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对应于另一种历史性情境。借助于新技术及新的感受和思维形式,原初的作品可以被阐释、编排和“翻译”,从而可能变得更丰富、更复杂、更精巧、更有意味。可是,对于艺术家和欣赏者来说,作品已不是它曾是的东西了。“那种构成作品的独一无二、经世不衰的同一的东西,那种使一件制品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的东西——这种实体就是形式。借助形式而且只有借助形式,内容才获得其独一无二性,使自己成为一件特定的艺术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其他艺术作品的内容。”(21)审美形式构成文学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品格,以此来抗拒被复制和被商品化。
文学艺术凭借其异在性和独特性来反抗现实异化、反抗被商品社会同化;正是审美形式创造并维护着文学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以及与任何他物的距离,标示着自己独立于现实的异在性和独特性。因而,马尔库塞认为,“反艺术”对形式的蔑视和鄙弃恰恰使它更易于被商品社会所同化。当今,真正的文化危机在于:随着后现代社会逼近和大众媒介迅猛发展,高级文化中对立的、异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被日渐消除,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被日渐消除,文学艺术日益被俗化,审美被日常生活化,这种状况是否可能最终导致文学艺术政治功能的衰竭?“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22)这也正是詹姆逊所担心的“去差异化”。
商品社会以其巨大力量敉平各个领域的差异,以交换价值来统一衡量整个世界,包括文学艺术的虚构世界,贪婪地吞噬它能遭遇到的一切。在这大一统的商业王国里,不仅文学艺术,人的身体、精神乃至灵魂也将贴上商标被任意拍卖和随意消费。面对这一危境,马尔库塞的审美乌托邦还能否保持它的革命性呢?
在评论马尔库塞的文章中,理查德·沃林说:“马尔库塞主张,进步的历史变化的出现与个体意识和洞察力有着必然联系。社会改造必定是一个有意识的意愿过程——一个自我改造过程,否则它就毫无意义。”(23)身临人人遭受严重异化的现代发达工业社会,马尔库塞把社会改造的希望寄托于个体的感性重建,寄托于文学艺术的异在性,以及由这个异在世界所孕育的新感性。这是个审美乌托邦。但是,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说:“我们把所有超越环境的思想(不仅仅是愿望的投入)都看做是乌托邦,这些思想无论如何具有改变现存历史—社会秩序的作用。”(24)
①⑤(1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3、137、135页。
②③⑨(2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145、140、57、53页。
④Herbert Marcuse,An Essay on Liberation,Boston:Beacon Press,1969,p.11.
⑥⑧(1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性考察》,《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34、213、210~211页。
⑦[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论新感性》,《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第123页。
⑩[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艺术与革命》,《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第176页。
(11)(1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论新感性》,《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第106、120页。
(13)[美]S·阿瑞提:《创造的秘密》,钱岗南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1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6页。
(15)Douglas Kellner,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55.
(1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自然与革命》,《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第152~153页。
(17)[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20)[美]杰拉尔德·格拉夫:《反现实主义的政治》,赫伯特·马尔库塞等:《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2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第193页。
(23)[美]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张国清、王大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24)[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