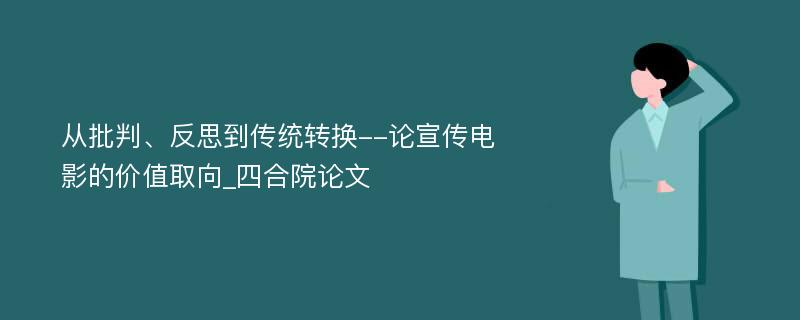
从批判、反思到皈依传统——论张扬电影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取向论文,传统论文,电影论文,张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鲜有像伯格曼那样,用电影来改善父子关系、缓和内心深处因为与父母不和而带来的愧疚和孤独的作品,伯格曼曾经说:“不论当时或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在整部《野草莓》中,一直在向双亲哀求:看着我,了解我,可能的话,原谅我吧。”[1] (p11)相信导演张扬会与之有深深共鸣。除却第一部商业意味较浓、导演控制权较弱的《爱情麻辣烫》之外,张扬的另外三部作品《洗澡》、《昨天》、《向日葵》重心都在探讨家庭问题,尤其是其中复杂难言的父子关系。现实中张扬和父亲的关系也一直并不融洽和睦,和伯格曼一样,他显然也是在使用电影这种奢侈和高调的形式,抒发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表达的对父亲的理解、感情以及对父子关系的深层思考。他的电影,视点往往从“子”出发环视或反观“父”的形象,纠缠于“父”与“子”永不停息的争斗和爱,叙事重心永远落在家庭生活中男性一方,男性生存空间和精神世界得到细腻的展示,而家庭中其他的女性角色则沦为陪衬和被动的所谓“空洞的能指”。在父子故事的表层意味之上,其实是通过“子”对“父”的逐渐肯定和最终趋同,辅以具体场景被赋予的彼此对立的象征意味,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潜意识中的认同和回归。这种价值取向虽然与第六代的整体创作大异其趣,但是在电影商业化的潮流中,却有其存在的必然原因。
《洗澡》、《昨天》和《向日葵》这三部作品,都从男性视角出发讲述故事,表现男性生存空间,其中父子关系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洗澡》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女性缺席的家庭之中,一个叛逆的男性最终得到了父亲的谅解,得以回归父子秩序,重获心灵的宁静;《昨天》的主人公是一个因为吸毒和不稳定的生活导致思维和自我定位暂时发生混乱的男性,整个家庭都来帮助他,而父亲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向日葵》则是更纯粹的男性故事,张扬第一次采用半自传的形式,完整地展开了父子在几十年间争斗并相爱的全景。在张扬所讲述的父子故事中,往往存在着一个“子”对“父”从叛逆到认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子”和“父”各自都有激烈痛苦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体验,而最终父子之间达到了一种基于血脉和性别之上的深切的精神和价值系统的认同。“父”的形象在张扬作品中,往往指代着传统伦理、传统文化以及与之适宜的生活方式、价值系统,因此,“子”对“父”的认同,其实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甚至膜拜。
《洗澡》中大明对于父亲的背叛属于过去时态,他不想继承“澡堂”事业而出走深圳,电影开始之时,他回到久别的家中,西装革履地走进澡堂,神情落寞、心事重重,从着装到精神状态,和澡堂中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父亲和弟弟看起来都是如此隔膜、格格不入。刚开始,父亲对他的态度冷漠客气,却和二明亲密无间,配合默契。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明一步步融入到澡堂的氛围之中,开始脱下衬衣西裤而穿上汗衫短裤,也渐渐能和父亲一起默契地劳动,甚至在雨晴之后的清晨聊聊天。在此期间,大明逐渐被父亲的人格魅力所吸引——父亲仁义、慈爱、热心,做事情有理有据有节,周围街坊邻居无不受惠。等到父亲去世之时,大明已经完全认同并且继承了父亲的一切,开始主动承担起父亲的角色,在澡堂被拆之前,他一个人躺在水池中,在温暖柔润的水中默默沉思。
貌似简单的一个故事中其实“机关”重重,无论是“深圳”、“澡堂”这些场景空间,还是“水”这种物质、“洗澡”、“跑步”、“唱歌”这些行为,都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未曾真正出现过的“深圳”,在这里显然是与传统文化相对立的“他者”,而“澡堂”,则是一个浸淫了传统文化精髓的老少咸宜的人间天堂。剧始的父子冲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案,而是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冲突;剧终时大明彻头彻尾的转变,也并不是简单的亲情和伦理的回归,而是因为他成为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精神遗产继承者。“子”对“父”认同的深层含义,则是对“父”背后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全面膜拜,正如尹鸿所说:“大明一直被安置在一个被动的观看位置上,他在影片中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性,他只是一个被教育者,如同我们所有观众一样,是通过看而成为了父亲和父亲所代表的‘澡堂文化’的俘虏,我们被父亲的宽厚、被父亲的亲切、被父亲与周围人的和谐和睦、被父亲所代表的超功利性的东方人伦情感所感动、所征服,于是我们也同大明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恋父认同,也完成了对‘澡堂文化’的认同。”[2] (p102)
《昨天》中贾宏声刚刚出现的时候,头扎发带,身穿黑色睡袍,仿若受难的基督。他对父亲说,在四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是我的父亲,而不是列侬。精神的混乱崩溃和对父亲的背叛并行而进,愈演愈烈,而以打在父亲脸上的两记响亮的耳光作为最高潮,父亲扭曲的面孔、悲痛绝望的哭声让这一赤裸裸的背叛彰显出更为巨大的悲剧性。经过卓绝的努力之后,他终于从空中落回到凡尘,回归家庭和秩序。贾宏声思想的混乱,核心是“我的父亲是谁”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似乎整个精神的废墟才有了重新建立的根本,强大的父子秩序收回了一个背叛的灵魂,同时还给了他心灵的宁静。
“子”对“父”的叛逆和回归在《向日葵》中有更为完整细腻的展示。《向日葵》甫一开始就是一个经典的俄狄浦斯的情境,父亲多年之后归家,而儿子已经成长为淘气少年,他在屋顶伏击一个陌生人(父亲),并用自己的拿手好戏——弹弓打伤了他的额角。在人生的每个阶段,父子之间的主要冲突各不相同,归根结底,矛盾的起源在于父亲的观念问题。他理所当然地把儿子看成是自己的,对儿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自己终身不得志,儿子就一定有义务代替自己实现理想,从另一方面来讲,儿子成功了,也和自己成功毫无二致;自己是父亲,就一定有权利掌控儿子的生活道路和感情问题,而不问他是否需要、是否喜欢;自己是父亲,所以就有权利命令儿子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事实上,这种“父亲”的形象以及附加其上的观念并不罕见,而是相当普遍的、东方伦理中的父子关系模式——“父”对“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子”对“父”必须是无条件的服从和孝顺。尽管张扬用“子”的叛逆和反抗表达了对这种父子关系的批评,但剧中一系列情节和象征元素的设置,又说明了创作者的态度并非是简单明确的。
首先,“向日葵”的设置。向阳画画,和父亲种植向日葵、给向日葵松土施肥常常同时进行,父子冲突的室内戏,镜头也往往将墙上悬挂的向日葵的图画纳入其中,意味着父亲之所以管教儿子,往往是因为有一份美好的愿望在里面;向阳成为父亲之后和妻子、母亲回到住所,首先看到的就是出走的父亲悄悄放在门口的一盆向日葵,向阳抛下妻子和母亲,独自一人走向前去,和向日葵微笑对视——其实也是在表现他对于父亲的重新理解和认识;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则是一片辽阔的向日葵的花海,微风轻轻拂动,同时伴以怀念父亲的画外音。虽然很难给向日葵一个明确的象征定位,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浓浓父爱,却是显而易见的。其二,父子情感方式的类同。父与子都曾经格外着意于猫,猫曾经是向阳“俄狄浦斯”情结发作之时,攻击父亲的“利器”,也是他从父亲那里受到伤害之后,得到抚慰和温暖的小小生物。而当父亲老年之时,对废墟中的流浪猫的眷恋和照顾,这种情感恐怕就更为复杂了,有因为父爱难以倾泻而带来的苦恼和孤独,也有对于过去时代的留恋和不舍。并且,父亲用小猫的“连环画”赢得了儿子的喜爱,而儿子用同样的方式来博得心爱的姑娘的心。儿子厌恶画画,但表达情感的方式却和父亲如出一辙,情感方式的类同,强烈地表达了父子间的深度认同。其三,从向阳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家庭和父母的重视和爱,尽管表面上彼此之间充满了伤害。前来观看画展的父亲最终停留在两幅画上,一幅是儿子的肖像,一幅是父亲的肖像。儿子坐在自己的肖像前,父亲也坐在自己的肖像前,父子俩在这里握手言和。结合在微风中飘拂的花海这个收尾镜头,事实上,“子”最后所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解放,与《洗澡》、《昨天》相同,都是奠基在父子关系的重修上,心灵宁静的源泉,在于对传统伦理和“子承父业”的父子秩序的回归和融入。尽管和观念先行的《洗澡》不同,《向日葵》因为融入了更多张扬的亲身体验而变得复杂多义,但是对男性艰难的成长过程,以及自觉地将“父之名”、“父之法”内化的过程的表现还是以一贯之的。
拍摄电影所选择的场景决定着故事的基调,烘托着角色的气质和精神状态,同时也表现着创作者本身的情感以及审美倾向。张扬最倾心难忘、用胶卷一再记录的,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大规模拆迁活动中逐渐消失的各种传统建筑和场所,澡堂、四合院、胡同。90年代初,张扬为何勇拍摄那首著名的《钟鼓楼》的MV,选景就在后海一带,其中的一个镜头为工人们在拆除那里的平房,而何勇慢慢地走进尘土飞扬的废墟之中。“走进废墟”已经成为张扬电影中的一个经典意象,传统建筑和场所、废墟其实就是即将逝去的时代、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具化物,镜头拍摄它时那一唱三叹的抒情节奏,暴露了张扬对于它们的留恋,表达了他潜意识中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
《洗澡》中的澡堂功能齐全,人们在这里除了可以洗澡、按摩之外,还可以惬意地品茶、睡觉、斗蛐蛐,池子里氤氲着一波清水,墙上反射着荡漾的水纹,人人怡然自得,仿若一个世外桃源。据说这个澡堂是剧组花了很大力气在河北某地找到的,可见场景对于这部电影的重要性。在这里,澡堂宛如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中的电影院,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它不仅起到了其应有的物质层面的作用,还给人们提供了交流和娱乐的空间,丰满和充实了人们的精神心灵。影片最后,澡堂和西西里的电影院一样,都要被拆掉,曾经的生活方式一去不返,创作者的遗憾和惋惜之情充盈于表,以至于使用重复蒙太奇的方式,一遍遍再现角色从澡堂内部慢慢走出,将灯一盏一盏关掉、澡堂完全陷入黑暗之中的仪式化的画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最像《天堂电影院》的电影,并不是那部刻意模仿的《电影往事》,而是这部《洗澡》。
同为第六代导演的贾樟柯,在电影《小武》中,也选择过一个澡堂,与之不同的是,这个澡堂非常之不美,墙面破败,木床简陋,被褥肮脏,在看起来暧昧可疑的水面上甚至都难以找到一缕多少能让画面感觉柔和的水蒸气,但仔细想来,这却是一个属于真正的中国西部县城的澡堂。场景选择的不同,不仅仅是出于故事的不同需求,还凸现了创作者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
以三个不同年代为坐标的《向日葵》更清晰细腻地表现了场景的变迁、老建筑的渐渐消失和新的钢铁城市的崛起。片子伊始,母亲追打向阳的一出戏采用了跟拍的方式,让摄影机在四合院和胡同里来回穿梭;接下来,向阳在父亲那里受了委屈,躲到屋顶上去,一个远景的俯拍,摄影机匀速地摇移,将夜幕初临的四合院的全景完整地勾勒出来。1999年电影片段的开始,就是沉重的拆除废墟的声音,此时的北京已经是高楼和脚手架林立。头发灰白的父亲推自行车回家,仍旧是一个长长的跟镜头,将已经衰败破乱的四合院展现出来,父亲老迈的背影与之相得益彰。父亲把车子支好,镜头略升,一个广角镜头,将远处崭新的高楼纳入,高楼带给四合院最直接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突兀、侵犯和压迫。而父亲端坐在即将拆除的废墟之中的镜头,则又一次强化和印证了场景的象征性:父亲和这破败的场景一样,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然过去。而吟叹的摄影机运动节奏,以及伴随着的呜咽叹息的乐音,将隐藏在镜头后的创作者的主观情感暴露无遗。
“迄今为止,文字所记载的全部人类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度之下的文明,因此,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叙事形态都具有男性主体叙事的特征。在这数量浩如烟海的文字与叙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女性的形象和意义大都是相对于男性主体而设定的。”[3] (p136)“女人被先在地派定在绝对被动的、客体的位置上,作为男性行动的客体与男性欲望的客体。”[4] (p124)戴锦华的论断可以作为张扬作品女性形象塑造特点的一个注解。张扬作品所采取的男性视角以及所持的价值取向必然带来的,则是女性形象的被弱化和客体化,她们不折不扣地成为了劳拉·穆尔维所谓的“空洞的能指”。
在《洗澡》中,家庭里女性的角色是缺席的。母亲的形象只在一段突兀的插曲中以少女的面目出现,目的仅仅是为了证明象征传统文化的“水”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毫无意义;大明妻子的角色则干脆简化成了电话另一头的女声,相对于逐渐趋于协调温暖的父子世界,电话铃声是那么刺耳冷漠,不合时宜,永远都在打破环境的协调,甚至父亲也是在催促大明回深圳的电话中死去的,这个情节的设置格外突出了创作者对这个角色的排斥性。这个冷漠自私、完全不合常理的女性形象,显然被创作者放在了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上,从反面烘托了以父亲为中心的传统人际关系的融洽和温暖,而影片的最后,她也被排除在父子世界之外:“我们(兄弟俩)一定会在一起的,这是最重要的”。《洗澡》中唯一真正出现在现在时态叙事的女性形象,是邻居张进浩的妻子,她也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澡堂”中泡澡的女性角色,在其乐融融的“澡堂”空间中,原是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地的。但是她仍然是没有名字的,仍然是一个被讲述、被评论、被操纵的客体,她出现在澡堂中,不过是作为治疗男人阳痿的美妙药饵,同时也烘托了父亲尽善尽美的形象。
在张扬的作品中,《向日葵》中的女性形象最多,但反而能更清晰地体现出被客体化、欲望化的痕迹。母亲这个人物形象,没有太多的性格特征,仅仅是起到一种平衡和协调父子关系的作用。她只有一个强烈的、明确的愿望:搬出四合院,住到高楼里去。为此,她不惜和丈夫单位的领导吵架,也不惜和丈夫假离婚。而当丈夫失踪之后,她痛心疾首,认为自己鬼迷心窍,现在是得到了“报应”。事实上,和《洗澡》中大明妻子对应着被创作者所批判的深圳现代文化一样,母亲所追求的“楼房”,也正是传统文化所寄居的“四合院”的对立面,母亲这唯一明确的生活目标,不过是为了反衬父亲对于四合院、对于旧时代生活方式的迷恋,而这也正是张扬电影所一贯渲染的基调。从这方面来说,父子又一次获得性别的认同,甚至将作为异性的母亲排斥在外,而女性角色的确定、意义的所指仍旧是参照并依据男性来界定,由此再度成为了“空洞的能指”。向阳初恋女友于红的一出场,便处于“被看”的位置。“女人作为影像,是为了男人——观看的主动控制者的视线和享受而展示的。”[5] (p574)接下来,于红的举动颇类似于《聊斋志异》中那些“自荐枕席”的各色狐狸精,大方开放,主动脱去自己和对方的衣物,向阳仿佛是完全被动地、几乎是无辜地有了人生的初次经验。意料之中发生的流产事件,更给人刻意安排的感觉,私拆向阳信件者为母亲,陪于红去流产的反倒是父亲,“男孩父亲带女孩去流产”——这一不合常理的细节设置显然是为父子更深刻的冲突作铺垫,于是才会有在什刹海的冰面上父子追逐、角力与和解的象征性场面出现。《向日葵》中发生的另外一次流产事件最终的意义指向依然是父子关系——在父亲“我是你的父亲,你为我生一个孩子有什么不可以?”的怒吼中,向阳毫不犹豫地让妻子小韩流产,此时此刻小韩的身体,和向阳小时候用来向父亲示威的炮仗的功能是相同的,它存在的意义只在于又一次深刻地展示了父子之间的矛盾和彼此之间的角力。和“流产”具有相同意义的细节是女性的“生育”。《向日葵》的影像以生育始,以生育终,但本片的极其写实的、血淋淋、残酷的生育过程,非但不有助于建立深刻的母子之间的关系认同,反而将叙事的意义重心再一次落在了父子的纽带之上。第一次生育过程的展示中,影像从痛苦挣扎中的母亲转移到焦急地在外面徘徊的父亲身上,并且伴随着向阳的画外音:“因为院子里的向日葵正在开放,父亲给我取名向阳。”;第二次生育过程的展示中,影像最终结束于向阳凝视婴儿时的一滴初为人父的眼泪,儿子自己做了父亲之后,终于对父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同,父子关系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父子之间互相理解的情感链条,借女性的身体得到加强和确认,女性的身体只是叙事和表意的桥梁,一旦把儿子带给了父亲,她们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也就结束了,而女性的身体本身,完全没有真实的疼痛和灼热,从而被彻底工具化和客体化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扬的电影中有母亲、有女儿、有妻子、有恋人,但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尽管张扬的叙事重心表明了不在女性这一方,但在叙事动机以及形象内涵上对于女性的忽视仍然是触目惊心的。张扬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女性观念,和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态度如出一辙,从侧面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张扬作品所体现出的价值倾向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中颇引人注目。第五代电影崛起江湖的致命武器之一,便是对传统文化以及附着其上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猛烈批判以及深刻反思,在他们的镜头下,传统文化已经如《黄土地》中的那个苍老愚钝的父亲一样,只有像憨憨那样勇敢痛苦地与之诀别,才能够获得崭新的世界;在90年代之后第六代的创作中,则很少出现强有力的、正面的父亲形象,处于“父亲缺席”的状态之中,如尹鸿所说:“新生代电影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一群没有父亲庇护、也没有父亲管制的青年人那种飘荡和游离的迷惘和狂乱,处处洋溢一种没有家园和憩居的青春骄傲。”[6] (p101)而在张扬的创作中,传统文化乃至父亲的形象变的前所未有的崇高神圣,尤以《洗澡》为甚。从文化反思和批判转向文化皈依的背后,除却创作者个人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方式的原因,还埋藏着经济原因的制约。
中国电影的市场化、商业化潮流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90年代中后期则配合着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而愈演愈烈,如何获得更高的票房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利润越来越多地为投资者和创作者所考虑。由于国内电影事业的萧条,更多的电影从业者将目光转移到国际,希望能够进入到世界主流电影市场,这样就造就了一批按照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进行创作的中国影片。在《洗澡》中,“水”作为一种意象被反复地歌颂和赞美,它简直是万能的:它是父亲向叛逆的儿子表达父爱的渠道;苗壮的西式美声《我的太阳》只有在“水”的滋润下才能完成;“水”提供了一个其乐融融的集体空间;“水”甚至成为了信仰,不但能够洗净身子,还能够治百病,洗干净灵魂。对“水”的顶礼膜拜以及对澡堂空间的美化,其实是人为地建构和想象出了一个西方视野中宁静祥和的东方。介于中国在国际电影市场上的边缘地位,想要达到文化输出的目的就不能不讲求叙事和表意的策略,因此张扬的作品在第六代中率先取得商业的胜利并非偶然。值得一提的是,张扬的父亲张华勋导演80年代早期执导的电影《神秘的大佛》,融合了多种商业片元素,可算是新中国最早的商业电影,在当时取得了上亿元的票房佳绩,可惜由于整个社会经济模式的滞后,电影商业化苗头只能是昙花一现。结合张扬的商业成功以及作品的价值倾向,可以看成是“子承父志”的文本与现实人生的有趣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