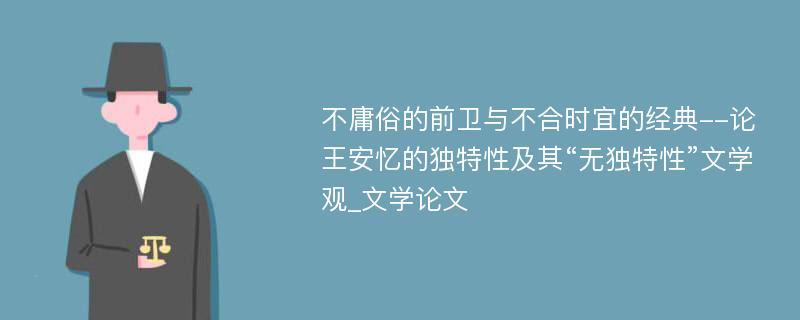
不媚俗的前卫与不落伍的古典——论王安忆的独特性及“不要独特性”之文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卫论文,独特性论文,性及论文,独特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
王安忆在中国文坛绝对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三条理由是比较充足的:
独特的文学地位
在新时期汹涌澎湃的文学浪潮之中,王安忆虽然不属于“舵手”级的作家,但无疑,她却是个动辄就能在浪尖上跳出漂亮舞蹈的角色。有评论者曾经冠以她“新时期文学中的旗帜性人物”[1]这一称号,只要罗列一下王安忆这二十多年来的创作成果,相信没有人会对此称号提出异议。从1979年至今,中国文坛经历了从“伤痕”至“反思”到“寻根”,又从“寻根”到“新写实”、“新体验”、“新历史”、“新状态”、“女性文学”、“晚生代”到“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等种种的漫长沿革、巨大发展和快速淘汰,这期间流派蜂涌、主义纷呈、佳作不断、新人辈出——真所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台,八仙过海各显其才,但王安忆却能一如既往游弋其中。尤其令世人惊讶的是,她还能频频爆出佳作震动文坛,比如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雨·沙沙沙》,因其叙述的清纯和美丽首次引起文坛的关注;1985年,中篇小说《小鲍庄》一炮打响,一时间文坛更是四座皆惊,小说中寓言似的故事,凝固着的意象以及登峰造极了的白描手法,都使人对这位往日抒情的单纯的女青年刮目相看,而这部作品也由于主题的多义性而成了“寻根文学”的经典之作;1986年,以情爱、性爱及婚外恋分别为母题的三个中长篇“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发表,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作者的笔触大胆地伸向了“原始的伊甸园的快乐”[2],用女性特有的浪漫和唯美情怀(有别于刘恒的冷静与贾平凹的庸俗之处)把世间男女的生命本能写到了极致,一时间评论界争论激烈,可以说基本是毁誉参半,尽管如此,“三恋”的影响是巨大的,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足以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大概评论界后来也渐有同感吧,总之,“三恋”在以后的评论中均被归为王安忆创作中的辉煌时期;九十年代,小说书写的大部分领域(指感性领域)日益被其他东西(尤其是电影电视)所占领,而剩下的小部分领域也被沸沸扬扬的感官刺激所掠夺的时候,以写隐私、写欲望、写身体而“惊倒、肉倒一大片”[3]的“小妾文学”、“麦当娜文学”、“戏子文学”、“美女文学”便堂而皇之地走上文坛并且大有横扫一切之势地引导起了人们的消费潮流的时候,王安忆却以她独特的文人书写姿态、洁净的精神追求以及形成技巧上的变化多端迎来了她小说创作道路上的又一次重要转机——虽然她的小说根本就没畅销过,反之,是越来越抽象、越来越难读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小说的高品味和高质量,因为,它们在小说领域里的探索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这时期,她相继发表的中、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香港的情与爱》、《伤心太平洋》、《长恨歌》、《叔叔的故事》等一系列作品,不但使她本人的写作风格焕然一新,而且,更重要的是,她还有力地粉碎了批评界关于小说已近末日的预言,为中国文坛“展示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可能性。”[4]尤其是她的《叔叔的故事》,甚至给我们点燃了这样一种希望:即,如此的抽象竟然能激发出我们最深处的情感,公然的虚构竟能蕴藏深切的现实性——总之,严肃的小说也是可以走抽象与理性的道路的,虽然这与小说的本性是水火不相容的,但王安忆却以表面是背叛而实际上却在拯救的方式构建着一个别样的小说世界——她的这一破坏与重构相统一的行动自然又引起了文坛的一片喧哗与骚动……。
谁,能一辈子当定生活的主角?哪个主角,又能在每一次的演出中总是连连获胜、捷报频传呢?
但文坛上的王安忆却似乎更有资格笑傲这一生活常规。
在一篇名为《面对自己》的演讲词中,王安忆就这一问题也曾做过认真的反思,她说:“我自以为是一个远离一切文学潮流的作家,其实却得了一切文学潮流的好处。每一次生死攸关、而又荒诞不经的冲破禁区,都为我的创作开辟了道路,使我一无负担,二无拘束地在往昔的战场上自由自在的活动。我是一个幸运的孩子,能够在前人或同辈的掩护之下,从容不迫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应该承认,在我开始创作的不多几年之中,更多的时候不是在做理性的思考,而只是摸摸索索的行动,由着一个看不见、摸不清的冥冥念头所推动。直到较长一段时间之后,理性的思索才显现出来,雷电般一闪,照亮了过去和未来的道路。”[5]似乎也可以这样说,这是王安忆对自己漫漫创作生涯所做的简要又精辟的概括和总结。从这段自白中,我们还有幸得到了两点启发,即:
启发一,成功的作家不能没有独特而丰富的个性与禀赋
“能够远离一切文学潮流”但又能“得一切文学潮流的好处”,首先,我们知道王安忆是一个不媚俗不趋时的作家,她耐得住寂寞,独守一处,不随波逐流,有着清醒的头脑和自信、骄傲的个性。其次,她的艺术感觉又非常优秀、非常前卫。不屑于跟随潮流但又能合一切潮流之精华并且善于使自己超越潮流转而又引导潮流——这显然得益于她敏锐的眼光和准确的判断。“即使新生活现象初露端倪以及被一些耸人听闻的舆论夸大其后果的时候,她的艺术形象几乎像一篇政论文一样,已经在深入地剖析这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意蕴了。”[6]再次,她胆识过人,善破禁区。写作对于她,“每一次”都是“生死攸关”、“荒诞不经”的,而“每一次”面临的又都是一个新的“禁区”。可以说,这也是王安忆能够在文坛屡战屡胜的有力武器之一,众所周知,如果没有这样的创作勇气,那么,有“里程碑”之称的“三恋”也许早就胎死腹中了。第四,不唯我独尊、不恃才傲物。“我”所以能“一无负担、二无拘束地在往昔的战场上自由自在地活动”,所以能独步文坛久战不败,原因在于“我是个幸运的孩子”,在于命运之神的格外垂青、“老人或同辈的掩护”。
一斑能窥全豹,由此可见,王安忆是一个多么能容纳百川而自成一格的大气的作家啊!
启发之二,她道出了自己能够实现多次飞跃的成功秘诀,即“理性思索的显现”犹如“雷电”一般,顷刻间便“照亮了过去和未来的道路……”。理性,使王安忆的创作日趋走向独特和成熟;理性,使王安忆有了自成系统的激进的文学主张——这,便是笔者归纳的王安忆的第二个独特之处。
独特的文学观
这一文学观使王安忆的笔致更加随意、自由,使王安忆的创作激情更加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一位北大荒的战友曾对王安忆下过这样的评语:“拾到篮里都是菜。”[7]上海著名的作家陈村在与王安忆笑谈时也戏谑说:“一条棉裤,能写出几千字来。”[8]当然,作为深受自然主义文风濡染的王安忆,面向底层,客观真实地反映底层生活的原貌,这是王安忆的天职,写尽天地间的人、事、景、物,这还称不上王安忆的拿手好戏,王安忆的拿手好戏是: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一片绿、一点红中分解出五光十色来(比如她的中篇《小鲍庄》、《流逝》等);给那怕是一片树叶也赋予一个境界(如她近年来的一系列短篇像《小饭店》、《轮渡上》等);用“瀑布”[9]般浩浩荡荡、泥沙俱下、元气淋漓、奔流不息的反经典的语言使那些原来平淡、轻巧、随意甚至古老陈旧的故事起死回生并使它们内涵十足、韵味无穷(如她的中、长篇《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流水三十章》、《岗上的世纪》、《叔叔的故事》等)。
这,无疑也是王安忆的独特之处。
同时代的作家不是已销声匿迹了,就是已偃旗息鼓了,但王安忆却为什么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并且滔滔不绝地能够越“诉说”而越精彩呢?原因固然很多,但笔者认为,这与她渐趋成熟渐趋独立的“文学观”的形成关系更为密切。
“走上独特性道路是二十一世纪作家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不幸!”这便是近年来王安忆小说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断,之于文坛,大有宣言的味道,令人联想到1949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口吻和气势。评论界对此预言反应强烈,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启用了这么一个修饰词:“惊世骇俗。”笔者认为,同时也称得上“惊世骇俗”的还有她的“四不要”小说观,即“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10]笔者认为,这“四不要”可以从浅层的角度和深层的角度去分别加以理解。“四不要”表面看像是在并列,其实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前三者是第四者(不要独特性)的具体表现,而第四者(不要独特性)才是这四条中的核心,它是对前三者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前三个“不要”最终想抵达的彼岸。也就是说,这四个“不要”实际上要说清的只是一句话,即“不要独特性”。
当然,以上是对“四不要”浅层次上的表述,而实际上,“四不要”还有它深层的含义,下面,笔者就将她的“四不要”小说观略作分析,从中我们可以透视一下“不要独特性”了的王安忆又是怎样实现了她的独特性的。
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
文学形象(包括人物、场景、氛围)的典型性的高低,历来是衡量作品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一条重要标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要求,同时,还是十九世纪以来基本左右中国政治高层和大众共同审美习惯的现实主义传统,它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因而一度曾是我国所有作家进行创作的行动准则。“不要特殊(在这里‘特殊’似乎就可以理解为‘典型’)环境特殊人物”,王安忆的言外之意是她“将放弃传统的反映世界的方法,以此来尝试在“不特殊的环境里”塑造“不特殊的人物”。
——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传统的对立面,这如果不是螳臂当车之举,那就一定是作家本身已具备无敌的本领和超人的斗志了,王安忆无疑是属于后者的。因为这一理论体现在她同期的创作中,便使我们看到了作家在塑造人物方面极富挑战性的一些倾向,即(一)小说中的人物以极端的写实(这是“新写实派”的显著标志)为原则,不做任何“杂取种种,合为一个”或“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加工和提炼,也不让他们承载任何的社会内容,附加任何的政治、思想意义,他只是一个生活中原汁原味的人,他的身份是随意的、他的性格是模糊的、他活动的环境是日常的、他的行动也是琐碎的……而这些人物在大千世界中却是随处可见、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的,他们就如空气的灰尘一样,作者无须挖空心思去精心构思,而只需信手拈来、娓娓叙起;(二)小说中的人物以极端的虚构(这是“先锋派”的显著标志)为原则,常以抽象的形式出现,他们成了“主题先行”的产物、成了“一般化、共性化了的抽象的人”,是符号,是作家思想的代言人,如《叔叔的故事》中的“叔叔”的形象和“我”的形象,“叔叔”已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整整的一代人、一代文化的抽象集合,可以是王蒙、张贤亮、陆文夫、高晓声这一代中青年作家;“我”也不是“王安忆”自己,而成了“王安忆这一代人、一代文化的抽象集合”,另外,在《乌托邦诗篇》、在《纪实与虚构》、在《伤心太平洋》这几部中篇里,人物形象也多是这样经过归纳了的“类型人”。
很明显,王安忆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恰恰是传统写作所强烈反对和坚决要杜绝的,早在1885年《致敏·考茨基》一文中,恩格斯就“小说中人物要力求个性化”提出过要求,他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12]而王安忆竭力要否定的正是“这个”,她更热衷追寻、关注和书写的是“这一代”、“这一群”、“这一类”,其间的对抗显而易见。
二、“不要材料太多”
这是继王安忆对小说的第一大特征(刻画典型人物)放弃之后又对小说第二大特征(安排曲折完整的情节)的断然放弃。
“曲折完整的情节”即故事。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英国著名的当代小说家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一书曾提到:“……故事虽是最低下和最简陋的机体,却是小说这种非常复杂机体中的最高要素。”[13]
众所周知,小说是必须由人物、情节和环境这三个要素组成的,与之相应的,小说便有了它的三大特征,即(一)刻画典型人物;(二)安排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三)描绘典型环境——而到此(前两个“不要”)为止,王安忆算是把小说与生俱来的所有的特征都给否定了。那么,在她的心目中,小说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王安忆有这么两个经典句子是常常挂在嘴边的,即“小说即故事”、“好小说就是好神话”,并且,她还专门指出:“故事必须是一个过程。”[14]按照她的逻辑推理一下,“不要材料太多”,但得完成“一个过程”,怎么实现这一目的呢?除非舍弃故事的曲折性、完整性和可读性,而这一点正好与西方现代派的不注重讲故事或者干脆淡化情节的小说观念相吻合。李陀把这种倾向看成是“小说的一种进步和发展”,[15]王安忆对此更是深有感触。在她的《故事不是什么》一文中,她写道:“我们曾经非常醉心于寻找不凡的故事,那些由于阅历艰深而拥有丰富经验的作者使我们非常羡慕,并且断定我们所以没有写出更好的小说,是因为没有生活,于是我们漫山遍野、或者走街串巷地收拾起故事来。我们的历史很长,地方又很大,民族众多,风俗各异且又多灾多难,只要做出努力,是一定能够找出很多很多美妙的故事。然而,在大多数时候,生活非常吝啬,它给予我们的更多的仅仅是一些妙不可言的片断,面对这些片断,我们有两条出路:让片断独立成立,或者将片断连接起来。”[16]
的确,生活的真实面貌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更多的是以“细节”、“片断”的形式而不是以九曲回肠或气势磅礴的“故事”形式,对“故事”过分重视虽然可以产生紧张、激烈的戏剧性效果,但同时又因其偏离生活的固有形态而给人一种人为的做作甚至虚假的感觉。所以,王安忆站在近似自然主义者的立场上,对传统小说过分依赖于故事情节的做法采取抵制态度,这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
实际上这可以理解为是对第一个“不要”(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的补充和强调,既然不需要人物的典型化,也就不需要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了,虽然,此处的“语言”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到底是作家的语言呢,还是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就“四不要”总体来看,无疑这应该是针对作品中人物的语言的。
“动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和性格,这是文学创作的特殊任务。”[17]一部作品有没有思想性、感染力,能不能赢得读者的喜爱,这要看它具不具备鲜明的特点(即个性),而作品中人物的个性又决定着这部作品的个性,人物的个性是绝对离不开他的个性化语言的辅佐的。所谓“口中语,能肖声情。”既然王安忆连作品中人物的典型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都可取消,而比较注重的是刻画尤其具有“共性”的人物(如纪实人物、类型人物),那还要这“个性”化的语文有什么用途呢?好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一样。
四、“不要独特性”
表面看这是含意最为模糊的一条。“独特”在这里具体指什么呢?是作家、作品的风格、个性,还是纯粹个人的独特的经验、话语,抑或二者的意思都有?
要理解这句话,第一,得联系王安忆那个惊世骇俗的宣言(“走上独特性道路是二十一世纪作家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不幸”)中的“最大的可能”和“最大的不幸”;第二,还要理解王安忆所谓的“最大的可能”和“最大的不幸”之深意,就得联系这个宣言提出的大环境大背景。
九十年代以后,功利主义盛行,道德与理想失落,“日常生活伦理”居于主导地位,由于不再有强大的共名像整个八十年代那样来限定文学的发展趋向,中国文学继而走向了一个“无名的时代”。[18]在这个时代,个体有绝对的书写自由,人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独一无二的个人经验而在一夜之间成为作家,因此,文学的整体叙述风格便呈现出这么一种趋势,即无名化的个人代替着共名化的宏大的历史;个人对日常琐碎欲望的喋喋不休地叙述覆盖着以往那种对崇高理想激情地追求和呼唤。王安忆自觉地远离着这么一种趋势,与此相反,她还打出了“不要独特性”的旗帜。在她看来,这种好象已形成“代替”与“覆盖”之势的“个人”化书写,在某些意义上是体现了一定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容易使人迷恋、强调局部、发展和扩张个别的东西,而“忽略了总体性的达成效果,忽略了经验的真实性和逻辑的严密性”,[19]容易使作家走向狭隘的“小我”,满足于一叶障目,形成零散化、局部化和片面化的写作局面,因此是有害的。与反对这种“独特性”相对应的是,她提倡在作品中“营造总体效果”。可见,王安忆的独特性正是体现在她的要取消独特性上。“不要独特性”使王安忆成了一个“随物赋形、富有高度表现力和综合抽象能力”[20]的大气的小说家。
总而言之,王安忆的“四不要”是大胆的突破,是积极的探索。在“四不要”中,作者既表明了自己不与旧阵营为伍、“自觉与传统叙述风格分离”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了自己更不愿随俗入流要与同时代各种新潮流派的叙述风格“划清界限”[21]的立场。相对于她的创作而言,这“四不要”一方面使王安忆把自己的未来安排在了一条偏僻的崎岖小道上。在这条小道上,既没有开拓者、同行者,甚至也看不到多少喝采者,她是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的;而另一方面,“四不要”又像是一把钥匙,它打开了长期以来囚禁着小说家们的精神樊篱,并解掉了历代文人自行套在头上、身上的道道绳索——王安忆因此像鸟一样地飞了起来,她一无牵挂、自由自在;她纵情飞翔、豪气冲天——她的笔触由此便伸向了海阔天空、伸向了无际的时间和空间……
这其实才是王安忆能够在不同时期适时地完成对自己以往高度的超越、并能独立于同时代作家群之外的关键所在,即她身上前卫的一面(当然也包括她那些前卫的思想、前卫的文学姿态和前卫的艺术感觉),我以为这无疑更像王安忆的双翅,是王安忆最具特色也备受文坛关注的地方。其次,王安忆还有一个独特之处颇受读者喜爱,那就是本文的理由之三:
独特的人生理想
王安忆在与施叙青的一次对话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表白,她说:“我现在特别想回到一种自然状态,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在家里操持。”[22]——如果这样的话出自封建社会里千千万万个中国普通妇女之口,我想,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反而,我们会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因为“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显然很古老、很正统的“家”的模式,它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并且,它是以无视甚至扼杀女性的诸种权利(包括爱与被爱的权利、“性”的权利、自我发展的权利)为代价的。然而,发此感慨的不是普通的不觉醒的女性,而是颇具前卫意识和先锋思想的一个当代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生长在一个可以说基本已摆脱了传统思想束缚的时代(当然指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时代,妇女在法权上早已取得了“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在意识形态上所倡导的“男女都一样”也基本已经深入人心,而在社会实践中,妇女不但能顶“半边天”,而且,有一部分女性家里家外甚至撑起了一片天,与此同时,她们不仅获得了爱与被爱的权利、“性”的权利,甚至还在社会上像男人一样地拥有着无限的发展的机遇。不用说,王安忆是这些女性中最觉悟、最幸运、最富有也是最成功的一位。中国古代女性拚死反抗的封建意识,她几乎没有;中国当代女性共同争取的自由和平等,她样样都有。
——然而,就是在这种无比优越的环境里,王安忆却非常忧伤地怀念起了那个传统的“家”的模式以及那个极具古典人文精神的家园里的精神与内涵,恰恰是前一代女人在走向觉醒过程中曾极力要摆脱、坚决要抛弃的。对爱情的执著、对男人的依恋、对做母亲及生育权利的要求等等这些,曾是历史留给女人的传统,在王安忆的潜意识里,它,好像也是无法反抗而必须要坚持下去的。
……拥有了独立和自由之后的“娜拉”,如今又反戈一击,她要对自己所获得的独立和自由重新审视了!因而,在王安忆的憧憬和呼唤声中,她似乎又想回“家”了。
王安忆的“三恋”发表以后,很多评论家便自然而然地将她归属到“女权主义”的大旗下,认为王安忆的创作正是一种“以女话话语对传统男话话语进行的颠覆和努力”,[23]王安忆当然不会赞同,她认为她并不颠覆传统,也从不以激烈的姿态对传统的男性世界构成反叛,相反,她对传统采取顺从和认同的态度。
这一态度,显然是和她朴素、独特的人生理想相统一的,体现在她的小说创作中,便十分具体地外化成了以下三个模式:
模式一:常常被母性“圣化”着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擅长写女性,尤其擅长的是写上海弄堂里虽过着普通日子却骄傲、优雅的水一样永带着感伤和怀旧情调的传统型女性(如《流逝》中的“欧阳端丽”、《蜀道难》中的私奔女、《小城之恋》中短小粗壮的女文工团员、《荒山之恋》中大提琴手的妻子等等形象),这些女性本来骨子里都潜藏着浓重的“弱者”意识,寻找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热恋自己的男性是她们孜孜不倦的梦想和追求,然而,一旦遇上她们所倾心、所爱慕的男性,她们身上那神圣、纯洁的母性的一面便会刹那被唤醒,像《荒山之恋》中女文工团员与大提琴手之间的关系:“就以其忧郁格外地打动了她的柔性,唤起了她那沉睡的母性,她不是那种女人,表面上柔弱文静,而内心却很强大,有着广博的胸怀,可以庇护一切软弱的灵魂。心中洋溢的那股激情,是爱情还是母爱,永远也分不清……”而由于母性的苏醒,在接下来的爱情或婚姻的日子里,她们便一改少女时期的矜持和胆怯,而变得主动、坚决、成熟甚至勇敢起来,似乎,生活中没有她们适应不了的环境,磨难中没有她们面对不了的现实,她们脚踏实地、专一执着地营造着自己的幸福,她们义无反顾、昂首挺胸地迎接着爱情的风雨,即使情况发生突变,她们也依然坚强,依然执着。如《蜀道难》中的私奔女子,面对途中意外变卦的“他”,她没有愤怒,也没有埋怨,而是独自凄然地继续往前走了;《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子”,在舆论和丈夫的双重围攻中,她选择的也是和所爱的人去双双殉情;《小城之恋》中“短小粗壮”的女文工团员,经过了一场浑浑沌沌的情欲激战之后,面对着不该出生的私生子,她的精神却仿佛得到了洗礼一般:“心里明净得像一潭清水,她从没有这样明净清澈的心境,新生命的声音对一个母亲来说,犹如来自天穹的声音。”[24]
王安忆总是把这些女性写得很美、很自然,而她们的这种美、这种自然又均源于她们天生的母性的呼唤和皈依,在她认为,这才是女性的自然属性,也是所有传统妇女终生所能奔向的最高的境界了。
模式二:“永远也长不大”(王安忆语)的令人失望的男性形象。
这些男性由于品貌的文雅、出众,性格的温柔和体贴,在初次相遇时,往往颇得女孩子们的青睐和爱慕,但随着交往的日渐加深,他们身上所隐隐暴露的脆弱与怯懦,又会使这些女性们欲退不能、欲进也不能——他们一概撑不起自己头顶的那片天空,甚至连他们的爱情,也多是建立在对母性呼唤的基础之上的,而深恋着的女性之于他们,几乎就是母亲的化身,他们所以走近她们,走进爱情或者婚姻,完全不是出于成熟、出于需要,而是因为这些女性“内心的强大”、“有着广博的胸怀”、“可以庇护一切软弱的灵魂”,总之一句话,是因为这些女性可以给予他们安全与依靠!就是这样的连自己都需要别人来保护的一些男性,在危机四伏、大难临头之际,他如果不选择逃离(如《小城之恋》中的男主人公“他”)、不选择听之任之(如《流逝》中欧阳端丽生活中的男性),那么,他们又能去干些什么呢?
因此,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便不自觉地成了生活中的强者形象,她们一方面明显地克制着对男性失落的不满和无奈,另一方面,却能仍然忠贞不渝地守护在这些男性们身边,默默地充当着奉献者的形象,甚至,能像怜爱自己的孩子一样自始至终地怜爱着这些男人——王安忆对此早有洞察,在《荒山之恋》中她就曾写下过这么一段近似名言的句子,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作家对这类现象所做的剖析和评判,她说:“其实,那男人配不上她那样的挚爱,可是,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爱情的理想。”[25]
模式三:作者对两性关系的妥协和宽容。
与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红极一时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家林白、陈染所具有的鲜明的解构男性神话、颠覆男性权力的激进的写作倾向截然不同的是,王安忆始终很温和、始终很传统。虽然在她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在心灵深处,都充满了对当代男性的悲悯、感伤、失望、怨恨,但她们却从不因此就抛弃他们、蔑视他们、排斥甚至诋毁他们,相反,“她们正是在两性之爱的基础上重新树立着自己的女性形象。”[26]笔者认为,王安忆的这种妥协与宽容的态度正是她对传统认同和顺从的具体表现,她甚至还向往能回到几近原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自然状态,这进一步阐明了王安忆的植根于传统但又直指现实的独特的女性观,即(一)王安忆对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还是维护的;(二)王安忆对“男女平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却出观的“阴盛阳衰”现象明显不满;(三)妇女也能顶一片天之后,“男主外女主内”其实就成了一种最自然、最具古典人文之美又最合人伦常情的家庭模式——由于王安忆的女性观乃至人生理想于无形中暗合了当代中国妇女的现实生活处境与态度,因而她在这一方面的质朴立场以及执着追求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总而言之,鉴于王安忆所具有的上述几个独特之处,因而笔者便直观地将她归结成——一个把不媚俗的前卫战士与不落伍的古典女性两种气质完美和谐地统一于一身的杰出作家——我想,这绝对不是妄加评判。
[收稿日期]2000-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