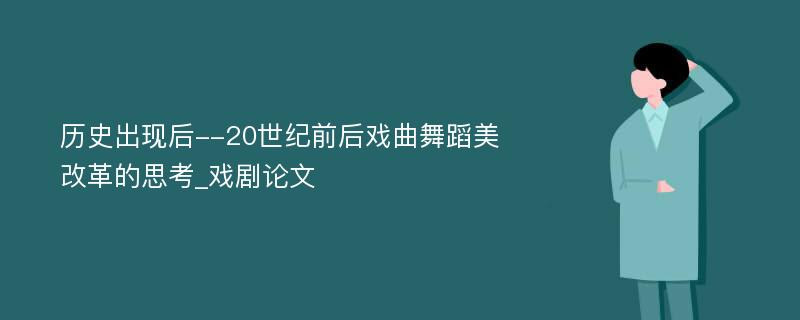
在历史的表象后——对20世纪前后戏曲舞美变革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舞美论文,表象论文,戏曲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风东渐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的戏曲舞台美术曾发生了一 系列引人注目的变革。1874年,英国侨民在上海建立了兰心剧场,这个具有较标准的维 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建筑物,直接影响了中国剧场的建筑样式,1908年,仿造欧美剧场的 新式戏曲演出场所——上海新舞台建成,剧场结构上吸收日本、欧洲的舞台样式,为我 国第一座具有近代化设计的新式剧场。此后,以新舞台的基本样式,上海、北京、西安 、武汉、广州等一些大城市竞相建造了一批新式剧场,并于其中废除了传统观剧中的陈 规陋习,净化了演出场所,改善了观演关系。在这种新式舞台的演出中,戏曲舞台美术 发生的变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既有西方戏剧的影响,也是传统戏曲演出长期以来“欲 补从来梨园之缺陷”[1]的探索和表现。灯光在旧式茶园和新式剧场中的出现,机械装 置作为一种新的在舞台上制造变化的技术手段被大量运用,写实画景更成为戏曲演出中 吸引观众不可少的一部分。纵观这一时期传统戏曲受西方舞台美术的冲击而形成的这一 波澜,它的大受观众欢迎,令观众趋之若狂,这一现象本身都说明了些什么?在将近一 个世纪过去之后,这段演出史留下的轨迹和新的戏剧观念使我们重新探索,寻求对当今 戏曲舞台美术发展有启示性的东西。
1.戏曲观众视觉欣赏力的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戏曲舞台受到西方舞台影响的前后或同时,那一期间中国人无 论是在海外观剧,还是对于外国戏,包括洋人来华演出和中国早期话剧,几乎都津津乐 道于其中景的运用。《航海述奇》中,张德彝在介绍了巴黎的戏园之后,不无欣赏地描 述了演出中的舞台美术:“其戏能分昼夜阴晴;日有电云,有光有影;风雷泉雨,有声 有色;山海车船,楼房闾巷,花树园林,禽鱼鸟兽,层层变化,极为可观。”光绪五年 (1879)正月19日,张德彝在俄国巴立帅戏院观看了芭蕾舞剧,舞台上四季的变换,“景 致尤觉奇异,一望千里,真假非目所能辨。[2]”在《随使法国记》中,他描写巴黎演 出《浮士德》的舞台,“……高山皓月,长江石桥……以双眼千里镜望之,真假难辨。 ”
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19世纪60年代在香港巴黎等地都看过一些外国戏,当时西方剧场 中还在用瓦斯灯照明,但西方舞台美术的发展已可以在舞台上逼真摹写各种景象,从布 景绘制到灯光由于长期的积累和探索,都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从王韬所著的《漫游随录 》可以看出,“只有西方舞台的布景、灯光和服装,令他惊羡不已。”[3]
兰心剧院19世纪后期在中国建立之后,虽然这里演出的外国戏只有极少数中国人进去 看,但它毕竟为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直接了解西洋演剧的窗口。看过兰心剧院演出的人 ,最感兴趣的还是“其裳服之华洁,景物之奇丽。”[4]1907年,王钏声领导的春阳社 在兰心戏园演出了根据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黑奴吁 天录》,采用西洋话剧的布景、灯光和服装,使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西方风格的舞台美 术,其中的布景、灯光使台下的观众惊羡不已。
1919年天津出版的《春柳》杂志中,齐如山也这样介绍西方的布景:“所以西洋戏园 ,于这些地方也很注意。比方风雨雷电、火车轮船、空中海底以及各种设施、建筑,到 戏园中一看跟真的一样,然而都是假的。”他还举出许多例子说明洋布景何以优于中国 舞台。戏曲舞台上出现“西法”布景后,新舞台——这个带转台的新式剧场的演出中, 舞台布景“非常动目”、“处处皆肖”,“观者无不抚掌”,[5]令观众大开眼界,甚 至成了新舞台开幕以后,生意鼎盛的原因之一。周志辅在《北平皮黄戏前途之推测》一 文中也这样记载:“迨于清室既亡,帝制推翻,人的关系先随之消灭,而外汇戏逐渐来 京。其来自沪上者,昔日谓之海派,近且大受欢迎,如真山真水,五色电光,均为都人 人士所未习见,故民国以来演戏者不能不趋迎时尚,凡所新编者,无不采取外汇演法。 ”
使人深思的是,上述在当时戏曲演出中,布景因素为观众所需要的程度,这一现象并 不是这一时期中国戏曲舞台所独有,在西方演出史上亦有类似的例子:“在英国王政复 辟时期和18、19世纪,剧场中新布景上台成了特殊的事件,它轰动一时的魅力使得门票 价格因之上涨。”[6]1856年,英国著名舞台美术家威廉·台尔宾设计莎士比亚的《冬 天的故事》,布景使用写实的手法,以壮观华美的描绘表现了奢侈的东方。尽管它与原 剧本精神相距甚远,但仍被评论界当作是舞台演出的一大胜利而见诸于极端,创出了连 演120场的记录,并首开英国为每个戏的演出专门制作景的先河。
甚至中国戏曲本身,演出史上也不乏其例。最为人所乐道的是明张岱的《陶庵梦忆》 ,其中对于戏曲演出中的这类处理不无赞赏地有过如下描述:“刘晖吉奇情幻想,欲补 从来梨园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叶法善作,场上一时黑魆地暗,手起剑 落,霹雳一声,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圆如规,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中坐常仪, 桂树吴刚,白兔捣药。轻纱幔之,内燃‘赛月明’数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 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此外,《扬州画舫录》上记载,乾隆年间的 江湖行头中已把大帐、小帐、云旗、水旗、布城等作为昆剧戏班的基本设施了。
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戏曲舞台上出现的这一变化并非孤立的现象,其后至今将近 一个世纪戏曲演出中这一现象的延续更说明,在这方面仅仅将之贬斥为“观戏者多观几 张油画而已”,[7]迎合观众、取悦观众,或者简单地停留在满足观念“看热闹”,“ 好奇”的解释上,显然是表面的。
那么,在这种令观众悦目、好奇的舞台布景的表象之下是些什么?或者说景“好看”在 哪里呢?
在人们的视觉经验中,“好看”的范围并不狭窄,淡雅或浓郁,鲜艳夺目或沉静朴素 都可以是“好看”的。与传统戏曲表演中常用的“身段画景”同理,舞台布景在表现环 境时,主要不仅在于表现了什么,更在于怎样表现在其中,依靠形状、色彩、速度和节 奏影响着观众。今天,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当时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这些:“舞台设 计是一种经过组织的空间,充以各种记号和符号,存活着各种形状和物体、色彩和材料 。这种装置会产生一个能抓住观众注意力的世界,起着启示作用。”[8]在演出空间中 ,这些本质的造型因素,是中外戏剧中都存在的。
舞台美术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如果其作用仅在于表明一个环境,那么用台词、演员动 作、甚至音响也可以交待清楚,大可不必用舞美手段。在舞台美术造型手段表达环境的 层次下面,有着一个更丰富、更深、更微妙,也更直接地触动观众心灵的天地。在这个 天地里,正是依靠图形、色彩(光)和质地材料作为表现语汇,靠它们之间的组织和构成 的空间作用于演员动作,表现出一些复杂的超出于环境交待的内容,从手段上极大地丰 富了表演艺术,增强了舞台美术的能动性。所有能够为表演艺术锦上添花的手段都是不 可排斥、不可否定的。
20世纪前后,戏曲舞台上的用景远非完善,但它无疑具备了上述起码的这些造型因素 ,并且正是以此形成了吸引观众的力量,使观众在戏曲舞台新的景观冲击之下,获得了 新鲜的视觉体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观众视觉欣赏力的觉醒。如果由于其发展 初期的不成熟,乃至弊端而一味否定无异于因噎废食。
2.戏曲舞美原则的拓展
19世纪末,在“西法”绘画和画景方法的影响下,上海开始有了“画景戏”。1893年1 1月,天仙茶园在排演《中外通商》一剧时,就曾聘请“闽广彩匠”和“西洋画师”来 从事整堂戏软片的布景绘制工作。1909年初群仙茶园演出《建造洛阳桥》一剧时,在报 刊广告上大加宣传这个戏的“特别画景”,即平面绘画写实布景的景物造型方式。上海 新舞台建成之后,曾请“名画家张津光君精绘各种背景,随剧敷设,令人眼界一新。” [9]许多当时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如梅兰芳、欧阳予倩等都曾在这种写实布景的舞 台上演出过。著名京剧演员、戏曲教育家王瑶卿在在1951年北京召开的“新中国戏曲舞 台装置座谈会”上说:“以前我在北京第一舞台唱戏时,每一出戏都是有布景的,…… ”。
很明显,在这一时期中,无论是画景还是立体、机关布景,戏曲用景中出现了大量的 写实因素,市井旷野、卧房厅堂、花园森林、寺院佛殿、“真山真水”等几乎无所不包 。尽管其绘制还无法与西方写实景相比,使用中也成败参半,但它为观众所认可的结果 说明,这种舞美造型手法上的写实并不是与戏曲程式化表演格格不入的。
在戏剧演出中,演员表演可以给同一环境或景物带来不同的意义,这一规律几乎是与 这门艺术的历史一样长久了。在传统戏曲剧目的演出中利用演员的表演,在明亮的舞台 上,为《三岔口》创造了黑夜的感觉;在《秋江》中演员的表演可以使舞台台板成为一 江秋水。一桌二椅更是由于演员的表演规定而超越了其本来的意义。从那时以来笼统地 争论戏曲能否用写实景,表面上看似乎是出于维护戏曲中景和表演的统一,而实质上却 忽视了活生生的戏曲演员对景物因素的规定作用,将景与演员分开开来孤立地看待。剧 场演出的假定性,可以使人们对演员的规定作用深信不疑,这种约定俗成导致对写实或 具体因素的规定是多种层面的,它可以是剧场舞台原有意义的改变,也可以是舞台上包 括道具在内的具体景物的本来意义的超越,这种变化有时可以是类似另一种意义上的“ 指鹿为马”,如一桌二椅可以是城池、山坡、店堂等,有时仅仅将之视为装饰,如传统 戏曲中的守旧、台帐等,在这种情况下,景物本来的意义是近乎视而不见的。
所有这些,无不源于戏剧演出的“剧场性”物质,而这种由演员表演给舞台上景物所 带来的不同程度或层面的规定,说明在表面上苛求舞美造型手法与表演形式一致实际是 不符合剧场性艺术规律的。西方芭蕾舞剧、歌剧中表演形式与写实布景因素的成功结合 证明了这点。二十世纪以来,中外话剧演出中,接近生活的大量表演形式与抽象舞台设 计因素的结合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当代话剧演出中,因演员表演规定而改变 景物形象原先意义的例子更有助于说明这点。话剧《桑树坪纪事》中,转台上组合在一 起的山涯、窑洞、院落,这些写实的形象,在分别使用时表示了各自具体的形象,而当 它们在演员长途的表演中旋转起来时,原先局部的意义便发生了变化,进入了大范围的 整体形象中,也就是说,它们已不再是那一家、那一村的院落和村头,而成为整个黄土 高原的缩景。鲍加特列耶夫指出:“舞台上起着记号作用的事物……获得了它们在现实 生活中所没有的独特面貌、性质和特征。”[10]K·布鲁莎克也认为:“对于一堂布景 最重要的是它的意指功能。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物体的实用功能比它的意指功能更重 要。”[11]明确地区分了舞台上与生活中景物形象的不同,也暗示了舞台布景在表现手 段和方式上更多、更灵活的可能性。
演出进行过程中,正是这种“记号”在相互作用下变换着它们的意义。在此情形下, 无论是演员直接触动的景物形象,如道具和其它直接与演员动作相关连的造型因素,还 是作为背景的那些间接与演员发生联系的景物,其意义都在于彼此存在的联系之中。在 这种联系之中分析对待戏曲舞台美术造型因素,特别是写实因素,有助于对景物与演员 的关系有更清醒的认识。面对观众和评论界对戏曲用景的不同看法,前者的热情和后者 的怀疑持续多年。然而以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场来看,它写实的 背景画幕曾被认为是与演员驰骋的虚拟表演在内容和风格上都严重不符,但是在与演员 表演的结合上,这一布景已不仅仅是一个具体地点的交待,而是暗示了整个林海雪原, 一般观众也没有迁怪景物的静止不动而影响演员的虚拟动作。相反,布景的具体性由于 演员的表演而得以淡化,并且起着有效的装饰作用。可见,在戏剧空间里,在演员作用 下,写实的布景因素,并不仅仅是对于特定场面的地点说明。适合于全剧所有场景的综 合布置,一组真实的环境形象或者一桌二椅,一个概括全剧气氛或主题的画幕都可以表 达比地点说明之外更多的内容,这并不会削弱戏曲本身的特点,危害演员的表演,相反 ,它正是前面所述的剧场性规律、戏曲景物造型规律的延伸、拓展,体现了具体性与虚 拟性共存的可能。
从20世纪初到现在,写实手法的舞美手段在运用中确实良莠杂陈,有不少失败的教训 ,但这并不应成为戏曲不必用景或不能用写实景的理由。戏曲演出中各成份的比重、关 系、戏曲舞美的写实程度、用景程度、应全盘把握,而不应孤立论其成败。审美观念、 方式以及具体的艺术技巧可以相互借鉴、渗透、融汇,不应有一种固定的配方。时代社 会,剧本内容,演出条件,审美需求诸方面的变化,要求戏曲舞美与之相适应,而变革 的突破点正在于戏曲本身的特点与新的审美角度的交汇处。戏曲写实景中具体性与虚拟 性共存的规律,正显示了这样的突破点之一。
3.多元化戏曲舞美的新开端
当中国戏曲舞台美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趋于写实手法的热潮时,西方戏剧却正 在突破19世纪写实风格的舞台美术,追求单纯、抽象和反幻觉的表现手法,经历着一场 重大的革命。瑞士舞台美术家阿披亚的“节奏空间”,英国设计家戈登·克雷的条屏布 景以及梅耶赫德和莱因哈特对演出形式的实验和探索,使得这一时期欧洲舞台美术呈现 出五光十色的局面。“这是个充满危机的时期。旧世界逐渐消失,新形式以经验与思想 这两者的异乎寻常的对抗中产生……。”[12]
为什么会有上述反差?为什么一方面是当时观众对戏曲使用“西法”布景的极大热情, 一方面是后来西方人认为戏曲不必用景?其间包含了两种不同文化相互渗透的辩证法。 事实上,每一方都在从对方的戏剧形式中寻求自身革新的支持,欧洲人评价戏曲舞美自 有其文化背景,每当一种艺术形式达到成熟、完美,被充分应用到饱和点之后,就必然 会重使人感到不满,而又尝试着寻找新的形式。在欧洲的演出史上,镜框舞台和写实布 景曾是对旧有演出形式的革命,但它发展到十九世纪末,舞台布景对于写实的追求达到 了极端,其中以法国的安图昂在舞台上挂起真的牛肉、骨骸,美国的贝拉斯库买下废旧 房间搬上舞台用于演出最为登峰造极。所以,正如丹尼斯·巴布莱特指出的那样,欧洲 舞台“布景幼觉的创造不可能再取得任何进展,除非以现实本身来取代形象,这也就等 于是对它的否定,……现实主义已经把幻觉发展到最完善的程度,正象其它艺术那样, 已到了背叛曾使其获得发展的这种结构本身的时刻了……。”[13]
就艺术手法来说,当陷于一种思想之中,用一种方式观察事物的时候,人们所获得的 全部感觉、经验都是经过这种方式过滤的,这就容易使用自身的感觉无法超越自己的方 式,感觉与表现方式互相依存,互相验证,想要超越既有的方式,除非有别外一种力量 的推动和别样的方式来冲击。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东、西方戏剧互为发展、推动的 历史正说明了这一点。二十世纪前后,经过长期发展趋于成熟完善的中国传统戏曲,也 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面对舞台景物造型方面的长期“缺陷”,在西方舞台美术表现形式 的影响和冲击之下,形成了新的变革条件,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的视觉需求,使之在 舞美因素上得到了发展。甚至著名戏曲演员盖叫天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那时候,上 海有电影,有话剧,有魔术,有飞车走壁,……舞台上灯光布景,五颜六色,全是新鲜 玩意儿,我寻思:要是老靠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幔子,不是太单调了吗?”[14 ]这些都更具体地说明传统戏曲在这一时期受西方舞台美术影响而产生变化的必然。
从历史上看,这类现象于后来的几十年里至今发展并不平衡,在艺术格调、表现手段 、技术手段上出现了新旧杂陈或停滞的状况,由此而引发的戏曲用景也成了长期以来有 争议的问题。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写实绘画布景,还是类似机关布景的机械装置在戏曲 演出中一直没有中断。从六十年代戏曲现代戏到八、九十年代多种对戏曲用景的探索, 不仅延续、发展了本世纪初我国舞台美术的追求,而且也是在更大程度上与西方舞台美 术交融的产物。六十年代,现代京剧《黛诺》、《节振国》、《沙家浜》、《红灯记》 等戏的写实布景,八十年代评剧《邻居》中与戏曲动作密切结合的旋转门装置,沪剧《 月朦胧鸟朦胧》、汉剧《弹吉它的姑娘》中,从“一桌二椅”演化出的平台与写实性局 部景的结合,都表明了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艺术上,一种新形式的产生并不意 味旧形式的灭亡,在求变求新中走向多样和丰富是艺术发展的趋势。从今天的角度重新 审视二十世纪前后戏曲舞台美术的变化,对当时写实布景等现象主流的肯定,不在于这 一形式可以取代传统戏曲舞美形式,而在于它打破了在那之前戏曲演出中景物处理上基 本上单调的局面,表明了一种多元化的可能。
时至十九世纪末,整个人类社会都处于空前的剧变之中,在中国伴随着鸦片战争之后 相继发生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西方戏剧文明以多种渠道传入,在这种 情势下,亟待改进的传统戏曲在舞台美术面貌上的改观是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致的求 变、图新的历史性选择。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一历史现象与同时期西方舞台美术的革新相比,彼此进展不同 。后者的努力丰富了二十世纪西方戏剧演出形式和舞美风格,成为西方现代戏剧舞美的 重要标志;而前者的发展却并不平稳,成为长期以来总是引起争议的问题。将其归结于 不符合戏曲艺术规律的说法显然有所偏颇,不利于戏曲舞台美术的发展。
与西方舞台舞术相比,当时中国戏曲舞台美术采用西法的时间短,技术手段与技术规 律方面的素养尤其显得薄弱与不足,不象前者经历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自然成熟 过程,其时间达几百年之久,这就使得中国的“布景画师们往往都是用师傅带徒弟的方 式带出来的,”“没有从生活中直接吸取养料的习惯,也没有经过比较科学的方法训练 ”。[15]这种自身的不足,使得其成分芜杂,没能形成一种统一的风格语汇。此外,西 方舞台美术的变革和发展是随同几代在导、表演上有创见的戏剧家全方位推进的,阿披 亚戈登·克雷、梅耶赫德、莱因哈特等等,无不对戏剧有整体的把握和主张。中国戏曲 在当时,却缺乏这类将舞美手段与表演统一改革的人物,使得舞美与戏曲演出没能具备 总体上协调应变的能力,而这恰是戏曲表现手段上的自足所要求于舞美变革的。
不同文化的会合,不可能不引起矛盾,不可能短时期轻而易举地成功结合,需要付出 具大的努力和长期的实践。戏曲舞美在二十世纪前后所产生的变革说明,不同文化、艺 术的相互会合、影响和促进是势所必然,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从根本上说,也是符 合艺术发展规律的。对于外来文化的“借鉴”、“拿来”、“用之”、“化之”要经过 长期的消化,戏曲艺术的生机正决定于自身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程度,囿于守成也就走向 了僵化。20世纪前后戏曲舞台上发现的一系列变化,予示了戏曲舞台美术多元化的可能 ,其积极的方面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标签:戏剧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演员论文; 剧场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都市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剧情片论文; 艺术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