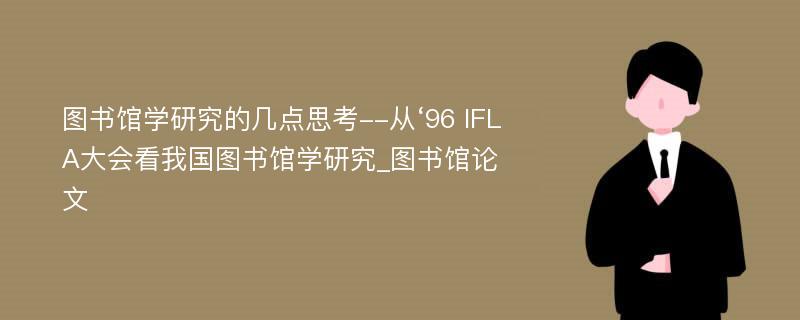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从’96IFLA大会看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书馆论文,几点思考论文,大会论文,国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家、学者谈北京国际图联大会
盛况空前的北京第62届IFLA大会已在一片赞誉声中和热烈的掌声中降下了帷幕。它既给我们带来了光荣与自豪,也给我们注入了新的能量、新的思想和新的气息,同时,更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视野和无限的思考空间。在经历了炽热的思想碰撞和文化交流之后,笔者谨以个人的亲身感受,谈谈自己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1 我们做了什么
从《IFLA大会计划》来看,这次大会在1996年8月23日至30日的8天中共举行了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各类会议。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1]:在大会期间共举行了大约63次比较正规的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约285篇,其中中国作者77人次宣读论文54篇,约占宣读论文总数的1/5。
与历届IFLA大会相比,我国代表在这次IFLA大会上所提交的论文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论文数量最多。这次大会,我国代表共提交了54篇论文,加上费孝通的基调发言论文,实为55篇,这与1929年召开第1届IFLA大会(意大利)时中国代表提交的5篇论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比其后我国代表向IFLA历届大会提交的论文数量亦要多出许多倍。第二,提交论文的作者人数最多。这次大会,我国提交论文的作者人数共达77人次,这亦是空前的。第三,涉及面最广。在63次学术研讨会上,我国代表提交的论文涉及到39次学术研讨会,占研讨会总数的61%,这也是空前的。所有这一切的确令我们感到高兴,但并不值得骄傲,因为这并非在完全意义上反映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道主之“优惠”。
即便有如此之多的之最,我们也不难看到我国代表所提交的论文有如下几点不足:第一,论文作者的层次不高。虽然我国共有77人次提交了学术论文,但是在这77人次中象张琪玉教授这样的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很少,因此,没有完全反映出我国学者在图书馆学各研究领域的真实水平和实际的高度。第二,研究的领域局限性大。我国代表提交论文最集中的主要有4个研讨会,1.“图书馆建筑与设备”(主题:中国图书馆建筑)3篇4人次;2.“生物和医学图书馆”(主题:东西方医学图书馆界)5篇9人次;3.“儿童图书馆”(主题:中国的儿童图书馆与儿童的阅读活动)3篇5人次;4.“教育与培训专题研讨会”(主题:中国的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3篇6人次。这4次研讨会,我国代表共有24人次提交论文14篇,分别占我国代表提交论文总人数的31%和论文总数的25%。而这些研讨会的主题均为“中国”,由此可初见其局限性。再者,作为更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研讨会,大会共举行了17次,而有我国代表论文参与的仅7次,这亦颇能说明问题。
2 我们没做什么
从这次IFLA大会来看,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整体的方向把握上存在着不少重大的缺陷,而这些重大缺陷的存在说明了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聚性的封闭式研究。
其一,自70年代迄今,IFLA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相继制定了“世界书目控制与国际机读目录(UBCIM)、“出版物世界共享(UAP)”、“出版物的保护与保存(PAC)”、“世界数据流与远程通信(UDT)”和“发展第三世界图书馆事业(ALP)”等5项中期计划。这5项中期计划一直是IFLA工作的核心,更是全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远大理想与目标,它们几乎涵盖了图书馆事业领域的一切重大课题,是70年代以来世界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然而,虽然过去我国有少数学人曾注意到这一点且做过一点初步的研究,国内亦曾开过几次专门的学术研讨会,但是,我们的研究仍停留在介绍的层面上,且许多人因为并不了解这些计划,许多研究在想当然的情况下谬之千里。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在本次大会上凡是有关上述5项核心计划的会议,我国的学人均是既无论文,亦无发言。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我国对IFLA的5项中期计划参与不够,关注不够;二是我国的图书馆界学人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不仅没有着力研究,而且严重地忽视了。因而,在天时、地利、人和这种万事俱备的大好时刻,我们在这5项计划的研讨中找不到或者看不到国人的一席位置。
其二,如果说严重地忽视了对IFLA的5项核心计划的研究,仍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在宏观方向把握上的严重失误的话,那么,在微观研究层面的把握上我国同样存在着诸多盲区。从本次大会来看,有关“地理与地图图书馆”、“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采访与馆藏发展”、“政府信息与官方出版物”,以及“盲人图书馆”、“艺术图书馆”等主题的研究,我国亦有许多的忽视。典型的例子是在“艺术图书馆专题研讨会”上,主持人企图寻找一位中国艺术图书馆界的代表介绍一下国内艺术图书馆开展有偿服务的情况,竟然不能如愿。诸此种种说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在研究面上有不少被忽视的领域,许多方面的研究我们不是做得不够,就是没有做。
第三,我国的图书馆界学人对国际图书馆学研究组织的参与极为欠缺。迄今为止,我国图书馆界学人在IFLA专业机构中任职的屈指可数,且几乎无人担任要职,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图书馆界学人的“自我推销”很不够,在世界图书馆学研究的舞台上畏手畏脚,冲不出去;另一方面亦说明我国图书馆界学人中确实缺乏能够走向世界的人。而这一点十分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水平。或许,人们也许会说中国乃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起点低,但是,同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印度,为何能够产生一个世界顶尖的图书馆界学人阮冈纳赞。这其中颇值得我们回味与思考。
3 我们在做什么
回想一下80年代以来的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我们的学人一直在做许多可能是现实的却是没有意义的研究,或者说是没有学术价值的研究。
其一,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上,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研究先后经历了几次“转变方向”式的变化。变化的结果是引进了许多新的名词、概念、术语、理论,不断地破坏和构筑了一个又一个的“思辨”性的理论框。理论性越来越强,越来越玄,而离现实越来越远。图书馆学乃是一门致用的学科,欧美图书馆事业发达,但并没有象我们这样的连自己都看不懂的高深图书馆学理论。一言以蔽之,我们一直在做“空疏”的理论研究,而不是“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其结果是场面热闹,实效甚微。
其二,前几年大家都十分热衷于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图书馆事业,如“有偿服务”、“信息开发”和“信息商品”之类,似乎颇具新意和现实性,但这的确是一种畸形的研究,一种“中国特色”的研究。这种研究在另一种经济体制的欧美图书馆学界看来既是难以理解的,也是滑稽可笑的。
其三,近几年大家又热衷于研究信息产业,新人新作新思想层出不穷,热闹非凡,就连《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亦不厌其烦地连篇累牍地刊载许多“佳篇名作”。然而,仔细分析一下,除了研究很“热”以外,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而尤为重要的是,这其中有一个颇不为人注意而又十分危险的研究趋向,那就是,人们在纷纷地回避图书馆这个信息服务业中的“支柱产业”。言“信息产业”往往只谈电脑业、通信业等“信息技术业”,而忽视“信息服务业”;言“信息服务业”往往中谈“信息咨询业”,而忽视“图书馆事业”。这样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4 我们该做什么
放眼看一下世界,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虽然有了可喜的进步与发展,但是与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潮流尚有不短的差距,还有许多的领域等待我们去开拓,还有许多的工作尚需我们去做。而在众多的需要做且应该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恐怕乃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做且能够做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着力从事“世界图书馆学术”的研究。这里所说的“世界图书馆学术”乃是指全球性图书馆学术的重点、热点、焦点的研究,如UBCIM、UAP、PAC、UDT、ALP之类。学术没有国界,图书馆学术更是没有国界。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固然要立足于国情,但首先应该是随着世界潮流演进,否则,我们的研究则是封闭性的研究,是一种“化石”性的研究,是一种不入流(“三教九流”亦为入流)的研究。事实上,80年代以来,我国在分类编目诸方面的研究上成就最为突出,文献工作的标准化已颇近国际水平,但如何从更高的角度去认识、去研究,我们则没有做到。如果不去抓图书馆学研究的全球性热点、焦点,而是人为地自我制造热点,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就难以与他人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没有“碰撞”,没有“共鸣”;也就冲不出中国,走不向世界。
其二,积极参与世界和国际图书馆学研究与活动。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该做的工作还很多。在这一方面,至少有两点亟待我们去做。第一,努力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我国的图书馆界学人的外语能力与水平能够应付国际交流的太少,这次IFLA大会,中国有800名代表参加,绝大部分中国代表与外国代表没有“共同语言”,根本就无法“交流”,甚至连组委会的要员亦不乏此种情形。在大会期间,有同声传译的场合可以见到我国的部分代表,但在许多研讨会上,占大会代表总数三分之一的中国代表却凤毛麟角;许多人只不过是拿着大把的“银子”去看了一场热闹,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哀。第二,要在图书馆学研究的国际舞台上谋取一席之地。这至少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将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努力推向世界。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学人在国外图书馆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者甚少,国内的期刊虽然国外某些地方亦有订购,但因为语言的障碍,外国同行无法阅读。有趣的是,在国外的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图书馆学术的论文大多是外国人写的,虽然不乏优良之作,但皮毛之作亦不少。近数年来,笔者担任美国《图书馆与文化》(Libraries and Culture)杂志的审稿工作,每年要审数十篇有关中国问题的稿件,但几乎全是美国人的东西,真不是滋味!我们的成果不是没有,而是没有“推销”到国外,别人也就无从了解,我们也就始终摆脱不了“神密的中国图书馆学”的状况。另一方面是要努力在国际图书馆学研究的组织中去谋取一席职位。国内有的人很看不起这一点,颇有点夜郎自大,然而,谋取这样的一席地位本身就是一种国际的认可。有了它,我们才能在国际图书馆学研究中去扮演角色,而不是做“群众演员”,中国的图书馆学术才会具备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
其三,大力弘扬我国的图书与图书馆文化。许多年以来,笔者一直对外国图书馆学界对中国悠久的图书和图书馆历史知之甚微颇有感叹,现在看来,我们完全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怪自己无能。在这一点上,根本就不存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原理和规则。仔细地看一看我国学人在国外图书馆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和国外发表的有关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学术的论文,几乎清一色的集中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这一主题。这一方面说明别人非常希望了解和认识我们,另一方面也说明要走向世界,首先要把我们的“形象”推介出去。以笔者为例,在本次大会上笔者应邀撰写和宣读了两篇论文,其中在图书馆史圆桌会议上宣读的《庚子北京困围时期中国典籍的劫毁》(与美国戴维斯教授合作),在国际上引起了始所未料的广泛反响。国内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China Daily》以及许多其它报纸均纷纷刊发了新华社的专题报道;香港、东南亚、北美的华文报纸纷纷转载;英国《泰晤士报》(Times)发表评论,现在《IFLA杂志》(IFLAJournal)、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刊《Amcrican Libraircs》、法国图书馆协会会刊《Bullctin de informations L'ABF》亦将以不同形式发表。另一篇在图书馆学理论与研究组宣读的《中国图书馆学信息研究之文献计量分析》亦将在亚洲第一份区域性图书馆学期刊《Asian Librarics》(马来西亚)上发表。前者可以自吹为本次大会最有影响的论文,但是,扪心自问一下,这篇论文的确做得不好,很平常,甚至投到国内的许多杂志上去都会退稿。而且这两篇论文如果不是受IFLA专业组的邀请而写,在我国的论文推选中亦不可能入围。这其中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当然,它更说明了弘扬我国图书和图书馆文化的重要性。如今不少人不愿研究历史,甚至对历史研究采取鄙薄的态度,试想抛开中国图书馆的悠久历史及其研究,我们在世界图书馆事业舞台上还有多少力量令我们挺直腰板呢?
其四,应该勇于面对现实。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图书馆学信息学研究自觉或下意识地形成了一些“禁区”。对于“信息自由”、“信息民主”、“信息权利”等十分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学人不是忽视了,就是有意回避。大会期间的此类冠以“内部”的研讨会更是阻吓了不少的学人。笔者觉得,没有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人文精神,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学术成就。学术研究不应该设立“禁区”。而上述问题正是“信息社会化”、“社会信息化”的关键之所在,只有技术层面的支持,而没有制度层面的支持,这“两化”也就“化”不起来。因此,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努力地去研究这些问题,大可不必谈虎色变,或因噎废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