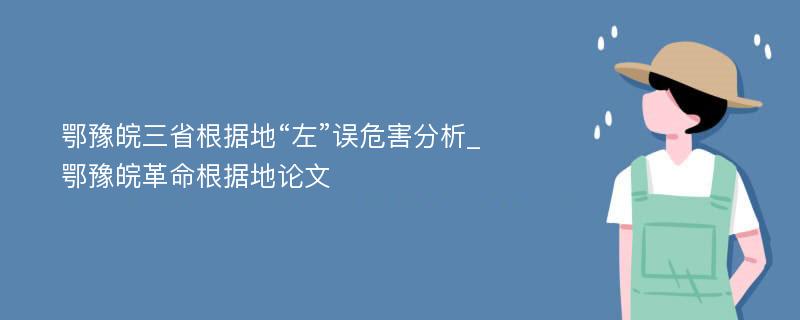
三次“左”倾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危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鄂豫皖论文,根据地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1)11-0072-0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先后发生的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了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本文对三次“左”倾错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害进行初步分析。
一、在革命形势分析上,认为“不断高涨”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1928年毛泽东说:“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6页。)但是,“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不切实际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5页。)1927年11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中说:“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页。)“各地农民暴动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暴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他对革命形势过高估计,对各地武装起义领导人分析当时的形势起了一个错误的导向作用,使有的起义没有正确分析当时敌我形势。戴季英总结黄麻起义经验教训时说:“工作上有某些盲动主义的错误。”(注:中共麻城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黄麻起义》,1987年版,第113页。)王树声说:“没有适时地主动地把领导中心和工农革命武装的主力转移到农村。”(注:中共麻城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黄麻起义》,1987年版,第144页。)不仅如此,甚至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有的同志认为武汉反动政府“派一个团不敢来,派两个团打不进,派一个师未必有”,“农民政府可巩固了”(注:郭家齐:《红安县革命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因而对敌人反扑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致使12月5日敌人反扑黄安城时,因敌强我弱,起义军在突围中损失惨重。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副总指挥刘光烈、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等牺牲,起义军300多人剩下72人,被迫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在皖西地区,1927年10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临委)不顾六安农协会只有一千余人,武器只有10支枪,而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势力强的实际,要中共六安特委立即组织农民暴动。六安特委坚持实事求是,没有执行省临委的错误指示,使一些同志受到处分。1928年3月,中共河南省临委指示六(安)霍(山)县委以六安为中心立即举行暴动,六安县委认为条件不成熟,应继续开展抗租反霸斗争,争取群众。这些正确意见被河南省临委斥之为“改良主义”。3月18日,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对反动势力估计不足,加之没有作好充分的群众工作,中共河南南五县特委发动的大荒坡暴动失败,特委书记汪厚之等28人壮烈牺牲。
党的六大指出:“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但是,1930年5月,李立三说:“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而且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群众组织可以飞速的从极小的组织发展到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伟大的组织,同样党的组织也可以在几星期甚至几月以内变成广泛的群众的党。”(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4页。)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提出:“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的战略总方针。”(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0页。)李立三“左”倾错误使鄂豫皖根据地也受到一定影响和严重损失。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发展,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的进攻路线。在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以后,就一直认为“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到来了”,叫嚷“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在其“左”倾错误领导下,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明积极鼓吹“中国革命高潮”,“中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要“准备向帝国主义国家战争”和“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二、在阶级关系问题上,加紧反对富农、中农
党的“二大”明确指出:党在目前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专题讲义》(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页。)党的“六大”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党的六大还指出:“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并指出反对富农的斗争要根据富农的态度。“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因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之更快的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为革命的积极的仇敌。”(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但是,193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特委指示中提出:“肃清富农的路线……特委的富农与机会主义的路线非常的严重。”(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96页。)在这种“左”倾政策指导下,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加紧反富农斗争。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7月提出“坚决反对富农”的口号(注: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在经济上实行大量的征发,并没收富农的一切土地。六安六区和霍山三区发生打倒富农,没收富农的财产,把富农赶上山头上去开垦等过火行为。由于“加紧反富农斗争”,致使农村阶级关系紧张,富农强烈不满。1930年秋,黄安县发生地主和反动富农煽动落后农民群众“反水”(反对共产党)事件。
王明在反富农问题上提出:“富农(大多数是封建的剥削者)的土地亦在没收之列,但是在他自己耕作的条件下,他可分得一部分坏的劳动份地。”(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3页。)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强调在土地政策上集中火力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上(以下简称中央分局),批评“有些地主富农分得了好的土地。”(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280页。)7月,又规定“富农土地亦应没收,没收后在用自己的劳动力耕种条件之下,可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富农多余的牛和耕具房子可以没收。”(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323页。)根据中央分局规定,出现了许多“左”的作法:对地主“扫地出门”,不分给任何土地,罚其做苦工。甚至地主家中寡妇也不给予出路。黄安县桃花四乡的农民把富农的小麦草头拿去填牛栏,紫云八乡把富农所有的东西全部没收。富农的猪还未养大,就杀着吃,怕被没收了。不准富农做小贩,富农做生意不给他路证。皖西北地区规定地主阶级和富农的土地全部没收过来,地主阶级土地没收后,不能取得任何丝毫的土地,富农如果要田地,可以给较坏的地,但必须自己耕种。富农收下的粮食只留给一点给他吃,其余的征发。有的地方曾驱逐富农。商城县有的地方实行“调换”,富农的好田与贫农的坏田换;富农的好稻子与贫农的差稻子换;富家的好房子、家具、农具与贫农调换。
侵犯中农利益。党的六大指出:“在中农占多数的地方,尤不可强施‘平分土地’。”(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0页。)“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8页。)而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规定:“使中农自动地拿出土地来平分。”“对过去分得好的土地不愿意拿出来重新分配的人,要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与他斗争。”(注:于吉楠:《张国焘其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61页。)这样,不仅抽出了中农多余(超过平均数)的土地,而且有的地方把中农的好地也抽出来了。在划阶级成分标准上,有的以余粮多少作为标准,结果把一些中农错划为富农。商城县四区六乡在重划阶级中,富农由21户增加到80户,中农由86户增加到118户,贫农由原来的348户减少到230户。这些作法,违背了团结中农的政策,损害了农民内部的团结,造成许多富农和富裕中农外流,树敌过多。
三、在军事战略上,推行“冒险主义”进攻路线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特征是调动各路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如毛泽东所说:“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提出:“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省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命令鄂豫皖边区的党和红军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切断平汉路,以进逼武汉。鄂豫皖根据地立即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地方暴动,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制定六(安)霍(山)暴动计划,强调凡有党员的地方都要举行起义。结果由于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出击平汉线,使根据地防卫力量空虚,给敌人进攻根据地以有利空隙,不仅起义失败,根据地也受到严重损失。到10月初,皖西苏区“几乎完全塌台,军事上只留很少部分”(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287页。)。敌人侵占根据地后,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在六安、霍山两县就杀害革命干部500多人,屠杀群众19600多人,拍卖妇女1690多人。革命中心区域的舒家庙等17个地方几乎没有人烟。黄安县行动委员会为配合全区总暴动计划,10月,强行组织地方武装攻打黄安县城,城未克,还死伤100余人。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无视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事实,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提出:“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在中共中央“左”倾思想指导下,7月,在商城县的余家集军事会议上,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威胁或占领大城市,竟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内下英山,出潜(山)太(湖),逼进安庆,威胁南京。红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当时形势,主张打下英山后,出击蕲(春)黄(梅)广(济),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援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但是,张国焘对红四军领导人的正确意见大加责难,说改变原有计划,“政治上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是与中央分局“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
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在1931年12月23日黄安战役胜利的当天,中央分局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1932年1月10日,张国焘在鄂豫皖省等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注:《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在这种轻敌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鄂豫皖省委又提出“偏师”说,认为“国民党的洛阳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提出“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和准备夺取武汉”(注:成仿吾:《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罪行》,《中共党史资料》(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6月18日,张国焘向中央报告说:“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根据张国焘的指导思想,6月19日,陈昌浩说:“国民党军队一天天的缩小,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已经占了优势。”(注:《鄂豫皖中央分局向新集市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分子联系会议的报告》(1932年6月19日)。)“过去是敌人包围我们,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注:《鄂豫皖中央分局向新集市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分子联系会议的报告》(1932年6月19日)。)“偏师”说和“坚决进攻”的错误战略方针,“种下了鄂豫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
四、在组织上,“肃反”扩大化
“左”倾机会主义者为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在组织上实行排斥、打击甚至残酷迫害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主要表现在排斥富农、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及“肃反”扩大化上。1930年9月,《中央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提出:“要切实组织并且整顿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吸引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参加,排斥富农和投机分子。”(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在这种“左”倾干部政策指导下,在组织上大批清洗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团员和干部。
张国焘为了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建立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在改组鄂豫皖根据地领导机构,独揽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大权后不久,开展“肃反”运动,作为宗派主义的排除异己的手段,以便建立他在党和军队内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
军队中肃反。1931年6月28日,张国焘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出“首先改造红军的成分,加紧红军中的肃反工作”。9月13日,派陈昌浩到安徽六安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撤销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替。陈昌浩污蔑“红四军过去实际上是改组派领导”,“红军中党团组织大半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包办,红军党的下层组织与领导完全在改组派手中”(注:于吉楠:《张国焘其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58页。)。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指示,立即开始进行“肃反”。9月底,红军移驻河南省白雀园,在张国焘亲自主持下,掀起了军队“肃反”的高潮。他打着反对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旗号,以红四军领导同志与其在军事方针上的分歧为借口,以蒋介石派特务搞离间为突破,以知识分子、地富出身和白军过来的人为主要对象,大搞刑、讯、逼、供,大搞株连。使一大批红四军优秀指挥员被杀害,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被张国焘等人整肃与杀害的红军排级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2500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有许继慎等10余人,红军第三十团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大约有500人上下。
地方上的“肃反”。11月3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中指出:“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地进行。”(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134页。)12月,中央分局临委发布通告,要求“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把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从我们党内、团内、苏维埃、工会……中清洗出去。”(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7页。)于是地方上的“肃反”开始在党、政、军内部进行清洗。张国焘全部否定鄂豫皖根据地过去的工作,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诬蔑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注:于吉楠:《张国焘其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58页。)。把黄麻地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说成是“土匪行为”;说“大部分商城共产党员是国民党左派,就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实际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或明或暗的反对共产党”(注: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篇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125页。)。结果,仅在商城县被错杀而有名可查的就有2150余人。张国焘还诬蔑皖西的党“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反革命”(注:于吉楠:《张国焘其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58页。)。从1931年5月到9月中旬,皖西共改造了9个区苏维埃,74个乡苏维埃。黄麻地区的8个县委书记被撤换了7个。英山县的苏区8个区委只剩一个区委书记。河南新集是3000余人的镇子,“肃反”搞得晚上没有行人,白天不敢一个人走路。
这次“肃反”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被张国焘整肃与杀害的红军、革命干部与群众有一万多人。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在“肃反”中,中央分局发出了“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的指示。(注:《鄂豫皖分局给陂孝北县委的指示信》(1931年9月19日)。)张国焘将“凡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解放军出版社。)。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一个连队要找一个能写写口令,搞点统计的人都没有。在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
肃反,不仅捕杀了大批军政党群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亡何时将至。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一部分革命群众不愿入党。“各县都是党龄极浅或能力极弱的同志。支部在停顿状态,支部中的党团员差不多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有的不愿当干部,“在地方上有一点文化的,成分不大好的人不敢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注:常毅:《我所了解的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几个片断》,《信阳党史通讯》,1983年第4期。)。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不如过去密切了,人民群众有时发现敌情也不主动地向党、政、军机关报告。
三次“左”倾错误,给鄂豫皖根据地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组织上造成了严重危害。究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03页。)
标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论文; 张国焘论文; 红军肃反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根据地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共党史论文; 李立三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