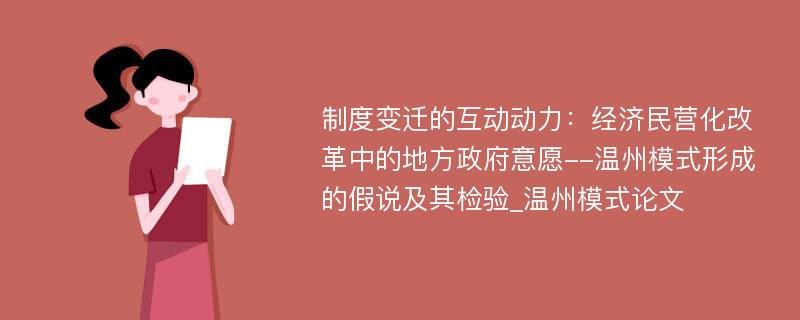
制度转型的互惠性动力:经济民营化变革中的地方政府意志——关于“温州模式”生成的一个假说及其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温州论文,地方政府论文,互惠论文,意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中国市场制度生成及其合法化的漫长变革进程中,温州的改革路径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被概括为“温州模式”,成了一种颇具代表意义的经济发展样式。显然这反映出“温州道路”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就温州模式的生成及其变迁,许多学者提出过许多理论假说。准需求诱致性变迁论[1]、自发秩序论[2]、民间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论[3]、市场交易替代论[4]、国家无为而治论[5]等等,多是从温州民间力量发育、成长等角度来分析温州改革以来独特的经济表现,认为温州的经济民营化运动较好地契合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因而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是不是只要有了快速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就能在市场化背景下立竿见影地看见经济快速成长呢?即便的确如此,为什么唯独温州的民间经济力量能够主导一场民营化运动并取得良好的绩效表现?
事实上,在传统体制构筑的国家集权强势控制之下,民间力量的滋生、增强直至导演经济民营化运动其始终要面对滞后、僵化但又极其牢固的传统体制,绕开或跨越这种不利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民间经济力量成长的先决条件。而在中国自上而下的市场化改革框架下,对外部制度环境最初的某种程度的改良显然有赖于地方政府努力的意愿和改革的智慧。由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一些关键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在真正的市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时,地方政府处在国家—政府委托代理链的末端,它的意志与行为取向对改革进程和经济发展绩效影响极大。历史地看,温州模式的产生、演化,是在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展开的,对传统制度框架的突破有时甚至需要依靠一些非制度化的手段来实现,没有地方政府的直接支持是不可想像的。从经济体制的快速市场化推进到微观市场主体的先发性成长,所有温州模式的特别之处无不与地方政府意志有着种种关联。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在刚性体制空间中顽强地推行富有成效的边际突破与改革,获得了某种区域范围上的制度屏蔽效果,形成所谓“制度落差”,才构筑起温州最初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忽略了对地方政府的意志和行为考察,就难以完整地解释温州模式的缘起及其持续增长能力。
二、地方政府的功利考量
以颠覆施行30多年计划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显然困难重重,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说服政府放弃“计划”。因为,市场经济制度对计划的更替之于地方政府意味着权限的缩小和部分既得利益的丧失,至少短期内政府不可能是赢家。自然,为维持既得利益政府会变相阻挠甚至干脆拒斥改革。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形下地方政府意志左右着改革发生与否、发生的时机、改革强度以及影响程度等改革变量的容忍区间。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有了掌握改革尺度的能力。至少在一开始政府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一个关键的背景是,当年的行政性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了相对可支配的地方财政,同时担负着地方民生的政治任务。两者均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这种利益追求只有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满足——一个发达的地方经济符合温州地方政府的利益。这就使得处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与温州民间涌动的经济改革力量之间一种以“互惠”为基础的生产性政治关系(注:生产性政治关系,是指通过类似交换的生产性转让活动推动政治发展并获得相互间的社会福利增加。参见罗纳德·J·奥克森《互惠:一种颠倒的政治发展观点》,载国际经济增长中心《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6年,110页。)的生成有了可能。
1978-1985年期间,温州处于对传统计划体制的“侵蚀改革”阶段。地方政府推动改革是通过“政策默许”或“政策追认”等相对被动的方式来操作的。改革之初,温州大量的家庭工业尽管具有了公开经营的合法性,但是,在政策上对个体、私营等纯粹私有性质的经济组织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歧视和比较多的限制。为了避开这些不利的约束,家庭或个人以及它们的联合体将其生产经营活动挂靠在具有法人资格的公有制企业(或政府)名义下,向被挂靠单位交纳一定的费用后,对外以被挂靠单位名义开展业务,取得公有制企业所特有的便利条件从事经济活动。这种被称之为“挂户模式”的经营方式其本质是购买身份,通过挂靠寻求“政治庇护”。这样的行为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是不可想像的。地方政府以默许的方式表明了态度,并根据后续发展的态势作了更为积极的举措。一是鼓励社队干部直接创设村办“皮包”公司以利农产挂靠;二是明确“三借、四代”挂靠服务内容(注:“三借、四代”包括出借介绍信、合同书和银行帐户,代开发票、代建账记账、代征税款和代交集体提留。)。现在看来,当时如果没有挂户这层缓冲机制来化解各种来自方方面面的干预和管制,温州的农村家庭工业化进程可能早已因为难以适应多变的政策而被迫中断。已有人认为,同届浙江省的杭嘉湖和金衢丽一带家庭工业终究未成气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没有挂户经营这层缓冲制度[6]。
1986年以后,地方政府有了前阶段改革经验的积累,出于稳定自己的政绩和获取更多租金的考虑,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倡导制度创新。1987年11月温州市人民政府以温政[1987]79号文件的形式颁布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使温州成为中国最先采用“股份合作企业”名称并将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成功推广的地区。这一次地方政府更为积极的表现是,将业主在两人以上的所有事实上的合伙企业都称之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这一意见与“劳动者的劳动合作和劳动者的资本合作有机结合”的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标准定义相去甚远。然而,正是这个巧妙的概念转换凸显出地方政府融合改革政治目标和经济取向的艺术,也很明显地反映出政府与经济组织之间密切的生产性政治关系。随着改革的推进,温州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逐年下降,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35.7%降至1985年的19.2%,缩水近一半,下降趋势已不可逆转。而日益壮大的民营经济已是地方政府利益所系。随之,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继温政[1987]79号文件之后,温州市委、市政府1988-1997年几乎每年出台一个文件,先后出台了共7个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文件。所有这些以高频率颁布的文件,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给民营经济披上股份合作制外衣,视其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公开的政策支持。比如在1992年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决定》中,提出了废除累进税,实行15%的比例税;对年产值300万元以上、上交税收3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减免流转税;新企业首年免税,第二、三年半额征税;许诺贷款方面给予优惠;土地使用予以落实等等(注:参见浙江省体改委编《股份合作制实务手册》(内部印行),1993年11月。)。这些措施的推出带动了股份合作制企业新一轮的扩张。1993年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数量就达36887家,其中工业企业27771家,工业总产值192.84亿元,占全市当年工业总产值的56.2%。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收入。温州市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长十分迅猛,1978-1992年间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6.8%,在财政分权之后,温州市预算内的地方财政收入连年超过上缴的中央财政收入,且两者差距逐年扩大(注:其实,地方政府并没有在税收上做到“应收尽收”,用当地官员的话说是“温州税收的最高原则是藏富于民”。)。
三、地方政府的“退”与“进”
从理论上讲,中国政府决策者对改革目标设定采取了动态化的做法,所以对改革(选择)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而不可改变的边界[7]。因而只要竖起“三个有利于”大旗,在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口号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可以大胆演绎,作进一步的创新,甚至能够对权威进行扩展性使用[8]。然而,这些说法只是提供了操作的可能性,并没有排除这样做的风险。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地方政府不畏风险,冒险尝试改革?
张维迎等通过一个三阶动态博弈模型以解释分权如何导致地方政府竞争,并最终促成经济民营化。不过,这里的民营化是经由国有企业转制完成的,也就是说模型是首先假设地方政府掌握资源,并有资源动员能力。对于温州而言,上级政府是“只给政策,不给钱”,地方只有少量公有制经济存在。所谓“只有政策,没有钱”(注: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改革开始之前便要从不稳定的政策中作出方向上的判断,直接运用政策资源引导民间力量推进经济民营化。这一改革思路较之中国其他地区依靠体制内资源进行改革更接近经济民营化的本质要求。事实证明也更为成功。),即政策成了地方政府启动改革唯一可利用的资源。然而,这种看似不利的条件却使温州市场化进程取得了加速先发的机会。首先,有了政策资源就有了“生产制度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调整较其他资源(比如涉及人、财、物等生产能力的调整)的变动更为迅速,恰恰适应了改革中上级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政策频繁变化。其次,改革从“开发”政策资源着手,不涉及也没有存量资产改革的问题、没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的进行(注:改革之初,当中国其他地区地方政府为修正自己扭曲的产业投资错误而焦头烂额之时,温州没有这个包袱,改革可以轻装上阵。)。再次,由于上级政府没有给温州提供启动改革的物质资源,因而有了温州所谓“自费改革”的说法(注:温州人自己总结是“四自”精神,即“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求发展,自强不息”。),温州在改革中表现出的“大胆”也正是因为地方政府有更多的底气和筹码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争取更大的政策空间。
由于中央政府决策者对改革选择集只是给出了一个带有方向性的基本界定和大致的许可范围,其中还有不少选择的“模糊地带”,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对改革选择集进行扩充,细化或修改、变动的机会与条件[9]。温州地方政府几乎放大了所有可以放大的政策空间。其一,放松价格管制。温州在1984年打破价格管制,是除特区外在价格上随行就市实行议价议销的唯一地区。对价格实行宽幅度的浮动管理,允许计划外组织商品进入温州,许可企业自行定价,这一方面解开了购销价格长期倒挂的死结,彻底甩掉了财政长期背负的价格补贴包袱;另一方面形成了价格多元化格局,激活了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二,筹建专业市场。自中央政府允许完成计划后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上市出售规定出台后,地方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对民间力量因势利导先后筹建了桥头纽扣市场、仙降塑革鞋市场、宜山再生腈纶市场、柳市电器市场、金乡徽章市场等等。此后仅仅三、四年时间年成交额过千万元的市场就有16个。专业市场的大批出现及扩张为温州农村工业化提供了稳定的共享式供销网络,也成就了以商带工式的“小商品,大市场”经济格局。其三,推进金融市场化。利率浮动一直是中国金融管制的禁区,由于体制内贷款的严格管制,当地政府抓住时机授命农业银行于1982年全面推行浮动利率,在理顺民间借贷无序混乱局面的同时促进了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这在全国亦无先例,堪称金融“放管”结合的典范。其四,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改革初期,中央决策者从搞活经济、增加就业角度出发,允许个体经济有条件地存在和发展。国务院分别在1981年和1984年先后发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对个体经济发展作了较为明确的规范。在1987年温州被国务院确定为试验区后不到一个月,温州市人民政府迅速发布了《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这一文件成了新中国第一份关于私营企业市场主体资格确定及准入条件详尽说明的地方性管理规定,也是后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重要参考依据。其五,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尽管国务院1983年曾发出《关于制止买卖、租赁土地的通知》,明令限制土地进入市场交易。然而就在1984年温州市龙港镇建镇时便利用土地的级差,通过土地有偿使用办法成功地解决了城市建设的资金瓶颈和土地稀缺问题。在土地租赁方面,地方政府不仅对土地的租种、转包予以保护,一些地方甚至出台了土政策,由乡村干部出面来调配租种的土地。市场化土地流转制度的形成,一方面使从事工商业的农民彻底摆脱了土地束缚,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的集约化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也让农村小城镇建设的土地需求得到了满足。
温州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很长时间上级政府对其改革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外界对温州的“异端”也存有颇多质疑,温州的民营化改革一度被上升到“反和平演变”的高度来加以否定。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国务院有关部门多次组织人员对“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温州经济的“资”“社”属性,“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等问题进行调查论证。浙江省政府对温州一些超前的做法也有颇多非议(注:浙江省的各届领导和人大都不赞同温州的做法,甚至不允许提“温州模式”。1987年初,省里还有人攻击温州模式是“自由化”的典型。)。温州地方政府不是被动应对,而是有针对地予以说明。以温州市政府研究中心名义提交的报告包括《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考察报告》、《关于温州模式的几个问题》、《关于温州问题调查的补充报告》等重要文件,或是积极陈述或是顽强辩护。
1987年国务院批准建立温州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既然是“试验”,应该允许出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就意味着它的行为即便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也不至于招致严厉的惩罚。这为所有可能属于“出格”的改革行动卸下了包袱。正是有了“试错权”,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才有可能在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前提下就具体的制度安排展开博弈,地方政府也就可以比较放松地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与上级政府对话。这也让温州较其他地区更早地做到了“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试错权”成了地方政府对抗上级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及其他外部干扰的有效的护身符,也让改革有了成本底线。可以肯定,当时地方政府并不清楚“未来”是什么样的,也没有有关改革“彼岸”的蓝图,但可以试错至少给温州地方政府留下了一个有关改革成果的想像机会。这个合法化的改革特许权很快显示出巨大的租值。
四、实证检验
我们利用实际数据来分析并检验上述假说。根据前面的讨论,可能用于解释政府利益或表达政府意志的变量可以是:政府规模(ZFGM)、银行贷款(YHDK)、工商税收(GSSS);用来表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我们选择了工业企业数(QYSL)、民营经济从业人数(CYRS)、非国有工业产值(FGCZ)、居民储蓄余额(JMCX)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GDP)作为构造函数的变量,基本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样本
政府规模 工业企业数 银行贷款 工商税收 民营经济从业 非国有工业产 居民储蓄余 人均国内生产
年份
(人)
(个) (万元) (万元)
人数(万人) 值(万元)额(万元) 总值(元)
(YEAR) (ZFGM) (YHDK) (GSSS)
(QYSL) (CYRS)(FGCZ)(JMCX)
(AGDP)
1980262361757158713063 237.3111114910783 312
1981343165307729514316 175.1611735914367 327
1982448863138191315604 190.7311674518482 358
1983587079978646618364 212.2114987424912 401
1984767813292
113181
23332 237.1121952231717 490
198510043
64724
138279
35958 261.6933934436044 605
198613136
53800
173314
44088 270.3639977459761 710
198717182
63715
197566
53994 274.5852089976291 859
198822474
49735
320247
71500 282.9367248694946 1067
198929396
45664
363891
84742 286.587461501993611110
199038450
41405
422537
85013 291.047940153110591174
199137101
33702
477025
98651 297.841030039
4155051387
199237356
40691
593689
119921 314.551578424
5542071877
199340915
86446
809591
175608 325.783110575
6801822880
199442688
152393 1179798 188213 329.224882208
9877664286
199545270
117533 4675436 242752 336.226717411
1420469
5806
199646467
126975 2187519 300126 342.029576465
1994759
7242
199749373
121021 2913400 361069 347.3311858941 2557000
8553
199849043
127828 3693600 423580 353.2613309887 3229400
9495
199949556
121494 4554945 530771 357.7615022154 3795863
10186
200050413
122658 5952994 697370 375.3517552601 4641487
11360
200150534
131851 7081071 909233 374.5 19539170
5829091 12637
200250279
132677 9326125 1159664381.1322167293
7459660 14357
注:政府规模(ZFGM)数据是指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由于1980-1989年政府规模统计数据缺失,本表提供的相应年份政府规模数据是推算结果。
通过对1980-2002年的23组数据样本进行相关性检验,我们发现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是较高的,所有的T检验均通过了99%水平的检验(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QYSL ZFGM YHDKGSSS CYRS
FGCZ JMCX RJGDP
QYSL
1.000
ZFGM .856[**]
1.000
YHDK .742[**] .714[**] 1.000
GSSS .725[**] .709[**] .972[**]1.000
CYRS .895[**] .950[**] .771[**]
.775[**]
1.000
FGCZ .804[**] .766[**] .958[**]
.967[**] .815[**]1.000
JMCX .731[**] .710[**] .972[**]
.995[**] .771[**]
.982[**]
1.000
RJGDP .839[**] .804[**] .954[**]
.954[**] .844[**]
.997[**] .970[**] 1.000
说明:**表示P值<0.01
以工业企业数(QYSL)、民营经济从业人数(CYRS)、非国有工业产值(FGCZ)、居民储蓄余额(JMCX)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GDP)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考察政府意志对民营经济成长的相关性,采用如下形式的方程:
Y=α[,o]+Σβ[,i]χ[,t]+ξ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X为解释变量(i=1,2,3),分别表示政府规模(ZFGM)、银行贷款(YHDK)、工商税收(GSSS)。根据上式模型,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影响因素的估计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Ⅳ 模型Ⅴ
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 (RJGDP)
(JMCX)
(FGCZ)(CYRS) (QYSL)
ZFGM0.064963.8790.0026 0.333
(3.406)[***] (2.237)[**]
(9.151)[***]
(7.591)[***]
YHDK
GSSS 0.0115
6.80519.9450.00004
(10.237)[***](48.052)[***] (11.809)[***] (2.313)[**]
常数项 -590-179050.48
-1193562.2
206.6761421.804
(-1.190) (-3.234)[**] (-1.607) (28.167)[***]
(0.130)
R[2] 0.9430.991 0.948 0.923 0.733
AdjR[2] 0.9380.991 0.943 0.915 0.720
D.W
0.268 0.5 0.311 1.096 0.786
F
11.601 2309.04 5.002 5.348 57.623
说明:表中()内的数值为t值。*、**、***表示分别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Ⅰ)、模型(Ⅲ)和模型(Ⅴ)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非国有工业产值及工业企业数与政府规模、银行贷款、工商税收之间并无明显的线性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政府规模的大小,银行融资环境的宽松与否以及税收负担程度对温州当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企业个数和产值不构成重要影响。
模型(Ⅱ)和模型(Ⅳ)通过了95%的检验,
JMCX=-179050.48+6.8050GSSS(Ⅱ)
(-3.234) (48.052)
CYRS=
206.676+0.0026ZFGM+0.00004G SSS(Ⅳ)
(28.167) (9.151)
(2.313)
从模型(Ⅱ)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工商税收每增加1元,对应的居民储蓄增长约是6.8元。或者说,居民储蓄每提高1%,可为工商税收增加带来约0.15%的贡献。这就是说,随着民间富裕程度的提升能够更多地带来地方政府的收益。无疑,在这里,地方政府的利益与民营经济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正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与温州民间谋富力量之间一种以“互惠”为基础的生产性政治关系是存在的。显然,辖区的富庶符合地方政府的预期。在地方政府看来,所辖地区居民的富裕不仅能够成为一个彰显政绩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它能满足地方政府对可支配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的追求。在温州,如此强烈的相关性使得生产性政治关系的互惠形式能够非常直接明了地表现为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公开合作,尽管这种官商或官民的互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显得十分突兀和十二分的不合时宜。从模型(Ⅳ)看,民营经济的从业人员每增加1%,政府管理人员只需要相应增加0.03%,这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以1995年为例,中国每一千人口中平均有8.4个国家公务人员。模型表明,工商税收每增加1%,相应的民营经济从业人数会增加0.004%(注:尽管在温州,从业人员的人均产出可能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个比例还是明显偏低。)。从这里可以发现温州税负水平是较低的(注:一位温州财政部门的领导曾在公开场合声称,温州的税收征管有着所谓“藏富于民”默契规则。)。
检验发现,首先,政府意志与民营经济之间存在互惠式生产性政治关系的假设是成立的。体现政府利益的财政收入与当地居民储蓄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在温州地方政府看来,一个“民富温州”才是政府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不必要也不可能与民争利,官民利益勾连直接表现在行动上的合作。当然,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经由温州政府手中控制的国有企业无论在实力还是数量上都不足以让地方政府相信能够作为自身利益实现的基础。换句话说,当地方政府转而寻求与民营经济合作时,放弃从国有经济中取得任何可能的回报,作为一种机会成本显得不会很高。其次,温州的地方政府较少地介入微观经济,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对于初期的市场经济精神和规则的培育十分关键。因为从理论上说,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政府角色应该是“守夜人”。地方政府的“无为”显然是温州经济体制改革能够“自下而上的”发育出一个近似纯粹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强政府主导模式的惯性下,温州地方政府的规模之小出人意料。可能的原因是,一个小规模的地方政府之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可能不在于财政开支的节约,而是唯有一个机构精简、人员适度的政府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扰民的可能!
当然,温州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能先行一步表明,地方政府并不仅仅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严格地“无所作为”,还是作了一些颇有成效的维护民营经济发展的努力。比如对意识形态“屏蔽”、政策有意识的“误读”、策略性的政绩“张扬”等等。
另外,温州民营经济的成长除了得到地方政府的帮助之外,实际上还有其他背景因素。在上述两个模型中,常数项概括了基本因素的作用。我们发现这个常数项解释了很大一部分居民储蓄规模和民营经济从业人员规模的平均值。这就是说,有很多模型之外的基本因素决定了居民储蓄规模和民营经济从业人员规模的变动。仅有经济因素的解释是不够的,它最多只是说明了因此而引起的变动。一些很重要的因素还未涉及,比如温州的社会文化传统、地理区位、政治体制、宗教信仰乃至偶然历史事件。这些因素的影响可能都包含于模型的常数项内,它们所起的作用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五、结语
地方政府的意志介入是温州模式能够在由主流意识形态催生出的排挤和歧视中顽强地得以继续的重要条件。温州的改革起点脆弱,资源空间较其他地区明显狭窄,为了较快速地置换出“改革红利”,地方政府很快与民营化力量达成稳定的互惠默契。另外,温州的边缘化地位和改革的“边际”性质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扩大了的试错机会和低成本的改革路径。让地方政府在并不清楚将“改成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敢于大胆地对“改什么”、“怎么改”作出决策。温州模式变迁中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较为成功地通过对政治与市场的耦合方式的调适,契合了制度变革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变化。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与相互关联(交易)进入良性循环,得到了双赢的改革结果。
在整个中国转型进程中,有关民营经济成长与地方政府意志之间的互动性影响的研究和讨论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应该还有更丰富的因素需要发掘。本文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提出了观察温州经济现象的一个视角。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围绕这些课题展开更为宽泛、更为细致的研究工作。
标签:温州模式论文; 温州论文; 民营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税收原则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土地政策论文; 经济学论文; 温州银行论文; 温州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