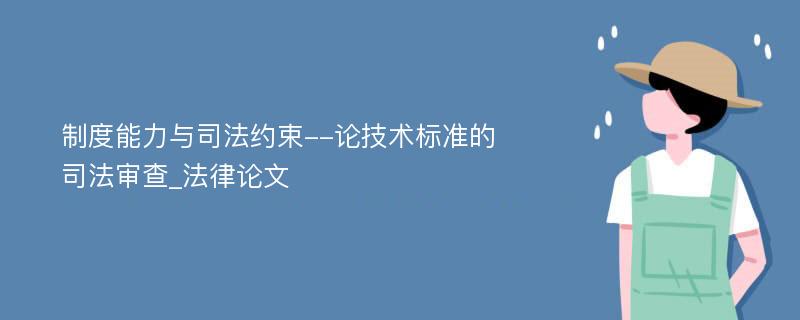
制度能力与司法节制——论对技术标准的司法审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论文,技术标准论文,能力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81(2008)01-0046-9
技术标准已经成为现代行政国家的重要法律问题。技术标准尽管不具备《立法法》所规定的“法”的外形,也不直接规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它们每每会成为行政机关进行事实认定并做出法律结论的重要依据,从而对公民的生活和福祉可能会产生比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更为密切的关联。[1](P38-47)
在现代行政国家下,技术标准有可能使“依法行政”被架空,乃至蜕变为“依标准行政”,让法治国家陷入形骸化乃至空心化的境地。因此对技术标准加以监督和规范,就成为行政法应当关注的课题。本文着重关注的是,在我国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司法权能在何种程度上对技术标准予以尊重或审查。本文以比较法为借镜,着力引入制度能力和司法节制的原理,并结合对我国现实法律规范和实际案例的整理,来对我国技术标准的司法审查展开初步讨论。
一、制度能力与司法节制
(一)司法节制的原理
1989年颁布《行政诉讼法》,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行政诉讼法》颁布前,组织和个人遭遇纠纷时,所诉诸解决的途径局限于官僚体系的内部性救济;《行政诉讼法》颁布后,作为独立的裁判机构,法院成为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审查成为法治国家下一种不可替代的限制国家权力的形式。司法审查具有国家权限配置上的意义,它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权力划分,而且参与形成和执行国家决定的各方力量间相互的监督、制约与平衡。[2](P5)司法审查固然可以遏制行政权力滥用,提高行政决策质量,但也存在法官将自己的价值和政策偏好来代替行政官员判断的可能。法官不应就实体问题做出替代行政机关的判断,原因有四:
首先,科学技术的复杂性要求法官恪守节制姿态。技术标准问题可能会涉及有着高度不确定性的未知事项,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从“事实”到“法律”的推理,还要求在复杂模型和统计学帮助下,在纯技术“事实”间的推演。面对法律和事实的混合问题,面对法律和科技的绞结,法院很难肩负起对技术标准进行司法审查的重担。[3](P975-981)正如美国David Bazelon法官在1973年的一个判决中写到的那样:“苏格拉底说,智慧在于认识到自己有多少无知。如果这就算智慧的话,那么我还算明智,因为我认识到对于机械力的探究、劣化系数的调整,以及去判定政府在这些事项上所采取的进路是否在统计学上是有效的,自己了解的都很不够。”①在1976年的美国四乙铅公司诉环保署案中,Bazelon法官则明确提出了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ompetence)的概念,指出“这些更为微妙,更加不为人所见的科学判断事项,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法官的制度能力之外。”
其次,技术标准制定中的“多中心”(polycentric),使得司法审查不一定是解决蕴涵其间的科学和政策问题的最佳方法。[4]在风险规制领域中,标准制定涉及政府、要负担成本的被规制方(如企业)以及规制受益方(如消费者),其中还涉及劳工组织、行业协会、专家等多重不同的角色。这对行政诉讼所针对的单面法律关系提出了挑战。在法理学家富勒笔下,法院并不适合去解决这样一个并非“双极”(bipolar)而是“多中心”模型的争端。[5](P60-61)
第三,法院即使判决规制标准无效,或者对规制标准提出了附加的程序要求,但是它必须有能力强制行政机关或者企业遵守其判决。法院作为“最不危险的部门”,作为“既无权又无剑”的机关,既无强制,又无意志,只有判断。[6](P391)它作为官僚体系中最为脆弱的一环,也缺少足够的资源和权威让判决落到实处。
第四,在我国,行政审判法官不同于法国行政法院法官,法国行政法院法官绝大多数经过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埃纳”的培训,而且所有行政法院的法官都必须外调到实际行政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法院。[7](P556-557)在这样的机制下,尽管法官还是无法成为“纯”科学问题的专家,但可以对“科学政策”问题有更好的把握。我国的行政法官尽管有着较为浓郁的学术情怀,与学界有着相当多的交流和互动,但他们多为毕业于法律院校或者至少具有法科背景,很少接受过专门的技术培训,缺乏行政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也没有去行政机关实习或工作一段时间的机会,[8](P96-98)这也决定了他们是或许也只能是去关注司法审查实践和行政法学理论的交融,缺少了解自然科学知识的畅通途径,以及相应的勇气和能力。技术标准问题涉及广袤的行政领域,每个领域都有着自己的专业知识,有着类似于“行话”的不易为外人理解的科学术语,环境保护行政案件涉及环境科学的知识,食品中毒案件涉及流行病学原理的争议,法官是有着任职身份保障的通才,而并非这些问题的专家。[9](P293)美国早期的一个判例对此作了形象的叙述:“在我看来,法官不适合对这类事务采取行动。这不是盲人领盲人,而是既聋又盲的人坚持认为他们比具有眼力和听力的,在认识有关问题真实情况的具有最大的优势的人看得更明白。法官在能够理智地对这类事务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具备花费多年工夫才能够学得的大量的知识和经验。”[10](P235)
法官们尽管可能可以通过“干中学”来理解行政运作环节的实际流程,但对于更为复杂性的技术标准问题,可能会看不懂相关的工具书、图表、著作、测试报告,很难对其进行实质性司法审查。法官也无法依赖律师,律师未必是这方面的专家,律师的任务是打赢官司,不是教会法官知识。法官不可能有动力和能力去利用业余时间来进修科学知识,他更多的限于针对双方当事人递交的材料来进行审查。政府官员还可以通过成立内设研究机构、聘任专家、组成咨询委员会等形式来处理行政过程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但在中国没有法官助理制度,法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就技术问题无论是向哪个系统专家去咨询,都是不符合其中立立场的。[11](P101)
(二)制度流脉的概观
在美国早期的判决中,就已认识到通过国会来对复杂政府机器的每个部分的微小发展加以规定,是不可能的。②在1878年的判决中,法官就指出“那些负有行政职责者对法律所作的解释,在考量时总是应得到最多的尊重,而且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就不应去推翻它……相关的官员通常都是有才干的人,是这些主题的专家。”③
Dickinson在1928年指出,技术专家行政“搭起了民治政府和科学政府鸿沟之间的架桥”。[12](P277)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的改革者们,试图通过“专家”决定来促进社会和经济福祉,他们认为行政专家具有专门的技术和知识,他们应独立于法官以及其他接受政治任命的官员,来确保立法政策的实施。[13](P599-600)作为新政的拥簇者,Landis认为法官、立法者和行政官员应该各自恪守自己的能力边界,司法审查应仅仅限于对法律问题的审查。[14](P1302)在19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判决中,法官们认为行政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成了相互结盟的“伙伴”(partnership),例如Harold Leventhal法官这样写道:“应该将司法监督同有益的司法节制原则结合起来,认识到在促进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行政机关和法院在一起构成了‘伙伴’关系,它们是‘促成正义的协同手段’。从实际意义上看法院是整个行政过程的一部分,而并非乍看上去那样是敌视官员的陌生人。”④在1983年的巴尔的摩天然气和电力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中,⑤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判决核能管制委员会规则制定是恣意和反复无常的,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个判决,指出:“一个审查法院必须铭记,[核能管制]委员会是在其有着特别专长的领域,站立在科学前沿,做出预测。与单纯的事实认定不同,当审查这类科学决断时,法院通常必须对其予以最大限度的尊重。”⑥
在我国,对制度能力和司法节制讨论的基点,应以合法性审查原则为起点。[15](P13)根据《行政诉讼法》起草者的解释,合法性审查是定位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界限和基准,其间隐含的精神和美国法上的“制度能力”理论暗合:“我们国家在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对于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等都有明确的划分。这是为了使它们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在考虑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时,需要处理好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关系。根据1982年《宪法》规定,行政权即国家管理行政事务的权力由行政机关行使。……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应当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判决维持,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判决撤销,对需要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判决行政机关重做,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职权。”[16](P74-75)
法院不能替代行政作最终实体性的判断。但这是否会使得技术标准成了司法的不入之地?如果法院拘泥于司法自治,回避判断,是否会使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17](P203)在我国的相关案件中,围绕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环节,还有可能涉及对技术标准的间接审查。这也构成了本文接下来要着力讨论的问题。
二、对事实认定的司法审查
(一)技术标准与事实认定
我们生活在一个“事实”的世界中,以至于维特根斯坦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18](P28)但法律事实并不同于生活事实,在对法律事实加以认定的过程中,需要必要的判断与评价。法院在审判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必须认定法律事实,但是一般而言,法官并非身临其境的这类事实的目击者。[19](P242)法律事实的判断,可能会以事实或价值作为判断基础。对于专业性的行政领域而言,技术标准可能作为发展出来的成文化法则,成为判断法律事实的基础。
我国实行的是法定鉴定制度,在行政过程以及审判实践中,要求获得鉴定资格,具备必要的检测设备和技术手段,具有一定数量专业人员的组织机构,利用自己专业知识和科技条件,以技术标准为准则,根据案件事实材料对需要鉴定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查、测试、分析、鉴别后,得出科学的结论。[20](F343)根据《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4项的规定,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对其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这样的规定还可散见于许多单行的实体行政法律规范之中。在我国,大量的依据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符合法定资质要求的单位,依据技术标准,做出鉴定结论。⑦这些鉴定结论在诉讼活动中同样是作为证据来使用的,只要能经受质证,就同样能成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21](P106-10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的规定,对于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的证明效力,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
例如,在某精制大米厂不服湖南双峰县工商局以投机倒把为由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决定案中,受双峰县工商局的委托,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所对抽样大米进行了质量检测。根据《国家标准—大米》(GB1354-86)所送样品13个项目,特等大米和标准一等大米各有5项不合格,标准二等和标准三等大米各有4项不合格。因此检验结论为“样品所检项目不符合GB1354-86晚籼特级大米标准。样品不合格。”娄底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大米是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国家对其等级标准有明确规定,加工销售单位必须遵守。因此法院支持了双峰县工商局对大米质量的事实认定。[22](P292-298)在本案中,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所是受行政机关委托进行事实认定的专业机构,它根据大米的国家标准对精制大米厂的大米进行检验,所作的样品不合格结论,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证据。
在德国,依据技术标准做出的鉴定结论被视为是“先定的专家证言”。[23](P605)在上海哈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服镇江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管理行政处罚案中,在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法院对原告采取一定配比下的甲醇、石脑油、二甲苯以及少量苯甲酸化工原料能否调制生产出合格的93号车用汽油进行专家论证,法院受理后组织专家进行了论证,论证结论是采用一定配比下的甲醇(50%),石脑油(25%),二甲苯(25%)以及少量苯甲酸调制生产出93号车用汽油,其质量不可能符合《国家标准GB484-93车用汽油》标准要求。[24](P791)在本案中,法院组织专家依据标准对原告生产汽油质量所作的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行政审判中的专家证据。
在由于科技发展水平或者检测设备等因素的制约,无法出台技术标准的情况下,也可能会以感官的观察为基础来认定法律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8条的规定,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例如在路达(厦门)工业有限公司因排放恶臭气体污染环境被厦门市环保局行政处罚案中,在该案中,如何认定恶臭污染事实,成为争议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没有恶臭气体排放的国家或者地方标准,而且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也难于通过仪器检测查明恶臭气体的具体成分。在审理中,经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同意,厦门市环保局就如何判断恶臭污染请示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答复:目前国家尚未颁布恶臭物质监测规范和标准,在国内有关的环境管理实践中并借鉴国外办法,恶臭污染是根据人群嗅觉感官判断进行鉴别和确定的。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国内有关环境管理实践并借鉴国外办法,恶臭污染是根据人群嗅觉感官判断进行鉴别和确定的。在该案中,与原告一路之隔的福建体育学院师生不断向被告和上级领导部门反映该车间排放恶臭气体污染环境问题,并提供了该院卫生所的疾病患者统计资料。市、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议案反映该车间的污染问题,在被告和一审法院调查时,现场闻到了恶臭气味,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工厂恶臭污染的事实存在,并的确危害了周围环境。[25](P569-574)
(二)对事实认定的司法审查
行政机关以及标准制定组织比法院有着更强的事实认定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事实认定完全留给行政机关,只把法律问题留给法院。因为这样可能会使得行政机关在事实认定帷幕掩饰下来进行政策制定,改变了法律规则运行的轨迹。因此,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6节中,规定了对事实问题的三个审查标准,即实质性证据标准、滥用裁量权标准以及法院重新审理标准。
在美国,对标准制定的司法审查主要适用实质性证据标准(substantial evidence test)。1938年休斯大法官在Consolidated Edison Co.v.NLRB案中指出,“实质性证据不仅仅是一个衡量的证据,它意味着这样相关的证据能为一个理性的心智所接受,从而足以去支持结论。”⑧勒尼德·汉德法官在1943年,认为实质性证据标准构成了司法对自身权力的“退让”(abdication)。⑨
在1980年的关于苯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对实质性证据标准给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说明,要求在采取任何规制行为之前,应能表明“显著风险”的存在,认为“显著风险”应该是一个能为实质性证据所确证的技术性概念。⑩此外在美国还发展出来了一个题为“合理性区间标准”(zone of reasonableness test)的学说。也就是说,当可量化的技术标准落在以证据为基础的合理性推定范围之内时,它将得到支持。就如Hercules v.EPA案中Tamm法官写到的那样:“‘合理区间’概念的首要理念,它让法院免于特定的琐细计算,相应的,它给予行政机关裁量权,去适用普遍的程式或方法学,来对特定案件的诸多面向予以处理。”(11)
因此,实质性证据标准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事实上的准确性,而更多关注在一个科学框架下,事实认定本身是否是合理的;它是一个法律标准而非科学标准;它的正当性并非来自科学标准,而是以法治、审议民主以及正义理论为基础的民主原则。[26](P306-311)实质性证据标准允许行政官员在事实认定环节有较大的裁量权。
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被告对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意味着在和事实问题相关的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有可能要提供鉴定结论以及所依据的技术标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原告可能会主张被告适用了错误的标准,影响到了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多尊重行政机关依据标准做出的事实认定。例如,在泉州市宝岛卡拉OK音乐厅因向外界排放噪声超标被泉州市环境保护局予以行政处罚案中,被告泉州市环境保护局于1993年7月8日委托泉州市鲤城区环境监测站对宝岛音乐厅向界外排放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为向界外排放值为65.8分贝。11月25日,市环保局以此事实认定结论为基础,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第13条、《福建省征收排污费实施办法》第2条的规定,以泉环保(1993)086号文,决定对原告征收环境噪声超标排污费。鲤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支持了被告对超标单位征收排污费的决定。[25](P1170-1173)在这两个案例中,法院都对行政机关依据技术标准所作的事实认定给予了支持。
在英美法中将事实和法律加以区分并采取不同的审查态度,在于认为行政机关和法院在专门职能上有着不同的分工。法官是法律问题的专家,他们无法承担起对涉及专门知识行政领域的全面审查任务。(12)尽管不一定就能把美国法上的“制度能力”理论搬到中国,但是依据技术标准,通过鉴定、检测、检验等方法做出的事实认定结论,对法院而言可能具有专家证据效力。法院对技术标准虽然有着最终审查权,但可以借鉴美国法上的实质性证据标准,对其进行合理性审查,所更为关注的并非是否达到了客观真实,而是关注事实认定结论是否落在合理性的范围之内。
三、对法律适用的司法审查
所谓事实问题,是指关于事实上发生了什么的问题;而法律问题则是指该发生的事件,根据法律规范上的标准,具有怎样法律意义的问题。[19](P247)《行政诉讼法》第54条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对法律问题的审查权,根据对我国行政审判案件实态的考察,可以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一)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用了无效的技术标准
《标准化法》第14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第13条规定“标准实施后,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以确认现行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废止。”例如在吕梁通润加油站不服交城县技术监督局处罚决定案中[22](P1124-1131),原告通润加油站诉称吕梁地区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所的油质检验结果的数据不具有科学性,因此1997年6月4日交城县技监局据此做出的(交)技监罚字(97)第030号《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没有事实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提审中,认为1994年已公布了新的轻柴油国家标准GB252-94,原国家标准GB252-87已停止使用,而地区质检所仍以废止的轻柴油国家标准GB252-87为依据,该标准作为产品质量检验依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根据此做出的质量检验报告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二)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用了错误的标准
例如在广东省肇庆化工厂不服肇庆市环保局行政处罚决定案中,原告不服肇庆市环境保护局根据肇庆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监测结果所作出的《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噪声标准应按照《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规定执行,被告引用《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来衡量是错误的,所以被告适用法律法规不当。[20](P1173-1179)又如在西凯视觉光学技术有限公司不服浙江省标准计量局行政处罚决定案中,国家对《软件亲水接触镜》的检查标准只有GB11417.2-89,而且这个标准是国家强制性标准。该标准规定,出厂产品必须按GB2828规定进行检验。GB2828检验标准是判定批次产品质量状况的唯一方法。省标准计量局没有严格按GB11417.2-89强制标准中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操作,而是采用GB2828和GB2829混合使用,而GB2829检验不是判定批次产品合格与否的依据。因此其检验结论不能作为认定西凯公司生产的隐形眼镜为伪劣产品的依据,所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撤销了浙江省标准计量局(浙)技监罚字(1993)第一号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20](P1072)
(三)依据技术标准来填补法律漏洞
在福建省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不服省地矿厅行政处罚案中,原告诉称《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44条规定:“地下水资源具有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双重属性。地下水资源的勘查,适用〈矿产资源法〉和本细则;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适用〈水法〉和有关的行政法规。”地下温泉属于水资源。因此对于原告开发、利用地下温泉的行为,应当依照《水法》(以下简称水法)以及《福州市地下热水(温泉)管理办法》的规定,由城建行政主管部门而非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因此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职权。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归纳起来是:温度为72度的地下热水属于矿产资源还是水资源?它应当由矿产资源法调整还是由《水法》调整?这首先要认定地下热水属于“地热”还是“地下水”。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1990年起实施的GB11615-89号国家标准《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中规定,地热资源是指在我国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地壳内可供开发利用的地热能、地热流体及其有用组分。该标准将地热资源按温度分为高温地热资源、中温地热资源和低温地热资源三类。其中低温地热资源里,又将小于90度大于或等于25度的地热分为热水、温热水、温水三项。本案涉及的地下热水平均温度为72度,是地热,不是地下水。而作为地方性法规的《福州市地下热水(温泉)管理办法》,没有根据国家标准把温泉按照温度的不同区分出地热和地下水,以致将部分地热归入地下水中,由此给这部分地热确定的行政主管部门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符。法院判决维持被告福建省地质矿产厅第03号《违反矿产资源法规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个案例的核心争点,在于认定地下热水属于“地热”还是“地下水”,以确定其由《矿山资源法》还是《水法》调整。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国家标准《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中对地热资源的定义为依据,选择适用了正确的法律法规,驳回了原告认为被告超越职权的诉讼请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适用技术标准对法律中具有高度专业性技术性概念的解释,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它一方面具有组织权限分配上的意义,可能从而改变规制体制的框架以及规制机构之间的职权划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构成认定行政机关是否“超越职权”的前提。
四、对程序问题的司法审查
法院是程序问题而非实体问题的专家,在对标准制定的司法审查中,法院会较少的介入实体面的争议,而是将目光投射到程序面上的考量。[27](P19)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Simon所说,“也许只有经由程序法,才能防止法与技术之间,成为司法之无人之境”。[17](P427)
在美国,除非决定是明显不合理的,法院不应对实体性问题做预判,而是看标准制定是否符合联邦行政程序法及其他法律中的程序性要求。[11]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促进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法院要求环保署在规则制定中适用比联邦行政程序法更为严格的程序。(13)
例如,在美国1976年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诉核能规制委员会中,(14)多数意见认为核能规制委员会“没有对废料处理中涉及的问题,包括过去的错误,对不确定性以及专家间的歧见,作一个全面的分析,这类行为很难算得上是理性决定。”Bazelon法官在判决意见中认为,因为核废料的处理可能会给公众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行政机关应该采取比通告评论程序更精确,保证更多准确性的程序,例如包括非正式的协商、文件开示、由来自行政机关之外持不同见解的专家组成的技术咨询委员会、交叉质证、由政府资助的独立研究、对技术报告的详尽演绎、对已有文献的整理以及方法学上的备忘录等等。(15)该案的判决要求核能管制委员会为科学技术问题“创设真正对话的程序装置”,强调确保就核心问题进行实在的“意见交换”。(16)
在美国,法院对标准制定记录进行审查,以审查标准制定是否理性,是否有着充分的事实基础并保证所有相关问题都得到了考虑。在我国,《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中规定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标准送审稿的审查程序,规定对于有分歧意见的标准或条款须有不同观点的论证材料,审查标准的投票情况应以书面材料记录在案,作为标准审查意见说明的附件。但是并没有规定要对标准制定过程制定完整的记录,更没有规定记录中包含哪些内容。而且即使保存了完整的记录,但由于标准制定所倚重的科学信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需要考虑诸多不确定因素、标准制定的相关组织和人员甚至都说不清楚自己当时的考量,因此也很难对记录进行实质性审查。从制度层面来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可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但由于《行政诉讼法》第12条排除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诉讼,因此在我国很难以程序违法为由对技术标准制定程序提起诉讼。
五、小结
在制度能力与司法节制的理论下,法院不能代替行政作最终的实体性判断。如果从我国的实定法律规范和行政审判实践出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在更多的情况下尊重行政机关依据技术标准做出的事实认定;会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用了无效或错误的技术标准,还可依据技术标准来填充法律漏洞。在我国,目前尚难以程序违法为由对技术标准制定程序提起诉讼。以上这些相对概括化的见解,对于在我国未来的行政审判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更为成熟的对技术标准加以审查的方法和技巧,或许会有些微的促进。
[收稿日期]2007-09-28
注释:
①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v.Ruckelshaus,478 F.2d615 at 650-51(D.C.Cir.1973).
②United States v.MacDaniel,32 U.S.(7 Pet.) 1,14 (1833).
③United States v.Morre,95 U.S.760,763 (1878).
④Greater Boston Television Corp.v.FCC,444 F.2d 841,851-52 (D.C.Cir.1970),cert.Denied,403 U.S.923(1971).
⑤103 S.Ct.2246 (1983).
⑥103 S.ct.2256 (1983).
⑦例如根据《药品管理法》第6条、《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承担依法实施药品审批和药品质量监督检查所需的药品检验工作。药品检验机构依据药品标准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可以作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定药品质量的依据。
⑧305 US 197,229 (1938).
⑨NLRB v.Standard Oil Co.,138 F.2d885,887 (2d Cir.1943).
⑩448 US 60 (1980).
(11)598 F.2d 91 (D.C.Cir.1978)at 107.
(12)例如尼利法官指出,“如果法院要全面审查诸如州医疗检查委员会这样的行政机关的决定,‘它将发现自己在医疗学的迷宫中徘徊,或在药典的秘籍中蹉跎’”。转引自杨伟东.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行政审判权纵向范围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5.
(13)Kennecott Copper Corp.v.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462 F.2d 846 (D.C.Cir.1972).
(14)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Inc.v.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547 F.2d 633 (D.C.Cir.1976).
(15)547 F.2d at 656,657.
(16)547 F.2d at 645.
标签:法律论文; 司法行政机关论文; 司法审查论文; 法官改革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行政诉讼法论文; 司法程序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