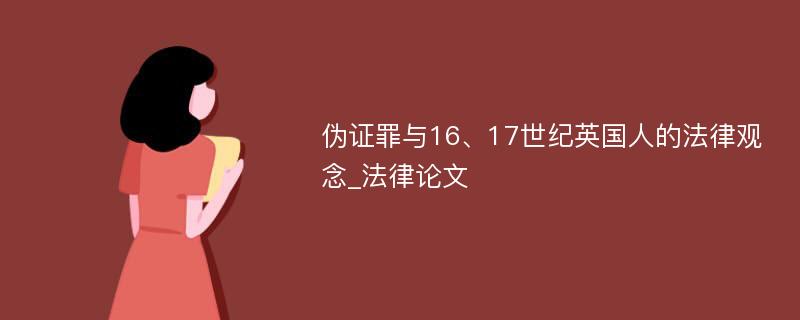
伪证与16、17世纪英国民众的法律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伪证论文,英国论文,民众论文,观念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6)04-0114-05
法律史、犯罪史在历史研究中曾经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涌现出许多研究成果,这些开拓性的研究揭示了英国法律制度的沿革,法律观念的变化以及法律运用中的诸多问题。而证人作为司法审判中的关键因素,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这些普通人在英国司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他们在第一时间判断出谁是凶手,是他们的宣誓证言被法庭记录在案,成为研究法律史的丰富资料。”[1]1因此,本文将以证人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其作证过程中的真与伪入手,透析其伪证背后的心态,希望从中能管窥到16、17世纪英国普通民众法律观念之一斑。
一
严格讲,证人作为法庭审判中的关键一环并非自古就有。在中世纪的英国法庭,司法审判主要由法官和陪审团进行,往往全靠个人判断,带有相当的主观色彩。法官依据个人的阅历和见识来判断是非曲直,陪审团依靠自己所了解到的相关情况进行裁决。在当时封闭的生活环境里,在相对闭塞又联系紧密的小小村庄中,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秘密,家长里短、绯闻、谣言交织成一个相对有效的信息网络,为身处其中的执法者提供了审判的依据。陪审团的成员大多从本地挑选,他们身处案发所在地区,对诉讼纠纷的来龙去脉相当了解,对双方当事人也不陌生,还可以在开庭前自己寻找证据,勘察案情。因此中世纪的陪审团与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大不相同,他们兼具了现代证人向法庭提供证据证言的功能,这种情况下专门的证人就可有可无了[2]80。虽然近来有学者对陪审团的“个人判断”提出疑问,认为他们可以从被告、起诉人、法官和地方官员那里了解到案件真相,并不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判断来裁决的,但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中世纪的陪审团相对于今天的陪审团拥有对被告和案件足够多的了解,他们依赖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判断就可以做出判决,甚至在诉讼发生之前,纠纷发生当时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基本判断和倾向,即使偶尔听取证人的证言也只是为了佐证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想从证人那里了解真相[3]55-80。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联系逐渐紧密,各种诉讼日益增多。15世纪末期以后,法庭所面临的不再是各种琐碎的庄园事物,而纠纷发生的地点、所涉及到的当事人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庄园附近地区,陪审团依靠自己的所见所闻再也难以完全掌握整个案件的发展,因而证人的证词逐渐重要起来,只有通过听取证言,才能再现案子发生的真实情况,使得法官和陪审团得以了解真相,做出正确判断。证人证言发展成为庭审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最初作为知情者的陪审团也逐渐发展成为专司裁断事实的判断者。在16世纪证人提供证词成为英国法庭审判的一个固定程序[4]187。
证人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作证成为普通民众参与法律事务的重要途径。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都表明:近代早期英国的各种法庭多如牛毛,面对纠纷时普通民众已经习惯于诉诸法庭,诉讼数量也在逐年增多。然而打官司毕竟不是简单的事情,需要面对复杂的诉讼程序,掌握微妙的诉讼技巧,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选择最为有利的法庭等等。这些都为普通民众参与诉讼制造了一定的障碍。而作证,则没有如此诸多的限制,除了智力缺陷和利益相关者,各个阶层和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证人。就整体而言,中下层民众参与作证的比例很高。“对1630年至1639年英国诺里季教区宣誓作证者的研究表明,在总人数为382的男性宣誓作证者中,140人是小贩和手工业者,90人为约曼,84人为农夫,当然,这只是数量极小,地理范围有限的样本。1560至1700年的诺里季、埃塞克斯、达拉姆和伦敦等教区得到的数据,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地理分布广泛,结果同样表明:在教会法庭中涉及作证的大多数是中下阶层,商人、手工业者、约曼、农夫通常构成了男性宣誓作证的80%。”[5]252
法律也在制度上规定了普通人参与作证的义务。“在古老的英国法律中,如果发生了盗窃、抢劫,那些被盗者或目击者须向法庭提供线索……而苦主、原告、巡警和其他可以提供证据的人都须出庭作证,并根据案件的性质和法官的判定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以确保审讯时他们能出庭作证。”[6]107伊丽莎白时代曾经发布公告:“人人都有响应法庭召唤,出庭作证的义务,无故不出庭作证者罚款10英镑,以弥补苦主因为证人缺庭而造成的不便和损失。”[7]438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是司法审判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责任和义务。英格兰中部的西勒比教区是一个仅有341名居民的小教区,从17世纪30年代该教区的一桩诉讼案可以看出,参与作证的人形形色色为数众多,几乎涵盖了该教区所有职业和年龄层,从绅士、教会执事、教会官员、富农、农民、手艺人、学校校长到面包师、磨房主、接生婆,还有劳工、长工和仆人等,年龄从20-78不等[8]55。由此可见,作证已经成为近代早期英国普通民众参与法律事务最经常的途径。
作证不仅是普通民众的法律义务,也是一次法律观念和司法程序的普及。通过作证,证人明白了司法审判程序及意义,通过作证,他们清楚如何组织出最能说服陪审团的证言。“通过与法律机构的频繁接触,无论是作为诉讼参与者、地方官员、证人、陪审团成员、担保人还是罪犯都开始熟悉法庭和法律,英国的日常文化以及他们看待社会生活的方式,他们行动或者希望别人行动的方式都从法律中引申的观念表达出来,并且经常要去适应法律,遵守法律。”[5]256
二
证人作证所要追求的是“真实性”[9]16。为了达到这种真实性,英国早在亨利七世时期就颁布法令严格禁止收买证人作伪证。同时在司法程序上也有相应规定,要求证人作证前要在法庭上进行宣誓,“我发誓我所说的是真话,句句实情,绝无谎言,上帝保佑”;法庭还会询问证人是否理解这些誓词,并能严格遵守,在得到肯定答复后,证人的证言才有效。这种宗教化的法律仪式将法律对真实、正义、诚信的要求具体化,在近代早期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保障证言真实性的程序性设置。
尽管有法律和宗教上的约束,但当涉及到自身利益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讲真话,伪证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托马斯·莱丁,1637年担任西勒比教区执事,继任者是托马斯·丘奇,前者起诉后者的妻子布里切特与数人通奸,行为不检。布里切特对此坚决否认。而莱丁的一对夫妻证人,约翰·塞尔特和伊沙贝拉·塞尔特,则作证亲眼看到她与邻居儿子的奸情。在被告的否定与证人的肯定之间,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讲了真话,必有一方作了伪证。要么是被告,一名23岁的年轻已婚女性,丈夫是曾担任过教区执事的村中重要人物,为了名誉和婚姻而掩饰自己的放荡行为;要么是证人,为了养家户口而作假证,因为就在一年前,伊沙贝尔因为未婚怀孕而被布里切特的父母解雇,她不得不草草与约翰结婚,这成为他们悲惨生活的开端,而解雇他们的雇主就是被告布里切特的父母。正是这种关系使法庭对他们的证词大为存疑,因为在他们作证后,马上就得到了教区的济贫救济,生活好转了很多[8]58-63。至今天,布里切特的清白与否不再值得探究,但其中因为个人的利益而背弃誓言的伪证现象却初现端倪。
这并不是个案,虽然在档案资料中,关于伪证的文字并不是很多,但从都铎政府不断重申的禁令中,可以看出伪证问题在当时并不鲜见。亨利八世即位之初就重申先王亨利七世关于伪证罪的处罚规定,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为了对付这种日益增多的有损国王威严和上帝旨意的罪行”,曾历次重申,敦促实施。1531年又颁布了一部新的禁止伪证的法令,由于意识到伪证在全国的增加正是不合理的审判制度造成的,该法令在程序上进行改革,缩短令状申请到政府批准之间的时间,不给收买证人等活动可乘之机[7]365。及至1562年,伊丽莎白女王认为伪证和收买证人现象屡禁不止是因为亨利八世的惩罚措施不够严厉,从伪证中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10英镑的罚款,因此重新规定了惩罚措施:“……凡是以任何形式收买证人者都要处以40英镑的罚款……而作伪证者则会被处以20英镑的罚款。”[7]437
从西勒比的案子中证人夫妇作证后生活好转及都铎政府对“收买贿赂证人”的严厉惩罚中可以看出,16、17世纪大多数伪证是在证人受到被告或原告收买贿赂或是威胁逼迫的情况下被动做出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伪证都是这么被动出现的,还有一种是证人自己主动选择、不受外来影响、不受利益驱使的伪证。这类伪证通常出现在一些带有神秘性质的案件中,如强奸、投毒、以及巫术等,这些案件作案手段隐蔽,很难找到直接目击者,验尸官又不具备相当科学鉴定的条件,因此在法庭上经常会出现在现代人眼里很荒谬的证词。如会说话的灵魂,1660年,威施特摩兰地区的罗伯特·霍普称他看到罗伯特·帕金的灵魂在当地教堂游荡,不停地呢喃:我被谋杀了,我被谋杀了……。于是霍普向治安法官报了案,并且根据他所听到的帕金灵魂的暗示,法庭最终认定这个幽灵是被一个女人用刀子刺伤头部而死。如会指认凶手的尸体,1629年,赫特福德郡一名死者被开棺验尸,许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一桩普通的自杀案件,但是当死者姐姐应验尸官要求将手放在尸体上时,所有的证人都称看到被触到的部分立刻变了颜色,青灰色的尸体逐渐鲜活起来,并流出了鲜血,而且死者手指上戴结婚戒指的地方也有鲜血流出。最终法庭根据这些证据判定死者的姐姐和丈夫犯有谋杀罪[1]14。这种超自然的夸张的证言在巫术审判中则更为多见。1586年兰开夏郡著名的三巫女案中,原告称这几个巫婆多年来一直在骚扰她,经常看到她们幻化成有两条腿的黑狗的形状,劝她投河赴死,或令她失去知觉等[10]221。
以上几个案件中,在没有人强迫,也没有人收买的情况下,证人借助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灵魂或者尸体影响法庭和陪审团的判断,可谓主动伪证。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法庭中此类证言频频出现,成为当时法庭审判体系的一大特色。近代早期英国谋杀案件中证人提供的证言不是超自然的奇异想象,就是对自己所知的事实进行加工或者提炼其中符合个人的揭示,同时对此进行重新组合、重新编辑以使其达到特定的司法目标[1]19。但在证人看来,并不认为自己的证言是“伪证”,相反认为自己的证言是准确真实的,这恰恰反映了这类证言中的主观判断和证人先入为主的印象。对于前者的谋杀而言,罗伯特·霍普早就怀疑甚至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但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直接目击证据,需要借助死人之口来提出控诉。而后者以尸体流血作证,则秉承了古老的“触摸尸体”的神裁法,认为是神的力量在揭示真凶。根据现代医学,中毒致死的尸体在受到触压后可能会流血,但是并不像证人所说的那么夸张,证人显然对自己所看到的现象进行了加工[1]10。
在当时的证明体系中,这些案件在审判过程中难以找到充分的证据,因此法庭仅凭间接证据就可以做出最终判决,若非这样,就很难通过其他方式找出证据展开审判。因此这些证言在当时的法律上并不构成“伪证罪”,但就真实性来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多多少少经过了夸张歪曲或捏造。如关于尸体流血,虽然现代的研究成果表明,中毒后的尸体一经触碰可能流血,但是并不像证人所讲的喷流而出那样夸张,而巫术中的变幻人形则更是凭空捏造的无稽之谈。就这一点来看,这些都是有违真实性的“伪证”。
三
证人出庭作证的逐步规范化和程序化显示了近代早期英国法制的发展和进步,而伪证却揭示出民众参与法律的消极一面。伪证为何会出现?如果说外在因素造就了被动的伪证,那么主动伪证呢?如果说证据采集困难而使法庭不得不接受这些半迷信的证言,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证人愿意做出这样的证言?要解释这些,就必须要从当时英国民众的法律观念,以及证据法发展的时代特点来进行分析。
首先,16、17世纪英国民众法律观念中蕴涵着浓厚的道德判断因素。中世纪末期以来,英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在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中的进一步渗透和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强,贫富分化加剧,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逐渐趋向多元化。与此相伴的是失业、流民、社会失序、道德沦丧,因此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成为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的首要任务,并为此颁布了大量的法令和政令。这些法令必须依靠地方基层官员来实施。这些地方官员来自于乡绅、富农阶层,他们既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地方上的道德楷模,无论推崇清教的禁欲还是奉行上帝之爱的基督教伦理,他们都希望通过道德教化或宗教感化来维护社会和谐,保持社会稳定。同时这些人在地方法庭也非常活跃,积极担任法官、陪审团、验尸官、庭吏、保甲等角色,这就决定了当时英国基层法庭浓厚的道德色彩。
这种道德色彩首先影响到司法机关对证人和证据的判断,道德代替客观成为一个人可信不可信的标准。“如果某人性格温和,彬彬有礼,出身良好,那么他就是值得信赖的,不会犯罪也不会作伪证,如果一个人看起来愚蠢,鲁莽,粗鄙,那么他就很可能是会犯罪的那个,也很可能会作伪证。”这就是16世纪的乡村法官在判断证人证言时所遵循的原则[11]17。道德判断同时也影响了执法者对伪证的态度。虽然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时代对伪证和收买证人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但真正的伪证罪审判和相关处罚却很少见。1676-1688年肯特郡巡回法庭受理的1600多件诉讼中,只有一件涉及到伪证,且被判定无罪[12]55;由于缺乏详细的资料,我们无从知晓伪证罪的记录较少,是因为伪证确实太少了,还是因为法官对伪证网开一面。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在巡回法庭以下的地区法庭中,法官和陪审团常常会根据个人判断为被告减免罪责,特别是当被告出于生活所迫而触犯法律时,他们的同情心会将死罪变成流放,将流放变成鞭挞等,尤其是处理最常见的盗窃案件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将赃物价值估低,以避免报送巡回法庭,使之免受牢狱之灾。这些都清楚地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犯罪作为一个相对概念,是罪犯个人行为和那些证人、起诉者、审讯者、宣判者主观抉择的共同产物,必然带有当时社会价值和道德观念的烙印[13]106。法庭的最终裁决从来都不仅仅是陪审团12个人的裁决结果,而是整个社区、全体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
司法官员对于这种主观判断的认同鼓励了证人作证时的主观和夸张。在缺乏直接的目击证人和有力的证据下,社会成员通过他们自己的叙述来展示自己的判断。行政官员和验尸官不仅乐于认可其法律效力,甚至还参与共同伪造,他们帮助证人把不太可能的证据包装整理成为最可信的证据,最大程度地惩处那些地方难容的败类或者人们心目中的坏人[1]28。在全社会共同营造的这种道德至上的司法环境中,英国的普通民众也相信法律是整饬道德的最好途径。因此证人在作证时对道德真实的追逐超越了法律真实,将道德判断凌驾于澄清事实之上,成为说出不真实证言的主要动机。1691年约克郡的托马斯·拉弗尼被怀疑谋杀妻子,有人证实曾经在他妻子的头发上看到水银,验尸官证实她身上有毒药发作造成的物理痕迹,而曾帮忙装殓尸体的妇女也证明只要托马斯碰到尸体就有鲜血流出。正是这些证词导致了托马斯的被捕并被判有罪。而一切怀疑皆源于周围邻居对他的强烈不满,因为妻子生前常常遭到他殴打。正是这个众所周知的不满才使得人们对“她的突然死亡感到奇怪”,从而导致对他的指控。这些证词与其说是揭示了托马斯的罪行,不如说是强化或印证了公众的猜测[1]13。在殴打妻子这点上他所表现出的不被邻里和地方认同的品性使人们更加坚信他就是凶手。在许多案件中,这种对嫌疑犯的先入为主的品格道德认定导致了证人在作证时的倾向性。“如果一个人连自律都做不到的话,他是极有可能犯下各种罪行的,洁身自好、自控能力是确保清白的最好标准。”[13]108而这在巫术案中最为明显,品性不好的人更容易被人相信犯下各种罪行,平时任何一点不符合道德判断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将来被控实施巫术的借口。只要在动机上存在着一些可能性就可以被看作充分证据。只依据其行动和影响上的可能性,而非真实实际影响或者效果在审判中起作用。
梅特兰在分析12世纪的法庭证明体系时说:“我们必须明白自己对待的是一个与当今生活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14]598同样,在看待16、17世纪英国的证人时,也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与现代法治社会完全不同的时代。当证人的道德判断和上层机关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目的相互作用时,就出现了伪证,在这里,真与伪都显示出了时代合理性。如果我们将这些证言还原到当时英国的社会环境中,就会发现伪证,特别是主动伪证,只是一种言语技巧,捏造并不一定是为了歪曲事实,而是为了追求法律上的真实和道德上的统一。而法官和地方官员对伪证的容忍也体现了他们希望在法律中表达的道德训诫和社会责任意识。
其次,从法律程序本身的历史发展看,近代早期证据法的发展不足也是伪证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真与伪的辨别并不是绝对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证据法的发展清楚地显示了这一脉络。近代法律史学家一致同意,英国的证据法很大程度上是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15]310。甚至到了18世纪,普通法法庭的法庭审判仍然会将一些有用的、可能提供重要信息的证人局限在作证体制之外。在此之前,在法庭审判中的证据收集、证人传唤和证据采信方面都是杂乱无章相对低效的自然状态。在中世纪的法庭上,证明一个人清白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神裁法,一个是誓言,两者都借助了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当时的科学认知条件下,无法解释的神秘就是上帝的神喻,人们对此虔信不疑,它代表了当时的真实性。将一块烧红了的热铁放在嫌疑人手上,如果被烫伤,这个人就有罪,反之,则是清白的[14]623。而当事人和证人的誓言,在当时是被看作是重要的证言,而不像现代法庭中仅是一种程序性的仪式。这种将事实的真实性寄托在宗教信仰和神秘的自然现象上的证据观念是与科学发展的时代局限性相适应的,它代表了当时社会观念中的真实性概念,却不符合法律求真的精神。这两种证明方法在12世纪虽然被广泛使用,但人们已经开始逐渐对之产生了怀疑。后来英国的证据法借鉴大陆罗马法的原则,任何案件必须至少有两个直接的目击证人的宣誓证言或者被告个人的认罪供词才算是充分证据,间接证据不能当作定罪的依据。但对于那些很难鉴定的、隐蔽性质的案件,如强奸、巫术、投毒、谋杀等,因为难以找到直接的证据,间接证据也可以采信。正是这种证据法的模糊之处为伪证提供了生存空间。
17世纪末,随着科学革命的发展,许多原来令人迷惑的现象得到了解释,巫术审判的案件也越来越少。证据学得到了发展,甚至出现了专家证人的雏形,医学的发展也为验尸官提供了初步的科学鉴定手段,虽然还很不专业,颇有江湖郎中的意味,但毕竟为证据法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随着不断加大的社会差距,扩张的城市化以及地方利益的分化,法官和证人以及社会成员间对道德关注的默契减少了,法律中的道德判断逐渐减弱,法官开始强化事实的重要性,证人的证言只有在合法可信的情况下才会被采信。这种追求法律真实的做法更接近现代法官,特别是重罪发生时,道听途说的、超自然的神裁法或夸张的捏造遭到质疑,其法律效力逐渐降低。1852年,随着科学试验的发展为证据法的充分发展创造了条件,新的证据法出台,扩大了证据的来源渠道。至此,证人的法律参与也越来越规范,制度的完善逐渐破坏了伪证的生存空间,很难再看到16、17世纪那样充满灵异色彩的伪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