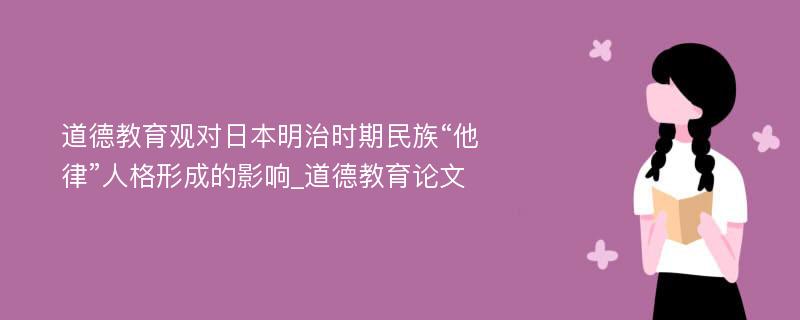
日本明治时期的道德教育观对国民“他律”人格形成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道德教育论文,日本论文,人格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从“天皇政体与规定道德”、“家族社会与活动道德”和“学校教育与知识道德”三个方面研究、探讨了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天皇至尚的国家主义政体下的道德教育观与日本国民“他律”人格形成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最终确立的服务于“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学校”三位一体的日本战前国家主义道德教育模式的分析,揭示出这种道德教育模式对日本国民人格发展造成的危害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缺乏自主性的“他律”人格。
【关键词】 人格 道德教育
明治时代是日本近代经济发展获得极大成功的时代,因为它创造了日本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即用了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便跨入世界列强的行列。但经济成功的背后,同时也写出了一幕日本国民性格扭曲发展的悲剧,而造成这幕悲剧的主要角色便是日本明治时期形成的道德教育观。
研究、探讨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天皇至尚的国家主义政体下的道德教育观与日本国民“他律”人格形成过程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日本战前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认识,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格”又称“个性”,它是指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正的自我,即外部的要求与自身的需要没有受到扭曲的一种真实的自我。而“他律”人格则是相对“自律”人格而言的,它意味着个体的道德判断受他自身以外的价值标准所支配,服从外在的道德准则,当没能与自身的社会性成熟相统一时,或者说在外界不断地消除其“自我”发展过程中,其道德思维水平也只能受外界“权威”的控制或制约。那么这种环境下人格的发展是片面的不成熟的,甚至是有害的。这可以从我们下面的分析论述中寻求出答案。
1、天皇政体与规定道德
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是以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揭开序幕的。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治口号的指引下,开始了“破旧来之陋习”之遗风,并以“师夷之技”、“和魂洋才”之精神振兴皇基;提倡“立身出世”的实业思想和“家无不学之人、邑无不学之户”的教育理念。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追赶上西方列强并使日本经济与西方接轨。可是,经济发展只能说明日本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就日本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而言,“文明开化”并未能使日本的社会组织、文化构造、道德教育与西方同质化,也没能使日本国民人格发展西方化,这确实是值得人深思的问题。
日本学者源了圆在其所著的《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一书中指出,“社会组织、文化构造与科学、科学技术不一样,它不存在普遍皆准的正确性。”其中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风土、社会、宗教”等因素,尤其是日本社会中的“家族”式构造更显示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而“万世一系”千古不变的天皇体制更是日本社会所“独有”的。因此,也就出现了“文明开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与西方接轨、文化发展与西方异化的“独特”现象,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它对日本国民性格做了哪些“规定”?
战前日本的教科书中写道:天皇是神的化身,天皇是作为“现人神”而出现的。日本国体形成也是从“神话”中诞生的,它是通过以“天照大神”开始,继以对“神武天皇”、“日本武尊”、“神功皇后”的神话般的叙述而形成的“万世一系”的国体,天皇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
为了巩固天皇政体的长久统治、强化天皇的“神”的地位,明治维新以后,尤其当“文明开化”带来的西方思想文化对日本的传统道德思想产生猛烈冲撞过程中,明治政府中主张以维系日本传统道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代表人物元田永孚、山县有朋等人意识到传统道德教育的社会教化与法律规定的重要性,它可以保持日本国民对天皇的世代忠诚,对天皇制国家政体的绝对服从。
1879年发表的由元田永孚执笔的“教学大旨”便表明了明治政府开始对西方道德思想文化采取批判立场,并重新反思日本的传统道德思想。“教学大旨”中指出:“教学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此乃我祖训国典之大旨,上下一体之教之所在也。”以此为契机推动了日本道德教育的国家规定化和社会教化的进程。
1881年,文部省颁布的“小学教员须知”中第一项规定:“教人以善良,比教人多识更为重要,故为教员者,更应致力于道德教育,使学生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将道德教育放在一切知识教育的首位,道德教育的顺序依次为“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
1882年颁布的由山县有朋提议、西周起草的日本近代“军人敕语”,不仅规定了日本军人必须遵守的“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素质”五条准则,它还成为战前日本天皇制国家的道德支柱。它与同一时期颁布的“幼学纲要”,对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起到了奠基作用。
“教育敕语”的颁布不仅是对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所提出的“主权在君”思想的进一步强化,而且作为“道德教育”的大法,还明确规定了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使其有了“法律”依据,“朕唯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同时将此作为教育课程编制的最高的理论权威。
为了配合道德教育的国家规定要求,与此同时,作为社会教化的途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890年能势荣发表的带有官方论调的“德育镇定论”一文。其基本观点是:(1)“国人之习惯,凡事依赖于政府。”这无异于教化日本国民只有靠政府的支持、帮助,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自己不能超越政府而有所作为;不能有自己的主张、意志、人格。(2)“德育主义期待政府制定。”并通过“臣民克忠克孝”,完成“亿兆一心”,在社会生活中养成政府规定的“他律”人格。
关于“忠”的具体含义,1937年5月31日文部省发表的“国体之本义”对此作了高度的概括:“忠”乃奉行以天皇为中心,绝对顺从天皇之道,即舍我去私。“忠”是日本臣民所奉行的根本之道,它是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根本,使之与爱国主义一脉相承。这种“解释”无疑对日本国民人格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是在失去自主性的前提下,发展国家道德所规定的不平衡的或被扭曲的“自我”。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爱国主义观也是狭隘的,甚至是盲目的,同时由于“家族社会”的存在,又被注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成份。
2、家族社会与活动道德
我们以为,“天皇政体与规定道德”对日本国民的“他律”人格形成起到“主体性”的作用,它从国家、法律上对道德教育结构、内容进行了规定,但是,这并不能因此说它是日本道德教育的唯一方式。因为对“天皇政体”与“万世一系”的解释和规定不能仅仅建立于“法律”条文之上,它还需要将条文、德目加以具体化,使之付诸于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日本的家族社会对“天皇政体的规定道德”具体落实起到了补充作用,或者说,正由于日本“家族社会”的独特性,将国家的道德教育“内化”为日本国民思想观念起到了“积极”的强化作用。
在“国体之本义”中,对“家族”概念的解释为:我等皆天照大神之子孙,是以天皇为中心形成的家,我们的生命和活动源泉皆仰赖于天皇。所以说,我们的家族生活是始于远古的祖先,在继承和发展祖先业绩之时,教化子孙重视、尊重祖先为我们建立起的家族荣誉。玷污它不仅是个人的耻辱,而且还使整个家族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蒙上耻辱。
而我们之所以能有“深仁厚泽天长地久的国家、海内一家亿兆相和、国体组织的至善至美,完全有赖于皇恩之福。”日本天皇的君德便在于“以古来王道为治国大训。”故尔提倡一国一家之淳风美俗。由此可见,百姓视皇室为万家之宗,天皇则为君臣一体的大家族社会的族长。并由此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族观,爱家即爱国的观念便顺理成章。
在“家族”社会中,道德教育方式主要是侧重行为养成与精神陶冶,即借助“风俗”和“民俗”养成少年儿童的礼仪,修炼他们的意志品质。
新井白石(1657—1725)在《折焚柴记》一书中描述他父亲的举止行为时写道:“天性不露喜怒之色,从不高声谈笑。批评人时不粗野,少言寡语,举止稳重。从未见其惊慌、烦躁和遇上什么难以忍耐之事。”父亲常告诫新井白石“男儿要学会忍耐、克制”。新井白石父亲形象被视为少年儿童礼仪的典范。
心学家手岛堵庵(1718—1786)在其“前训”一书中倡导的家族生活是:早上醒来,洗手后首先要拜神灵,然后在佛龛前叩头行礼(即对祖先灵魂的崇拜和感谢之意)。吃饭时和临睡前都要向祖父、祖母、父母请安。外出时要得到父母的允许,回来时要汇报,对父母的指令要用“是”来回答。这些行为“美德”直到今天仍保留在日本社会的家庭教育内容之中,并作为少年儿童遵守的“礼仪”始终提倡着。
另外,作为实现“家族社会”道德教育的另一途径,是通过修炼柔道、剑道或茶道、花道等形式,炼成少年儿童的意志品质。尤其是经过长期的“劳其筋骨”而养成少年儿童一种吃苦、忍耐、顽强的意志,以达到精神陶冶的目的。
所以说,在日本的家族社会的活动道德教育中,无论是“家风”的礼仪养成,还是“民俗”的精神陶冶,其宗旨是为“万世一系”的天皇政体下的道德教育服务的。通过借助家族社会的敬礼仪,维持上下秩序,重视忠孝节义,以达到维系天皇政体的统治目的。这种“活动道德”的教化过程本身,使少年儿童从小便学会盲目服从,养成缺乏主体性行为,形成“他律”人格。
3、学校教育与知识道德
学校教育往往被认为是教育的主体,这不仅因为它担负传授知识的任务,而且还要完成对下一代的教育任务。即在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意志方面养成符合国家规定的人才。
明治初期,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西方式的“学制”,并提出“家无不学之人,邑无不学之户”的普及教育思想。主张以“立身”、“治产”、“昌业”的西方文明“破旧来之陋习”。而且西方的道德思想在学校得以宣传,学校教育、管理出现相对的自主性。但是,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西方式的个人主义道德观与日本旧有“家族式”的“忠顺”道德体系发生冲突时,日本政府便着手加强天皇政体下的国家主义道德观。其转折点是1879年颁布的“自由教育令”被废除,颁布新的“改正教育令”。在这一时期里还先后颁布了“小学生须知”,对学生的“言行举止”作了严格规定;发表“教学大旨”进一步明确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道德教育,使学校教育完全服务于天皇政体,其统治过程是通过三个方面的措施实现的。
一是制定颁布国家道德教育方针——“教育敕语”,以及“教师学生须知”,借助所谓法律条规细则等手段规定“万世一系”、“主权在君”、“君民一体”等国家主义道德德目。同时因与西方的“人情风俗之异、国制各自不同”原因,在道德教育内容中摈弃“欧美之风。”
二是加强学校教科书内容的国家统治,由国家编写修身科。
1882年,文部省颁布的“文部卿关于小学修身科编写方针之训令”指出:“现今确定小学修身科中道德之要点,首先应着眼父兄最注重之处,子弟最敬重之处。尊崇我万世一系之天胤;爱重我完美无缺之帝国,……选择本邦圣主贤哲之嘉言善行,杂以中国圣贤言行。尤要扶择有裨益我国风化者,加以斟酌取舍,以此编写修身教科书,庶几得到启迪其尊王爱国之理义,服膺修身齐家之要训。”1903年规定国家对小学修身课教科书国定化,到了1904年便完成修身教科书国家化过程。其中对道德教育内容的规定:孝行第一、忠孝第二、和顺第三。主张扬弃西方的古典内容,引入中国“四书”中的“论语”、“孟子”;“五经”中的“礼”等内容以及日本的古谚语内容。
三是学校教育中在道德知识的传授方式、方法上,采纳了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倡导的“五段教学法”。这种做法本身有利于当时日本国家主义道德教育内容的传授。一方面借此可以从内容、时间、形式上对学校的教师进行强有力的统一规定,便于政府的监督与指导;另一方面它可以无视学生对道德知识的理解,立足于“他律”的道德判断立场上,采取注入式的教育方法,其结果使学生的道德认识、道德判断完全建立在“他律”的国家主义道德教育立场之上。
总之,我们通过对明治以来日本政府的道德教育的立场、观点及方法的概括分析,可以从中归纳出这样的结论:明治以来,日本天皇政体下的道德教育观对塑造日本国民的“他律”人格是通过“天皇——家族——学校”三位一体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实现的,并完全服务于“万世一系”这一根本的指导思想。
这种以维护天皇政体为核心,服务于“万世一系”为目的,经过家族社会教育、教养修炼,同时依靠学校注入式的知识强化所形成的战前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道德教育模式,不仅造成日本国民人格发展的缺陷,也形成了日本人所特有的立足于家族观念基础之上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意识。它不仅抹杀了人的个性发展的和谐性,也使日本国民的人格内容发展中充满矛盾,其危害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也就需要日本人对明治以来所形成的道德教育观加以不断的、深刻的反思。
The Influence of Moral Education Concepts in the Period of the Meiji Reform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Citizen's Personality Disciplined by Others
Wang Jianping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Meiji Reformation,nationalist political system was founded.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concepts and the formation of citizen's personality disciplined by others under such political system.It points out that such a model of moral education has harmed th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itizens and formed citizen's personality disciplined by others which is short of independence.
Key words:personality,moral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