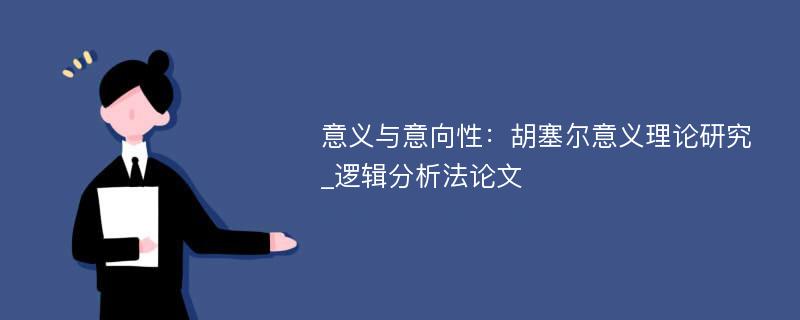
意义与意向性——胡塞尔的意义学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向性论文,意义论文,学说论文,胡塞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导论
1901年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的发表,正式揭开了现象学运动的序幕。此后随着旧术语的扬弃和新概念的引入,《逻辑研究》之后的现象学或多或少已经偏离了胡塞尔最初的设想。但是在众多的现象学术语中,“意义”(Bedeutung)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aet)这两个概念却贯穿了胡塞尔思想发展的始终。由此引发出来的几个重要问题是,在其思想的不同阶段,“意义”概念有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意义”?它同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关系何在?这二者又怎样体现出现象学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
本文认为,对“意义”概念之“意义”及其与“意向性”之关系的讨论是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关键所在。胡塞尔对“意义”概念的追问,始于《逻辑研究》中的语言表达现象,终于《经验与判断》中的前语言性的经验;这一思路的变化恰恰对应着胡塞尔在不同时期对现象学的不同理解。所以接下来本文将从结构、构成和发生这三个方面,来具体考察胡塞尔的意义学说以及它同现象学之间的关系。
2.意义的结构分析
2.1.意义与表达式
《逻辑研究》(第二卷)以“意义与表达式”开篇点题,这并非偶然。因为无论在传统形式逻辑中,还是现代符号逻辑中,其共同出发点都是作为基本意义单位的判断或命题。逻辑是其他科学的基础,而科学也是由一系列意义所构成的。(注:《逻辑研究》(第二卷),德文版,菲尼克斯.美纳出版社,汉堡,1992,第97页。)所以考察意义的本质、有效性和来源是逻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同时又成为其他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所以,同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一样,胡塞尔也从语言表达式现象来开始他对意义问题的思考。
任何语言表达式(如命题、谓词、专名等)都是一种“符号”(Ze-ichen),但是与一般符号不同的是,表达式是“有意义的”(bedeuts-am)符号。表达式为何具有意义?在胡塞尔看来,这是因为,在运用语言表达式(如言谈、交流、阅读、写作等)时,我们赋予表达式以意义。“赋予意义”大抵相当于“理解意义”或“把握意义”。在胡塞尔的术语中,它们都被称为意指(Bedeuten)或意向(Intention)。
但是赋予意义这一功能并非为语言表达行为所独有。在没有相应词语伴随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把握或理解意义。有鉴于此,胡塞尔说道,“物理表达、语音在这一整体中可被视为不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它完全可以被忽略掉。”(注:《逻辑研究》(第二卷),德文版,菲尼克斯.美纳出版社,汉堡,1992,第419页。)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胡塞尔使用“意义”一词的独特语境,它有别于罗素、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等同时代的分析哲学家。美国学者莫汉提(Mohanty)正确地指出,在前者那儿,意义与意识行为有亲缘性;而在后者看来,意义则首先与语言符号相关。(注:莫汉提,《胡塞尔与弗雷格》,第20页;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82)具有赋予意义功能的行为被胡塞尔称为“意向性行为”(intentional Akt),考察它的结构与功能是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故此意义问题就被设定在更广泛的现象学语境中。
意义和虽然和意向性行为密切相关,但二者却断然不可相互等同。因为行为本身是飘忽不定的主观心理事件,而意义则超越了具体的意指行为而保持客观同一性。(注:《逻辑研究》(第二卷),德文版,菲尼克斯.美纳出版社,汉堡,1992,第83页。)在胡塞尔看来,意义本身构成了一类特殊的对象领域,胡塞尔名之为“理想对象”(Ideale Ge-genstaende)。作为理想对象,它和其他的理想对象如“红”等一样,可以在个别对象,也就在意向性行为中被个别化(Vereinzelt)。反过来说,意义是意向性行为的“属”(Species)或本质。它是对众多具体的意指行为“本质直观”(Ideation)的结果,正如本质“红”是对众多具体的红色物体本质直观之产物一样。(注:《逻辑研究》(第二卷),德文版,菲尼克斯.美纳出版社,汉堡,1992,第105-106页。)
意义与指称对象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构成这意义区分的理由有二:其一,指向同一对象的表达式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譬如“耶那的胜利者”和“滑铁卢的失败者”虽然都指称“拿破仑”,但其意义却判然有别;其二,假如意义就是指称对象,那么象“金山”这一类表达式就是无意义的。但实际上我们都能理解其意义,尽管在现实世界中并无此类对象存在。意义之所以有别于对象,是因为意义正是行为指向对象的不同方式。
从行为方面来看,意义是行为的本质;而从对象的方面来看,意义是行为指向对象的不同方式。行为、意义和对象三者之间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意向性关系,即行为通过意义来指向对象(注:很多学者将意向性关系简单地看成是意识对对象的指向性。但这一看法却忽视了意义(或行为内容)在这一关系中的核心地位,正是它才使得意识能够指向对象。)。因此我们可以将意向性行为划分成两个环节:意向(Intention,Meinen,Bedeuten)和充实(Erfuellung)。前者是对一个意义的抽象把握,后者是对该意义的充实,亦即使对象自身呈现在行为中,所以它又被称为直观行为,包括知觉、想象和回忆等。意向把握意义但无直观,充实使对象直观显现但却不拥有意义。二者的统一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向性行为。
但在《逻辑研究》中,意向性理论对意义问题来说作用不是特别明显,甚至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我们可以从静态的结构和动态的功能这两方面来分析意向性理论对说明意义问题有何作用。
2.2.意义与意向性
从静态方面来看,一个意向性体验或行为包含了三个部分(要素)(注:要素(Moment)与片块(Stueck)二者的区别可以参考《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三研究“部分与整体”。),即行为的质料、质性和感觉材料。质料是指一个行为指向对象的方式,质性则是对所指对象存在状态的设定,包括单纯的表象、确信、猜测、怀疑、希望等等。质料和质性都有实在(reell)与理想(ideal)或意向的(intentional)之分。在胡塞尔看来,实在的质料和质性就是行为的具体内容(或不独立部分,即要素)。当我们对诸多行为中作为具体内容的质料和质性进行本质直观时,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行为的意向质料和质性。它们构成了一个行为的理想本质,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作为行为之本质的意义。(注:《逻辑研究》(第二卷),德文版,菲尼克斯.美纳出版社,汉堡,1992,第431页。)
除了质性和质料之外,一个具体的意向性行为还包括“感觉材料”(Empfindung)。感觉材料的作用在于,它作为“再现内容”(Raeprese-ntant)使行为的质料得到证实。而质料对感觉材料进行“立义”(Auf-fassen)的结果,是一种“立义之含义”(Auffassungssinn)。当质料和感觉材料之间有一种符合(Deckung)关系时,意义就在相应的直观行为中得到了充实。由此看来,“质料”概念强调的是意义的充实,所以偏向于意义的对象性层面。
从动态方面来看,意识的意向性具有认识论功能,它说明了意识如何超越自身而切中或认识对象。胡塞尔的回答是,“意义”充当了二者的中介。但是认识论的考察却也暗示了,构成意义的最初源泉是直观行为,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知觉行为。在一个知觉行为中,意识首先获得了知觉对象的侧面显现(Abschattung),后者成为意识的感觉材料。随后感觉材料被意识把握为一种含义(Sinn),假如我们给它以语言表达,那么它就成了我们所说的意义。
2.3.《逻辑研究》中意义学说存在的问题
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逻辑研究》中对意义的两种解释是自相矛盾的。作为意识的本质,意义是一种事先被给予(vorgegeben)的理想对象,它与对象的直观显现无关。但作为意识指向对象的方式,它却是在直观行为中被构成的。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把知觉等直观行为同样看成是意向性行为,它们也拥有质料,或者说拥有对象性意义(Si-nn)。
这种自相矛盾与《逻辑研究》中隐含的本体论立场密切相关。意向性原本意味着,意识通过意义而指向对象。但在《逻辑研究》中,这三者却处在不同的本体论地位。(注: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逻辑研究》中潜在的本体论预设,参见蒙西,《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存在’问题》,玛提努斯·尼霍夫出版社,海牙/波士顿/伦敦,1981,第71页。)意识行为是时间性的个别对象,意义是超时空的理想对象,而“对象”概念的含义则非常暧昧。依胡塞尔之见,它既可以是实在的时空对象,又可以是虚构的对象,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对象。假如意向对象是现实世界的个别物,那么说这三种根本不同类型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对象性关系,似乎是不可理喻的。假如意向对象是虚构的或者根本不存在,那么说三者之间的意向性关系会导致悖论。
3.意义的构成分析
3.1.意识活动与意向对象
《逻辑研究》之中意义学说所存在的困难,迫使胡塞尔在此后的思考中逐步修正乃至抛弃自己早期的某些看法。在后来发表的《1908年夏季学期:意义学说讲演录》中,胡塞尔承认,《逻辑研究》的意义学说有偏颇之处:《逻辑研究》过于强调意义的意识或行为层面,而忽视对象相关性的层面。《意义学说讲演录》据此将意义区分为“物候学的”(phaenologisch)意义和“现象学的”(phaenomenologisch)意义。(注:《1908年夏季:意义学说讲演录》;海牙,玛提努斯·尼霍夫出版社,1987,第30页。)说得更简单些,前者是作为意识本质的意义,如同物候学的“种”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中保持不变;而后者则是作为对象性相关物的意义或“含义”(Sinn)。
在《大观念》中,胡塞尔基本上抛弃了前一种意义概念,而把作为对象相关物的意义或所谓的“现象学意义”视为与“意识活动”(Noes-is)相对的“意向对象”(Noema)。(注:在国内学界,Noesis和Noema这两个概念通常被译成“意向作用”与“意向对象”。这种法译不太准确,而且容易引起误解。但为了便于交流,本文依然沿用旧译。)与此同时,胡塞尔也抛弃了《逻辑研究》时期预设的本体论立场,并发展出一套现象学还原方法。作为确立先验现象学的主要方法,它分成先验还原和本质还原。(注: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有多种解释,本文依据的是倪梁康先生的说法。参见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三联,1994,第97页。)大致说来,前者是对一种本体论存在“信仰”(belief)的排除,后者则是从先验还原的剩余物——纯粹意识中进一步还原出纯粹意识的本质,即所谓的“意识活动”与“意向对象”。意识活动是意识的真实部分或要素,或者说是内时间性对象。抛却现象学立场的差异不论,它大抵相当于《逻辑研究》中的“立义”、“意指”和“意向”等概念,其作用是对意识中的另一真实要素——“材料”(Hyle)进行综合,赋予它以某种对象性意义。这种被赋予或被构成的对象性意义,就是作为“意识活动”相关物的“意向对象”。意识活动和意向对象是一种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意识活动都对应着一个意向对象,反之亦然。
“意向对象”与《逻辑研究》中作为意识本质的意义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在三个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其一,作为行为本质的意义,是在自然态度下对具体的意识行为进行本质直观的结果,而“意向对象”则是在先验还原之后对意识反思的产物。其二,即使是在先验还原之后,意义也只是构成“意向对象”的一部分(尽管是核心部分)。其三,“意向对象”彻底摆脱了对意识所指对象存在状态的设定。
那么作为意识活动相关物的意向对象,又包含了那些要素呢?胡塞尔认为,“意向对象”首先包含着一个纯粹空洞的对象“极”(Pol)。“对象极”与《逻辑研究》中的“对象”之区别在于,它不包含一切对它存在与否的设定,同时有关对象的任何规定、任何性质等都被排除。胡塞尔把这个纯粹的“对象极”视为“可能谓词的可规定主词”(注:《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317页。),或“在抽离出一切谓词后的纯X”。(注:《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237页。)在此含义上,“对象极”非常类似于罗素所说的“逻辑专名”或“实指定义”的对象,比如“这个”或“那个”。
X不含有任何规定性,但这并非意味着X不可规定。当X被负载上规定性之后,这些规定性就构成了意向对象的核心部分意向对象意义(ne-omatische Bedeutung)。假如我们用“拿破仑”、“耶那的胜利者”或“滑铁卢的失败者”来规定X(一个具体的人),那么这三者就都成了意向对象的意义。除了具体的规定性之外,X还包含着其他可能的规定性,它们组成了意义的视域(Horizont)。对象极X、X的谓词规定性或意向对象的意义、以及意义视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向对象。
3.2.意义与意识的构成作用
以上是我们对意向性行为的结构分析,但它并没有考虑意向对象意义的构成问题。构成的过程开始于感觉材料,经过意识活动的综合作用,最后形成作为意识相关物的意向对象之意义。由于意识活动与意向对象之间的平行关系,意识活动的构成过程与纯粹对象X获得谓词规定性或对象性意义的过程,就形成一种对应关系。
胡塞尔以知觉为例来说明意向对象意义的具体构成。在知觉行为的一开始,我们就一下子从整体上把握住对象,但这时候对象还没有任何规定性,它对应着作为意向对象组成物的X。在对对象X整体把握的同时,知觉行为还伴随着对对象的部分(独立的片块或不独立的要素)的部分知觉,在意向对象方面它对应着对象的谓词规定性。随之由于意识本身的综合作用,整体知觉与部分知觉获得相符(Deckung)或同一化(Ident-ifizierung)。在意向对象方面,我们就可以说对象X是如此这般这般,或者说获得如此这般这般的谓词意义或规定性。用符号S表示对象,P表示谓词意义,那么其结果就是“S是P”。
但分析并没有到此结束。胡塞尔认为任何知觉行为都是一种侧显(Abschattung),因为知觉对象是时空之物,这意味着对象的侧面和背面对知觉者来说不是自身给予的。虽然知觉行为一开始将对象视为整体,但接下来的各个部分知觉则只能显现对象的某个侧面。这样每个知觉必然包含着对前一个知觉的“保留”(Retention)以及对后一个知觉的期待。在意向对象方面,这意味着对象的每个谓词规定性必然包含了一个境域(Horizont),亦即其他谓词规定性的可能性,它们构成意向对象的第三个层次。
意义的构成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在《大观念》中,胡塞尔虽然还坚持意义的理想和客观性,但不再将它视为意识行为的本质,而是在意识之中被构成的。从构成的角度来看,胡塞尔在逐步放弃了《逻辑研究》之中意向与直观行为之间的二元对立。我们可以看到,在《大观念》中,知觉等直观行为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一个空洞意义的充实,它们自身就构成了意义,也就是说通过知觉意识活动对知觉感性材料的综合而构成一个意向对象意义。
在分析完知觉等直观行为的意向对象意义之后,胡塞尔又转而考察判断行为的意向对象意义。在判断行为中,他区分了“被判断者”(Ge-urteilte)与“判断内容”(Beurteilten)(注:《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237页。)。前者是判断所涉及的对象,如“S是P”中主词S的指称对象,而后者则是作为判断完整意义的命题或事态“S是P”。我们知道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将判断的意义看成是命题性的意义,它有别于作为知觉等表象行为的命名性意义。从纯粹句法学的角度来看,前者是复合性意义,因为它包含了一个范畴结构(如“辰星是暮星”,"a>b"等),是高阶行为(指包含范畴结构的谓词化行为或关系性行为等)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不含范畴结构的简单意义(如“辰星”、“暮星”等),是素朴的知觉活动的产物。
但是意识活动与意向对象学说仍然未能解释意向对象意义的确切所指。因为既然高阶行为奠基于素朴的表象行为,那么按照意识活动与意向对象的对应关系,这两种行为的相关物(意向对象意义)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种奠基关系。胡塞尔《大观念》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是知觉等表象或素朴行为的意向对象意义,而它与判断等高阶行为的意向对象意义之关系则被一笔带过。这一决非无意的疏忽恰恰暴露出《大观念》之中意义学说存在的困境。从意识活动方面来说,胡塞尔未能指出判断行为如何奠基于知觉等表象行为中;从意向对象方面来说他也没有说明,判断行为意向对象意义(命题或事态)怎样奠基于知觉行为的意向对象意义(谓词规定性)之中。
对意义的构成性分析所存在的问题,预示了胡塞尔后期考察意义问题的思路:从意识活动的发生源头追溯意义的具体构成过程,而非简单地停留在对意识活动与意向对象的二元结构的分析上。正是这一思路把我们引向了胡塞尔对意义起源与发生问题的追问,亦即意义的发生学分析。当然这一思路并非是对《大观念》中意义学说的简单抛弃,毋宁说是进一步深化。
4.意义的发生分析
后期胡塞尔的意义学说主要集中在《形式与先验逻辑》、《经验与判断》这两部著作中。从总体上说它们关注的都是,作为科学和逻辑最基本意义单位的判断或命题,是怎样在前判断的经验意识中发生的。因此后期胡塞尔的意义学说,一方面是在发生现象学的语境之下来被思考,另一方面又是发生现象学的重要组成内容。简单说来,《形式与先验逻辑》强调的是行为相关物或意向对象层面,而《经验与判断》则侧重于行为本身或意识活动层面。接下来本文将从这两个层面来讨论胡塞尔的后期意义学说。
4.1.意义的历史
所谓的“意义的历史”旨在描述表象相关物(名称)与判断相关物(命题)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构成《形式与先验逻辑》的思考主题。为简洁之故,我们以“S是P”这一最简单的判断形式为出发点,来考察意义的具体发生过程。所谓“最简单的形式”是指,主词"S"还没有获得任何具体的谓词规定性,亦即《大观念》中所说的作为纯粹“对象极”的X。
在对"S"的表象(如知觉)基础上,我们得出“S是P”这一判断。用现象学的术语来描述就是,S以承载了意义P的方式显现给我们。但“与此同时也一道产生了范畴产物SP:P显现为S意义中的积层。”(注:《形式与先验逻辑》,海牙,玛提努斯.尼霍夫出版社,1974,第315页。)“积层”(Niederschlag)意味着,在判断行为发生之后S不再是纯粹对象X,而是在其中沉积了意义P。这样当我们再次表象S时,我们面对的就不是赤裸裸的S,而是作为P的S(或SP)。以这一新的表象为基础,我们可以重新进行判断“SP是Q”。以此类推,我们就会得到“SPQ是R”、“SPQR是T”……等等无数的判断,同时对象S也拥有一个意义的积层,如SPQRT……。但这些谓词意义之间不是杂乱的排列,而是一种有序的前后依存关系,也就是说,每一个随后的谓词意义(如T)都预设了前面所有的谓词意义(PQR)。换言之,正是S的意义P引发(mot-ivate)了意义Q,而意义PQ又引发了意义R……。诸多意义之间的前后引发和依存关系构成了一个“意义的历史”。
“意义的历史”是从意识的对象相关物(意向对象)角度对意义发生过程的描述。根据意向对象与意识活动的平行原则,这一过程也应该相应地体现在意识的意识活动方面。这就涉及到表象与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在《逻辑研究》和《大观念》中,胡塞尔屡次提到这一问题,但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它。《形式与先验判断》虽有所涉及,但更详细的考察则是在《经验与判断》一书中。
4.2.判断、经验与生活世界
《形式与先验逻辑》中所说的“意义的历史”之观念,已经隐含了胡塞尔后期对意向性关系新的理解。意向性不再简单地被看成是意识与对象之间的静态关系,而是意识或自我的构成功能。胡塞尔的这一看法在《经验与判断》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该书将“意义的历史”视为意识的意向性作用之结果。意义的“历史源头”不是现代语言哲学和逻辑学中所强调的判断和命题,而是前语言和前判断的经验。为此,胡塞尔将判断还原为最源初的经验,“从判断的明证性问题回溯到对象的明证性”。(注:《经验与判断》(第五版),非里克斯.美纳出版社,汉堡,1976,第20-21页。)这样,意向性学说就成了对意义的发生学追问。
同胡塞尔的其他著作一样,在《经验与判断》中,(外)知觉再次充当了经验的典范。在面对一个对象S时,知觉行为在其开始阶段表现为一种“素朴的把握”(schlichte Erfassung)(注:《经验与判断》(第五版),非里克斯.美纳出版社,汉堡,1976,第116页。)。知觉通过事先被给予(vorgegeben)的感觉材料从整体上一下子把握住对象(如S)。同时,有关对象质性或规定性的部分伴随知觉虽然没有被清晰化,但却隐含在知觉意识中。随后知觉行为从“素朴的把握”过渡成为“清晰化行为”(Explikation)。它有“注意性清晰化”(Explizier-en der Betrachtung)(注:《经验与判断》(第五版),非里克斯.美纳出版社,汉堡,1976,第124页。)和“相关性清晰化”(Explizi-eren des Beziehendes)(注:《经验与判断》(第五版),非里克斯.美纳出版社,汉堡,1976,第177页。)之分。前者凸显的是一个对象及其具体规定性,后者则显现了数个对象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在从“素朴的把握”到“清晰化行为”的过程中,知觉意识具有一种综合功能,它将这二者都看成是对同一个对象的知觉,也就是说是一种相符关系(Deckung)。只不过这种综合还是一种被动综合,即对象以其质性规定性或关系规定性而显现在意识中,但没有变成体现在判断等谓词化行为中的主动综合。
从“注意性清晰化”方面来看,随着对一个对象观察角度的改变,在不同的知觉阶段(如W1、W2、W3、W4……),对象的不同性质(如P、Q、R、T……)得以显现。在这些不同的知觉阶段之间存在着一种联想(Association)或动机化(Motivation)关系,意即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包含了对过去阶段的滞留和对将来阶段的期待。从形式上看,这和休谟等经验论者所说的“习惯联想律”很类似。但由于排除了意识的经验实在内容,在胡塞尔那里,它就不再是心理现象之间的偶然连接,而是意识的先天和本质结构。举例说来,在W3这一阶段,意识还直接或间接地留有W2和W1这两个阶段的痕迹,这决定了它对W4而不是其他阶段的期待(联想);而在W4阶段,意识直接或间接地留有W3、W2和W1阶段的痕迹,这又决定了它期待(联想)的是W5而不是其他阶段;……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就意味着,意识是一种目的论式的意识流整体。从对象方面来说,它的最终目的是充分显现对象的“内视域”(Innenhorizont),或者说对象的一切内在规定性。
意识的目的论特征也体现在“相关性清晰化”活动中,只不过这种知觉活动的目的是充分显现对象的“外视域”(Aussenhorizont)。(注:《经验与判断》(第五版),非里克斯.美纳出版社,汉堡,1976,第28页。)“外视域”是指一个对象在与其他对象关系之中的一切可能的规定性。因此在“相关性清晰化”活动中,意识最终指向的是整个世界的规定性(意义),“世界是意识的终极视域”。
在胡塞尔看来,作为传统逻辑和科学最基本的意义单位,判断或命题的发生学源头正是包括知觉在内的经验领域。在“注意性清晰化”活动的基础上,意识用主谓范畴形式进行综合,形成不同的主谓判断“S是P”、“S是Q”、“S是P”……。在“相关性清晰化”活动的基础上,意识用关系范畴形式进行综合,形成不同的关系判断,如“张三比李四高”、“张三是李四的舅舅”等。同时判断的各种模态如“肯定”、“否定”和“可能”等也来源于“清晰化活动”的信念(Doxa)。“肯定”意味着一个知觉阶段中对象规定性的显现在另一知觉阶段得到证实;比如说最初我们看到这朵花的红色,接下来它为另一知觉阶段所证实,于是我们就肯定,“这朵花是红的”。否定则意味着对象的某一规定性在另一知觉阶段被证伪,比如说,最初我们看到这朵花的红色,但紧接着我们证实了它是黄的,于是我们就得出判断,“这朵花不是红的,而是黄的。”(注:《经验与判断》(第五版),非里克斯.美纳出版社,汉堡,1976,第325-347页。)“可能”则来源于介于这二者之间不确定的信念。
《形式与先验逻辑》已经表明,经验与判断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在《经验与判断》的第二部分中,胡塞尔再次重申了这一看法。意义最初发生于前判断的经验,虽后经过判断行为的主动综合而成为一个确定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活动的结束。判断经过命名化(Nominali-zation)之后,可以成为新的判断主词。随之,在以后的经验活动中,对象又承载上新的规定性,并有待被判断活动进一步综合,成为新的判断。正是在二者的相互转换中,新的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构成一个“意义的历史”。
意义从静态的、抽象的判断或命题领域,被回溯到前判断的经验中。正是这一洞见引发了胡塞尔后期对科学问题的思考,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真)命题集合,而它的意义源头是前科学、前判断的经验。在《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书中,前判断的经验领域又被称为“生活世界”,或者用美国现象学家古尔维奇(Gurwitsch)的话来说,是一个源初的意义世界。(注:《现象学与科学理论》,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伊万斯顿,1974。)科学原本来自于生活世界的素朴直观和经验。但是自近代以来,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却逐渐以一种“数学化的自然”来取代生活世界,也就是说用数学化的公式和公理取代了生活世界,并且抽空了它的意义。(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选自《胡塞尔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1024-1026页。)既然科学的危机由此产生,那么危机的唯一解决之途就只能是让科学重新返回到前科学的生活世界,并且在生活世界中追溯构成科学判断和命题的意义源头,或“意义的历史”。
5.结语
从《逻辑研究》到《经验与判断》,我们追溯了胡塞尔意义学说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胡塞尔的意义学说与现象学思想的发展是同步的。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将意义理解为意向性行为的本质,而这一意义观的困境恰恰植根于《逻辑研究》中所预设的本体论立场。这迫使胡塞尔在《大观念》中发展出先验还原和先验现象学观念。在《大观念》中,意义不再是意识行为的本质,而是由意识所构成的、并且与意识行为(意识活动)相平行的意向对象相关物。但意识活动与意向对象的二元结构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说明意义的发生。在其后期著作《形式与先验逻辑》和《经验与判断》中,意义的发生源头被进一步追溯到前判断、前语言的经验领域。正是在经验与判断的互动关系中,意识的意向性特征得以最后体现,并且创造了一个“意义的历史”。
作为意义发生源头的经验领域也就是《危机》中所说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预示着胡塞尔思想的又一重大转变。它意味着,现象学不再被局限在封闭的意识世界,而是被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在胡塞尔之后,现象学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并且衍生出生存哲学、解释学等新的现象学派派。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胡塞尔的最初设想,但却为意义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就此而言,本文仅仅是一个开端。进一步考察胡塞尔之后现象学意义学说的流变,则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