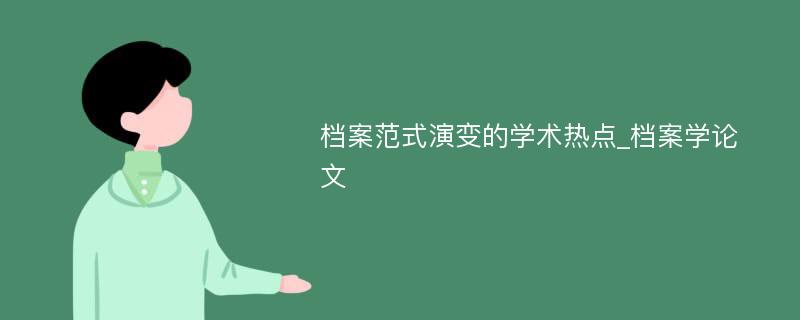
档案学范式演进中的学术热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范式论文,学术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特定时期内不断地被为数众多的档案学者研究、探讨的档案学研究内容可称为档案学术热点。档案学范式演进史显示出了库恩式的科学演进模式,它已经历了前科学、常规科学时期,“当前档案学正处于常规科学向科学革命转变的时期”。[1]在档案学范式演进的不同历史时期,有过各种各样的学术热点,来源原则这一学术热点最终发展为共有核心理论,并发展为了共有经验、共有理论、共有方法论和共有世界观的金字塔形结构,促成了档案学范式的确立。[2]档案学术热点与档案学范式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往不少学者从论文统计、观点归纳、关键词归纳等微观的角度研究过档案学术热点,这些研究为从宏观角度研究学术热点对档案学范式演进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1 学术热点对档案学范式演进的影响
学术热点的典型特征是研究主体大量集中在几个方向进行深入研究,体现为研究活动的量变。将学术热点置于档案学范式演进中观察,这种量变会对档案学范式产生什么影响呢?量变是否会引起质变性的范式转换?笔者认为,学术热点包括纯量变的部分也包括因量变到质变的部分,纯量变部分完成的是已有范式的完善工作,这类量变并不一定会引起质变,而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撼动传统范式,这些才会引起质变,并形成新的学科范式。以下试分析具体效果:
1.1 档案学术热点纯量变部分的影响效果
在档案学范式演进史上,学术热点纯量变部分的影响效果主要体现为:
1.1.1 档案学主导范式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向纵深发展。在常规科学时期,以来源原则为核心共有理论的档案学主导范式支配着整个学科的发展。当档案学范式已被档案学共同体基本认可后,学术热点开始进入“扫尾解谜”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是档案学范式演进中 “扫尾解谜”期。来源原则和鉴定理论是这一时期的理论热点。从布鲁塞尔大会的国际传播,以及英美在“文件组合”中的运用,德国自由来源原则的进一步修正,苏联和中国在全宗理论中的继续发展,这一阶段来源原则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形式,其追求的都是高效的管理目标。来源原则得以扫尾性进一步发展的代表作有:英国档案学家詹金逊1922年的《档案管理手册》(其“档案组合”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来源原则),意大利卡萨诺瓦1928年的《档案学》(针对荷兰学者关于来源原则的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苏联克雅捷夫1935年的《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认为档案全宗是在某机关或个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地形成的档案材料总和)和德国布伦内克1953年的《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历史》(阐述了自由来源原则,主张“来源一致性基础上的事由一致性”)等。研究的纵深发展直接推动了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编研、利用理论与实践的纵深发展。例如:关于档案鉴定的热点研究从行政官员决定论到宏观职能鉴定论的演变历史体现了来源原则在档案鉴定子范式上的纵深发展;关于电子文件的热点研究更是从全过程地深化了原有的学科范式。
1.1.2 档案学亚科学共同体业已形成并不断壮大。档案学共同体因档案学范式的产生而产生,也因档案学范式的发展而发展。档案学共同体作为一种组织,其成熟的过程会经常伴随产生档案学亚科学共同体,即以档案科学中的某一研究方向为主的科学共同体。例如由于电子文件研究的持续升温,中国档案学共同体中已经有了电子文件亚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周寄中教授曾经概括了科学共同体的一般组织形式,其中的“有形组合”包括核心式组合、学派式组合及师徒式组合。[3]在中国,电子文件亚科学共同体主要体现为同事式组合和师徒式组合。例如:在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师大、南京空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苏州大学等高等院校都有电子文件方面造诣较深的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已经自然形成亚科学共同体。随着档案学范式的发展,热门研究领域的定向聚合作用会越来越明显,这种亚科学共同体还会不断产生。
1.1.3 档案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反响不断扩大。档案学研究成果或发表于期刊杂志,或出版专著,或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公开交流,通过成果交流,档案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反响就会越来越大。不少档案问题在研究初期并不为人们所关注,就是由于其广泛传播才使其有了更大的价值空间。档案学术热点中,无论是来源原则研究、立卷改革研究、电子文件研究,还是家庭档案研究、民生档案研究,无一不是沿着从无到有,从冷门到热点的发展轨迹进行的。更重要的是:随着研究力度的加大,研究结果还可能直接影响法规政策标准的制定。《机关档案工作条例》、《档案馆工作通则》、归档文件整理规则、电子文件管理标准、元数据标准都曾经历过从研究热点到法规标准产生的过程。
1.2 档案学术热点从量变到质变部分的影响效果
量变的档案学术热点达到质变并引起档案学范式的转换的过程是有一定规律的。从总体上看,它遵循从档案学研究经验层、理论层、方法论层到世界观层渐次推进的规律。它在从前科学时期向常规科学转变的时期体现出“质变”的效果,产生了档案学范式,这种“质变”经验对判断当前学术热点的影响力具有借鉴作用。
16世纪到19世纪末20世纪是档案学范式尚未形成的时期,即档案学的前科学时期。这一时期,档案研究内容较为广泛,学术热点主要是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基本问题:档案的价值、档案的分类、档案馆及档案开放。其中关于档案的分类原则的探讨与档案学范式确立有直接关系。档案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对档案进行最优化管理,探索档案分类原则的实践与理论探索是前科学时期最热门的议题。代表性的观点有:拉明根的君主、臣民和外交职能分类法,波尼法西奥的地区、事由和时间的系统分类法,木尔茨的归纳分类法,斯皮斯的朴素的来源分类法,卡缪-多努事由分类法,法国档案工作改革期间出现的“尊重全宗原则”,德国的“登记室原则”等等。对档案分类原则的思想碰撞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当时档案管理的现实需要也要求人们能够尽快地确定一个统一的实用客观的原则。思想碰撞的结果是:观点归于统一,“战火”归于平息,最终诞生了《荷兰手册》,来源原则得到档案学共同体认可,形成了专业的核心理论,并在方法论上走向以历史方法为指导的系列方法,形成相应的档案学观。由此可见,档案学术热点化是新范式的产生的重要推力。由于档案学术热点的研究群体基数大,在从经验层开始的探索中,就经常出现新观点、新方法,在不断出新的研究成果中,档案学共同体会发现,有些观点已经不太符合原有范式了,从这时起,反常出现,当其中的一部分成为反例,并为大多数共同体成员所认可后,档案学革命就会发生,新的档案学范式就能确立起来;如果其中的反常并没有成为反例,新的范式就不可能产生,但不影响它们对常规科学的扫尾式完善作用。
以史鉴今,档案学术热点对当前的“反常解谜”期(20世纪中叶至今)的学科范式又有何影响呢?当前的档案学术热点已有很多学者[4]做过归纳,以下是5组学者(黄存勋,1998;罗永平,1998;牛耕,2005;傅荣校,2006;王新才、朱玉媛等,2009)中至少有4组认可的学术热点:档案及其本质属性,文件生命周期与文件连续体理论,全宗理论,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有2届国际档案大会涉及),新技术的运用、电子文件及数字档案馆,此外,档案的产业化,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档案法制建设等问题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反复研究。其中电子文件及数字档案馆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问题至少有6届国际档案大会明确涉及。根据中国知网对档案类“学科学术热点”的2010年5月26日的统计数据,电子文件研究又是热点中的热点,其研究主要文献数、相关国家课题数、主要研究人员数及主要研究机构数均居首位。电子文件出现后,来源原则被重新讨论、出现文件连续体理论,有部分共同体成员开始质疑原有的档案学范式,档案学范式也的确出现一些反常,这些反常是否足以撼动原来的档案学范式仍需观察,但这种波动已经开始了。档案学范式的核心共有理论——来源原则就经历了被质疑和重新发现的曲折。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机读档案的出现,来源原则遭受质疑;1985年,理查德·莱特、戴维·比尔曼发表《来源原则的力量》,重新认识到来源原则的地位,呼吁学者们重视对文件形成者和文件格式的研究,也引起国际档案界的重视。1993年,瑞典国家档案馆在纪念建馆375周年时召开的关于档案学理论与来源原则的学术研讨会上,来源原则的适用范围也在会上引起了争议。[5]1996年的国际档案大会意大利的A.穆勒提交的《来源原则:仍是本专业的基本原则吗?》,加拿大学者特里·库克的“新来源观”和元数据的引入为来源原则的当代适用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但这显然与《荷兰手册》中的来源原则已有了很大不同,随之而来的是文件连续体理论立体思维的构建、档案的宏观鉴定原则,档案学研究中开始出现后现代端倪。由于电子文件研究的热点化,原来以现代性为特征的来源原则已经出现反常,这种反常也似乎有了成为反例的可能。
可见,学术热点与档案学范式转换有必然联系。学术热点虽然不一定产生反例,但已经是反例的学术观点必须经过档案学共同体的深度研讨、达成一致,经过必要的热点化过程才能真正引导范式转换。亦即:档案学术热点化不是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档案学范式演进需要学术热点,学术热点中的最创新、最积极的部分将成为推动档案学范式演进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学术研究中,要对学术热点进行科学调控,时刻为档案学范式转换做准备。
2 档案学术热点化进程的科学调控
研究内容能否成为学术热点与社会背景、学科发展阶段都有一定的关系,但又常常带有很强的主观主义色彩。学术热点就像一种流行元素,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眼球,但也很可能鱼目混珠。如果盲目地追求“学术时尚”,唯“热点”是瞻,档案学范式就可能走入迷途。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调整引领有益的研究领域走向档案学术热点是摆在学界面前的一大难题。承担起这种科学调控任务的是全体档案学共同体成员,具体可以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专业学会和包括学术期刊、网站在内的学术交流媒体。调控的基本准则是:看档案学术热点是否能推进档案学范式的发展。
2.1 对学术热点的学理把脉
档案学范式发展需要通过学术热点的讨论研得理论精髓。从学理上看,有利于档案学范式发展的学术热点应当是符合以下两种需要的原理或法则。它在宏观上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需要,在微观上必须符合学科核心理论发展需要。
档案学属于管理类社会科学,它必须研究如何高效地进行档案管理,脱离国家和社会的实情是不可能有成就的。来源原则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顺应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产生的。必须强调的是:这种需要还应当围绕学科核心理论前沿,适应长期需要。这期间,关于电子文件及数字档案馆热点研究就不仅顺应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且提出了核心的前沿理论,指引着后续研究的进行,属于长期需要。诚然,适应短期需要的学术观点也能够推进学科发展,但它们不应当成为热点。在常规科学阶段,如果热点研究仍然只是停留在一些基本概念、应时性或跟风性的短期问题上,它们就很难推动学科核心理论发展,更不用说影响档案学范式了。
2.2 对学术热点的实践考量
学理的进步为的是更好地指导实践。因此,从实践上考量学术热点并对其发展进程加以调控是非常必要的。学术热点应该围绕档案管理的重点和难点而展开。学术研究不可脱离实践,学术热点作为大多数共同体成员关注的问题,更应当以实践为评价依据。从档案学范式演进史看,有生命力的学术热点都是多针对实践的研究,无论是档案管理实践、还是档案学科建设实践研究都是对实践反映。档案学范式的发展轨迹也是从总结实践经验开始的,没有这个根基,理论的升华、方法论的产生和世界观的形成都是一句空话。以档案学范式的“反常解谜”期为例,有关电子文件管理实践的研究就属于典型的实践性学术热点,这些研究直接推进了电子文件管理技术与方法的进步,提高了档案管理效率,解放了人力成本,也产生了诸如文档一体化、电子文件全程管理、数字档案馆等实践经验,在这方面“徽式探索”、广东经验都是值得称道的。
2.3 对冷门学术研究的价值发现
“热点问题”与“冷门问题”是相对的,“一个时空背景下的非学术主流,可能跃居另一个时空背景下的主流”[6]创新性的冷门研究领域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成为学术热点的。有报道称中国某留学生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攻读电影档案学硕士,开设在艺术类专业中。[7]笔者以“电影档案”为检索词在中国期刊全文库(1979-2010)30多年间仅检索到16篇相关文章,其中档案界的研究仅4篇,这种状态足见其“冷”。但仔细分析,这一研究是可以大大促进电影档案的理论与实践水平提升的,并达到完善档案学范式的目的,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其研究价值和前景看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价值的冷门学术研究对于档案学范式的完善,尤其是“扫尾解谜”式完善意义重大。
各级各类的档案科研、学术机构是承担科学调控使命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些以松散型的学术组织为主的调控主体来说,对学术热点进行科学调控并非易事。档案学共同体成员应当在遵守基本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担负起学术责任,“一个有生命力的档案学共同体应当对社会、对学科、对自身发展负责。”[8]对已经形成热点的学术问题应加以科学引导,对尚处冷门的学术问题也不可忽视,对于其中的重要学术问题要有意识地加大研究力度,人为地通过下达各级各类科研项目计划进行调控,推动整个共同体成员的参与,推动档案学范式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