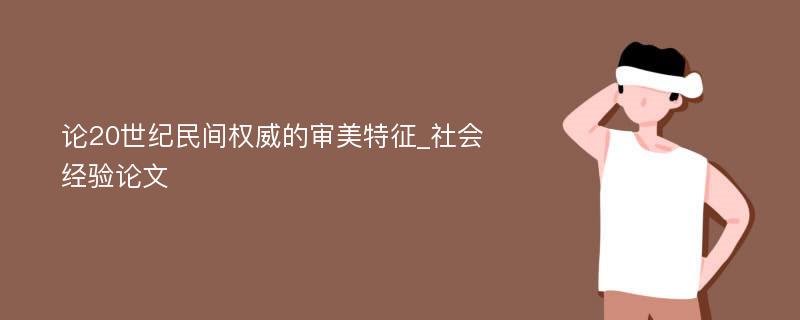
论二十世纪民间权威的审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特征论文,民间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中国社会文化形态变换最大的世纪。从根本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是不同文化观念和社会权力的冲突与轮换。民间权威作为民间社会的无冕之王,他们的矛盾冲突及其权力轮换,代表或体现着社会文化转型的基本情态,作家对民间权威的审美把握与描绘,使文本形象具备了历史、文化和审美的丰富意蕴,形成审美批评的崭新视界。
所谓民间权威主要是指相对于上层社会和官方机构的主体所拥有的比其他人优越的地位、才能、权力和人格魅力及其对他人的影响力。这种民间权威可以是个体(本文主要指个体),也可以是一个集团或民间制度。因为他具有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超人的经验、才能和威慑力,能令相应于他的客体产生敬畏、赞赏、佩服等感情,从而乐于趋从与服膺他。因此,民间权威在地方民众中间具有较高的威望,往往能在一个重要的事件纠纷与地方冲突中起到调节、治理和疏导作用,成为不用暴力或不靠暴力而达到“统治”的“领袖”(注:权威(authority)一词源于西方社会学。马克斯·韦伯把早期基督教语汇的“卡里斯玛”(charisma)的神助天赋的原义创造性地拓展为具有原创性和感召力的人物。本文在社会学有关“权威”的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民间社会的现实和20世纪小说的创作,提出民间权威这个概念。)。
民间权威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传统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是指依靠传统(习惯)的“合理性”和神圣性而实现其“统治”的权威。在传统社会中,依据传统信念而得以实施统治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古老传统的神圣性以及实施权威者的合法地位的牢固的信念”(注:D·P·约翰逊:《社会学原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82页。)。这种“合法”地位的获得往往不是后天创造的,而是先天设定的,因为实施权威的人“天生”归属于(或选择了)一个传统上实施权威的关系、地位或群体组织,民众对这种传统习惯的认可与服膺,因而使他具有了权威的“天然”权力。传统型权威的形成和发展与宗法家族制度密切相关。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由于人们对土地、耕作和气象等经验的依赖,使以血缘关系凝聚起来的村落家族凭长幼辈份实行等级管理,即特定的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形成了传统社会的“地位”,“族老由于出身就在整个村落家族血缘关系的中心,因而他们便拥有权威”(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每个人都“命定”在这种关系中生存,试图超越这种伦理关系将被视作不忠、不孝和大逆不道。
20世纪中国以乡土社会为主体,在由传统农耕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传统权威既发挥了巨大的经验性作用,又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传统与现代、经验与科层发生了诸多冲突,反映了转型社会丰杂的文化情态。族长、孝子及其与村长、土匪等法理性权威的矛盾斗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农耕社会的权威类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原生态生活相,生动、真实地展现出传统社会艰难的蜕变过程。
二是法理型权威。法理型权威也可称为科层式权威,是指依据法律制度赋予的权力所施加的影响而形成的权威。它与传统权威尤其是与感召式权威有所不同,它并非靠个人的才能、品质、人格魅力影响和感召民众,而是由于他占据了可以实施权威权力的地位。尽管日后可能由于他的出众的管理才能亦感召了下属于他的民众,使之集法理、传统和感召诸权威类型于一身,但在此前,他主要是凭靠法理权力才获得的权威力量。“简单地说,行使合法权威的人如此行事是由于他所占据的社会地位被现行法规确认为权威地位。下属服从这一权威,是因为法规规定他们所占据的社会职位在某一特定的范围内处于从属地位。”(注:D·P·约翰逊:《社会学原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87页。)
法理权威的出现是科学理性推广的结果,也是对传统宗法制度的挑战。在民间,以血缘和地缘关系联结起来的人们,总是趋向维护传承已久的现存制度。农耕社会中,血亲关系的盘结,使“乡党”之间决少商贸算计,任何帮工都可以以“亲情”互惠。在这种社会中,商贸法理很难发展。然而,一旦人们走出血缘关系,踏出血缘“投影”的地缘界限,人们便马上变得“陌生”,任何物品交换都易于清算了,签字画押标明了法理社会的形成。
血缘关系退出社会事务,代之以法理权威行使族老权力,是中国民间社会迈向现代的标志。在20世纪中国,一旦传统、封闭、保守的血缘家族的权威被行政(政治)手段所建立的法理权威所替代,无论是农乡还是市巷,现代商贸活动和自由民主精神便迅速发展起来。村长、里长、队长、居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这些基层法理权威,遍及民间社会各个方面,成为社会转型的基本推动力和新法规的执行者。在他们身上深刻而广泛地聚现了民间社会民众的思想、行为及其追求。
三是感召型权威。感召型权威也可称为自然式权威或情感型权威,它指的是那些因自身所具有的超众的智慧、品质、才能而对民众产生了感召力和吸引力的权威。感召型权威的基础是民间领袖的个人才能、气质、品行。由于他具备了为民众所推崇的规范和道德,他的才能和品质才吸引感染了民众,使民众乐于追随他,服膺他,并在感情上趋近他。
与传统权威和法理权威维持现存秩序不同,感召权威往往总是力图改变现存秩序,建成新的社会秩序或道德规范。因此,感召权威多是一些不满足现状,渴望变异的活跃人物,在他们身上,凝结了民间许多智慧与奇想,形成了民间的“思想村落”。但这种才能品质并非纯然天生的和神赐的,而主要是在后天的生存活动中锤炼出来的。即由于种种曲折的经历逐渐培养了他们的聪慧、才识、胆略和人格魅力。在他们的周围所聚集的或被感召的人群,既有与他同类的人物,也有为相关利益所趋动的普通民众。一旦社会危机或社会突变的时候,如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等,人们就会在感召权威的召引下,“揭竿”而起,成为新的社会变革的力量。20世纪的社会文化转型,为感召权威的应运而生提供了无数个机遇,一个个权威从家族、村落、街道、里巷、工厂走向民间变革的“枢纽”,成为历史评判的关捩。
民间权威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处在权力或信息的中心,能够映照出民间社会丰富的生活相。虽然从现在时态上看,民间权威是一个静态的坐标,然而透过他们的生成过程,却可以触摸到民间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权力轮换的真实图景。当作家准确地认知把握了民间权威的品格,并以审美情感加以透视、提炼时,就会赋予人物形象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民间权威的形象身上,已经蕴涵了历史因素、地域因素、政治经济因素、民族文化心理因素等诸多文学创作和审美要素,因而使民间权威形象成为源于生活又高于原型的“典型”,成为意蕴丰富的文化符码。
根据民间权威的现实作用和文学形象的审美意义,民间权威审美特征可以归结为:
1.历史集成性
民间权威是一种应对各种事变、承受历史重压的人。在他们身上,集中反映了当代各种势力矛盾斗争的复杂情态。每当事变关头,他们或以其智慧、经验、侠义、胆识、魅力、权力、威望控制局面,扭转局面,调解矛盾;或因身处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而备受冲击,承受磨难。他们之所以具有非凡的胆识,超人的卓见,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历史变异的契机,总结、继承、创用了前人的经验,并在这种历史变异中成功地发挥了自身积累的知识、经验、能力和智慧,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事变的有利条件,才成为驾驭历史事变的人,成为民间历史的见证人。民间权威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血缘与地缘关系维系紧密的空间中,在无数个民间事变的合力运动中,如民间纠纷、婚丧大礼、乡约制度的商议制定等,具有超众才干的民间权威才逐渐显露出来,成为民众推崇或惧怕的偶像而突出于民众生活之中。它本身就构成一个民俗事象,像一个习俗惯制,每逢事变,必为众人推举,或牵头起事,或排解纠纷,或安顿乡里。因此,民间权威如无冕之王,为民众服膺。这也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因此,民间权威并非神助天赋的奇才,而是历史运动和社会实践的集成者与见证人。
张炜《古船》中的赵炳之所以成为全镇人仰慕的权威,就是因为他把握住了历史变革的契机,经过“解放”、“大跃进”、“饥荒”等多次社会变故的考验,逐渐培育和具备了众人服膺的才干、智慧、胆识和人格魅力,才成为集传统、法理和感召权威于一身的民间权威,成为洼狸镇的太上皇的。他的形象既融入了儒家和道家的修身养性、刚柔并济、老谋深算的文化秉性,又颇显江湖好汉的敢做敢为、济施百姓的本色,更兼有流氓泼皮的淫荡和无赖。审视这样的形象,确能让人感受到民间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厚重的文化意蕴,以及超凡入俗的各种能人合构的历史表演。
民间权威人物在作品中往往处在人物群体关系的核心或事变的关节点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并非人人都生发着平等的作用,那些聪颖和富有才干的人往往处在社会关系的关节上,或者矛盾的焦点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作家通过描述网结或关节上的人及其关系,最易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塑造出一个典型并暗示出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来。所以,民间权威形象代表了作者构思立意的“轴心”,全力塑造好关节点上的人物,将会带动其他人物鲜活起来,并提升整部作品的品格。民间权威形象将会因其集历史、心理、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于一身,而成为人类的、民族的、地域的和历史文化的集成者,显示出丰厚的文化、历史、社会的意蕴。
2.现实感召力
民间权威的非凡才能与出众品质,对民众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他们宛如救世主为众人簇拥和追随。民间权威的感召力并不以权力的强制为主导,虽然他们排解矛盾纠纷和创建新秩序时常常伴以权力和制度的化身,但他们的优异品质和人格魅力使他们的才能更充分地显现为一种情感的感染力量,使民众在一种心悦诚服的心境中接受他们的安排和调节,而较少感到权力或说教的力量。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感召力也是民间权威最突出的特点。它相对于现代理性制度、秩序权威(如政府的官税、工商、司法等辖治)的严密理性和缺少人情味,表现出民间社会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笼罩下的亲情感召基础。
民间权威的感召力取决于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判断、继承与创新。民间权威的人格魅力和出众才能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培育出来的,他们往往汲取了前人的优秀品质,借鉴了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经验,才建立出新的民间关系秩序。《红旗谱》中的主人公朱老忠的性格成长史,即从普通农民成长为民间感召权威的过程颇有代表性。他年轻时目睹父辈们与地主斗争失败的悲剧,愤而出走——下关东的经历,闯荡“江湖”所形成的传统式豪侠本色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品格,使他逐渐积累了与“恶人”斗争的经验与胆识。尤其是他在共产党员贾湘农的帮助下阶级觉悟的提高和斗争理想的确立,更使他具备了民间权威的智慧、才能与见识,因此,他才在与地主冯老兰的斗争中,叱咤风云,智勇双全,成为锁井镇一带的农民甘愿服膺的领袖。
民间权威的感召力也是形成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审美因素。民间权威作为特定地域的“能人”,他所具有的丰富的人生经验,超众的胆识魄力与才能,使他成为文学审美的绝好原型。因此,当作家将他提炼加工写进作品时,在特定的地域文化时空中,激烈的矛盾冲突将使权威的性格在矛盾双方的碰撞中激发出夺目的形象之美,令读者感受到具有了审美指向的民间权威(人物)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和人格魅力。朱老忠的形象魅力就是通过反割头税、保定二师学潮、巧救张嘉庆、高蠡暴动等阶级对抗与冲突中展现出来的,每一个读者都不难被他耿直、忠义、豪爽、敢做敢为的英雄品格所感染,为他在历史事变关头的睿智、老练所倾倒,获得审美的共鸣与愉悦。
3.文化象征性
民间权威形象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个例,它具有艺术符号的象征功能,是在文本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具有能指与所指、物象与意象丰富意蕴的象征符号。文学形象源于现实生活却又高于现实生活。它是作家审美理想与创作灵感对现实印象进行提炼、加工,创造出的具有虚拟性质的语义符号,因而它具有符号的编排关系和符号所指的语义拓伸性。它使文学形象表现出既与现实物象世界相联系,又与审美意义世界密不可分的艺术象征性。比如在传统权威形象身上,我们不仅可以复现能指所具体呈现的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物性格,而且能够通过能指所暗示的语义的拓伸指向,联想到其所代表的特定时代或历史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使这一个独特的民间权威具有了某类权威和某种社会(历史)的代码意义。
文化语境是民间权威形象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与社会关系双向互动所形成的文本总的话语情境。这种社会关系不仅指促发或制约民间权威行动的社会环境,而且包括构成当下人们思考或行动的政治、经济、伦理、习俗等社会总的关系因素。这些关系或显或暗地与民间权威发生着联系,构成民间权威性格发展的话语情境。之所以把话语情境称作文化语境,是因为民间权威生存于社会中下层,与广大民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所持存和使用的话语,是经历了年代陶砺和民众传承的文化符号,而这种民间话语又经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所复制加工,更加文化化和艺术化,因而使民间权威形象更具符号化、象征性,成为新的文化语境。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之所以一被创造出来就作为20世纪文学史上的“典型”而载入史册,就与他的丰富的象征性分不开。在表象层面上,作家只写了白嘉轩从清末到解放初50年的人生历程,但是,阅读《白鹿原》的人,决不会把白嘉轩仅仅当做关中某乡村的一个族长和地主,在这个蕴涵丰富的传统权威身上,作家通过符号的准确、精当的编排,使能指与所指互为预应支撑,极大地丰富了语义的拓伸性,借助人物办学堂、兴乡约、修祠堂、耕读传家等一系列传统文化活动,寄寓了传统民族文化如何被振兴、发扬,又怎样在社会转型中遭冲击、被分解的历史发展趋向,表现出族老统治走向法理统治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