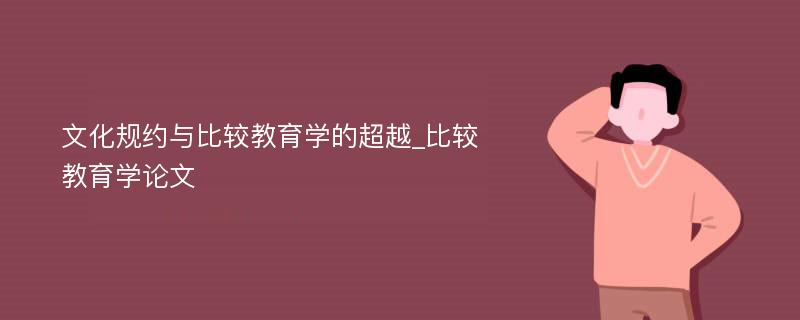
比较教育学的文化规约与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约论文,教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0)01-0015-05
自朱利安创立比较教育学以降,比较教育学的实证主义情节就挥之不去,人们试图寻找一种超越所有民族文化传统的普世视角来言说本族和异族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然而,教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术史却证明了教育学的文化秉性和比较教育学的跨文化学科品质,我们根本无法找寻到这样一种普世的视角。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教育具有文化性,又不存在普世的视角,那么,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相互间的识别与理解何以可能?比较教育学存在的可能与合理性何在?比较教育学的内在秉性与价值诉求何在?比较教育学应该站在怎样的立足点进行言说?文化规约似乎已经成为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危机之源,解读和超越文化上的规约,追寻合理的立足点和研究视野,对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认识的起点——教育学的文化性
当前,教育学缺乏“科学性”的声音依然此伏彼起,教育学因缺乏科学性而自卑地生存于诸学科之中,教育学者们也为此战战兢兢,甚至于在教育学者内部喊出了“教育学的终结”的声音,[1]教育学和教育学者们的这种生存处境和精神风貌确实是教育学的“悲哀”,而这种“悲哀”产生的前提预设是,科学化是教育学发展的应然方向。然而实际上,教育学的学术实践史已经充分证明,教育学的科学化只会让教育学的发展误入歧途。这种科学化的诉求无疑是基于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的。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强调像研究客观事物那样研究人和教育问题,强调教育事实和教育价值相分离,追求教育研究的客观性,因而主张教育研究主体保持价值中立,并强调对研究过程的精密监控和对研究结果的量化处理,而事实上,科学实证主义恰恰否定了教育研究中最为本质的部分,即教育中的价值世界,没有价值存在的教育学是冷冰冰的、不完整的教育学,换句话说,不存在剔除价值存在的教育学,教育理论研究本质上是基于教育实践的价值沉思,因而,只有以文化作为立足点才能对教育实践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文化性是教育学与生俱来的内在秉性。文化是教育学活动的时空,任何教育活动都是一定历史文化时空中的教育活动,教育中的每个元素都饱含着文化的符号,是人们价值趣味的投射,教育研究的主体亦不是只具理性的冷冰冰的主体,而是完整的、具有独特个性品质的、具有独特生活体验的人,他们认识教育活动的过程是以自身所在的历史文化场域作为认识背景,深入教育实践的历史文化场域的完整体验。这样的认识活动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是研究主体基于文化交往的深度理解和价值生成活动。因而,在教育研究中,不存在高高在上的、超越一切历史文化的普世视角,也不存在超越一切历史文化而适用于所有民族的教育真理。任何教育理论成果不过是代表其所处场域中的文化传统,为着特定场域的文化生活需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实证主义是偏于一隅的,在教育学中使用“奥卡姆剃刀”无疑是自掘坟墓的举措。概言之,“教育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2]
教育学的文化性内在地包含了教育学的另一个特性,即教育学的民族性,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任何民族的教育学活动都是在其特定的文化场域中进行的,深受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和影响。如德国教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美国教育学的实用主义气质等。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教育学就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映射,充满着民族文化传统的气息,只有认识到教育学的民族性,教育研究者才能守护住教育学的根,才不至于在无根的状态下四处漂泊,以至于受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毒害,也只有抓住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之根,才能以理性的心态面对教育中的跨文化交流,促进本土教育学的发展,对于充满“西化”气质的中国教育学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更是尤为重要。
二、比较教育学的文化规约
我们之所以称这门学科为“比较教育学”在于比较的方法是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而关于如何比较、比较为何,比较教育学史上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认为应以教育事实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以客观中立的态度介入教育研究,反对任何的价值涉入,试图寻找超越一切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而历史主义研究范式试图以价值研究取代事实研究,以价值论取代方法论,认为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受西方客观主义的影响,又逢诞生于实证主义盛行的年头,比较教育学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有实证主义的情结,普世的视角和理论成为许多比较教育学者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然而,这种尝试和追求注定是要失败的,在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践中遇到无数次历史与价值因素之后,比较教育学者们不得不回到历史主义的传统中去。如前所述,教育学具有文化性和民族性的内在品质,文化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视野,比较教育的根本在于深入教育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比较。而问题在于,既然文化是不可通约的,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我们无法完全将自己置于“他者”的视角认识异族教育,我们也无法找寻超越一切文化的普世视角,那么对异族文化中教育的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绝不是简单或可以忽视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实质上是对比较教育学合理性和存在意义的追问。究竟是什么文化上的因素规避了比较教育学者的学术实践,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教育学的文化规约问题。我们认为,比较教育学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文化规约:
第一,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文化屏障问题。所谓文化屏障是指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个体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所造成的文化交流障碍。实际上,既然文化性是教育学的根本品质,比较教育学中存在文化屏障就成为一种必然,“有些人否认文化屏障的存在,但是他们自己却总在不同程度影响整个人类。那些最少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往往就是受蒙蔽最多的人;而那些否认文化屏障存在的人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察觉到它们的存在。”[3]丹尼尔的这句话指出了文化屏障存在的客观性,也指出了文化屏障对人的规避作用,这种规避在于历史文化传统使研究者形成一定的“先见”,从而“误读”了异境文化传统中的教育。所谓“先见”是指在理解异文化之前,研究者受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影响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及思想见解。研究者的“先见”是构成研究者研究能力和研究思维的重要成分,研究者以自身文化上的“先见”作为认识背景来理解异族文化中的教育,从而造成“误读”。这种误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做到对异族文化和教育进行原汁原味的解读。乐黛云先生就认为,“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总之,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以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课题文化中吸取新义,还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的立场上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4]
第二,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文化殖民问题。尽管二战之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是文化上的殖民远远没有结束。教育学的文化性意味着文化霸权在教育学中生存空间的存在,文化殖民直接影响到比较教育学者的言说方式和学术轨迹。“比较教育学在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初期所采取的内省批判方式,使它建立了一种与东方学正好相反的权威假设模式,即假设其他民族的教育中必定有某些可以为本民族‘借鉴’而改良本族教育的东西。”[5]这种“他族优越假设”也使“西方中心主义”成为被殖民国家比较教育学者的文化潜意识,“西方教育先进,本族教育落后”几乎无可非议地作为定理嵌入每个第三世界比较教育学者的学术意识当中。在此种情况下,加上本土教育学失范的影响和科层制的科研评价体制的催生,在第三世界的比较教育学者们的学术实践中,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往往演变为单方面的引进和虔诚的崇拜与信服,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尊奉”成为比较教育学者在学术品质上的“常态”和必须,西方教育理论对于第三世界比较教育学者而言已成为比本族教育学理论更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摆脱西方教育思想运用本土话语进行学术实践,至此,“西方”已经不仅存在于西方,而是存在于全世界了。
当然,实际上,即便如此,第三世界的比较教育学者也不会在“他族优越假设”和对西方教育理论乐此不疲的虔诚中完全丧失自我。因为教育学作为文化科学,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无时不在地影响着研究者的学术实践,学者们总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在本族文化场域中将本族与他族或他族与他族的教育进行比较,以获得所谓的“借鉴意义”,不过,这一过程中,比较教育研究却必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文化屏障的存在,造成比较教育学者对西方教育的误读;二是在借鉴过程中缺乏对西方教育理论合理的本土转换,从而使比较教育学者渐长的民族文化自我意识恰恰助长了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霸权话语。两方面问题使第三世界“有偏误地”“借鉴”着西方教育体系和教育思想。
三、比较教育学文化规约的解读与超越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无论文化上的规约如何影响了比较教育学的合理性和解释度,比较教育学存在的意义和学科贡献都是无可置疑的。首先,教育发展的世界性语境和外部资源是研究一个民族教育的基本视野,比较的方法是研究教育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对于我们研究教育研究的基本范式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比较教育研究是确立自我和认识自我的重要途径;第三,比较教育研究也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挑战,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国际化的有力途径。至于比较教育学所遭遇的文化上的规约,可以说,这是当代语境中比较教育学所必然面临的问题,这也是自朱利安创立比较教育学之后比较教育学者不断提升学科自觉的结果。文化性是比较教育学的内在秉性,跨文化视野是比较教育学的基本学科视野,其所面临的文化规约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解读和超越。
文化屏障是否意味着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成为不可能,更或者意味着比较教育学学科合理性的消融?其实不然。的确,我们永远不可能作为第三者俯视一切世间的文化与教育,这种“上帝的视角”早已被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实践证明是不存在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对本族或他族的文化与教育进行合理地识别与解释。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虽有民族性的差异,但不妨碍相互间的沟通,“文化之诸基本倾向,亦一切文化之所同者,各文化之不同,在于其畸重畸轻之不同,在于其以何种倾向为主导……一切文化莫不大同,所异只在偏重。东方文化之所有种种,在西方非无,不过不发达,不过只具萌芽。西方文化之有种种,在东方非无,亦不过不发达,或只具萌芽。”[6]即文化上的不同是由对不同要素的偏重所造成的,对不同要素构成的认识和改变,理论上是可行的,因而,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意味着文化间不可相互认识和理解。也就是说,对于比较教育学而言,对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的认识同样是可能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各自的文化传统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内对本民族和异族的文化中的教育现象进行分析,并在主客观统一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言说这些分析和认识。”[7]至于文化中的屏障所造成的“先见”和“误读”,解释学认为,人的理解就是在“先见”中的理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视界的融合,实际上,先见便构成了人们理解的基本文化背景,视界就是人们从先见出发所能理解到的范围,解释者从先见的视界出发,选择一定的文本进入自己的视界,解释的过程就是解释者的视界和文本的视界二者融合的过程,以此为基础,解释者又不断扩大自己的视界,形成新的“先见”。解释学理论为“先见”的合法性作了有力的解释。因此,所谓的“先见”对于比较教育学而言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恰恰是对其具有重要价值的言说背景。比较教育学正是比较教育学者以自身所在的场域中的历史文化作为言说背景,对异族历史文化中的教育进行识别和解释,比较教育研究的过程就是两种历史文化进行对话和交往的过程,因此,基于文化的视野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恰恰是比较教育学今后努力和发展的方向。
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交往?如何最大限度地跨越文化障碍,最大限度地提高认识的准确性?如何提升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文化安全?
在这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所谓文化规约的超越不可能是完全的、绝对的超越,那样就意味着我们重新回到了实证主义的旧巢,文化规约的超越只能是在承认教育学文化性和比较教育学的文化视野的前提下的有限超越。若不能有限地跨越文化障碍,或者让西方中心主义肆意横行,那么比较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比较教育学存在的价值就会丧失大半。这样的比较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他者和自我,基于这样比较的公共知识也很难达成。有限超越文化规约的一个首要前提在于意识到文化屏障和文化殖民的存在,而有限超越文化的根本途径不在于继续寻找所谓的“上帝的视角”,而在基于主体间性的哲学理念、以文化作为立足点和基本视野进行比较教育研究。主体间性一方面意味着交往双方都以主体的身份进入交往,保持交往双方的独立性、平等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意味着交往双方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意义的增值和生产,即主体间性的交往是交往双方主体平等介入的文化(意义)的生产性关系。巴赫金的对话哲学对我们理解如何在主体间性哲学理念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研究颇具启发,巴赫金提出交往中的外位性,“我所看到的、了解到的、掌握到的,总有一部分是超越任何他人的,这是由我在世界上唯一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决定的:因为此时此刻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唯有我一个人处于这一位置上,所有他人全在我的身外。”[8]交往双方超越于彼此的视野之外,从各自身上优先看到某一种东西,“我”具有与“他者”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独特的内涵。要理解他人的文化,只有将自己至于外位,才能深刻理解他人的文化,看到他者看不到的东西,在文化的对话和交往中,把别人对自己的理解和自己对别人的理解两者作创造性的理解,双方各自展示自己的文化的过程,是视域的互换与丰富对各自文化理解的过程,也是文化“增值”的过程,“它一方面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文化的交流中认识他人的文化和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以求共同的完善和发展,并结合传统的参与,在自我文化上形成新的素质,继续以新的面貌参与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9]因此,比较教育研究要有限地突破文化上的屏障,一方面要将自己置身于异族文化的外位,以自身的视域去理解异族文化传统中的教育;另一方面,必须将自身换位于异族文化情境,通过对异文化传统的深刻体察,使自己的“误读”最小化,同时也尝试以异文化的视野来审视本族文化中的教育,并将自己对他者的理解、他者对自己的理解、他者对他者的理解和自己换位为他者对自己的理解加以创造性地理解。比较教育研究者不断进行角色的转换,在自我与他者间出入,从而在主体间交往中,一方面不断达成对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教育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也不断形成对各民族教育的共识,这些理解与共识又构成新的相互理解的基础。这一过程便是比较教育学者不断超越文化屏障的过程。无论是对于比较教育学者跨越时间或空间上的文化障碍还是对于他们将教育的个人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这样的有限超越过程都是同样适用的。
而这一过程中如何有效地避免文化霸权的侵入呢?以西方的主体间性理论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是否意味着又在无意识中陷入西方文化殖民的旧巢?实际上,一方面,主体间性哲学理念倡导交往中主体的平等身份,本身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霸权的,平等、独立与完整是有效交往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中和”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也内在地包含了主体间性理念,这也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张岱年先生所说的“一切文化莫不大同”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可能。因此,关键在于比较教育学不必全然畏缩于主体间性可能带来的文化殖民祸害的忧虑或是“中和”可能造成的“民族中心主义”质疑,而应该在不断提升民族文化自觉的基础上,确实做到“不偏不倚”,确实地在东西两种话语体系间建立真正的意义联系,并锤炼自身的东西方话语的转换技术,从而合理地用西方话语表述中国教育事实和向中国表述别国教育事实;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比较教育学者应该真正致力于基于主体间性哲学理念的比较教育学话语秩序的建立,反对文化殖民,并在树立民族文化自觉的同时,共同致力于全球教育(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教育问题)的发展,正确处理教育的去殖民化和教育国际化二者的辩证关系,当然,这是以比较教育学者具有很强的东西方文化素养和东西方话语转换能力为前提的。这也是以文化作为立足点和基本视野的比较教育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世纪难题。
收稿日期:2009-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