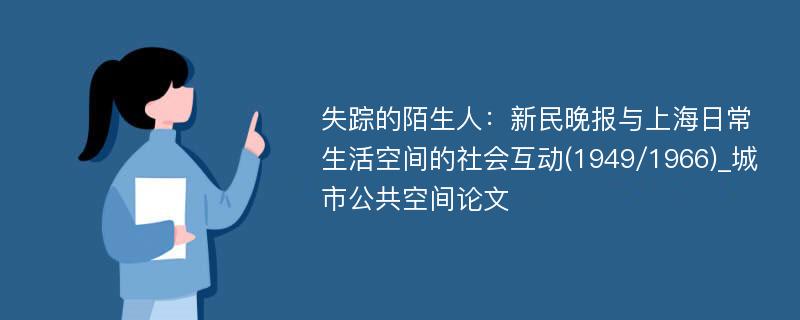
消失的陌生人:《新民晚报》与上海日常生活空间中的社会交往(1949~196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晚报论文,生活空间论文,上海论文,陌生人论文,日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是陌生人较为可能相遇的地方。①如果说乡村是熟人社会,那么城市便是陌生人社会。据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考证,“大都会”这个词是在18世纪的欧洲出现的。它意味着一个差异很大的陌生人交往的公共空间。②1949年前的上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其生活风格极其多元;上海解放后,伴随着新政权对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城市的生活条件改变,生活目标单一化,日常生活空间中的陌生人逐渐消失,社会交往方式发生巨变。本研究试图运用社会学中的“陌生人”视角来研究微观层面人们日常生活空间中社会交往的变化。 一、陌生人、城市、上海——另一种城市交往方式 陌生人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领域。从齐美尔发轫,经历了从陌生人到陌生人社会的研究转向。前者主要围绕陌生人的分类与整合,讨论陌生人-本地人情境,在边缘人和新来者两大传统中完成了整合。后者从讨论陌生人-陌生人情境下的互动策略起步,研究在陌生人的情境下如何对待陌生人的问题。③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齐美尔、桑内特和鲍曼关于城市陌生人和陌生人社会的论述,界定核心概念。 (一)城市中的“陌生人” “陌生人”概念首先由齐美尔提出,至今仍被广泛引用。齐美尔的陌生人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他是“脱离既定的地域空间的漫游者”,他或许会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范围中固定下来,但是,“他并非历来就属于它”。④他在物理距离上离我们很近,但在社会和文化距离上和我们很远,无法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齐美尔进一步阐释了作为社会距离概念的“陌生人”。在他的阐释中,“陌生人”是一种“同时包含着近和远的关系的方式”,“只要我们感到在陌生人和我们之间存在民族的或者社会的、职业的或者普遍人性的相同,陌生人对我们来说就是近的”;相反则是远的。⑤很明显,在齐美尔看来,这里的“陌生”,主要是指社会距离,而这种社会距离又有地域(国家、城市)的、职业的、行为规范的、思想的多个层面。都市人虽然彼此陌生,但是一旦有某些方面的相似,也就有了认同。远和近、陌生和熟悉都是相对的。 桑内特从欧美城市的形成过程出发,认为陌生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个地方的外来者,而且这个地方的人对他们自己的身份有相当的认识。比如纽约的其他国家、种族的移民。另一类情况下,陌生人不是一个外国人,而是一个未知的人,原籍、家庭背景、职业等常见的身份标签不明确,因此无法被“定位”。在第二类陌生人聚居的城市,必然有一个新的然而尚未成型的社会阶级形成,如18世纪的巴黎,新兴的阶级则是商业布尔乔亚。⑥ (二)城市交往与陌生人社会 城市聚集着陌生的人群,要求人群以新的方式互动。陌生人构成城市社会交往的基本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陌生人是城市的本质特征。在齐美尔看来,陌生是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的方式。陌生人是群体的一个要素,它也许“引起疏离”,产生叛逆,但是这些因素在这里反而“构成相互结合在一起和发挥相互作用的统一体”。⑦陌生人不是某一种特殊的人群,而成为社会交往和互动的方式,并且由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这种带有冲突性质的互动反而促成社会的整合。 桑内特将“陌生人”置于城市发展进程中考察,认为其构成城市公共领域的基本内涵:“公共”这个词不仅意味着一个处于家人和好友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还意味着这个由熟人和陌生人构成的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群相互之间差异比较大的人。⑧与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也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动力:由于陌生人的存在,城市里会出现一些使得人们的外表取信于陌生人的规则,一旦这些内容上具备连贯性的规则形成系统,一个公共领域便告形成。在这套共同系统的帮助下,人们能够自如地出入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合和陌生人群体。在此基础上,18世纪的人们发展出一些模式,用于在不确定交往对象个人背景的情况下过上一种有意义的公共生活。⑨城市经由陌生人的出现产生了公共生活的机制。同时,与陌生人相处的经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都市体验,人们能够轻松自如地应付体验的差异性,并从这种差异中吸取养分,这对个人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 鲍曼把陌生人和现代性联系起来。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他基本沿用了桑内特对陌生人的看法,同时补充:“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没有未来的事情”,是一个不合适的相遇。⑩不过,鲍曼认为,桑内特提出的“得体的”或者“值得信任的”行为需要一个“作为普遍的善、作为共同任务和作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而展现在它的居民面前的地方”,也就是一个让人们随心所欲、表现自我、表明内在感情的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空间。(11)而在当今的城市里,虽然存在着大量的被看做是“公共空间”的场所,但是它们大都背离了“文明空间”的理想类型。如大型的对人毫不友善的广场,只适合观看而不适合进入;再如大型购物中心,鼓励行动而非互动。 齐美尔提出了“陌生人”概念并将它贯穿到社会互动研究中。桑内特从西方城市形成的过程,鲍曼从后现代都市的实例对陌生人社会理论提出了发展和修正。可以说,陌生人是现代性的产物。在本文中,匿名性、异质性、流动性是陌生人的主要表征,不确定性是陌生人社会的主要特征,与陌生人的交往构成城市公共领域的基本内涵,与陌生人相处的心理过程构成独特的都市体验和都市主体,只有在相互成为陌生人时才能持续与完整。 (三)1949年前后的上海与陌生人 1949年前的上海,正是一个充满异质文化、异常多元的国际化大都会。从地域距离来看,近代上海人口多元;从文化距离来看,货币多元、教育多元、宗教多元,更别说语言、报刊、饮食、服饰的多元化了。熊月之认为,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12)上海处在两界(租界、华界)三方(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控制的缝隙,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13)在近代上海,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18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15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60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这个时期的上海同时囊括了桑内特所提到的两类陌生人:既有通过种族可辨认的陌生人,也有无法定位的“未知”的人,其异质程度极高。他们的生活目标和生活风格异常多元:既有明显的享乐主义氛围,也有浓郁的小资氛围,还有比较重视的职员氛围,也存在追求安定富足生活的小市民氛围。(14)他们之间有差异和冲突,更有认同和协作,这才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的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陌生人才具有了正面的意义。 1950年代是一个新旧交替、时空叠合的时代。在共产党政权之下,上海进入一个新的格局。1949年以前的上海繁华曾经是城市的骄傲,1949年以后这些特质成为上海的污点与政治包袱。社会主义的新政权为上海规划了新的正面图景:这个新上海是制造业中心,而不是商业和金融中心。(15)在毛泽东时代,上海对国家的发展贡献巨大。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9年,上海向中央上缴的财政收入超过了上海自身市政预算收入的13倍。上海多年来上缴的地方收入保证了中央收入的六分之一。(16)因此,上海具有双重性——政治上的复杂性和经济上的有效性。由于上海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即便上海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也不能成为领头的城市,因为这种角色要留给首都北京。(17)政治上的暧昧,信贷资金的不足,让上海不可能具备社会主义的大气派。(18)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社会主义上海的空间实践中,旧上海的实体景观在17年中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如原租界地区仍然是新上海政治、经济的中心,上海人的住房空间在1970年代末期仍然没有改善,除了工人新村之外,仅有几次城市空间发展计划(棚户区改造、建造卫星城等)最终也由于资金问题而无法完整地实施。 解放后的上海,实体景观没有实质变化,整个社会的氛围却大有不同:“艰苦朴素的风气逐渐形成。大商店的橱窗变得平淡无奇。身着西装的人一天天减少,而穿着中山装的人越来越多。最有抱负的上海人开始学习使用新的政治词汇,也掌握了‘干部’和‘人民大众’等词汇的含义。……虽然这还不是革命的清教主义的胜利,但至少令这座城市改变了颜色,披上了道德主义的面纱。”(19)由于上海日常生活空间的特殊性,在本文涉及日常生活空间的讨论中,必须区分实体空间与空间中的氛围。笔者提出一个概念“空间氛围”,用以指称上海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氛围变化。空间氛围区别于固定的建筑物,主要指实体空间中人的行为、语言以及并非紧紧附着于建筑物、但与建筑物有某种联系的物(比如商店的橱窗),这些人与物的出现或消失揭示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与空间、社会交往、权力规训构成有机联系。在本文中,上海日常生活空间中陌生人的消失很多情况下是指向这种空间氛围。 这种“空间氛围”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除了上述经济上对上海的管理和控制,新政权在社会生活上对城市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造。上海经历了驱赶外侨、遣送游民返乡、人员的内迁、建立户籍制度、重构基层组织等过程,新政权保证了城市秩序,人口的自由流动事实上被禁止,社会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状态;同时,新政权通过人性改造计划和思想革命化制度,(20)试图擦掉资本主义的过去,改变原先上海浓厚的殖民地生活氛围,把上海变成无产阶级的大本营。通过这些具有“反城市”色彩的举措,都市生活的条件逐渐消失,其生活目标也由多元变为统一,旧上海生活风格中的小资氛围和享乐主义氛围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批判和压制,小市民氛围被改造,而职员氛围被鼓励。(21)上海由异常丰富、复杂、多元的国际大都会转变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限制人的自由流动使社会学意义上的陌生人逐渐消失,而思想一统、行为一律以及生活风格的单一也使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异质性逐步减少,由此,上海城市社会交往方式发生巨变。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新政权控制社会流动的具体政策,而在于微观视角下人们日常生活空间中社会交往的变化,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而“陌生人”视角的研究基本都是从微观角度观察人际交往,因此,本研究运用这一视角来阐释、探究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文革“前十七年,新政权对上海城市、上海人思想改造的种种举措是如何渗透进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空间,改变着城市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客观上使得城市陌生人的存在条件渐渐消失的?透过《新民晚报》在这一时期的文本,我们或能发现一些线索。《新民晚报》是建国初期全国唯一的晚报,(22)它是当时上海人消磨闲暇时光最重要的市民报纸。《新民晚报》的人员构成、办报传统的历史传承带来了报纸的话语弹性,大量特色栏目致力于建构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导致了《新民晚报》与同时期其他上海报纸相较的特殊性。透过《新民晚报》对社会主义上海社会风气的转换的细枝末节和关键性细节的记录,我们可以发现“陌生人”是如何从上海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间中渐渐丧失立足之地的,发现城市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个人体验是如何发生巨变的。 二、公共空间 如前所述,在桑内特笔下,“陌生人”不仅构成城市公共领域的基本内涵,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形成也正是在陌生人的互动之中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城市的模式变得更适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正是在大都会兴起的时代,欧洲的城市开始兴建许多新型公共空间以促进陌生人的交往,如大型公园、马路上的人行道等等。已有的一些城市设施如戏院、歌剧院等,开始公开售票以广纳观众,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将座位分配给赞助演出的贵族。咖啡馆、客栈成为社交的中心。(23)陌生人与城市的公共空间是相互造就的关系。 (一)组织起来的街头 在麦奎尔关于街道的分析中,虽然在由桑内特、伯曼和本雅明提出的公共空间分析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这3位作者都感到了公共文化的重要性。(24)在公共文化中,人们作为能够理解进而改变其自身社会境遇的积极当事者进行互动。其中,街道构成了特别具有现代意识格局的重要剧场。伯曼认为,街道构成了19世纪城市的“普通的会面地点和交流路线”,(25)不同阶层的人群在此相遇。本雅明则在其著名的“拱廊街计划”的研究中提出,巴黎有拱廊的街道的一个特征,是行人可以在不与车辆交通竞争的情况下随意漫步,并赋予波德莱尔诗歌中“游手好闲的人”以正面意义。但是,驯服拥挤、混乱、无序的街道成为20世纪后半叶现代派建筑思想的支柱,(26)在主要为速度和流通而设计的街道上,“游手好闲的人”的闲逛艺术已经毫无立足之地。由于私家车的普及,街道的社会功能和循环功能在现代社会无疑是分离的。 《新民晚报》自上海版1946年创刊初期,就有柯灵主编的专刊《十字街头》。这一时期的《新民晚报》颇多以左翼视角描摹街头众生相的报道,关于街头文人、拳术家、街头图书馆、烟摊等等的报道。(27)这时的上海街头还是多元而富有活力的。解放后,《新民晚报》延续了注重街头百态报道的传统,除了专门报道,并有栏目《上海点滴》,大量反映城市街头细微变化的细节见诸报端。当然,更多的报道是关于政府如何动员、组织街头环境及街头的人。1950年1月,《新民晚报》刊登了题为《把政治推向街头》的上下篇评论,为社会主义的上海街景赋予了政治属性,也为共产党对街道的“规训”定了基调。(28) 1949年后,街道的面貌有了巨大改变。在街道的实体形态上,表现在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开展的政治主题展览:1951年5月,新成区石门一路工商界,为配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主义的宣传,特联合“抗美援朝街道展览会”,在石门一路的南京西路口及威海卫路口,搭建电灯五彩牌楼两座,马路两边满布小型旗座,旗座上写有标语,入晚大放光明。(29)1952年6月,南京西路人民广场对面,有一块黑板报,是附近店员办的。27日登了一篇稿子,题目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九大类型》,许多过路人看了,都拿出日记簿抄录下来,一直到天黑以后,还有人在抄。该黑板报的负责同志接受读者要求,特地从店里接了一盏电灯出来,以便读者抄录。(30)这可算是“国家主流政治符号走向民间”的“学习”风潮的表现。 在街道上的行动者——人的方面,《新民晚报》呈现了政府对街头艺人改造的过程。在1949年前的上海街头上,特别是西藏南路中法学堂门前一带,经常可以看到一堆一堆人围着看街头游艺者——唱滑稽的、说书的、打拳的表演。他们的票价卖得极低,棚户居民花上五分钱,也可以消磨一晚,听听古往今来的故事。但是,《新民晚报》认为:“这些街头游艺者所表演的,全是一些陈旧的、封建的东西,这对于人民大众,是没有丝毫好处的。然而,这些街头游艺者,是有天才的,他们也有着广大的观众,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能向正确的路线去学习,使他们变成教育人民的宣传家,不是好的多么?”(31)其后,文艺处召集本市街头艺人在大世界共和厅开第一次座谈会。(32)接着,街头艺人唱起了新歌:路过八仙桥,……只见有三个男人,一个女小孩,他们几个人都化了妆,正用流利的调头唱着《保卫世界和平》、《重见光明》等歌曲;两个卖梨膏糖的在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接着又唱了《解放歌》、《和平曲》、《四大欢喜歌》,他们说:“我们现在唱的新歌曲,都是我们自己编的,将来编的多了,我们都要不唱旧的歌了。”(33)除了编唱新歌曲,他们还举行救灾游园会,唱快板宣传抗美援朝。(34)到了1956年,政府开始对街头艺人实施正式登记制度。在上海街头献艺的三十多个民间职业演唱团体,分别领到了市文化局所发给的登记证或临时演出证,分别由所属各区人民委员会管理;单档(一般指一个人演出的戏)的街头艺人也发了证。(35)至此,政府彻底将街头艺人纳入管辖。 除了街头艺人,著名演员及大量戏剧、音乐、曲艺工作者也在节日和有宣传任务的时候走向街头,(36)“从外滩到沪西,一条条主要街道上,到处都是文艺工作者组织的宣传队在向市民群众宣传总路线,……他们打着红旗、红色标语,吹吹打打,穿梭往来,每到了一处可以演出的地方停留下来时,他们的四周的群众立刻汇成一片海洋。”(37) 1949年后的上海街道虽然同样受到了规训,但与现代西方的街道不同,这种规训力量并非来自商业(38)与技术。街道的循环功能和社会功能,让位于政治宣传。街道变成了政治主题展览的空间,街头艺人变成了“教育人民的宣传家”,街道上人们的流动方式被改变了,由不确定转为确定;这时候的上海街头,似乎已没有供“游手好闲者”漫步的空间。政府对街道的规训从街道的空间氛围开始,经由对空间中主体的改造,改变了人在空间中的流动方式。 (二)公园里应该吹什么风? 公园通常被看做是“都市之肺”,一个为城市改善自然环境的空间;公园也是为市民提供公共交往的空间。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说者之角,允许人们自由发表演说,表达自己的主张。而在近代上海,作为市民各界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的张园,更是陌生人相遇的地方。在张园,可以赏花、看戏、评妓、照相、宴客、吃茶、纳凉、集会、展览、购物……张园之名,日日见诸报端;张园之事,人人喜闻乐见。(39)这个“不分民族、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区域的公共活动场所”,(40)是脱离了熟人(包括家人与同事)的自由空间。 解放后的上海公园,增加了面积和数量,“都市之肺”的休闲功能在延续。然而,作为交往空间的公园,却发生了变化。《新民晚报》认为:“人民的公园不单是给人民游憩的地方,同时还是市民们学习文化的场所”,(41)强调公园的政治功能。也就是说,在《新民晚报》的话语中,除了日常的风景游览,只有“学习”这样一种社会交往的形式才具有合法性。 1964年12月,《新民晚报》刊登了题为“公园里应该吹什么风?——园林职工来信批评一些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人民公园的工作人员来信,揭开了一场大讨论的序幕。来信中说,“在人民公园,有些人不是认真锻炼,‘活推手’的‘拳术’,大多数是男女对打,这种拳除了手的姿态以外,它的步法完全和解放前跳舞厅里跳舞一样,嘻嘻哈哈,怪模怪样;同时他们还散布资产阶级的吃喝玩乐思想。一见面就称呼‘某先生’、‘某太太’。接着便大谈:昨天我上某菜馆吃了什么,味道好;那一家菜馆比另一家菜馆小菜烧得入味;一见面都是谈论吃吃喝喝,非常起劲”。茶室内,“有些人边喝茶边谈什么地方好玩,肉骨头如何烧才好吃等等。也脱离不了吃喝玩乐,很少谈些正当问题”。凉亭里,“有的人利用这个地方,谈论和散布反动封建迷信”。当公园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可是他们竟说这是他们的自由,说我们未免管得太宽了”。(42) 此文刊登后,引起巨大反响。从12月17日起的一月间,“公园里应吹什么风?”的讨论成为《新民晚报》的常设栏目。在1964年底的报道中,《新民晚报》通过报道公园中出现的新风气,如老工人读报讲革命故事、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爱护公物等,来树立公园的新的形象和作用,以引导讨论。(43)这场讨论深入展开,并逐步扩大到茶馆、饮食店、浴室等公共场所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甚至引起了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注意,《解放日报》特地为此讨论发表编者按语:“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解放前长期是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的‘乐园’;解放十五年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某些角落里,资本主义的遗毒犹存,还在散发出它的毒气。公园等公共场所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争夺的重要阵地之一。”(44)这是对日常生活空间中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氛围”的批判和对讲究精细生活的小市民氛围的压制,以及对“无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宣扬,城市的生活风格趋向单一。 讨论继续进行,这时“资产阶级风气”在舆论上已经完全没有生存空间,群众来信聚焦在建议如何改进公园设施,以进一步创造社会主义公园的新风:“讲讲园史,有助于阶级教育;增加些宣传形式的画和标语;儿童乐园也要改造;主动和有关部门联系、有组织教拳、播送革命音乐。”还有观众提出“凳子和灯光也都值得注意:灯光过分柔弱,显得暗了些;每条凳子的座位可以多些,不要都是两个人坐的;不要设置在篱笆角落的地方和偏僻的树荫下”。(45) 1965年5月,本次讨论结束四个月后,《新民晚报》又刊载了人民公园服务组全体职工给报社的信,信中表示,自讨论后,公园的各项健康活动越来越多,读者给予他们有力的鼓舞,宝贵的意见;他们按群众意见调整公园布局、增阅览室、组织读报、加强服务,并组织多样活动。(46)后续报道也涉及许多公园改进设施、增添活动的情况,算是对讨论效果的检验:“部分公园为游人讲园史、不断改善园容、调整绿化布局、组织多种活动、文娱活动室也将进一步改进。”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公园改变设备的举措:“各公园对原设在偏僻冷角的圆椅,已搬迁到游人比较集中的地点。虹口、淮海等公园已调整和加强了照明设备。”(47)这表明在这一点上,读者的建议通过媒介的力量直接参与了空间实践。而这样的举措——对座椅和照明的调整——改变了公园的空间布局,消灭了公园中的私密角落,也改变了人们游览公园的方式。公园再也不能容陌生人随意游荡、谈笑了,即使谈论的内容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甚至值得提倡的对精致生活的追求。这场对公园空间的改造由市民的自我规训开始,引起了官方意识形态力量的注意和赞同,扩大舆论并持续发酵,结果是公园的空间氛围的改变。在行为、言语规范层面的陌生人消失,空间中的异质性被取消,陌生感荡然无存。作为公共空间的公园逐步退场,而以政治宣传和改善环境为目标的公园空间依然存续。 (三)书场:从自由散漫到井然有序 评弹作为一个剧种,在解放前后的上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书场,是弹唱评弹的场所,也是戏院的一种。大都会的戏院,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只是提供文化艺术活动的场所,更建构了一种城市的社会交往方式。听戏看电影,至今仍然是城市人最为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在桑内特笔下的巴黎,戏院里展开的陌生人之间的公共交往,构筑了城市中重要的公共领域,越来越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中心。(48)解放后对书场的规训,使得陌生人存在的空间更加逼仄了。 书场大多是在下午一时或一时半就“开书”的(有几家还特设了“早场”),而散场却多在五时左右。《新民晚报》在1950年提出:“我们不反对市民们在其工余之暇‘听书’来娱乐自己;可是,当我们发现这里竟有许多人会得如此有闲的把它们在一天之内的最好的工作时间‘杀戮’在书场里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感到如此浪费的可惜,可惊和可耻呢?”(49)到了1954年,同样的话题却有了不同的结果:这时的书场里,星期日或其他节假日的营业,已经大大地超过一般的日子。“可举大沪书场的日场为例:每天都是那几档节目,但在平时经常卖座五成以下,甚至于有时只有一两百客;而星期日却能卖座九成以上”。(50)很明显,天天上班的人多了,大家都进了“单位”,“游手好闲者”自然减少,以至于大多数人除了假日以外无暇抽出下午时间来听书。书场中的“陌生人”从绝对数量上减少了。 1954年2月,上海市政府发布通知,改进与加强对本市娱乐场所如私营剧场、游乐场及书场的管理,市文化事业管理局开始办理登记手续。(51)仍旧自由散漫的书场空间,也要开始整顿了。解放前,“在书台的上面,是一顶布幔,上面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画着和写着一种雪花膏的广告;在台后面,演员座位的上方是一排耀眼的霓虹灯,做的是某种牌子的香烟广告。”(52)除此,在评弹书场里,一直有着这样一种习惯,听众们进出书场是非常自由的。“作为评弹的演出场所的书场,一般总是非常嘈杂散漫和凌乱。在演员们正在认真说唱的时候,托着各种小吃甚至热气腾腾的点心的小贩,经常在听众身旁穿来穿去……还有卖书场节目单和说明书的,也夹杂在内;有时,忽然在书场里出现了一块黑色的木板,上面写着哪一位听客的大名,高高举起……”(53)1955年,人民评弹工作团决定在演出中篇评弹“王孝和”的静园书场(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书场),开始重点推行“幕间入场制”。(54)这是评弹团学习话剧的经验,接受了听众代表的意见,征得书场的赞同后,为了改善书场秩序而进行的一项新措施。实行新制度的第一天,“在开书以后,从头到尾,都保持着静谧的空气,使场子里不再受到任何困扰,演出者能够聚精会神的说唱,获得了最好的效果。”(55)一个月后的读者来信中提到,“场子里不再出售瓜子之类的硬壳果物。在开书以前,场内的播音员一再要求听众不要吃有声音的食物……在说唱最后的一回书以前,播音员还婉言要求听众不要在演唱未完毕时提前离座”,“我觉得我最大限度地欣赏了它的艺术,也接受了它的教育”。(56) 桑内特认为,表演若要获得成功,必须有一群陌生的观众;但表演在亲近的人中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57)1949年后的上海,原本自由、散漫、流动的书场空间经由评弹团的自我规训,其氛围变得凝固、静止。空间中的主体——观众听书时各种自发的社会交往被禁止,无法自由穿行,正襟危坐成为听书的规定动作。对书场中的观众来说,此处在行为规范层面的陌生被消灭了。同时,由于缺乏陌生身体之间的凝视与互动,作为城市公共领域的书场空间发生了变形。原本,观众作为公共交往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演员;但是由于“公共场所越是遭到社会环境的侵蚀,人们就越少有地方可用来操练这种表演的能力”,(58)观众逐渐成为“没有演技的演员”,旁观取代了参与。规训中的书场空间失落了公共领域的基本条件。 三、居住空间 居住空间是典型的私人空间。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原本应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是个人权利的集中体现。私人空间和社会交往并非无关,这不但体现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也决定了个人自由空间的尺度,因此也和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交往直接相关,更是在抽象意义上成为塑造个体性的重要因素。1949年后,政治权力不仅改变着公共空间,而且渗透进家庭、里弄这样的私人领域。如前述的上下篇评论《把政治推向街头》,不仅为社会主义的上海街景赋予了政治属性,也为私人空间的“规训”定了基调。文中提出:“不仅要把政治推向街头,还要转进里弄,深入家庭,希望无分东南西北,人不问男女老少,都能够谈谈政治,坐言起行。”(59) (一)节约之家:消灭个人独立空间 “节约”是新政权倡导的一种主要生活氛围。有一些报道(主要表现为读者来信的形式,出现在“新家庭”栏目中)直接涉及到为了节约而改变家庭成员交往关系和个人休闲方式的问题。节约既已被新政权抹去为“小我”的合法性而成为公共议题,而作为公共议题的节约又深入到人们的私人空间。一位读者谈到,他们的家庭为了省电开了节约会议:过去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各自为政”。“晚餐过后,是我例有的读书写稿时间,大家为了好使我安心,总让我一个人躲在房里读和写。弟弟和妹妹最不合作,一个要做算数,一个偏偏要读国文,为免得争吵,总是分开在两个极端(那就是说各人要点一盏灯)。剩下来的一个小间,由母亲和妻分享。至于王妈呢,她工余在厨房里,不是扎鞋底就是缝衣服,也一个人点着一只灯。”这样各行其是,互不干扰的局面在这位读者看来,是一种浪费,应该改变。家庭会议达成了一些节约的共识:“关于电灯,大家议决以最多同时点用二只灯为原则,无论如何不超过三只。弟弟做算学可和我写作一起,妹妹保证不同时朗诵国文,故亦可参加我们一起;王妈做完工作,若要做针线,也可搬只凳子坐在我们旁边。”(60)叶文心认为,物质的使用,把上海建构成一种新的空间,会改变人们在其中交互往来的机会与方式。(61)可以想见,如果这次家庭会议的决议付诸实行,由于电灯数量的变更,原来所存在的家庭晚间生活格局就起了变化,个人空间没有了,独处的条件消失了,一个家庭成员不同以往的交往空间因此得以构成。即便是在家庭中,个人的独处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使人们形成独立性和差异性,这构成了个体与陌生人交往的心理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才会成为女性主义的名言。家庭中减少电灯使用的“节约”举措作为市民的自我规训,并未影响家庭空间的实体格局,却改变了家庭的日常交往关系,也改变了家庭中每个人独立的心性。 (二)里弄中的学习 1949年之前,上海人并没有形成以“里弄”或者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社区”为基础的认同概念。(62)人们养成了一盘散沙的散漫习惯,甚至于一幢房子里住了五六家住户,彼此连招呼都不打,谁家是哪一种情况,更互不了解。因此,组织一个由几百个或几千个生张熟魏结合在一起的里弄,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从共产党接管上海起,新政权就开始建立有效的城镇居民管理制度。解放初期的主要里弄组织——冬防队使用夜锁弄堂铁门、站岗、夜归登记等手段,限制这个城市中人口的自由流动和陌生人存在的可能性。城市的本性本来是在于流动,就像雅各布斯说的,要想在城市的街道和地区生发丰富的多样性,必须要确保人流的存在,不管是按照不同的日程出门的人,还是因不同的目的来到此地的人。(63)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虽然使里弄的管理和安全得到了保障,但也限制了城市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很快,冬防服务队改组为居民委员会。到1951年底,短短的两年多中,由一盘散沙的三百多万无组织的群众,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组织起来了。(64)《新民晚报》无疑忠实地反映了这一过程,并且本身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设置相关的栏目(如“里弄事件”),花费大量的篇幅对里弄组织的重要性、形成过程、阶段进行描述和总结,捕捉相关细节;而且设置读报栏目,组织读报活动,解释相关政策。 “学习”是1949年后另一个重要的上海生活氛围。人们面对新政权的好奇和不解,在日复一日由单位和各种里弄组织发起的配合建国初频繁的各项政治运动、学习活动中得到答案。根据《新民晚报》中大量的里弄组织和各个家庭订立爱国公约的报道,里弄学习分为学习小组、识字班和读报组等多种形式,由于当时和苏联的联系紧密,还有居民报名学习俄语。(65)学习目的是吸取新思想和新知识,属于精神生活,但也不难看出,学习这种组织方式,给市民的交往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由于学习小组轮流在各家举行,无意中在做着每个家庭的访问,使全里弄的各户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个人”在小组中不再有重要地位。另外,由于各种学习班大都安排在晚上,也改变了里弄居民们的休闲方式。解放前,上海人的夜生活非常丰富,晚上是“消费”的时间,“有的喜跑茶室咖啡馆,有的往观影剧或听滑稽弹唱,有的还要逛跳舞场,更有参与家庭中秘密性的赌博”,《新民晚报》这样评论道:“无一不消费金钱,浪费精神和时间。现在,大家有了正经的事干,埋头阅读,侧耳聆听报告,热烈发挥意见,真正做到了‘精简节约’”。(66) 集体学习没有影响里弄的实体空间,却改变了人们晚间的社会交往,邻居们聚在一起学习,便无法到咖啡馆、电影院、跳舞厅遇见陌生人。因此,集体学习,与其说是一种学习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集体的仪式,这个仪式旨在限制空间中人们的自由流动,把一个里弄里的居民由陌生人转变为精神、外表双重意义的熟人和有同样目标、行动的“一致的人”。这种自上而下、细致入微的规训不仅造成了高度组织化的社区,而且也是对人性和思想的改造,对上海基数巨大、素来自由散漫的里弄居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报纸用人们喜爱的文艺小调描述和表达这种变化: (用“五更调”的调子来唱)空仔下来没事情,读报真开心!咿呀呀得儿喂,日日有新闻。一个人读报大家听,讲得清!有头有尾,越听越起劲;咿呀呀得儿喂,好过山海经。 读报小组方法强,辰光弗嫌长,咿呀呀得儿喂,弗会没心相;有说有笑有讲张,好白相!小组里向,大家好商量,咿呀呀得儿喂,自家人样。(67) (三)工人新村与集体生活 共产党进入上海以后,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数量,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生产型城市”,再加上“低工资高就业”的经济政策,上海工人数连年迅猛增长。(68)工人地位提高的同时,城市工人家庭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100万的产业工人(连同家属约300万人)住在条件简陋的棚户、厂房和旧式里弄,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方米,(69)恶劣的居住环境严重影响了工人的生活与社会主义生产。 伴随着数量上增长的是工人阶级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前所未有的提升,“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上海”城市改造的诉求:意识形态的考虑(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改变殖民化城市的面貌、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同时也关系到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因为“工人新村”一方面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形态的变化以及“生产型”城市功能的发挥,需要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和投入。(70) 因此,缓解住房压力只是1950年代建造工人住宅的目的之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新政权必须通过实际行动——为工人建新村——来履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依靠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政治承诺。 1952年6月25日,陆阿狗、杨富珍、裔式娟等百名首批140户“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告别了阁楼和草棚,欢天喜地地入迁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可以说,解放后三十年间,这种“为工人阶级建造的住房”,亦即当时人们熟知并向往的工人新村,是社会主义时期上海为数不多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空间拓展。(71)以工厂为核心,以提供无所不包的社会职能的单位聚合而成的单位空间,成为建国以后中国城市的主导性新景观。(72) 有学者认为,工人新村是标准化的单元设计,过去由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房地产开发方式逐渐转变为以国家计划为导向的标准化住宅设计。(73)为了降低造价,不断减小的私人住房空间和相对增多的公共设施促进了一种“日常生活集体化”的趋势。(74)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网点系统性的组织,把新村工人日常生活安排在一个以居住区或小区为单元的集体化生活的网络之中。睡觉之外的其他生活需求几乎都要借助于公共空间,包括每天必需的日常活动如洗澡、吃饭、上厕所。而合作社、卫生所、银行、邮局、文化馆、运动场和电影院设施一应俱全。居民统一在食堂用餐,各户的拆缝补洗由集体劳动完成,家庭妇女被组织参加街道工业,幼托和照顾老人的工作也由街道统一组织。这不仅是房子式样和建筑格局的标准化,同时也促进了“日常生活方式集体化”。 “新村”不仅仅是一种居住模式,而且包含着一种新生活的实验和确立,“村民”们将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逐渐适应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新方式、新场景、新习惯和新秩序。反映在《新民晚报》上,报纸文本的主调是充满了对宽敞、整洁、卫生、有序的新村生活的赞美以及新旧对比,至于其他方面,像后来人们所讨论的,诸如建造材料和建造技术方面的“低标准”,住房面积的狭小,以及因此时常引发的家庭矛盾,厨卫合用带来的邻里纠纷,甚至工人新村标准化的审美和单调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消了工人生活和城市的多元化等等,当然不可能在当时的这份“市民报”上出现。 “工人新村”这个名词本身指明了在这样的居住空间,居住主体职业上的单一性;而单位制所带来的集体化的新村生活更将这种同质化不断加强,推向极致。在邻里关系密切程度大大强化的同时,个人的私密性几乎不复存在,而城市生活的快乐之一就是维持匿名性的可能。(75)一个人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熟人们的目光下:家里来了访客、孩子交了新朋友,甚至今天吃了什么菜、穿什么衣服出门,都在众多熟人的眼皮底下。新建起来的工人新村天生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基因,在实体空间上从无到有,区别于其他的日常生活空间;空间中行动者在职业、文化、思想上的同质性前所未有的高,其交往方式也基本是固定、确定、公开的,一个陌生人完全缺席的空间被建构起来了,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讨论与结论 (一)日常生活的革命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一场革命,如果没有产生出新的空间,那么它就没有释放其全部的潜能;如果只是改变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而没有改变生活的话,它也是失败的。真正的社会变革,必定会在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中体现出它所具有创造力的影响。”(76)19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场从空间到思想、生活的革命。如前所述,上海没有能力完全除旧布新,除了工人新村这个新上海最具实质意义的空间扩展。在这个面貌几乎没变的城市里,不仅产生了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而且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这种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渗透进上海的日常生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在前文中,关于“公园里应该吹什么风”的讨论首先由园林职工的来信发起,是为了“批评一些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在后续讨论中建议“改变公园的布局和灯光”也是出自群众来信;书场中的“幕间入场制”是评弹团接受了听众代表的意见而进行的一项新措施;家庭中关于“减少电灯数量”的讨论也是来自读者来信。这样的例子在《新民晚报》上比比皆是。新政权试图系统性地改造城市的自然秩序,建成社会主义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改造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过程;在本文中,市民不仅接受了新政权的规训,而且将其内化为思维方式,在政策不能或者尚未到达的微观领域改变着实体空间或空间氛围。 (二)作为社会距离的陌生 有学者认为,城市的能量大部分来自对外部的开放性,来自抵达且加入了混合体,并可能参与创造新文化的新移民。(77)1949年后,新政权通过驱逐外侨、遣送游民、建立户籍制度等形式,限制了城市与国家间的流动,因此本文讨论的“陌生人”并非这种外部的开放性所带来的新移民(即桑内特所说的一望而知的“外来者”)。 齐美尔认为陌生人有“对国家陌生的人、对城市陌生的人、对种族陌生的人”等等的情况,(78)又有地域的、职业的、思想的等多个层面。本文中的“陌生”,主要是指社会距离;远和近、熟悉和陌生都是相对的,社会与文化上的异质也可理解为陌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场里捧角的、跑来跑去的跑堂的,公园里散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们,里弄中身份不明的流动人员,虽然不是地域意义上的“外来者”,却都是那个时期,国家政权意义上的陌生人,而他们是不是城市的陌生人呢?也许对于上海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此处的陌生在于揭示,相对于解放前的多元文化,是熟悉的;而对于解放后的强调计划、一律、集体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陌生的。1949年之后,共产党对上海城市在社会、思想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造,造成社会交往方式与社会主体人格思想的高度同质化,使最关键的思想上的社会距离无限缩短;虽然在整个社会范围看,还存在其他层面的(如地域、职业)陌生人,但在本文所讨论的几个日常生活空间,陌生人存在的条件基本消失。这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交往方式,重塑了都市主体及其人格、体验,重构了城市中的社会关系。作为城市基础的日常生活方式被改变,城市原有的面貌和精神气质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同时,这种同质化规训减少了城市的有机环节,以及由适度的紧张关系所激发的自发的公共生活以及由此而来的城市活力和能量,造成原有公共空间(公园,剧场)的变形,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的消失。 (三)都市主体及其体验与人格 现代城市的典型体验是生活在始终是陌生人的陌生人中。与陌生人相处的经验对个人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人们能够轻松自如地应付体验的差异性,并从这种差异中吸取养分。1949年后的上海强调一律、禁止流动,这与桑内特所说的19世纪西方大城市中的“亲密性的专制统治”形成的原因和内在动力(79)虽然不同,其后果却是一样的:这会令人们的心理体验趋向贫乏,并且缺乏想象力,因为缺乏陌生人与他者性的刺激。桑内特呼唤的是都市性的精髓:人们无需拥有成为相同人物的冲动也能够共同行动。(80)桑内特更将城市中陌生人的公共生活上升至文明的高度,借此表达他对都市公共生活的理想化期待。他认为,文明就是以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对待他人,保护人们免遭他人骚扰,然而又使人们能够享受彼此的相伴。陌生人了无踪迹的上海,无疑和桑内特意义上的“文明”背道而驰,是另一种“再部落化”。人们无法再从体验的差异性中获取养分,只能过一种静止、安全但贫乏的生活。 (四)上海陌生人的过去与未来 如果将上海看做文本,《新民晚报》无疑提供了揭示“文革”前十七年的上海与民国上海、1992年后上海之间内在联系的密码。1990年代,中央决定把改革重心从广东向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转移,上海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得以重新确认,成为改革开放的龙头;上海成为新的金融中心,经济产业结构实现重组,1992年浦东的开发战略更是为上海的腾飞插上了翅膀。在当时,即使借助了国家层面的巨大行政力量,陌生人在上海从来没有彻底消失。上海城市的文化脉络,潜伏于日常生活的边缘绵延不绝,时隐时现。直至国门重新敞开,上海重返世界舞台,开始迎来五湖四海乃至海外的陌生人,关于“新上海人”的新闻不时出现在《新民晚报》的头版。这个城市重新接纳、改变了大量的“陌生人”,“陌生人”也使这座城市重新焕发出活力。 ①[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②[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③张杰:《“陌生人”视角下社会化媒体与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研究》,《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1期,第34-40页。 ④[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1-342页。 ⑤[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5-346页。 ⑥[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58-59页。 ⑦[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1-342页。 ⑧[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⑨[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⑩[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147-148页。 (1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12)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13)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14)许纪霖、罗岗等:《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05-206页。 (15)在解放军进入城市的第二天,1949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便发表社论《解放大上海的经济意义》,奠定了新上海建设的基调。在这篇社论中,上海被描绘成“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使我们国家殖民地化的一个最大侵略基地”和“全面绞杀中国老百姓的总枢纽”,而“它将变成一个人民的工业大都市,对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它将依据自力更生的原则,尽其最大的贡献”。 (16)Ho Lok-sang,Tsui Kai-yuen,Fiscal Relations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in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China's Open Door Policy,by Yeung,Sung,Shangha 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6,p.154。 (17)[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19页。 (18)[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19页。 (19)[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02页。 (20)在王宁的论述中,1949年后,为了配合社会结构的变革,国家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结构的变革,以配合国家做出的各种制度安排。其实质在于将国家的目标看做检验个人的动机、观念和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道德标准,是一种促使全国人民思想一统、行为一律的机制。见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6-127页。 (21)许纪霖、罗岗等:《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09-229页。 (22)《北京晚报》于1958年创刊。 (23)[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24)[德]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92-193页。 (25)[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张辑、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6页。 (26)[澳]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94页。 (27)《街头文人》,《新民报(晚刊)》1947年8月5日第2版。《街头拳术家》,《新民报(晚刊)》1947年8月12日第2版。《街头图书馆及其顾客》,《新民报(晚刊)》1947年8月12日第4版。《略谈街头买卖》,《新民报(晚刊)》1947年8月15日第2版。《街头的烟摊》,《新民报(晚刊)》1948年4月10日第3版。 (28)董倩:《规训与溢出:〈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商业空间和商业文化建构(1949-1966)》,《新闻大学》2013年第5期,第1-14页。 (29)《石门一路工商界举办 抗美援朝街道展览》,《新民报(晚刊)》1951年5月4日第4版。 (30)《街头学习热潮》,《新民报(晚刊)》1952年6月29日第4版。 (31)《街头卖艺者》,《新民报(晚刊)》1949年7月20日第3版。 (32)《街头艺人组织起来 今晨在大世界座谈》,《新民报(晚刊)》1949年9月28日第2版。 (33)《街头艺人唱新歌》,《新民报(晚刊)》1949年10月14日第2版。 (34)《街头艺人 举行救灾游园会》,《新民报(晚刊)》1950年4月3日第2版。《宣传抗美援朝 街头艺人唱快板》,《新民报(晚刊)》1950年11月22日第2版。 (35)《五剧种组报喜队向街头艺人道贺 街头演唱团体领到登记证》,《新民报(晚刊)》1957年2月26日第2版。 (36)《文艺大军 三路出动 著名演员街头宣传“除七害”》,《新民报(晚刊)》1958年1月23日第2版。《街头也能产生不朽之作》,《新民报(晚刊)》1958年6月17日第5版。《街头的教育》,《新民晚报》1959年3月3日第6版。《节日的“街头舞台”》,《新民晚报》1963年10月3日第2版。 (37)《千军万马宣传总路线 上海街头百花盛开》,《新民报(晚刊)》1958年6月4日第1版。 (38)虽然在解放初期,仍有相当数量的街头商业散落其间,但历经数次取缔、整顿,已经逐渐失去生存空间。 (39)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410页。 (40)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410页。 (41)《特写:在人民公园里》,《新民报(晚刊)》1952年12月27日第4版。 (42)《公园里应该吹什么风?——园林职工来信批评一些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新民晚报》1964年12月15日第1版。 (43)《许多好游客争为公园做好事:请看此新风气 羞煞那旧思想——老工人读报讲革命故事向年轻人进行阶级教育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爱护公物的人越来越多》,《新民晚报》1964年12月30日第4版。 (44)《解放日报》就本报《公园里应吹什么风?》的讨论发表编者按语:坚决扫清公共场所的歪风邪气——希望广大读者继续来信参加这场兴无灭资移风易俗的斗争,《新民晚报》1965年1月10日第4版。 (45)《人民群众爱护自己的公园——广大读者热情向公园提出积极建议,横扫歪风,进一步创造社会主义公园的新风》,《新民晚报》1965年1月22日第1版。 (46)《社会主义新风洋溢 健康活动丰富多彩:人民公园面貌更新游人更多》,《新民晚报》1965年5月22日第4版。 (47)《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许多公园改进设施增添活动》,《新民晚报》1965年5月22日第4版。 (48)[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97-98页。 (49)《杀戮在书场里的时间》,《新民报(晚刊)》1950年10月11日第2版。 (50)《从书场听众看一个问题》,《新民报(晚刊)》1954年6月6日第3版。 (51)《改进与加强对本市私营剧场、游乐场及书场的管理:市文化事业管理局召集有关方面开会——自今日起分区办理登记手续》,《新民报(晚刊)》1954年2月19日第1版。 (52)《谈书场的秩序和布置》,《新民报(晚刊)》1955年3月26日第3版。 (53)《谈书场的秩序和布置》,《新民报(晚刊)》1955年3月26日第3版。 (54)《欢迎在书场推行“幕(回)间入场制”》,《新民报(晚刊)》1955年2月19日第2版。 (55)《静园书场实行新制度的第一天》,《新民报(晚刊)》1955年2月25日第2版。 (56)《书场新气象》,《新民报(晚刊)》1955年3月23日第4版。 (57)[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58)[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59)《把政治推向街头(下)》,《新民报(晚刊)》1950年1月11日第2版。 (60)《我的家庭里的节约故事》,《新民报(晚刊)》1952年1月6日第3版。 (61)叶文心:《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王琴、刘润堂译,台北:时报文化,2010年,第14页。 (62)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01页。 (63)[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65-166页。 (64)《全市百分之八十以上里弄居民有了组织》,《新民报(晚刊)》1951年12月17日第3版。 (65)《光复西路里弄居民 集体报名学习俄语》,《新民报(晚刊)》1952年6月17日第4版。 (66)《里弄学习小组成立后的副收获》,《新民报(晚刊)》1949年11月4日第2版。 (67)《读报小组》,《新民报(晚刊)》1952年5月24日第4版。 (68)杨辰:《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上海工人新村(1949-1978)》,《人文地理》2011年第3期,第35-40、64页。 (69)杨辰:《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上海工人新村(1949-1978)》,《人文地理》2011年第3期,第35-40、64页。 (70)罗岗:《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上海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第91-96页。 (71)杨辰:《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上海工人新村(1949-1978)》,《人文地理》2011年第3期,第35-40、64页。 (72)于海、邹华华:《上海的空间故事: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绿叶》2009年第9期,第85页。 (73)杨辰:《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上海工人新村(1949-1978)》,《人文地理》2011年第3期,第35-40、64页。 (74)杨辰:《日常生活空间的制度化——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新村的空间分析框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2期,第38-45页。 (75)[英]朵琳·玛西等:《城市世界》,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74页。 (76)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1991,p.54. (77)[英]朵琳·玛西等:《城市世界》,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24页。 (78)[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7页。 (79)根据桑内特的叙述,19世纪后期,封建制度的衰落,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世俗的城市文化形成,使得共同生活结构发生了内在的变化。18世纪人们发展出的陌生人之间有意义的公共生活模式,在19世纪被改变得面目全非,公共生活变得神秘化和私人化。 (80)[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