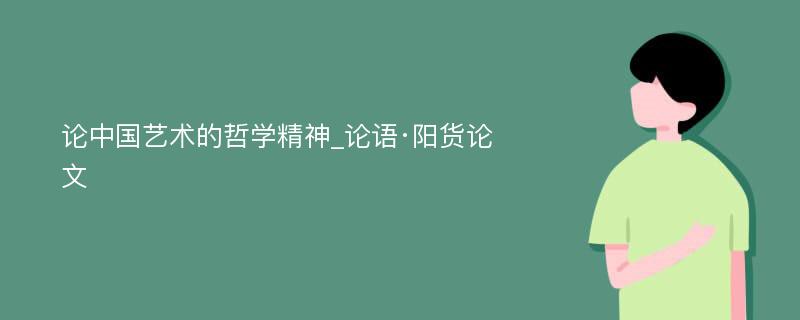
论中国艺术的哲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艺术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长期以来,学术界都以“天人合一”观念阐释中国艺术的哲学精神。这种阐释之所以盛行,究其原因,在于现代以来中西哲学的比较视野的影响:以西方哲学精神为“天人相分”,则以中国哲学精神为“天人合一”。在这种比较视野的局限下,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刻内容被简单化了,“天地”这个最具内涵的观念必然被忽视了。以“天人合一”阐释中国艺术,不仅不能真正在中西比较中确立中国艺术的特色,而且必然不能深入中国艺术的内在真实。为了正确把握和阐释中国艺术的内在精神,今天,有必要超越“天人合一”这个浅泛的观念,重新认识作为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精神基础的“天地”观念:天地境界和天地之心。
所谓天地境界,冯友兰认为是对宇宙大全的哲学觉解,是中国哲学所提炼出来的独特的心灵境界。天地境界的要义,或可以用董仲舒的话来概括,“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注:《春秋繁露》。)这一要义包括两层意义:一、人生天地间,人与天地并生,万物为一,因此,人若欲求自我生命的充实与发展,就要尽心知性知天(天地),并实现与天地精神合一;二、天地只是一个可能(空间),需要人生来实现(充实),也就是说,天地之精神,宇宙之壮丽,有待于人的努力和展示。所以,一方面人是天地一分子,人离不开天地,另一方面天地也有待于人,没有人的天地,只是虚设,是万古常如夜。在现实生成变化中,人与天地共为一体,相互生发,这就是天地境界的核心意义。道家讲自然独化,儒家讲虔诚尽性,百虑一途,最后都归于“人与天地参”。陆象山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注:陆象山:《杂说》。),王阳明讲“天下无心外之物”(注:王守仁:《传习录下》。),也就是这天地境界的精神表达,是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以及庄子所谓“旁礴万物以为一”诸义的通会发扬。
天地之心,就是“实天地之心”,也就是以觉悟的心投入天地的无限创化生育之中,而与天地万物合同一体。因此,不需要另成一种境界,另起一种心思。所以,于天地是“大象无形”,于自我是“情顺万物而无情”。以顺物无情之心鉴无象之大象,就成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与天地为“一”。这“一”就是物之初,而游心于物之初,就归根守真。因此,中国的天地境界,是无象(无形)的境界,它没有像西方宇宙精神寻求永恒理想的怀抱。天地之心是不出于天地的,而且惟恐出于天地。庄子的逍遥游,所谓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游于方外,也是在天地之中的,所求者,不过“自然”二字——这正是天地的精神。至于他所叙神仙真人之说,只是“寄言出意”,寻意者当“忘言得意”。以天地为心而实天地之心,既然无意为天地造象(以之为完美永恒的形式),也就泯冥了把天人格化为神(帝)的宗教渴念。据郭沫若考证,“天”在周代以前,即为“帝”(上帝),是人格化的神,经过周代,至春秋则获得自然的规定性(“天”成为与“地”相对并置的“天”)。而这一转变,开拓了中国的非神学观念(注:参见郭沫若《青铜时代》,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此后,神学观念再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宰。姑且不论汉魏的神仙方术,即使隋唐佛教一时兴盛,也终未成正果(以宗教立世),其对中国文化的真正影响,主要在于学人以玄理释佛,借佛谈玄,佛玄相互映发,深化了中国文化的哲思(注: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简编》第4卷。)。
中国的天地境界,由于神学观念的退出,突出和活跃了生命观念。从孔子讲“不知生,焉知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到《易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再到程颢讲“生之谓性,万物生意最可观,斯所谓仁也”(注:《二程遗书》卷二。),燃发出中国天地境界昂然热烈的生气,使天地之心落到自我生命的实处。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究竟无得”。所谓“究竟无得”,是对宇宙大全的形而上觉悟,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又是对这认识的超越,把觉悟化为生活,以生生为德。“天何言哉?”宇宙大全是不可以认识终止的,因为认识就有了分别,就不是大全。由生命而产生的认识,要回到生命本身的活动中,才是真正大全。这是现实的归根,“归根曰静”。静不是止,而是动,但是“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焉”(注:《中庸》。)。所谓“中庸之道”,大而化之,以生的意义而言,就是“人生天地之间”(庄子)——也就是“究竟无得”。
在把握中国哲学精神时,对这“究竟无得”的“人生天地间”的“生”(不是观念,而是生活),应当特别着重关注。李泽厚认为天地境界下一转语,就是审美境界(注:参见李泽厚《华夏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94页。)。但这一转语是下不得的,一旦下了,则将不再有中国的天地境界,也将构不成中国独特的审美境界。因为正如中国的哲学是以这“生”为旨归一样,同时也确立了独特的中国艺术精神指向——不是生活转化为审美的(从存在转化为形式),而是静观转化为存在(形象转化为生命)——不是自我为天地拟象,而是个体化入天地。
二
《庄子》、《乐记》和嵇康《声无哀乐论》(注:《声无哀乐论》作为一篇“玄学著作”,由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作了精辟阐发,笔者正是从两先生的论述得到启示而关注此文。但是,作为一篇关键性的经典音乐哲学论著,在美学界,至今似乎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较确切的阐释。)是构成中国音乐哲学体系的三种基本著作。其中,《庄子》是从道家指向自然的立场,《乐记》是从儒家指向人伦立场,《声无哀乐论》则是融贯两家,筑成“乐者天地之和”的中国音乐精神。《乐记》宗旨是,“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其音乐理想是“中和”(神人以和)。《庄子》宗旨是“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其音乐理想是“太和”(神会无方)。一主人伦,一尚自然;一以乐导欲,求通于和静;一任性无为,求归于虚寂。这两者如何统一起来?两者同归于天地境界。司马迁说:“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这实在是儒道两家共同的宇宙感识,也是他们音乐思想的共同基础。差别仅在于,儒家主张以乐节情,在人伦调和的基础上与天地调和;道家主张以乐逸性,荡涤尘俗而与天地同奏。以乐(乐教)和同于天地,是儒道的共同旨归,由于这个共同旨归,在乐教中,两者的分殊就不是本,而是末,两者的统一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因为人伦与自然乃是人类存在不可割弃其一的两极。
嵇康把中国音乐引入了统一的天地境界中,使中国音乐真正成为“天地之和”。《乐记》“乐者天地之和”,是《声无哀乐论》的基石。“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但是,进一步,嵇康就否定了《乐记》确立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的观念。《乐记》主张音生于人心,治乱在政,人心感物而发,以哀乐形于音乐。所以听音知德,闻乐知政。嵇康认为音乐以自然成文(按音律原则),与人心情感无确定联系(或者情同而声异,或者声同而情异),也就是说,声音只有美与不美,情感只出于人心(哀者闻歌而泣,乐者闻乐而喜)。“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所以不能以声音之道与政通(听音审政)。否定音乐与情感的密切联系(对应关系),面对的根本诘难是,如果音乐与情感无关,乐教感化人心的功能怎么实现?我们知道,嵇康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倡导者,但是,仅以《声无哀乐论》为一篇反名教檄文,实是一种皮毛之见。实际上,在此文中,正是在对其面对的根本诘难的排解中,嵇康超越了他名士的佯狂,而展示了他融合儒道而成天地一体之仁的天才哲思。
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自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由是言之,声音以和平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注:嵇康:《声无哀乐论》。)。
联系到中国美学史、艺术史的发展,这段话极其重要,极其深刻。它承前启后,总结了先秦音乐哲学思想,开拓了魏晋以来的音乐哲学,从而成为中国音乐式微的枢纽所在。根本上讲,古代乐教的中心思想,就是正人伦,设秩序。这在中西同然。但是,随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由于天地观念的非神学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以建构天地境界为指向,乐教的人伦秩序内涵,就日益表现出它的狭隘性,并且形成与天地观念的对立。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上下与天地同流”(注:《孟子·尽心上》。),庄子所谓“游心于无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注:《庄子·天下》。),这种人格理想和生命意识,是不可能在古代的乐教体制中完成的。这个矛盾,在孔子的时代,在《乐记》的时代,都还没有发展起来,但庄孟以后不断酝酿,至于魏晋,就非常尖锐了,深刻卓识如嵇康,就不能不觉悟到这个矛盾,也不能不思考根本的解决。就传统乐教的立场看,如果声无哀乐,乐教的职能怎么实现?然而,就欲成就天地境界的立场来看,却是在这人伦秩序(实际上是确定有限的情感调节)的教化中,怎么可能实现真正的同天地之和?“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嵇康称声音无情,实际上是以“和”同“情”,“情”归于“和”!并非是音乐不能感人情,但是,感人情(有限的人伦情感)不是音乐的本义,音乐的本义是陶冶人心,净涤情感,使之归于天地之情——无情而莫大之情——和。
嵇康深化了儒家的“中和”观念,但同时也突破了这个观念,使它与道家的“太和”观念融合。“大同于和”,这就取消了孔子“正乐”的必要性,它暗示了这个结论:无论雅郑,唯和(优美)是举。这不仅对于儒家,对于道家也是不能认可的,因为它的下一转语似乎是乐教可以沦为欲念的满足(享乐)。“妙音感人,如美色惑志”,实人情之向。但是,儒家求善,道家求真,都是远弃尘欲的。嵇康就此打住,结尾草依“秦客”(文中代表儒家)之说,“雅郑还是辨一下吧,这样少点麻烦。”然而,嵇康思想的下一转语,其“大同于和”的真正结论是:非乐。非乐,不是如墨子责难儒家的那样,因为礼乐过侈,而是因为具体有限的礼乐不足以同天地之大和。从嵇康而下的非乐,是老子“大音希声”,庄子“至乐无乐”,“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注:《庄子·天道》。)的“天乐”观的逻辑发展,更是孔子“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注:《论语·阳货》。)的乐教观的逻辑发展。不过,嵇康的结论,要等到宋明大儒来表达(展开)。程颐说,“此间固有礼乐不在玉帛钟鼓”,“天下无一物无礼乐”(注:程颐:《遗书》卷十八。)。王守仁则说,“乐是心之本体”,“此心安处即是乐”(注:王守仁:《传习录下》。)。所以,孔颜寻常日用之间,无论穷通,不待弦歌,却动静从容,乐以忘忧。所乐者何?自得其乐,“而其胸次悠然,直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居之妙”(注:朱熹:《论语集注》卷六。)。
以天地为心,以寻常人生为乐,中国音乐哲学的非乐精神在这里被完成而展示出来。这是对《乐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深一层阐发。“乐由中出……乐由中出故静”(注:《礼记·乐记》。),静故出于简易。但是,乐以和为本,和以同于天地为大和,如明代徐上瀛所言,以琴而论,求和须“指”“弦”“意”三合。所谓“意”,是合天地之意,因此,可以说,意者逸也。也就是说,以意论静,静就不是收,而是放,是逸,逸放于天地。这就是以琴接弦外之音:
其有得之弦外者,与山相映发,而巍巍影现;与水相涵濡,而洋洋徜恍。暑可变也,虚堂凝雪;寒可回也,草阁流春。其无尽藏,不可思议,则音与意合,莫知其然而然也。(注:徐上瀛:《溪山琴况》。)
这一段话,是嵇康论乐的下一转语,当然也是庄子这一思想的音乐阐发:“若一志也,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也”(注:《庄子·人间世》。)。这段话非常精要地揭示了魏晋以来中国音乐的美学特征和内涵,这就是:一、以意为重,乐不在管弦的音声;二、意在弦外,得意在于与弦外天地相合;三、至乐无乐,为乐之功当归于自我与天地生命的神气化合——“莫知其然而然”。这样,就可以明白俞伯牙何以观沦海而得“移情”真谛,终于成为“天下妙手”。所谓“移情”,就是逸放心神而合于天地之和。伯牙移情的传说,确可以作为中国音乐的全部象征,意蕴兴衰都在其中。
三
给事物命名,并通过命名把事物展示在它与人的存在关系的状态中,即把世界展现为人类存在的世界,这是语言的最原始的意义。在这个最原始的意义上,语言就是诗。诗是比交流和表达更原始的语言形式。一切艺术,在展示世界的意义上,是以诗为根源,并且趋向于诗的。海德格尔正是在艺术的语言哲学本义上指出,“一切艺术的本质是诗。”(注:Martin Heidegger,Poetry,Language,Thought,Harp-er & Row,Publishers,1971,p.75.)正因为在文化初萌时期(商周之交)就放弃了天神观念,中国文化就一直承担着没有原型(终极形象)的压力,使“说”的需要特别突出,成为原始的悲忧。“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注:《易传·系辞下》。)在这种“说”的原始性忧患中,诗被绝对突出了。在中国文化中,诗的突出是超越了艺术范围的,这是中国语言文化极度发展而视觉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根源所在。这在孔子的思想中表现得很明显。
孔子的忧患,在深一层的意义上应当理解为对中国文化的语言本体的原始忧患。作为中国文化的第一位教师,他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忧,以“诲人不倦”为天职,但又以“述而不作”为规范。他深知言的力量(可以兴邦,可以丧邦),但他又深知言的可疑(巧言令色,言不由衷)。作为开辟鸿蒙的教师,他不能不言(“吾与回言终日”),但又认为自己“根本”的无知(“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予欲无言”(注:《论语·阳货》。)。他不讲天道与德性,只讲好学、信古、勤思、力行、慎言。因此,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注:《论语·公冶长》。)最后,一切矛盾与欲求,都归于“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注:《论语·阳货》。)天自可无言,但人不得不说!因为没有终极的根据(天无言——无神),言说始终是对根本性的提问,使言说始终是诗——展示世界的行动。但另一方面,因为言说是没有终极根据的,言说本身就不可能被终极化为信念(教条),因此,言说本身就是忧患。诗与忧患,构成了中国语言的本体特征。所以,与西方语言相比较,中国语言是直觉性的而非阐释性的,整体性的而非分析性的。
进入魏晋,经过玄学阐发——言意之辨,孔子“以天地无言”为内函的慎言观和庄子“得意忘言”说相沟通,成为中国诗学的语言哲学。孔子的慎言观通过《易传》等经典的进一步形而上化,实际上形成了中国诗学的语言无意识(语言禁忌):“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注:《周易·系辞上》。)“言意之辨”则从老庄道学的虚无本体观出发,认为本体(道)虚寂无言无象,言象的功用在于得意(道),所以,要忘言忘象、超言绝象,才能体悟本体(得意)。这就是“得意忘言”。与“慎言观”一样,“忘言说”也是把言意之辨引入人生风范,这如汤用彤所指出:
形骸粗迹,神之所寄。精神象外,抗志尘表。由重神之心,而持寄形之理。言意之辨,遂也合于立身之道。
魏晋名士之人生观,即在得意忘形骸。(注: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41页。)
慎言与忘言,两者都把语言与个体自我的整体生存活动相关联——言就是行,同时,两者都以语言为有限工具,要简约语言,不以言废意。这使魏晋的文学自觉特别着重于文字锤炼,以求简约通透,直逼灵境。就诗歌而言,不可无言,但言的作用当只在于境界的兴发,理想是“惟我诗人,众扶妙智,但见性情,不着文字”(注:袁枚:《续诗品》。)。
与语言的形而上学自觉相关的是文体的建设,其中最主要的是把《诗经》四言体诗转化为五言体诗,开始了以后七言体诗(律、绝)、长短体诗(宋词、元曲)的演变——中国诗歌格律化的发展。格律化对于中国诗歌的作用,类似神意在西方诗歌中的作用,它把无神佑的中国诗心安顿在低吟浅唱的格律之中,使之在一唱三叹之间,忘却或消解了对语言的本体忧患(“一联如称意,万事总忘忧”)。格律是营造诗歌境界的大而化之的格局。说它是大而化之的,是因为由这一格局所成的境界长短方圆,是以诗人自我诗意的贯注而变化的;说它终是一格局,是因为千变万化总在这一格局之中。深而言之,即如宗白华所指出的,在中国诗歌的独特形式(格律)中活动着中国式的时空意象,“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注:《宗白华全集》卷二,第431页。)。
语言的本体之忧的另一面,就是没有“不朽”意义的生命之忧。更直接地说,对语言的“无可言说”的忧患,本身就是对生命意义的忧患。《论语·子罕》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庄子·知北游》。)屈原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注:屈原:《离骚》。)这是天地无限、人生有限的感怀。但是,先秦时代理性觉醒之际的人生忧患往往与个体自我的人生际遇直接关联,还不是普遍社会的人生感受,因此,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义上,都脱不了个体的印痕,所以屈原才有“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孤愤。这就使得对生命的形上感悟,不能在人生总体的层次上展开。汉魏之际连年持久的社会动荡和普遍的人生苦疾,使对人生的形上忧患真正成为普遍的人生觉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注:《古诗十九首》。)。
这是普遍也是最根本的生命忧患,必然要通入中国哲学关于“本一末”、“有一无”的本体论思辨。由于没有神学观念和非图象化的宇宙意识,这种本体论归为以天地为大,以虚无为本。但虚无并非“无有”,而是可以气化相感的“天地精神”。怎么达到这虚无的天地精神?就是心旷神逸而逍遥于天地之间——无为而常自然(庄子)。魏晋玄学大畅,魏晋人在先秦道家学说的启发下开辟了展现和安顿生命的形而上忧患的渠道——以空灵的心胸化入天地的生气运行,在倏忽悠游之间感觉自我生命与天地一体的无限底蕴。对内在生命的感发(心灵)和对天地万物生意的体认(自然),是魏晋时代生命形而上的两大觉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白华说: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然而扩而大之,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论的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注:《宗白华全集》卷二,第274页。)
的确,这种“泛神论的宇宙观”是魏晋以来中国文学的基础,它就是天地境界的天地之心。
“诗者天地之心。”这样,就引入了魏晋时代对文学的形而上意义的确认和对文学本体的探讨。这是自曹丕开始的。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注:曹丕:《典论·论文》。)文章如何能成为“不朽之盛事”?因为“文以气为主”。钟嵘阐发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注:钟嵘:《诗品》。)“文气说”以天地万物的内在生机(元气)为文学的本体,这一方面为文学存在的独立价值(自律)提供了形而上根据,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特点:内心的感发(“兴”)。中国诗歌以“赋”、“比”、“兴”为三种基本表达方式,但这三种方式都必须落实到能“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兴”就是通过有限具体的物象感发内心,触动自我天地一体的生命感受。这形成了中国诗歌的审美特点,正如叶朗所说:“这种审美特点,并不像有的著作所说的,是在于情感性重于形象性。因为‘赋’、‘比’、‘兴’无一例外都重视形象,无一例外都不能脱离形象。这种审美特点,在于重视内心的感发。”(注: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无疑,“文气说”是对早期“兴”的概念的阐发和突出,而“兴”也因此被提炼、升华为中国诗歌的本体。后世讲“兴趣”(严羽)、“神韵”(王渔洋)、“性灵”(袁宏道)、“现量”(王夫之),虽各有侧重,但都是以“兴”为本体,以“兴”为核心的。中国诗歌以“自然”为最高品格,而这“自然”的精义实在就是“能兴”。进而言之,因为始终没有形成确定性(图象性)的天地原型,对于中国诗人来说,就不是在一个既定的宇宙模式中铺展天地万物和世事人生,而是由天地万物的感触,引发一个可感可意的境界。唯有这“境界”,是中国诗歌的旨趣所在。王国维以境界论诗词,无疑是最得中国诗歌真意的。拟物叙事,乃至于抒情都要归于这境界的创化,有境界就不“隔”,无境界就是“隔”。进一步说,“兴”不是对具体物象的幻觉的描绘(再现),而是物我一体、天地一片的生命境界的感发。中国诗歌的审美本体,就是这生命境界,因此,它的存在形式也是生命的存在形式:存在与生成的统一,即感兴与境界的统一。“隔”与不“隔”,就在于能否“兴”,也就是能否“自然流出,兴象天然”(注:纪昀:《瀛奎律髓刊误》。)。
由意象的感发而远离人生,同时又由心胸的拓展而深入人生,这是兴的真谛,也就是中国诗歌的至深意义——神韵。叶朗说:“‘韵’是远离人生和深入人生的矛盾统一。”(注: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中国诗歌之所以以内心感发为审美特点,就在于它以深入人生为鹄的。不是在天地之外另造一个天地的幻境,而是自我生命与天地合一,与天地共化灵境;不是诗歌自成一人生的镜像,在诗歌中玩味人生,而是诗歌根本就在人生中间,是人生深一层的创造和展开。在这里,对王国维所谓“隔”与“不隔”,又可做再深一层的理解(注:李泽厚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的真义在于强调艺术本体世界(境界)“所透露出来的人生,亦即人生境界的展示”,这是对王国维的深一层把握。见《华夏美学》,第216页。)。所谓“隔”,就是诗与人生相离;所谓“不隔”,就是诗为人生之开拓与展现。因此,中国诗歌直接与中国哲学相通,成为人生境界的深化、提炼、开拓,在天地境界中,成为“诗者天地之心”。这可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终极处,在这里,良知即是诗心,诗心即为良知——两者统一于创造性地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就是王阳明所谓“心外无物”。何以心外无物?“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注:王守仁:《传习录下》。)台湾学者杨祖汉解释说:“阳明的答语,是表示花的存在依于人心的觉,但这存在依于心觉,应并不是依于经验的认知心,而是依于超越的,普遍的良知。良知心觉对于花的知,并不是横摄的认知,而是创造性的实现之。”(注:杨祖汉:《儒家的心学传统》,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这个终极点就是对天地万物一体境界的创造性的实现,在这个终极点上,中国诗心的原始的生命之忧展现为无限的生命的生,生生不尽之乐。“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中国诗歌在最深刻沉痛的人生感怀之中,酝酿的是醇厚深隽而又直朴无言的生命之乐。
四
与西方艺术不一样,中国造型艺术没有一个图象化的宇宙观念作为形而上的原型。中国的宇宙观念,最集中表现在《易传·系辞》中,可以概括为三个基点:一、“一阴一阳之谓道”;二、“天地之大德曰生”;三、“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矣”。这三个基点展示的是一个以生成变化为本体,也就是体用同一的天地境界。“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是说天地万物是由阴阳变化而成,阴阳变化就是天地万物的根本(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以阴阳变化为根本,天地存在的最高形式就是生生不息,发展变化;易是天地万物变化的总体表象,离开天地万物的变化,则不能显出易,反之也可以说不能显出易则天地万物也归于死寂毁溃,这就是“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矣”。这个生成变化、体用不二的宇宙观念,与西方绝对完整永恒的宇宙观念相比,确实以“神无方而易无体”为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为中国造型艺术确立了独特的走向。
“神无方而易无体”,这否定了中国造型艺术直接从现实景物去把握、描绘宇宙本体的可能。实际上,中国式的宇宙观念不仅没有为艺术提供一个形而上的原型,而且使艺术在根本上采取否定形式(形象)的形而上观念。这是与“大象无形”、“天地无言”一脉相承的。就艺术作为呈示世界的语言“说”的本原意义而言,中国造型艺术因此是“无言可说”的(没有原型作为元语言)。但是,“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注:《易传·系辞上》。)。尽管大象无形,天地无形,但在天地变化、万物成毁中间,仍然见出了宇宙最内在的动律和情态——象。所以,人就可以仰观俯察、拟取宇宙阴阳变化之象,这就是“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注:《易传·系辞上》。)。因此,“观物取象”,就成为中国造型艺术特殊的出发点。
《易传》讲了两种象,一是天地变化之象,是客观的;二是圣人所立之象,是主观的。天地变化之象,自显于天地,圣人摹拟这客观的象而成象。“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注:《易传·系辞下》。)即是说,易象是摹拟天地变化之象而成。但是,因为天地以阴阳为道,变化不居,天地的原象,是变化之象,无形之象,是“神无方”;所以,圣人不是凭借直观印象模仿现实景象,而是仰观俯察,远近比拟,体会天地阴阳变化(“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得易象,因此“易无体”。易象无体,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易象在现实中没有原型。卦象、爻象,都是对阴阳变化之象总体的摹拟,而不是对某种物象具体的写照(“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二、易象没有具体的、确定的形状和规定。卦象、爻象,“唯变所适”,不能做一定之规来解释和应用,而要因时变化,感应天地。
易象的根本在于变。“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对易象的把握和运用,则在于感。“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注:《易传·系辞上》。)正是以变为本,以感为用,使易象既不同于具体有限的器物(形),也不同于超然物外的虚静守一的理(道)。在《易传》中,象(易象)、形器与道是相互区分、处于不同层次的。象与形器不同,因为形器是具体化的象,是定形的象(“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就象与器的关系而言,不是象模仿形器,而是形器模仿象(“制造者尚其象”)。象与道不同,因为象是天地变化之象,是道的呈现(注:庞朴对“象”“器(形)”“道”三者的关系有很好的阐释,可参阅《一分三为·原象》,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由此可见,象处于形器与道之间。易象是虚实相生、动静一体的,正因为如此,易象与自然之象相合,能“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以变、以感来体悟易象,就要超越对易象做实体性的和具象性的理解,要在创化天地境界的层次上来把握易象,而这正是《易传》把《易经》从卜筮之书发展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思想源地的关键所在。在《系辞》中阐释得最充分的是天地观念,而天地观念却是展现为易象与天地的同位关系(“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共生关系(“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同形关系(“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包容关系(“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实际上,《易传》非常清楚地阐释了易以天地为象、易即天地之象的观念,以易象为天地境界,就是以象得意。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象之所以能尽意,是因为象同时超越了具体物象和语言的有限性和规定性,它以变、以感与天地之意会通。这就是“夫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注:《易传·系辞上》。),“变之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注:《易传·系辞上》。)。就此可以说,易象在不断地生成变化和与天地感应会通之中,实现了象与意的同一,极而言之,易象的本体就是这天地阴阳变化之象——圣人所尽之“意”(道)则在其中。因此,立象尽意,立言明象,贵在明象得意。易象之所以广大,就在于最终是超言出象,会同于天地的,这就是王弼所说的:“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易传》所阐释的象,是中国造型艺术的审美本体“意象”的原象(无形之象)。易象就是天地阴阳变化的意象。与西方造型艺术以宇宙精神的完美形式观念为原型,不懈追求绝对完满、整一独立的形象不同,中国造型艺术以易象为原象,化有形为无形。西方造型艺术凭借幻觉营造一个逼近真实的想象情景,从中呈现宇宙的秩序、比例、匀称、和谐;中国造型艺术则努力突破景象的有限时空,把心意精神引向天地阴阳激荡的无限时空。王微说:“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注:王微:《叙画》。)宗白华阐发说,“绘画是托不动的形象以显现那灵而变动(无所见)的心。绘画不是面对实景,画出一角的视野(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而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那无穷的空间和充塞这空间的生命(道),是绘画的真正对象和境界。”(注:《宗白华全集》卷二,第147页。)
以易象为原象,以意象为本体,中国造型艺术创作形成了三个特征:尚意、尚简、尚自然。
中国绘画和书法都有“意在笔先”之说。张彦远论画说:“守其神、专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吴生之笔,向所谓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也。”(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孙过庭论书法也说:“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谐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愉逸神飞。”(注:孙过庭:《书谱》。)所谓“意在笔先”,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就创作而言,要以意为统帅、为向导,先得意,用笔随意;二、要把外在技巧的运用化入内在精神生命的抒发之中,依意忘技(“无间心手,忘怀楷则”——孙过庭)。所以,一方面要得意,另一方面要忘技。所谓得意,不是对艺术形象的构思,而是与天地风物心契神会,即如虞世南所言:“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注:虞世南:《佩文斋书画谱》。)而忘技则“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出无方”(注:张怀瓘:《书断》。)。
中国书画又尚迹简意澹。尚简,不求全,而求略;不求深,而求浅;不求色彩铺陈,而求平淡无华;不求精细巧密,而求粗率直朴。关于这种尚简精神,《易传》论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然示人简矣”。尚简,是为了得意,是“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书画实践。尚意、尚简,宗旨是归于自然。中国书画,都以达于自然为最高境界。“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孙过庭);“是以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张怀瓘);“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张彦远)此处讲的“自然”也有两层含义:一、创作自然而然地展开、完成,不以书画为意,书画却又自然成为作者精神心意的自由抒发。二、创作过程实现自我心意精神与天地运行的沟通,以天地生命充实、熔炼、拓展自我的生命,以使之与万物化合一体,书画意象成为一片生气流行、古今融会的天地境界。
以自然为旨归,以同于天地为意象,不是以营造另一幻象的世界为鹄的,中国书画又是忘言忘象的,由此而言,不仅书画同源,而且诗书画一体,迹化无形,同归于天地之大象。“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注:孙过庭:《书谱》。)与西方艺术有形之象相比,是否可说中国艺术是无形的艺术,或归于无形的艺术?尚意、尚简,而归于自然,因此,中国艺术不是立体的艺术,也不是线的艺术——它根本就是无形的艺术!在这无形的艺术中,诗、书、画,同源共体,同归于天地生生之乐(所以,中国“古乐失传”,反而没有音乐的进一步发展)。这便是天地之心的究竟无得,恰会归于庄子所谓: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注:《庄子·知北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