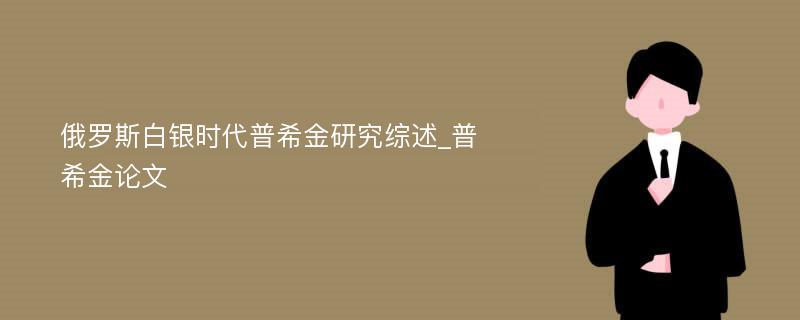
俄罗斯白银时代普希金研究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概观论文,俄罗斯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即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普希金的名字恐怕是被提及最多的,不只是艺术家到这座宝库探索宝藏,关心俄罗斯历史、俄罗斯国家及民族命运的思想家也在这风雨飘摇的世纪之交屡屡回溯以普希金为中心的文化黄金时代,分析他,研究他,试图找到诸如俄罗斯“该往何处去?”、俄罗斯“可能往何处去?”这样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的答案。全部概述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界和思想界对普希金的认识和评价不是本文的目的。鉴于对材料的掌握有限及研究兴趣,本文截取的是当时的思想家,主要是宗教思想家对普希金思想范畴的挖掘和论述,包括谱希金与俄罗斯民族性、普希金与创造、普希金与自由、普希金与新时代的基督教精神,等等。为此在这里涉及的思想家主要是瓦·罗赞诺夫、尼·别尔嘉耶夫,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和鲍·维舍斯拉夫采夫。
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在进行自己哲学思考时从文学创作中寻找生动的例子并以此为自己的理论作注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事情,其内在的原因俄罗斯学者M.马斯林和A.安德烈耶夫剖析得很透彻,他们以普希金为例指出,思想家对表现在普希金诗歌中的道德自主性观念、“智慧之美”和“对美的敏锐感觉”的论述表明,艺术创作的哲学内涵就其根源来说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有三种:通过艺术表现出来的世界观有一部分的确是艺术家从理论思维领域直接得到的,简言之,它来源于已有的哲学体系,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把他所领悟的世界观形象地表现出来;另一部分与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有关,艺术家对其进行加工提炼,使之与理论哲学并驾齐驱,不过其表现形式是独特的、艺术性的;但在艺术中尚存在一些哲学理念,不可能完全把它们归于上述两个根源,它们正是产生于文学艺术自身,其中的许多思想不只不重复理论哲学中存在的概念,而同时对理论哲学来说却是真正创新的思想,这样的艺术思考的一系列观点实际上起的是哲学思考的作用,因此艺术成为哲学思想发展的一种形式,部分地参与到历史哲学过程的运动之中。(注:M·马斯林,A·安德烈耶夫:《论俄罗斯思想·俄罗斯侨民思想家论俄罗斯及其哲学文化》, 载《论俄罗斯及俄罗斯哲学文化》, 莫斯科1990年版,20页。)因此我们认为,作为世纪之交“新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和代言人,上面提及的思想家更多的是对最后一种,即艺术思考—哲学思考感兴趣,因为从以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文学艺术家的创作中努力挖掘的是对自己的理论有意义的内容,他们离析出的思想有时是艺术家本人没有意识到甚至与之相左的内容。
一、像普希金那样去爱
瓦西里·罗赞诺夫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令人惊奇的文化现象,他涉及的研究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他除了撰写了多部论述俄罗斯宗教思想、文化现象、文学批评、教育体制、家庭问题和在当时的社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性问题的专著以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杂文,这些杂文同样论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本人引以为自豪也让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人叹为观止的著作《离群索居》、《逝者如斯》和《落叶》几如老子的《道德经》,简洁凝练,如滴滴透明的智慧水珠,也似颗颗迸溅的灵感火花,其中折射出的是对生命意义、文化本质、民族价值和人类终极目标的感悟和思索。他的哲学思考的典型特点是直觉和感性思维,是植根于生活本身,是“用心感知,让心说话”,而且他没有定型的政治取向,这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优势所在。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他对普希金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感知,他没有把普希金看成政治色彩浓厚的“公民诗人”或社会的“先进分子”,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我们知道,罗赞诺夫建构了适用于个人、民族和人类发展过程的三阶段论,即率直天真的、原始的清澈阶段,堕落阶段和从堕落中走向新生的阶段。普希金对于他就是第一个阶段的代表,普希金是纯洁、和谐、平衡、圆满的象征,是使人免于堕落或使堕落的人摆脱危机的保护人和“指路明星”,是俄罗斯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的希望。
罗赞诺夫屡次说道:普希金“已经渗入我心,在血液中奔涌,为头脑更换新鲜空气,把灵魂中的罪孽洗净……他的一行诗‘面对如斯逝者喧嚣的白昼将会屏声静气’等同于第50首赞美诗(‘饶恕我吧,主啊!’)。同样的伟大,动人,充满宗教性。”(注:B.罗赞诺夫:《逝者如斯》,《白银时代·文化随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68页。)普希金是“灵魂纯洁并且一生纯洁度过的人”;(注:B.罗赞诺夫:《关于文学的断想》(即《落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52,48,49,57,57页。)普希金永远不会衰老的奥秘“在于其精神不同寻常的圆满”,(注:B.罗赞诺夫:《关于文学的断想》(即《落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52,48,49,57,57页。)这“不同寻常的圆满”的突出表现是:“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没有一点恶毒的东西,他对于灵魂是有教育作用的,是健康的,没有一页表露出对人的蔑视。”(注:瓦·罗赞诺夫:《回归普希金》,载《罗赞诺夫文集》,莫斯科 1990年版,374页。)结合罗赞诺夫的总体思想,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通过普希金及其创作罗赞诺夫获得了对至关重要的概念“爱”的深化理解和对基督教的重新认识。在罗赞诺夫的观念中,“爱”是什么?答案是:“爱着的人在意识中根本不把自己与被爱的人分割开来,并且似乎与被爱的人在血肉上精神上不可分离,只有对人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不与爱的本质及其宗旨相对立的爱。”罗赞诺夫认为这样的“爱从不欺骗我”,在这样的爱中他“看见了真实,没有‘月亏’的真实,”在这样的爱中他“根本发现不了一丝道德的‘皱纹’。”而因此“假如我本人也是如此,那么,我的生活就圆满了,我也就完全幸福了。”(注:B.罗赞诺夫:《关于文学的断想》(即《落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52,48,49,57,57页。)在普希金的身上,罗赞诺夫体会到的就是如许真爱。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爱中他得以窥见其深刻的宗教性,窥见的是揭去了虚假的道德面具的、充满了基督教仁爱特质的关于爱的真理。罗赞诺夫的结论是:“美好的人——正是在‘善良的’的‘天赐的’意义上的美好——是人间精髓。”(注:B.罗赞诺夫:《关于文学的断想》(即《落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52,48,49,57,57页。)虽然罗赞诺夫的这些感慨源于被他称作自己的“朋友”、“教育者”和“指路明星”的妻子,但从对她与对普希金评价所用的措辞的一致上,我们有理由断定,在罗赞诺夫的心目中,普希金与自己的妻子是同一,是真正的爱的精神圆满的化身,是不需要任何道德伪装的、承载着真正的宗教精神的人间体现,是与历史基督教相对立的存在。为此罗赞诺夫自豪地宣告:“我拥有的是温和,而你们(指历史的、官方的基督教——本文作者注)占有的是墙壁。我拥有的是祈祷,而你们——还是墙壁。并且上帝在我心中,并且上帝与我同在。并且宗教在我心中。全部命运就归结于这一瞬间。为的是使隐秘的而却总是存在的东西最终变成明显的,感觉的到的,可以看见的,能够嗅到的东西……”为此罗赞诺夫在自己心中给旧的基督教及其信徒宣判了死刑:“……而你们恰恰残酷、傲慢……恰恰冷漠……你们心中没有上帝,并且你们除了言辞、许诺、希望、空洞和钟声,什么都没有。你们全部以及你们全部的手段和工具,你们的财富和藏书,学术和智慧,连同你们所说的‘神赐的奥秘’本身皆不能创造一点点活生生的,现有的,现实的善,而它是亘古未有的,不是套用样板和曾经有过的例子……”(注:B.罗赞诺夫:《逝者如斯》,《白银时代·文化随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89页。)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罗赞诺夫向动荡的俄罗斯社会泣血呼唤普希金的“回归”,呼唤爱、美和宽容,拒斥旧的基督教表现出来的假仁假义、生硬的教条、残酷和冷漠。但是对于这一点罗赞诺夫并没有多少信心,因为普希金“结束了一切”,他是“整个文明的黄昏和傍晚”,而在其后的俄罗斯社会里,在晨光初现的“清晨”,“魔鬼突然用一根小棍搅乱了水底:于是从水底泛上来一股股渣滓,一串串沼泽气泡……一切都四分五裂。”(注:B.罗赞诺夫:《关于文学的断想》(即《落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52,48,49,57,57页。)俄罗斯社会由此从率直、天真、明朗的第一阶段坠入了“忧郁、疑惑、激忿”(注:B.罗赞诺夫:《关于文学的断想》(即《落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52,48,49,57,57页。)的第二阶段,俄罗斯堕落了。不管相信多少,信心如何,但罗赞诺夫看到摆脱困境和危机的出路唯有爱,在普希金身上体现出来的宽容的、温和的、和谐的、精神圆满的爱。
二、像普希金那样去自由地创造
尼·别尔嘉耶夫在自己对俄罗斯社会命运和人类归宿的哲学思考中同样多次提到普希金的名字,但与罗赞诺夫不同,他通过普希金领悟的是俄罗斯民族的优秀禀性和人类创造的意义。别尔嘉耶夫是公认的“自由”和“创造”的思想家,在他的哲学思想构架中至关重要的概念是人、自由和创造。如果说他对自由概念的认识更多的是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尤其是《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关于大审判官的传说”的片断,那么,对于人类创造意义的思索主要依据的是普希金及其创作。
别尔嘉耶夫在自己的著作《创造的意义》之《文艺复兴的终结和人道主义危机·人的形象的瓦解》(注:尼·别尔嘉耶夫:《创造、文化和艺术哲学两卷集》,卷1,《创造的意义》, 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396—405页。)一章中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本质及其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作了充分的论述,他认为,探索完善的天性、完善的人类形式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热潮,它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联系就表现在这里。文艺复兴的本质在于其中表现出的是人的充沛的、自由的创造力量和创造精神,文艺复兴的激情就是高扬人的个性,就是自由创造的欢乐。在文艺复兴终结的过程中俄罗斯占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这表现在俄罗斯对文艺复兴的终结和人道主义的危机感受比之西方任何地方都要剧烈,在这样的感受中蕴含着俄罗斯历史命运的独特性和本真性,因为俄罗斯从未品尝过文艺复兴的自由创造的喜悦和欢乐,俄罗斯从未有过真正的人道主义激情,俄罗斯全部伟大的文学、在西方面前为之骄傲的最伟大的创造物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并不具备文艺复兴的气质。如果说俄罗斯文学及俄罗斯文化历史中存在过一个瞬间,在那个瞬间闪烁过文艺复兴特质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是普希金创作的出现,但是这一个瞬间太过短暂,没有能够确定俄罗斯精神的命运。以“迷人的天才”普希金为起点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不是普希金文学的延续,它展露出的是普希金创作和普希金精神的不可能性,因为在普希金之后的俄罗斯作家不是出于欢乐和喜悦而是由于痛苦和磨难才创作的,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基础之中有的是伟大的悲伤,是对赎罪和拯救世界的渴望。俄罗斯的思想、哲学和道德气质以及国家命运的全部特征中蕴含着某种痛苦的东西,与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的欢乐精神相抵触的东西。别尔嘉耶夫的这种认识也表现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注:尼·别尔嘉耶夫:《创造、文化和艺术哲学》,卷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20页。 )一书中,除了在普希金的创作中他看到了自由创作之光的灿烂闪耀以外,“整个的俄罗斯文学浸润在痛苦和折磨之中……其中完成的就是对某种罪责的忏悔。”在《捍卫亚·勃洛克》一文中别尔嘉耶夫写道:“从普希金到勃洛克,从我们第一次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诗歌复兴到20世纪初我们的第二次诗歌复兴,俄罗斯创作经过了一条怎样悲伤的道路!普希金了解诸多痛苦和忧伤,但同时他也了解创造的喜悦,了解天堂的轻松愉快。”(注:尼·别尔嘉耶夫:《创造、文化和艺术哲学》,卷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487页。)
作为宗教思想家的别尔嘉耶夫一方面肯定禁欲主义,他在《创造的意义》第七章“创造与禁欲主义·天才与圣徒”(注:尼·别尔嘉耶夫:《创造、文化和艺术哲学》,卷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163—180页。)中指出, “就其过程和方法是否定的而就其内容是肯定的之禁欲的道路是向上帝怀抱的回归”,但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禁欲的道路不是创造的道路,圣徒和神秘主义者的禁欲激情是回归上帝的激情,是渴望上帝之光的激情,而不是创造新世界、创造新生活的激情,创造的体验和创造的激情或者完全被旧的宗教思想所否定,把它当成“世俗的”事物来看待,或者仅仅容许其存在。因此,别尔嘉耶夫倡导一种新的宗教思想,依据新的宗教思想,创造体验本身就是宗教体验,它不是次生的,是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活动。创造激情就是宗教激情,震撼人的整个本质的创造道路就是宗教的道路。别尔嘉耶夫认为,这是新的、前所未有的宗教思想,是全球创造时代的思想。
与此同时别尔嘉耶夫指出,在创造活动中不是使“此岸世界”得到好的安排,而是创造另一个世界,真正的宇宙。创造活动总是“出世”,而不是“入世”,禁欲主义否定的“世俗”,创造也完全否定,因此对历史基督教的批判其着眼点应在抨击它与“世俗”的妥协和交易,而不是它对“世俗”的彻底否定。因此别尔嘉耶夫断言,忏悔是“出世”的道路,但不是唯一的,况且忏悔本身不是“复兴”,只有创造的热情才是复兴,“世俗”应该通过禁欲和创造两种方法来战胜。基于这样的观点,别尔嘉耶夫认为普希金是最伟大的俄罗斯天才,与普希金同时代的圣谢拉菲姆是最伟大的俄罗斯圣徒,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其中一个的“修行”和另一个的“创造”都不是“世俗的”,皆为“出世”,皆为深刻意义上的“宗教行为”,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生活来说他们缺一不可。如果说圣徒通过禁欲途径创造的是自身,另一个的、更完善的自身,那么,天才创造的却是伟大的作品,完成的是世界上的伟大事业;如果说创造自身的结果是使自己得到拯救,成为圣徒,那么,创造伟大的作品就可能扼杀自身,在天才的创造中他牺牲了自己。因此别尔嘉耶夫认为,普希金比之谢拉菲姆作出的牺牲更大,而因此可能扼杀普希金灵魂的他的天才在上帝面前与拯救谢拉菲姆自身的圣洁是等同的。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观点,成为圣徒是完成上帝的使命,而天赋同样由上帝赐予,普希金的伟大和富于牺牲精神就表现在他完成了上帝的使命,“他不仅不可能成为圣徒,而且不应该也不敢成为圣徒。”如果说谢拉菲姆的圣洁是顺从的圣洁的话,那么普希金创造中展露出来的就是果敢精神的圣洁,正是通过自己自由的创造普希金满足了人类的另一种要求,即对新天地的渴望,因为“在生活的昏暗内核中流淌着反抗的、忤逆上帝的血液,奔涌着自由创造的泉眼。”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别尔嘉耶夫“新宗教思想”的内核和实质与其说是神本主义,不如说是人本主义更合适和贴切。
在普希金身上别尔嘉耶夫领悟了创造的意义,但除此以外,通过普希金他演化了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认识。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俄罗斯民族性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它的全人类性,是它对整个世界的同情心和对异族天才的完全彻底的吸纳,俄罗斯辽阔的疆域造就了其人民热爱自由的天性,俄罗斯多灾多难的历史培养了其人民对精神价值的不懈追求。在俄罗斯的精神流浪者身上别尔嘉耶夫看到了民族的价值和优势所在,“在俄罗斯人的流浪行为中、在俄罗斯人的离经叛道中展示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全人类精神。”就文学创作来说这样的精神最早体现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在阿乐哥身上普希金已经发现并且天才地指出了故国大地上不幸的流浪者形象,是俄罗斯历史的受难者……而为了获得自身的安宁俄罗斯的流浪者需要的恰恰是全球幸福:绝不妥协。”(注:尼·别尔嘉耶夫:《创造、文化和艺术哲学》,卷 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117—118页。)但这只是端倪,尚且没有深化,可是普希金之后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流浪越来越多地沾染上了与宗教狂热类似的偏执和排他性,在精神痛苦中经受折磨,而普希金创作中的流浪者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对自由的追求,是为自由而感到的痛苦和欢乐,至少这痛苦和欢乐仍旧是单纯的,明快的,而非压抑的。这归功于普希金的文艺复兴气质。
三、像普希金那样让灵与肉和谐共处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也建构了一个“新基督教”的体系,但这个体系的本质与别尔嘉耶夫的“新宗教”不同。在一系列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和长篇小说)、文艺批评、哲学理论著作(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不是和平,而是剑》、《果戈里和魔鬼》等)及大量的杂文随笔中,梅列日科夫斯基都在阐释自己的新宗教思想,即他称之为“第三约言基督教”的宗教思想。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第三约言基督教”与“历史基督教”和“历史教堂”格格不入,是一场俄罗斯乃至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精神革命,它宣告的是一种新的信仰,即对圣灵与神圣肉体的信仰。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别尔嘉耶夫也否定“历史基督教”和“历史教堂”,但否定的是它与“世俗”的妥协,而不是它的禁欲手段,与之相反,梅列日科夫斯基反感和极力排斥的恰恰是这一点,即象历史上的基督教苦行僧那样通过遵守福音书戒律,通过禁欲行为、不眠的祈祷和战胜肉体欲望来获得对肉体的改造,他认为对历史基督教的胜利就是取消关于人堕落的教条,因为正是罪孽感阻碍神圣肉体王国在地上的实现。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只有庸人和凡夫俗子才会害怕让两个无底洞(“玛多娜的无底洞”,即圣女玛多娜身上体现出来的无限的纯洁和神圣;“所多玛的无底洞”,即《圣经》中的邪恶之城所多玛代表的淫佚和放荡)同居一体,害怕承认两者都是神圣的。
在《果戈理与魔鬼》(注:德·梅列日科夫斯基:《果戈理与魔鬼》,莫斯科天蝎出版社1906年版。以下出现引文,只在之后的括弧中标注页码。)一书的第二部“生活与宗教”中梅列日科夫斯基通过对果戈理和普希金进行比较详细而又深入地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思想。他完全认可果戈理的说法,即普希金形成于两种元素,一种是精神性的,非肉体性的,是“对地和现实性的摒弃”,是“渴望进入非肉体性的幻影领域”,另一种是肉体性的,是“依附于地和躯体,依附于可感的现实。”(83)梅列日科夫斯基进一步指出,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果戈理本人,即果戈理也形成于精神与肉体两种元素,“这是地上的天,而封闭苍穹的关键的一块石头是古罗马最后的思想:地就是天,人就是上帝。”(86)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果戈理在普希金的建议下写出的批评论著《与友人的通信》是俄罗斯文学史中的崭新篇章,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永恒的、全球宗教意识的萌芽,这是从诗歌的直觉向宗教的行为的不可避免的转折,是“从语言过度到行动”,而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俄罗斯文学的终结,即纯粹艺术的、无意识的、普希金式的创作的终结和新的宗教思想的滥觞皆植根于果戈理的创作,正是自果戈理起俄罗斯文学“开始了别样的事业”(141—142)。这别样的事业就是重新认识基督教的本质:它不是黑暗,而是光明,对世俗不是否定,而是肯定,对肉体不是抑制,而是复活,它不是非肉体性的圣洁,而是神圣的肉体。因此新的基督教中将展示出来的是“这两种元素,即肉体与精神、人与神、地与天的高级综合和平衡。”(149 )在普希金身上体现出的是两种元素“最纯粹的结合”,只是这种结合是无意识的,普希金身上的一切都是“平衡的”,可他的平衡在果戈理那里已经被破坏了,他的“和谐”在果戈理那里变成了“不和谐”,他的“统一”在果戈理那里变成了“分裂”,“一致”变成了“分歧”(95)。普希金是与生俱来的身心健康,而果戈理的精神和肉体却携带着与生俱来的疾病;普希金会说:人可以没有沮丧没有恐惧地生活在基督的世界里,因为爱可以把恐惧驱走,而果戈理却说:“生活在上帝之中就意味着生活在自身以外,可这在尘世是不可能的,因为躯体与我们不可分离。”(149 )因此果戈理独自与自己心中的魔鬼进行最后的战斗:意识告诉他,让躯体死亡,但无意识的、植入其内心深处的、在他看来是 “多神教的”、“罪孽的肉体”的本性马上就会反驳这一意识,他越是用自己的基督教思想压制这无意识的本能,则后者就隐藏得越深,远离思想意识之光,最终的结果就真的成为了罪孽的、阴暗的、魔鬼的本能,这种本能被压抑着,悄悄地积聚着,有的时候就会象炸弹一样地爆炸。而果戈理就是在这样的挤压中经受折磨,发生人格的裂变。也正是因为此,梅列日科夫斯基说道,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受尽折磨、身心憔悴的果戈理“突然想起了普希金儿童般的笑声,家乡的哥萨克的歌谣,仍旧未与尘世割离,爱着土地……在他的内心之中异常的健康与异常的疾病展开搏斗,健康的力与疾病的力相等。”(161 )因此当果戈理曾经是“多神教徒”的时候,他是光明、欢笑和喜悦的泉源,可当他成了“基督教徒”以后,却使得他周围所有人的心灵感到无以言表的压抑和忧伤。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导致这一切的罪魁就是历史基督教。正是历史基督教的偏执和排他“使得基督学说中的两种元素中的一种、两个极端中的一个成为了唯一,并且吞噬和否定另一种元素。”(178 )梅列日科夫斯基因此断言果戈理“从普希金那里获得的是生命,从神父马特菲(果戈理的忏悔牧师,历史基督教的代表)那里得到的是死亡。”(178)在梅氏看来,只有把精神和肉体都神圣化、 使它们和谐地同居一体,如普希金那样,果戈理才能摆脱困境,结束精神与肉体折磨,获得最终的“平衡”。而他也渴望着俄罗斯乃至整个人类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行,以获得全人类最终的“和谐”。
四、像普希金那样协调低级自由与高级自由
普希金是公认的自由的讴歌者,他关于自由的诗篇响彻四海。就这一主题白银时代的思想家也多有涉及。鲍·维舍斯拉夫采夫在《普希金的无拘无束(个性自由)》(注:鲍·维舍斯拉夫采夫:《普希金的无拘无束(个性自由)》, 载《论俄罗斯与俄罗斯哲学文化》, 莫斯科1990年版,398—402页。)一文中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这一点。他论述道,自由真正的深度和高度只在个人的具体生活中、在单个人的个性和民族的个性中得以展示,普希金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感觉到并且通过创作表达了自由方方面面的内容。在普希金身上表现出了为所欲为的激情,即低级的、心灵深处的、非理性的自由,它是灵魂无意识的、自发的能量,是不屈服于人类法律但就其神秘的力量来说是美好的本性。维氏认为,撇开普希金灵魂中的这种非理性而去认识他是不可能的,人们在谈及普希金时总是说到他的“清醒和和谐”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与他青年时代的行为、他的婚姻和他的死亡是矛盾的,并且没有疯狂和迷醉是不可能创作出诗歌的。但是与此同时维氏也指出,仅有迷狂同样不可能产生诗,智慧也是必需的,而普希金拥有智慧,因此,如果说在生活中普希金理性不足,那么在他的诗歌中拥有圆满的智慧。艺术不是混乱而是和谐,是美,艺术中包含两种成分:意识和无意识,阿波罗太阳神和狄俄尼索斯酒神,和谐和不和谐,圣洁的迷狂和神圣的智慧。真正的艺术是无拘无束的艺术,真正的天才永远是“无拘无束的天才”,但天才的无拘无束是双重意义的:它需要低级的、自发的、内心的自由,也需要高级的、精神的、神秘的、遵从上帝旨意的自由。这种高级的自由是对上帝召唤的应答,是创造地服务于上帝,是神圣的牺牲(这种论点与别尔嘉耶夫的一致),但这种牺牲是自觉自愿的,是精神的自由。自由的创造就是在低级自由和高级自由之间、在自然本性的深度和上帝精神的高度之间运动,创造的自由就是战胜混乱、矛盾和偶然性,由对立的自然力中创造出宇宙的和谐。维氏认为这一原则即适用于艺术创造,也适用于道德创造,而道德的任务及道德的条件就是控制人灵魂中的无意识的自然力,并且他认为普希金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从来没有混淆善与恶的界限,借助于自主的、自由的道德判断逐渐达到高级自由的境界,不受任何外在的影响、任何私欲、任何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任何社会“订货”所左右。正因为这样,普希金才成其为伟大的诗人,既服务于人类,也服务于上帝。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思想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普希金及其创作进行了剖析和阐述,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到普希金在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为什么俄罗斯对普希金的热情常盛不衰,尤其是在俄罗斯历史进程每一个关键时刻、在社会最动荡的关口总是会提到这个伟大诗人的名字,比如19世纪60—70年代、80年代,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及20世纪末的今天。正是如本文所描述的那样,对于俄罗斯民族而言普希金是和谐、圆满、宽容、爱、美、自由和创造的化身,是永远的“指路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