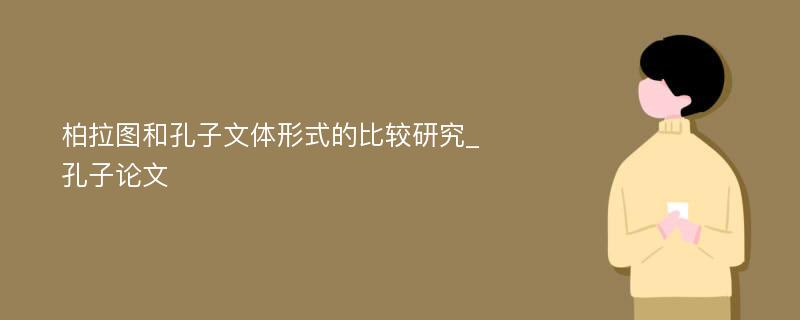
柏拉图与孔子文体形态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孔子论文,文体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和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处在奴隶社会逐步衰亡、封建社会逐步兴起的交替时期;具有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社会文化身份;他们都积极入世,企图恢复贵族统治,力挽狂澜于既倒,带有极大的保守性;他们都广收门徒,对教育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等等。关于孔子与柏拉图思想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弃栋,对二者著作的文体却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企图对两位思想家文体的特点作一对比考察,并揭示其所隐含的价值取向。正如巴赫金指出的:文体与哲学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文体自身就是有意义的思考方式”,“它能展示批评家对时间、社会、人的基本看法”(注:New Literary History,Vol.22,No.4(Autumn,1991)P.1077.)。
柏拉图全部的哲学著作,除《苏格拉底的辩护》外,都是用对话体写成的,约有四十篇。对话体在他的著作中占有绝对地位。在柏拉图的绝大多数对话中,主角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对话来体现的。关于文艺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朱光潜先生译的《文艺对话集》中。对话文体在当时的希腊非常流行。除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对话外,还有色诺芬的对话、安基斯芬的对话等。哲学家西密阿斯就写过二十多种对话,虽然都已不存在,但从侧面反映了对话文体在当时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注:《文艺对话集》,柏拉图著,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13页。)。此外,还有许多重要作品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琉善《被盘问的宙斯》、古罗马西塞罗的《论灵魂》、文艺复兴时期被特拉克的《秘密》、阿尔贝蒂的《论家庭》、布鲁诺的《论英雄激情》、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塔索的《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辩护》、古典主义时期费纳隆的《亡灵对话录》、启蒙时期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和《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等都成为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作品。当然还有人把荒诞派戏剧当成对话体文学。黑格尔和德国杰出哲学史家策勒尔则把柏拉图的对话当成“文学艺术作品”(注:《古希腊哲学史纲》,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7页。),甚至有人直接把它看成戏剧(注:《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陈中梅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3页。)。孔子的思想言行则主要集中在《论语》里。《论语》的文体有一部分采用对话形式。从整体上讲,和柏拉图的对话相比更具有语录体的性质。语录体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除《论语》、《孟子》外,还有西汉扬雄的《法言》、隋末王通的《中说》、宋明理学中的《朱子语类》、《陆九渊集》、《二程遗书》、王阳明的《传习录》、佛教禅宗中的语录、诗话中的各种问答体式,甚至“文革”期间的各种语录口号等,可谓贯穿中国文化的始终。语录体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身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一
《论语》的语录体首先是由孔子与他学生之间的等级关系决定的。孔子的学生多出于贫贱,孔子在设立学校广招门徒时也不存在门户之见,即他自己所说的“有教无类”。学生之间除了教学的需要以外,他们在孔子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如《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问仁”,孔子有三种不同的回答。冉由和子路问“问斯行诸”时,孔子的回答也完全不同。可这并不表明他们在孔子面前的地位有所不同,而是孔子因入施教的表现。虽然孔子在《子罕篇》中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不是“不多能”的“君子”。在与学生的关系上,孔子却把自己当成一个充满智慧的老人和装满各种知识的百科全书,随时对学生(包括象鲁哀公那样的诸侯)各种各样的提问给以完满的解答,而学生在他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论语·为政篇》谈到:孟懿于问孝,孔子答“无违”,樊迟又问“何谓也”,孔子又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何谓也”是典型的孔子学生的话语,它是没有自己意见、没有自己观点、必需由孔子的观点来充实的空白,他必须按孔子自己的意思来理解孔子。这和苏格拉底对话中的“是”、“对”不同,因为“是”表明答话者有自己的意见,只是和讲话者相同,当然也可能存在不同和需要争辩的地方。但“何谓也”只是使说话者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听者却没有自己的见解,更不要说不同的见解了。这种问答体中,每一段对话看似两个主体,其实是一个主体的行为,另一主体只是为这一主体的言行提供契机,而不是平等的对话和参与。所以如果学生侃侃而谈,充满辩论,根本不把孔子放在眼里,那一定会使他非常不满。因为学生忽视了“礼”,这是孔子最为注重的东西。《颜渊篇》说“克己复礼为仁”;《季氏篇》说“不学礼,无以立”。其实,“礼”就是他在《颜渊篇》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然这句话也隐含了另一个含义“师师,生生”,“师者,人之模范也”。“礼”的根本含义就是对等级制的无条件肯定。孔子虽然处在一个动荡时期,等级混乱,一切都在进行新的组合,但孔子仍想恢复过去的等级制,他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便是他理想社会的基本模式。孔子对“大人、圣人、小人”的区分,对“生而知之,困而知之,因而不知”的界定,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判断,都是孔子对等级关系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深信不疑的表现。《论语》中体现的这种关系隐喻了孔子思维模式的深层结构,是孔子对人生和社会的基本理解。孔子的这种思想同样决定了“仁”自身的等级特征。面对不同行为主体,“仁”的内涵是不同的。所以,孔子反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看起来孔子是实行了一种对等原则。其实,“父为子隐”在于“慈”,“子为父隐”在于“孝”,二者并不对等。“子为父隐”能推导出“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而“父为子隐”就推导不出“为贱者讳”、“为少者讳”、“为愚者讳”。孔子《阳货篇》主张,父母死后“三年之丧”,守三年孝,即《子张篇》的“三年勿改父之道,可谓孝也”。原因在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儿女生下来三年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这可谓对等原则的体现。在谈到诗的功用时,孔子主张“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如果“迩之事父”是对等原则体现的话,那么“远之事君”又如何证明呢?孔子对言语主体等级关系的强调决定了孔子的“侍于君子有愆”,其一便是“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即在言谈时必须察言观色,不能贸然开口,否则就和瞎了眼睛没有差别了。
与此相反,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对话者都是一些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比他还高贵的贵族的思想家。如戏剧家阿里斯托芬、悲剧家阿加通、诡辩派修辞家斐得若、演说家高尔吉亚、修辞学和语法学家普罗泰戈拉、哲学家巴曼尼得斯等。如果苏格拉底不是充满智慧和辩论技巧,他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听,因为对话者不是他的学生,更不是他的仆人。加答默尔说:“谈话艺术的第一个条件是确保谈话伙伴与谈话人有同样的发言权。我们从柏拉图对话中的对话者经常重复‘是’这个情况,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一点……进行谈话并不要求否证别人,而是相反地要求真正考虑别人意见的实际力量。”(注:《真理与方法》,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471-472页。)正如苏格拉底常说的“使对手的地位更加巩固”。所以,黑格尔说柏拉图的对话体之所以是“特别有吸引力的”、“美丽的艺术品”,就在于这种“客观的”、“造型艺术的叙述形式”“充分避免了一切肯定、独断、说教的作风”,“容许与我们谈话的每一个人有充分自由和权利自述和表现他的性格和意见。并且于说出反对对方、与对方相矛盾的话时,必须表明,自己所说的话对于对方的话只是主观的意见”。“无论我们怎样固执地表达我们自己,我们总必须承认对方也是有理智、有思想的人。这就好象我们不应当以一个神谕的气派来说话,也不应阻止任何别的人开口来答辩”。这种“伟大的雅量”使柏拉图的对话“优美可爱”(注:《哲学史讲演录》卷二,黑格尔著,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4-166页。)。由此看来,古希腊的贵族民主政体固然是柏拉图对话文体的外在原因,对话主体之间的多元平等关系却是对话文体的内部构成机制。
对话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话主体自身的匮乏、缺失和对话主体间的距离。主体通过对话交流联系在一起,通过他者认识自我,丰富自我(注:STCL,Vol.12,No.1(Fall,1987)p.96.)。孔子眼中是不存在他者(学生)的。当然,孔子也讲“予欲无言”,但那是因为“天何言哉”,是为了“行不言之教”。孔子《为政篇》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孔子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总要保持“以有知教无知”的心态。孔子对学生的基本态度是“启蒙”与“灌输”。《八佾篇》中,孔子说“起予者商也”,承认卜商的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的观点对自己有启发,看起来孔子以平等的身份来对待自己的学生了。但是孔子接着又说“始可与言诗已矣”,现在可以同卜商谈论《诗经》了,仍以导师自居。《八佾篇》还有关于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的记载。孔子自己认为这就是“礼”,把自己本来处于被教育地位的境况转换成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这都是孔子自己及文本叙述者保持对孔子优势地位尊重的心理反映。他这种“好为人师”的心态和苏格拉底根本不同。正如弗莱所说,“教师从根本上说,并非是教无知的有知者,这一点至少早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就已确认了”(注:《伟大的代码》,弗莱著,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页。)。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位勇敢、坚韧、品格高尚、具有智慧的老师。但他自己从不声称是“诲人不倦”的老师,只是“神特意派来刺激雅典城邦,这匹‘身体庞大而日趋懒惰’的‘纯种马’的‘牛虻’”。“我高于众人的本质就在于我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常常承认自己的“无知”,他的名言就是: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原因就在于自己承认自己的无知,而其他人却自认为有知识(注:《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著,余灵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45-56页。)。孔子在《卫灵公篇》说“当仁不让与师”。很类似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孔子很少承认自己的学生有“仁”。如《公冶长篇》就连续否认了子路、冉有、公孙赤有“仁”,连续说了三次“不知其仁也”。虽然孔子自己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这又往往可以理解为是“夫子自道”。如《宪问篇》,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看似孔子在自我批评,但还是子贡更能理解孔子的内心世界:他说这是“夫子自道也”,是他老人家在自我表白呢。孔子否定了他的对话者具有“仁”,也就否认了他的对话者具有正义、真理和美德,自然也就否认了学生平等对话、参与讨论的可能性。
二
对话主体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对话主体的言说方式。孔子与学生之间的等级差异对孔子的言说方式起到了决定作用,可以说是孔子语录体的根本原因。《论语》第一篇《学而篇》全部都是语录体。语式的一开始就是“子曰”。每一句话都是对经验、价值、立场的直接陈述,内容平铺直叙,不含有任何争辩性质。没有语境,没有叙事,没有原因,没有结果,没有过程,更没有戏剧性。不是讲述具体事件的话语,而是抽象的语言,只有最后不证自明的真理和结论。如主张“孝、悌、信、仁”,“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没有丝毫的证明。孔子从自己的立场对《诗经》作出了解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如何“思无邪”,他没有说明,这就导致了后来因循守旧之人反而从这句话倒过来推导出对《诗经》的解释。如果孔子平等地举出其它看法或找出相反的意见来与自己争辩,就不会导致后来很多牵强附会的论断。但习惯于“攻乎异端”的孔子是不会承认有其他合理解释的。《诗经》是一部创作年代、作者、风格差异很大的诗歌总集,根本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柏拉图就不象孔子。他对待荷马充满了具体分析,根据自己的标准指出了荷马的伟大,也指出了他的局限。并且,孔子语气舒缓的陈述,具有千古不易、坚无不破的真理气概,和苏格拉底充满机智、充满戏剧性的争论也非常不同。苏格拉底宣扬什么都是通过他与另一个反对者展开论战。当然,有时候他自己就担当了对手的角色。无论怎样,苏格拉底的结论不是不证自明的结论,他不是对真理进行宣布而是对真理进行探讨。苏格拉底的言说方式是由他和对话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决定的。
孔子与弟子之间的等级关系不仅决定了孔子对弟子的言说方式,而且决定了整个《论语》的基本内在结构。《论语》文体的基本结构一般都是:开始是“子曰”,然后是弟子某“问”,最后是“子曰”。据统计,《论语》中“子”共用431次,特指孔子就375次。“曰”字用755次,大都是作“说”“道”解。“问”字用120次,作“发问”讲用117次(注:《论语译著》,杨伯峻译著,中华书局,1988年,第217页、225页、273页。)。可见,整部《论语》孔子的话占绝对优势。孔子在对话中占据的主要言说者的地位和他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一致的。孔子学生的话语主要是对孔子言说内容的进一步发问。所以,孔子在《为政篇》中说他最得意的门生、“闻一以知十”的颜回:“我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孔子整天对颜回讲学,颜回从不提出疑问,更不要说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提出反对意见了。可见《论语》文体的特点是由孔子的宣讲和学生的沉默与对话角色的丧失为客观依据的。这就是孔子独白话语的根本特征。《阳货篇》记载了子游和子路两人向孔子的“发问”,但他们都是用孔子自己讲过的话来质问孔子。这样做既能提出自己的疑惑,又遵守了师生之间应有的礼节。子游想用孔子“教育总是有用”的思想来驳斥孔子“对小地方不用教育”的思想,被孔子一句话“前言戏之耳”打发掉了。子路想用孔子“君子不到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去”来反对孔子自己到佛肸那里去。但孔子却用“最坚硬的东西不能磨薄,最白的东西染不黑”来为自己辩解。两次对话的实质都是孔子自己内部思想的争辩,并没有另一平等主体的介入。正如巴赫金所说的:“独白原则最大限度地否认在自身之处还存在着他人的平等的以及平等且有回应的意识,还存在着另一个平等的我(或‘你’)。在独白方法中(极端的或纯粹的独白),他人只能完全地作为意识的客体,而不是另一个意识。独白者从不期望他人的回答,对他人的回答置若罔闻,更不相信他人的话语有决定性的力量,能改变自己的意识世界里的一切”(注:《巴赫金全集》卷五,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第385-286页。)。
颜回“如愚”一样的沉默源于他对师生等级关系的尊重与恪守。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却不这样。柏拉图在《国家篇》里指出:从当时流行的观点看来,荷马是“最高明的诗人”,是“希望的教育者”,也就是全希腊民族的教师(注:《理想国》,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07页。)。荷马的诗也是当时希腊教育的中心和焦点,每个希腊儿童都能背诵这些诗(注:《语言和神话》,卡西尔著,丁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79页。)。但他并不因荷马的伟大而无条件的奉若神明。所以,他在《国家篇》卷十中说,“荷马的确是悲剧诗人的领袖”,但是“尊重人不应该胜于尊重真理”。苏格拉底以平等的对话者的身份和对话者展开对话,以至于斐德若说他“你所说的全是废话”。苏格拉底并没有以训斥诅咒的口吻来对待他。他说:“这都是我不能和你同意的……如果我因为爱你而随声附和你,他们都会起来指责我……我很明白我是蒙昧无知的。”后来苏格拉底又以调侃的口气说:“我和你要好,和你开玩笑,你就认真起来吗?”斐德若说:“别让我们要象丑角用同样的话反唇相讥。”“我比你年青,也比你强壮,想想吧,别逼得我动武!”苏格拉底最后说:“我要蒙起脸,好快快地把我的文章说完,若是我看到你,就会害羞起来,说不下去了。”(注:《文艺对话集》,柏拉图著,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02-105页。)柏拉图用纯客观摹仿的方式来叙述自己老师的言语行为,他这种中性的叙述者角色让孔子的学生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柏拉图没有掩盖自己尊敬的老师的平凡、宽容和世俗性格而仅让世人看到他高不可攀的崇高地位,而孔子的学生却只想这样。在苏格拉底对话中,互相调侃的地方很多。但在论语中却没有这种情况。《子路篇》讲到子路说孔子“有是哉,子之迂也!”(你的迂腐竟到如此地步吗?)这在《论语》中是非常少见的,遭到了孔子的训斥,“野哉,由也!”(你怎么这么卤莽!)《论语》甚至很少描写孔子师徒之间自然而亲切的笑声。“笑”字在书中共出现五次,仅《宪问篇》就出现三次,都不是描述孔子师徒之间关系的。“笑”是日常言语行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笑的亲昵性能消除一切距离,化解严肃性,打破等级秩序。它反映对话者之间深层的平等关系。正如赫尔岑所说的:“在教堂、在宫廷、在前线、面对行政长官、面对警察区段长、面对德国管家,谁也不会笑。当着地主的面,农奴侍仆无权笑。平等的人之间才会笑。如果准许下层人当着上层人的面笑,或者他们忍不住笑,那么下级对上级的尊敬也没有。”(注:《巴赫金全集》卷六,第107页。)
当然,苏格拉底也常常长篇大论,如《会饮篇》。但他不是直述真理,而是充满了辩解,充满了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自言自语,对话者的立场与价值包含在他自己的话语之中。苏格拉底自己的对语本身就是对话,和严格统一的孔子话语不同,自身就分为两部分,互相争论。所以,在他的陈述里充满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充满了疑问和对答。苏格拉底和对方辩论,也和自己辩论。他对真理的追求靠的是思考和智慧,而不是不证自明的权威。所以,他说:“不能反驳的是真理而不是苏格拉底,反驳苏格拉底倒是很容易的事。”把真理置于自身之上,和孔子把自身当成真理与权威化身的心态是不同的。在苏格拉底看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算是真知的,知其然仅是处于真知与无知之间的东西。真正的真理必须经过辩论和论证。
等级原则是贯穿《论语》的一个基本原则。对话的内容、形式,甚至对文本的阐释都起到重要作用。《微子篇》讲,丈人在子路问“子见夫子乎”时,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是丈人在责备子路,说他“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但在宋代吕本中、清代朱彬等都认为是丈人在说自己。甚至,还有人认为是讲孔子。虽然子路对隐者作了批评,认为隐者忽视了长幼关系,没有尽到臣对君主的责任。但从《论语》的整体来看,很少有针对孔子而发的议论,特别是这种含有否定含义的议论。如《子张篇》讲“叔孙武毁仲尼”,叔孙武的话根本没有出现。叙述者只用了一个“毁”字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此相关,只有子贡的反驳。反驳也并非是用“讲事实、摆道理”的方法进行辩论,而是对孔子的地位和伟大进行直接的宣布,说:“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得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自量也。”叔孙武也就落得个“蚍蜉撼树谈何易”的评价。当然,从能指与所指一致的语言学角度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当然指子路和孔子,因为他们确实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从整个文体呈现出的一个基本价值倾向来看,把它解释成“农夫自道”,或以“自道”来表达讽刺更有道理。虽然孔子自己也说“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那是“夫子自道”,其中隐含的并非是自卑感而是自豪感。如讲话者是另一主体而不是孔子,那么隐含的讽刺批评意味就会更多,文本就会采取策略来消解这种有损于伟人形象的话语了。孔子完美无瑕的形象和苏格拉底的“无知加自我批评”的智者形象根本不同。正如巴赫金所说,“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双重的自我吹嘘,也是典型的:我比一切人都聪明,因为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通过苏格拉底的形象可以观察到一种新型的非诗意的英雄化”(注:《巴赫金全集》卷三,第528页。)。
总之,这是由贯穿本书的“为尊者讳”的等级思想决定的。当然,语录体的语句结构也非常容易引起误读,以致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因为语录体大都是祈使句,没有主语,没有宾语和行为对象,没有时间,也没有地点。看起来是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情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从具体语境中抽象出来的语言掩盖了言说者的立场和利益冲动,而貌似中立与客观。这种语言最合适于表达纯粹的价值判断。因为纯粹的价值判断和抽象的表述一起掩盖了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与“价值应分”之间的对立,用一种直接宣布的方式而不是争论对话的方式实现了从“客观存在”到“价值应分”的过渡。当把这种语言重新置入具体语境中了解其真实指向时,出现歧义是必然的。弗莱批评《圣经》的话非常适合于《论语》。他说:“由于作者的兴趣在于道德说教,因此在这种叙事结构中我们所读到的是不断重复的同一类故事。作者对叙事结构特别重视,说明了这里的每个故事实际上都经过加工,使它能纳入这个模式。这些故事远离历史事实,就象抽象派绘画远离其所表现的现实一样。而且它们和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方式也和抽象派绘画与现实的联系相似。作者首先考虑的是故事的神话结构,而不是其历史内容。”(注:《伟大的代码》,弗莱著,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页。)《论语》只不过把《圣经》中的“神话”转换成了“日常生活”(并非指《论语》受《圣经》的直接影响)。但其隐含的深层结构是一致的。所以弗莱称《圣经》是一部“极为偏见”的著作,是一部“用于教学的经过加工的历史”。但是在这部传统上被称为“上帝的修辞学书”中,我们仍能听到与上帝争辩的声音。如《圣经·诗篇》第四十一篇中写道:“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周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作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们在《圣经》中都能听到这种与上帝抗争的声音,在柏拉图对话录中也能听到这种声音,但是在《论语》中这种声音却被孔子一个人的声音淹没了。
柏拉图用对话体的方式记述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但苏格拉底却反对对话的体裁。苏格拉底认为:“凡是诗和故事可以分为三种:头一种是从头到尾都用摹仿,象你(阿德曼特)所提到的悲剧和戏剧;第二种是只有诗人在说话,最好的例子也许是合唱队的颂歌;第三种是摹仿和单纯叙述掺杂在一起,史诗和另外几种诗都是如此。”而且指出“摹仿最受儿童们,保姆们,尤其是一般群众的欢迎”,以至于“禁止一切摹仿性的诗进来”。在苏格拉底看来,文体的运用并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叙述文体有自身隐含的价值倾向。所以,他对叙述的文体进行了划分,“一种是真正好人有话要说时所用的;另一种是性格和教养都和好人相反的那种人所惯用的”(注:《文艺对话集》,柏拉图著,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0-60页。)。苏格拉底对纯摹仿和纯叙述所作的区分,使纯摹仿遭到了苏格拉底的彻底排斥。原因在于纯摹仿“把对话中间所插进的诗人的话完全勾销去了,只剩下对话”。纯摹仿否定了叙述者对叙事的全视角和绝对权威,取消了诗人检查官的角色和对诗歌的价值评判,使叙述成为行为主体展示自身的过程,和纯叙述的单一的价值视角形成了对比。文体形式与行为主体的一致性决定了摹仿是各种文体的混杂,正如巴赫金所说的小说是各种文体的百科全书一样。苏格拉底对纯摹仿与纯叙述的区分对西方叙事文体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亨廷顿·凯恩斯说,对话使他“拥有了现代小说家的自由”(注:《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陈中梅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56页。)。
三
对话不是宣布真理而是对真理进行探讨,真理在讨论中展示自身。在苏格拉底对话过程中,有很多“当然是”的回答,这既表示苏格拉底的观点得到了同意,而且表明了对话者的主体性,因为他们不同意就会发表自己相反的看法。如果把苏格拉底的话合在一起,对话者所有的对语“是”、“对”、“当然”合成一个,把对真理的探讨变成对真理的宣布,把一个不断展开的时间过程变成一个超时空的存在,其实质也就是把对话的结构变成独白的结构。独白的本质不仅在于把自己的话语当成绝对的真理,而且同时掩盖了自己得出结论的过程,把自己必须证明的结论当成无时不在、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证自明的真理。独白的真正含义在于企图不证自明。《国家篇》卷十,虽然整篇都充满了格罗康对苏格拉底赞同的回答,但是,一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答案的,答案“诗不但是愉快的,而且是有用的”在最后面,随着对话的展开而得出。所以苏格拉底不是宣布真理而是探讨真理,不是象演绎一样从结论开始,而是象归纳一样,最后得出结论,不可论证的独白就会在辩论中显露出自己的虚妄和无根基。辩论的前提是对话角色的平等和互换性,即在地位、知识、道德等方面都互相平等,只是由于探讨真理而走到一起。《会饮篇》为说明爱情就用了可置换的角色。不象孔子与弟子的等级角色一样不能互相置换,一个宣讲,一个聆听。对话首先是对话主体角色的确定,不象孔子讲话的角色那样。既可看成是父亲,也可看成君王;既是上级,又是老师。总之是一种优势地位。苏格拉底在《伊安篇》中一开始就对伊安的角色进行限定,从身份、阶层、性别等角度,否定了诗人(作为叙述者)的全视角和权威性,承认诗人只能说诗人的话,不能说船长、奴隶、医生、妇女所说的话。讲话者的角色不可能象孔子那样是万能的,价值上是客观中立的,语境上是不分对象的。苏格拉底和伊安角色的平等必然导向对话结论的开放性。苏格拉底其实并没有用“灵感说”说服伊安,虽然他最后给伊安出了一个二难选择,即在“灵感”和“不诚实”之间作出选择,伊安出于道德的考虑选择了灵感。但他仍然犹豫不决,并非象接受命令似的接受苏格拉底的论断,最后的结论仍然是开放的,并没有以说服为归宿。真正的对话不仅在于互相辩论的形式,而且在于开放的结构,不定的真理。对最终真理、绝对真理的深信不疑是独白的根本原因。真理是开放的,没有已经掌握了的现成的真理,真理诞生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在“他们的对话交际”中,苏格拉底只不过是谈话的“撮合者”,真理的“接生婆”(注:《文艺对话集》,柏拉图著,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44-145页。)。特别是《大希庇阿斯篇》关于“什么是美的”结论,苏格拉底一开始就承认自己由于“愚笨”不能替“美”下一个定义。最后,苏格拉底得出自己的结论:“我面面受敌,又受你们的骂,又受这人的骂。但是忍受这些责骂也许对于我是必要的;它们对于我当然有益。至少是从我和你们的讨论中,希庇阿斯,我得到了一个益处,那就是更清楚地了解一句谚语:‘美是难的’”(注:《文艺对话集》,柏拉图著,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开放的结论和多元的选择是柏拉图对话文体的基本特征。柏拉图在他著名的《第七封信》中讲到自己从事哲学的缘由:“三十寡头”的统治、他的朋友苏格拉底被控告杀死、政局“以惊人速度向四面八方急速恶化着,我变得头晕目眩,迷茫不知所从”,以至于“我不得不宣告,必须颂扬正确的哲学”。但什么是“正确的哲学呢”?什么是“正义”和“善”呢?他在《曼诺篇》说:“其实我不但不知道道德性是否可以传授,而且连德性自身是什么,也完全不清楚”,“我并不是自己明明白白而去困惑别人。相反,正是因为我自己更加模糊才使得别人也感糊涂。目前,什么是德性,我就不知道,虽然你在与我接触之前可能是知道的,可现在却同样茫然不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同你一起考察它,以求发现它到底是什么。”在《国家篇》,当格老孔恳求苏格拉底对“善”作出解释时,苏格拉底说:“我恐怕我的能力不足,我轻率的热情会使我出乖露丑,成为笑料。朋友,还是让我们暂且不管善自身的实在本性吧。要理解它是什么,这对我现在的思想翅膀来说是一个难以到达的高度。”苏格拉底对“真理”、“善”、“美”本质的无法确定使他采取了运用文学手段即“真理的比喻和影像”来说明真理的方法(注:《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4-249页。)。至于《巴曼尼得斯篇》这篇最难理解的对话,陈康先生说:“全篇‘谈话’中无一处肯定,各组推论的前提是同样客观有效的。因此各组推论的结果在柏拉图自己的眼中并非皆是断定的。既然如此,这些结果的合并如何能构成柏拉图的玄学系统呢?”(注:《巴曼尼得斯篇》,柏拉图著,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页。)所以,策勒尔说:“这些对话篇大多数是以无确定的结果告终,这样做符合苏格拉底‘一无所知’的原则;但它们也表明了柏拉图自己完全沉浸在对真理的追求之中。”苏格拉底真诚地把文明置于一种道德的基础之上,毕生探求“善”的意义,但是他“从未解决这个问题”(注:《古希腊哲学史纲》,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1-139页。)。卡西尔说:“当我们研究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时,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对这个新问题的直接解答……他从未冒昧地提出一个关于人的定义……苏格拉底哲学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一种新的客观内容,而恰恰在于一种新的思想活动和功能。哲学,在此之前一直被看成是一种理智的独白,现在则转变为一种对话。”因为真理存在于“人们相互提问与回答的不断合作之中”,人是一种“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注:《人论》,卡西尔著,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7-8页。)。总之,人是一种开放的存在。正如巴赫金所说:“世界上还没有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面。”(注:《巴赫金全集》卷五,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21页。)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并没有提出关于世界和人的最终真理,并非仅仅由于“时代的限制”,而是由于世界和人是一种开放的存在。加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中赞扬柏拉图的《斐多篇》“开始了西方形而上学真正的转折”:“希腊人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典范,因为他们抵制概念的独断论和‘对体系的强烈要求’”(注:《哲学解释学》,加达默尔等,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在加达默尔看来,“我们的思想不会停留在某一个人用这或那所指的东西上。思想总是会超出自身”(注:《真理与方法》,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798页。)。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苏格拉底反复强调的德尔福神庙上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认识你自己”。
当然,苏格拉底采用对话的形式并不能否认他同样有占有真理的企图。如他在《国家篇》里提出的“神只是好的事物的因,不是坏的事物的因”的论断,并没有展开论述,也没有提出论据,这是由苏格拉底的立场决定的。他赞美或否定很多东西,并非从事实出发,而是认为应当如此。他的文艺观的两个出发点“神的完善”和“对教育有利”是不证自明的。他无法举出考古学的、历史学的、甚至是现实生活中的论据,而是从“应分”、“应该如此”的角度倒过来推导。苏格拉底的立场决定了他对文艺的看法和根本要求:对神的描写是否真实取决于对神的描写是否恭敬。他反对描写神干坏事,是担心:比人聪明、比人完美的神都干坏事,年轻人就会以此为理由替自己的坏事辩解,并原谅自己。虽然苏格拉底承认自己对“乐调是外行”,但他仍然从音乐的作用来推断出音乐的价值,决定音乐的保留与取舍(注:《文艺对话集》,柏拉图著,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8-58页。)。罗素就从逻辑学的角度提出了柏拉图理论的非统一性和荒谬性。他说:“柏拉图说神并没有创造万物,而只是创造了美好的事物……他的结论是不诚恳的,是诡辩的;在他暗地的思想里,他是在运用理智来证明他所喜欢的结论,而不是把理智运用于知识的无私追求……他是一心一意要证明宇宙是投合他的伦理标准的。这是对真理的背叛,而且是最恶劣的哲学罪恶。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可以相信他有资格上通于圣者;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来说,他可就需要长时期住在科学的炼狱里了。”(注:《西方哲学史》,罗素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4-189页。)策勒尔也说:“苏格拉底的这位辩护人陷入一种不能容让的和僵化的独断论之中”(注:《古希腊哲学史纲》,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
四
柏拉图采取对话文体,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谈话者采取对话态度;孔子采取语录体和对学生采取独白态度,除了和谈话主体之间的关系有关,还与他们对“神”、“真理”、“善”等关于世界与人的终极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神”在哪里?“真理”掌握在谁手中?怎样才能具有“善”?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他们对他者的根本态度与话语方式。
孔子在《雍也篇》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述而篇》讲“子不语怪,力,乱,神。”《先进篇》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中有很多处讲到“鬼”、“神”、“帝”、“天”、“命”,但孔子对他们的基本态度却是《子路篇》中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也就是“六合之处,存而不论”。当然,孔子也有发牢骚需要“天”来安慰的时候,如“知我者其天乎”。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何言哉?”既然“天何言哉”,又怎么知道孔子呢?可见,孔子也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讲话,并没有代表“天”、“帝”、“神”。
与此相反,柏拉图对“神”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在柏拉图看来,“神”无处不在,宇宙体现了“神”的意志。《会饮篇》、《裴德罗篇》、《国家篇》有很多颂“神”的篇章。《斐德罗篇》、《伊安篇》反复提到诗是“神”给人的礼物。《蒂迈欧篇》指出人不过是“上帝”的“孩子”(注:《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7-319页,第378页。)。“人”、“神”的截然对立,人怎样才能接近“神”、掌握“真理”、具有“善”成为柏拉图终身思考的问题。策勒尔说:“柏拉图主义自始至终殚精竭虑想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要在超验的理念世界和感觉的现象世界之间的鸿沟上架设一座桥梁。”(注:《古希腊哲学史纲》,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也就是说,他终生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思索“上帝”、“真理”、“善”的本质,而且还在探索如何才能走向“上帝”、“真理”与“善”。这便是柏拉图对话思想的最终根源。孔子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他心里不存在“上帝”,“真理”和“善”又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他不是“二元论”者,没有什么“鸿沟”需要填补。他需要的只是发布“真理”和“诲人不倦”。柏拉图对“神”的理解不可能用“唯心主义观点”一批了之,对世界的“唯心”看法和对人类信仰的探索并不能划等号。柏拉图知道:就是因为“神”的存在,人才需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首先是认识自己的局限。人生的短暂、宇宙的无穷使凡人不可能象“神”那样完全把握真理。人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有限的生命和智慧使他对自身和世界不可能获得最终的、绝对的、彻底的认识,“永无止境的探索”才是他应该采取的聪明立场。所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反复强调人的无知并非仅仅在于人“所知甚少”,还在于“以无所不知、固步自封”来自欺欺人。注重“开放”与“兼容”的苏格拉底对话精神告诉人类:不要违背“神”的愿望停止对真理的上下求索,任何企图独占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终极真理的妄想,任何追求一劳永逸、颠扑不破权威的嗜好都是无视自身局限,忽视他者存在,隐入僵化与成见之网的表现。
总之,对话文体的流行说明柏拉图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雅典社会急剧变化,也是希腊文化的转型时期。代表民主势力的诡辩派的兴起使旧贵族的权威受到质疑,自由辩论的风气和自由思想的形成昭示了“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将开始”的开放社会心态。我们从柏拉图在《法律篇》描写的“让全体观众举手表决谁获胜”,“剧场的听众由静默变成爱发言”的境况和在《国家篇》中描写的“能卷去一个年轻的心”、“引起岩壁和会场回声”的“鼓掌哄闹”看出当时社会上下交融的狂欢情景(注:《理想国》,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1页。)。当然,柏拉图仍然想把社会的各个阶层、阶层的每位个体都纳入到他为贵族统治设计的统一稳定的秩序里。他对文艺的理解、对文艺作用的认识都来源于这个根本动机。这种企图复古的出发点和孔子基本一致。与孔子仍然保持他的优越感和高傲姿态不同,柏拉图面对正在丧失的贵族优势,必须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重新找到证明。优越感和不可动摇地位的丧失使他采取了对话的争辩的态度,他的长篇大论正说明了他的这种危机感。柏拉图在辩论中说明的方法和孔子不证自明的思维方式相比含有更大的开放性和现实性。孔子对社会现实的积极介入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评价之间的距离,不仅在于他的思想不符合现实的需要,而且在于他对待现实、对待他者的态度、方法与策略:唯我独尊、自我封闭的话语模式并不能适应转型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在对话与交流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才是唯一可行之路。
标签:孔子论文; 柏拉图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孔子的名言论文; 论语论文; 国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国家篇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