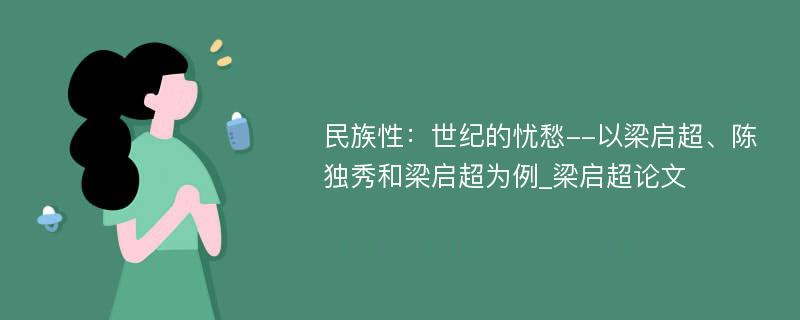
国民性:沉郁的世纪关怀——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的思想个案出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国民性论文,沉郁论文,个案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0)02—0117—06
近代以来,国民性改造思潮几度成为时代的主题。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即是颇具代表性的先驱。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构成了世纪一大思想景观。在新世纪开始的日子里,回眸并梳理先哲的思想理路,必将为走向现代的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积极意义资源。
一、着眼点:同立于思想晕轮的圆心
就家庭背景与个人游学经历而言,三位先哲自幼生长于传统观念极深的“士大夫”家庭。以科举取功名的思想在他们的心中烙下了鲜明的痕迹。无论是热衷科举还是厌恶科举,先哲的“科举”理路都是驾轻就熟的。这就告诉我们,“士”的心理在他们心中埋下了坚实的种子。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为先驱的责任承诺找到了理论依据。“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道出了历史的沉重使命感。于是,我们看到,跃然于眼前的知识先驱在其心灵深处无不激荡着寻觅报国之路的满腔热情。“报国惟忧是后时”,梁启超的英雄时势观念造就了他特有的精神气质,刚刚步入社会的他就发出了狂气冲天的“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狂欢欲语谁”的豪言壮语;与梁启超的颉颃齐飞,陈独秀在日本的《咏鹤》也颇见真情:“本有冲天志,飘摇海湖间。偶然息城部,独自绝追攀。”[1](P105)任凭花开花落,依然故我,陈独秀气贯长虹, 一生尽在“独自”中履行着“绝追攀”的诺言。无独有偶,接踵而来、老成早熟的鲁迅更是一位后来居上的“后起之秀”。1903年,鲁迅在日本弘文书院同班同学中第一个剪掉辫子并留影纪念,写下了激情满怀的报国诗篇《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比起“虽九死而未悔”的屈原毫不逊色。
应该看到,这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在内涵与外延上都不一样,毕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有感召力了。为此,我们的先驱在严酷时代的“证词”里不约而同地找到了通向现代之路。十分巧合,也是非常“必然”的是,三人都曾有过多次东渡日本的游学资历。从他们的首次游学时间来考察,几乎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间。那时,日本的改良道路已经初见成效。1853年,当美国人佩里带领舰队到达日本的一个海岸时, 一向封闭的日本立刻张皇起来。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很快将“大和”民族牵引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一个由封建幕府统治的“蕞尔小国”腾飞于亚细亚。日本成了亚洲的英国,虽然它一开始并不曾有英国式的议会制度,但是它是“戴着镣铐跳舞”,“开明专制”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无穷的活力。 1894 年甲午战争与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令中国的“士大夫”们目瞪口呆。在“小日本”与“大中国”的巨大心理反差下,他们不能不对这个“蕞尔小国”刮目相看。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就发生在那一年。颇费心机的洋务运动并未能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文明道路,为什么?对于渴望走出危机、济世拯民的一代先觉而言,铁腕政治人物大久保利通的改革路线值得“仿求”,而开思想先河的文化先驱福泽谕吉也更是启蒙主义者自我对象化的头号种子。
无论是政治上的改良还是革命,抑或在两者之间摇摆,先哲们在“改造国民性”的意义上理论设计却如出一辙。梁启超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为福泽谕吉的观点叫好,而且处处暴露出福泽对其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日本大儒福泽谕吉”所论的礼教重视“礼乐”之故的判断就甚为其所推崇。[2](P141)如上所论, 我们选择的三位思想先驱都不约而同地受到了这位日本思想先驱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这里仍无意于对这种影响的程度作全方位的比较,毕竟,我们的论题决定了笔者的立意。就文学之一的体裁——小说设下的“鸿门宴”来看,就足以说明先哲经历不谋而合之趣了。众所周知,鲁迅当年赴日留学的原由之一就是因为日本是受了西学启发而后起的强国,现在看起来既有理想化的成分也有神圣的因子。日本发达源于西方科学中医学的事实,以及想治疗像他父亲那样为中医所误的疾病之冲动使他选择了“西医”。过去,我们论述鲁迅“弃医从文”的转变多认为只是因他那次仙台医专的“幻灯事件”所致,其实在这一“时间”的背后还有更为有力的策动,只是无形的间接作用而已。这就要说到小说启蒙的问题了。世纪之交的日本正是福泽谕吉如日中天的时期,沿着这个背景,继福泽的思想启蒙——“内在的文明”之后,日本以“经济济民”为宗旨的政治小说应运而生。福泽思想昭示下的日本文学引起了留学日本的中国先觉的注意,他们甘冒几千年轻视小说为邪道的“大不韪”,转眼间将小说提高到了启迪“国民之魂”的位置,鲁迅将它称之为“牵引国民前进的灯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1896至1911年,中国翻译出版日本小说101部,其中政治启蒙小说占50多篇。 这充分说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娘家远在东瀛。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行文学杂志《新小说》,为新型的政治启蒙小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创作园地。梁氏的“新民说”也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1904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连载的《黑天国》显然是一篇典型的政治启蒙小说。他将自己要讽刺与革命的对象命名为“满周苟”,意思显然是“满洲狗”的变体。时至“五四”,他1917年的《文学革命论》比起留学美国的胡适就更见功利色彩了:“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苦何效果也。”[3](P172)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地先去模仿别人。”鲁迅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也在履行着这种“随着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的理论。鲁迅后来在谈到“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情节时,一再说是“仍是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不过是想利用小说来改良人生与社会,无疑是日本启蒙思潮中功利主义影响的结果。就文学的角度看如此,换一个角度,从梁启超与陈独秀的“尚武”之良苦用心来看,也不难发现他们“立等可取”功利思想的演绎。梁氏的“冒险精神”之提倡以及他在《少年中国说》中岳飞“满江红”词句的引用足以让人感受到撕杀争斗的战火硝烟;陈氏的论述则不遮不掩、一语中的:“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3] (P88)
可以这样说,由立人而立国的思想逻辑与日本近代化先驱福泽谕吉的建立现代化国家必须造就一批具有文明独立人格国民的理论设计一脉相承。恰恰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文化熏陶,令我们论述的的对象“仿佛一个人有两个头脑,两个身体”,也使他们有了一双慧眼,而立于更高的角度去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走向。
二、兴奋点:“同唱一首歌”
相同的传统情结凝聚成了对国事的同样感受;同样的经历又使他们“同唱一首歌”:由立人而立国。从日本的近代精神里面,思想家们找到了借鉴的资源。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之改造国民性、变革人心的经验成了中国特定时代有识志士的精神宝典。面对岌岌可危的国情,梁氏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以立人为本的思想在这里肇始。为何对立人情有独钟呢?原来,在启蒙者那里,在“立人”与“立国”之间,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里解释得很清楚:“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这正是“民族主义之根底源泉”。[2](P211)对此, 他的逻辑构成十分到位:“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2](P211 )正由于他是从国家的文明独立的立足点出发启蒙的,所以才导致了他在讲述“己”与群、个人与社会、“私德”与“公德”的关系时,总是将“利群”放在首位,甚至有本末倒置的现象。按照梁氏的说法,中国是一个公德奇缺的民族,私德却可以从“独善其身”里找到资源。这就出现了明显的错位。因为西方的个人主义、群体主义同中国的私德、公德不可同日而语。
过分强调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与义务,势必就会形成这样的思维逻辑。深受这位思想启蒙先驱影响的“五四”先觉在国民与国体上的辨证同样有一种道义责任的浪漫。梁氏说过“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2](P214)与陈独秀那“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 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人民程度与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2](P104)的不止一次的述说可谓如出一辙。鉴于有立人必先立国的逻辑在前,所以就可以理解他的这种议论:“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3](P282 )在后来者眼里,一个国家的政体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要实现民主共和,就必须从个人启蒙开始。具体到人与国的关系即是:“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2] (P201)显然,梁、陈的默契突出表现在立国先有“新人”的思想逻辑上,着眼于“新人”,归宿于立国,这正是他们的全部。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梁氏在开启民心、启迪民智的过程中强调了“利群”的思想力量,而陈氏则在激发民力、注重素质的过程中倾向于“国民运动”的中介作用。这也是陈氏后来走上“身体力行”道路的潜在理论基因。
循这一潮流而下,间接受惠于“戊戌”的先哲,直接为“五四”先驱催化的鲁迅又该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众所周知,鲁迅在思想文化的舞台一亮相就显示出了非凡的“立人”底牌。1907年,他于早期所作的文章《科学史教篇》中同声共求地批评一味强调“振兴实业”者是舍本求末。他不无忧虑地说道:“举国唯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拔耳。”[5](P33)“源”即“本”,“末”即“标”。翌年8月,他在《河南》杂志发表《文化偏至论》, 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思想:“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P57)鲁迅这里所说的“根柢”,意即极言其重要性和社会功能,与梁启超、陈独秀是在一个意义上运作的。鲁迅自称为是一个“听将令的战士”,所写的作品也是“遵命文学”,自觉“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目的还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他关心“国事”是从批判“民瘼”开始的。与前两位的前瞻性相比,鲁迅更注重对过去的解剖与批评、反省与忏悔。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中国如同“染缸”的传统是非常可怕的。国民的精神麻木被他用两句话一针见血地概括了出来。继他将中国历史总结为“吃人”的历史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历史的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6] 深刻而又准确地把握比同时期的思想家来得深沉、睿智,因此将鲁迅称为国民性解剖的大师是不算过誉的。思想文化史上的梁、陈、鲁正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格调“同唱一首歌”的。
三、归宿点:来自不同终端的关怀
血浓于水,澎湃着振兴中华的声音令先驱们担负起“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的文化与承诺。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由于个人性情与兴趣所致的原因,智者的尊严也会显示出不同层次的意义。
就他们的政治情怀而言,我们看到较为强烈的还是陈独秀;就他们接受外来文化资源的活跃性来看,较为易变的还是梁启超;就三位思想质地的规定性来说,较为醇厚的当推鲁迅。显然,如此纷繁错落的“比较”视野很难理出明确的头绪,不过,从民族和民主关系的角度予以考察则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角度。
从梁氏一味强调“群”性、“族”性的价值趋向来分析,处于中国动荡关头的他有着十分近利的现实色彩。对“公德”的关注使他没有来得及思考:中国孕育了一个一盘散沙式的民族。或许,甲午战争的炮声未落,八国联军的枪声又起的原因在起着支配作用。总之梁氏已经无法将那极富价值但却看似散漫无力、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放在显赫的位置。在家国、民族岌岌可危的情形面前,我们还有什么比这更要紧的事?如果说纯正的个人主义属于民族范畴、群体至上偏向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在个人与团体、小我与大我、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思想交战就可以窥见一斑了。
在德、智、体的素质启蒙布局里,三位先驱都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梁氏一再述说中国国民道德的堕落、匮乏:“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一端也。”[2](P213 )陈氏不也曾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吗?鲁迅对国民道德素质之忧愤深广的评论是家喻户晓的。他说他“向来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对民众的体验是“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7](P20)足见其为中国道德堕落的悲哀与痛苦。
同样是对道德伦理的关注,由于梁启超多受现实感驱动,因此他时时显示出“易质流变”的特点。从民族的救亡独立出发,他眼里的一切学理与主义都是左右逢源的得力资源。比如他与陈独秀同是进化论的信士,但是在他们的笔下,前者明显属于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后者则是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这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梁氏的思想路径。从“利群”为“放诸四海而准”的理论出发,梁启超得出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价值判断:“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2](P227)在此, 梁氏于个人权利与社会义务两者之间选择了社会义务,并且认为义务大于权利,“小我”应该服从“大我”。这一带有明确偏向思想路径的内核还是民族情感驱动下的集体主义意识。质而言之,他在民主与民族这一支援社会前进的“舟车之两轮”间作了“偏至”的处理。本来,“民主”作为一种“工具”是为保证“自由”而设计的手段,可在梁氏眼里“民主”却被生硬地拉到了“民族”的麾下,一意为其效力。这样,原本立于民主之上的“自由”也都不够自由了,甚至时刻有被拉来做“民族”拐杖的危险。梁氏就曾在《余之生死观》中作过这般表述,人的个体物质存在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因为它是次要的,很快便会湮没无闻;真正可以依赖的是群体的集合体,因为在这个集合体中包含了每一位成员的精神价值,成为一个永久的存在物。梁启超把个体的物质存在划为“小我”,把群体的集合称作“大我”。他甚至推论说,只要“大我”具有生命力,“小我”的生死是无关紧要的。不难理解,这种以激进集体主义为特征的哲学显然忽略了个人的生命存在与价值,至少没有看到“大我”之生命力与精神价值来自何处。
无庸讳言,梁氏的文化抉择明显受到了现实的策动。在现实面前,他是时代潮流中的一叶无可奈何的思想扁舟。“五四”之前,无论是受益于进化学说,还是恍悟于日本“脱亚入欧”的改造国民性潮流,一旦民主与民族、个人与社会、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发生冲突,前者都无一例外地让位于后者。尽管严复以及梁启超率先提出了民德、民智、民力的问题并想方设法予以解决,但并未能为时代所接受。梁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只有“团体之自由”和“利群”公德而杀青;即使后来辛亥革命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也还是“服从”了历史的安排:“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8]就这样, 改造国民性的潮流将个人的位置一让再让,时代的局限充分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9](P426)在这一层次上, 梁陈的不同价值趋向有着深刻的时代性。而且对这一时代性起着决定因素的还是他们分别属于“辛亥”前后的两代人。梁启超的时代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交织的危急关头,那时的中心课题首先是保国保种,于是一股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汹涌思想潮流便滚滚而来。然而,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面临袁世凯称帝的变迁,那位从“革命”丛林中走出的老革命党人陈独秀在民主共和的希望破灭之后便怀疑起不分理智与情感之爱国的危害性来。恰恰是在这一怀疑上,我们发现陈氏的“民族”思想下沉,“民主”意识上升,形成了与辛亥前思想先驱不同的立意。他的这一思想命题一方面体现在他对盲目爱国气质民族主义情绪的批评上,另一面则体现在他对个人权利地位的发挥上。
改造国民性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启蒙。这一自觉具体表现在陈独秀那里,即是怨己不怨人的自我忏悔意识的浓烈。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首先讨论理智与感情的关系。因此我们说“五四”人本主义的发生决非偶然。早在《新青年》创刊的前一年,陈独秀就急不可奈地借助他人的刊物以《爱国心与自觉心》为名痛陈了“范围天下人心”的“情与智”:“过昵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由斯以谭,爱国心虽为立国之要素,而用适其度,智识尚焉。其智维何?自觉心是也。”[3](P67)《新青年》号角吹响之后,他颇富激情地说:“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3](P132 )同样是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活动,陈氏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与眼光,他将与这种意志对立的“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等狭隘意识做了一定程度的消解,正应验了瑞士思想家在评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那句话:“在最有才能的集团里边发展起来的世界主义,它本身就是个人发展的较高阶段。”[10](P129)在“五四”先驱那里,他们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将民族主义思想压低到了最小程度,一心惨淡经营着民主的个人主义空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决心抛弃“党派运动”从事“国民运动”的发誓就足以表现出这一心迹。
换个视角,与梁启超一味强调义务相对,陈独秀关心的是社会能否保证个人才智的正常发挥,能否保障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在社会不能保证的情况下,个人就有必要去标异见、抗群言,去争取自我的人格与平等。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各与个人主义利益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3](P239 )陈氏的个人本位主义是针对传统的利他主义而说的,与梁氏的个人让位于团体的设计相反,他唱了反调。值得说明的是,这个反调并不意味着一心一意的自私自利。陈独秀的诠释是,个人本位主义注重的是个人自由意志和民主精神,与极端利己主义不可混为一谈。非但如此,愈是张扬个人主义,就愈对社会有利。倘若一味强调责任与义务,忽视了个人的权益,社会就会对个人才智的自由发挥产生阻碍和影响,从而也就不利于社会。既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那么失去个人独立人格也就意味着社会的窒息,由此“集人成国”的国家与社会也就没有了富有生机的细胞和分子。就此而言,按照梁氏将单个细胞与人体的比喻,如果单个细胞都失去了生命力,那人体还有生机吗?难怪陈氏会有对“自表面观之”论者作以“浅矣”的批评了。他的关怀已经超出了“类”、“族”的意义,不但有中国,百且也有中国以外的“社会”。至此,梁、陈之论已见分晓矣。
及此,作为后起之秀的鲁迅该从容登场了。上面说过,就鲁迅的启蒙世界来看,他的思想纯粹性是远远高出梁、陈的。何以言之?单从其社会角色来说,他既缺少陈氏的激情,也没有梁氏的直接参与欲望。鲁迅的冷峻与深刻铸就了他在中国启蒙思想史上显赫而特殊的位置。因此,我们在分析他的终极关怀的时候,就可以放心地在文化视野里透视他于民主和民族间的定位。要而言之,鲁迅的关怀可以说是不带丝毫的“杂念”,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人生关怀。比起前两者,他的思想理路更直接、更本质、更具有终而极之的韵味。
他早期与友人许寿裳讨论的“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是他一生的生命守侯,直到临终还职守这一节操。对这一课题的“任重”估计之不足使他曾极度失望过,从他思想放射之前的“黎明前的黑暗”之事实不难发现其关怀的“过正”。在他开始“遵命文学”的创作之前,先驱者的“将令”曾一度失灵,“战士”自有其理由:“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毁灭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数可援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5](P419)探究微言, 这是他人生关怀思想的一个反正。小说《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揭露,《药》中的愚昧麻木,《阿Q正传》中的颟顸不争, 都在履行着启蒙思想家的诺言:“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若,引起疗救的注意。”[11]继小说《伤逝》对个性解放与自由之路探讨之后,杂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更是充满忧患,充分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的关怀。对弱者的关心与对未来的期望,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主题,“孩子”与女性一直是他笔下关注较多的话题。既有娜拉式的子君,也有旧式的祥林嫂;不但有《狂人日记》里“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自我真切体验与放射:“肩袭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这就是他身体力行的关怀。即使是在反思自己的婚姻与爱情时,他也没有忘记“孩子”,因为孩子就是将来。“我”自己无爱的婚姻已经无可挽回,作为“中间物”的我只能从长计议——“旧账如何勾销?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5](323)这时鲁迅并无孩子,他的“孩子”即是普遍人生意义上的“新生代”。
相比较而言,鲁迅既没有梁启超的现实感那样强,也缺少陈独秀式的力抗社会的外倾倾向。由于这个缘故,鲁迅笔下的未来与希望总给人以渺茫的感觉。他在《希望》一文中引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即使是在说到自己对“希望”的相信时,他仍还是一副模糊的情形:“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12]在小说《故乡》里,他也认为我们的后辈“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的生活”,但转眼间这种“新的生活”又很快变成了“我自己手制的偶像”。离开故乡时的那段结束语更让人有一种希望茫远的感觉:“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冷峻的美与孤独感像牢牢嵌入了鲁迅的作品,与梁启超的英雄气、陈独秀的救世感形成了对照。
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去分析,就不能止于福泽谕吉的“指点”了。我们说三位思想先驱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日本启蒙先哲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譬如梁启超在福泽之外,就有欧美的拿破仑、华盛顿等等一系列英雄为向导,这时他的理论中心还是进化论;陈独秀固然推崇福泽谕吉,但“推倒一时豪杰”的胸怀是他对德国的哲人尼采、意大利的马志尼等特立独行者也是情有独钟。他的立论中心还是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尤其是来自法国的“惟民主义”人权思想;鲁迅的人生关怀除却福泽的改造国民素质理论,更有西方现代化人本主义哲学作其后盾。叔本华、尼采、基尔凯郭尔等一批注重个体生命意志的天才哲学家给了他无尽的思想资源。在个人与“类”这一尖锐对立的矛盾体之间,西哲极力强调自我意志与精神自由的现代归宿,张扬个性、异见,鲁迅自觉地担负起了“历史中间物”的重任。
在20世纪末回眸先哲的精神历程,生的苦闷与智的快乐尽在其中。理解这种苦是为了不再苦闷,寻觅到这种快乐是为了更好地用诸现代人生,更积极地享受快乐。发起于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在百年之后渐渐失落,回想当年,不禁自问:难道就让它这样随风飘逝?但愿世纪末的反思引发的不仅是自慰。毕竟,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平庸。
收稿日期:1999—11—25
标签:梁启超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陈独秀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福泽谕吉论文; 新青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