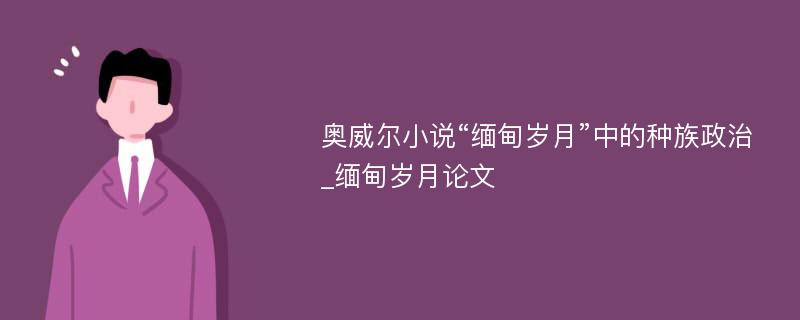
奥威尔小说《缅甸岁月》中的种族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缅甸论文,威尔论文,种族论文,岁月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85年,英军攻占缅甸首都曼德勒,开始了对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①在此期间,驻缅英国人将缅甸人视为劣等人种,而且对于“给土著士兵或佣人造成的不公与苦楚,臣属国民中仅有的一些职业人士的堕落,以及弱肉强食的自我扩张,大多数英国人甚是自得,或者至少也是默许”(Voorhees 75)。
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缅甸担任警察期间目睹了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尽管他承认英国人在管理缅甸方面确实比本地人做得好,②但依旧将殖民统治视为不合理的苛政,并对自己参与其中感到深深的罪责,因此在退役时间尚未到时就辞掉了这份收入颇高的工作——“我确实曾在印度警察队中服役5年,也确实中途放弃这份工作,部分是由于它并不适合我,更主要是由于我不愿再为帝国主义卖力。我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我深知其中的内幕。这段岁月的历史可以在我的著述中找到,包括一本小说”(Orwell 237)。此处所指的即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故事的背景是在英殖民统治日薄西山之际的缅甸小镇凯奥克他达,一群英国人相聚在白人俱乐部,整日饮酒,以排遣内心无法言说的寂寞。其中内心柔弱的弗洛里深知英国殖民统治毫无意义,可又缺乏足够的坚毅,不敢为自己的印度朋友维拉斯瓦米医生争取进入白人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奥威尔在书中不仅对驻缅英国人的生活做了生动的记述,还探讨了其中复杂的种族关系,特别是英国人对印缅土著行使权力的各种方式。
一、从权力关系看种族政治
现代社会的权力行使方式以规训为主,指的是实现服从的各种系统方法(包括观察、记录、计算、调节和训练等)。根据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观点,规训是“一种权力类型,是一种行使权力的形态,包含一整套的工具、技术、程序、应用标准以及对象”(Foucault 215—6)。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权威对个体的塑造和控制。在国家政治的语境下,权力行使方式被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划分为压制性国家机器(RSA)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Cormack 11)。RSA指通过警察、军队和刑法制度等手段对从属阶级公开行使权力,这些暴力手段不仅在经济上花费较高,而且在维持社会生产与阶级关系上的效果也并不理想。根据福柯的观点,对权力的行使必须谨慎小心,以此减少引发抵抗的可能性。③而过度依赖暴力的方法显然是“一个软弱政权的标志,在这种政权中,从属阶级(也包括部分统治阶级分子)会认为自己处于不公的境地,并试图改变它”(Lentricchia 308)。因此,更好的方案应该是一种从统治群体到从属群体,人人都觉得当前体制公正合理的局面,即“确保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使用权力的局面在大多数社会成员眼里是无比自然的,或者根本就不让他们意识到”(Eagleton 5)。这就需要非暴力的ISA手段来调节社会矛盾、复制阶级关系。ISA指通过宗教、教育、大众传媒等手段对从属阶层行使隐含的权力。由于这种隐秘性,ISA更为高效和恐怖,没有它的支持与协助,RSA根本无法长期维持社会现状。在《缅甸岁月》中,英国人对印缅殖民地行使权力,不仅利用了警察、军队和刑法制度这些压制性国家机器(RSA),更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这个无形的武器实现了思想上的统治,把一种人为构建出来的劣等民族身份强加到土著头上,并让他们予以认同,从而将自身的优势地位永久化。
“身份”(identity)一词在字面上是“同一”的意思,即将个体视为某个群体成员所依据的一整套行为或个人特点。根据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的观点,所谓“自我”是抽象与空幻的,只有通过与一个坐标点(即“非我”)的不断比照与互动才能实现自我认知,这个对构建自我不可或缺的坐标点即为“他者”。换言之,自我(感知者)与他者(被感知者)并非作为单独的实体孤立存在,而是作为“两个坐标之间的关系存在……彼此进行区分”(Holquist 26)。在种族政治中,身份的建构和区分往往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而是文化和思想意义上的,并且常常伴随着夸大与扭曲,成为“一种用以支持和巩固帝国主义自我界定的产物”(Fanon 292)。正如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43-)所言,既然人们总是通过“我们不是什么”来界定自我身份,那么“我们所不是的”就必然被客体化和妖魔化为“他者”——“疯癫、任性和相异之人被内化为‘他者’,这样有助于我们巩固自己的身份:他们的存在意义,仅仅就是证明既定权力的合理性”(Selden 190)。
欧洲人深知构建一个对立面的形象对自身至关重要,随即将目光对准了东方人。为了把二者区别开来,他们把东方人简化成一种固定的形象,总是跟无知、野蛮、肮脏相关联,以此来衬托自己的种族优越。换言之,在欧洲人身份构建的过程中,东方人失去其真实的身份,被迫变成他们被期待的样子。赛义德(Edward Said,1905-2003)曾提出:“东方是欧洲的文化对手,是其最深刻和最常见的他者形象。此外,东方作为对照性的形象、思想、个性、体验,也有助于界定欧洲(西方)”(Said 297)。不管这种形象正确与否,它“一直是大众的参照系”(Bailey 42)。其结果便是:欧洲人认为自己的优越感乃是理所当然,并希望被殖民者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即有意无意地以欧洲中心观为先决条件)内在化,从而习惯于毁损自己的民族、接受自身的从属地位。
二、不可逾越的身份界限
在《缅甸岁月》中,欧洲人在各方面都强调自身和缅甸土著的区分,因为任何模糊这种区分的行为都会对他们的身份构成潜在的威胁。这让人想起霍米·巴巴(Homi K.Bhabha,1949-)的“模仿人”概念——所谓模仿人,就是深受宗主国文化教化的被殖民者。“他与殖民者越相似,就越容易对殖民权威构成进攻型威胁。殖民话语中模仿人的在场,就是针对殖民权力表征结构的解构”(陶家俊205)。
这种例子遍及整个小说——埃利斯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沙文主义者,此人鄙视缅甸土著,其无礼之言充斥整个故事,如“这个国家暴乱横行就是由于我们对他们太手软了。唯一有效的政策,是把他们当成臭泥”(奥威尔29)。④与这种公然的咒骂相比,书中的一处细节更能体现英国殖民宣传(即把先进文明引入落后国家)的虚伪:在一个骄阳似火的早晨,埃利斯问俱乐部管家还剩有多少冰块。当管家回答“我发现如今保持冰块低温可真够困难的”(I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keep ice cool now)的时候,埃利斯勃然大怒。发火的原因倒不是因为防暑的冰块不足,而是由于土著管家的英语过于标准和文雅:“你他妈的少这么讲话——还什么‘我发现可真够困难的!’难道你刚吞了一本字典不成?‘对不起,主人,冰块冷不了’——这才是你该说的话。哪个家伙英语开始讲得太好了,我们就得让他走人。我可受不了会讲英语的佣人”(23)。在英国人高傲的作态下,是一种潜伏于所有帝国主义者心中的恐惧,这种恐惧导致征服者无法容忍土著的任何才智——虽然从纯语言学的角度讲,英语并不优于其他语言,但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一口文法严谨、措辞文雅的英语,代表着良好的修养和显赫的身份,假如土著变得和他们一样有教养,其“他者性”自然也就不复存在,随之一同消失的自然还有英国人的优越感。因此,殖民者对土著的教化(哪怕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只能有限度地接受。正如阿特金斯所言:“帝国的伟大时代,就是他们带领土著奔向文明之光的岁月,而当这光芒真的就在眼前的时候,却变得不能忍受”(Atkins 72)。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欧洲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故事中的英国人没有几个真正相信教义,但他们又把基督教看做自身与土著之间差异的象征,由此出现了殖民时代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个现象:西方传教士不遗余力地宣扬教义,劝说土著信仰基督,而普通欧洲人则对土著的皈依充满恐惧,害怕由此导致身份上的混乱。在《缅甸岁月》中,埃利斯本是个愤世嫉俗、亵渎神灵之辈,在祈祷时总是用赞美诗集挡着脸低声咒骂上帝,可面对土著信徒的加入,又俨然一副基督教捍卫者的姿态:
“我可受不了那些他妈的土著基督徒挤进咱们的教堂。一帮马德拉西佣人和克伦人教师,还有那两个黄肚皮,弗朗西斯和塞缪尔——他们也自称是基督徒。牧师上一回来咱们这儿的时候,他们俩居然胆敢跑到前排跟白人坐在一起。应该有人出来跟牧师说说才对。我们对那些在缅甸的传教士听之任之,真他妈傻到家了!居然去教那些集市上扫大街的,说他们跟咱们没什么分别。‘抱歉,先生,我是跟主人一样的基督徒啊。’真他妈厚颜无耻。”(23—24)
在埃利斯眼里,东方人就应该维持低劣、野蛮、粗鄙的他者性,他们在任何方面与欧洲人的趋同都会破坏欧洲人用以自我界定的参照系。正因为这样,欧洲人不肯与土著交往,而是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整天在俱乐部打牌饮酒、闲谈漫扯,生活死一般的沉寂和无聊。
主人公弗洛里不同,他对东方文化异常痴迷,十分反感帝国主义统治以及本国同胞对土著的蔑视。虽然他也曾酗酒狎妓、沉沦度日,但是对自身乃至整个大英帝国的堕落却能感到道义上的羞耻,对身边同胞的矫揉造作和无知自大深感嫌恶。因此,他走出俱乐部,与缅甸本土社会建立了广泛联系——他不光同仆人科斯拉以及医生维拉斯瓦米关系密切,还同中国杂货商李晔交好,这些关系同帝国主义理念以及英印地区的种族隔离与等级制度背道而驰。因此在其同胞眼里,弗洛里的言行实属异类,而他跟维拉斯瓦米医生之间的友谊,更是破坏了他本人在白人社区中的种族身份。埃利斯把弗洛里比作美国黑人教育领袖布克·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1856-1915),把他蔑称为“黑鬼的伙伴”,以此将其“他者化”。就连初来乍到、对弗洛里尚有好感的英国女孩伊丽莎白,也对他领着自己到土著社区观看当地的皮威戏感到困惑不解——弗洛里对美好生活尚有企盼,巴望能有一个异性知己来分享自己的感受,去除心中的落寞与孤寂,所以才对初来缅甸的伊丽莎白充满了遐想和期待,可对方根本不欣赏这种蕴藏在原始文化中的美,心里只有惶恐与不安:“她环顾四周,看着这大片的黑色脸庞和可怕的火光;这奇怪的场面令她惊恐。自己在这种地方做什么?毫无疑问,像这样坐在黑人当中、几乎触碰到他们、闻着他们身上的蒜味和汗味,这难道对吗?为什么自己不回俱乐部跟那些白人在一起?为什么他把自己领到这儿,跟这群土著在一起,看这种丑陋野蛮的表演?”(109—110)只有在返回俱乐部以后,伊丽莎白才感到安全和宁静,因为俱乐部那种“温文尔雅”的氛围,还有四周那一张张白人面孔,都能让她倍感安定。
小说还有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就是弗洛里的胎记。虽然在故事中被描述成“暗青色”,⑤但在埃利斯眼里,这个胎记根本就是黑色,——“就我看来,他也有点太布尔什维克了。我可受不了谁成天跟土著混在一起。假如他本人就有黑人血统,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脸上有块黑斑的原因”(32)。根据后殖民理论,肤色是种族政治这一指涉体系中的能指,而所指其实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Klages 153)。与肤色类似,胎记“暴露了弗洛里的他者性,是其非英国性的标志”(Jayasena 245),象征了他对缅甸土著的认同、对种族界限的挑战;而在他自杀身亡后,胎记代表“他者性”和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随之消失,于是也就慢慢褪色,成了一块淡淡的灰斑。
反观遭受殖民统治的土著,帝国主义者人为建构的身份左右了他们的言行与思维,甚至成为某种无意识,以至于他们把这种强加到自己头上的身份看得十分自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借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有关“压抑”(repression)的思想,提出了“政治无意识”的概念,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压制“革命”——不仅压迫者需要政治无意识,被压迫者也同样需要它,假如“革命”没有遭受压制,他们反倒无法承受自身的存在(Selden 115)。也就是说,东方人在有意无意地根据西方人构建的他者形象塑造着自己。在《缅甸岁月》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此人谨言慎行,为人谦和,但极度崇拜欧洲文明,坚信东方人天生比白人低劣,单凭自身无法成就社会进步,而要依靠英国先进的管理技术来拯救这片落后的土地。他那一口句式冗长、极不自然的英文,是当时印缅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跟白人朋友弗洛里的争论中,当对方斥责大英帝国“就是一部为英国人提供贸易垄断的机器”时(39),作为被统治民族一员的维拉斯瓦米却坚定地捍卫大英殖民统治:
“我的朋友,听到您这么说,我感到很可悲,真的很可悲。您说你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没错,这一点不假。缅甸人靠自己会做生意吗?他们能造机器、造轮船、修铁路、修公路吗?没有你们,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在你们手里,林子越来越好。你们的商人开发我国的资源,而你们的官员则出自纯粹的公德心,使我们得以教化,将我们提升到同他们一样的水平。”(39)
由是观之,维拉斯瓦米医生不仅接受了施加在自己民族头上的原型形象,而且以西方文化为模范。实际上,当时有很多这种“黑皮肤、白面具”的中高层印缅知识分子持有类似态度,这自然符合殖民者的利益。
三、俱乐部:种族身份的象征符号
小说中种族区分最显著的例子当属欧洲人俱乐部的排他性。对于驻印英国人而言,俱乐部已不仅仅是一处供娱乐和社交的场所,而是种族身份的象征符号,是白人至上的中心所在:“整个俱乐部概念可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具英国性的事物……尽管别处确实也都有俱乐部,但英国算是最超群的俱乐部之国”(Liebert 67—68)。在这个国家,“凡是人尽可入的地方都不会受到尊敬”(Liebert 68)。因此,英国俱乐部常常限制会员人数,以此体现其卓尔不凡;而在英属印度地区,俱乐部会员资格更是英国人的专属权利,它能大大强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区别:“这种苦心造就出来的俱乐部会员制,其功能就是一方面确保殖民者独特非凡的素质,另一方面则是确保被殖民者永远都是等待被拯救的角色”(Sinha 515)。由于这种种族排他主义,欧洲人俱乐部在当地土著眼中被赋予了一种神秘感甚至是神圣感:
当你看到俱乐部的时候——那是一座破旧的独层木制建筑——你就看到全城的真正中心了。在印度的每座城镇,欧洲人俱乐部都是其精神堡垒,是不列颠权力的真实所在,是土著官员和百万富翁们徒然向往的极乐世界。就这一点而言,此地尤为如此,这是因为,凯奧克他达俱乐部引以为傲之处,就是在全缅甸所有的俱乐部当中,它几乎是唯一一家从不接纳东方人会员的俱乐部。(14)
这家严重排外的白人俱乐部俨然成为“英国人的要塞,守护英国性不受外人侵扰的最后象征”(Jayasena 212);而对于土著来讲,它则代表声誉和权力的觊望,是一处“遥远而又神秘的殿堂,那座比天堂还要难登的至圣之所”(149)。⑥
20世纪20年代,面对亚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狂飙以及紧张的种族关系,驻印英国政府发出一份公函,要求尚无土著会员的俱乐部吸纳至少一名土著。作为全缅甸最后一个抵制土著会员的俱乐部,这一决定自然在凯奥克他达俱乐部引起了一阵骚动。除了弗洛里,所有英国人都极力反对,他们一想到“肚皮大、个头小的黑鬼隔着桥牌桌直往你脸上呼大蒜的臭气”就感到恶心(19)。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因为他们深信:给土著(即使是身处高位者)以会员资格,将无可避免地模糊种族差别,威胁到自己的身份。因此,他们决意捍卫这仅存的公共空间,抵制非欧洲人的介入。
在土著社会中,俱乐部纳新的消息也引发了地方治安官吴波金与维拉斯瓦米医生之间的争斗。医生既是弗洛里的挚友,又是本地职位最高的土著官员,入选的可能性极大。同样垂涎会员资格的吴波金则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代价搞臭医生的名誉。俱乐部会员资格并非正式官衔,为什么这两人还如此不遗余力地争取呢?欧洲俱乐部这种物神崇拜般的价值,部分来自这样一个观念,即“它是英国性的本质所在,因此获得了会员资格就等于融入了大不列颠的内在传统”(Jayasena 212)。换句话说,既然俱乐部已然成为英国性的象征,那么一旦土著得以登堂入室,就等于获得了“准欧洲人”的身份,而这种新身份所起的实际作用要远远胜过一千份公文。因此,当弗洛里不明白维拉斯瓦米医生为什么如此想要加入俱乐部时,医生极力强调其中的“声望”所在:
“我的朋友,这种事情,就是声望决定一切。其实吴波金倒不会公开攻击我,他也没这个胆子;可是他会诬蔑和诽谤我。而他的话有没有人信,完全取决于我在欧洲人中间是个什么样的地位……你根本不知道,一个印度人一旦成为欧洲人俱乐部的会员,他的声望能提高多少。进了俱乐部,你几乎就变成欧洲人了。任何流言蜚语也不能把你怎样。俱乐部会员是神圣不可亵渎的。”(45—46)
医生将俱乐部视为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垒,一旦获得会员资格,自己就会变得不可侵犯,谁也不会相信对他的诋毁。这种“准欧洲人”的身份情结也适用于权力争斗的另一方吴波金。作为凯奥克他达的地方治安官,他已是权重一方,可在他眼里,同俱乐部的会员资格相比,自己一生的其他成就都不值一提:
一个低等官员一路爬进欧洲人俱乐部——这将是真正的伟业——而在凯奥克他达更加如此。欧洲人俱乐部,那座遥远而又神秘的殿堂,那座比天堂还要难登的至圣之所!波金,这个曼德勒的光屁股穷孩子,这个小偷小摸的办事员和无名小吏,将会走进那个庄严的地方,称呼欧洲人为“老伙计”、喝着威士忌和苏打水、在绿桌子上把那些白球敲来敲去!(149)
这番内心独白同维拉斯瓦米医生对弗洛里的倾诉如出一辙。尽管两人在性格和人品上有着天壤之别,但在对俱乐部会员资格的热切渴望上实在别无二致。吴波金的妻子玛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缅甸妇女,她对丈夫不择手段要搞垮维拉斯瓦米医生很是不屑。可即使是她,在听到吴波金提到自己意欲跻身欧洲人俱乐部的宏愿时,也不禁憧憬起来:“她将在脚上套上长筒丝袜和高跟鞋,坐在高高的椅子上,用印度斯坦语同欧洲女士们谈论婴儿衣服。无论是谁想到这番景象都会感觉眩晕的”(149)。思考着欧洲人俱乐部及其包含的荣耀,她平生第一次不带责怪地思量起吴波金的阴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里的最终覆亡同土著人对俱乐部近乎病态的迷恋是分不开的——吴波金对会员资格的贪求,使他必须将支持自己竞争对手的弗洛里除掉;而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维拉斯瓦米医生,对白人俱乐部亦是痴恋不改,最后参加了一家经常有印度律师出入的二流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最大的荣耀便是其唯一的白人会员,此人由于嗜酒如命而被船队公司解雇,如今靠修车过活,日子极不稳定——“迈克道格尔是个乏味的笨蛋,只对威士忌和磁电机感兴趣。可是,医生就是不肯相信一个白人会是傻瓜,几乎每天晚上都试图让他参与进自己所谓的‘文明交谈’中来,可结果总是让人很不满意”(301)。
四、结语
在整部小说中,帝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没有哪个英国人能够完全摆脱影响。弗洛里似乎是一个勇于对抗种族政策的悲剧英雄,但他内心也有着遵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诱惑。他一方面反抗殖民者强加到土著头上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在有意无意地按照“白人老爷”的原型形象(即阳刚、高尚、文明)进行自我塑造。尽管弗洛里一心想要平衡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让土著获得俱乐部会员资格),但他对土著女性的态度却十分符合帝国主义逻辑——弗洛里的性伴侣缅甸女孩马拉美始终以一副客体化和他者化的形象出场,如同一个宠物或玩偶,而非独立的个人:“她那椭圆形的平静脸庞呈鲜铜色,眼睛小小的,很像个洋娃娃,是那种长相奇特却异常漂亮的洋娃娃”(51—52)。“她的牙长得很好,就像小猫的牙一样。她是他两年前花了300卢比从她父母手里买了下来的”(53)。从弗洛里的视角看,马拉美根本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而只是一个养来供自己玩乐的宠物。由此看来,弗洛里虽然在某些政见上同自己的同胞激烈抗争,但实则跟其他英国人没什么本质区别。而整个故事中正面人物的缺场,也揭示出奥威尔的态度,即殖民统治对宗主国的国民思想具有普遍的腐化效应。
由于当时的奥威尔尚未形成系统的政治观点,只有个人道德上的好恶,所以面对帝国主义制度,他并未提出什么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正如兹沃德林所言,《缅甸岁月》“对帝国主义做出了深刻的诊断,却没有指出脱离这个泥沼的路径”(Zwerdling 64)。为了摆脱这种罪恶感,奧威尔离开缅甸后即放弃了皇家警察的体面工作,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与社会底层的劳工、无业者、流浪汉厮混在一起,将自己的关注重点从种族关系转向了阶级关系,以更加敏锐的观察力和更加犀利的笔锋创造出了《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维冈码头之路》等作品,为日后深度挖掘社会权力关系的扛鼎之作《一九八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①1885年12月,英军占领缅甸王国当时的首都曼德勒;1886年1月,缅甸成为印度帝国的一部分,因此本文的“印度”一词也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
②在英占领时期,缅甸是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根据统计数字,1936年缅甸的人均GDP高达776美元,而在脱离英国统治独立后却每况愈下,人均GDP跌到2004年的356美元。数据来源: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C%85%E7%94%B8)。
③福柯在探讨规训手段与社会管理时提出了新权力策略异于旧权力策略的三大标准:(1)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最低的成本代价为基础:就经济而言,意味着尽量降低开支;在政治上,是指权力的行使必须谨慎小心,以减少引发反抗的可能性。(2)权力的影响、强度、作用程度必须不受干扰地实现最大化。(3)权力的“经济”增长要同“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器(教育、军事、工业、医疗)的产出”密切相连(引自Smart 109)。
④原著引文节选自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本(李锋译),以下只标明页码,不再额外注释。
⑤根据Jayasena的观点,从生理学上讲,胎记在白人身上并不多见,作者在这里是想让埃利斯利用胎记来证实弗洛里的他者性(Jayasena 245);而Alok Rai甚至认为,胎记在殖民小说当中是标志反帝国主义的英国人的边缘地位的一个常见手段(Rai 35)。
⑥Historian Valentine Chirol甚至认为,欧洲人俱乐部的这种种族排他性,是造成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原因之一(Sinha 4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