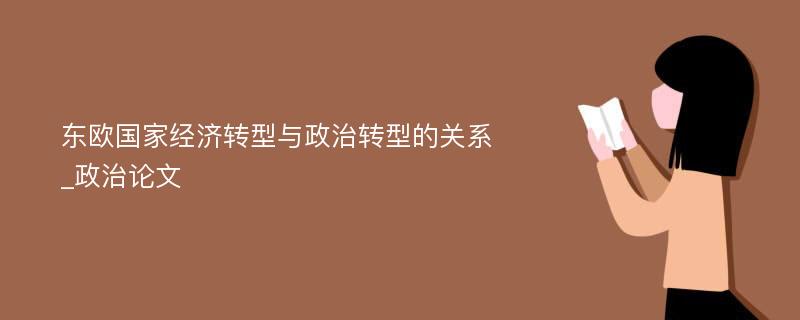
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关系论文,东欧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和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转轨进程(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的转轨基本按先政治,再社会福利政策,再经济结构的顺序进行,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的经济转轨则没有涉及所有权的根本转型,并且这些国家的政治转轨都没有牵涉到国家阶级性质的根本改变。)不同,1989年后的东欧国家经历了政治上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向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由公有制占主体的中央计划经济向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变,同时进行的政治和经济转轨彼此交织,相互作用,构成了东欧舞台上独特的现象,也为我们观察和分析经济转轨和政治转轨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一
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东欧国家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推行经济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作为摆脱困境、发展经济的惟一出路。在它们看来,西方的繁荣得益于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似乎只要实现了“民主化”和“市场化”,就可轻而易举地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如《全球化的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中所写:“民主能承受多少市场?几年前,追问这一问题还显得是多余的。终究是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中,市场经济明显地使更多的人过上了没有太大的物质忧虑的生活。市场加民主,这是胜利者的公式,它最终迫使东方的政党专制不得不就范。”(注:〔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著:《全球化的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10~311页。)的确,“民主”与“市场”之间固然不存在内在冲突,但这并不意味它们在东欧确立的过程始终可以彼此协调,相互促动。实际上,经济和政治转轨的困境时常会阻碍彼此的进程,这也正是双重转轨的困难之所在。
随着经济转轨的展开,东欧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论是采用“休克疗法”的波兰和捷克,还是推行渐进改革的匈牙利,经济都曾一度出现危机,更不用说经济转轨起步较晚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陷于战乱的多数前南斯拉夫国家了。国内生产总值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整个东欧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即使改革后的体制将更为有效,……物质条件的短暂恶化也可能损害民主制或改革进程。”(注:Adam Przeworski,Democracy and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and Latin Ame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37.)而经济重建的紧张甚至对设计得最好的制度也是个挑战,更别说是处于向西方民主体制转轨中的国家了。东欧的政治转轨虽然没有因经济转轨的痛苦代价而出现重大转折,但是,经济转轨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困境还是导致了人们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和政局的波动,这显然不利于政治转轨的顺利进行。
首先,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新上台的反对党或反对派运动由所谓“自由和民主”的斗士变为经济困境的直接责任者。如果说转轨之初,东欧民众由于身受苏联模式之苦对反对派上台,对政治上的改天换地寄予厚望的话,那么随着生活水平的下降,他们对于新上台的当权者产生了怀疑,对所谓的“民主政治”也逐渐变得无可奈何和漠不关心了,这构成了对尚不稳固的政治体制的潜在威胁。
1990年到1992年间在波兰所做的三次调查中,民众对议会下院、政府和部长以及总统的不赞成率呈上升趋势;而在1994年的斯洛伐克,74%和50%的被调查者感到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去影响在国家和地方水平上关于自身利益的重大决策,55%和42%的人不把国民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看作是他们参与政治的途径(注: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26~227.)。同时,选民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也在不断下降。在波兰,1990年总统选举的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中选民的投票率分别为61%和54%,而到了1991年议会选举时,投票率下降到了43.2%,1993年的议会选举,也才得到了52%
的选民的选票(注: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The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7,第78、80、81页。);在斯洛伐克,选民在1990年、1992年和1994年议会选举中的投票率由95.39%降为83%,再降为75.65%(注:1990年和1992年进行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和民族议会的选举,此处为斯洛伐克的单独统计数字。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7,第210、212、213页。);同样,在保加利亚,1990年大国民议会选举的选民投票率为90.6%,而仅1年多后,议会选举中的选民投票率就降到了79.2%,1992年总统选举第一和第二轮的投票率为75.41%和76.02%,直到1994年的议会选举,情况仍未有起色,选民投票率为74%(注:见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Politics,Power,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South-East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369、p.337、p.380、p.390.)。
其次,各国面临的经济困难,乃至经济转轨政策常常成为国内各党派相互攻击的主要内容,从而导致政府频繁更换,甚至政局动荡。
1994年,保加利亚政府因经济改革不力,私有化进程停滞不前引起各党派的攻击,民盟先后6次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社会党也表示,如果政府不能控制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上涨,恢复生产,社会党将取消对它的信任,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政府宣布集体辞职,总统解散了议会,提前进行了大选。政局一直较为稳定的匈牙利因1995年3月12日宣布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出现了剧变5年来最为动荡的局面。1996年年底,处于经济困境中的阿尔巴尼亚因高息集资案的败露引发了全国性的武装暴乱,最终在国际社会斡旋下,才实现了民主党向社会党的权力转换。罗马尼亚1998年乔尔贝亚总理和1999年瓦西里总理的下台也与经济转轨不顺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密切相关。
如果说经济转轨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政治转轨的进行,加剧了政局动荡的话,那么,由于“政府的主要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性的,如税收、国防、教育、能源保护和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和讯息传递、社会保障、经济稳定,以及推动增长”(注:〔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 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8页。),政治转轨的状况又反过来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如《民主转轨和巩固的问题》中所说:“即使以顺序的和合法的方式缩小公共所有权范围(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目标,强大的国家(依据能力)也比弱小的国家执行得更有效。”(注:Juan J.Linz and Alfred Stepan,Problem of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South America,and Post-Communist Europe,The John HopkinsUniversity Press,1996,p.13.)强大的国家和稳定的政治体制有利于推动经济转轨,而处于政治转轨中的东欧国家几乎无法满足这个条件。此时的东欧虽然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实施、共产党的蜕变和执政地位的丧失,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阶级本质,确定了西方式多党议会民主制的发展方向。但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关乎政治体制的重大问题还远未解决,政党五花八门,党派斗争错综复杂,选举制度繁琐混乱,议会和政府频繁更迭,司法机关难以独立,立法与行政关系矛盾重重,政局时有波动,少数国家甚至四分五裂,政治体制和政治局势的不稳构成了政治转轨期内的独特景象。
激烈的党派斗争分散了各党派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纲领、解决严峻经济问题的精力,议会、总统和政府的分歧削弱了行政机关执行经济政策、克服经济危机的能力,频繁的政府更迭、甚至政局动荡更是直接危及经济转轨计划的顺利实行和国家经济的正常运作,使经济一再陷入困境。
1997年年底1998年年初罗马尼亚的政府危机使1998年度财政预算案迟迟得不到通过,乔尔贝亚政府推出的2000年中期发展计划也难以贯彻,国民经济全面滑坡。阿尔巴尼亚原本就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在不时爆发的党派争斗和政治骚乱中屡遭打击,绝大部分工矿企业陷于瘫痪,粮库存粮几近告罄,外来投资减少,债台高筑,经济复苏乏力,远未恢复到剧变前的水平。
而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则多少延缓了经济转轨战略的执行。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前的近两年中,因为其联邦议会基本延续了以前的组织形式,即人民院议员按捷克和斯洛伐克两族居民人数比例产生,捷克占2/3,斯洛伐克占1/3,而民族院议员则基于两个民族的均等原则产生,所以,即使反对激进改革的斯洛伐克议员在人民院中处于少数地位,也可能通过民族院来有效地阻止任何关于经济转轨的联邦立法,这就使得捷克政府所推崇的“休克疗法”的推行由于斯洛伐克的阻挠而变得困难重重。
伴随着战乱频仍的南斯拉夫的分裂,更是严重破坏了除斯洛文尼亚(注: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后,也曾与当时尚存的南联邦间因双方海关官员联合在斯边界行使职权问题发生危机,但在欧共体的调解下,危机很快得以控制,从而保证了斯洛文尼亚的稳定,为其能够在东欧国家的转轨中走在前列创造了有利条件。)外的前南地区4国的经济,打断了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起步的经济转轨。且不说长期受国际制裁的南联盟和马其顿,更不用说历经数年内战的波黑,难以形成并执行系统的经济转轨计划,就是经济恢复稍快的克罗地亚,由于战争造成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许多小的股份持有者不得不把手中的股份退回给私有化基金,其私有化进程的展开也是步履维艰。到1992年6月底,在3619家计划转型的社会所有制企业中,只有119家开始了私有化,而其中仅60%的私有化得以完成,结果,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实际上甚至比转轨前实行社会所有制时还要多(注:转引自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Politics,power,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South-East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90.)。
由上述可见,政治转轨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状况,经济转轨需要协调运转的政治体制和稳定的政治环境,而这恰恰是处于双重转轨之中的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因此,在转轨期内,尤其是在转轨之初,经济危机下的政治转轨和政治动荡中的经济转轨往往加重了彼此的代价,陷于某种恶性循环之中。
二
然而,撇开经济转轨的沉重代价对政治转轨的威胁和政治转轨期内特有的政局动荡对经济转轨的阻碍不谈,单就转轨的基本目标来说,经济上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与政治上的多党议会民主制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冲突。因此,随着双重转轨的推进,随着多党议会民主制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乃至协调运作,经济转轨和政治转轨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上的私有化为多党制提供了日益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的西方式民主制则强化了私有化的选择,部分缓解了经济转轨的消极后果。
与在阶级矛盾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基础上产生政党,“在政党发展的早期阶段”形成多党竞争局面,并使之“制度化”(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7月第1版,第387页。)的西方国家不同,东欧国家的多党制是由当权者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宣布实施的,因而转轨之初林立的政党大多缺乏明确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甚至有些组织,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论坛、斯洛伐克的公众反暴力、保加利亚的民主力量联盟以及斯洛文尼亚的德莫斯等还只是一个在反共的共同目标下由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各不相同的政治势力组成的庞杂的集合体。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私有者作为一个阶层在不断地扩大,社会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结构,在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的驱使下,鱼龙混杂的政党和反对派运动在各国不断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了几个稳定的有固定阶层支持的能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党,为多党制的完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反过来,政治制度性质的根本改变使得东欧国家不约而同地把私有化作为经济转轨的重中之重。在此,私有化已绝不仅仅是经济转轨的一个主要内容,而且更带有浓厚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色彩。也正因为如此,转轨10年来,不论经济转轨的代价如何沉重,不论政党间的权力转换如何频繁,以私有化和市场为核心的经济转轨的根本方针却始终没有动摇,保持了经济政策的一贯性。如,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匈牙利社会党上台后,非但没有改变上届右翼政府制定的私有化方针,反而更加快了私有化的步伐。前者迅速地贯彻了团结工会政府拖了3年没有实行的大众私有化的有关法案,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补偿股份证和大众股份证的发放工作。后者则修改了原有的私有化法,进行了电力、电话、燃料、银行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的私有化,减少了国家准备长期保留的国有资产比重,从而把私有化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同时,西方式民主制的确立还为吸纳和消化经济转轨的负面影响提供了较多的回旋余地。在这一体制下,“总有不需制度变化便可产生替代的社会经济纲领和替代的政府的前景。这意味着最新的民主国家大约有8年的喘息空间——第一届政府4年左右,替代政府4年左右”。一些学者对南美的分析发现:“非民主政权在连续3年负增长中存在的机率为33%,而民主政权的可能性为73%。……没有一个非民主政权在超过3年的连续负增长中存活,而民主政权在4或5年的连续负增长中存活的可能性分别为57%和50%。”(注:Juan J.Linz and Alfred Stepan,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South America,and Post-Communist Europ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79.)在东欧,虽然经济的持续衰退曾一度削弱了人们对当权者的信任和参与政治的热情,但由于上述所谓“喘息空间”的存在,人们似乎可以对转轨的经济和政治结果分别作出判断,他们容忍了恶劣的经济状况,对当权者的不满和对政治的冷漠也没有发展为对整个政治制度的否定。
正是因为经济和政治转轨间越来越多的相互促进,尽管转轨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其根本方向始终没有改变,“在柏林墙倒塌后的5年多时间内,东中欧社会巩固了民主制度并取得了经济增长”(注:David Stark and Laszlo Bruszt,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以私有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和西方式多党议会民主制道路已难以逆转。
三
综上所述,经济和政治转轨困难,带来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越大,它们越有可能相互威胁,彼此拆台。相反,经济和政治转轨进展越顺畅,越趋向于以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和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则越是能够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如某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注:〔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第1版,序第3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注:〔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27页。)。反过来,得到了大多数人认可的政治体制“可以为痛苦的经济重建提供一个有益的缓冲”(注:Juan J.Linz and Alfred Stepan,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South America,and Post-Communist Europ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439.)。因此,在整体趋势上,经济转轨进程和政治转轨进程间往往存在着一致性,也就是说,经济转轨进行得较早、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一般也是政治转轨步伐较大、新的政治体制较为巩固的国家。
事实也是如此。在经济转轨上,从作为向西方式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步骤——私有化的进度以及经济发展速度来看,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中东欧国家明显走在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东南欧国家的前面。
首先,在私有化的进度上,匈牙利早在剧变前的改革中,对所有制的认识就在不断地变化,到1989年则开始抛弃传统的所有制改革观点,主张对国家所有制部门实行私有化,1989年10月,由社会主义工人党演变而来的社会党在其纲领中首次提出实行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任务,并于1990年3月成立了私有化的领导机构——国家财产局;波兰议会于1990年7月13日通过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法》和《设置所有制改造部长职位的法令》,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1990年9月4日公布了经济改革纲要,提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实行私有化的一整套措施,着手改造所有制。而东欧其他几国的经济转轨则显得稍慢一些,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1991年3月12日通过了《关于允许和维护私人经营的法令》,这是阿解放后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允许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罗马尼亚1991年11月颁布的新宪法列入了保护私有化的条款,以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法规和实施细则;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分别于1992年3月20日和4月23日通过了《保加利亚农业土地所有和使用法》和《国有和乡办企业改造及私有化法》,这是其私有化的法律依据。
经过几年的努力,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匈牙利、波兰和捷克的私有化进展最快,比重最高,1993年匈牙利私有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达到了55.6%,1994年波兰和捷克私有部门产值分别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6%和56.3%(注:转引自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33、p.102、p.158.),而1994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这一百分比则只有40.2%和35%(注:转引自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Politics,power,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South-East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391、p.425.)。
其次,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波兰自1992年在东欧第一个摆脱了经济衰退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并于1996年率先超过剧变前的水平,年增长率不仅在东欧,而且在整个欧洲也是名列前茅。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紧随其后,成为开始恢复经济的首批国家。相比之下,保、罗、阿等国经济则由于基础薄弱,投资环境差,资金匮乏而显得恢复乏力,直到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还出现了负增长。前南地区4国受战乱影响,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尚处于复苏起步阶段。
在政治转轨上,如果我们用西方学者所推崇的“两轮转换的考验”,即“在转轨阶段的首次选举中赢得政权的党或团体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失利,把权力让渡给那些选举的赢家,并且后者继而和平地把权力让渡给下一次选举的胜利者”,来衡量所谓“民主制的巩固与否”的话(注:即"two-turnover test",见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ed.),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dl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43.),不难发现,尽管东欧各国大都通过选举,实现了不同政党间的权力转换,但中东欧国家政权的和平交接与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国政党易位的恶性运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东欧国家已基本巩固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在某些东南欧国家仍步履维艰。
在波兰,分属不同政党的8位总理和1位总统都和平地把权力交给了继任者;在匈牙利,分别由右翼的民主论坛和左翼的社会党占多数的两届议会都是在根据宪法任期届满后举行下一次选举以实现权力的转换;捷克左右翼政党的权力交接在平稳有序的条件下举行。但在阿尔巴尼亚,几乎每次议会选举都伴随着丑闻、混乱乃至暴力冲突;南斯拉夫2000年9月的议会和总统选举更是引发了罢工、罢市、罢课等抗议活动,社会一度陷于瘫痪。
当然,对于东欧国家的转轨进程来说,经济转轨和政治转轨相互间不利或有利的影响还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双重转轨的成败还有赖于历史传统、经济基础、民族关系、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