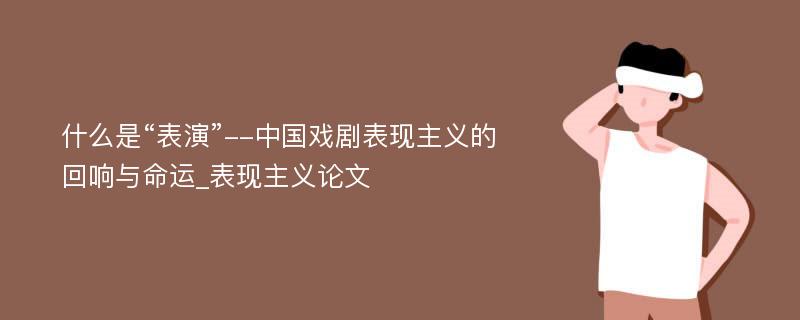
“表现”什么——表现主义在中国剧坛的回响和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坛论文,表现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表现主义戏剧出现于19世纪末而极盛于20世纪初至20年代前后,是西方现代戏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兴起和成为一时潮流是和对现代人的心灵更加深入的探索分不开的。它理论上的依据和推动力可以溯源到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促使人们努力开掘人的深层灵魂,表现主义戏剧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它关注的重心既不是性格的塑造,更不是对外部现实的表现。它要求突破事物的表相揭示其内在本质,更主要的是它要求突破对人物言行的模写而表现其深藏在内部的灵魂,揭示人的精神困境并试图找到精神的归依,追求比人物个性更深层次的原始性的永恒品质。
为达到这种追求,表现主义戏剧运用了各种戏剧手段把人物的潜意识戏剧化,将人物内心无法名状的心理状态与精神困境用戏剧形象表现出来。它借用了象征主义戏剧中的诸多象征手法,使用幻象、梦境、具象化等主观表现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同时往往运用内心独白,在舞台表演上又长于用灯光变幻和扭曲抽象的舞台美术手段达到震撼观众心理的效果。表现主义戏剧的“表现”手法和技巧非常丰富多彩,但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现代人的深藏在内部的灵魂和无法名状的精神困境尽可能形象地表现出来,如果抽去了这一目的而只剩“表现”手法,那么表现主义戏剧就会失去它活的精神和存在的理由。表现主义的戏剧家是先有了探索心灵的需要之后才想到应用各种技巧将其“表现”出来的。
就在表现主义戏剧的盛期,还很幼稚的中国现代剧坛就已有了它的回响。1920年,尤金·奥尼尔的表现主义名作《琼斯皇》在外百老汇公演,造成极大轰动,它对人深层心理和最终归依的探索以其最有力的表现主义手法深深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深受震动的观众中有一位中国学子——洪深。洪深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当时在哈佛师从著名的戏剧教授倍克先生,与奥尼尔是前后相差两年的同学,可谓缘份非浅。他在两年后(1922年)自己创作的剧本《赵阎王》中就采用了《琼斯皇》中的表现主义技巧。
奥尼尔创作出《琼斯皇》和《毛猿》等表现主义名作是很正常的。他是一位探索人类灵魂的最纯正的悲剧作家。他说:“戏剧应该回到古希腊的宏伟壮丽的精神。如果我们没有神祗或英雄可供描写的话,我们有潜意识,潜意识正是所有神诋和英雄的母亲。”(注:转引自刘海平、朱栋森《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20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戏剧中以最大可能的明晰性和最经济的手段——表现人们头脑中那些深藏的冲突。”(注:《奥尼尔评论集》317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奥尼尔之所以写剧本不为名也不为利,他只是要表现他自己(也是所有的现代人)的精神痛苦和危机,他穷其一生在为自己也是人类无可归依的精神寻找一个归宿。他在解释他所写的《发电机》这个剧本时表明了他所感到的人类精神痛苦的根源就是:“老的上帝的死亡和科学与物质主义的失败,它们已经不能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信仰本能提供任何新的支持,来安慰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在我看来任何想在今天完成大作的作家都必须在他们的小说和剧本的具体的主题后面表现出这个大的主题……”(注:Quo-ted in:Poris V.Falk:《Eugene O'veill and the Tragic Tensi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New Brunswick,New Jersey,1958)128页。)奥尼尔在分析他的另一表现主义剧作《毛猿》时说,他所塑造的杨克就是所有人的象征,人已失去了原先与自然界的和谐。他不可能走向未来,因此他企图倒退,这就是他和大猩猩握手的涵义,但倒退到过去,他也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大猩猩杀死了他。奥尼尔强调“这是个古老的题材,过去是,今后也永远是戏剧的唯一题材:人以及人与自己命运的斗争。人以前和神斗争,现在则和自己斗争,和自己的过去斗争以及为试图得到的‘归宿’进行斗争”(注:《奥尼尔评论集》351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琼斯皇》比《毛猿》更集中地运用了表现主义手法,目的也是表现人的深层灵魂和人的精神的最终归宿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只有借助于运用表现主义的技巧才真正深刻而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琼斯在逃入森林之后就开始了向自己的记忆、潜意识直至种族无意识的追溯和回归。奥尼尔前后安排了六个场景来展现这个层层深入的过程。在前三场中,琼斯在幻象中看到他杀死的黑人杰夫,重新加入黑人囚犯的行列,受到白人狱卒的虐待。这是琼斯退入自己个人的记忆中,揭示了他个人的精神状态。而在后三场幻景中,他则逐渐深入了他的种族的无意识中,揭示了琼斯作为一个黑人,一个人所无法抹去的种族记忆。在黑暗的丛林中,在他同样黑暗莫测的精神世界中,他逐渐被剥去了外在的“文明”的伪装,逐渐向种族最深层的无意识回归。笼罩这整个一幕的最咚咚的非洲手鼓声,这是黑人举行宗教仪式用来召唤象征着自己种族精神的神祗的,作为黑人的琼斯与这有魔力的代表种族宗教仪式的鼓声有血缘般密切的精神联系。鼓声的时疾时徐象征了琼斯的精神状态,迫使他引导他走向种族无意识。在这渐渐加速的鼓声中琼斯一身花哨的制服一件件被剥落,最后只剩下一块围腰布,这正象征着他的“超我”、“自我”的被剥离,逐渐走向最原始的“本我”。他在幻境中经历了他的祖先被贩卖的过程,最后回到了他的种族祭坛,在一位刚果老巫医的召唤下不由自主地爬向一条张着大口的鳄鱼,要得到拯救就必须成为祭品。在最后一刹那他将那最后一颗子弹射出,杀死的却是他自己。他回不去了,他不可能得到救赎。
作为中国剧坛的先驱者之一的洪深,在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戏剧事业之时是抱定了要通过戏剧来反映、干预、感化社会人生的理想的。他解释胡适提倡西洋戏剧的目的“是要想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这可以说是第一代戏剧家的共同理想追求,他们学习、接受西方戏剧也是从这个方面这个角度来理解接受的。有代表性的如郁达夫在《戏剧论》中就把无论易卜生,还是表现主义大师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等都理解为只是表现态度不同而表现的精神都是一致的,是“近代剧所共有的精神:咒诅现代的社会组织,表同情于孤苦无告的被虐阶级,高倡博爱同胞的人道主义,带有革命的民主的色彩的”(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这种理解无论如何是欠妥的,而洪深在自己的创作中所坚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目的。所以他与奥尼尔无论在最基本的人生观、艺术观,还是美学追求上都是有极大的不同的。他的用力在于对社会现实层面的表现上,是把戏剧作为“感化人生的工具”(注:洪深《戏剧的人生》,《洪深文集》第1卷41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的,还谈不上对人物深层心理的把握。实际上不单是洪深,这个时期的戏剧创作根本还没达到有意识地开掘人物深层灵魂的阶段。洪深所表现的领域是外在的、社会的,整个还停留在社会剧的阶段。从他早年的试笔《卖梨人》到成名作《贫民惨剧》,中经《赵阎王》直到其代表作《农村三部曲》,这种追求一以贯之。
洪深自述:“《赵阎王》的企图是想说明‘社会对于个人的罪恶应负责任’”(注:《〈洪深选集〉自序》,《洪深文集》第1卷490页。),“我把许多人的遭受,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以见从一九二二年上溯三四十年的社会充满着多样的黑暗,自然会得造成《赵阎王》这类的罪恶者的。”(注:《〈洪深选集〉自序》,《洪深文集》第1卷491页。)
可是这样的题材、主题,洪深却以表现主义的手法出之。很明显,《赵阎王》几乎是完全套用了《琼斯皇》中的表现主义技巧。文学创作中的影响和接受影响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不能用是否接受了前人或旁人的影响来评判创作价值的高低,而是要看接受者是在什么层次上接受影响的,是否溶入了自己创作的血肉。技巧、表现手法的借鉴尤其要考虑到所借鉴的表现手法与自己所要表达的主题和创作思想的结合能否达到必然的程度。严格说来,《赵阎王》中借用的表现主义技巧就没能达到这样的高度。表现主义技巧在洪深手里不是用来表现人深藏的、不用表现主义技巧就很难表达的精神冲突和灵魂真相,而只是成为他借以展现黑暗现实的一个方便的工具。这种层次上的现实是不必一定要使用表现主义技巧才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的。
洪深通过赵大的六次幻觉,依次展现了三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如军阀活埋战俘,官兵烧杀掳掠,官员残害百姓,甚至追溯到洋人对中国百姓的压榨,洪深在追溯黑暗和压迫的根源。这六场幻觉尽管对应了琼斯越来越深的对于种族无意识的追溯中体现出来的时间顺序,却依然只是在表层意义上搬演中国历史的黑暗和苦难。赵大成为洪深意图的单纯的传“画”筒。作者关心的不在于个人,他既不关心性格(虽然作者明确点出赵大是什么样的人,但在剧中却始终非常模糊),更不关心深层心理的挖掘。表现主义技巧与仅是浅层次地暴露现实的剧作主题无法融为一体,成为必然的结合。这不但使形式与内容产生一种不协调的后果而且必然地,单就形式——表现主义技巧的应用而言也产生了不自然的弊病。如:在最后一场幻觉中对应种族祭坛、刚果老巫医而出现的是天兵天将,种族祭坛代表了琼斯作为黑人种族记忆中最原始的宗教本能,而天兵天将则显得荒诞无稽。更重要的是对鼓声的应用,《琼斯皇》中的鼓声是另一个主角,它时快时慢的节奏象征了琼斯的精神状态,是因为它与琼斯的精神和灵魂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它成为剧中最有力的表现主义技巧。而《赵阎王》中袭用的军鼓声因为与赵大根本不存在密切的精神联系,故根本不可能成为形象的表现手段。
洪深本人对自己要“表现”什么有明确的认识。在1933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欧尼尔与洪深——一度想象的对话》的文章为自己辩护并再次声明自己的创作观。他用欧(奥)尼尔取材《俄瑞斯忒亚》三部曲的《悲悼》是创作而非模仿来比拟自己借用《琼斯皇》的技巧写《赵阎王》并非抄袭,并借奥尼尔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戏剧观:“一出戏最主要的,是中心思想;就是那作者阅历了人生,受了人事的刺激,所发生的对于社会的一个主张、一个见解、一个哲学;简单地讲,就是他对于大众要说的一句话。……他说的这句话,必须是正确的,是能改进社会的,这戏才算有价值。”(注:《洪深研究专集》20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剧作家,洪深有自己一以贯之的创作观。他虽然袭用了奥尼尔的技巧,他所说的那“一句话”的确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这种借用除了展现了社会现实之外,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赵大的人性所受到的摧残。只是作者用意原不在此,至使这种内在的揭示仍仅仅停留在社会学层次上,在极大程度上只成为一种表现社会的工具。所以整个剧本衡量起来,表现主义形式与社会学内容的结合无法达到必然的程度。
在洪深应用表现主义技巧创作《赵阎王》二十多年之后(注:继洪深的《赵阎王》之后,伯颜于1923年创作的《宋江》、谷剑尘于1929年创作的《绅董》均是明显借鉴《琼斯皇》的表现技巧的作品。参见刘珏《奥尼尔在中国》,《中国话剧研究》1991年第3期。),曹禺在《原野》中再次应用了表现主义技巧。
曹禺自述《雷雨》的创作时说:“《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了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注: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21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原野》的创作也源于这种冲动和憧憬。我觉得,《原野》和《雷雨》是最能反映曹禺的本真的两部剧作,相比之下,《日出》和《北京人》都有特意的面对现实、反映社会本质的追求,而在《雷雨》和《原野》中,曹禺似乎只面向自己的心灵。
《原野》是反伦理反文明的,它是一首人的生命力的颂歌又是哀叹,它是对道德和秩序的反抗,它凭借的力量就是人的原始生命力和渴求自由的欲望。但人在自我肯定的生命追求中就已包含了自我否定的因子,一切的悲剧冲突实质上都是自我灵魂深处的冲突。奥尼尔说得好:“当灵魂进入躯体时,悲剧也随之进来了。”人的自身是“已写成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注:《奥尼尔戏剧理论选择》,见《外国当代剧作选》(一)747-74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人永远在追求自由同时又永远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从自我肯定到自我否定,从生命的自我张扬到生命的无可奈何的自觉毁弃,人一直在寻找精神的归宿又一直无处归依。这些最为矛盾极端的冲突和痛苦就存在于人的精神内部。这是永恒的悲剧。
《原野》就是这样的悲剧。为了形象而深刻地表现出人深藏内部的灵魂,曹禺应用了表现主义技巧。
因此我不同意传统的认为《原野》的主题是写农民觉醒复仇的看法,也不同意认为《原野》的表现方法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表现主义只是点缀的观点。我认为《原野》在根本精神上就是表现主义的:《原野》中事件的发生是在没有时间、地域性的神秘而野性的原野和黑森林,人物是象征了野性生命力的仇虎、花金子,狠毒的焦母、忠厚软弱的大星、昏庸的常伍和痴呆的白傻子。人物的这种极端的个性本身就是经过表现主义符号化了的。而通过这些极端化了的人物,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带有普遍性、深刻的灵魂悲剧。仇虎不单是个农民,就象《毛猿》中的杨克不单是个工人,他是个人,作者借他要表现、挖掘人的精神状态和最深层的带有普遍性的精神冲突。作者同时又集中运用了表现主义技巧来“表现”。从整个剧作的轻重布局来看,前两幕的复仇故事只是为了在第三幕中形象地展现仇虎最深层的精神冲突作一个铺垫,整个剧作的中心就是第三幕。如果《原野》没有了集中应用表现主义技巧展现灵魂的第三幕,那么《原野》本身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曹禺也根本不会写这么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
第二幕结束的时候,仇虎表面上已完成了复仇的愿望,可是他的精神状态却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他杀死的不是恶贯满盈的焦阎王,而是无辜的大星和小黑子。在复仇的过程中他的内心冲突就极为激烈,在完成之后他就已经开始自我否定了。他与焦母已完成了角色转换:焦母已成了可怖的复仇女神而他则成了自感罪孽深重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的俄瑞斯忒斯。
第三幕集中使用表现主义技巧就是要把这种心灵的斗争、精神的压力和最后的崩溃这些不可名状的心理状态以最清晰的方式展现出来。焦母的叫魂声、诅咒声、为黑子招魂的鼓声、木鱼声、红灯笼,以及后来的“妓女告状”的歌声等等都对仇虎的精神造成不可承受的压力,他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幻觉,这些幻觉清楚地展现出他的精神状态。他逃不出这个黑森林,这个黑森林就是他自选的心狱,他不是撇不下一个瞎老太婆的追赶,而是逃不脱自己对自己无可奈何的毁弃。虽然他的自由意志仍在挣扎着为自己辩护,他在金子的提醒下看到了屈死的爹爹和妹子,但很明显,他的肯定的力量已不再占优势。叫魂声和招魂的鼓声代表着焦母(复仇女神、永恒秩序的惩罚)与他自己灵魂中的自毁自弃的力量一起一直追索着仇虎的灵魂。在最终逃出黑森林之后,他迎面碰上的就是他曾经丢掉过的脚镣,他无处可逃,只有开枪自杀。
曹禺应用表现主义技巧揭示人类精神最隐秘的内幕和最激烈的冲突,并不比《琼斯皇》昭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的成就逊色,而且也用得非常自然。第三幕中每一个幻景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外部刺激之后潜意识的自然联想和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琼斯的幻景虽本身有逐步向深层种族潜意识掘进的发展逻辑,但就各幻景而言却并没有必然联系,相比反而显得突兀。《原野》中鼓声、枪声源自《琼斯皇》,但作者又加入许多音响、灯光等表现手段,叫魂声、“妓女告状”的歌声、红灯笼等都有对仇虎的精神产生作用的力量,其综合之后对仇虎精神的作用显得更大更丰富。而且鼓声也不是生搬,招魂的鼓声时刻提醒仇虎的犯罪感,象征了焦母本人紧追不舍,它与仇虎的精神有极为密切的血缘联系。为了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曹禺还安排了金子与仇虎一块儿逃亡,她可以起到见证、提醒、外部刺激物的多重作用。曹禺说:“至于那些人形,我再三申诉,并不是鬼。为着表明这是仇虎的幻想,我利用了第二人,花氏在他身旁。除了她在森林里的恐惧,她是一点也未觉出那些幻想的存在的。”(注:曹禺《〈原野〉附记》,《曹禺文集》第1卷683页。)
曹禺所要表现的人的最激烈的精神冲突和心灵悲剧与他应用的表现主义手法是完全契合的,而且表现主义技巧本身的技巧应用也极为贴切自然。曹禺一直都不承认自己是有意借用《琼斯皇》的技巧,实际即使是有意借用也无损《原野》的成就:表现主义技巧与剧作精神如此完美地溶为一体,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已达到了真正必然的程度,即使是借用也是已溶入了自己血肉的成功的再创造。
尽管表现主义在中国现当代剧坛都不乏应用的例子,但总体看来并不容乐观。大部分剧作家应用表现主义手法是源于纯粹的技巧方面的诱惑。中国话剧的历史只有短短几十年,而且由于社会大环境、民族心理的限制,现当代剧坛的创作走的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路子,强调的是对外部社会现实的描写和表现。总体来说连人物性格的塑造都还不能完全让人满意,更遑论对人物深层心理的开掘了。少数剧作家虽也致力于人物内部的表现,但总体说来也多嫌深度不够。 当代剧坛中有些剧作也运用了表现主义的技巧,如王培公的《W·M》中使用了一些表现主义的道具、服装和灯光等,而且某些段落用表现主义的手法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形象地表演了出来,如:将军愤于板车的堕落,剧中让将军在幻觉中拿起鞭子狠狠地抽打板车,李江山在悔恨中又看到自己醉醺醺走向堕落的身影,白雪实际上看到了她正在思念的将军等。但这些心理变化都是非常浅层次的,是不必一定要用表现主义手法就能很好地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部剧作运用表现主义也止于片断,整个剧本的精神就不是表现主义的。
高行健的剧作勇于尝试各种技巧,他的名作《绝对信号》中应用最多的戏剧技巧就是表现主义手法,而且这部剧作基本上就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如果抽去表现主义的段落,整个剧本就会坍塌。剧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借表现主义手法表现出各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采用的表现主义技巧的手段也很丰富,音响(列车的节奏)、灯光、独白旁白运用得都颇为成功。但是通篇所要表现的人物的心理动作也是比较浅层次的,这是问题的最大所在,剧作不过是把以前需要借助外部动作才能让观众感受到的人物的内心活动让人物干脆表演出来,让观众直接看到。而表现主义绝不应该只起到这种作用。它应当用来形象地表现那些隐藏最深的心理状态和深层灵魂。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现当代剧坛对于表现主义的接受大多止于技巧的借鉴,而忽略了或者说还没充分地有意识地去开掘它要“表现”的最根本的精神。其根本原因是大部分剧作家还没达到有意识地深挖人物灵魂的阶段。唯一一部可视为成功的表现主义剧作《原野》又一直被当作社会剧来理解和领受赞扬。总体来说,表现主义在中国剧坛的命运是孤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