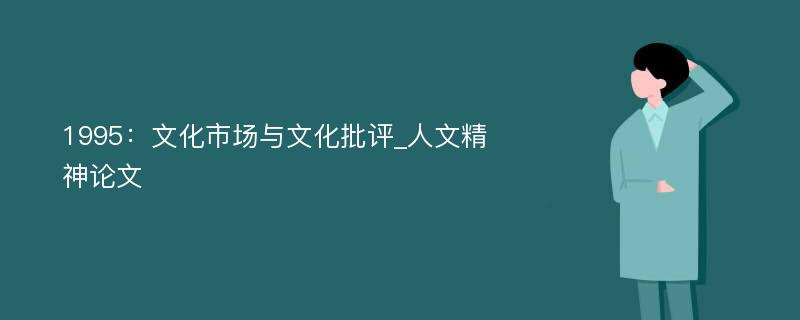
1995:文化市场与文化批评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市场论文,批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在于市场机制的合理化与规范化
按照已往的习惯,新闻界一定会用足球年和电影年来概括1995年的文化景观,这两个在去年盛况不绝的事件主题,使我们对去年的描述要从文化市场的层面开始,原因当然也很简单,足球和电影都是最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消费形式。
几年前,中国人以高昂的价格买下一件欧美名牌服装,以期获得所谓与世界市场同步的物质消费享受;今年,几乎能够同时观赏到在世界电影市场上放映的商业巨片,使中国人开始了他们与世界市场同步的文化产品消费,虽然这仅仅是差不多“同步”。95年的进口片基本都是94年左右在美国极为上座的影片,十部的数目也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它将持续——可以确知的是,11月初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影公司和国际电影发行商所达成的交易无疑将继续为中国观众引进更新乃至更多的新片。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在电视台和地摊报纸上初识了“全球共享文明时代”这个概念,想必不久便能够心领神会,应用自如。
助长这一“时代感”的另一个相关事实是,1995年欧美流行乐队罗克塞特、空气补给、平克·佛洛伊德在北京舞台上成功地上演,使中国观众领略了世界当代流行音乐的风采,使某些记者惊呼欧美风又要刮过来了。而今年克莱德曼音乐会的惨状,确确实实证明了中国乐迷们的一种“进步”。
在进口大片激活了电影市场、把观众重新带回电影院的同时,95年《红粉》、《红樱桃》、《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在国内市场发行成功及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也为国产艺术片插上了几面小红旗。虽然94到95年之初,电影界还普遍地为中国电影滑向最低谷而悲哀,且95国产片的这番“红”运其实远未把中国电影带出低谷,仅仅是票房集中在几部影片上而已,但足以重新唤起希望。
同样令人产生希望的另一些相关事实是,1995年在政府支持及民间赞助下,国内各大乐团继续举办交响音乐会及民族音乐会,市场行情持续看好,而国外交响乐团来华也创音乐厅有史来的票房记录,其实不止于严肃音乐,加上芭蕾舞等项,几乎都可以看到一幅严肃艺术抬头的风景。当然,这也不足以改变近年来严肃艺术的悲哀,不过微妙地说明了,文化市场其实潜藏着多种可能的前景。
正由于这样一些市场活跃的迹象,使中国文化市场的走向,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一方面,必须摸着跳动的脉搏继续走下去,把握抬头的契机及多样的可能;另一方面,已经显露出的诸种问题前所未有地纠缠在一起,使1995年的文化经营倍感含辛茹苦。
95报刊上耐人回味地唱着“……为什么这样红?”,它被称为“中国电影市场成熟的前奏曲”——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成熟”呢?
的确,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类似于95年春节《红番区》在中港台三地电影院内同一天首映的事情,会不断地、甚至更大规模地重复搬演。十几年来合拍电影的扩大增强,似乎已经把华人华语范围内的制片发行融为一体即汉文化圈电影业出现的前景展现在眼前。与之相伴的是,进口片的引进,以及在此之前发生的、第五代导演制造的“东方奇观”在西方的票房效应,已经引起西方资本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意图,它亦打开了中国电影在海外发行、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另一种前景。实际上,今年国内最具实力的中影公司已经开始了他们把国产片推向海外的步骤。两种前景都有引人入胜之处,也都有令人焦虑的距离,前者要本土的经济实力,后者要面临跨国资本的压力和世界市场的竞争,而无论任何一种前景的出现都把中国电影市场的成形与规范提到了紧迫的日程上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批的社会投资涌向电影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金匮乏的问题,然而有关融资的一系列法规有待健全,制片方式也有待变革,95年来自境内境外的独立制片的呼声比已往更高。
当然,要想解决资金问题,前要有社会投资,后要有制片业的回报,因此95年由于部分国产片发行的成功使发行与放映业的规范整合成为更关键的问题,同时也把影片质量的问题放到了首位。目前,政府对进口片的发行及合拍片所进行的限制性管理,使电影业处在一个不完全开放的瓶颈式市场,两难之处在于,这既是保护民族电影的一线屏障也在约束着某些扩大生存领域的希望,而想要在瓶颈处即保护自己的市场利益前提下实现市场良性循环机制,电影人还要作艰苦的努力。
制作质量与市场规范,也是流行音乐界的关键问题。签约包装还没有热过一年已是解约如潮,95年歌手跳槽的事件接连不断,“养大的孩子不认娘”被人看成95歌坛的一大风景。人们往往只看到表面上的职业道德问题,却不能理解这其实是市场行为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就象江珊史可事件背后的、国家剧院与独立制作人之间在票房分帐上的矛盾冲突也被人们所忽视一样。毁约不仅表明人们的市场行为还不够规范,更表明已往的包装意识和操作方法遇到了挫折,以为只要包装好就可以卖出去,是过于简单也过于虚幻的。人们普遍认为被包装出台的94新生代群体在95年的表现足以说明他们缺乏实力派素质。他们的制作人,虽然被人认为是掌握媒体、操纵市场的文化大腕,他们“玩”文化,却不观照市场或依据盲目的市场通理,过分相信人造气候,过分依赖文化的自我调节机制去调节时尚风向,蔑视商业性的结果是使制作业处在赔本生意的恶性循环中。著名音乐人苏越因亏损而被解职是95年震动歌坛的新闻,也是一个最好的警告。95歌坛,虽然国产MTV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海外,“现代新民歌”酿成热浪,甚至有《阿姐鼓》——我国第一张走向世界的CD,但总的说来,不复有94年都市民谣、校园民谣、摇滚乐竞相摇曳的辉煌,基本是反响平平。95年制作业鉴于歌迷们既厌倦老歌星又不认新歌手的心态和专辑越作越滥的状况,普遍采取了以单打曲试探市场的谨慎态度,多少表明了他们的某些共识。95年是政府强化打击盗版的一年,然而大陆原创歌曲的购买力还是远远低于欧美原版音乐带,除了在市场研究中摸着石头过河之外,更关键的问题还是解决市场机制的合理化与规范化,以及提高流行音乐的产品质量。
95年的电视,历史剧仍旧是一个主流,《三国演义》、《武则天》之后,还有《水浒》、《东周列国》、《大秦帝国》等等处于制作和待播之中。可喜的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都市剧增多,但制作水平最佳的还是电视连续剧《孽债》。
今年的电视论谈节目大大增多,广泛涉及当代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多以专家、行家为主,构成95屏幕引人注目的特色。
另外,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电视台及上海电视台等出现了把正在播映却收视率不高的电视剧拨出黄金时段甚至停播的个别情况,这对于提高电视剧的制作质量当然是一有力的举措。
为了迎接世界妇女大会,影视方面的妇女题材增多,女作家的作品也成套出版,人们忽然发现在不知不觉中,当代的女性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的梯队阵营,从一般的历史进程而言,女性写作的传统被认为是零散的和不连贯的,因此这种前所未有的、整齐的队营,确实耐人寻味,值得批评家重视研究。
另外,学术著作与严肃刊物的发行量在95年有所增长,但愿并非事出偶然。《顾准文集》的出版是思想学术界的重要事件,已引起广泛的影响。除此而外,95年文坛比较平淡,没有新旗号也没有轰动的作品。也许可以说,没什么比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廊桥遗梦》更显风流的了。
争论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明确语境
自93年末开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持续到95年似乎进入白热化阶段,批评之激烈与创作之低温之间有着令人不适应的温差。截止到94年底,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遇到强大的质疑,虽然提倡人文关怀作为一种富于良知和渴望建设的声音引起普遍的同情和理解,但有关它的“失落”的话语前提及概念内涵却须经受历史及学理的仔细推敲:它不等于人文学科,如果仅仅是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可能还好说,多数参与讨论的人把这种边缘化看作学术独立的契机与条件;也不能视作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它只是到上世纪末才影响到中国,在一百年的历史中它始终是若隐若现的,也是变化百样的,因此谈不上真有也就谈不上失落;它亦不能视作中国古代的文人传统,除非我们将它作现代化的处理,简单地认定它的现实意义是值得怀疑的态度;那么,除此而外,它还能是什么?恐怕正是因为这种空洞的被披露,人文精神的讨论很可以被说成“当代最大的神话”,也导致“杂语时代”或“共识破裂”的结论。因此并不奇怪,95年讨论的中心已移到所谓道德理想主义的话题上,如果说94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其话语的重音多敲在精神颓唐与价值失落上的话,95年的强音则是文化与社会批判。如果把时间拉得长一点,我们更可以看出这一移动是90年代以来学术思想界重大争论的内力外延的必然结果,虽然建立学术规范与重建学术传统的意向贯穿始终,但却一步步地脱离所谓书斋本位而深入现实:
91—93年,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基本上是转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而这一反省基本更多的还是针对整个80年代的文化策略及其在现代历史中的根源;同时在学术上基本强调了研究方法上的规范,批判的是已往空疏浮泛的学风。从整体情势看来,知识分子在转型的现实面前,大致采取了一种重新省思自己的位置,退守书斋的姿态。
93—94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批判主要针对的是90年代在市场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动摇、困惑,以及退却、背叛,但更多的还是讨论如何面对价值失落、文化失范,如何寻找精神的支点;比之先前,它更强调的是学人如果没有自己可依赖的学统,没有一种延续性的精神传统,学术活动必然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陷于失语的混乱和精神的坍塌;因此,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虽然没有形成一个“鲜亮的思想中心”,确实反映出话语的分歧,但仍旧在争论中达到了某种实际上的清理门户。尤其当我们避开争论焦点的吸引,注意到整个波及面时,不难发现,94年最大收获乃是于争论不下的状态里辨明了双方各自的话语前提,关于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不消说坚守岗位的人,就是走出岗位的人也是冷暖自知,而带来这一处境的内外因素到底哪个起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面对这场并未有几处真正交锋的争论,确实有意义的乃是在话说出来了以后看清楚了自己话语的来源归属。94年的所有话语仍旧没有逃出现代性这个大的范畴,换而言之,80年代以来中西两大话语谱系,向来被认为分界对立的,而现在本土问题就好象是一个坩锅,里面溶炼的是来自东西方各种谱系的话语片断。矛盾内化,是忧也是喜,从表面或近前的意义上看,它悲剧性地显示了话语的杂乱与共识的破灭,但从内在的或长远地看,内讧不仅使情绪外化宣泄从而引向对话沟通,也从话语前提的清明走向学术的规范。94—95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最重要的收获应是从中确认我们的研究课题并进一步明确谈话的环境,坩锅当然是令人沮丧的混乱,但还是应该看到,熔炼它们的正是一股解决本土问题的现实热情。
95年,说它延续94年的话题似乎不太确切,从“人文精神”这个中心词到“道德理想主义”这个中心词,针对性已对准商业化的社会本身,在很大程度包括了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行为及心态,已有几分“一致对外”的架式,而且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所谓“道德优先性原则”,由质询和怀疑转入批判和进攻,离90年代学人主要的学术自省立场已经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种态势或这种描述的形成,在很大程度带有传媒造势的虚构与虚假,显然作为中心的二张(张承志、张炜),其言论均出现在95年以前。客观地讲,95年出现几个话题并举的局面。其一,是再次回到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这个中心,新的共识在于本土化不再局限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这个单一的背景,而是被理解为跨越国界和族属的全球化过程,从而为本土化确立了一个普遍主义的背景(见《中国书评》等杂志);其二,是文学理想主义的讨论,它通过对文学的本性是作为一种理想话语形式的肯定,而强调写作的专业精神。应该说它是针对人文精神的前提之一,即文化产品的创作与批评失范与失控而来的(见《中华读书报》、《文艺争鸣》等杂志),因而有着把讨论引向具体现实的切实意义;其三,既是94话题的综合深入,如王蒙等人在《读书》上“精神家园何妨共建”的谈话,也是针对性继续质询,如陶东风、李辉及王蒙在《读书》和《东方》等刊上发表的文章,其质疑的中心在于道德理想主义在现实语境中的误区及历史语境上的醒示。
有一个并非始自95年但却是在95年引起越来越广泛关注的话题,那就是有时候被人笼统称为民族主义的问题。其实,被归于这一标题下的诸多观念有着很不相同的学理背景和社会、文化乃至心理根源,很难一概而论。
不过,在95年比较集中地引起注意的一个论点是,由于“中国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的特殊性,不仅使得西方学术理论不足以解释之,从而提供了构建本土学术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且有可能使中国摆脱西方发展模式,从而以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为世界提供一个被称为“中国现代性”的模式。与这个论点相辅相成的则是对西方近现代文明或“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人们把这个论点与“民族主义”挂钩,大约是因为它显然有意于强调民族认同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反抗西方文化霸权的倾向。当然,这个论点所提出的问题恐怕比它所想解答的问题要多得多。可以预见,在1996年它将引起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
简短的结语:创作之流何在?
’95文化景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卡”在了“市场”上,当文化经营者面对依旧混乱的市场艰难地寻找着一条清晰的道路时,文化批评的领域里却高扬着批判市场化的大旗。’95文化市场的综述,多少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直接影响着文化制作的萎缩,而对95文化思潮的评述却可以得出精神失落导致创作疲软,不过这并不是什么针锋相对的话题,只是在各自的圈子内唱着各自的调子罢了。
于是,’95景观很象一出双城记,很难找到产品或作品的主体位置,在双方的城头上望去,都看不见夹在两城之间的河,那是经过我们身边的创作之流。产品与作品的稀少,是否意味着创造力的缺乏?抑或只是因为进入市场有障碍和批评的视野有所疏漏?尽管可以认为这样一幅图景是本文的叙事策略,但毕竟在这样一个重构的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已往的文化叙事是在文化精神、文化产品、文化市场三者缺了后一者的情况下进行它的描述的。如果我们不否认我们所从事的是现代文化的批判,那么没有文化市场呈现于其中的文化批判就是一个有逻辑缺陷的批判,而这样文化建设就仿佛是在建一个比萨斜塔,它不会倒塌就如同什么人文精神都不会失落一样,却永远斜着,也永远叫人紧张,它对我们目光的吸引力使我们无暇四顾广阔的地平线。仅以此作95文化景观描述的、并不幽默的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