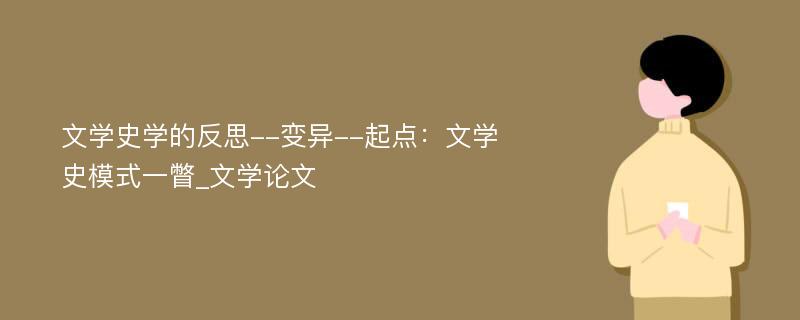
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变异——起点:文学史模式回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文学史论文,起点论文,模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研究者已指出,本世纪前七、八十年间所用的基本上是“他律”的文学史模式,只注重文学外部条件,而忽视了“心灵史”,忽视文学形式的内部动因等等。有人将这种他律型的文学史模式称为“诗——史范式”。笔者颇有同感。然而,传承中总有变异。从众多文学史著作中寻找并归纳出特殊的东西,也就是发现变异的种子,它或许可能成为我们新的起点。就以闻一多对文学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大略说来也还是“以史证诗”的类型,但是所重在文化,而且似乎也并不忽视心灵史。闻一多研究中国文学史是将其放在世界文明史中来考察的,所以有一个庞大的规划,可惜过早地被夺去生命,我们只看到这一规划的初级阶段。但仅从这露出地面的基础工程,便可窥见一些超越传统的倾向。让我们一瞥这一可贵的变异。
闻一多首先重视的是在文化视角下文学环境的复原工作。他在《匡斋尺牍》中提醒我们:“你该记得《诗经》的作者是生在起码二千五百年以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自己的心理去读《诗经》,行吗?”“你如何能摆开你的主见,去悟入那完全和你生疏的‘诗人’的心理!”恢复文学环境的目的还是为了沟通古今那差异极大的审美心理结构。这种方式不但用于鉴赏,还用于“知人论世”。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与《杜甫》(片断)为我们留下了如何由恢复文学环境进而悟入诗人心理的轨迹。傅璇琮《国学今论·闻一多与唐诗研究》曾指出《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眼光的非同一般”说,“宋代以来,为杜甫作年谱者不下几十家,但都没有像闻先生那样,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的确,《年谱》不但辑入政治背景,还辑入音乐、绘画、宗教等资料。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资料,他尽量恢复杜甫当时所处的文化环境,由此推断人的性格与诗心。所以我们在《杜甫》中看到那些资料复活了!看到杜甫四岁时骑在爸爸肩上看著名的艺人公孙大娘舞剑器;我们还看到杜预、杜审言、杜升、崔行芳,还有杜甫的姑母,这些血亲如何用血性铸造着杜甫那高傲的性格,如何影响着他那刚健诗风的形成。于是我们对杜诗中凤凰的意象,对“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的诗句,有了更亲切的感受。再如《唐诗杂论·孟浩然》一文中,闻一多极力描绘襄阳的人杰地灵,为的是表明孟浩然向往家乡先贤的心理,“是襄阳的历史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从而将隐居提升为规律来认识,因为在士大夫生活中,“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闻一多文学史观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将审美趣味与生活方式联系起来。闻一多因此而意识到以王维为代表的田园山水诗派的意义。他认为此派之风格与六朝贵族诗是一脉相承的。就在那种生活里,诗律、骈文、文艺批评、书画等等,才可能相继或并时产生出来。要没有那时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条件,谁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创造出这些丰富多彩的文艺成绩?他进而指出: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后代中国人对诗的观念大半以此为标准,即调理性情,静赏自然,他的长处短处都在这里。这种真正的文学史家才具有的客观、透辟的见解,既不陷于“道德评价”,也不迷于“唯艺术论”,是深知中国文化者言,至
今仍属难得。由此又可见恢复文学环境不但是为沟通古今之审美心理,更是为了“这民族,这文化”!
《唐诗杂论》还为我们提供了文学环境是如何“读入”文学形式内部的分析样本。如《类书与诗》一文,便是从唐太宗时期大量出类书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入手,指出“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者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于是由此切入,展开论证,描画六朝以来“沉思翰藻”的文风,唐太宗重实际的文艺政策,通过“学术化”潜入文学的内部机制,促成了初唐诗“堆砌性”的总体风格,这样的一道运动轨迹。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则专注于文学形式是如何由于内容的变更而变更。“宫体诗”本属讲究词藻与声律美的一种新体式,但由于内容的病态而成为“一个污点”。庾信北上入周,给这一形式注入新的内容,于是“比从前在老作家作的同类作品,气色强多了”。至初唐卢照邻手中,内容更有所不同:“似有劝一讽百之嫌。”而在“宫体诗中讲讽刺,多么生疏的一个消息!”卢照邻《长安古意》之成功,首先是“在思想上的成功”,“他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卢照邻与骆宾王因思想内容变更的需要,改造了宫体诗,形成大篇幅、大气势,使之血脉贯通,一改过去贫血的病容。刘希夷则以其健康的爱情内容使这一形容趋于正常的健康的状态,至张若虚手,则升华为一种“夐绝的宇宙意识”,于是乎造成“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使这一形式有了质的变化,这就是“诗中的诗”——《春江花月夜》的出现。由上述线索,我们可以归纳出如是的图式:文化视野中文学环境的复原→审美意识的沟通、把握→文学内部机制(内容、形式)之变化。在这一探索的基础上,再去发现、总结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是的,闻一多留给后人更多的是启发,他的一些思想也的确在后来一些研究者手中得到强化、补充,乃至某种程度的完善,但闻先生的启发是多端绪、多走向的,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林庚对中国文学史的大体看法与闻一多有相通之处,这一点从林著《中国文学史稿》中《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所列分期大纲的比照中,可以明了。闻著始于“黎明”,林著则始于“启蒙”;闻著结于“伟大的期待”,林著则结于“文艺曙光”。中间都以建安至盛唐为诗歌之“黄金时代”,都以宋为文学史转折期,此后乃小说戏剧之时代。总体框架相似,且细读内容,林著也是循闻一多以“民间影响”与“外来影响”为“本土文学”发展的“二大原则”。而更本质之相似还在于:都注重诗与生活之关系。如林著之第三章“女性的歌唱”,指出“诗经为生活中最古的一声歌唱”。他将许多风诗归结为“生活的美趣”、“生活的乐趣”,并总结道“这些可喜悦的诗篇,却往往出诸女子之手”,国风中有名的篇章“都莫非女性的歌唱,汉魏乐府偶有以女子口吻作为篇章的,像曹植的弃妇篇,甄后的塘上行,但都是客观的描写,而缺少真正的情操,是男子写女子的口吻,或者女子学男子的笔法,而没有直接的强烈的表现”,“农业社会的田园的家的感情,乃是女性最活泼的表现”。这里所强调的“女性的歌唱”、“家的感情”,在后来的《中国文学简史》及其修订本中已淡出,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最神似闻一多解读《国风》。可以说,闻一多正是抓住“女性”对“家的感情”来剖析二千五百年前“都完全和你生疏的‘诗人’的心理”的。不过,两人神似之处也仅此而已,在对具体的文学史现象的处理上,林庚有其独得之处。
闻一多处理生活与诗的关系,着力点是再现诗的环境,用一切方法“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风诗类抄·序例提纲》),通过审美理解诗的本质,沟通古今;林庚处理生活与诗的关系,则偏重提示时代精神如何透过生活进入诗的语言形式促成其演进,从而沟通古今,殊途而同归。
以唐诗为例,闻一多强调“诗唐”,即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唐诗是生活化了的诗。林庚在这一思路上继续拓进,对唐诗之语言形式尤为重视。闻一多对诗歌语言形式的演进有过两个重要的意见,一是认为,节奏是关键,四言诗到五言、七言诗的演进,是从韵律向旋律的演进。二是认为,诗的语言的演进与虚字的减省有关。林庚丰富、发展了闻一多这一意见,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富于形象……诗歌语言为了适应这个要求,因此形成它自己特殊的语言形式:一种富于灵活性,旋律性的语言……也正是这内在的要求,才形成它外部完整统一而有节奏感的形式”(《唐诗的语言》)。他同样抓住《楚辞》这个关键,指出它是四言发展到五七言之间的桥梁,是“诗化”的重要阶段。归纳起来,“诗化”有三个要点:(一)语言的形象化。这个诗化过程自魏晋至南北朝,当时的文以及赋都随之逐渐与诗相近。六朝骈文是文的诗化,赋从王粲的《登楼赋》到庾信《哀江南赋》,渐近歌行。而诗歌语言的诗化最重要的是形象性的丰富,展开对形象的捕捉。从曹操《观沧海》起,诗歌开始将内心思想感情通过景物集中地表现出来。在用典上,也能将原来并没有形象的老典故非常新鲜地形象化了。甚至无足轻重的数字,也都起了鲜明的作用等等。(二)形成诗歌自己的特殊语言。突出表现在散文中必不可缺的虚字,自齐梁以来的五言诗中,已经可以一律省略。如“妖童宝马铁连钱”这类诗中常见句法甚至省略了动词。像“一洗万古凡马空”,也只能是诗中语法。(三)从日常语言中来,又回到日常语言中去。唐诗语言是唐文化生活中最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它是诗的,也是生活的。唐诗语言高度诗化,基础是唐人的现实生活,其语言是日常生活的。唐诗具有丰富而健康的生活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生活本身就近于诗。所以唐诗语言不可及处在于“深入浅出”。这第三点尤为重要,它既是闻一多“诗唐”认识的继承,更是深化。这一认识之形成反映林庚文学史观质的进步。当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林庚则完成了《中国文学简史》上、下卷的全面修订工作,并于后记中说:“主要是加深描述了寒士文学的中心主题,语言诗化的曲折历程,与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无妨说乃正是先秦至唐代文学发展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多费些笔墨。”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确立,标志着林庚文学史观的成熟,它已走完一个正、反、合的全过程。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作者成功之处还不在于三个组成部分的确立,更在于无论“寒土文学”还是“浪漫主义”都是通过“生活”为中介进入文学形式而起作用这一深刻的认识。在《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上发表的《盛唐气象》可视为林庚的代表作。在这里,作者“求解放”的一贯精神,相信“那能产生优秀文艺的时代,才是真正伟大的”。因此“只要求那能产生伟大文艺的社会”的理想,都得以充分展开,呈露其诗人兼文学史家的情怀。在这里,作者将“诗的唐代”归结为一种时代精神,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二者虽处于一乱一治截然不同的社会中,但都处于一个“解放的时代”,从礼教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从贵族文学中解放出来,从六朝门阀势力下解放出来。他认为“盛唐气象是一个具有时代性格的艺术形象”,唐诗浑厚而开朗的风格乃“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所以“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由于作者将形式与艺术风格放在“时代精神”的大格局下考察,所以论及具体作家如陈子昂,具体风格特征如“深入浅出”,都有极精彩的意见。《唐诗的语言》正是在这一宏观认识的基础上撰写的。林庚对“诗唐”的理解,既与闻一多有联系,又有其独到之处。最重要的是,林庚所称“时代精神”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如唐的时代精神是建安以来数百年历史渐进的过程,故唐诗成为这一整个潮流的高峰——“诗国高潮”。其总体特征“盛唐气象”于是有两个层次的内涵:(一)它包含了“建安风骨”乃至六朝“诗论”的丰富内容;(二)它包含了蓬勃的精神面貌、七言为主流的形式、雄浑明朗的风格等多方面特征,是个统一体。这就将内容与形式、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正是由于对这一段历史理解的透彻,建安至盛唐文学史也就成为林著文学史中最系统最精彩的一段。
林庚与闻一多一样,“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朱自清:林著《中国文学史》序),但在“一以贯之”的文学史规律的探索方面有更大的投入,特别是在生活与语言形式关系上有新发现,使闻一多模式轮廓更为清晰,层次更加丰富。
李泽厚《美的历程》虽是美学史,但其中四、五、七、八、十诸章连贯起来,也不失为一部文学史纲要。正是这位美学家,在新历史时期站出来呼吁回到闻一多的文学史模式上去,以审美趣味和审美范畴的变更做为观察文学史发展一以贯之的因素。
我们曾提到闻一多为沟通古今差异甚大的审美心理结构所做的努力,他所作的恢复文学环境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今人能悟入前人的心理,领会古人的审美情趣。从审美趣味上去把握文学史现象,进而寻觅其中隐藏的逻辑关系,是闻一多努力的方向。李泽厚正是从这一出发点开始,化入陈寅恪、宗白华的一些成果,吸收闻一多、林庚的一些观点方法,完善了这一文学史模式。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吸收不是“鱼纹的象征意义”或“少年精神”之类的个别、枝节的东西,而是一种整合。比方,李泽厚用陈寅恪士族与庶族斗争的基本观点,取代、改造、充实了闻一多关于“盛唐之音”乃是贵族诗的最高成就,以及林庚关于“寒士文学”、“布衣感”、“盛唐气象”论述的具体内容;用宗白华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是节奏化、音乐化了的宇宙感,“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的观点,重新解释了“盛唐之音”,指出音乐性的表现力渗透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的魂灵”。尤为重要的是,他将林庚关于七言形式的意见提到“反映了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上升阶段的时代精神”这一层面来认识,指出中唐以后“贵族气派”让位于“世俗风度”,此后的整个走向是“走向世俗”。而中唐以后形式的规范要求恰好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体现。由于李泽厚用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的变化为线索来把握文学史发展过程,并从盛唐向中唐过渡的诸现象中抓住“走向世俗”这一线索,所以这一段文学史、美学史的论述便更觉新鲜,更觉融贯。林庚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中已提出“晚唐为文坛的彩绘时代”,词为“彩绘的自由园地”;在《中国文学简史》中又进一步指出孟郊有些诗已“开始了强调感官的彩绘的笔触”,但点到辄止,尚未成为“一以贯之”的因素。李泽厚则指出李商隐、温庭筠诸人诗所表现的审美趣味完全不同于盛唐,“而是沿着中唐这一条线,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彩色的捕捉追求中”,并对这一审美趣味的形成从时代精神的变换等诸多方面予以解释。同时循此以求,追踪诗向词形式嬗变的轨迹。总之,在李泽厚手中,“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已成为揭示文学史规律的重要线索,从而补足了闻一多模式最后一环。
由上述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文学史模式虽然大量吸收了“他律”的文学史模式的手段与成果,但它始终将目标指向文学形式的内部。它既是“诗——史范式”的继承,又是其变异,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新的起点。
标签:文学论文; 闻一多论文; 林庚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诗歌论文; 唐诗论文; 李泽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