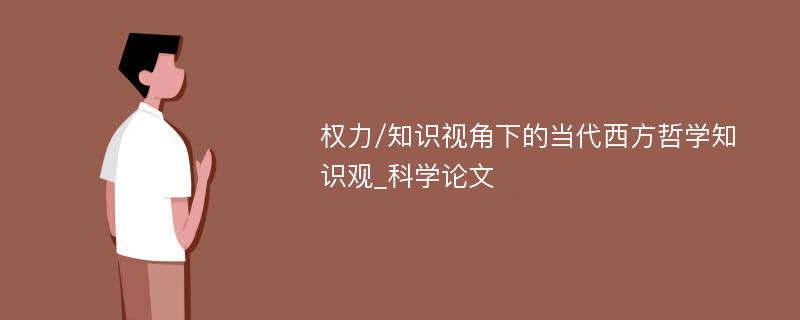
从权力/知识观点看当代西方哲学的一种知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论文,当代论文,权力论文,观点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哲学史上,知识和权力(power )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开始,人们逐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知识观,如笛卡尔的基础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是惟一真正的知识,社会、文化和传统对于知识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20世纪上半叶的分析哲学,如维特根斯坦早期的命题意义理论、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波普的证伪原则等科学主义,也把文化和社会排除在知识研究的视野之外,脱离我们的语言、文化背景和权力关系。到了50年代末,由于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把科学史引入了认识论,从而开始重视社会、文化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观:知识之所以是知识,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能够满足权力意志的需要。当代致力于研究知识和权力问题的哲学家首推福柯,对于福柯来说,权力不限于国家权力,社会中一切机构,诸如学校、工厂、医院、家庭等都普遍有权力关系。权力不只是给我们以压力,抑制知识,而且是一种创生性的网络,形成知识,产生言谈,福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识观。
一、知识、言谈和真理
自笛卡尔以来,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科学知识是惟一真正的知识,其他非科学的信念或意见都不是知识,个人主体按照理性确立知识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科学大厦,而社会、文化和传统是偏见、错误和假象的来源,必须摒弃于知识大厦之外。本世纪20~30年代的分析哲学,把这种科学主义知识观推向顶峰。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经验科学知识论”,致力于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其意义标准或可证实性原则可表述为:当且仅当一个陈述或者是分析陈述(例如“偶数可以被2整除”)或者是原则上可以证实时,才是有意义的。“阐释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注:石里克:《意义和证实》,1936年,引自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3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在那里,人与世界的关系没有了,最多只有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他们探讨的主要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如,一个陈述是不是可证实的;一类观察陈述是否(直接或间接、完全或不完全)确认一个假说(即一个假设的语句),两个理论(即语句系统)是不是逻辑上相容的,或者是否一个可以逻辑地由另一个导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关于陈述与陈述之间,或整类陈述系统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知识论只是一种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世界与知识的关系仅仅是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的二元关系。
由于逻辑实证主义打出统一科学的旗号,试图把一切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都还原为物理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这导致它特别强调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强调其他文化领域向科学靠拢,否则就被排斥在科学范围之外,因此,可证实性原则这个意义标准,同时又是真理标准的惟一依据。按照这个标准,经验自然科学的命题是有意义的、可证实的;数学和逻辑真理是永真的重言式;而其他不可证实的、无意义的、无所谓真假的陈述应当作为“形而上学”或伪科学而被清除。所谓理性、合理性、方法论原则等只是达到客观真理的手段而已。在这里,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传统,而只有逻辑。
波普致力于科学逻辑的研究。在他看来,科学方法论,包括划界标准,不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也不是逻辑,而是一种约定,它的目的是真理,但真理是通过科学的进步而逐步接近的。因此,虽然我们的知识总是可误的,但我们可以证明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符合事实,具有更高的真理性程度,即“逼真度”。在波普看来,一种理论只要是可证伪的、可反驳的,它就是科学的;反之,凡是不可证伪的,不可反驳的,则是非科学的(其中包括不是经验科学的和伪科学的)。同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波普提出证伪主义原则,就是要建立一个指导科学家进行研究并对理论进行评价的方法论规则或规范,这既不符合科学实际的发展历史,又脱离我们的语言、文化背景和权力关系。
20世纪下半叶,由于人文科学的解释学的影响,以及库恩、费耶阿本德、玛丽·赫西等人从科学史的证据出发对实证主义的全面批判,反基础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新的知识概念,如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费耶阿本德);科学理论“不是外在地和自然界相比较而引出的假说——演绎的说明模式,它们是事实本身被理解、被设想的方式(玛丽·赫西);“科学是一种社会制度”(布卢尔),它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受同样的检查。美国新一代科学哲学家劳斯(Joseph Rouse)则提出科学知识的局部化或境域化(contexualization),劳斯特别强调在一个局部的、存在的(existential )领域中科学的实践活动,它包括劳动场所、材料背景及技术实践的技能、实验室内的权力斗争等等。劳斯指出,“当我们考虑这些因素时,就会发现科学上局部的、存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对设备、技术和方法、社会角色以及运用它们的思想可能性的一个整体的实践把握基础之上的” (注: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s a philosophy ofscience,first published 1987,b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P116.),“在这方面,我们最好把理论看作是处理各种现象的策略,而不是陈述系统;当做方针而不是信条”(注:Joseph Rouse, knowledgeand power:Towards a philosophy of science,first published 1987,b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P116.)。
以上社会化的认识论表明:传统知识观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区分是不存在的。劳斯在他的《知识和权力——走向政治的科学哲学》一书中,指出了这种科学划界的不合理性, “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把这些区分当做已经给出或是自然的”(注: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s a philosophyof science,first published 1987,b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P207.),与人文学科一样,自然科学知识同样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晶,同样不能免于意识形态、权力策略和政治统治的检查和批评。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知识、真理和方法。
对此,尼采提出“观点主义”(perspectivism),他说, “就知识一词有任何意义的范围来说,世界是可知的;但它也可以用不同方式解释。它不是蕴含着一种意义,而是无数种意义”(注:尼采:《权力意志》(英译本),第481节,第337页,纽约,1967年出版。)。尼采认为,一切知识都是解释的,而“解释本身作为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为作为一种情绪冲动的生存所固有”(注:尼采:《权力意志》(英译本),第481节,第556页,纽约,1967年出版。)。因此,权力意志,乃是追求知识解释的原动力,知识即权力的工具,知识随着权力的增长而增长。同样地,既然不存在“自在的知识”,也就不存在与人无关的“绝对真理”。要问什么是真理,必须首先问一下什么是“求真理的意志”,权力意志。
福柯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强调历史话语对人类知识的制约。福柯指出,每个时代都标志着一个确定其文化的潜在外形,一个使每个科学话语、每个陈述产品成为可能的知识框架,福柯命名为“知识型”,意即确定和限定一个时代所能想到的——或不能想到的东西——深层基础,或知识和话语的形态。福柯称之为“特定的言谈的机器”,而“考古学”不是纯粹描述的方法,它揭露产生心理学实践的条件以及那些实践的言谈。心理学力求发现“构成规则”。这些规则规定在一定历史时期言谈必须具有什么元素和什么结构才会被准许进入知识的竞争场所。这些规则是管理那些言谈的常规,虽则它们自身永远是言谈实践的一部分。同时福柯用“系谱学”来说明建立在对局部言谈的描述基础之上的策略,通过这种策略,受压制的知识被解放出来。在这里,福柯揭示了权力和话语(知识)的联系:一切知识、言谈(话语)都处于权力网络之中,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权力,没有纯乎其纯、不计功利的话语,存在的只是权力笼罩下的话语。因此,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不可能是中立的、纯粹的。福柯通过知识的系谱学,剥夺了知识的貌似客观性,揭穿了真理的幻象。他认为,对某一特定的权力关系来说,知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的区别,任何知识都不是来自某一知识学科,而是来自于笼罩它的权力关系。
二、权力的阐释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辉煌成就,强化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信心。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power)”, 正是这样一个体现着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命题。
在培根看来,知识是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正是科学知识,赋予了人主宰和支配自然的力量。这里,“力量”一词具有多义性,到尼采那里则发展为“权力”学说,从培根到尼采,知识与权力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知识在培根那里是一种客观的、对自然的正确认识,人首先要服从自然,然后征服自然。而在尼采看来,知识不外是人的权力意志的外化,它服从人的权力欲望,无所谓客观与真假。其次,在培根的命题中,知识和力量(权力)的关系不是固有的,即权力外在于知识。而在尼采那里,知识内在地包含于权力意志之中,权力是整个世界的本质。再次,在培根那里,科学知识是普遍有效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真理;其他一切都是非科学。尼采彻底批判科学理性主义,他认为任何理性主义都是掩饰某一权力意志的假面具。
自培根以来,传统的知识观坚持知识仅仅是对语言的一种逻辑句法分析,是关于陈述之间的关系,或整类陈述之间的关系,因此科学研究所体现的不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最多只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而权力:①属于政治领域;②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权力是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而知识的研究,只有在远离政治权力的压力和控制时才能最好地获得。权力与我们相信为真的东西无关,即知识的组成和权力的构成在原则上彼此独立。劳斯总结了这种传统的知识/权力观的看法:“权力能够激发我们去获取知识,并能改变我们的研究方向,但在决定什么是知识这一点上,它并不能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注: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s a philosophyof science,first published 1987,b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P14.)
库恩以科学史、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取代科学逻辑,引发了对知识权力关系的重新思考。“应该已经清楚,最终分析起来,说明必定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这就是说,说明既要描述一个价值系统,一种意识形态,还要分析把这个系统传授下来和加强起来的那些制度。”(注: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见《批评与知识的增长》,第21页。)
尼采明确地提出了“权力”(power)概念,在他看来, 世界的本质是权力意志。一方面,权力意志是无机界、有机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永恒生成的原因;另一方面,它又是最高的价值尺度。尼采用它来衡量人类的一切精神文化价值。“权力”一词,在尼采看来,并不等同于政治含义上的权力。尼采对政治含义上的权力往往持否定态度,斥之为“权势的贪欲”、“求权力(求帝国)的意志”、“权力的爱好是人生的恶魔”、“权力是无聊的”等等。尼采所肯定的权力,不是外在的权力,不是表面的暴力、统治、禁止和镇压,而是内在的权力,是生命力的充溢、自我超越和意志的自律,而知识之所以是知识,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能够满足权力意志的需要,即知识是权力的工具,求知的意志依赖于权力意志;求知的目的在于支配和控制。
福柯是继尼采之后当代西方最伟大的权力理论家。他采纳了尼采的“系谱学”名称,致力于“权力系谱学”的探索。他通过对知识、理性和性欲的考古研究,在对监狱、疯人院、精神病等的调查、分析之中,展开了他对权力问题的深入思考。可以看出,①福柯所说的“权力”一词绝不囿于常人眼里的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因此,权力不是某种能被获得、被掌握或被分享的东西。权力是一种网络,其网点蔓延到任何一个角落。因此,权力的分析应该从权力的应用出发。我们不应该问“谁拥有权力?”或“权力拥有者的意图和目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应该研究权力的效应对主体的构成。②福柯认为要分析权力,就不能先验地把权力同压抑联系起来。他说“在本世纪60年代,往往把权力定义为一种遏制性的力量: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事。据我看来,权力应该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注: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我认为禁止、拒绝、抑制不仅远远不是权力的根本形式,甚至它们造成了权力的局限性,使权力受挫并走向极端。”(注: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42~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福柯强调指出权力具有创造机制:“权力是一种创造;它创造现实,创造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注: 福柯:《监禁与惩罚》(英译本), 第194 页, 纽约Vintage Books公司,1975年出版。)
在知识和权力关系问题上,福柯首先挑战如下传统看法:权力和知识之间不存在相容性。他指出,“我们也许应当抛弃这样的信念:权力造就癫狂,同理,权力的放弃是知识的条件之一。我们倒应当承认:权力产生知识(这不单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而鼓励它,或是由于知识有用而应用它);权力和知识正好是互相蕴含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力关系”(注: 福柯:《监禁与惩罚》(英译本), 第 27 页, 纽约Vintage Books公司,1975年出版。)。在1971~1972学年里,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惩罚理论与机构”的课程,进一步提示了知识和权力的共生关系:权力关系——不仅对知识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它们也不只满足于怂恿或激励、歪曲或限制知识;权力和知识不是惟一由社会利益或意识形态的作用来连结的;因此,问题不在于确定权力如何征服知识并使它终身侍奉,或是确定权力怎样在知识上打下权力的烙印并把意识形态的内容和限制强加于知识。倘若没有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并以它的存在和功能与其他形式的权力相联系的传播、记录、积累和置换的系统,那么知识体系便无法形成。反之,假如没有知识的摘要、占用,分配或保留,那么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在此层面上,既无知识也无社会,抑或既无科学也无国家,惟有知识/权力的根本形式。按照福柯的考察,知识和权力是相互关联的,权力对知识已不再适于用“远离”、“有害”、“无用”等字眼来加以说明。其次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关系。压抑说是一种片面的权力理论。没有权力便没有知识,没有知识也没有权力;权力控制了知识,知识也能给人以权力。因此“知识就是权力”。
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知识就是权力”,即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内在的、共生的关系,是否可以理解为把知识等同于权力的“知识即权力”呢?福柯指出:“当我读到不管是‘知识即权力’,或是‘权力即知识’的观点时,总是哈哈大笑。因为确切地说我的问题就是研究它们的关系:如果这是两个同一的东西,我就没法研究它们的联系了……我对两者提问的惟一事实就很好地证明了我不把它们视为同一。”(注:福柯与G.罗菜(G.Raulet)的谈话录《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Telos,vol XVI),参见钱翰《“知识就是权力”吗?》,载《读书》1997 年第7期。) 在福柯与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的以“对真理的关怀”为题的访谈中,也作过类似的声明:“如果我说过知识是权力的话,我就不用再说什么了,因为既然这两者是同一的,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还要指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注:福柯著,严锋著:《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福柯指出, 某种权力形式能够产生出对象和结构都极为不一样的知识。例如,对同样一种医院结构的权力形式来说,它既产生了精神病学形态上的监禁,形成精神病学知识,同时又产生了解剖病理学知识,推动了医学科学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里,权力及其相关的制度形式——精神病监禁、住院治疗等——与不同的知识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知识/权力。劳斯指出:“权力和知识既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也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们分别代表我们认识和相互交往的不同的实践方式。”(注:Joseph Rouse,The Dynamics of power and knowledge in science,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1,P665.)没有对权力和知识的相互关注,就不可能达到对(科学)知识的真理性的认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就是权力。
劳斯从科学哲学的视角进一步发展了福柯的知识权力观。他认为,首先权力不仅仅是从外部侵入科学和科学知识。权力关系贯穿科学研究中的多数日常活动。科学知识产生于这些权力关系而不是与它们相对抗。科学知识中产生的权力不是一些特殊的行为者拥有的财产,不一定为特殊的利益服务。权力关系构成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看见特殊具体的行为者和利益。劳斯强调,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毛细血管”式的权力关系,必须对照这种权力关系来理解科学知识。其次,权力与知识或真理有着内在的关系。劳斯察觉到至少有两点是传统知识权力观所忽视的:①正是使对象领域更加明白和精确的认识上的努力,使权力和知识相互交融在一起。②社会运动或变革可能同时在认识论或政治上产生影响。劳斯指出:“我们认识世界,不是作为主体把我们面前的对象再现给我们;而是作为行动者,掌握和抓住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各种可能性。从再现到操纵,从反映认识(knowing that)到操作认识(knowing how )的转变并不否认常识观点: 科学帮助我们认识周围的世界。” ( 注: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s a philosophy
ofscience,first published 1987,b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P25.)
三、结语
从以上对知识、权力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哲学知识权力观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动向及其演变过程。①关于什么是知识。从传统哲学(如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等)追求绝对理性的科学陈述、客观知识和真理到把知识同社会、文化和传统联系起来;从把知识看作是认识主体对对象的逻辑重建的反映认识(knowing that)到体现了实践的行为者对我们周围世界的操纵和把握的操作认识(knowing how),反映了当代西方哲学冲出现代主义的危机,寻求出路的种种有益的尝试。②权力是什么?在传统观念那里,认识论的科学讨论的范围是与政治权力相对立而形成的,因此是以排除的方式界定了权力。在那里,权力是静态的东西,外在于知识,具有独立性;权力的本质是压制和管制的。相反,当代权力观认为,权力内在于知识;权力的作用方式是生产性的而非压迫性的,权力是动态的。③关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传统观念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是外在的。知识和权力在各自的构成上不受双方影响,彼此独立,即权力可以影响我们获取知识的动机或阻止某一知识的进展或运用,但在决定什么是知识的问题上,起不了建设性的作用。然而新的知识权力观揭示了知识的解释是如何密切地与权力的理解相互关联的。知识与权力具有内在的、水乳交融的关系。知识产生于权力关系而不是与它们相对立等等。从以上分析我们至少可能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知识”这一概念已大大地拓展了,不再是指脱离实际的、客观的科学知识,而是有着更为广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意蕴,任何一个认识系统、信念网络都可以看作一个知识体系。其次,同样地,“权力”已不再具有单纯的政治意义,它蕴含了比政治权力丰富得多的内容,即一种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介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控制和支配的方式,因此有必要对知识/权力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福柯和劳斯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揭示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全新走向。
标签:科学论文; 尼采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权力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权力意志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福柯论文; 哲学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