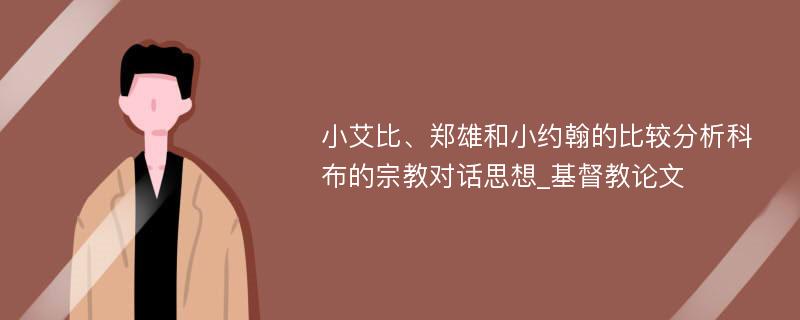
阿部正雄与小约翰#183;柯布宗教对话理念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宗教论文,理念论文,阿部正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0)02-0099-03
阿部正雄与小约翰·柯布是当代欧美耶佛对话领域的两位重要代表人,作为长期合作的对话伙伴,他们对宗教对话有着重要的共识:对话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基督教和佛教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更在于通过对话,使两种宗教传统在相互学习中达到创造性的相互转化。应当说,阿部和柯布各自的耶佛对话实践都是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展开的。不过,虽然二人的对话理念非常相似,但其中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这些差别使二人在学习和接受对方的宗教洞见时体现出不同的态度和侧重点。以下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首先系统地提出“超越相互理解而达到相互转化”这一理念,并使之成为当代宗教对话领域一项重要共识的是柯布。柯布指出,对于基督教来说,和其他宗教群体的对话首先和在最大程度上是为了基督徒自己,基督徒能够通过向其他宗教学习而丰富自己的生命和纯洁自身的信仰;不过真正超越对话的目标不仅如此,对话还有另外的使命,这就是基督徒希望通过对话使他人也有所改变。这并不意味着要从对话退回到还未经过对话的见证。对话和传统见证的不同就在于,对话的目的是为了对其对话伙伴作为一个宗教共同体而有所贡献,而非意图使这一共同体中的个人转而皈依基督教。
就佛教和基督教的对话而言,柯布认为基督教必须向佛教学习,在与佛教徒的对话中重新领会基督教的真理,他说“佛教具有对实在之本质的深刻洞见,这是我们所缺乏的……因此,目前我们需要通过对话而学习,并且超越对话,我们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信念。”同时,柯布也强调,所有这一切的目的,不应仅仅是让基督徒自身得到启迪和提高,它也必须有助于佛教徒。他说:“……我们相信如果不把耶稣基督融入佛教,佛教徒就会缺少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相信他们这样做就会成为更好的佛教徒。”
这一理论在阿部那里就体现为,一方面佛教要向基督教学习,另一方面也要从佛教的角度出发,帮助基督教深化其对自身的理解。在这一点上,阿部和柯布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阿部和柯布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对阿部而言,宗教间打破原有理论、实践框架而实现相互转化,最终是为了给人类的存在奠定共同的灵性基础,这同时也就是宗教的共同根基。这是阿部多年对话实践孜孜以求的目标。
从1963年发表《今天作为一个问题的佛教和基督教》开始,阿部就强调我们这一时代每个宗教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在宗教多元的处境下,如何理解与处理自己与其它宗教之间关系的问题,而更是宗教作为一个整体如何面对当代各种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挑战的问题。他说:“今天,我们发现所有的宗教,包括佛教和基督教,都处身于几种反宗教力量的毁灭性攻击之下。它们的批评已经远远不止于针对某个具体宗教,而是直接伸延至宗教存在的本身。”
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真理,有效回应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挑战,阿部指出,各宗教之间就必须进行对话,因为只有“在转化性的对话中,每个宗教都通过超越教义和实践的传统形式而证明自己最深的真正精神”。这种精神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人类精神”,只有它才能克服当代宗教受到的多元挑战。
除此之外,阿部对于当今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命运还有着更深刻的忧思,他认为同古代人相比,现代人更深地陷入同自然、同他人,归根到底是同自我的疏离之中,失去了精神家园,“人们以今天特有的方式离开了最后的安身立命处”。在他看来,人与自身的疏离或者异化的问题,在过去是通过宗教来解决,然而现在宗教本身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所以人的异化问题,虽然亘古有之,但是在现代却加剧了。阿部对此的解决之道就是,在东西方之间开辟一个能为宗教提供空间的新的灵性视界(spiritual horizon)。只有当各宗教在当代处境中重新找到自己最深刻的根基,才能够为人类提供一个统一的灵性基础,克服当今世界人类日益严重的异化问题。
与阿部不同,柯布从来没有表达过所谓追寻宗教共同根基的宏愿。在他看来,转化了的佛教和基督教将继续保持它们的不同,这些不同深刻地植根于它们各自的历史。至于这种不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随着彼此越来越多接纳对方的真理而消失,柯布认为这并不重要。他说:“佛教化了的基督教和基督教化了的佛教将继续通过它们彼此的差异而互相丰富,同时也丰富整个人类的文化。”
事实上,柯布对共同基础的追寻抱着相当怀疑的态度。他批评约翰·希克等人关于各宗教有某种共同本质的假定,认为它忽视了各个宗教的独特性,妨碍了各宗教间真正的相互学习。
对阿部而言,宗教对话的目的在于找到各宗教的共同根基,因此,佛教与基督教的相互转化是朝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这个方向也是所有宗教的共同基础。这一基础,在阿部的心中已经有所设定,这就是佛教对“终极实在”的理解——阿部所谓的“无相的空”(formless Sūyatā)或“动态的空”(dynamic Sūyatā)。这在他提议以佛教的“三身佛”理论理解世界诸宗教的多元性和统一性问题上可见端倪。
佛教的三身是指法身、报身和化身。阿部指出,在大乘佛教中,法身就等同于“空”,它是“报身”和“化身”的最终根基。它是空和彻底“无相”的:“法身,否定任何形相,也不断否定自身的无相并自由无碍地采取各种形相。”“报身”在大乘佛教中是多元而非单一的,例如阿弥陀佛和大日如来作为净土宗和密教各自崇拜的主佛,并没有冲突,都被认为是同一开放、无相的法身的不同显现。此外佛教中还有很多佛和菩萨,它们都是有特定名称和形式,实现了佛法、享有功德的报身。“化身”也不止释迦牟尼一人,印度的龙树、中国的天台智顗、净土宗的善导等,根据佛的三身理论,也可以看作是佛的化身。
阿部认为,这种佛教的“三身”理论,可以为宗教多元状态下的动态统一作出贡献。根据这种理论,实在可分作三重:主、神和无限的开放性(Lord,God,Boundless Openness)。“主”大致代表“化身”,是作为信仰中心的一个历史上的宗教人物,如耶稣基督、乔达摩悉达多、摩西或默罕默德;“神”代表“报身”,是一个超历史但有特定名称和德性的人格神,如耶和华、安拉、湿婆、阿弥陀佛等;“无限的开放性”代表“法身”,是真理本身,是人格的“神”和历史上的宗教人物的最终基础。阿部指出,“尽管‘无限的开放性’是包容一切的,因此,能够接受各种宗教而不取消它们各自的‘神’和‘主’的独特性,但它同时也不断地空掉它们——甚至让它们弃绝自身并返回作为最终根基的‘无限的开放性’”。
由此可见,阿部认为宗教间通过对话而达到的相互转化,最终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即朝向于佛教所理解的终极实在——“无相的空”。这同时也表明,阿部对于佛教对终极实在的把握相当自信,认为它表达了所有宗教最终极的真理。
阿部的这种自信使他在与基督教对话的时候,虽然强调佛教有向基督教学习的必要,特别是在社会正义和历史观等问题上,例如在《与基督教的对话对我作为一名佛教徒的自我理解的影响》一文中,他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佛教对社会不义的整体态度是相当薄弱的。我们必须向基督教学习怎样在更广的范围内解决社会和历史的问题,并且从佛教智慧和慈悲的立场加以诠释。”但一旦涉及更加根本的层面,即对终极实在的理解,阿部则并不掩饰其佛教的优越感。
柯布曾经这样说过,“即使在他们当中(那些积极参与耶佛对话的佛教徒),也有一个强烈的意识,那就是更深刻的根基可以在对‘空’的更深刻的理解中找到,而佛教已经以此为根基了。因此,可以从基督教那里学到的东西并非在最深的层次上开展,它的重要性可能只有在浅显得多的层面上才能找到。而参加对话的基督徒有更强的感觉,就是在更根本的层面上被吸引进了佛教经验的轨道……”
由于阿部认为佛教对“终极实在”的理解比基督教更加深刻,这使得他在与基督教的对话中,不断努力向对方澄清佛教的观念,并希望帮助基督教在“最根本”的层面深化对自身传统的理解。他曾提出以佛教的“空”,对基督教的上帝观进行改造,这就直接触及了基督教的终极层面。这一提议在欧美的耶佛对话领域产生了很大反响,引起了众多基督教神学家的回应。
对于基督教传统可能对佛教产生的裨益,阿部主要认为是在社会伦理和历史观这些“次根本”的层面。即便如此,由于阿部为宗教对话设定的最终目标是为人类的存在奠定共同的灵性基础,这使他在整过对话过程中,往往体现出一种偏重于普遍、超越、终极层面的讨论,而相对忽视具体、社会、历史分析的趋势。因此,他虽然常常强调在社会伦理方面佛教有向基督教学习的必要,但并未提出更为具体的方案。
例如在对具体伦理问题的分析上,他倾向于以人们对终极真理的“无明”,解释人类一切苦难的成因,并以“觉悟”作为问题的解决之道。例如针对纳粹的产生,身为日本学者的阿部并未从日本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而是从他一贯的佛教思维出发,指出每个人都对这一暴行负有责任,它是人类共业的结果,因为大屠杀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无明和盲目的生存渴望。
对于阿部的这种分析,柯布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虽然“原罪”和“无明”时刻伴随着我们,而像大屠杀这样的事情却不是每刻都发生。特殊的事件需要特殊的分析和解释,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与大屠杀相关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但是却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相对于阿部偏重于“终极层面”的抽象探讨,柯布更关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具体问题,近十几年来,他已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基督教与生态伦理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中。
与阿部相比,柯布对基督教在终极层面上向佛教学习表现出了更加开放的心态。他在《超越对话:走向基督教和佛教的相互转化》一书中,探讨了佛教的无执着、无我以及空给他的基督教信仰、对自我和上帝的理解带来了怎样的转化。这三点都涉及了基督教的根本思想。其中,对“空”和上帝的探讨更是直接触及了基督教终极实在的层面。
在柯布看来,如果像西方的传统那样,将终极实在理解为存在,那么存在具有一切现实性,这样就很容易将上帝置于存在之下了。接受“空”而非西方哲学传统的“存在”作为终极实在,可以免于将终极实在置于层级的顶端,而将它的实现(actualization)置于在本体论上次一级的地位。这是因为“空”作为终极实在不具有“现实性”,而“上帝”作为终极实在的一个宇宙的、永恒的实现则拥有所有现实性,因此,上帝在形上学的层级上并不次于“终极实在”。他说:“上帝作为终极现实性就和空作为终极实在一样具有终极意义。空不同于上帝,没有离开空的上帝。同样真实的是,也没有离开上帝的空。空并非超越于上帝。”
从柯布以“空”代替“存在”作为终极实在,以及将上帝理解为非实体性的“空的那一位”(the empty one)可以看出,他的上帝观深刻地融入了佛教的洞见,与传统相比确实发生了激进的转化。不过,柯布并不认为“佛教化”了的上帝概念会泯灭基督教和佛教之间的区别,反而有助于加深和丰富对基督教传统的理解,他说:“我们基督徒可以通过佛教‘一切事物的终极实在都是空’这一洞见而重新思考对于上帝的信仰。通过这种思考,我们自己的传统能够以新的方式得到阐明。其结果并非冲垮基督教而向佛教妥协,而是更加丰富和纯粹地领悟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认识的上帝的含义。”
结语:虽然阿部和柯布是“促进宗教间创造性的相互转化”对话模式的共同倡导者,二人对于“相互转化”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对阿部而言,“相互转化”的目的在于发现各宗教的共同根基和为人类生存奠定共同的灵性基础。由于这本身是一宏大而抽象的主题,导致了阿部在对话过程中更关注抽象层面,即“终极实在”层面的思考,而较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同时,在阿部的思想中,佛教“空”的观念已经最深刻地把握了终极实在,因此,佛教的“空”就是各宗教的共同根基,同时也是个宗教应当“转化”的最终方向。这种认识,使阿部在与基督教的对话中更多的是扮演一位“教师”,而非“学生”的角色。在整个对话过程中,阿部力图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使基督教伙伴发生转变,而佛教只是在“较浅”的层面有向基督教学习的必要,这使他有时会忽略基督教伙伴提供给佛教的洞见。
与阿部不同,柯布并未对“宗教间的相互转化”设定一个最终的方向,在他那里,转化是开放性的,这种转变没有终结,双方要不断地学习,永远“在路上”。这使柯布在与佛教对话的过程中抱有更开放的态度,他承认佛教在对终极实在的理解上更具深度,并毫不犹豫地将其融到自己的神学中。此外,柯布对抽象的“共同基础”不感兴趣,他认为转化的目的在于使佛教徒和基督徒各自变得更好。因此,与阿部相比,柯布更加注重佛教徒和基督徒应当怎样面对现实问题,如生态伦理问题,社会正义问题,并对此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
笔者认为,阿部的宗教对话虽然植根于他对当今世界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关怀,但他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之道都是相当抽象的,他想要澄清和建立一个共同的形上根基,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这在受后结构主义批判影响的学术圈里可能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同时,所谓一个“共同的灵性基础”对于宗教间的对话,以及全人类的福祉来说,是否必要,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越普遍的理论,可能就越抽象,因此,反而缺乏实际的力量。相对而言,柯布的进路则更为务实,也更有可能为耶佛对话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