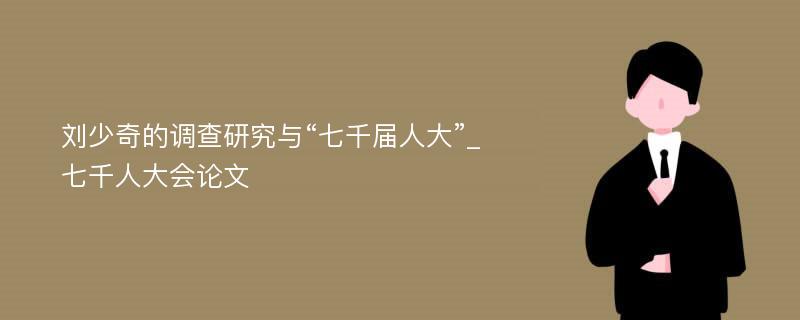
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研究论文,千人论文,大会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1287(2000)02—0035—04
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典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在这方面又形成自己的风格。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党的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情况、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及人民生活状况,刘少奇作过大量调查研究,从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对经济的严重困难以及产生困难的原因、形成错误的根源,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中央拿出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对症下药,才取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良好效果。研究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几年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对国民经济形势的认定、会风的形成、中央决策的制定等之间的关系,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一 对形势的客观估计来自调查实践
建国后,刘少奇在调查研究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一,目的明确,使调查有的放矢。他认为调查的目的有三个:一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二是了解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三是发现脑子里还没有考虑过的新问题。其二,调查的途径多样。50年代初,刘少奇特地从湖南老家找了几位老实的、有经验的、敢讲真话的农民,担任他的通讯员,要他们每年给他写几封信,如实反映情况。除了听干部汇报以外,他还身体力行,亲自去基层,跋山涉水,不辞劳苦。1961年去湖南长沙县、宁乡县等地的44天调查,堪称党内调查的模范。其三,调查细致深入而全面,往往轻车简从,吃住都在民间,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张扬,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调查流于表面、单听汇报,可能为假象所迷惑,因而作出的决策就会离题千里而遗害无穷。刘少奇在调查中善于体察群众情绪,常常不声不响地仔细观察人和事,从对方是笑脸还是苦脸,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等表情中,去探求他们的真意。其四,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是经常性的,决不是偶尔为之。据他的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回忆,1956年以后,差不多一年当中有1/3左右的时间在下面。“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刘少奇去基层次数更多,程度更深入。1957年2月,刘少奇率调查组赴河北、河南、湖北、 湖南和广东等省考察,他提醒随行人员对那些听到的“不实之词”要警惕,不能信以为真,因为他发现有的省在汇报时作假,“报喜不报忧”。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开展,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为此,刘少奇又于1958年9月到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考察, 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1960年4月在河南考察时, 他教育省委的干部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对困难要如实反映,同时不能盲目过度,不能搞跳跃,一下子想跳到社有经济、跳跃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应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1961年4、5月,刘少奇去湖南长沙县、宁乡县等地作了为期44天的实地调查。这次调查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形势的估计、怎样评价近几年工作得失等,影响很大。调查前,他定下了“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不扰民、自带油盐柴米、自备碗筷用具、一切轻装简行”[1]的规章,以了解实情。在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 他就住在猪饲料房(又作办公地点)。他一再对工作队强调“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不这样,调查研究之风就不能兴起”。
“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和形势的估计是有分歧的:有人乐观,认为形势已根本好转,“五八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有人在讨论刘少奇为大会作的“书面报告”时,认为“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2]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指出几年来的缺点错误是:计划指标过高,部门比例不协调;在公社化的过程中,进行了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不适当地建立了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虽然在报告中他说到“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但显然作了较多的保留。在大会讲话中, 他讲得更充分:从1959 年到1961年,农业不是增产, 而是减产, 减产还相当大, 工业也减产,1962年也难以上升;由于工农业减产,人民吃的粮食、副食品、肉、油都不够,穿的、用的也不够。“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是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3]这种估计是客观的。1961年4、5 月在湖南调查时,他看到不少人因粮食不够得了浮肿病,他到一些农民家里,揭开锅盖,打开碗柜,看到油盐罐子里只有盐没有油,锅里炒的是野菜,甚至来与他见面的亲戚、熟人当中,也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他的70多岁的老姐姐颤巍巍地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啰!”[4]5、6 月间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及大跃进中的惨况时,他语气沉重,痛苦、愧疚溢于言表:“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5]
二 调查的深入使他对产生困难的原因及工作得失的评估也更加深刻
1958年以来出现这么严重困难的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上从领导工作中去找原因。刘少奇对产生困难的原因,概括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1年在湖南家乡调查时,他与小时候一块放牛的农民朋友李桂生有一番谈话,他问:人们说去年干旱很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没有?当得知还有半塘水时,他回忆起小时候有一年安湖塘干得见底,但每亩田还收了两三担谷,李桂生快人快语: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的结果。[6] 故乡老百姓对公共食堂深恶痛绝,有群众说:“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国破家亡”。[7] 在长沙县天华大队等地刘少奇一举解散公共食堂,老百姓流泪鼓掌、奔走相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称“这下上面睡醒了”。[8]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不种自留地、 不养鸡猪,以至一年到头难得闻到肉星味,不仅湖南,其它地方不断传来农村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使刘少奇触目惊心。随后他又通过对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几个省干部的调查,得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困难主要原因的结论。他的调查研究就从点到面、由具体到抽象,从而就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由此进一步评价近几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得失(尽管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他有如下观点:“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9] 这就突破了党内流行很广的有关“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即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的框框。自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开展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以来,不少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敢面对当时现实,对工作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而习惯于用“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框框去套。刘少奇上述观点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没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不可能提出这种实事求是的意见来”。[10]正因为他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评价“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得失,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都能比较客观地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认真回顾与总结,为进一步顺利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 勇于自我批评,为大会吹来清新之风
刘少奇多次论述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敢于实事求是地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党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不仅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而且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必须采取的态度”。“既然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应该把它隐蔽起来,不应该不去纠正”。[11]1961年在湖南调查中,刘少奇曾与长沙县天华大队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谈到刮“五风”问题时,他自责地说:“刮‘五风’的错误不能只怪你王升平,各级都有责任,中央和我也有责任,我回来是向你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刻一块碑立在这里,或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镶起来,子子孙孙传下去,要大家记住,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12]在家乡宁乡县炭子冲与基层干部、农民的座谈会上,谈到近年来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他再次坦诚承认:“这是不是完全怪大队干部呢?也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上边要负主要责任……有的是中央提倡的,如办食堂,因此根子还在中央”,“这次回来,看到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13 ]在刘少奇的模范作用带动下,“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作了自我批评,从而使会议气氛空前活跃,“出气”之风大开,大家畅所欲言,以至到原定会议结束之日,许多人还觉得言犹未尽,于是中央决定会议延期,让大家把“气”出够,真正是“倾箱倒箧而出”(毛泽东语)。亲身经历过“七千人大会”的薄一波老人事后评价,象“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14]这种会风,其影响是深远的,对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
四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探索产生错误的根源
“七千人大会”上,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根源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有:经验不够;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分散主义严重泛滥;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过火的党内斗争和只反右不反“左”等等。刘少奇根据几年的调查得来的情况,进行研究,上升到思想理论高度,其论述与其他领导人相比较,又有自己的特点。
在刘少奇看来,这几年之所以犯瞎指挥、浮夸风、穷过渡等错误,主要原因是我们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够或者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比如食堂问题,上面说办公共食堂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但1961年刘少奇在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群众不这样看,群众说:我们这里的食堂专人砍柴、专人挑水、专人舂米、专人煮饭、专人做菜,光这些就占用了1/3的劳力;食堂吃大锅饭,要烧硬柴,不烧茅草,就上山砍树, 把成材的山林砍得七零八落,这哪里是节省,完全是浪费,是破坏,是造孽!食堂问题当时已成为政治问题,因为上面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谁说食堂不好,就是破坏社会主义阵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压制群众的意见,使群众不敢讲话,结果错误越来越严重。湖南调查期间,刘少奇发现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彭梅秀放不下天华这个“红旗大队”的包袱,阻止群众向他和工作队反映情况,刘少奇给予了严肃批评,并使彭心悦诚服。调查中,刘少奇一再启发群众讲真话,并且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及调查策略使群众讲出真心话。群众发自内心的诉说(甚至哭诉),使刘少奇为之震颤。“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深刻地指出: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麦子要割,食堂要办,这个事情人家晓得的,我们不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党内民主固然重要,但党内民主不能代替国家民主。他提出要充分发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他说,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要真正建立起来;党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要真正实行民主,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这种理论论述已论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保证问题,较毛泽东在会上的有关论述要来得深刻、具体。
在“大跃进”以来几年的调查中,刘少奇经常了解到下层有的干部为了讨好上面或掩盖自己工作的无能,不惜造假,说空话,瞎指挥。“大跃进”期间,各地的浮夸风愈刮愈烈,高产“卫星”越放越大,什么水稻亩产5千斤、玉米亩产5万斤、地瓜亩产30万斤,等等。听了这类报道,刘少奇非但没有喜悦之色,相反却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他曾斥责说“(水稻)亩产5千斤,肯定是吹牛!”[15] 当河北徐水县宣布“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这轰动全国的消息报道后,他亲自带队去徐水县考察。通过调查了解,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表明,徐水县的所谓“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吃公共食堂不要钱的平均主义和一张只画着电影院、图书馆却连居民区都没有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规划图”,他痛心了。“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对不作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指出:“最近几年,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决定问题时,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进行工作时,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他们听了一些假典型、假“卫星”,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他痛切地指出:有的人“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16]只有亲身经历了实地调查,才有如此发人深省之言。
综合刘少奇“大跃进”以来几年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上的有关论述,我们发现,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由此造成全国性经济动荡、人民生活困苦这种特殊年代,刘少奇通过深入而细致的调查研究,能够深刻把握问题的实质,“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的客观估计、对产生困难原因的分析、对犯错误的根源的探索,无一不是深刻反映了事物的本质,闪耀出真理的光辉。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对产生困难原因的分析基础上,刘少奇虽囿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仍从总体上肯定“三面红旗”,但在大会上已经对“三面红旗”发出疑问了,他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能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17]这又是一束来自调查研究的真理光芒。
收稿日期:1999—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