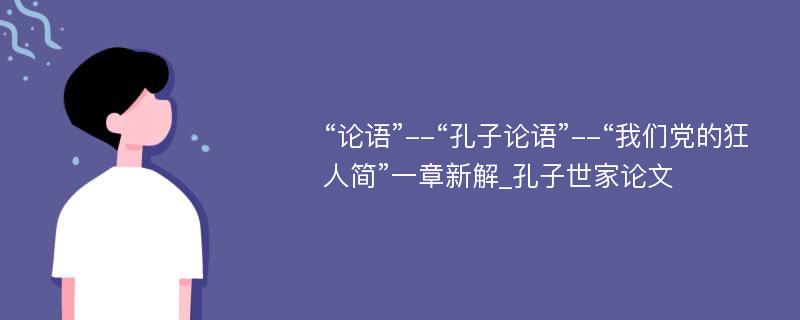
《论语#183;公冶长》“吾党之小子狂简”章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小子论文,新解论文,公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6-0046-06
一、前人旧解评析
《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篇多为孔子品评人物之语,此章则专论“吾党之小子”,亦不例外。
前人于此章之争论多集于一点,即“不知所以裁之”之主语,究为孔子本人抑或“吾党之小子”。由于此句主语省略,遂有如此歧义。一说以为:因说话人乃孔子,故当为孔子“不知所以裁之”。孔子称许“吾党之小子”狂简而又斐然成章,不需其教化陶冶亦能修身克己,卓然成才,是为赞赏之词。另一说以为:应紧承前句主语,乃“吾党之小子”“不知所以裁之”,其固狂简而又斐然成章,却不知以礼节之,如此则为孔子训诫之语。主语不同,此章所体现出来的孔子对“吾党之小子”的态度亦迥然不同。
其实,此二说均有据可凭。前说的依据是《史记·孔子世家》:
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其中引《论语》为“吾不知所以裁之”,加入了主语“吾”,显然属于前说,可简称其为“司马说”。《史记·儒林列传》又引此章以证鲁地儒学之盛,自然认为这是孔子的赞美之词。
后世学者中,郑玄《论语注》、戴望《论语戴氏注》和刘宝楠《论语正义》均依“吾不知所以裁之”作解。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363号墓所出之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此处正文作“吾不智(知)所裁之”①,也有“吾”字。清人戴望《论语戴氏注》此处正文作“吾不知所以裁之”,注云:“言虽己亦不能加之裁制,美大之。”认为这是孔子对吾党之小子的赞美。刘宝楠《论语正义》则据《史记·孔子世家》说解此章,亦持此论。
后说则源于西汉孔安国之见,可简称其为“孔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云:
简,大也。孔子在陈,思归欲去,曰: “吾党之小子狂者进取于大道,妄穿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当归以裁制之耳。”遂归也。支持此说的有皇侃、邢昺和朱熹等人,何晏既然引用其说,肯定也是赞同的。
而笔者认为,两说相较,孔说更有说服力:《论语》本文不当有“吾”,此章也当为孔子对“吾党之小子”的训诫之词。理由有四:
1.《史记·孔子世家》之引文与《儒林列传》相抵牾。
此章两见于《史记》,除《孔子世家》外,《儒林列传》引为:“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此处引文与《孔子世家》几乎一致,惟独没有“吾”字。《史记》不同篇章引用《论语》中同一段话,却有如此歧异。这就使我们对《孔子世家》引文的可靠性产生一些怀疑。
2.《史记·孔子世家》之引文与裴骃注相抵牾。
《孔子世家》引文下有裴骃注,《史记集解》引孔注疏解此句。而孔注又是按“不知所以裁之”来解释的,与其《史记》引文相抵牾。可能裴骃所看到的《史记》在这里并没有“吾”。
3.《史记》之前的定州简本《论语》没有“吾”字。
今核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汉代简本《论语》,此章作:“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间,[斐然]成章,不智……”②也没有“吾”字。而定州简本写成于西汉初年,在司马迁之前。
4.郑玄注之义理实与孔说一致。
吐鲁番唐写本郑玄注本《论语》虽有“吾”字,但其注云:“狂者进取而简略于时事,谓时陈仁(人)皆高谈虚论,言非而博,我不知所以裁制而止之。”郑玄其实也并不认为这是孔子对吾党之小子的赞美,不是孔子感叹自己的学识没有资格裁制这些年轻后学,而是一种夹杂着无奈的抱怨口吻,意思是连自己这样的人都不知如何去裁制这些人了。郑说和司马说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有“吾”字,但对本文的理解却与孔说一致。
如此一来,《孔子世家》的引文是靠不住的,郑玄的观点又与孔安国殊途同归。司马说所赖以支撑其立论的两条最重要的依据就已经不成立了。在这两派中,我们当以孔安国、何晏、皇侃、邢昺、朱熹等人的看法为佳。但笔者以为,即便是孔说,其实也并未能将本章之意旨理解得完全正确,笔者愿意在本文中提出第三种解释。
二、“吾党之小子狂简”章新解
司马说和孔说在最后一句的主语是孔子还是吾党小子上有争论,在这段话的态度是训诫还是赞美上也有争论,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狂简”和“斐然成章”都是用来形容“吾党之小子”的,而且是因为“狂简”,所以才“斐然成章”。无论历代学者如何解释这两个词,最后都将二者看作是“吾党之小于”的特点。而笔者以为,说“狂简”是“吾党之小子”的特点,这没有问题;但“斐然成章”则要另当别论,因为它并非紧承“狂简”而来,而是和下文“不知所以裁之”相连属。我的理由包括以下三条:
(一)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狂简”和“斐然成章”体现了相反的特征,彼此矛盾。
1.狂简:
前人对“狂简”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情况:
其一,将简释为大,此为古书中之常训。但进而又引申为大道,将“狂简”释为“进取于大道”,为动宾结构。孔安国、皇侃、邢昺皆主此说。
其二,以“狂简”为并列结构,仍释“狂”为进取,即志向远大,却释“简”为略。比如朱熹《论浯集注》:“狂简,志大而略于事也。”戴望《论语戴氏注》:“狂者,进取于古,其志嘐嘐然。简者,识大有所不为。”
前者将“简”说成是大道,未免过于牵强,而将“狂简”释为“狂于大道”,于语法不合,亦有增字为训之嫌。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研究孔子思想,最可靠的材料就是《论语》。而在《论语》中,狂和简这两种品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以礼节之”,是不得乎中道之后退而求其次的选项。
先说“狂”。
《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认为狂和狷是两种偏激的处事态度,一个过于进取,一个过于谦退,都不合于礼所要求的“中庸”精神。最好的做法自然是“得中行而与之”。如果无法做到,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狂或狷。《先进》篇中的一章恰可做“狂狷”二字的注脚: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 “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和冉有问孔子同样的问题:“闻斯行诸?”但孔子对子路说要听父兄的意见再行动,而对冉有说要马上行动。公西华不解,便问其故。孔子说是因为子路“兼人”,争强好胜,所以教导他在做事之前要多听听父兄的意见。而冉有为人谦退,其缺点就是临事不决,所以孔子教导他做事要果决,敢作敢为。子路就可以算是“狂”,冉有就可以算是“狷”。
孔子多次批评子路的“狂”,其原因就在于狂是一种失礼的表现。《先进》篇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也体现了狂、狷与礼之间的关系: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孔子让众弟子各言其志,子路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嘲笑他,是因为“为国以礼,其言不让”。子路的话太过好强,说了半天治国之道,不是强兵,就是足食,其目的在于“摄乎大国之间”,都无关于礼乐教化,因此孔子认为他忽视了“礼”的作用,“其言不让”。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狂是一种失礼的行为了。
冉求说: “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孔子对这样一种谦逊的态度也并不赞同,因为冉求也只是在做一些“足民”的工作。至于礼乐教化,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做,所以才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他和子路一个谦退,一个进取,但都没把礼乐教化纳入到治国的轨道中来,这就都是失礼之举。所以孔子说:“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狂是一种失礼的行为,这又具体地表现为“不好学”。《阳货》篇云: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后三句意旨相近,“直”、“勇”、“刚”三者大同小异。《泰伯》:“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可与此相印证。可见,此处所说的“学”就是学礼。如果一个人好刚却不学礼,其弊端就是狂。
《泰伯》:“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可见,孔子将“狂”和“直”看作是同一种品质。孔子认为“直”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为政》:“举直错诸枉,则民服。”《雍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季氏》:“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阳货》:“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但这却不是最好的品质,离君子的境界始终差点,比如《卫灵公》篇云: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 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无论“邦有道”还是“邦无道”,史鱼都是正直如矢,一味进取,这就是“直”;而应当像蘧伯玉那样,懂得何时应当进取,何时应当谦退。
再说“简”。
《雍也》篇中说: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问孔子怎么看子桑伯子这个人。孔子说这人不错,就是过于简,也就是不重视外表的修饰。但仲弓认为只要内心恭敬,行事简略也是可以的。孔子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最后同意了仲弓的看法。这番对话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孔子认为一味的简就容易失礼。
曾子曰:“巧甲甚则相简也,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庄足以成礼而已。”(《说苑·谈丛》)
这段话告诉我们,过于简是不能“成礼”的。
而“简”又类似于“质”、“易”和“野”这样的概念,与“文”相对。《说苑·辨物》: “孔子曰:‘可也简。’简者,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
一味的简是不对的,对于个人修身来讲,应当做到文质兼美,内外兼修,也就是《礼记·中庸》所说的“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对于治国齐家来讲,也应当文之以礼,做到制度简易而又完备,正如《韩诗外传》卷五所说: “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义简而备,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
程树德在《论语集释》按语中指出:“‘狂简’,《子路》篇作‘狂狷’,《孟子》作‘狂獧’。《说文》无‘狷’字,应作‘獧’。简、獧声相近,狂简即狂獧也。”他认为“简”通“獧”。诚然,二字在上古音中同属元部,读音相近。但笔者并不赞同此说。因为《孟子·尽心下》中,万章问孟子:“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这里引用孔子的话,用的是“狂简”一词。狂是进取,獧是谦退,意义相反。但万章却只说孔子思“狂士”,并未提及“獧士”。可见,“狂”和“简”意义相近,“简”不可能是“獧”。
综上可见,“狂”和“简”都是缺乏礼仪约束的处事态度。而与它相对的是“文”,也就是本章所谓的“斐然成章”。
2.斐然成章:
斐,《说文·文部》:“斐,分别文也。”本义是形容布帛纹理分明、光鲜亮丽,如《诗经·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后用以形容人的修养,如《礼记·大学》引《诗经·淇奥》:“有斐君子。”
章,就是布匹上的纹理,又特指赤色和白色的花纹。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五章,奉为五色。”杜预注云:“赤与白谓之章。”又可以用来形容人的修养。如《诗经·小雅·裳裳者华》:“我觏之子,维其有章矣。”
因此,“斐然成章”是说布帛上的纹理光鲜亮丽。历代学者也基本是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的。他们的区别在于:若持司马说,认为孔子是在赞美吾党之小子,则“斐然成章”也是一种赞誉;若持孔说,认为是孔子的训诫,则“斐然成章”就成了孔安国所说的“妄作穿凿以成文章”。我们认为,“斐然成章”和“不知所以裁之”共同充当一个比喻,说详后文。“斐然成章”则用来比喻“文”这一品质,也就是注重用礼仪规范来修饰自己。
上文说“狂简”的表现是不好学。那么,如何用礼来修饰自己,使自己“斐然成章”呢?其实也就是一个“学”字。《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子贡问孔子,孔文子为什么以“文”为谥?孔子说是因为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正是由于不断地学习,才使得他成为一个善于用礼仪修饰自己的人。《逸周书·谥法解》:“学勤好问曰文。”亦即此意。关于学、文、礼三者的关系,可以参看以下几章: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这几章都表明了达到“文”的途径是“博学”,再用学到的东西约束自己的言行,也就是“约之以礼”。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狂简”是一种不懂得礼仪修饰的表现,也就是“质胜文则野”,其原因在子不好学;而做人则应当博学,用学到的礼仪规范匡正自身,以期达到“文”的境界,这样才能算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狂简”与“斐然成章”体现了相反的特征,彼此矛盾,不能同时用来形容“吾党之小子”。
(二)《孟子》引用此章的情况可以说明“狂简”和“斐然成章”当分属两句。
《孟子·尽心下》中,孟子曾与万章就《论语》中的这句话展开讨论: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处万章只说到“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是对“狂简”的解释。如果万章认为“斐然成章”是紧承“狂简”而来的,那就会一并引述出来,而不会笼统地称之为“狂士”。在孟子的解释中也并没有提到“斐然成章”,可见“吾党之小子狂简”与“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是相互独立的两句话。这样,万章只引用前面一句就比较正常了。
(三)“斐然成章”与“不知所以裁之”可以共同充当一个比喻。
既然“狂简”与“斐然成章”是相反的概念,又分属于相互独立的两句话,那么,“斐然成章”只能连属于下句“不知所以裁之”。
前人基本都能将“斐然成章”解释为“文貌”。但根据上文的分析,“斐然成章”其实就是说布帛纹理鲜明。但前人多将其抽象意义提取出来,解释为“礼文”。我们认为,这里其实就是个比喻而已,并不抽象,也并不复杂,只不过是用裁制布帛之事比喻成德成才罢了。
前人基本都将“裁”训为“节”或“制”,相当于“约之以礼”的意思,是一种抽象的行为。其实,这样解释未免迂曲。试想,孔子为何不直接说“不知所以节之”呢?就像《学而》篇中有子所说的“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一样。其实,这里就是在说裁衣的事。
这一点明确之后,我们再重新审视此章,梳理其脉络,便可作出如下解释,也就是我们给出的新解:孔子是在说,“吾党之小子”志向远大,却过于进取,疏于礼仪。没有礼的约束,他们就不知道拿什么来匡正自身,成德成才。这就好像一匹纹理鲜明的布料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却不知拿什么去裁制它,把它变成一件衣服一样。
“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和“不知所以裁之”这三句话,前人基本都将前两句摆在一起,认为都是在说“吾党之小子”的特点,而又集中地去探讨第三句的主语到底是谁。而笔者以为,后两句可以组成一个比喻,应当放在一起。由于前人多数都把这两句话看得太抽象了,所以才没有发现这其实就是个比喻而已。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呢?其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三、“吾党之小子狂简”章背景管窥
《论语》中对于此章背景的描述只有三个字:“子在陈。”“吾党”之“党”近于乡党。孔子在陈言“吾党”,故前人多释为鲁国。 《子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是楚国叶人,孔子跟他说“吾党”,应该也是说鲁国。
关于其具体背景,前人多认为是孔子在陈既久,思欲返鲁,裁制小子,故兴此叹。孔安国注云:“孔子在陈,思归欲去,故曰吾党之小子狂简者,进取于大道,妄作穿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当归以裁之耳。”皇侃、邢昺、朱熹皆从其说。
然而此说只是从“子在陈”和“归与”这样的只言片语中猜测出来的,而且只能体现出孔子周游列国不受重用的无奈心情,与“狂简”这一具体内容并无关联。说他“思归欲去”,其实也并没有真的去陈归鲁,因为他离开陈国之后去的是卫国,距他晚年返鲁尚有数年之差。
至少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孔子并没有因为这一句感叹而离开陈国,因为这不合乎《论语》体例。笔者发现,《论语》中一旦涉及孔子转徙他处之事,一定会明确写出来的。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微子》)
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
孔子离开鲁国是因为季桓子接受了齐国送来的女乐。后来孔子在齐国不得重用,齐景公以年老相推脱,于是孔子离开齐国。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又使孔子离开卫国。这三处都明确说“孔子行”或“遂行”。而“吾党之小子狂简”章则没有。因此,说此章的背景是孔子离开陈国,这是说不通的。
关于其背景的另一种说法,则源于《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陈。……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这里将《论语》中的话和《孟子》引《论语》的话放在两处,又说孔子两在陈,均殊无道理,前人早已有所批判,本文不赘。公元前492年,季桓子去世,季康子即位,遂任用冉求做季氏宰,当时孔子正在陈国。季康子召冉求之前,曾征求过孔子的意见,《雍也》篇云:
季康子问: “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最后,季康子在子路、子贡和冉求之间选择了冉求。其临行赴任之时,孔子便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综合考虑以上这些记载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这一章所透露出来的某些细节,我们可以为这一章的背景找寻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一) “吾党之小子”云云,到底是在说谁?
前人有两种看法:一说以为泛指鲁国后生末学之士,如皇侃:“小子者,乡党中后生末学之人也。”邢昺:“吾乡党之中末学之小子等。”另一说以为指在鲁之孔门弟子,如朱熹:“吾党小子,指门人之在鲁者。”笔者赞同朱说,因为古书中大量例证可以说明:“小子”主要用来指门人弟子。相关用例引述如下: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 《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论语·子张》)
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于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离娄上》)
仲尼闻之,曰:“小子识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晏子春秋·问下》)
孔子曰:“固哉, 由也!《诗》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风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于斯不赠,则终身弗得见也。小子行之!”(《子华子·孔子赠》)
颜渊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下席而问曰:“小子敢问,回东之齐,夫子有忧色,何邪?” (《庄子·至乐》)
弟子曰:“……”庚桑子曰:“小子来……”(《庄子·庚桑楚》)
宰我闻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小子识之!”(《列子·黄帝》)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韩诗外传》卷七)
宰我曰:“昔者,予也闻诸夫子曰:‘小子无有宿问。’” (《大戴礼记·五帝德》)以上数条,凡称“小子”之处,皆是老师对弟子的称呼或弟子与老师交谈时的自称。
《史记·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 ‘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司马迁在这里引用此章,意在证明“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可见,司马迁也认为这里的“小子”并非泛指后进末学之士,而是专指孔门弟子。
(二)冉求赴任,孔子单单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这又是为什么?
笔者以为,其中别有深意。孔子是希望冉求能够借任季氏宰的机会,用礼去引导在鲁之弟子的狂简习性,因为冉求本人正是一个温良谦退之人,具有很好的垂范作用。关于冉求的谦退品质,上文所引之“闻斯行诸”章和“子路、曾晢、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已可观其大概,另《雍也》篇云: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冉求为人优柔寡断,遇事犹豫不决,所以孔子才会鼓励他“闻斯行之”;孔子弟子各言其志,他不敢以贤者自居,便自称“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在这一章里,他又自愧不能践行夫子之道,结果就被夫子斥为“中道而废”。以此诸事,足见冉求崇尚谦退的品格。“吾党之小子狂简”,盲目进取,不顾礼仪,恰恰就需要冉求这样的人来约束“吾党之小子”。
孔子认为“狂简”的根源是,“不好学”,而冉求恰恰是一个热爱学习,崇尚学习的人。《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说冉求是:
恭老恤孤,不忘宾旅,好学省物而不③懃,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语之曰:“好学则智,恤孤则惠,恭老则近礼,克笃恭以天下,其称之也,宜为国老。”
冉求还曾向鲁哀公陈说过学习的重要性,见于《韩诗外传》卷八:
鲁哀公问冉有曰:“凡人之质而已,将必学而后为君子乎?”冉有对曰:“臣闻之,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
让这样一个温良谦退、好学善思之人代替自己去熏陶那些在鲁之弟子,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令孔子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冉求却为虎作伥,帮助季氏聚敛财富,以至于孔子对众弟子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季康子问孔子曰:“厓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孔子对曰:“如求。”
季康子能够向孔子请教,那一定是孔子返鲁之后的事。他同时问到了冉有和子路,那就当是二人同为季氏宰之时。从这番对话中,我们能够看出孔子对冉求之聚敛已经深恶痛绝了。看来,冉求并没有像孔子所期望的那样。
通过上文对“吾党之小子狂简”章的分析,我们不仅对其意旨做出了全新的解读,而且还对冉求任季氏宰的背景多了一些认识。此章意旨深远,若不经这番分析,很多字里行间的滋味就会这样轻易错过。这一章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品评,而是在其中蕴含了孔子对冉求的殷切寄托。他曾经苦口婆心地期望冉求能够遵行自己的志愿,为在鲁之弟子做出表率,但最终事与愿违。连好学知礼如冉求者亦且沉沦于乱世之风,为僭臣贼子聚敛积蓄,而浑忘复兴王道之重任,又何况于他人呢?恐怕孔子在批评冉求的时候,想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弟子的沉沦,而是一个时代的倾覆吧。千载之下,每思及此,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收稿日期:2010-01-13
注释:
①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②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③“不”当为衍文,《孔子家语·弟子行》作:“恭老恤幼,不忘宾旅,好学博艺省物而勤也。”说见[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12引王念孙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