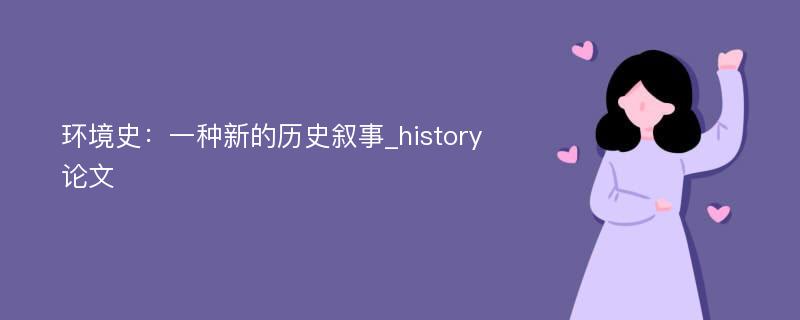
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7)03-0038-07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为这次会议提供背景材料的非官方报告《只有一个地球》的前言中写到:“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地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个行星。”[1](前言p.10)对于这一说法,有史家作了这样的延伸:“如果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国家需要关心,那么,我们也有两种历史需要书写,这即是我们国家的历史,以及‘地球这个行星’的历史。并且,到了我们开始询问第二种历史是什么的时候了;我们开始不仅仅探寻这个或那个孤立于其他所有民族而生存的民族的历史——赞扬他们的成就或追踪他们的罪恶,而是要探讨在宇宙中一个日益缩小的岛屿上相互碰撞与合作的所有民族的历史。”[2](p.6)现在,对联合国的报告和历史书写作上述解读的史家有了自己的称号,叫环境史学家;他所探寻的第二种历史也有了自己的学名,叫环境史。这一历史大体兴起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此后不断发展①,其研究范围和主题一步步拓宽②,已涉及整个的世界、大大小小的区域、许许多多的国家,以及不计其数的专题,成果十分丰富。这一历史不仅以自己的特色屹立于世③,而且开始影响着上述的第一种历史④,因而在现时代的历史研究中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对于环境史的学理及意义,中外研究者已从定义与主题、性质与特征、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探讨和分析⑤。本文拟选取历史叙述的一些方面⑥,进一步认识环境史的革新意义。
一、环境史叙述的对象和重点
环境史,按照唐纳德·休斯的定义,“是一种试图理解在时间变迁过程中,人类生存、劳作和思考时与其周围自然环境之关系的历史”[3](p.1);环境史研究的一个明显结果,是使史家的视野从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察扩大到了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历史探询,由此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自然史与社会的历史相关联的历史叙述模式⑦。这样,环境史在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与文化史之后,成为了历史编撰和叙述的新类型。[4](p.95)那么,环境史叙述的新意体现在哪里呢?这里,我们首先从叙述的对象和重点来分析。
概言之,环境史的叙述对象,是在时间流变中存在着的人与自然之关系。而与“自然”发生关系的人,不仅仅有政治史中的“大人物”,还有社会史中的“小人物”,这样,环境史必然将大大小小的历史人物囊括其中⑧。此外,在环境史研究者的笔下,人,不仅仅以文明的创造者和历史的推动者之形象出现,而且还以垃圾的制造者和自然的干扰者之角色登场。⑨另一方面,环境史中的“自然”,不仅涉及滋养世间万物的大地,而且涉及晴雨交替的天空⑩……因而,环境史将上上下下的自然景致尽收眼底。此外,自然并非静止不变,也并非死寂一片。相反,自然是充满生机的,是与人一起共同作用于历史的活跃的因素;是慈爱的“母亲”,也是可憎的“女巫”,诸如之类的思想观念,也是环境史研究者纷纷表达过的。(11)其中,常被人提到的,是克罗农的这一说法:“……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也作用于历史,重大的自然进程同样如此。这样,忽略它们之影响的任何一部历史,都可能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12)这样,环境史研究和叙述必定围绕人与自然之关系及其变迁,来解释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述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的影响及其对人类自身的反作用。
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什么?从实然的层面说,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基本方面,如科学家所说的.是一种交换关系,即:人与自然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发生相互的作用。这种交换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的?是互惠互利?相互加害?还是利害参半?只要仔细想一想,人与自然各自交换着什么,交换的结果又如何,上述问题的答案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言而喻,自然像聚宝盆,献给我们茂密的森林、宽阔的草原、清澈的河水、翠绿的山岗……一句话,自然以其丰饶的馈赠,养育着我们人类,让人类感受到她的慷慨施与。另一方面,自然又像女巫,用干旱、洪水、地震、海啸等灾害诅咒和毁灭人类,让人类在她面前不寒而栗。这一切是福还是祸,对自然来说,是无意识的,也是无意义的。并且,“非人类行为通常是我们所不能评判的”[5](p.1370);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也只能尽量谨慎地防范,并要不断地自我检讨。(13)人类需要检讨和自问的一个问题则是,我们还给自然的究竟是什么?
人,并非像牛一样,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人,在消耗了大自然的馈赠之后,还给自然的却是固体的、液体的、气体的废物或垃圾;而且,随着文明的日益发展,人类从自然索取的物质越来越多,返还给大自然的垃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毒,越来越有害。结果,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还是从环境史的主题研究中看到了大地沙尘滚滚(14)、天空青烟袅袅(15)、河流越流越脏(16)的情景。另一方面,环境史的著述也让我们看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少到一个人,多到一群人,他们表达了对自然的关爱与呵护;(17)或者某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它们体现了与自然友好相处的可能。(18)
就这样,人与自然之间早已结成并不断延续着那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这对关系而一再演绎的或悲壮或凄美的故事,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抑或本属天人共演的故事,恰是环境史叙述的重点所在。讲述这样的故事,并通过讲这样的故事,来再现本来存在着的那部分历史,是历史学应有的任务。而且,由于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我们已知的就很多,我们未知还不知有多少,就需要更多的人来研究环境史,叙述环境史的故事。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环境史研究和叙述的行列;“历史上的人和自然”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亦成为不争的事实。(19)
二、环境史叙述的主体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环境史与历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其研究和叙述的主体,多半是职业史学工作者,如唐纳德·沃斯特、约翰·麦克尼尔、伊懋可等国际知名的环境史学家,他们莫不拥有像样的大学教席。但是,与历史学的其他领域相比,环境史叙述的主体至少有两点重大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首先,环境史的研究和叙述并非只能由职业史家来承担。相反,不仅“地理学、哲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学者”撰写了大量的环境史著作,[3](p.8)而且并非专家的环境史叙述者也在不断涌现。关于前者,学界已有较多的论述(20),这里仅就后者举例说明之。
在非专家型的环境史叙述者中,澳大利亚的恩里克·罗斯(Eric Rolls)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罗斯原本是一个农场主,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和自然主义者。他还做过广播员,也被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21)。当然,他肯定不能被纳入职业史家的行列,因为他既不在某个大学也不在某个研究机构任职。不过,正是这样一位虽具多重身份但并非职业史家的作者,却奉献了有关澳大利亚环境史的诸多著述。(22)对欧洲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这片土地及其上生长的动植物的情况,他作过这样的描述:“欧洲人来的时候,这片土地上的覆盖物已存在好几千年了。这儿的表土十分松软,你用手指就能耙动它。它既没有被轮子碾过,被皮后跟踩过,也没有被裂开的蹄子踢过。虽然挖掘用的棍棒刺伤过它,但从没有铁铲翻动过一整片草地。我们的大型哺乳动物并不蹂躏它。忙碌的袋鼠三五成群,分散移动,不像羊群和牛群似的,走到哪都像锉刀一样毁掉一切。那为数众多的袋熊每一只都会守住几个地洞,这样,它惯常出没的地方就不像兔子窝似的绕某一个中心向外辐射。而每一种食草动物都有两排锋利的牙齿,将咬断的植物吃得干干净净。其他任何土地都不曾被这样温柔地对待过。”[6](p.22)从罗斯的叙述中我们还了解到,18、19世纪初来乍到的欧洲殖民者——那些有名有姓的绅士淑女留下了大量的相似的记载。他们说“这片国土很浪漫,大自然将它装点得美轮美奂”;“新南威尔士是一片野花盛开的花园”;昆士兰的翡翠乡(the Springsure-Emerald country)“绿草如茵,五颜六色的野花镶嵌其间”。[6](pp.22-23)罗斯在其著述中还介绍了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火耕文化,并说到:“土著人不喜欢森林,因为光着脚丫进林子很不舒服,而且森林供养不了太多的猎物。欧洲殖民者来了以后,扰乱了土著人的生活,大片的林子很快地得到发展,这样,拿着斧子的欧洲人就涌入了。”[6](p.25)进而,由于欧洲人的畜牧业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很多植物枯死了,很多地方裸露出来了。
恩里克.罗斯的这些叙述,虽然有其明显的认识局限(23),但它们至少从一个方面增进了人们对澳大利亚环境变迁情况的了解。像恩里克一样,其他的人,无论环保工作者,还是普通大众,只要他愿意,只要他有心去做,并遵循一定的叙述规范(24),他都可以成为环境史的不凡的叙述者(25)。对于他们所发表的有关作品,即便是专业史家,也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26)
第二,环境史研究和叙述者与以往的历史学者不同,他们在从事自己的工作时,除了视觉之外,还必须充分调动其他的感觉器官;只有视、听、嗅、触、尝无所不用,才能全方位地接近和感知所研究和叙述的对象(27)。而且,即便是视觉,仅盯着文字也很不够;树木的年轮、孢粉、画作等等,都是环境史家用以观察自然环境并获取有关数据以及了解人们对环境之感知的重要来源(28)。再者,即便是文字,环境史家也不满足于阅读正史、方志或档案等材料;他们还欣赏诗歌、戏剧和史诗(29),从中寻觅历史上的环境认知,也包括古代环境问题的蛛丝马迹。
环境史叙述主体本身的这些变化,无疑是环境史研究不断地向下探索,以致“深入到作为历史中的能动力量和存在物的地球本身”的结果。这正如沃斯特所说的: “在这儿,我们将发现自始至终在起作用的更为基本的力量。并且,为了去鉴赏那些力量,我们必须不时地走出议会大厅,走出产房和工厂,义无反顾地步出家门,去原野、森林和空旷的户外漫游。”[2](p.289)这样,环境史叙述者必然会打破历史研究中惯常的文本优势和视觉霸权,去用心观察,去侧耳聆听(30)。所以,如果说,学术研究不应“闭门造车”(31),那么,对于环境史研究和叙述者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此外,就像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多弗斯(Stephen Dovers)所分析的,由于“所需要的信息散落各地,而且并不充足,这样一来,对于正式的学术调查程序来说,就存在很多局限……那些非专家式的人物常常敢于冒险,比专家说得更多,因为专家受到了严格的正式的分析过程的约束。”[6](p.12)于是,在讲述环境变迁之故事的事业中,在涉及自然万物的诸多领域,业余爱好者亦可大显身手。更何况,由于“地球这个行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家园,对家园的关爱,是“地球村”的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而讲述与自然关联的故事,并通过讲述这样的故事来认识自然的变迁及其缘由,进而反观人类自身的行为及其影响,也是现代公民尽职尽责的一种体现。因此,在环境史的事业中,人人都可以是也应该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32)。
三、环境史叙述的寓意和目的
迄今,环境史的叙述者在讲述人与自然的故事时,大都是以某一地方的某群人与那个地方之上的他物之间变化着的关系为主线,选取这变化着的关系中的某一段,来铺陈变化从何时开始,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其结果又如何等。如果要进一步明晰环境史的叙述结构,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抽象:从前,在某个地方,有一群什么人,和一群什么物,它们之间为了什么、怎么样而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什么结果。而从现有的环境史文本来看,这一“结果”对人和自然而言,好像大都是“苦果”或“恶果”。换言之,现有的环境史著述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环境史叙述和勾勒的历史画面之基调是冷色、昏暗的,带有阴郁、衰退的特征,与长期以来我们所熟知的历史进步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被归结为“衰败论”叙述(‘Declensionist’ Narratives),并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3](pp.99-100)
对于环境史的这种叙述,我们当然要像认识历史进步叙述所存在的线性进步观及其危害一样,警惕其所隐含的脱离历史语境的衰退观及其局限。但是,笔者认为,问题的本质并不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是,在今天这个“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一批职业的或非职业的学者人士所作的环境史叙述的寓意在哪里,由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环境史的当下意义或目的。
说起环境史,人们无不认识到,它是二战之后兴起的现代环保运动推动的结果,有学者甚至说“没有现代环保运动,就不会有环境史”(33)。换言之,在20世纪中后期,人类在饱受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危害之后,痛定思痛,需要了解环境问题产生的历史,揭示造成环境问题的或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于是环境史应运而生,它“将人类事件放在生态系统的背景之下进行叙述,探讨每一个时代人类事件与自然交相作用的历史”,[7](p.9)以追寻自然现象之背后隐含的人类活动的踪影。结果,环境史的叙述就突破了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范畴,而扩大到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乃至整个地球。这样的史学实践活动,在极大地拓宽历史视野和历史研究单位的同时,必然引起认识和评判人类行为之参照系的变化。环境史,说到底,就是更换了评估人类行为的参照系,它不再以短期利益而是以长期效应来看待人类的行为。于是,人类行为是祸是福,是谁之祸、谁之福,就不再只是从人类自身来看待,还顾及到了共有这个星球的其他事物乃至这个星球本身的利益和命运。这样一来,环境史的叙述有时就可能使那些从前的历史英雄不再那么英明神勇(34),并且人们一贯视之为真理的知识和观念都开始经受着重新评判和估价(35),历史从而不再是一片玫瑰色。这正是环境史叙述的一个革新之处,也是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异化之历史真相的反映。就此而言,环境史家常用的“自然之死”、“地球的终结”(36)等短语,即隐含了以对自然的生死之忧来重估人类行为的重大寓意,由此环境史的叙述必然游离自然之境,而进入人类的价值王国(37)。
的确,环境史的叙述让我们看到,在人世间的许多灾难中,有的可能是自然所为,有的可能是人为之果,有的可能是人与自然合力所致。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的“尘暴”为例,沃斯特的相关研究和叙述表明,尘暴,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生态灾难,是美国文化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依沃斯特之见,尘暴的发生,与同时代的经济大萧条具有共同的根源,那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文化;尘暴和大萧条暴露了美国文化的根本弱点:“一个是生态意义上的,另一个是经济上的”。[8](pp.3-4)他还将资本主义精神所教导的生态价值观概括为“三句铭言”:1.“自然必须被当作资本”;2.“为了自身不断地进步,人有一种权利,甚至是义务去利用这个资本。资本主义是一种急于向最大极限发展的文化,总是设法从世界的自然资源中获取比它昨天的所得要多的东西”;3.“社会制度应该允许和鼓励这种持续不断的个人财富的增长”。[8](p.6)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农业的目标“不是简单地维持生活,而是赚钱”。在农业企业家看来,大自然对他们所施加的遏制和社会制约一样可恶。“在自由放任的不断扩张的1920年代,大平原被大面积开垦,小麦轮作变成了高度机械化的工厂式的农场”;[8](引言p.7)而对土地的破坏性使用受不到任何遏制,“资本主义的破坏因素”在美国南部大平原的开发过程中得到了“突发性和戏剧性”的表现。“在大平原社会中没有任何东西去制约商业性耕作的发展,也没有任何东西去防止商业性耕作为了利润而冒的风险。这就是尘暴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原因。”[8](引言p.7)
沃斯特这样来叙说和解释尘暴,并不表明他认识不到自然因素与尘暴灾难的关联,其实他很清楚“自然也做了某些与这场灾难有关的事情”,所以他说道:“没有大风,土壤就会一直呆在那儿不动,不论它是如何地裸露着,没有干旱,农场主们就会有能够抵御风沙的茁壮健康的作物。”[8](p.7)但他强调,自然的因素只是使尘暴成为可能,它却没有制造尘暴。尘暴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地面上的天然植被已被剥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那里没有了抵御干燥的风的屏障,没有草皮来固着多沙或粉状的尘土”;而毁坏草皮的目的,则是为了建设农场、种植小麦以赚取钞票。显然,沃斯特在认识和研究“尘暴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时,是有他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的。这就是,将貌似自然现象的“尘暴”灾难,与人类的作为和欲求勾连起来,并聚焦于人的行为、思想和价值观而加以重新评判。这样的做法,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在沃斯特眼中,“尘暴”既是美国环境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又是“一个越来越关乎人类未来的事件”。他坦陈,他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是希望能让大平原这个地区及其命运成为读者们关心的对象,就像他自己关心它们一样。[8](引言p.2)这样,沃斯特的尘暴叙事画面虽昏暗并带悲剧色彩,但其动机却十分明朗而积极,即是要通过“尘暴”这样的历史叙述来引发人们对尘暴故事上演之地的关怀(38)。如果《尘暴》可以被视为环境史的一部经典(39),那么也可以说,尘暴叙述在环境史叙述中颇具典型性。
环境史的叙述,简言之,是要讲一部我们人类所居住之地方的变化的故事,“就是要解释我们是如何到达我们所在的地方的:为什么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像这个样子”。[6](p.4)而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小到我们早夕栖止的地方,大到整个地球,其变化的故事无不可以成为叙述的对象。之所以要叙述它们,不仅是为了推动历史学的发展,而且是为了促使今天的人们更好地关心被叙述的对象——环境(大气、水、土地,等等)以及环境中的人,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存家园的呵护,同时审视自己对待自然和他人的态度与道德水平。而非职业史学工作者之所以能够成为环境史的叙述者,正是人们关心环境保护并不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体现。因为正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说的,拯救环境是“一场全球性的内战”,这场战斗所对抗的,不是法西斯那样的人类公敌,而是“现今世界文明的逻辑体系”,是人类向自己开战——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敌人,“而这场战斗的胜负将仅仅取决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充分觉醒,共同意识到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即“渐进的、日益严重的一系列生态灾难”。(40)这样,环境史的叙述虽然因为对生态灾难或环境问题的呈现而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甚至悲剧色彩,但这决不是中世纪基督教末世论的翻版,也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认识自身的行为及其影响,并促使人类跟自己斗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待的自然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一贯以来,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正确了解和评价是历史学的意义之源,环境史的叙述也就因为对人类如何创造历史的考量以及对人类行为的重新解释与评价,而具有了正当性和意义。
后记
本文应张广智先生之约,初作于2007年2月笔者旅日期间的某个星期。那时,案头上没有堆积如小山的文献,于是,只能凭借以往的些许积累,还有漫步于横滨街头和大冈川边偶得的灵感,在空荡荡的20平米斗室内任思想驰骋。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写作状态是何等的自由。所以,非常感谢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部的长谷部勇一教授。没有他的邀请,我就不会有那次到横滨国大作客座教授的机会,也就难得有那么一段安静而富于思考的时光。更何况,长谷部教授本人有关投入产出之产业关联分析的理论研究,对本人也是颇有启发的。
(2007年3月16日)
注释:
①现今世界各国对环境史都有研究。欧美国家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尤为丰富,这里仅列几本中译本著作供参考。[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美]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三联书店,2003年;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许友民、许学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德]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王国豫、付天海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美]斯蒂芬·派因:《火之简史》,梅雪芹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
澳洲、亚洲国家对环境史也有各自的研究。关于澳大利亚环境史研究情况,参见Stephen Dovers,ed.,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Essays and Cases,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关于南亚和东南亚环境史研究情况,参见David Arnold & Ramachandra Guha,eds.,Nature,Culture,Imperialism:Essays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s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Richard H.Grove,Vinita Damodaran,& Satpal Sangwan,eds.,Nature and the Orient: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近年来,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里仅列中国学者有关环境史研究的几项理论探讨成果:Bao Maohong,“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10(2004),475-99;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梅雪芹:《论环境史关于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刘向阳:《环境政治史理论初探》,《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②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主题,可参见唐纳德·修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一书中所作的总结(J.Donald Hughes,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pp.3-8)。
③环境史已成为史学的新领域,甚至被称为“21世纪的新史学”(唐纳德·沃斯特:《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侯深译,《世界历史》 2004年第3期,第6页)。
④参见[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9-94页。
⑤关于这些方面的具体内容,可参见:R.Nash,"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A New Teaching Frontier,"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1,no.3(1972); Donald Worster,"Appendix: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Donald Worster,"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6,4(1990),1089-1091; 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42,4(2003); J.Donald Hughes,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1-8.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高国荣:《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⑥关于环境史的叙述,美国环境史学家威廉·克罗农已作过分析,参见William Cronon,"A Place for Stories:Nature,History,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8,No.4 (Mar.,1992),pp.1347-1376;关于历史叙述的理论研究,参见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⑦拙文《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重点列举了有关环境史的几个定义,抽出了环境史的本质定义和研究对象,还分析了“环境史研究必然将自然史和社会的历史勾连起来”的道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第14页)。
⑧譬如在美国环境史学家卡罗琳·麦茜特主编的《绿色挑战金色》一书中,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人的声音,包括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黄金潮的淘金者、林务员、农场主、水利开发者、城市居民、科学家以及环境论者等(Carolyn Merchant ed.,Green versus Gold:Sources in California's Environmental History,Washington,DC:Islan d Press,1998)。拙文《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世界历史》 2006年第6期)专门论述了环境史研究中人的存在问题。
⑨其实,“人是自然的干扰者”之观念并非当代环境史家的创造,1864年马什在发表《人与自然》时,就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George Perkins Marsh,Man and Nature,1864.Edited by David Lowenthal,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在该书中,他系统地考察了环境恶化问题和自然资源耗竭的可能性,由此他甚至被视为“环境史的第一位先驱”(J.Donald Hughes,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30)。
⑩从学术性的界定来说,环境史中的自然,指的是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即“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普雷斯顿·詹姆斯等:《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页)。高国荣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专门论述了环境史对自然的书写问题(高国荣:《环境史学在美国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5月)。
(11)参见: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
(12)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此译文与笔者在其他地方引用该说法时所用的译文有些微差别,这是经仔细核对原文并考虑到中文语境中措词习惯的结果。此处原文是:"…human beings are not the only actors who make history.Other creatures do too,as do large natural process,and any history that ignores their effects is likely to be woefully incomplete" (William Cronon,"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Vol.17,No.3(1993),p.13)。
(13)夏明方先生阐述了人口增加、生产扩大与灾害次数的正比例关系,参见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14)如: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
(15)如:Peter Brimblecombe,The Big Smoke:A History o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16)如:Elizabeth C.Economy,The River Runs Black: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s Futur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17)关于个人对自然的关爱,可参见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2005年;林达·利尔:《自然的见证人:蕾切尔·卡逊传》,贺天同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关于群体组织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成立于1895年的英国“国民托管组织”(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是一个范例(参见:Jennifer Jenkins and Patrick James,From Acorn to Oak Tree: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Trust 1895-1994,Macmillan,1994)。
(18)关于与自然友好相处的文化或生活方式,美洲印第安人的例子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主题(参见:Calvin Luther Martin,Keeper of the Game:Indian-Anim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Fur Trad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19)2005年7月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将“历史上的人和自然”列为一大主题。
(20)参见:高国荣:《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
(21)"About the Authors," in Stephen Dovers,ed.,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Essays and Cases,v.
(22)Eric Rolls,They All Ran Wild,Sydney:Angus & Robertson,1969; Eric Rolls,A Million Wild Acres,Melbourne:Thomas Nelson,1981; Eric Rolls,"More a New Plant than a New Continent," in Stephen Dovers,ed.,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Essays and Cases,pp.22-36.
(23)譬如他关于兔子和袋熊之行为习性的描述,就停留于现象的揭示,而没能深入分析其行为差异的成因。
(24)对于环境史的叙述规范,克罗农阐述了三点(three narrative constraints):一是故事不能违背已知的历史事实;二是故事必须具有生态意识;三是环境史学家以社会成员的身份编写故事,工作时必须考虑社会因素,纯粹个人的意识形态不足以完全决定对史实的取舍、对语言的选择和与读者的交流(William Cronon,"A Place for Stories:Nature,History,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pp.1372-1373)。
(25)参见拙文:《环境史:一种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譬如,中国记者、“绿家园”的创办者之一汪永晨女士的《绿镜头:大自然的昨天和今天》(三联书店,2004年)“用照片和叙事,娓娓讲述自然和人类的故事”,就值得关注和研究中国环境问题的学者们阅读。
(27)在西方史学中,有关感觉史的著作已不鲜见,“感觉史的写作……把我们从启蒙时代开始的视觉霸权中解救出来,启发我们利用其他的感官更全面地去体验和理解历史,揭示经济、政治和文化互动关系……”笔者以为,这一方法在环境史研究和叙述中,尤其在对环境污染的追踪调查和研究中,将大有用武之地。而美国环境史学家雷蒙·斯米勒(Raymond Smilor)则开创了城市噪音史研究的先河。参见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2-301页。
(28)唐纳德·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中,特别谈到“温带地区树种的树木年轮与南极和格陵兰岛冰帽积雪层中积储的空气”,是考察历史气候的重要资料,参见:J.Donald Hughes,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12.
(29)伊懋可在《大象的退隐:中国环境史》一书中对诗歌,尤其是对张应昌编辑的《清诗铎》的运用,堪称范例。关于这部著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意义,包茂宏先生已作了详实、深入的分析,参见包茂宏:《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辑。休斯在《潘神之苦:古希腊、罗马的环境问题》一书中,对有关古代环境史的各种文献作了总结,其中,诗歌、戏剧和史诗赫然在列(J.Donald Hughes,Pan's Travail: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
(30)譬如,苏格兰环境史学家T.C.斯马特教授(T.C.Smout)就是这么做的。多年来,他养成了观鸟的习惯,以从鸟儿年复一年的到来和来的时间之细微变化中,感知不同年份季节循环的差异。2006年11月斯马特教授应笔者之约来北京讲学。这期间,我们一起参观圆明园、颐和园和长城。每到一处,他都不急于欣赏湖光山色,而是先聆听啾啾鸟鸣。据他夫人说,他几乎能从鸟的鸣叫声中分辨出鸟的种类。笔者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十分关注人们对自然的态度——是功利的使用还是审美的愉悦,以及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如何变化这类问题,这正是斯马特教授的一本著作的主题(T.C.Smout,Nature Contested: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Scotland and Northern England since 1600,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
(31)对此,有学者作了专门论述,参见:肖国忠:《学术研究不应“闭门造车”》,《光明日报》,2006年6月21日第6版。
(32)“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是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Carl Becket,1873-1945)的用语(见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将这一用语运用到环境史叙述之中,可以说是恰当不过的。笔者清晰地记得,在1998年8月参加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at Santa Cruz)举行的一个环境史学术会议时,所遇到的与会人员,除了史学家、林学家、生态学家等各类专家外,还有公园管理者、公司雇员、中学教师等。而在大会主题发言中,一位印第安老妪讲述的印地安人与自然相处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33)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高国荣的文章《什么是环境史?》
(34)参见:唐纳德·沃斯特:《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35)拙文《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对此作了专门的分析。
(36)“自然之死”和“地球的终结”分别是美国环境史学家麦茜特和沃斯特所撰写和主编的著作的名称,前者为《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Carolyn Merchant,The Death of Nature:Women,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后者为《地球的终结:对现代环境史的考察》 (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ry,Edited by Donald Worster)。
(37)克罗农明确指出,将人与自然勾连起来的环境史叙述,其主角和对手依然是人,它体现的是人类的价值之战。这些价值其实就是我们为可评判的人类行为所赋予的意义——非人类行为通常是我们所不能评判的,这样,“我们故事的中心将依然聚焦于人类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William Cronon,"A Place for Stories:Nature,History,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pp.1369-1370)
(38)克罗农说到,任何人读了沃斯特的《尘暴》之后不可能不为之感动:William Cronon,"A Place for Stories:Nature,History,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p.1374.
(39)参见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40)参见:[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陈嘉映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标签:history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