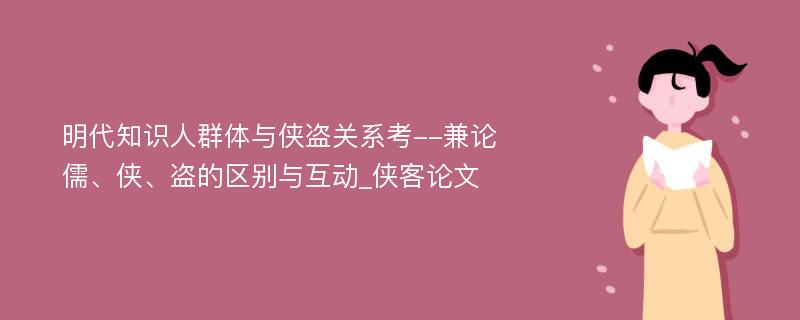
明代知识人群体与侠盗关系考论——兼论儒、侠、盗之辨及其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侠盗论文,明代论文,人群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2-0038-11
中国侠客史的演变历程,大抵可以唐宋为界,分前后两期。唐宋以前,战国、两汉“游侠”乃至六朝“轻侠”,应该说是侠客史的主流,进而形成一些游侠集团。换言之,前一时期的侠客史,相对比较纯净,其宗旨是崇尚义勇。自唐宋以后,纯粹的游侠已不复存在,而游侠集团亦日趋式微。代之而起者,则是侠客集团的内部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儒侠”的崛起[1-3],二是“侠盗”的勃盛。这种分化趋势,导致儒、侠、盗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最终蔚为一股儒、侠、盗合流之风。
时至明代,侠客史的发展出现了以下三大转向:第一,随着“儒侠”与“儒盗”之类概念的出现,知识人日趋侠盗化。在明代,无论是一般的读书人,还是士大夫甚或道学家,无不有尚侠之风。更有甚者,士大夫不仅“种盗”、“养盗”亦即庇护盗贼,甚至亲身为盗,具有一段投身绿林的传奇经历。第二,侠、盗之儒者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侠盗”这一概念的出现,乃至随之而来的文人士大夫为侠、盗大唱赞歌,以及盗贼投身到儒家学者的讲学运动之中。第三,侠客与盗贼出现一种互动的症候。换言之,随着侠客之堕落,以及盗贼之尚义,在侠客与盗贼之间,仅仅只有一线之隔。
毫无疑问,无论是儒者之侠客化乃至盗贼化,抑或盗贼之儒者化,无不是明代“社会流动”加剧的明证。这是相当值得关注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之外,王学崛起以后导致讲学的平民化乃至士风的突变,显然是最为直接的因素。
一、儒、侠、盗辨析
众所周知,始于韩愈的唐、宋道统观念,无疑已将道统观念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统绪结合起来,并将“道”界定为这些远古圣人相互传授的脉络。至宋、明两代,诸儒继续界说尧、舜所传之道的含义,最终确立了道统的权威。显然,先秦诸子将上古帝王系统理想化的努力,是唐、宋道统权威最终得以确立的基础。在先秦诸子中,除了儒家的孔、孟之外,尚有墨子,共同参与了古帝理想化的工作。传统中国的理想化人格,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先秦诸子的理想人格追求是“圣王”,而自秦汉一统天下之后,知识人所向往的则是成为一个“人儒”。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前者以天下为志,但玄远难能企及。后者以修身立己为本,多属切实可行的行为规范。”[4]2-3,22
儒者,柔也。汉代以后,“儒”与“士”合流,形成了“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儒士”。于是,儒者已成文弱书生的典型。至明代,随着文、武两分,学校亦开始分化,进而演变成“儒学”与“武学”。进入儒学者,属于“文生”,所读之书为儒家经典;进入武学者,属于“武生”,所读之书为武学经典与兵书。文弱儒者的演化历程,其典型之人格裂变,大抵有二:一为两汉之“经生”,其普遍的行为特征是皓首穷经、抱残守缺;二为宋明之“道学先生”,其群体之行为特征则是迂腐与伪饰。这显然是儒者人格的一种堕落,与原始儒者人格已相距甚远。
侠之定义,众说纷纭,但大抵可归为两类:一是语言学家与文献学家的解释,二是历史学家的看法。就前者而言,无论是《说文解字》,还是《史记集解》所引唐初司马贞《索隐》,或将“侠”通于“俜”,或将“侠”通于“挟”、“持”,凡具有轻财仗义而又能强力雄霸地方之特征的人,可称之为“侠”。今人将侠之原义定为挟持大人物并供其役使之人[5],亦由此引申而来。就后者来说,最为典型者有东汉末年荀悦与三国魏人如淳两家。荀悦《汉纪·武帝一》:“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集解引如淳之说:“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有学者综合上面两类之说,将侠解释为“是一种讲究意气交合而扬威天下江湖、逞强一方乡里的社会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人”[6]32,大体上符合历史的真义。
从社会史角度来说,“盗贼”通常是指“侵犯统治者威权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是“国家公权力的挑战者,更是破坏地方治安最主要的一股势力”[7]。就法律角度而言,魏文侯时李悝首制《法经》,其中就有“盗法”、“贼法”,成为法律篇目。自秦汉至后魏,皆称“贼律”、“盗律”。至北齐,始将两者相合,称“贼盗律”。后周一度改称“劫盗律”,后又出现“贼叛律”名目。隋开皇年间又称为“贼盗律”,并为唐代所承袭[8]。明代继承唐代的法律思想,在《大明律》中亦设“贼盗律”。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再参之社会史的史实,大抵可知“盗”与“贼”在性质和意义上均有区别:劫掠财物者为盗,窃取财物者为贼。两者相合,即可泛称为“群盗”、“盗贼”、“盗匪”。若再作细微区分,“盗”更多地指“强盗”,亦即民间所谓绿林土匪。在民间,一般将他们尊称为“太保”[9]卷4:37。又因多喜占山为王,故民间又称为“山大王”。如明代成化年间说唱词话《花关索出身传》:“林前一捧[棒]罗[锣]鼓响,撞出强徒落草人。大王披了板红被[袄],一柄刚[钢]刀手内呈[擎]。向前把住咽喉路,你把黄金买路行。”又云:“大王披了金锁押[甲],手执刚[钢]刀似板门。山前栏[拦]住咽喉路,言把黄金买路行。说道半声言不肯,这张刀下没人情。”[10]可见,大王就是拦路抢劫的“强徒”,也就是落草为寇之人。在明代,最有代表性的强盗团伙,分别有北方的“响马”与广东的“飘马”[11-12]。而“贼”多指小偷小摸之人,诸如“剪绺白撞、偷鸡钓狗”之类的各色“小贼”[13]。
《韩非子·五蠹》所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从根本上揭示了儒、侠二者最为重要的区别。从先秦儒、墨、道三家来看,儒、侠之别亦相当明显。在《论语》中,有诸多关于“勇”的论说。如《论语·为政》孔子云:“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阳货》子路云:“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细绎上述两段文字,前者无非是说,“勇”的界定,必须合义之行或依义而行;而后者则明确认为,惟有合乎“义”的行为才真正称得上是勇武,否则就流于悖乱[14]。假若说勇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侠客的气质,那么就儒而言,更多的则是考虑道德标准。正是在这一点上,儒、墨两家之辨相当清晰。如墨家言儒之“特立”为“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说“刚毅”为“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追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这明显就是墨家的任侠之风[4]22。其实,从《庄子·说剑》所言“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不难发现,最初的游侠剑士,并无多少道义可言。就此而论,无论是李亦园、杨国枢主编的《中国人的性格》,还是美国汉学家赖特(Arthur Wright)所著《儒者的人格》,他们所揭示的中国人以儒者为主体的传统人格,均与侠者的英雄、豪杰气质迥然不同[15]。
值得关注的是,在随后的不同时代,儒家开始将“义”的准则施之于侠,如唐人李德裕《豪侠论》将侠“节义”化,以及宋代儒学复兴之后“义侠”的涌现,最终形成了中古时期的儒侠[6]8。当然,就儒侠演进史来说,明代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阶段。正如梁漱溟所说,真正的孔子精神,亦即“刚”的精神,或“刚毅木讷近仁”,在传统中国并未得到充分切实的发展。他又认为,这种儒学真精神,已由明代“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的王学左派即泰州学派所继承。换言之,泰州学派中人,多具豪侠之风。可见,明人的英雄、豪杰精神,当是孔子真精神的传衍[16]。
至于强盗与好汉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在明末人沈自晋根据水浒故事改编的戏曲《翠屏山》中,身为强盗的黑旋风李逵,在听到桃花山也有劫盗时,不禁吐露了口风,称:“吓,这里也有强盗?”还是神行太保戴宗机灵,及时纠正道:“是好汉。”于是李逵就坡下驴,改称:“吓,好汉!好汉!”可见,在这些梁山英雄当中,自己也并不讳言是“强盗”[17]。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豪杰与盗贼、光棍之间仅有一线之隔。在民间俗语中,既言“伶俐不过光棍”,又有“光棍不吃眼前亏”之说,这无不是说博徒、无赖之类的光棍,是一种“伶俐”人,他们能及时看透时机,不吃眼前之亏。与此同时,在民间又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之说,可见,真正的英雄豪杰,其行径也是识得时务,不吃眼前之亏。事实确是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英雄与贼寇之间的区分,并非十分清楚,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中国自古以来兴衰成败,是非短长,大抵如此。可见,民间所流传的“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说法并非凭空杜撰。
二、“儒侠”与“儒盗”:知识人之侠盗化
细究明代知识人群体行为,有两大转向颇值得关注:一是知识人之侠客化,随之而来者则是“儒侠”的广泛出现,以及儒与侠之合流;二是知识人之盗贼化,而“儒盗”的出现,更是儒、盗互动的明证。
明代的知识人,无论是朝廷命官,抑或布衣文人,大多带有一种侠客气,已成一时风尚,以下不妨详举其例。武进人陈组绶,在兵部任职时,曾结交壮士千余人,全是“渔阳大侠,时劳以金帛”。组绶死后,有人拟将其门下侠客收为“列校”。但这些侠客却说:“我等激于义为陈君效死,岂肯仰文吏鼻息耶?”哭丧之后,纷纷散去[18]圣集《先正流闻·陈组绶结客》226。这是朝廷命官豢养侠客之例。又大理寺评事常伦,多力,擅长骑射,“时驰马出郭,与侯家子弟侠少较射”[19]卷17《豪爽》,561,此即官员与侠少交往之例。
至于一般下层知识人,亦无不崇尚侠义之举。如王寅,安徽徽州人。史称少年时英气勃勃,自负具文武之才。他曾向少林僧人学习兵杖之法,尤其是“扁囤”一技最为精通。倭寇乱起,王寅投身胡宗宪幕府,却不得重用,抑郁而归[19]卷17《豪爽》,655;[20]。又如史忠,能诗,又能作新声乐府。其人性格豪侠不羁,不喜权贵之人,一有不合,就引去不顾。反之,若是遇到所善之人,则流连忘返,无论贵贱,都能与他们相处款洽。祁州人汤宝,雄武有才艺,喜与文人墨客游。因事来金陵,听说史忠的名头,夜造其门。时正值盛暑,史忠“散发披襟,捉葵扇而去[出],握手欢甚,不告家人,即登舟去”[19]卷17《豪爽》,654。可见,诗人兼画家的史忠,同样不乏豪爽之气。又康从理,好客任侠,东南倭寇乱起,随同将军刘子高入吴,“闻关兵革间,濒死数四。子高谢遣之,终不肯去”。倭寇平定之后,子高官拜大将,幕下之士日众,从理于是辞归金陵。子高病后,思见从理,从理“驰赴与诀,经纪其丧,扶柩至武陵”[19]卷17《义士》,639-640,侠义精神,跃然纸上。又莫云卿,亦是“负才气”,其人颇有武艺,能“穿靴舞剑,驰女墙上”[21]卷11《人篇》上,268。陶伟坎,字大本,号甓斋,浙江秀水人。初为儒学生员,以博物洽闻名于当世。后弃去衣巾,专以诗酒自豪。其人“负节侠,立然诺,行必择地而蹈,斩斩然不失尺寸”[22]。
明中期以后,道学家之侠客化蔚然成风。道学之人具有豪侠性格,早在道学形成之初即已存在。韩愈作为道学的先驱,就其性格而言,就带有豪侠因子。譬如韩愈《送董邵南序》,其中就有思念燕赵“屠狗士”之情;韩愈过田横墓,感慨田横高义,专门撰文祭之。如此种种,无不说明真正的道学之士,必然具有豪侠性格,惟有如此,才不会堕入迂阔一途[23]卷上《韩文公具豪侠性》,196。然细究明代道学豪侠之风的形成,不能不从大儒王阳明说起。综合诸多史料可知,阳明少时即“负奇气”[19]卷13《理学》,524。绍兴之香炉峰,绝顶之上,“复岫回峦,斗耸相乱,千丈岩陬牙横梧,两石不相接者丈许,俯身下视,足震慑不得前”。面对如此悬崖险境,王阳明少年时就可“趵而过”,人们不得不“服其胆”[24]。从阳明的学术生涯来看,亦有一个从“任侠”到“归正于圣贤”的过程,即“游于任侠,再溺于骑射,三溺于辞章,四溺于神仙,五游于佛氏,而归正于圣贤”。为此,明人何乔远称王阳明“惟其事功,以用兵显其俶傥权变、百谲千幻于蹈险出危之间,不无异时任侠之气,而世学讥其霸儒”[25]。毫无疑问,少年时期的任侠之气,对阳明一生影响至为深远。
这种任侠之气,在阳明后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以过去理学史著作所称王门“左派”与“右派”之两大弟子王艮与王畿为例,无不具豪侠之气,而与传统意义上道学家之迂阔迥然有别。袁宗道见李贽,问:“王心斋之学何如?”李贽答:
此公是一侠客,所以相传一派,为波石、山农、心隐,负万死不回之气。波石为左辖时,事不甚相干,挺然而出,为象蹴死,骨肉糜烂。山农缘坐船事,为人痛恨,非罗近溪救之,危矣。心隐直言忤人,竟捶死武昌。盖由心斋骨刚气雄,奋不顾身,故其儿孙如此。又王心斋一日与徐波石同行,至一沟,沟殊阔,强波石超。波石不得已,奋力跳过。心斋大呼曰:“即此便是!”[26]卷22《杂说类·杂说》,308
可见,所谓阳明“左派”,其学术精髓不外“侠客”之气。王艮迫使徐波石跳阔沟,其实就是培养其胆气。至于王门“右派”代表人物王畿,其拜入王门的经历亦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史载王畿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厮混。阳明亟欲与他一会,王畿一概拒绝。于是,阳明每天让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位弟子到王畿所至酒家,与他共赌。王畿笑道:“腐儒亦能博乎?”答:“吾师门下日日如此。”于是,王畿大为惊讶,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26]卷22《杂说类杂说》,307。可见,王畿之甘心归入王门,其起源仍在于共同的“六博投壶”之趣。
王世贞专作《嘉隆江湖大侠》一文,说明当时的讲学家也开始向侠客转化:“嘉、隆之际,讲学者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私,其术本不足动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27]用较准确的话概括,就是“儒心侠骨”。
若将时间往后延伸,从嘉靖直到万历年间,此类“儒心侠骨”之人,则显然以传统史籍所称四大“奸人”为代表,即方与时、颜钧、何心隐、邵芳。细加分类,四人又可分为两类:颜钧、何心隐可归于儒生讲学一类[19]卷31《惩诫》1109-1110,又与一般讲学家不同,所行多侠义之举,亦多轶出儒行之外。颜钧游侠,好急人之难。黄宗羲《明儒学案》载,赵贞吉赴贬所时,颜钧随同赴行,贞吉颇为感动。徐波石在沅江府战死,颜钧寻找他的骸骨归葬[28]。何心隐所独具的危言独行,被李贽形象地比拟为“见龙”:“终日见而不知潜,则其势必至于亢,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龙也,非他物比也。龙而不亢,则上九为虚位,位不可虚,则龙不容于不亢。公宜独当此一爻者,则谓公为上九之大人可也。”[29]卷3《何心隐论》,90无论是“见龙”之说,抑或“上九之大人”,无不说明在李贽心目中,何心隐就是一位儒侠合一之人。明末清初陈弘绪《答张谪宿书》称“有明异人”,嘉靖末,当数何心隐与邓豁渠两人。两人相较,陈弘绪对邓豁渠尚有微言,而称何心隐“生平所为,皆忠孝大节;即其诡异箕巫,阴去分宜之相,不烦批鳞请剑,而大奸忽尔败觉,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侠者”[30]81-82。“以忠而成其侠者”,确乎不刊之论。而方与时与邵芳则明显属于游士一类,他们并不熟谙讲学,更多地带有江湖方士习气。方与时“自幼险黠,有才辩,学书不成,去而学道”,此外颇能谈“圣学”及禅宗,又自称知晓剑术,甚至“四方剑侠之客,辐辏其门”[19]卷31《惩诫》,1108-1109。邵芳凭借权谲之术而纵游江淮,为高拱重新出任内阁首辅而广泛运作,带有战国纵横家与说客色彩[19]卷31《惩诫》,1110。
除上述四人外,吕光午、周复、李贽、盛顺等人,亦可归于儒而侠者。浙江人吕光午,少年时曾为生员,后成为何心隐的门生。吕光午一介书生,却具一人而击伤73个僧兵的技能,显然也是一位大侠[31]。陈弘绪在《答张谪宿书》中也曾提及吕光午受何心隐指派,“使走四方,阴求天下奇士。光午携蒯缑,衣短后之衣,挟健儿数辈,放浪湖海;穷九塞,历郡邑,所至凡缁衣黄冠,与夫商贾、驵侩、佣夫、厮养,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备一节之用,擅一得之长者,皆籍记而周旋之”[30]82,详细道出了其游侠经历。令人称奇的是,吕光午曾打算劫狱,从华亭县监狱中救出一盗。华亭知县深惧光午多力,只好提前将此盗扑杀。光午“每大恨,以为失人”[32]。周复,字明所,也是“儒而侠”[33]。李贽实亦深负侠义之气,自称:“仆隐者也,负气人也。路见不平,尚欲拔刀相助,况亲当其事哉!”[29]卷2《与曾中野》,52又称自己是一个可以抛却官位与名位的“真光棍”[29]卷2《复焦弱侯》,47。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李贽在侠客论上,以“烈士”取代“剑侠”,他认为:“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士,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又说:“侠士之所以贵者,才智兼资,不难于死事,而在于成事也。”基于此,他进而认为:“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29]卷4《昆仑奴》,193-194换言之,侠客凭借的是才智兼资,以及一股忠义节烈之气,而并非高超的剑术技能。具有国子监生身份的盛顺,尽管以周旋于崇祯政坛闻名,却亦具侠士之气。翰林黄道周被逮之时,盛顺“出千金佐行,一时推其义侠”[34]190。
综上所述,明代的知识人确实存在着侠客化的倾向,由此而来的是儒与侠之合流。在明代儒家学者中,就儒、侠关系加以阐述的颇多,较有代表性的当数汪道昆与黄宗羲。自韩非首倡“排儒击侠”论之后,祖述其说却有所发展者则属司马迁。针对两家之说,汪道昆均有所辨析,他说:“文则苛细,文而有纬则闳儒;武则强梁,武而有经则节侠。二者盖相为用,何可废哉!”随后以方景真为例说明儒与侠可以合一。方景真最初习博士家言,治四诗、攻六书,是一个儒者,但他又“出儒入商”,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不仅如此,“雅以然诺重诸交游,喜任侠”。在经商期间,甚至使用博徒叶宗鲁替自己负责经营之事。正是从此人行事中,汪道昆得出结论,方景真具有儒与侠的两面:说其是侠,却不是原、尝之类,既质有其文,又有儒行;说其为儒,却又能通有无,急人缓急,排难解纷[20]卷40《儒侠传》,856-860。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有两个比较:一是就“乡曲之侠”与“独行之儒”比较,司马迁倾向于侠者;二是就“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比较,司马迁深感做布衣之侠更难。明代由于时异势殊,黄宗羲对“儒者”之行侠仗义更是抱赞赏态度,认为他们“抱咫尺之义,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侠之途,既无有士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复闾巷布衣之事,岂不尤贤而尤难哉”[35]!由此可见,儒而侠之行为已经得到了当时知识人的普遍认同。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代的知识人存在着儒而盗的倾向。在明代,盗贼与士大夫交往已相当普遍。比如,万历年间,南京有一个“飞贼”,出入王侯之家,如履平地。其人“冠带驺从,出入呵殿甚都,与缙绅交,人不疑也”[36]卷5《人部》,96-97。后因盗窃魏国公的玉带,为家人所告发。假若说儒而侠尚属贤者之举,那么儒而盗则纯属儒行的堕落。明代知识人与盗贼之间的关系,大抵可从三个方面考察:
其一,地方官员之纵盗养寇已蔚然成风。高拱明确指出,盗贼之泛滥,究其原因,“皆起于有司之养寇,而成于上官之不察”。他说:“盖不惟贼之故态,官皆知之;而官之本情,贼亦皆知之。彼此相款,安然无事。”[37]410可见,“官”与“贼”之间已是彼此相安无事,习以成风。《豆棚闲话》亦有“种盗”之说,并借用番子之口,一语道出了实情:“这强盗多没有真的。近日拿来的,都是我们日常间种就现成的。所以上边要的紧,下边就有。”[38]于是,盗贼也就与瓜菜一样,可以“种得就的”。此论无不可以从明代史实中得到印证。如在山东东平、安山、武德一带,盗贼、富有的窝家与地方衙门之间,已形成一张利益攸关的关系网。即以武德为例,因其处于北直隶、河南、山东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颇易于盗贼窜匿。当盗贼来时,必有“富家窝引之”。更有一些地方官将盗贼视为大侠郭解之流,甚至“折节下之”[39]650。又如天启年间,崔呈秀任淮扬巡按御史,凡地方所获强盗,只要每人向他缴纳2000两银子,即可释放[40]。
其二,明代的很多士大夫,或在发迹之前有过亲身为盗的经历,或在跻身缙绅之列后窝盗或亲身为盗。就前者来说,高捷、刘焘、尹耕三人堪称典型。高捷颇多传奇色彩,留下来的传说亦多。他是大学士高拱之兄,排行第三,官至南直隶操江巡抚。此人自幼遍体赤毛,18岁时更是髭须满颊,有“高大胡子”之号。其人食量相当大,熟猪首一盘,馒首、馎饦数十枚,烧酒巨瓶,手撚而食,大杯倾酒,顷刻俱尽,一副豪爽之态[41]卷1《高捷》,35。少年之时,高捷有“轻侠”之称,武力绝人。中举人之后,他还与群盗一起剽掠行旅。盗贼被捕之后,所引时称“高三叔”,而匿去其名与居址。中进士之后,才稍改故态。操江巡抚罢归之后,一直居住在乡下。一天,有盗贼乘夜色前来抢劫。高捷下令洞开大门,自己手舞双刀,一个力士手持铁棒紧随其后,刀光如月,熛疾若风。数十名盗贼奔跌原野之间,俯首称臣,称道:“三叔尚雄武如是耶!”高捷大笑,招呼群盗入庄,“大作搥饼酒炙,饮食之”。其中亦有旧时相识,分别赠与钱帛,叩头别去。群盗中有三四个少年甚至愿意委身为奴,服侍终身[19]卷31《惩诫》,1100-1101。刘焘与尹耕均为嘉靖十七年进士。刘焘官至左都御史,尹耕官至兵备副使。两人皆有“武力”,擅长骑射,而刘焘尤其精通,却不修行检。尹耕中举人之后,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但囊中无一钱,于是与一群少年赌博,赢得10两银子,买一马直奔北京。至百里之外,则得善马;抵达北京,更是“橐装满矣”。何以如此?其实都是旅途中那些原本交好的“劫长”即盗贼首领所赠。刘焘任山东济南府推官时,一些中原的“劫长”纷纷投奔于他,一起饮酒食肉,殆无虚日[19]卷31《惩诫》,1101。
明代自南北多难以来,庙堂之上急于寻找知兵之士,一时用以御盗之人往往就是昔日之盗。如刘焘、高捷、尹耕三人,虽起于科目,但他们原先就是盗首。尹耕为兵备,以黩货而罢;高捷为操江,以避寇而罢;刘焘则南北疆场巨任,靡所不历,庙堂虽知其贪黩,而最终不能将其罢黜。万斯同为此感叹说:“嗟乎!士当承平之时,率相矜以文墨,一旦有事,遂使盗得志于天下,亦可慨已!夫天下方苦盗,而使盗得居吏民之上,盗何由息哉!顾其人诚足以御盗,用之亦何伤。乃彼自为盗则有余,为国家御盗实不足,亦安赖夫若辈而用之!”[42]
就后者而言,代表性人物有陈九畴、何吾驺、陈子壮、马维铭。“盗贼之源,皆由富家巨室藏匿分赃,官兵莫之敢捕,遂至猖獗。”[43]如北直隶鄚州,“响马”多盘踞其中,而任丘县之“各大家”又“为之窝主,几不可诘”[44]。所谓“富家巨室”或“大家”,虽不尽属士大夫,却以士大夫家族为主。都御史陈九畴凭将略在宁夏建立功勋,最有声望。然因遭到王琼、桂萼嫉妒,不能得到重用,晚年纵诞声酒。一次,因为宴客缺乏资金,“辄从一骑,出百里外,必有所获而归,人亦不敢问之”[19]卷31《惩诫》,1100。显然已堕落至“身为盗贼”。岭南巨宦何熊祥、黄士俊、何吾驺、陈子壮,家中均属巨富,但在乡里缺乏口碑。何吾驺“专贩海”,其家族成员或许亦有海盗经历;陈子庄更是“窟盗”[18]和集《丛赘·何吾驺》,607,成为群盗的窝家。又在浙江平湖,马维铭自万历八年致仕之后,横行乡里,曾藏匿大盗数人,盗贼所得财物,均得以分赃[45]。
其三,生员一类士大夫下层,不但窝盗,还成为盗贼“谋主”。生员窝盗,明人佘自强有“诸生中多有窝盗者”之说[46]卷7《贼盗门·投鼠》,164,具体事例则如贺承家,史称其“甘为盗薮”,贪图王如言家之富厚,诱使李一澄等强劫其家,并将劫得的“珠宝贵细”拿到自己家中“俵散”[47]。至于诸生成为盗贼谋主,亦有史实为证,如明末山东李青山占据梁山泊时,“诸生王某为谋主,分遣其众,据八闸,梗运道”[34]181。
三、“侠盗”:侠、盗之儒者化
明代侠、盗的儒者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盗贼群体的分流,其中一部分盗贼尚秉持侠义之风,为此引得知识人群体的赞誉;二是在盗贼群体中开始分化出这样一批人,即通过劫盗生涯发家以后,将自己的黑道印记洗白:或轻财好施,为此引得乡里百姓的尊重;或挟重赀而经商,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商;更有甚者,投身于知识人群体的讲学运动之中,力图成为衣冠楚楚的“儒者”。
从社会史角度看,明代盗贼群体的力量已相当庞大,进而引起当时一些学者的关注。如谢肇淛在论及北京游民人数之众时,有“绿林之亡命巨驵多于平民”之说[36]卷8《人部》4,157,虽有夸大之嫌,但大抵可以说明当时绿林势力之大。管志道在谈及各地已经引发社会问题的地方势力时,亦列举了吴中之“打行”、齐燕之“响马贼”、江淮楚越之“豪侠巨盗”[48]三类。宋人王禹偁曾有“六民”之说,说明当时社会力量分层尚未明显,而且盗贼尚未形成一个职业群体。入明以后,社会分层出现了巨大转变,姚旅对“响马巨窝”特意关注,说:“游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吞剑,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杂,官何敢问。”[21]卷9《风篇》中,202-203姚旅在王禹偁“六民”说之上,进而提出“二十四民”说,将“响马巨窝”归为“二十四民”之一。这一说法的形成,大抵表明当时的响马强盗已经呈现一种职业化的趋势。
平民投身绿林的原因或盗贼的来源,明清诸家各有阐述,大抵可以概括为两类:其一,临时性盗贼。他们投身绿林有不得已的原因,亦即被迫为盗,一旦有脱身机会,还是愿意回归朝廷统治下的编户齐民之列。其中不得已的原因亦可归为两类:一是“饥寒切于身”[49],清人孙时勋将此类盗贼的来源称为“饥民”,其目的是为了“求食”[50];二是“侵渔迫于外”[49],即明人许国所说的“有冤而莫伸,有资而见夺,皆驱之为盗者也”[51]。其二,职业性盗贼。此类盗贼,王廷相称为“得已而为之”之盗,如“无赖恶少,不事生业,习于下流”[49],最后脱身为盗。许国也说:“又有市井无赖,及恶少亡命者,吏不能养其民,以至游惰失业,荡而无归。方其平居,若宴然无事,一夫不逞,旦暮狂呼草泽之间,则踉跄四顾,而起者皆此辈也。”[51]明人佘自强更是将职业性盗贼细分为三类:一是“少年不事家人生业,恣意赌博,又三五成群,好争使气”,慢慢堕落为盗贼;二是“士夫子弟,亦有为盗者。或窥人子女,或杀人报仇,或嫖赌无赖,皆自士夫身后为之,亦有当其身为之者。且所劫者多亲属。其原皆自棍徒引诱始盗。棍徒欲引之入伙,以自为地”;三是“乡里豪杰,党与众多,不复为三尺所束缚,若纵之不问,养成大乱”[46]卷7《贼盗门·治盗四条》,156,最后投身绿林。这些职业性盗贼,清人孙时勋称之为“愚民”、“奸民”,其为盗的目的是“求福”或“求利”[50]。
强盗行状之区分,通常很容易识别。譬如,“平时不安生理,出入无时”,或“往来多面生可疑之人”,或“常有牛马银钱,费用不经”,或“行凶使酒,气焰逼人”,或“以妻为娼,相聚嫖赌”[46]卷7《贼盗门·察盗三条》,155,诸如此类,均可归为盗贼行状,极易察觉。当然,盗贼行状亦不能一概而论,往往各不相同:“有极富之家,自身为盗者,或养盗分赃者”;有“在别处为盗,至本地方轻财好施,为乡里所推重者”;又有“别处大盗,挟重赀至此,假作富商者”[46]卷7《贼盗门·察盗三条》,155。由此可见,明代盗贼很难从表面上判断,即使是那些“极富之家”、“富商”,或在乡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恰恰可能在背地里做一些盗贼之事。
在明代盗贼群体中,固然不乏临时为饥寒所迫者,但由“健侠之徒”所构成的职业盗贼亦复不少。明人高拱就指出,一些“健侠之徒,饮博宿娼,挥金如土,自相雄视,击剑杀人”,数千里外均可互相联络,“召呼之间,多可数千,少可数百”[37]409-410。明末吴甡亦认为,那些“闾左恶少、城市不逞之徒”,因为不肯忍饥待毙,所以“甘心为盗,东啸西聚,千百成群,以楔棹为矜戟,以帆樯为戎马,劫夺客商,焚掠村镇,杀人如麻,膏血川原”[52]卷4《水患日深生计日蹙民逃盗起两邑将废疏》,85。这些所谓的“健侠之徒”或“闾左恶少”,事实上就是侠客末流,在民间百姓中除了扰乱社会、危害地方百姓的一面之外,尚有崇尚侠义的另一面,因而被民间视为“好汉”。如在凤阳府泗州,一些市井恶少“动辄呼群引类,欺侮善良”,民间俗称“小好汉”[39]447。在小说中,同样将拦路抢劫者称为好汉,《鸳鸯针》载:“忽听一声哨响,几只柳木箭已到面前了,一齐慌张站住。只见十余筹好汉,将行李赶着就走。”[53]71《鸳鸯针》所刻画的强盗“风髯子”,其实就是一个侠客。他与一般强盗明显不同:就一般的劫盗而言,“连负贩的都不放松,破衣烂袜都收拾了去”;而他则有自己的行劫准则,“做好人,有好人的勋业。就做歹人,也有歹人的品节。大丈夫,既投胎在这里,也要为天公留些仁爱,为朝廷效些忠悃,为自家立些声名”[53]68,所以,他遇着小本经营的行商坐贾,“眼也不看”,一概放行,专劫那些“带纱帽”的贪官污吏。可见,尽管是强盗营生,却亦算得上此辈中的高人侠士。
正是因为盗贼群体中不乏侠义之举,因而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普遍回应,甚至不乏赞誉之声。在这些士大夫中,李贽堪称典型。关于强盗,历来就有不同看法。其中最为传统的看法,无非就是将其视为动摇传统社会基础的一股反叛力量。稍理性一些的看法,则是对强盗更多地带有一种同情。唐李涉《赠盗诗》云:“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明刘伯温《咏梁山泊分赃台》亦云:“突兀高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全寥落,何但梁山独擅名?”细绎二人诗意,于盗之众多与盗之擅名,或表示理解,或表示疑惑。作为盗贼对立的一面是官,且不说官匪本有一家之说,即使盗之猖獗,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无好官,甚至官之行为本来就与盗相似。《史记》即有“此皆劫盗而不操戈矛者”之说,《汉书》亦说“吏皆虎而冠”,云云。可见,官之夺民,绝不比盗逊色。正是基于此点,李贽更多地将批判矛头指向那些披着衣冠之“虎”,认为他们全是“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盗者”。为此,他专门引录盗赠官吏诗一首,其中有云:“未曾相见心相识,敢道相逢不识君?一切萧何今不用,有赃抬到后堂分。肯怜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谓私行不是公,我道无私公奚取?君倚奉公戴虎冠,谁得似君来路宽?月有俸钱日有廪,我等衣食何盘桓!君若十五十三俱不许,我得持强分廪去,驱我为盗宁非汝!”[29]卷5《读史》,212-213对那些衣冠强盗极尽讽刺之能事。
正因为对衣冠强盗有了清醒的认识,才最终导致李贽对巨盗多有称赞,甚至将他们的聚义之举提升到可与儒家忠义并称的地位。如林道乾,本是晚明的一位巨盗,横行闽、广一带海上长达30余年,但李贽却称之为“豪杰”、“英雄”。他说: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者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29]卷4《因记往事》,156-157
可见,正是因为科举、道学家讲学背景下士大夫的无才、无能,才促使李贽去寻求盗贼中的有胆有识之才。既然林道乾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那么,林道乾的见识如何?李贽认为,从林道乾藐视“世间一切大头巾人”的行为中,可知其人有二十分的见识。
明代骂人动辄曰“强盗”,无论是骂人者还是被骂者,都视之为极重之骂。但在怀林看来,世间强盗也有其不得已之处,他将强盗分为两种:“盖世上做强盗者有二:或被官司逼迫,怨气无伸,遂尔遁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下人,倘有一个半个怜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矣。”[29]卷4《寒灯小话》,190怀林时常伴随李贽身旁,听李贽说佛事,他对强盗的理解,显然受到李贽的影响。而李贽的盗贼之论,主要体现在将水浒一百单八人聚义山寨称为“忠义”,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见解,其理论结构大致可分三个层面:其一,正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或“小力”缚“大力”的不公正,才最终导致天下“大力大贤忠义”之人尽数投归水浒;其二,在水浒一百单八人中,无不“同功同过,同生同死”,均具一颗“忠义”之心;其三,在水浒一百单八人中,李贽尤其看重宋公明“忠义之烈”,宋公明虽身居水浒,却能“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换言之,宋公明并非“不知”,而是坚信“见几明哲”,不过是“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29]卷3《忠义水浒传序》,109-110。由此可见,李贽已经将绿林聚义上升到“忠于君”、“义于友”的层面,从而与儒家的忠义之说合而为一。
李贽之论得到了当时很多文人士大夫的回应,如袁宏道有诗云:“莫交无义儒,宁交有心贼。”[19]卷12《才能》,508这是通过儒、盗之辨,进而对“有心”之贼有所肯定,而所谓“有心”,其实就是合乎儒家之义。谢肇淛曾品评史上英雄如项羽、关羽、张飞等人,认为关、张并非“独以勇力胜”,而因为身具“忠肝义烈”,才使他们有“国士之风”。鉴于此,他断言,真正的豪侠英雄,除了“勇力盖世”之外,尚应“本之以忠义,济之以智术”。假若“忠义”不明,则不过是一个“剧贼”而已;当然,“智术”不足如关、张二人,谢氏觉得也是有遗憾的[36]卷5《人部》1,95-96。这是典型的侠、盗、儒合流之论。
明末清初魏禧通过《水浒传》将那些读诗书、讲道德之士,与那些被称为“狗偷子”的盗贼进行比较,认为在一个“君不择臣,相不下士”的社会里,必然会导致“士不求友”。尽管这些士人读的是儒家之书,满口讲的是仁义道德,事实上却是“尔富我觊,尔功我忮。一父之子,截为二体。我贵尔輘,我能尔矜。一人之身,不相为亲”。恰恰是那些盗贼,却信守着一种义气,相互交往之间毫无骄吝之色,“寒曰衣尔,饥曰食尔。曰相为生,曰相为死”,完全是一种“生死”相托的异姓兄弟之间的义气[54]。明清易代,时移势易,社会伦理道德亦发生惊人变化,诸如“士大夫之正气刚肠,销亡殆尽,廉耻之防荡然矣,而义侠之举,廉介之操,乃见之于盗”,归庄对此不禁发出了“盗亦义士”的感叹[55]。
这种大规模的称赞盗贼之论,在明末清初小说编者中亦有不同程度地反映。陆人龙在《型世言》中曾将盗贼广泛出现的责任归咎于地方官员,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官员“平常日子不能锄强抑暴,缓征薄敛,使民不安其身,是驱民为盗;不能防微杜渐,令行禁止,使民敢于作奸,是养民为盗”[56]。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对衣冠盗贼与绿林豪客进行辨析:“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其实就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亦是“大盗”行径;“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同样也是“大盗”。此外,在经纪客商、公门人役或三百六十行中,更是“尽有狼心狗行,狠似强盗之人”。与此相反,“倒不如《水浒传》上说的人,每每自称好汉英雄,偏要在绿林中挣气,做出世人难到的事出来。盖为这绿林中也有一贫无奈,借此栖身的;也有为义气上杀了人,借此躲难的;也有朝廷有用,沦落江湖,因而结聚的。虽然只是歹人多,其间仗义疏财的,到也尽有”[9]卷8,68-69。至于那些“神偷”与“侠盗”,凌濛初也多持肯定态度,《二刻拍案惊奇》引诗云:“剧贼从来有贼智,其间妙巧亦无穷。若能收作公家用,何必疆场不立功?”天下寸长尺技俱有用处,即使是贼,也有“贼智”,若能将这些贼人“收作公家用”,也可让他们在疆场之上建功立业。接着,凌濛初话锋一转,对当时的科举制度扼杀人才进行批评:“而今世上只重着科目,非此出身,纵有奢遮的,一概不用。所以有奇巧智谋之人,没处设施,多赶去做了为非作歹的勾当。若是善用人材的,收拾将来,随宜酌用,未必不得他气力,且省得他流在盗贼里头去了。”他在小说中就描写了懒龙这种穿窬小人中的“大侠”,认为这种侠盗,“反比那面是背非、临财苟得、见利忘义、一班峨冠博带的不同”[57]。此外,华阳散人在《鸳鸯针》中对强盗也多有颂扬,认为他们“也有仗义疏财的,也有闻难相救的,也有锄强扶弱拔刀借命的,也有败子回头替国家效用的”,这些投身绿林的好汉,“负不可一世之志,既不肯卑污无耻,与虫蚁生死,又不肯做瞒心昧己的勾当,掠那黑暗钱财。宁可拼着一身品节不立,光光明明作个畅汉。做得来,横挺着身子;坏事时,硬伸个头颈。却比那暗中算计人东西的,觉得气象还峥嵘些”[53]5859。
这些小说的故事内容主要来自民间,受众亦多为民间大众。就此而论,侠、盗、儒合流之论,作为一种新的是非道德学说,尽管倡自知识人群体,却开始渗透到民间的道德观念中。
在知识人看来,盗贼已是忠义之人,远胜于那些衣冠强盗。而揆之明代社会史,由于阳明心学崛起,倡导人人皆可为尧舜,于是,在晚明的讲学会中,大多能见到诸多盗贼的踪影,或成为讲学会的忠实听众,或成为讲学家。隆庆三年,马思恕在白沙关结社讲学,听者如堵。忽有48位“鵕冠佩刀”之人求见,道:“某等不幸为盗,习闻先生之教,愿自新归化,奈法不容何?”随之环拜而泣。马思恕从容语道:“律,自首者得免,尔果洗心无后悔,归熟思之,诘朝来。”经过三番求见,马思恕将此事上达知县,经过巡抚、巡按的批准,免除这48人的死罪[19]卷13《理学》,537。这是盗贼参与讲学并最后皈依儒家道德的典型例子。又如胡涍任永丰知县期间,有一位盗贼“衣冠颇怪”,却能“谈性命学而辩有口,邑中从游者几千人,缙绅亦多往焉”。邻府下檄文捕盗,按貌索盗,竟在讲学之处将此盗捕获[19]卷9《识鉴》,394。可见,盗贼不仅成为晚明讲学活动的参与者,而且成为其中的领导者。就此而论,明人谢肇淛云:“居家而道学者,大盗之薮也。”[36]卷14《事部》2,277堪称一语中的。
四、结束语
流氓、强盗是侠客堕落以后的产物。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侠客、剑侠一流人物,理应秉天地之正气,为人雪不平之事,霜锋怒吼,雨血横飞,最称得上世间第一快人、第一快事。所惜者,后世所谓侠客,已很少得此真传。世人偶然学得几路拳,舞得几路刀,便俨然自命为侠客,不是贻祸身家,便是行同盗贼,最后还是把一个“侠”字弄坏了。
何以言此?这可从《水浒传》得到说明。刘廷玑指出,《水浒传》的作者即使“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不过是“贼盗”,未免与司马迁《游侠列传》立意相同。他进而指出,若是“不善读《水浒》”,难免会产生“狠戾悖逆之心”[41]卷2《历朝小说》,83-84。龚炜亦说《水浒传》一书,“寄名义于狗盗之雄,凿私智于穿窬之手;启闾巷党援之习,开山林哨聚之端”[23]卷1《水浒》,27。钱大昕也指出,小说逐渐影响到民间百姓的伦理道德观念,“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58]。所谓“以杀人为好汉”,即指《水浒传》一书;“以渔色为风流”,则指《金瓶梅》一书。清末江苏巡抚丁日昌更是坦然承认,自从《水浒传》、《西厢记》等流行之后,“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最终则会导致“少年浮薄”之人“以绮腻为风流”,而“乡曲武豪”之人则“藉放纵为任侠”,甚至将“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59]。
上述四人说法,不能不说有夸大之嫌,但其无疑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水浒传》出来之后,侠客确实不再是完美的正面典型,而是“以杀人为好汉”,“藉放纵为任侠”。简言之,侠客已经成为像梁山泊一百单八将那样的“贼盗”。用清代小说《仙侠五花剑》作者海上剑痴的话说,在《水浒传》一类小说中,尽管也说一些“义侠”的事,但确实已经将那种“顶天立地”的“大侠”弄得像是“做强盗一般”,尽是一些“插身多事,打架寻仇,无所不为,无孽不作”的事,最后不免会使一般平民百姓将一个“侠”字与“贼”、“盗”两字并在一起,再也很难区分[60]。可见,在“强盗”与“好汉”之间,不过只有一线之隔。当他们行侠仗义之时,即为好汉;当他们打家劫舍之时,则为强盗。
与侠客堕落为流氓、盗贼相应,知识人的人格典范亦开始出现两大转向:一是从“儒者”向“豪侠”之转向。照理说来,传统的“儒者”典范,特点就是“择地而蹈,亦步亦趋;拟而后动,一俯一仰”。于是,“主一主静”成为先儒之“嫡传”,而“中律中度”成为后生模仿的样板。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知识人不再以传统儒者为典范,而是崇尚“豪侠”。为此,他们不再“无非无刺”做一个“乡之愿人”,而是气则欲爽,冲霄直上,高蒐倜傥,磊磊落落,犹如霜鹰不受天网拘束。所以,或登诗酒之坛,自著倚魁;或游声色之场,聊抒肮脏[19]卷17《豪爽》,648。二是从“王儒”转向“霸儒”、“盗儒”。与世俗从“霸”降而为“盗”相应,儒学亦开始从“皇儒”转向“盗儒”。按王嗣奭的看法,从周公到尧舜属于“皇儒”,特点是“浑然不露”;孔子属于“帝儒”,已经有所发挥;朱子属于“王儒”,开始费尽唇舌;王阳明流为“霸儒”;嗣后,罗近溪、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辈从“霸儒”降而为“盗儒”[61]。
知识人崇尚之人格典范,一旦从“王儒”流变为“霸儒”、“盗儒”,必然更多地关注如何管理与使用流氓、盗贼力量。按照传统观念,诸如像“天罡”、“地煞”、“打降”、“把棍”之类的流氓,无疑是一种“恶人”,即危害良民的“蝥贼”,只有去除这些“蝥贼”,良民才能安居乐业。在如何管理这些流氓的问题上,高攀龙提出,亦即不再是除恶务尽,而是利用流氓中的首领,即那些所谓“首恶”,由他们来管理与控制手下的党类,具体主张是将那些天罡党中的首领登记在册,由地方政府提供薪禄,平时由他们“摄其徒党”,一有事情再使用这些流氓,若是党类中发生诈害良民之事,惟首领是问[62-63]。吴甡亦是“用盗”论的支持者,主张任用盗贼中之“豪猾枭杰”者,他认为,这些枭杰之辈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习学韬钤,张大胸于胆,却因仕进无路,往往郁郁思逞,如果对他们不加谨慎使用,豪民就会铤而走险,流于盗贼之首,为此,吴甡专门上疏要求将“豪猾枭杰之流,分别验试,果有智谋超众,勇略过人者,荐之于朝,破格擢用”[52]卷1《御患莫如修备弭盗莫如安民疏》,29。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出自明代以讲儒家正统之学为主的知识人之口,不能不说流氓无赖和盗贼的势力在当时确实已是相当强大,以致儒家的正统人士也开始考虑如何适当管理和利用好这些势力。
值得关注的是,一至清初,知识人之“盗贼”论出现了波折。王夫之对“盗贼”的看法,就表现了一种逆转的状态。在如何使用“群盗”的问题上,他认为其中存在着“大利”与“大害”之别,必须加以辨析,亦即“盗可用”,而“渠帅不可用”。何以言之?王夫之认为:“为盗魁者,习与性成,终不能悛也。”[64]若与晚明知识人之“盗贼”论相较,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盗贼”论,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固然是历史经验总结使然,但更是为了适应清初统治秩序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