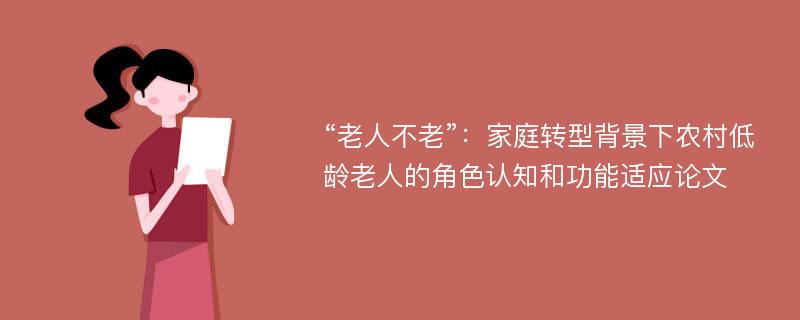
“老人不老”:家庭转型背景下农村低龄老人的角色认知和功能适应
黄丽芬1.2
(1.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 转型期农民家庭呈现出多层次的变迁,家庭的伦理、结构和功能发生转换,以代际合力形式完成的功能激活成为农民家庭应对转型压力和危机的秘诀。本文以“功能性家庭”理论为基础,将家庭中的老人群体区分为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并且通过着重考察低龄老人的“老人不老”状态,从角色认知和功能适应两个维度,梳理具有弹性的低龄老人和家庭功能激活之间的亲和性。研究发现,角色定位的模糊性和角色扮演的灵活性使得低龄老人成为家庭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权责不对等的家庭政治、发展话语主导的伦理转换相互作用,形构了转型期低龄老人的功能适应图景。在家庭转型中发现并关注低龄老人,才能更完整地把握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复杂机理。
关键词: 低龄老人;“功能性家庭”;角色认知;功能适应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农民进入市场和市场进入农村的双向运动引发了多方面的乡土社会变迁,推动了多层次的家庭转型。现代性力量进入农民家庭,在代与代之间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子代核心小家庭通过劳动力的要素化转移和城市化实现向上流动的阶层目标,集中体现现代性扩张和发展的面向,与此同时,亲代通过村庄退养降低生活成本的方式,支持子代的阶层流动,现代社会伦理去魅和风险升级的面向在亲代这里得到体现,形成了“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1]生活实践逻辑的对比。传统社会中,农民最重要的人生任务就是为儿子娶媳妇,子代结婚以及父子分家之后,当家权从亲代转移至子代,亲代即成为“社区性老人”,进入养老状态,不管是否有剩余劳动力,都从以生产为主的家庭角色转向以消费为主的家庭角色。农村调研发现,在家庭转型背景下,“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存在紧密互动,子代已经结婚生子,亲代并没有进入养老状态的情况大量存在。本文将在家庭转型背景下,老人已经完成人生任务,但是家庭角色并没有完成从生产为主转向消费为主的现象定义为“老人不老”,此种现象集中发生在农村低龄老人群体中。
家庭现代化理论是阐释家庭转型的主流路径,认为家庭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具有逻辑相通性,强调核心家庭与工业化之间的适应性,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夫妇式家庭制度的适应性。在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观照下,中国的家庭转型被概括为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功能外化和非独立化、家庭伦理弱化。具体而言,首先,家庭结构形态从原来的以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向以核心家庭为主转变,强调脱离扩大化亲属关系网络的核心小家庭的独立性和隐私性,结果,在家庭关系中,纵向的父子轴退出,横向的夫妻轴凸显,家庭权力转移的同时情感维度的重要性上升。其次,家庭融入市场导致经济生产、子代教育等功能的外移,“家庭成为治疗外部世界创伤的场所,成为家庭成员的情感避难所”[2],与功能外化相伴随的是功能的非独立化,家庭依赖于其他社会组织而生存,功能外化和非独立化与现代性组织的专业化息息相关。最后,中国家庭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和“伦理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转变[3],家庭成为个体基于契约关系的叠加,家庭本身的价值性和超越性意涵被剥夺,伦理去魅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导致“无公德的个人”[4]的出现,伦理弱化使得“不孝”成为老年人危机的解释之一。
家庭现代化理论具有鲜明的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色彩,以西方世界为模本,认为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家庭转型都会经历大致相似的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元的单线演进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修正。首先,在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方面,核心化被修正为“新三代家庭”[5]、“夫妇式家庭”[2],家庭代际关系和亲属网络重新被纳入考察,构成家庭转型的安全网和动力库,理论层面上独立于扩大化亲属网络的核心家庭基本上不存在。其次,在家庭伦理方面,贺雪峰提出农民伦理价值结构论,区分出基础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6],在此基础上,李永萍指出,家庭转型并没有完全导致伦理的衰落,年轻人的发展目标嵌入老年人的传统责任伦理中,导致本体性价值的扩张,重塑并强化了“家本位”的伦理观念,导致老年人危机形成并被锁定在家庭之内[7]。最后,在家庭功能方面,用关系实践的微观视角批判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结构功能宏观视角,发现家庭转型对家庭功能的激活和动员,弹性化的“功能性家庭”[8]成为农民应对现代性风险的奥秘所在。在家庭转型的背景下,农民家庭通过代际合力的方式实现功能适应,重塑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在此过程中,功能成为显性的,流动性的结构和被改造的伦理成为隐性的,具有弹性的功能面向成为理解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抓手。着眼于转型期家庭功能对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的统摄性,本研究将此种理论取向称为“功能性家庭”理论。
综上,无论是家庭现代化理论还是“功能性家庭”理论,都暗含着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探讨。在家庭现代化理论视野之下,传统与现代是相互对立的,并且有很强的价值判断色彩,传统代表着保守和落后,现代代表着创新和先进,因此传统是批判的对象,而现代是追求的目标,家庭转型就是家庭中现代性元素对传统性元素改造、替代和消灭的过程,此种进化论底色与西方模式中心主义不谋而合。“功能性家庭”理论指出,传统与现代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在家庭转型的多维实践中,对立、兼容和合作是共存的,三者统一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复杂性。农民家庭的现代转型可以借助传统生发,并且从传统家庭制度中汲取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传统被持续再生产和重塑,家庭转型既有传统的一面也有现代的一面。相较而言,从中国实践中产生的“功能性家庭”理论,从微观实践的角度,通过批判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单线演进逻辑,再现了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启发性。
问题是,“功能性家庭” 理论虽然通过考察农村代际关系实践发现了家庭转型的动力机制和老年人危机的生成机制,指出农村老年人在家庭转型中的重要性,但问题视角的“老年人危机”,因为没有探究农村老年人的内部分化,一方面,将差异极大的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① 本研究中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的划分没有明确的年龄界限,是社区性定义、家庭结构位置和劳动能力的综合指标,具体来说,高龄老人指家庭中那部分孙代已经结婚,没有独立生产能力的老人,低龄老人指家庭中那部分子代已经结婚,但尚有独立生产能力的老人。按照经验,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的年龄分界大致在70 岁左右。 一股脑儿地纳入“老人”之中,导致讨论主体不明晰,从而掩盖了低龄老人在家庭转型中的自发性、能动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直接将现阶段高龄老人面临的养老危机指认为低龄老人的未来,没有看到高龄老人和低龄老人具体境遇的高度差异,以不同代际的横截面分析取代独立代别的生命历程分析,使得分析过程存在代际层次谬误。因此,本研究即是在“功能性家庭”理论的基础上,区分高龄老人的养老危机和低龄老人的“老人不老”状态,将家庭转型中的代际合力过程进一步聚焦在低龄老人群体上,通过低龄老人的家庭角色认知和功能适应探索具有弹性的低龄老人与家庭功能激活之间的亲和性,在家庭转型中发现低龄老人,以期更加完整地把握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复杂机理。
笔者于2017年7月在河南驻马店D 村调研20 天,2017年10月在湖北沙洋G 村调研15 天,2018年5月在陕西扶风Q 村调研20 天,2018年9月在安徽繁昌X 村调研20 天,这构成了本研究的经验基础。
二、低龄老人的角色认知:“老人不老”
社会角色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 与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社会期望相一致的一套行为模式,社会角色具有复杂性、具体性和表现性[9]。家庭转型过程中低龄老人群体的社会角色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主要从角色定位和角色扮演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研究发现,角色定位的模糊性,使得低龄老人从原来的规定性角色转变为开放性角色;角色扮演的灵活性,使得低龄老人能够根据子代家庭发展的具体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行为,成为家庭发展过程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一)角色定位的模糊性:从规定性角色到开放性角色
传统的中国农村,普遍有着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梦想,但是真正实现四世同堂的只是一小部分农户,典型的是地主家庭。在生育数较多和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的背景下,老人完成传统的人生任务之后,基本上就耗尽了大部分的精力,进入了养老状态,养老状态的持续时间也不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长,养老意味着老人接近死亡,这样的家庭是很难实现大家庭梦想的。随着生活水平和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 岁上升到2017年的76.7 岁,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从1953年的4.4%上升到2016年的10.8%[10],根据2010年7 省区“城乡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调查数据,子代60~64 岁和65~69 岁祖父母及父母健在者分别为26.43%和15.78%[11],这意味着城乡老年人越来越多,并且高龄老人也越来越多。农村调研发现,农村四世同堂的家庭已不少见,甚至部分家庭出现了五世同堂。当前农村地区主要存在两种家庭结构类型:三代家庭结构和四代家庭结构,其中三代家庭结构包括青少年、中青年和低龄老人,四代家庭结构包括青少年、中青年、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对比发现,从三代家庭到四代家庭,家庭结构中多出了一代,意味着家庭结构的显著变化,这势必会影响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代际关系也会随之发生转变,甚至老人的定义都发生了模糊化。从三代家庭架构转向四代家庭结构,谁是多出来的那一代人呢?
(1)中间品进口的国际技术溢出对东、中、西部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差别较大,其中东部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性水平最低,主要原因是对外贸易是东部经济收入的重要源头,而技术是以加工贸易为核心,该种贸易方式使得东部地区需要更多的进口中间品。因此,中间品进口的国际溢出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显著。中间品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提高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显著性不够明显,因此应通过研发资本投入和吸引外资等技术沟通措施,实现中部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中间品进口的国际技术溢出能力。而相对于东部以及中部的中间品进口产生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西部的技术创新能力呈现明显提升。
从家庭年龄结构来看,多出来的一代人就是高龄老人,以前很少有人活到八九十岁。高龄老人的“多”,既体现在年龄上,也体现为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对于家庭发展资源的纯消费上。所以,高龄老人的“多”,是一种体现在生理年龄和社会心理年龄上的“多”,这意味着高龄老人很难被不断核心化的家庭所接纳,是被“新三代家庭”所排斥的“多”。
王跃生认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并非只有抚养—赡养此种反馈型的关系形式,在成年子女和壮年父母之间还存在着交换关系[13],也就是说,家庭生命周期中存在这样一个阶段,年轻子代已经成家立业,父母成为“社区性老人”,但是他们还有劳动能力,暂时不需要子代赡养,部分老人除了自养之外还通过存钱的方式为以后的养老生活做准备,这个阶段,低龄老人和子代之间践行着交换型的代际关系。但是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前提是子代能够独自面对家庭现代化压力,而这在大多数中西部农村家庭中是无法做到的,结果是,已经完成传统意义上为儿子娶媳妇的人生任务的低龄老人,普遍面临着人生任务链条延长的趋势,老人卷入到子代家庭之中,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卷入具有主动性、自发性和能动性。
河南上蔡农村的老人说:“现在年轻姑娘挑丈夫的标准真是没法说,一群老人闲聊的时候,总结出来‘三个不要’,年轻姑娘对媒人说:‘家里没买房子的不要,家里兄弟多的不要,家里有垃圾的也不要。’进一步追问,‘垃圾’是否指对家庭环境卫生的要求时,老人说:‘你们可天真,“垃圾”说的是年纪大的老人,孙子结婚了,爷奶就没用了,光吃饭占位置,不能帮干活,可不就成垃圾了?’‘垃圾老人’只能在地头搭个窝棚住,该给儿孙腾位置啦!”
1.4 叶果比不合理 一些果农贪图高产,留果量过大,叶果比失调(有些叶果比值还不到3),造成树体负载过大(亩产 2 000~3 000 kg),果实贪青晚熟,引起萎蔫。
农村调研发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存钱,一方面是尽可能地延长自养时间,尽可能地自我内部消化风险和化解老化危机,另一方面是为子代的不时之需做准备。但是老年人存钱,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钱具有完全的支配权,老人存下的钱被纳入了家产之中,他们可以支配的范围仅限于维持底线生存的日常消费,享受型消费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年轻子代的牵制,这使得老人花大钱必须和儿子商量。更常见的情况是,为了节余更多的资源支持子代发展,低龄老人在尽可能放大自己的生产能力的同时,将消费压缩至维持底线生存的水平。
也就是说,发展话语重置了家庭目标,加大了家庭再生产的难度,但是这种重置并没有带来传统主义的亲代责任伦理的瓦解,反倒是借助于“人生任务”这个本土概念,实现了亲代责任伦理的加载和转换,具体体现为人生任务链条的不断延长,“子代家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亲代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绑定在一起,使得亲代无怨无悔地为子代付出”[7]。发展话语主导的伦理转换使我们认识到,在“剥削型”代际关系中,虽然低龄老人扮演着“被剥削者”的角色,但是他们并不是受动的,而是主动地、自发地与子代建立此种代际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完成功能适应。因此,发展话语主导的伦理转换为“剥削型”代际关系提供了正当化基础,使得家庭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激活和动员。
家庭政治是一个由财产、 权力和伦理相互交织的分析框架,探讨的核心是家庭权力的分配情况。传统社会的家庭权力通过“当家权”体现出来,当家权与土地等家产高度相关,一般掌握在作为家长的父亲手上。与经典政治学理论强调权力的强制性不同的是,家庭政治中的权力接受“家本位”伦理的规约,当家人虽然掌握着家产和劳动力的分配和调度权,但这种权力的本质是责任,当家人承担着为家庭整体再生产和发展谋划和操心的责任,当家人是家庭实体的人格化,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他维护的是家庭整体的利益,这使得他的角色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家庭中的权力对应着家庭延续的艰巨责任,以及无限付出的伦理义务”[14]。
“门好进脸好看,办事缘何依旧难?”新华社记者在调查海南部分窗口单位后,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声。新华社记者采访发现,一些窗口单位仍有“软钉子”现象:门好进,脸也不难看,但事情却不好办。比如,考驾照,指纹录入窗口距离考场有20分钟车程;退休申报需要多次跑腿,卡在哪个环节搞不清楚;恢复外省手机号,必须本人到外省网点现场办理。
案例2:
陕西扶风的强某,已经64 岁,他有两个儿子都已经结婚,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建了两栋新房子,强某和老伴花光了十几年的积蓄,还欠下了十几万的外债。为了还债,强某买了收割机,承包了七八十亩地,空闲时间还去眉县打工,一年忙到头,经过五六年的努力,还剩下4 万多的债。老伴也已经60 多岁,也是没得闲,除了家里的活,还要照顾1 个老人和3 个孙子。前年,大儿子贷款买了一辆大货车,跑长途运输,但是生意不太好,贷款一直没有还上,这成了强某的一块心病。他说“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自己还是个小伙,身体好也放不下娃们,还可以再干10年,把自己的债还了,再帮老大把贷款还了,就歇下。”
在家庭转型的同时,家庭角色体系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不同家庭角色变化的方式和幅度不一样。青少年仍然是家庭整体的养育对象,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程度和教育目标的提高上;中青年人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仍然承担着最重要的生产者的角色,变化主要体现在以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发展目标导致生产任务的大量加载;作为纯粹意义上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仍然是家庭中被赡养的对象,变化主要体现在家庭转型导致“养儿防老”预期的不确定性和养老危机上;低龄老人本身作为一个不确定的角色,在年龄结构上是老人,但是在家庭功能方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人。由此可见,家庭转型时期,发展主义伦理的嵌入,使得每个家庭角色都发生了转变,但是转变最为彻底的是低龄老人。
根据角色空间的大小,社会角色理论将社会角色区分为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9],其中,规定性角色是指对角色的行为规范和标准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的角色,体现了社会角色的结构性面向;开放性角色是指对角色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而只是指出了扮演这种角色所遵循的基本思想,体现了社会角色的功能性面向。从社会变迁和家庭转型的角度来看,低龄老人从传统的“老人”角色走向了“不老”的社会角色,“老人不老”只是从性质上做出了“不老”的规定,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角色名称,以及与角色名称相配套的角色规范和标准,低龄老人的角色定位出现了从规定性角色“老人”向开放性角色“不老”的转变。
(二)角色扮演的灵活性:稳定器和蓄水池
当发展主义伦理嵌入家庭,作为其结果的“老人不老”,在具体实践中有多方面的表现,这也导致低龄老人内部出现较大分化。在生产劳动方面,不仅在劳动和不劳动上出现区分,还有农业劳动和工商业劳动的区别,劳动距离、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方面的区别;在孙代养育方面,不仅存在带孙子和不带孙子的区别,生活照料还是学习辅导的区别,还包括带孙子的时间长度、在哪里带孙子等问题上的差异性;在居住方式上面,不仅存在城居随迁和村居退养的区别,还包括与谁住、新房子还是旧房子的差异。低龄老人群体内部之所以存在众多分化,是因为低龄老人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性角色,核心小家庭的生产生活选择决定了低龄老人的具体境遇,使得低龄老人的角色扮演在具有被动性的同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农民家庭生活整体上呈现出策略性和权宜性的特征,并且以年轻夫妻为主的核心小家庭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低龄老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当前农民家庭再生产压力主要来自婚姻、买房和教育三个方面,婚姻和教育压力进一步使得进城买房成为刚性需求。在压力面前,农民家庭根据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积极调整生产生活策略。调研发现,部分中西部农村家庭调试出了最有利于家庭资源积累和子代教育的功能模式,在孙代出生之前,子代和亲代全部参与劳动力市场,家庭处于高积累阶段;孙代出生以后,亲代退回农村,年轻媳妇自己带孩子到七八个月,再交给在村里的低龄老人带,年轻媳妇进入劳动力市场,虽然家庭积累能力有所下降,但是仍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积累;等到孩子三四岁该上幼儿园的时候,奶奶带着孩子进城与年轻夫妻一起居住,奶奶负责孩子的生活照料,年轻夫妻全力参与劳动,下班后负责孩子的学业辅导,爷爷在村里生活,负责照管高龄老人以及农业生产。此种模式下,一方面两个最优秀的劳动力都可以干活,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12]还可以继续维持,另一方面孩子的教育也很完整,此种模式的实现建立在低龄老人夫妻的阶段性分离基础之上。
案例3:
2.1.2 采集地点。调查地点为河北省怀安县太平庄乡、阳原县大田洼乡。其土壤为北方典型的干旱半干旱贫瘠类型。河北省怀安县太平庄乡属高寒山区与丘陵区,耕地2 323 hm2,旱地2 306 hm2,旱地占比99.3%。阳原县大田洼乡耕地1 043 hm2,旱地面积705 hm2,旱地占比67.6%。
安徽繁昌的李某,61 岁,有一个35 岁的儿子,李某和老伴在家里种田、打零工、照顾老人和两个孙辈,因为儿子结婚早,当时没有买房子才能结婚的说法。儿子在杭州打工,媳妇为方便照顾两个孩子,就在县城打工。这几年,村里买房子的越来越多,媳妇心动了,旁敲侧击地打探两个老人的意思。李某说:“儿子成家的时候,我洗干净盐罐子油罐子,一股脑儿给他了,我以为任务完成了,没想到形势变了,现在别人有,儿媳想有也正常。我虽然有点积蓄,但是不能直接给,直接喂糖不行,得教会他们自己造蜜,给点压力,他们实在撑不下去了,我再顶上,可以让儿子知道我有钱,但是具体多少钱不能告诉他的。”
各位代表,刚才三个小组的代表都已经把每个组的论文汇报得非常详细而且精到,我这个学术总结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原来会议的议程上有这么一项,所以我尽量说得简单一些。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有47篇,后来会上又补了几篇,另外有11篇是存目的,存目的大部分论文也都在会上宣讲并且基本成文,这样共计有近60篇论文,应该说会议的材料是非常丰富的。
以年轻人为主,低龄老人为辅的家计模式中,年轻人是家庭转型压力的主要承担者,低龄老人是压力的分担者,年轻人负责在前方市场上“冲锋陷阵”,实现高强度的积累,低龄老人负责“稳定后方”,使得年轻人可以一心一意地打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扮演辅助性角色的低龄老人,为年轻子代带来压力感的同时输送安全感,家庭发展风险以代际合力的方式被内部化,低龄老人成为家庭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三、低龄老人的家庭功能适应
目前,在传播学领域,仅有部分以中华美食为对象的传播调查研究,对海外中餐馆本身文化传播的阐释性研究很少。⑨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一些机构的公开信息。
(一)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
案例1:
代与代之间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除了直接的资金转移方式外,还有农副产品等实物形式的输入,更重要的是低龄老人对于自己剩余劳动力的分配方式。一般来说,在人生任务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对于自己的剩余劳动力,老年人有三种处置方式:资助子代发展、积蓄养老资源、享受当下生活,其中,资助是直接性的资源输送;积蓄的目的是“不给儿子添负担”,因而是间接性的资源输送;而享受是对家庭总体资源的消耗,不具有积累性,当子代面临发展压力的时候,此种享受型消费不具有合法性。
从社会角色和家庭生产的角度来看,“多出来的一代”其实是低龄老人,他们的社会角色是模糊的,介于纯粹的老人和纯粹的中年人之间。因为他们,家庭中出现了半劳力和半老人的“尴尬”角色,他们一脚踏在老人角色之上,一脚踏在中年人角色之上,在生产性角色和消费性角色之间摇摆,并且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伴随着在他养和自养之间的选择,此种社会角色的模糊性从多个层面表现出来。社会角色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角色规范和社会规则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的境遇极具区域性和个体性,与家庭发展能力和子代家庭情况息息相关,不确定性和非规定性使得他们的角色空间在所有家庭角色中最广,最具伸缩性。所以,作为“多出来的一代人”,在他们身上,社会变迁的社会学意涵得到集中表现,老年人用“老人不老”的话语来描绘这种状态。
案例4:
湖北沙洋颜某,72 岁,两个儿子都已经在荆门贷款买了房子,颜某和老伴住在建了几十年的泥土房里。颜某将自己家的承包田改造成虾田,种田收入一下子翻了几倍,除此之外,他还打点小零工,摸鱼捞虾等,每年能存几千一万,手里头有了几万元的积蓄。看着别人都过上了好日子,颜某和老伴也想将房子装修一下,住得更舒适。老两口的想法在儿子那里遭到了反对,儿子说,“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那个房子还能住几年?过两年你们就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装修房子就是浪费,如果漏雨,可以修一下”。颜某表示,儿子不同意,是万万不能动工的,即使花的是自己的钱,影响到父子关系就不划算了。
(二)权责不对等的家庭政治
显效:常规治疗或者康复治疗之后,基本恢复了各项项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有效:各项肢体功能有明显改善且可以简单对话;无效:肢体功能和语言能力没有明显的效果。通过对两组患者的治疗调查发现,护理满意度高达78%,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例数×100%。
分家是一个当家权从亲代向子代转移的过程,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当家权:继替型当家权和裂变型当家权,前者指分家之后,亲代不再拥有当家权,无论在社区中,还是在家庭内,亲代小家庭都不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家,必须依附于子代获得物质性和社会性的生存,后者指分家之后,亲代仍然拥有当家权,与子代家庭并立存在,具有明显的独立性。
完整的分家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兄弟之间的分离;家产、社会资本和人情网络的继承;以子代为核心的家庭对以亲代为核心的家庭的替代。传统时期的分家,是分离、继承、替代三位一体的仪式性过程,市场化和家庭转型导致家庭内部农业和工商业的分化、城市和农村的分化,结果是分家的复杂化。首先,兄弟分家提前并且明晰化,从以前所有兄弟结完婚之后的“一次性分家”到“结一个分一个”,再到以婚姻支付的方式提前分家,兄弟之间的竞争关系越来越明显。其次,父子分家模糊化和名实分离,子代进入市场就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核算权,意味着子代与亲代分家的提前,此种形式的“自然分家”带来分家仪式的名实分离,亲代与子代的分家越来越模糊。兄弟分家的清晰化,子代与亲代“不分而分”,亲代与子代“分而不分”三者并存的情况,使得亲代在继续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失去了对家庭资源和劳动力的调配权,代际关系中出现明显的权责不对等,低龄老人只能通过充分调动自己来履行家庭责任。低龄老人的权力让渡和资源输送共同发生,虽然激活了家庭功能,但是代际关系从相对平衡的“反馈型”走向不平衡的“剥削型”[15]。
(三)发展话语主导的伦理转换
经济上的输送关系和家庭政治上的权责不对等关系造就了转型期“剥削型”代际关系,然而,这种家庭内部低龄老人遭受剥削的代际关系,却并没有造成亲代和子代之间的角色张力,反倒实现了家庭功能的充分激活和动员。学界首先从“孝道衰落”[16]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伦理弱化和伦理危机是“剥削型”代际关系产生的核心原因,但问题视角的“孝道衰落”,将子代置于道德危机之中,是“剥削型”代际关系的主导者和受益者,老人是道德危机的被动承受者,因为没有发现低龄老人在其中扮演的主动性角色,导致其在解释力上存在明显欠缺,如果只是子代单方面的索取,理性计算必然导致“剥削型”代际关系的瓦解。
功能是部分对整体所发挥的作用,是在整体生态系统之下各部分通力合作的结果,整体效应最大化是其根本目标。各部分的目标服从于整体目标的调配和引导,面向整体功能的各部分通过放大、压缩、让渡和转换等方式实现内部调整和内外对接,也就是各部分完成功能适应的过程。为了应对转型期家庭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压力,扮演辅助性角色的低龄老人根据家庭整体压力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通过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策略调整完成功能适应,与子代核心小家庭建立起了经济上自上而下的资源单向输送关系,政治上家庭权力从亲代让渡到子代,低龄老人进入权力边缘的同时继续承担家庭责任,权责不对等凸显,与此相配套,家庭伦理的转换为资源输送和权力让渡的单向度提供了正当化基础。
“剥削型”代际关系的正当化机制还必须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去解释。首先,现代性通过婚姻进入农民家庭,彩礼、买房、婚姻人情等项目要求大流量资源,发展主义嵌入家庭,大幅度提高为儿子娶媳妇的人生任务难度,为了完成人生任务,低龄老人必须拼尽全力。其次,子代核心小家庭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承受房贷、工作、教育等阶段性压力,低龄老人依附于子代家庭发展情况参与村庄竞争,在村庄熟人社会中,资助子代发展能够带来充足的社会激励。最后,现代性力量进入农民家庭,在代与代之间体现出明显的速率差异,以家庭责任伦理的现代转型为例,面对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低龄老人不仅努力自养,还充分调动自己的剩余劳动力,积累资源向下输送,这意味着低龄老人责任伦理的深化,与此相对的是,年轻人的养老压力得到极大释放。
1.1 一般资料 2017年9月~2017年11月,选取上海中医药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以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工作人员共13名健康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1名,女性2名,平均年龄(27.64±2.98)岁,平均身高(174.18±8.84)cm,平均体重(73.36±14.55)kg。所有受试者均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行测试。纳入标准:年龄18~40岁;近3个月无下肢外伤史;未患有影响步态的神经肌肉疾病;意识清楚能够主动配合完成测试。排除标准:患有其他可导致步态异常的神经肌肉骨骼疾病者;不愿意主动配合测试者。
朱熹写过这样一句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所谓“活水”,则是源源不断的清水。这句诗用来阐述读书的好处是再合适不过了,“活水”对于一汪清泉来说尚且是这个道理,那么它对于人创作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读书数目和种类越多的人,把书读得越透越清楚的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自然是“文思泉涌”,各种新颖的、秉具个人风格和特色的作品就能轻易地呼之欲出。
四、家庭转型背景下“老人不老”的实践意涵
对家庭的考察,一般从结构、功能和伦理三个维度以及相关关系着手。首先,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家庭体系中,伦理—结构—功能“三位一体”的构造模式给予中国家庭以立体感,家庭伦理居于首要地位,赋予农民的日常时间和生命周期以超越性的价值体验,使伦理道德代替宗教成为可能;其次是由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构造出来的家庭结构,不同的家庭成员在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每个位置都是由资源、权力、伦理相互交织形成的家庭角色;最后,每个家庭都要发挥一定的功能,如生育、抚养、生产、生活、赡养、宗教、保障等。在现代性进入农村之前,农民家庭通过“过日子”的方式实现家庭功能生产,不断再生产着家庭结构,从“过日子”到“人生任务”再到“传宗接代”,个体以家庭再生产为核心,践行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路径,家庭功能和家庭结构都受到家庭伦理的规范和引导。
“功能性家庭”理论认为,在家庭转型的背景下,家庭伦理、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三者之间的关系被改造,因为三者的转换速率不同,“三位一体”的构造模式发生变化。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家庭功能对外部世界变化最为敏感,在市场迫力之下,家庭功能突破原有的边界,失去了原有的结构基础和伦理支撑,成为家庭要素中最为活跃的力量,而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的转换相对缓慢,形成了新的功能—结构—伦理的构造模式。“功能性家庭”理论并不只讨论家庭的功能转变,而是以功能转变为基点探讨家庭转型带来的关于家庭功能、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的全方位的转变。
通过对转型背景下农民家庭再生产实践的考察发现,虽然在家庭与外部市场、国家、社会的交互过程中,部分家庭功能出现外移,但是家庭转型也塑造了新的家庭功能,部分原有的家庭功能得到强化,在“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的联系中,家庭功能的实践机制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家庭的功能转变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家庭的功能发挥通过对家庭关系的重新整合和调动得以实现,并且与整体性的家庭境遇高度相关,“私人家庭生活的内容、家庭与亲属群体的关系、家庭与社区的关系这些总括为家庭关系的变化才是当代家庭的显著特征,正是这些变化而不是从血缘扩大家庭制度向核心家庭制度的转变,是现代家庭有别于前工业化家庭的核心内容”[2],这里面既有策略性和权宜性的因素,也有规则性和体系性的因素。家庭转型背景下的功能性家庭理论,强调在家庭与社会系统高度互动的前提下,对家庭关系,特别是具有生产功能的低龄老人与中青年人的代际关系的全方位考察。具体而言,家庭功能就是在家庭的内外关系中,通过资源动员和资源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发展目标,而单独依靠子代很难完成这一目标,必须借助于代际合力的方式。老年人作为家庭角色的一个重要环节,卷入发展主义的家庭伦理之中,“新三代家庭”从功能发挥最大化出发,对老年人进行选择性吸纳和排斥,其结果是高龄老人和低龄老人具有不同的卷入逻辑。
高龄老人因为失去劳动能力,不能为家庭积累提供来源,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家庭合力逻辑就是理解作为他们子代的低龄老人的处境,高龄老人自我解释养老危机的话语就是“儿子也有儿子”,他们以尽量不给儿子添负担的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在家庭转型面前,高龄老人既有被动的一面,他们是被“新三代家庭”所抛弃的家庭角色,也有主动的一面,他们不添负担的行动取向具有能动性。从家庭资源动员和积累的角度来看,高龄老人几乎没有贡献,高龄老人实践的是存量逻辑,而不是增量逻辑,即在不能增加家庭整体资源的客观条件下,尽量减少对家庭发展资源的分流和消耗。
笔者认为,对裁执分离与《行政强制法》、新《行政诉讼法》及《行诉解释》的关系上,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与高龄老人已经完成人生任务,退出核心家庭的情况不同的是,低龄老人的人生任务链条存在明显的延长趋势,在完成人生任务的责任伦理下,低龄老人不把自己当老人,自主地、高强度地卷入到子代核心小家庭的发展之中。如果按照传统的生活轨迹,子代结婚后与父母分家,亲代就可以进入养老状态,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是家庭中的老年人,不仅可以从家庭生产和责任承担中退出,还可以从村庄人情和社会竞争中退出,负担不重使得他们可以在晚年生活中充分体会人生价值的圆满感和充实感。但是在家庭转型的背景下,低龄老人不能再按照传统的轨迹进入养老状态,“我们还不老,还可以再干十年,儿子不容易”成为他们的话语。低龄老人从“老人”向“不老”的实践策略是多层面的,角色定位的模糊性、角色扮演的灵活性构筑了低龄老人的角色认知特点,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权责不对等的家庭政治和发展话语主导的伦理转换形构了低龄老人的家庭功能适应方式。总体来看,低龄老人的家庭生活实践既遵循着存量逻辑也遵循着增量逻辑,即在尽量降低日常生活对家庭发展资源的分流和消耗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实现劳动力的变现。
基地的集聚能力基本形成。2017年,重庆市从事数字出版企业数字出版及相关产业的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事业部3000余家,其中法人企业715家,其中非传统出版单位设立数字出版相关业务企业471家。在法人企业中,有352家落户基地。全市21家有网络出版资质的企业中,有14家集聚在基地。对重庆市38个区县(开发区)的区位熵测量,两江新区数字出版基地区位熵为为5.66,呈现专业分工与规模经济性,具有产业集聚效用,专业化程度处于最高水平。
五、总结与讨论
农民家庭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虽然由于历史、地理、资源禀赋等方面差异,不同地区的市场区位,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农民与市场关系,但是在大多数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农民的城市化具有渐进性和接力性的特点[17],这使得“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互动。本文从农村低龄老人的角色认知和功能适应两个维度探讨了具有弹性的低龄老人和家庭功能激活之间的亲和性,研究发现,角色定位的模糊性使得低龄老人的家庭角色性质从规定性转为开放性,角色扮演的灵活性扩展了角色空间,低龄老人成为家庭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与此同时,转型期低龄老人的功能适应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权责不对等的家庭政治和发展话语主导的伦理转换完成。总之,农村家庭中的低龄老人群体因其在家庭结构中的特殊位置,成为家庭转型研究的有力抓手。
在四代家庭结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低龄老人要处理复合型的代际关系:向下的亲子关系和向上的子亲关系[11]。并且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恩往下流”和“儿童中心主义”的逻辑使得低龄老人为了适应向下的亲子关系而挤压了向上的子亲关系,从而造成高龄老人的“养老危机”。也就是说,在家庭转型背景下,如果不考虑“孝道衰落”此种个体性比较强的道德伦理因素,可以通过对低龄老人生活面向的考察,判断不同家庭的高龄老人是否出现“养老危机”,以及危机的严重程度。当低龄老人将自己的主要资源和剩余劳动力分配给年轻人的时候,在农村生活的高龄老人就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养老危机”,当低龄老人的分配抉择向下力度不强的时候,高龄老人一般就能够得到较好的照养。
作为家庭转型后果的“老年人危机”内部存在分化,在高龄老人身上表现为间接性的“养老危机”,在低龄老人身上表现为直接性的由“老人不老”带来的认同危机和价值危机。现代化压力不仅让年轻人疲于奔命,更打破了低龄老人的生活预期,无尽的操劳和无法完成的人生任务,使得低龄老人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备受煎熬,但是对于低龄老人来说,这种煎熬始终伴随着一种希望,那就是在人生任务完成之后的圆满感和意义感。以“家本位”伦理为基础的唯实论家庭观通过农村家庭中的低龄老人得以维系,打破了以“个体本位”伦理为基础的唯名论家庭观对中国家庭转型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杜鹏,李永萍.新三代家庭: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与转型路径——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1):56-67.
[2]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社会学研究,2010(3):199-222+246.
[3]刘燕舞.从核心家庭本位迈向个体本位——关于农村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9(6):42-46.
[4]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5]张雪霖.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新三代家庭结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20-126.
[6]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开放时代,2008(3):51-58.
[7]李永萍.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一种阐释路径[J].中国农村观察,2018(2):113-128.
[8]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4-60.
[9]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8.
[10]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11]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其新变动[J].人口研究,2016(5):33-49.
[12]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137+207-208.
[13]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J].人口研究,2008(4):13-21.
[14]张建雷,曹锦清.无正义的家庭政治:理解当前农村养老危机的一个框架——基于关中农村的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32-143+166.
[15]耿羽.农村“啃老”现象及其内在逻辑——基于河南Y 村的考察[J].中国青年研究,2010(12):81-85.
[16]钟涨宝,李飞,冯华超.“衰落”还是“未衰落”? 孝道在当代社会的自适应变迁[J].学习与实践,2017(11):89-97.
[17]陈文琼,刘建平.发展型半城市化的具体类型及其良性循环机制——中国农民进城过程的经验研究[J].城市问题,2017(6):4-13.
"Old people are not old":role cognition and functional adaptation of rural Younger age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Huang Lifen1.2
(1.School of Humanities,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4;2.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Wuhan,Hubei,430074)
Abstrac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 peasant families showed multi-level changes, the family ethic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were transformed, and the function activation completed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ynergy form became the secret of the peasant family's response to the transformation pressure and crisis.Based on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family”,this paper divides the elderly groups in the family into younger and older people,and focuses on the status of “old age are not old ”of younger age ,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role cognition and functional adaptation.Affinity between the flexible elderly and the activation of family function.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ambiguity of role orientation and the flexibility of role-playing make youngerage become the stabilizers and reservoirs for family development,top-down resource transmission,unequal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family politics,and the ethical transformation dominated by development discourse have shaped the functional adaptation of the younger age in transition.The discovery of younger age in the family transformation can more fully grasp the complex texture of rural family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younger age;"functional family";role cognition;functional adapt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18CZZ037)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9-0038-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9.004
作者简介: 黄丽芬(1991—),女,汉族,湖北黄石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基层治理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易晓艳)
标签:低龄老人论文; “功能性家庭”论文; 角色认知论文; 功能适应论文; 1.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2.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