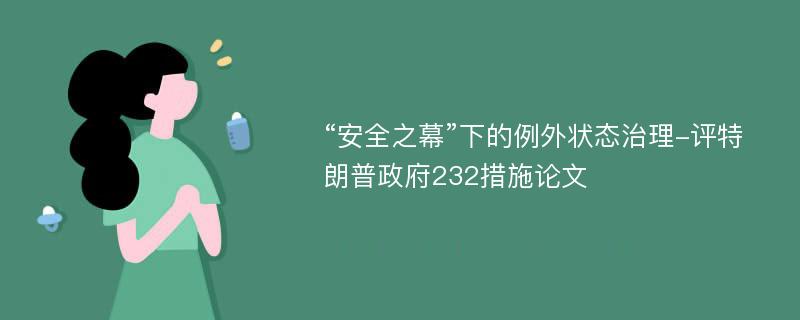
“安全之幕”下的例外状态治理
——评特朗普政府232措施*
陈若鸿
内容提要 :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经贸领域的举措呈现“泛安全化”趋势。本文以美国2018年3 起232 措施为切入点,指出“国家安全威胁”话语是特朗普政府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种政治建构,其目的是在“安全之幕”掩盖下实现其“例外状态的治理”,对外悬置WTO 法,推动特朗普式的国际贸易秩序;对内助推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在复杂的国内治理情境下强化政府权力。本文指出,各国应清醒地看到这套国家安全话语背后的意图,在话语上正本清源,在行动上联合抵制,防止特朗普政府将经贸领域的例外状态普遍化。
关 键 词 :232 调查;国家安全;GATTXXI 条;例外状态
一、近期美国经贸政策话语的“泛安全化”现象
特朗普上台后,“国家安全”频繁出现在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话语中,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高调凸显重振国内经济、增进自由公平及互惠的经济关系等议题,这些议题被归并在“繁荣”主题下,列为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之一。报告中“安全(security)”出现了117 次,“经济的(economic)”出现了115 次,两者出现的频率在历年报告中最为接近,突出了经济与安全的关联性。① 王秋怡:《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载《国际论坛》,2018年第5 期,第28—34 页。 第二,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先是动用许久未用的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 节对进口钢铝产品展开国家安全调查(下称“232措施”),最终对进口钢铝产品全面加征高额关税,税率分别为:钢铁25%,铝10%。之后不久,美国又以同样理由对进口汽车启动国家安全调查并加征25%的关税,不惜惹恼欧盟、日本等盟友。第三,在投资领域,仅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五起中资企业赴美并购,尽管这些案件涉案的金额远远算不上引人注目,这些案件所涉及的行业也与传统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相距甚远。2018年,美国国会又以较快的速度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强化对入美外资的审查。一时间,国际经贸领域许多问题似乎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挂上了钩,美经贸政策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现象。
那么,美国经贸领域诸多“安全化”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各国应如何应对?本文以美232 措施为切入点,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钢铝及汽车进行的232 国家安全调查及结论令国内外感到惊讶,各界对此批评如潮。正如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美国98%的汽车进口都是源自盟友国家,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居然认为进口汽车损害了国家安全,这显然是对国家安全制度的滥用,其本质是为了对进口商品征税。就钢铁行业来看,2017年,美国钢铁业整体产能利用率在72%左右,进口占国内市场份额的30%,进口产品的主要来源地也是盟友国家或地区,无论从产能利用率还是进口来源地的角度来看,钢铁业的进口都远未达到威胁国内行业的程度,更谈不上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对232 钢铁措施严重不满的美国国际钢铁协会甚至提起了232 措施违宪之诉。在国际层面,贸易伙伴国更是纷纷抨击美国政府232 措施是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各国除将其提交WTO 货物贸易理事会讨论外,还纷纷将此措施诉诸WTO。② 截至2018年8月15日,已有欧盟、中国、俄罗斯等九个国家或地区将美国232 措施诉诸WTO。 可以说,特朗普政府若干起232 措施犯了众怒。在232 措施如此牵强的情况下,特朗普为何还要运用这类措施?笔者认为,“国家安全”话语一方面是对现实的映射,有必要在美国身处的具体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去把握其背后的心态与认知;另一方面,话语也在影响着现实和未来,体现了美国政府在塑造世界秩序方面的意图。
二、一反常态的232“国家安全”调查
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修订版)第232 节(美国法典第19 卷第1862节,以下简称“第232 节”)授权政府对进口产品中对美国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调查,并采取应对措施。特朗普上台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美国商务部就根据232 节展开了3 起针对进口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分别涉及进口钢铁、铝及汽车。2018年2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美国进口钢、铝的232 调查报告,认定进口产品严重损害了国内产业,威胁到国家安全,据此建议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一个月之后,特朗普发布总统文告,决定对除加拿大及墨西哥以外的全球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进口关税。2018年5月23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又自主发起对进口汽车的232 调查,以确定进口到美国的SUV、厢式货车、轻型卡车和汽车零部件等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根据该项调查的结果,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
销售人员考核激励制度和应收账款回收质量有密切关系,考核激励制度不应仅将销售额作为考核指标,应收账款回收金额也是考核因素。而H公司考核体系更注重销售额完成情况,完成任务量有关工资直接挂钩,业绩未达标要扣工资甚至免职,对于应收账款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指标无考核,造成销售人员对应收账款不敏感,盲目销售导致应收账款过多。
如前所述,美国动用许久未用的232 条款,将钢、铝等基础材料以及汽车等民用物品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做法令国际社会感到十分诧异。这一做法背离了WTO 各成员在安全例外问题上一贯以来的审慎和善意。在WTO,虽然存在GATTXXI 条“安全例外”条款,允许各国基于基本安全利益采取违反WTO 基本原则的做法,但该条款被视为“君子协定”,在实践中成员方一直避免援用该条款,避免贸易纠纷升级到安全问题,而特朗普政府连续3 起232 措施无疑打破了维持多年的“君子协定”。
广元市“政担银企户”财金互动扶贫试点工作,探索出了贫困地区盘活农村资产、财政金融互动、贫困人口稳定增收脱贫的新路子。
透过以上情况我们便不难理解,虽然WTO 是美国亲手打造的多边规则体系,但当美国认为自己不能从中获得好处时,其实用主义哲学势必引向通过主张美国例外来悬置WTO 规则。这正是特朗普政府一反常态地动用232 调查的原因:一方面,232 的预防式安全逻辑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以未来不确定性为基础来塑造现在,在这种不可能否认或不可知晓的“国家安全被威胁”的假设情境中,任何情况都可以认为是例外的,政府可以在“安全之幕”下悬置现有的多边经贸秩序,将美国政府的各种进口干预措施合法化;另一方面,沿着这一路径,特朗普政府还可以沿用反恐领域的做法,使经贸领域的例外状态成为一种常规,使主权者不受法律约束,并让自身成为活的法律,在国际经贸中实现施密特所说的“主权专政(sovereign dictatorship)”,重建新的秩序。① Schmitt,C.,2013,Dictatorship.From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o proletarian class struggle. Cambridge,Polity Press.
三、特朗普政府232“国家安全”调查的国内外背景
在一定意义上,话语是对现实的回应。因此,有必要结合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去理解特朗普经贸领域安全话语的建构及其逻辑。
而在欧美,阅读是由来已久的生活常态。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英国,从一战后甚至更早,公立的社区图书馆就已经是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每个图书馆都设有专门的儿童区,面积和图书品种占整个图书馆的1/4~1/3。儿童阅读区完全按照孩子的审美心理和行为方式来布置,颜色艳丽的地毯、低矮的书架、卡通的桌椅、四壁是简单明快的装饰。图书馆不仅仅是免费借阅图书的场所,而且是社区聚会、儿童唱读活动、儿童阅读活动的主要基地,也是退休老人们喜欢的聚会场地,几乎每个村都有老人阅读会,图书馆也有专门的场地免费提供。
在国际层面,美国面对着霸权相对衰退的国际处境。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金融与实体经济,导致美国陷入了全面的经济衰退,步履维艰。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无论对国内经济难题还是国际经济困境,都未能拿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其经济发展态势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这一点触动了美国有关权力转移的敏感神经。当下,美国一方面没有足够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不再有强烈的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它在多边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自信心大不如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甚至指出,美国的超强优势正相对衰落,并将在20—40年内最终丧失。②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s 2020 Project ,Washington,D.C: GPO,2004,p.63.霸权地位的衰落、“他者”崛起对其霸权构成的挑战成为美国最“揪心”的问题。在总统特朗普看来,他接手的美国不再是一个伟大国家,世界其他大国也不再尊重美国。③ 陈积敏:《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载《国际研究参考》,2018年第4 期,第1—9 页。
一旦预警机构发出警报,并将预警信息传递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必须根据地质灾害警报专家组的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经分析,地质灾害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比较高,对人们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那么相关部门应当适时采取应急避让措施,在最短时间内撤离周边居民,并将其安置在相对安全的地区,最大程度地保护周边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232 措施发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对WTO 的满腹怨气。WTO 是美国一手推动并建立的多边贸易体系。历史上,美国通过打造WTO 这套体系获得了一系列收益:信用收益,即美国通过多边规则的自我约束建立起领导者的信用基础;国家安全收益,即美国在二战后通过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帮助其盟国恢复经济,防止其受国内外共产主义影响,以及在冷战之后通过经济相互依存为美提供国家安全保障;此外还有动态贸易收益和国内政治收益等。然而,在WTO 成立20 多年后,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美国对WTO 早已十分不满。近年来,美国影响力下降,伴随着来自欧盟、日本等昔日盟友的竞争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出现,美国不仅难以从这套自己主导的贸易体系中谋取贸易利益,国内政治平衡还因此受到了影响。WTO 由此成了替罪羊,美国开始批评多边贸易体系的合法性,不愿再为其背书。2016年大选前,美国已经因为输了案子而对上诉机构韩籍大法官的连任横加阻挠。到了特朗普这里,他对WTO 的批评更是直言不讳、登峰造极。在竞选时就曾公开表示,“WTO 完全是场灾难”,① Chris Isidore,White House lauded US record with WTO,which Trump now calls a ‘disaster’,https://money.cnn.com/2018/03/02/news/economy/trump-wto-white-house-economic-report/index.html,访问日期:2018年7月23日。 批评WTO“对美国非常不好(treats the U.S.very badly)”。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搁置WTO 争端解决机构中上诉机构法官的选任,使这颗WTO“皇冠上的明珠”已近瘫痪。2018年,白宫被传起草《美国公平互惠关税法案》,该法案所提倡的互惠原则和关税方案,实质上相当于宣告美国从WTO 退群。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WTO 的怨气可见一斑。
产业分工全球布局及“去工业化”引起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美国内部形成了“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即那些在新一轮全球化中被远远甩开的社会底层,包括中西部锈带的失业工人、底特律深受种族冲突冲击和经济衰退之苦的白人城市贫民、被北方自由主义城市深深歧视的南方农民等等。① 郦菁:《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特朗普政权的未来》,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12 期,第52—56 页。 伴随着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政治组织力的真空,这些群体遭遇了深刻的失落、危机和恐惧,结果是民粹主义泛起,这正是未曾有过从政经验的特朗普被选为总统的重要社会背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正是这些边缘化的劳动者和愤懑的中产阶级,在美国经济衰退中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特朗普正是抓住了这部分人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社会需要才得以当上美国总统,他给选民的承诺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此外,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后还要面对复杂的国内治理局面。一方面,社会矛盾不断累积,身份政治的兴起使美国社会陷入相互对立与怨恨,造成社会撕裂。另一方面,两党之争、府会之争也使政府一度陷入窘境。② 同上。
特朗普是在一片质疑的眼光中当上美国总统的。他迫切需要找到合适的执政工具,在较短时间内(特别是赶在中期选举之前)对内避开复杂的政治羁绊、凝聚国内力量,继续推动再工业化、促使资本回流重振美国经济;对外抛开美国认为已变得对自己不利的多边贸易秩序的约束,打造“特朗普式”的国际贸易秩序。在这种局面下,“国家安全”为其提供了抓手。国家安全威胁论被推到前台,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契合特朗普的政治需要:一方面,借着WTO 的“安全例外”条款,在“安全之幕”掩护下直接悬置WTO 的关税约束,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从而达到干预全球产业链、推动资本和制造业回流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建构一个外部的国家安全威胁,将内部成员的攻击冲动指向外部群体,减少群体内成员之间的敌意行为,强化行政机构在复杂的国内治理环境下的权力。① 薛晨:《社会心理、错误知觉与美国安全观的转变及实践——以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2 期,第7—15 页。
四、“安全之幕”背后特朗普政府的国际、国内目标
(一)经济层面:通过高关税推动资本回流,辅佐美国“再工业化”战略
对特朗普而言,“再工业化”对于重振美国经济、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十分重要。“再工业化”战略源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上世纪“去工业化”转型的深刻反思。奥巴马政府认为,必须进行“再工业化”,重振美国制造业,提升美国经济实力。然而,虽有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终因受制于经济规律而效果不彰。特朗普虽然在很多政策上都和奥巴马唱反调,但在“再工业化”战略这一问题上却是一致的。特朗普提出,“‘美国制造’不只是一个口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Made In America’ is Not Just A Slogan,It’s A Way of Life)”。为此,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内减税、对外加税的方法形成组合拳,敦促资本回流,一方面继续国内再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减少贸易赤字。在232 措施下,对进口产品加征高额关税虽有许多负面效果,但其意图是加重进口产品成本,迫使产业链进行重新调整,促使那些关注美国市场的资本回流,以重振美国制造业,振兴美国经济。正如其钢铁232 报告提到的,通过此类措施可以“帮助美国国内钢铁业恢复闲置设备的运行,让关闭的钢厂恢复生产,通过雇用新钢铁工人保护必要的技术,增加钢产量。”
然而,“再工业化”战略并不能解释特朗普政府的全部。虽然特朗普和奥巴马都力推“再工业化”战略,在手法上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奥巴马仍然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去推动其各项举措,他虽然对WTO 在规则谈判上的无所作为不满,但在贸易措施上一方面密集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对进口产品进行限制,另一方面通过TPP、TTIP 谈判来打造WTO PLUS 的新贸易规则。② TPP、TTIP 规定了比WTO 更高的开放标准,扩大了现有WTO 贸易规则的范围。例如,TPP 约定对包括纺织品和服装在内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一律实施零关税措施,或大幅削减关税和其他非贸易壁垒,还将贸易和投资与环保和劳工问题相联系……这些都扩大了现有WTO 规则的范围。 相比而言,特朗普在诸多可选项中选择了232 措施这种“核强度的贸易保护主义”,③ 榮民:《美国“232 调查”背后有玄机》,载《中国贸易报》2017年7月4日,第1 版。 其本质是借“安全之幕”悬置WTO 规则,以最直接、有效的关税壁垒去构建对“美国优先”有利的经贸秩序。应该说,与其他措施相比,232 这种“国家安全措施”在最大程度上契合了特朗普作为政治人物的独特个性和他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执政需要。
从保护国内产业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有一系列可以选择的替代措施,如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等。动用这些措施所引发的争议应该比232 安全措施小很多,然而,在特朗普政府那里,其他可动用的经贸手段都有各自的局限性。首先,中期选举的时间压力使他迫切需要能立竿见影的措施。奥巴马政府两个任期内的“再工业化”战略均效果不彰,在特朗普眼中,这种传统做法不是很好。第二,以保障措施为例,虽然该措施属于WTO 授予成员国的“安全阀”,使成员国在国内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时可以进行自我保护,但《保障措施协定》对于动用措施的条件、因果关系分析、措施强度及适用期限等都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美国2002年曾发起对进口钢材的保障措施,结果被WTO 上诉机构裁定为不符合WTO 协定并被终止。第三,在美国眼中,反倾销、反补贴之类措施也十分不便。美商务部长罗斯在VOA 采访中也提到了将双反调查弃置不用的原因:“这些年来,我们发起了很多涉及钢铁的贸易诉讼。我们事实上对不同国家发起过100多起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的诉讼……共发起了104 起,针对34 个国家的产品。所以这是个十分普遍的问题……然而,这些措施必须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中国最近做的更多的是……他们说要精确到产品,在一起诉讼案中,甚至说要在0.2 毫米内……他们还说要精确到国家。这就让他们容易规避惩罚,因为你可以改变一点尺寸,生产上加工一下。或者不管有没有进一步加工,还可以通过其他国家转运。所以关税的问题是,虽然限制了行为,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整体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开始通过其他国家冒出来了。”② 尹继武等:《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治偏好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 期,第15—22 页。 可见,对于特朗普政府的目标而言,动用传统的双反手段意味着要受到WTO 规则的各种约束,掣肘太多,制约了其目标的实现。
作为总统,特朗普有两个鲜明的特色。首先,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客。在当选总统之前,他没有执政经验。从个性层面来看,他性格不羁,历来对各种传统政治规范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进行各种挑战。① 尹继武等:《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治偏好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 期,第15—22 页。 这两方面共同作用,意味着在特朗普那里,抛开WTO 成员国一贯的善意、动用WTO 的安全例外服务于自身利益并不存在太多的心理障碍。
WTO 毕竟是美国一手建立起来的多边体系,在美国历史上,像特朗普这样毫无顾忌地直接以安全例外为由全面抛开多边规则的情形并不多见。但在反恐领域以及针对个别国家的经贸问题上,“美国特殊”“美国例外”的民族主义色彩一直十分强烈,美国通过例外条款和紧急状态来悬置国际法已成常态。
当美国感到难以再从WTO 体系中获得贸易利益,当特朗普决定时时刻刻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当传统的保障措施和双反调查受到WTO 规则的掣肘而不能实现美国所期望的美国优先效果时,232 调查可以在“安全之幕”下为美国提供最便捷有效的工具,同时将难题抛给WTO 和其他贸易伙伴国——假如WTO 认可美国做法,当然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被WTO 裁定败诉,就为美国退出WTO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美国既然可以退出TPP 和《巴黎协定》,为什么就不能退出WTO 呢? ② 榮民:《美国“232 调查”背后有玄机》,《中国贸易报》2017年7月4日,第1 版。
(二)国际政治层面:通过宣告例外状态悬置WTO 法,推动“特朗普式”的国际贸易秩序
在国内层面,经过新经济和“去工业化”的战略调整,美国新经济比重大幅上升,超过了钢铁和汽车。经济结构调整之后,美国从过去极具生产优势的制造业大国转型为以科技为基础、结合金融优势的新型资本发展模式。制造业部门在整个美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在跨国企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制造业开始向外转移,制造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占GDP 比重也从1980年的20.16%下降到2012年的12.05%,美国经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去工业化”特征。“去工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巩固了美国高端优势产业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利的隐患——美国虽然控制了利润最丰厚的高端优势产业,却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一方面,虚拟经济的泡沫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整个经济体系缺少实体经济的支撑,最终泡沫破灭,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对“去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并力推“再工业化”战略,但受制于经济规律,其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众所周知,GATTXXI 条是安全例外条款,成员方据此享有相当程度的自决权。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有一个著名的定义“主权者就是决断例外状态之人”,主权者透过宣告例外状态悬置整个宪法规范的效力,进而采取重建秩序的任何必要措施。特朗普屡屡在国际经贸中声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利用安全例外来悬置WTO 所建立的现有国际贸易秩序。
情况 2 u1,…,u10的颜色当中互不相同的仅有两种,不妨设f(ui{1,2}, i=1,2,…,10,则当每个C(vj)是2-子集时不包含颜色1或2,因此可以作为Y中顶点色集合的{1,2,3,4,5}的子集的数目为当20≤n≤30时,19个集合不能区分Y中的n个顶点,矛盾。令B=B1∪B2∪B3,其中:
在反恐领域,自2001年9月14日美国总统宣布进入例外状态之后,美国以反恐之名制定了《爱国法案》,对外悬置国际法,对内宣告永久的例外状态,悬置了许多美国宪法中保障基本人权的法律。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延续这种例外状态。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名著《例外状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例外状态下,关塔那摩监狱中被关押的囚犯既不具有日内瓦战俘公约中的战俘地位,也不具有美国法之下的被控犯罪人的地位。他们仅仅是“关押犯”,被完全从法律的视野中抹去。在这里,主权者不仅不受法律约束,更进一步让自身成为了一部“活的法律”。① 刘颜玲:《“例外状态”发展简史——兼论阿甘本例外状态的常规化进程》,载《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3 期,第27—29 页。 这种战争与例外状态的结合在两方面值得我们警惕,一是它在空间上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在内容上逐渐从军事领域蔓延到社会其他领域;二是战争从被动防卫转向主动预防,从起初针对特殊事件的例外措施转变为预防性的一般准则,例外状态成为常规,并成为政府治理的一种惯用范式。
对沈从文小说的原型研究,虽然存在成果数量少、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但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现有研究成果为解读沈从文的作品,特别是解读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同时也使得运用原型理论研究沈从文的小说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在经贸领域,根据1977年生效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IEEPA),当美国遭遇到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的非寻常的外部威胁时,总统有权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以阻止交易、冻结资产或没收与威胁相关的国家或个人在美资产等制裁方式予以应对。该法案给予美国总统的授权较为广泛,既可以是全面干预,也可以是重点打击,可以干预、许可或调查任何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外汇交易、银行支付、证券买卖,以及进出口、投资等各项活动,禁止或限制美国公民或企业与相关国家开展经贸活动。截至目前,美国政府以IEEPA 为由采取的制裁仍然有效的还有27 项,涉及俄罗斯、布隆迪、南苏丹、委内瑞拉等18 个国家,以及中东、西巴尔干等地区,还有6 项制裁为全球范围。由此可见,“国际紧急状态”已经失去了其名称所代表的真正含义,逐渐变成了美国政府单方面对外施加影响的工具,所谓的国际紧急状态成为常态。② 周密:《美国说的国际紧急状态是怎样的状态》,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10 期,第13 页。
起初,生意并不怎么好,毕竟,这个城市做花卉生意的太多了,几乎每条街每条巷都有。随着日子的推移,花店渐渐热闹起来。大多是一些男人,大多都是买玫瑰。玫瑰真好啊,大部分女人都爱。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232 措施甚至背离了美国历史上的常规做法。美国历史上的232 调查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基于232 条款采取进口限制措施的案件从未超越石油类案件的范围。自1962年《贸易扩展法》实施后到特朗普2017年上台之前,美国政府共发起过26 项232 调查,主要发生在冷战时期,涉及的进口产品主要是石油及制造业(涉及原材料、制成品及零部件)。总统最终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决定采取限制性的措施仅有7 起,全部都是石油类案件。第二,自1995年WTO 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仅在1999年和2001年发起过两次“232 调查”,最终均未采取任何进口调整措施。如今,在距离上一次调查十多年之后,特朗普政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起钢、铝及汽车的232 调查,并迅速决定对除加拿大、墨西哥之外的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全面征收进口关税,其涉及国家及产品范围之广、进口惩罚措施之重、决定做出之快,在232 调查历史上是罕见的。钢、铝和汽车并不是典型的国防用品,至多可以算作是军民两用物资,且进口远未达到严重冲击美国产业的地步,如2017年进口钢材只占美国国内消费量的30%,国防需求仅占全部需求的3%。①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Office of Technology Evaluation,The Effect of Imports of Steel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2018.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商务部仍认定钢铁进口威胁到第232 节规定的国家安全,这一做法不仅引发贸易伙伴国普遍不满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指责,还在国内引发了232 违宪之诉。那么,232 措施究竟可以在什么意义上帮助特朗普实现其国际、国内政策目标?
相比而言,232 措施最大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名义下对进口设限。国家安全属于政治敏感议题,为此,GATT XXI 条安全例外条款在表述上比其他条款(如GATT XX20 条)更为含蓄和原则,成为GATT/WTO 内“最为宽泛、争议性最强的例外条款”。① Peter,Lindsay,“Note: The Ambiguity of GATT ArticleXXI: Subtle Success or Rampant Failure,” Duke Law Journal Vol. 52,2003,pp.1277-1313.该条款的模糊措辞导致了不同的解释方案,现实主义政治学派多主张国家主权至上,排斥WTO 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司法权。因此,WTO争端解决机构是否有权审查此类纠纷,应如何裁决国家安全措施导致的贸易纠纷……这些问题均无明确答案。现实中各国遵循善意原则,尽量避免贸易纠纷升级。在美国的理解中,使用232“国家安全”措施来对进口设限是不应受到WTO审查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2018年3月接受VOA 记者采访谈到钢铝关税问题时,就清晰地传递了美国的这一“愿望”:“如果世贸组织告诉我们的总统,什么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在美国会非常不受欢迎。”而在被问及为何采取232措施时,罗斯的回答却与国家安全没有关系:“我们的贸易逆差有两个根本来源。一个是地理性的,那就是中国;另一个是产品,那就是汽车。所以,如果我们要想以有意义的方式减少整体贸易逆差,我们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和汽车问题。”② “美商务部长谈钢铝关税和中美贸易”,http://www.sohu.com/a/225825189_100053199,访问日期:2018年3月23日。 可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是美国关心的重点,而打国家安全牌,是因为可以抛开WTO 纪律的约束。在操作上,美国232 措施的法律基础条文(主要是美国《贸易扩展法》第232 节)措辞十分含混,232 节第(b)(3)(A)条规定,商务部部长对“进口产品在一定的数量或一定情况下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报告并就相关发现提出建议”。该条款未对“国家安全”进行定义,既未规定进口产品足以威胁国家安全的“一定数量”的阈值,也没有定义什么才是“一定情况”。该条文并不要求进口产品正在损害国家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无需是现实的或迫近的,只要有损害国家安全的威胁就可以得出肯定性裁决。232 条款将预防逻辑与含混措辞结合起来,意味着美国国家安全是否受到威胁,关税提高到多少才能应对进口产品的威胁,国内产能需要恢复到多少才能够消除国家安全威胁……这些关键问题均可由政府任意决断。在232 条款框架下,美国政府采取进口限制行动如入无人之境,且难以受到其他权力机构的制约。
(三)国内治理层面:通过建构国家安全威胁增强国内凝聚力,强化政府权力
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种社会事实,那就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并非总是客观存在的。相反,它们完全可能是凭借主观想象和观念假设而被制造出来,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政治建构。以研究安全化现象著称的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表明,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将事物安全化的本质,是通过建构安全“威胁”来操纵政治话语,使其对外政策行动“合法化”。③ 贺炜:《认同、话语建构与美朝核危机》,载《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夏季号;潘亚玲:《“9.11”后布什政府对“敌人”的建构》,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1 期,第98—105 页;李菁华:《方法与应用:话语分析与美国公众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 期,第37—44 页;孙吉胜:《国际关系中语言与意义的建构——伊拉克战争解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 期,第43—56 页;刘永涛:《建构安全威胁——美国战略的政治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 期,第118—129 页。
对安全“威胁”、“冲突”和“敌人”的社会建构是一种政治选择,通过制造这类想象的外来“危险”,政府一方面可以转移国民对某个社会事件或政策行为的关注,将其视线从政府不想(或不愿意)解决的问题那里引开;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把建构起来的安全“威胁”或“敌人”作为政治替罪羊,从而回避真正需要应付的社会及政治难题。① 刘永涛:《建构安全威胁——美国战略的政治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 期,第118—128 页。 在美国,一旦安全威胁、冲突和敌人消失时,政治家们便重新寻找并重建它们,这个过程未必是对国际政治的“感知或现实”的回应。② Jef Huysmans,The Politics of Insecurity, London:Routledge,2006,p.146.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说来自盟友的进口汽车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当国家声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正常的三权分立机制处于失效状态,政府权力被大大强化。国家安全有助于将所有决策权威集中于执行者,安全措施所要求的急切性使政府各部门的代理、审议、管制的制度机制非法化了。③ 冈萨洛·韦拉斯科·阿里亚斯:《生命政治安全设制中例外的正常化》,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3年第3 期,第39—52 页。 在232 条款以及《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下,行政部门有较大行动空间,基本不受限制,这一点令美国国内利益主体感到切肤之痛,以至于2018年6月美国国际钢铁协会提起了“232 条款”违宪之诉。美国国际钢铁协会在其诉状中指出,“232条款”不仅给予总统“开放式的选择”来应对进口产品可能带来的任何威胁,还允许总统基本上可以将对美国经济的任何影响纳入“国家安全”考量中;该措施违反了权力分立原则,违反了宪法保护的制衡机制,却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允许对总统依据“232 条款”做出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④ Americ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eel,Inc.,Sim-tex,LP,and Kurtorbanpartners,Llcv.Unitedstates and Kevink.Mcaleenan,Commissioner,United State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Court No.18-00152,参见http://www.aiis.org/2018/06/america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steel-files-lawsuit-challenging-constitutionality-of-section-232-steel-tariffs/,访问日期2018年8月25日。 这起诉讼以及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试图通过提案限制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征收关税的行动,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特朗普政府为何会频频动用232 条款。在国家安全问题面前,美国行政当局既是宣布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机构,同时又让自己成了执行者。正因为这一巨大的好处,吉奥乔·阿甘本敏锐地指出,在现代国家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例外状态已经成了政府治理的一种范式。
可见,特朗普政府选择232 措施,频频在国际经贸领域声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体现了其特定的政治需要。借着“安全之幕”的掩护,特朗普政府试图在经济上以高关税威胁资本回流,辅佐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在政治上悬置美国早已非常不满的WTO 那些束缚手脚的规则,并进而通过安全化议题来加强复杂环境下的国内治理,试图超出宪法架构来强化政府权力。对于WTO 各成员国来说,它们应清醒地看到话语不仅是现实世界的映射,同时也在“塑造”着现实,特朗普政府通过232 调查正在对国际经贸秩序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影响。阿甘本在他的《例外状态》一书中反复提醒我们,例外状态是一个不断向外推的过程,政府会以紧急情况为开端,然后将其变成永久的常态。以社会治安紧急状态为例,每当宣布戒严、动乱或其他紧急状态时,警察的权力就比平常要大,一旦扩大使用,再收回就比较困难。① 康宇:《例外状态的拓扑结构——阿甘本对施密特例外状态理论的重构》,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4年,第352—361 页。 因此,各国应格外警惕特朗普在国际经贸秩序中将安全例外普遍化的苗头,在观点上应加以批驳,在行动上应联合抵制。
优化教堂广场的空间属性,从目的上讲,即使教堂广场空间成为除具有文化优势外,同时又具有交通优势与视域优势的优质空间,促进更多的人可以到达或经过广场,提高空间活力.而从理论上讲,提高人进入广场的可能性,应提高空间的可达性与可见性.
以Pd(OAc)2/Cu(OAc)2为组合催化剂,无任何配体条件下,苯并恶唑与溴苯为反应底物,考察不同碱对反应的影响.当反应条件为:1(1.0 mmol),2(1.2 mmol),Pd(OAc)2(摩尔分数5%),Cu(OAc)2(摩尔分数10%),碱(2.0 mmol),甲苯(3 mL),110 ℃,在空气中反应3 h,结果如表2.
五、结语
安全的概念始终不能离开解释安全问题的情境而存在。美国《贸易扩展法》第232 条出台于冷战时期。在经济进入深度全球化、各国紧密依存的今天,特朗普将冷战零和博弈竞争思维下的军事、反恐安全逻辑运用于经济领域,并不是出于对安全问题的真实感知,而是要通过建构的国家安全威胁来实现对外悬置国际法、对内在复杂局面下强化政府治理范式的目的。这种做法脱离了真实的情境,不仅不能实现安全,反而会将各国带入安全困境。从国家免于被征服和摧毁的角度来理解安全,则不同领域的安全有着完全不同的前提——在传统的军事、反恐领域,现代武器弹药和战争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小概率事件可以瞬间摧毁一个国家,因此,遏制“敌人”、防止小概率事件的“安全最大化”思维显得十分必要。但在经济领域,上述前提假设完全不存在,甚至完全相反。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各种资源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全球布局,全球产业链得以发展并日臻成熟,相互依存合作是主流,每个国家、行业和企业都从这种模式中发展了自身的禀赋,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形成了其“免于被摧毁和征服”的基础。在合作依存的体系中,只要不出现背叛者,整个体系就是安全的。即使出现背叛者,也不会在很短时间内摧毁或征服一个国家,这一点从特朗普政府2018年对全球产业链肆无忌惮的干扰而全球经济仍继续前行的事实中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零和博弈竞争思维下所追求的绝对安全不仅形成自身的悖谬,并且会形成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avis)所说的安全困境。无须借助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术语,仅凭常识便可知,国家之间如果互相高度猜疑,都对彼此的意图做最坏的假设,进而在维护安全利益时完全奉行竞争与“自助”原则,就容易造成“安全困境”;相反,如果有足够的共有知识或“共识”使它们能够相互信任,宁愿通过协商合作来解决争端,也不愿轻易选择战争等对抗手段,这将有助于培育“安全共同体”意识乃至形成真正的安全共同体。因此,国际安全的状况不仅取决于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或“权力分配”,也受到国际社会在安全上的“文化心理结构”与“观念分配”的深刻影响。
安全的概念很重要,然而,国际经济领域的安全研究中仍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虽然WTO 不是讨论安全问题最合适的场所,也不是安全治理的适宜场所,但不能否认,在国际社会中,如果缺乏对例外状态的清晰界定,最终将因话语的混乱而被一些国家在“安全之幕”的例外状态下任意悬置WTO 规则。笔者赞同阿里亚斯(Gonzalo Velasco Arias)提出的外交现实主义的观点,不将国际法解释为一种无条件的预设,而是正视各个国家主权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不否认国际法作为一种象征性调解的必要性。在经济领域,一方面,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应该清醒地看到特朗普政府正通过国家安全问题悬置国际法,并有将此例外普遍化的危险倾向,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在话语上正本清源,在行动上联合抵制美国的恐吓与极限施压的讹诈做法。另一方面,各国也应广泛展开经济领域国家安全的对话,增进对以下问题的理解和沟通:为了谁的安全?为了哪些价值的安全?多少安全才是安全?全球产业链的格局下如何认定在什么情况下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当长期和短期的安全政策可能发生冲突时,我们如何看待二者各自的成本、手段,并展开理性的对话?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当下,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是一种最佳选择。但是,国际社会的相关共识严重不足,国际安全的基础十分脆弱,安全形势因而难有根本性改观。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提高新的国际安全意识,确立新的价值共识。经典现实主义者一般都能认识到,过度或无限制的国际权势斗争不仅会危害特定国家的利益与生存,甚至可能摧毁主权国家构成及各类交往互动的国际体系。国家安全不仅取决于以自强、自助与竞争为特征的安全战略,也取决于基本的国际安全,即大多数国家独立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秩序,以及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作者简介 :陈若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北京,100089)
中图分类号 :F75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2096-4536(2019)05-0019-14
*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仲裁中的审查强度问题与北京市对外投资企业的利益保护”(项目批准号:18FXB006)、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可持续发展视野下国际投资规则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任康钰)
标签:232调查论文; 国家安全论文; GATTXXI条论文; 例外状态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