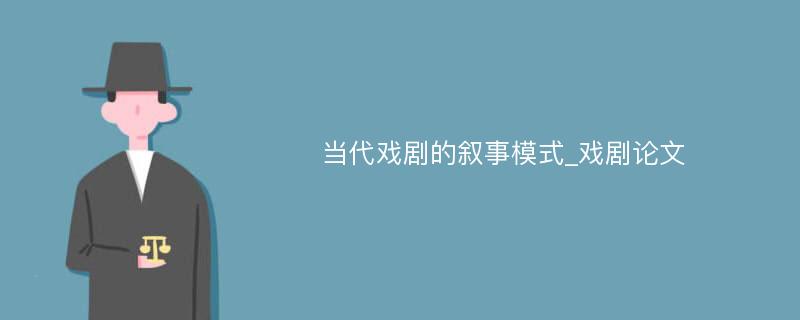
当代戏剧的叙述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当代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凡有文化的地方必有叙事。“我们不必到学校去学习如何理解叙事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世界的新闻以从不同视点讲述的‘故事’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全球戏剧每日每时都在开展,并分裂众多的故事线索。这些故事线索只有当我们从某一特定角度——从美国的(或苏联的,或尼日利亚的)、民主的(或共和的,或君主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的(或天主教的,或犹太教的,或穆斯林的)角度理解时,才能被重新统一起来”。(注:[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不难看出,叙述即意味着一种组织世界的特定方式。泽克尼克则说:“意识形态被构筑成一个可允许的叙述即是说,它是一种控制经验的方式,用以提供经验被掌握的感觉。意识形态不是一组推演性的陈述,它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延展于整个叙述中的文本,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注:转引自《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载《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戏剧叙述是把可感事物安排成序的一种表述,但它是以某一种为艺术家所理解的“秩序”为依据来“说故事”的。艺术和生活都拥有自身的秩序。古典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有一条自始至终的明晰线索,原因和结果存在着一种由此及彼的稳定的链式关系。因此,沿循古典主义的传统戏剧,往往从已有的经验出发充当全知全能的上帝,强调线性因果关联的有序性和内聚力,因而只能按照已有的经验符合逻辑地结构起秩序化生活的情节关联模式,情节的组织、事件的发展符合于生活的既定逻辑。单线发展的情节模式过分人为地简化了生活,在情节模式的因果链外,时常遗落生活丰富的涵盖面,同时,很难表达当代人复杂的意识、感受、经验和价值,阻碍了戏剧把握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这时,超越逻辑的叙述形式便责无旁贷地在传达视角的转换方面表现出超越的优势。在当代人的视角里,世界并非单相发展抑或是一张平面图,广袤的人的内外宇宙永远也不可能被逻辑的情节链所穷尽。当代戏剧超越了这种以情节为表征的逻辑表述,使传统的戏剧叙述辩证地超越了原来的故事性水平,而指向对事件的非逻辑性秩序的排列。非逻辑叙述方式决不意味着“艺术钟”的紊乱,它描画的是主体连绵不断的独到感受。对艺术主体精神的强调,使得当代戏剧蓄意将人们熟视无睹的事物陌生化,将习以为常的事情、人物置于高倍望远镜或哈哈镜之下放大和变形,任意折叠时空使外部动作的连续性中断。叙述的一切手法,“可以解释为最初局面的颠倒,不严格地说,是为了设想秩序恢复的最终结局而打乱一个秩序。”(注:[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第29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当代戏剧以其开放鼎新的态势,从多方面突破戏剧的稳定结构,使当代戏剧叙述表现出大胆创新的动态发展趋势。
1.先锋式叙述
在传统的叙述中,叙述形式只服务于主题,处于“用”的被动地位。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戏剧舞台,是现代中国戏剧文化风景里最富于色彩变化与层次纵深的景点,一群戏剧工作者在现实变得朦胧的非理性氛围里,开始淡化文艺传统的本体性,而日益着重艺术形式的本体性。他们把叙述的形式与文艺的目的性叠合为一,把对叙述的追求上升到艺术的本体地位。于是,叙述的形式受到特别的关注,叙述的游戏意义、叙述的直感愉悦、叙述的语言快感,成为先锋戏剧家们争相表现的创作方法。
a.“形式即内容”的叙述
尼采认为,艺术在本质上只是向他人传达感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表现在为一定的感受(内容),寻找适当的形式,因此,形式对于艺术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只有当一个人把一切非艺术家看作‘形式’的东西感受为内容、为‘事物本身’的时候,才是艺术家”。(注:[德]尼采:《悲剧的诞生》,第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林兆华执导的戏对于艺术手法的创造性使用,都达到了“形式即内容”的高度。八十年代的《车站》的总体演出形式本身就是内容。九十年代又接二连三地在《哈姆雷特》、《罗慕路斯大帝》、《浮士德》中,把玩解构的游戏。如为“演剧工作室”导的莎剧名作《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由濮存昕、倪大宏、梁冠华三人饰演,新王克罗迪斯由倪大宏、濮存昕两人饰演,梁冠华又同时扮演大臣波洛涅斯。他们的分工并不依幕次而定,而是在一种“无序”状态下的存在,有时在同一幕中,二者或三者的身份互换,甚至在面对面地念做之时也会发生身份对调。这种身份的变更是不露声色的,观众只能从台词中领会出来。
濮存昕饰演的哈姆雷特抒发了对母后的怨愤之情后退场,紧接着他又以毫无二致的形象与王后相携上场——却已在扮演克罗迪斯了。国王与王后亲昵调笑,但在观众眼里,此时的克罗迪斯还未把方才的哈姆雷特的影子摩擦退掉。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也是由三位演员同时完成的。分别扮演哈姆雷特、克罗迪斯、波洛涅斯的三个人,在一瞬间转身,相互背对,呈三角形站立,奇异地变成一个人。第一位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位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第三位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三个人的台词之间没有空隙,宛若回声。独白之后,一个转身动作,他们又变成了三个不同身分的人。剧末,倪大宏扮演的哈姆雷特杀死濮存昕扮演的克罗迪斯。但在舞台上,却是“倪大宏”訇然倒下,“濮存昕”站立良久,缓缓开口,念的是哈姆雷特的台词,并吩咐他的朋友霍拉旭(由扮演波洛涅斯的演员充任)向后世传述他的故事。这里身份的模糊,可能是四种解释:哈姆雷特杀死克罗迪斯;哈姆雷特杀死他自己;克罗迪斯杀死哈姆雷特;克罗迪斯杀死他自己。原初文本中的复仇,因先锋形式的叙述,变得丰富起来。而让三个演员对哈姆雷特这一人物作共时性叙述,成功地营造出“人人都是哈姆雷特”这一舞台意象。
b.叙述的游戏性
牟森和他的“戏剧车间”热衷于即兴式的叙述游戏。在他们搬演下的《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与艾滋有关》、《零档案》这些戏中,“没有剧本,没有故事情节,没有编造过的别一种生活”。(注:牟森:《写在戏剧节目单上》,载《艺术世界》1997年第3期。)
如《与艾滋有关》,观众只看到半扇猪肉从挂钩上摘下来,送进绞肉机,最后与大白菜、胡萝卜一道被做成热气腾腾的炸丸子、肉炖胡萝卜及三蒸屉包子的过程。演员或观众在食物制作过程中,可以随意当众讲述自己的任何事。同时,两名雇来的民工砌起了半包围的三面墙。这是“食品制作”、“自由讲述”与“砌墙工程”三种行为的无逻辑组合和平行展开。而《零档案》则根据于坚的同名长诗改编而来,据说在国内未上演过,却参加了1995年夏在伦敦举办的第8届伦敦国际戏剧节。整出戏,是在一位演员的回忆性独白中展开并完成的。那是一种对童年的压抑、苦闷与痛苦的回忆,叙述不时被同台男女演员走路、放录音机、锯焊铁条、吹风机的嘈杂声打断。接近叙述尾声时,锯好的铁条被焊在一个铁架上,像棵枝枝丫丫的铁树,每个“枝端”上被演员们戳上苹果和西红柿,像一颗色彩鲜亮、形状奇特的化学分子键模型。然后,男女演员取下苹果和西红柿,向开动着的吹风机疯狂投掷,让果浆纷落如雨,溅在戏剧活动空间里的所有人身上。牟森后来解释说,“我觉得我们喜欢给观众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并不代表特定的一种意思,而是各种各样的感悟,……我们没有想赋予它什么,不同的观众却赋予它不同的意思。”(注:转引自辰地:《怀旧·梦寻·咏唱——国际戏剧展神话》,载《艺术广角》1995年第5期。)
根据高行健《彼岸》和于坚的新脚本《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捏揉在一起的《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注重即兴型的形体动作表演,动作很随意,几近游戏状态。彼岸是什么?演员在激烈的身体活动的间歇,不断地质问着。语言在形体的停顿后,活跃起来。演员讨论着彼岸的汉语意义,它是一个有花的地方,一片蔚蓝的大海,一个形容词,一个名词,两个汉字,它是正在演出的戏。演员不断地用攀援直喻着人们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如此,语言动作便瓦解了形体动作的喻意,彼岸作为希望理想的象征,在语言和形体的双重叙述中被解构了。
包括牟森“戏剧车间”的其他剧作《红鲱鱼》、《医院》在内,注重的均为即兴式叙述的游戏意义。在《写在戏剧节目单上》(注:牟森:《写在戏剧节目单上》,载《艺术世界》1997年第3期。)一文中,牟森反复强调了这个意图。“《零档案》是一出充满了可能性的戏剧。从构想到排练到现在的结构,都充满了可能性”。“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走上这个舞台,讲述自己的成长”。“这是一出关于自己的戏剧,不是演员扮演别人的戏剧”。《与艾滋有关》是一出“直截了当的戏剧”。“参加演出的人都是作为他们自己。做他们自己的事,说他们自己的话,展示他们自己的生活状态,表达他们自己的生活态度”。《红鲱鱼》“是关于五个演员自己的,是他们对生活的感受、体验和理解。不一定是生活故事和生活历史”。“演员们说的都是关于自己的话,而且每一场演出所说的话都是不一样的话。请观众们不要把这些话理解成事先写好的台词。这些只是说话,日常生活。像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说的那些说话一样”。在这样的“充满可能性的戏剧”、“开放性的演出”当中,“只要你愿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走上这个舞台,讲述你自己”。
c.叙述的语体快感
高行健写过一组短剧,可称为把“舞台调度和动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语言的戏剧”。(注:《高行健戏剧集》,第184页,群众出版社1985年。)抒情短剧《躲雨》,进一对涉世未深的少女的呢喃细语:“甜蜜的声音”和“明亮的声音”。盼望“让毛毛细雨把衣服都湿透”、“恨不得脱光衣服,让雨水淋一场”、“想在雪地里打滚”的姑娘们,在那一段两个声音同时诉说的场景里,其实已各自领略了“不断破碎着的镜子比完整的月亮更好看”、“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的心境。加上“退休老人”的存在,则呈现出人物心境的“复调”。《喀巴拉山口》、《行路难》、《模仿者》也注意语言的密集,让角色絮絮叨叨地大段说理或叙事,以语体的浓烈,拓展现代戏剧的艺术表现力。
孟京辉编导的《我爱×××》,则强化语言组接、表达的语体快感。《我爱×××》于“爱”与“不爱”的语言游戏中来显现它的意义,在混乱无序的意象、幻灯画面的组接中显现出演出者创意的逻辑性。全剧由五男三女八个演员的“爱”与“不爱”的对话组成,革命导师、影星歌星、文学人物与生理疾病、抽象的灵魂与具体的肉身器官……林林总总,演员在“爱”的铺排与“不爱”的干脆中,纵情地张扬着作为个体生命选择的自由意志。“我爱病”、“我爱结核病”、“我爱肝炎病”、“我爱心脏病”、“我爱性病”、“我爱麻疯病”……“爱得爱不得,全在自己愿意不愿意”。全剧在唾沫横飞的语言讲述中,实现着个体生命选择的主观随意性。
先锋戏剧强化了叙述的本体地位,使叙述的形式意义更加突出,而观者也在叙述形式的玩味中获得一定的美感。
2.非常态叙述
近年来的戏剧叙述中,出现了一些非常态叙述的现象,它以别具一格的叙述方式和反传统、非常规叙述的倾向,对当代戏剧叙述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a.分裂式叙述
分裂式叙述是一种双向式叙述。在叙述中,主人公产生人格分裂,从本我中于分裂出另一个自我,而这个我既是本我的影子或幻影,又是处在非常状态的“我”。
如郭大宇、彭志淦的《徐九经升官记》中“苦思”一场,徐九经断案遇到困难,喝得醉醺醺地左右为难。这时舞台上出现了两个“幻影”,一个是徐九经的“良心”,一个是徐九经的“私心”,两个“幻影”互相撕打,三个徐九经同台表演。这在戏剧中是较为别致的。早在1929年,梅耶荷德就提出了两个演员同时表演哈姆雷特的设想,他说:“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同时有两个演员来扮演哈姆雷特,一个念悲怆的独白,一个念欢愉的独白,并不是两个演员轮流上台表演,相反,他们得形影不离。”(注:转引自《新时期文学六年》第3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梅耶荷德的设想是为了使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的矛盾视觉化、形象化,其理论基础是意识的“自我分裂”。六十年代苏联舞台上出现过五个演员同时表演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情况。《徐九经升官记》在这方面的借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洋为中用的新尝试。
高行健的喜剧小品《模仿者》也用了这种叙述方式。在《模仿者》中,形影相吊,影不离形。“这主儿”有自己的影子,时髦姑娘有影子,忧郁症患者有影子,长者也有影子。“这主儿”与“模仿者”(影子)的形体动作除了左右不同外,其它近乎一模一样,但表情与台词由两位演员分别扮演。“这主儿”讨厌“模仿者”,又从“模仿者”照见了自身。事实上,这“模仿者”既是“这主儿”的影子,又不完全是他的影子。加上“模仿者”语义上的宽泛性,远远大于“这主儿”的影子的含义。
林兆华执导的《浮士德》,两个浮士德似乎形影不离地出现在舞台上。浮士德由倪大宏和韩童生两位演员饰演。附着在前者身上的,是那个永远都在求索、时时苦思冥想的浮士德的灵魂。他灰衣旧鞋,蓬头垢面,被头脑中的思想逼得要发疯。韩童生饰演的,则代表着浮士德的另一个灵魂:易受诱惑、易否定、躁动不安、敏于行动的浮士德。从外形上看,后者颇似北京街头招摇过市的款爷。冥思苦想皓首穷经的浮士德对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的浮士德太放任,喝酒泡妞升官发财全凭他意愿,丝毫不加发问,不予反思。在这两个相互割裂的舞台形象演绎的历时性故事里,揭示了在理性和物欲中挣扎的灵魂的两极,浮士德的形象变得丰满起来。
显然,分裂式叙述已远远超出了形式的表层创新意义,与戏剧内蕴的表达密切关联,促进了戏剧主题的掘进。
b.病态式叙述
病态式叙述就是人物病态心理倾泻的叙述方式,其内容由人物病态心理构成。如过士行编剧的“闲人三部曲”,以“偏执狂”式的病态叙述来讲述故事。
《鸟人》讲了一群养鸟成癖的京城市民,领头人为既是鸟痴更是戏痴的三爷,他身在鸟人堆,心忧京剧衰落,特别是自己的行当后继无人。胖子,一个人到中年的京剧迷,日夜渴望成为三爷的继承人。华人精神分析学家丁保罗立志治疗中国的心理病患者,他顺利地将三爷与胖子等养鸟人收入“鸟人心理康复中心”进行治疗。鸟类学家陈博士为追求中国仅有的一只珍禽褐马鸡而混迹于养鸟人中。剧中每个人的视点都是偏执的视点,而整部戏也因此成了对人们在感情、事业等追求上的偏执的嘲讽。
《棋人》也讲述了一老一少因棋而痴的故事,老少棋痴的言行和心理贯串始终,也是一种近乎病态式的自我偏执的展示。《鱼人》讲述的是钓鱼迷的故事,那钓鱼迷为钓上一条巨大无比的大青鱼丢了孩子,老婆也弃他而去。30年后,钓神再次邂逅大青鱼,展形了一场人与“鱼”的较量。显然,无论是养鸟、下棋,还是钓鱼,本来是一种业余的休闲娱乐方式,而剧中人却似乎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事业——倾其所有为之奋斗的事业。偏导者正是通过这种几近病态的偏执狂的独特视角,重新引发了对“人”这一命题的思考。
c.朗诵式叙述
朗诵式叙述,这是一种“读戏”式的反戏剧叙述手法。传统戏剧叙述忌讳缺乏戏剧动作的语言朗诵式的讲述手法,那是对戏剧通则的一种悖离。而当代戏剧则不避其短,反而采用这种朗诵法,依然能使舞台满堂生辉。
上海青年话剧团根据美国剧作家戈奈的作品上演的作品《爱情书简》(袁国英导演),即是一出由两个演员出演的戏。舞台上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位男女演员往椅子上一坐,开始读他们手中的信,一读就是100分钟。信是从他和她从7岁在教室里写便条开始的,整整50年的书信往来,340封信。两个人的心灵流动及生活际遇,通过他们各自叙述的命运透视到社会的变迁和世态的炎凉。这是一出独具匠心的舞台艺术,其方式极为简单:读信。这是一次朗诵,也是一次挑战,因为把朗诵读行为变成戏剧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朗读却成为戏剧的叙述手段已是现实。剧作完全依靠演员的语调、情绪来感染观众。
王建平编剧的《大西洋的电话》,构思别致:一个名叫丁玫的中国女人刚来到美国,便或打或接了50个电话,电话中迎接她的,是变卦、敲诈、性骚忧、排挤、恐吓等,终于使她精神崩溃、希望破灭,不得不含泪回国。剧作成功而痛快地对出国及自由美国的神话进行了一次道德评判。该剧的叙事方式很特别,一个人,从头到尾接电话,故事、情节是通过她的语言表达“带”出来的,剧中人物如丁玫的丈夫容德和女人琪琪、老同学芬芬、外国人戴维、病人哑女及母亲沃伦太太、公司董事长埃米尔先生、气功师黄山和其女友阿慧、来自上海的经理夫人等,也均未出场,而出现在丁玫的语言中,以丁玫的语言塑造了这些未出场的各色人物。这种独角口语式的讲述方法,也是以往戏剧所不曾看到的。
3.戏剧性与叙述性相结合
戏剧性与叙述性相结合,这既是剧作的体例问题,也是当代戏剧舞台创作中喜欢用的一种叙述方法。布莱希特把欧洲传统话剧称之为“戏剧性戏剧”,把自己独立的史诗剧称之为“叙述体戏剧”。这两种剧作方式和演剧方式本是背道而驰的,然而,随着对艺术规律理解的深化,纯粹的“展示”抑或纯粹的“叙述”已不为多见,寥若晨星。而更多的以传统“展示”式为重的戏剧创作中,“叙述”总不失时机地穿插其间,叙述使戏剧获得了艺术升华的良好机缘。“现代戏剧一旦捡回了这门艺术本身就曾经具有而一度被丢失了的叙述手段,便会面临一个新的广阔的天地”。(注:高行健:《我与布莱希特》,《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第5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当代的剧作家和舞台表演艺术家们倾向于把戏剧性“展示”和叙述性的特长结合起来运用,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从演出来看,《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凯旋在子夜》、《中国梦》等剧目,都是这两者结合的很好的例子。
具体到表演来看,要求演员既扮演角色,同时又要跳出角色,在表演中渗进创作主体的“自我”对对象主体的“自我”的某种判评态度以及有时的客观叙述。要让观众感觉到有一个作为演员这个创作主体的“自我”在高屋建瓴地观察着自己的表演,并对创造角色形象和进行高超的技艺表演这两者的关系,从中加以调节、控制,有时也投以必要的评价意识,让戏剧性与叙述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饰演帅克的梁冠华,在表演被纳粹抓去当兵以后,向斯大林格勒进军的那段戏,便是一例。梁冠华一面以哑剧式、比较有规范的步态表演行军,一面扭头向观众述说:“现在,帅克正行进在通向斯大林格勒的大道上。”之后,他又同一只狗交流、对话。狗的形象实体并未出现,是演员假设的,存在于他的想象中。但是,狗的叫声,狗的大小形状,狗的行动,却是由演员同时表演出来的。也就是说,演员既在扮演帅克,又在表现狗的存在,而且还要表现帅克与狗之间的“谈话”。当演员以帅克的名义进行行军表演时,这是“戏剧性”的,当演员一面表演行军、一面用介绍者的口吻向观众说话时,即既是演员又是角色,戏剧性与叙述性得以结合。而演员在与狗交谈时,既要扮演帅克,又要表现狗的存在以及自己与狗的关系,就体现出两者结合基础上的技艺表演,而作为演员这个创作主体的“自我”,始终在驾驭和协调着角色创造和技艺表演的关系,并且担负着与观众直接交流的任务。
在北京人艺推出的《狗儿爷涅槃》中,除了序幕和尾声属于狗儿爷的现实生活之外,中间的几大块戏都是这一角色的回忆与幻觉。林连昆扮演的狗儿爷,根据这一情况,采取了现实与回忆两种时空重叠的双层次表演,即在不关闭大幕来改变化妆和更换布景的情况下,既扮演现实时空中的狗儿爷,又扮演“闪回”时的心理时空中的狗儿爷。当演员用回忆的语调叙述往事时,他是70多岁的狗儿爷在向观众诉说,他的口吻、心理状态和形体特征是老人的感觉;一俟由叙述进入回忆中的以往生活的特定情境中时,他便立马改变原有形态而成了彼时彼地所需要的年龄感觉和心理状态。比如土改那段,狗儿爷先是站在台口向观众诉说往事,当说到民兵队长出现在演区时,演员(角色)马上就进入了回忆中的土改情景。民兵队长一下场,这段戏一完,演员的心理形体随之改变,规定情景又回到老年狗儿爷向观众絮说的现实时空中。在土地、牲口“归大堆”(入合作社)后,狗儿爷到亡父坟前哭诉,演员是既“表”又“做”,即既叙述,又表演。一方面,演员富于感染力地表现了人物因失去发家致富的手段而向爹的亡灵哭诉委屈的心情;另一方面,又非常生动地叙述了他自己如何被村长拉去喝酒、谈话,又如何经不起挂大红花的诱惑,终于把土地和牲口倒进“大祸”去的情境。这种既“表”又“做”的方法,演员不仅扮演了角色,创造了活生生的人物性格,又显示了高超的技艺,同时,又有对角色厚重的评价意识,是“体验”与“表现”的高度“同化”。
由莫斯科共青团剧院导演执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红茵蓝马》,全剧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演员既扮演列宁,又作为列宁的扮演者出现。观众新奇地看着一个身穿茄克衫、牛仔裤的张秋歌,从观众席走上舞台,当众换上西装,并在面对观众的叙述过程中,逐渐由一位客观的叙述者“化身”为他所叙述的对象——列宁,又时时从“列宁”中跳出来,恢复为客观叙述者。演员说着“列宁走进办公室”的同时,也就“走进”了办公室,几乎在说着“列宁拿起报纸”的同时,也开始翻阅桌上的报纸。作为列宁的扮演者,他介绍剧情、评价历史,既是演员,又是观看评述者,作为“列宁”,他是列宁的扮演者所“引述”的剧中角色,传达人物思绪、复杂的内心体验过程。在角色与扮演者时进时出的转换中,将当代观众与历史人物情感、思索重叠在一起,引发观众与剧中人物的共同体验,又与剧中人物保持一定距离,以当代意识去探究历史,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当代社会。
显然,叙述性与戏剧性的联结,既有片断内部的细腻、逼真,重视矛盾冲突,发掘人物心理,又有直接对展示性场面的中断、评说,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用,无疑使演出场面别开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