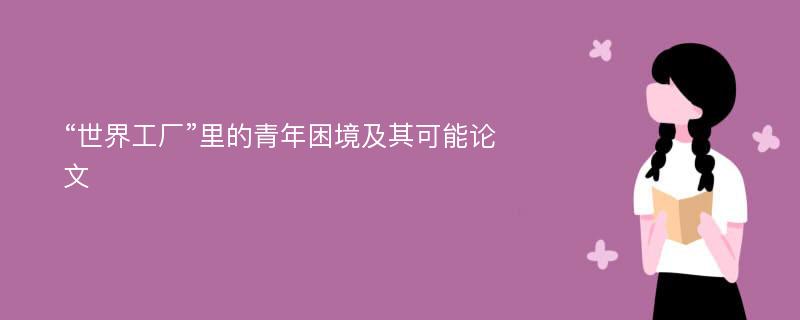
“世界工厂 ”里的青年困境及其可能 ①
蔡 博②
[摘 要 ]导演郭熙志的纪录片《工厂青年》(2016),聚焦于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工人群体,并以“工厂”“青年”“故乡”“日记”等四个章节,将工厂青年-知识青年、生产-消费、城市-乡村、中国-世界等不同维度,纳入到了对青年群体的整体性观察中来。透过该片对当代青年现实处境和精神困境的细致呈现,本文试图分析并阐明,今天的工厂青年不仅在工厂车间里完成着超负荷的生产劳动,同时还置身于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中。而知识青年与工厂青年既共享着这一意识形态结构,又被其加以区隔。如何有效地打破这种区隔,进而破除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迷思,成为了青年人在今天必须重新思考和共同面对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工厂青年》;世界工厂;知识青年
2014年底,郭熙志带着两名大学生,扛起摄影机,来到深圳市康佳通讯制造总厂,开始了纪录片《工厂青年》的拍摄。郭熙志是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在进入高校之前,他曾有过二十年在地方电视台工作的经历,并创作过《渡口》(1998)、《喉舌》(1999)等观照现实的重要纪录作品。此次和他一同参与拍摄的两名学生,阿婵和阿涵,一位已经毕业工作了两年,却感觉自己一直在浪费时间,另一位仍在学校念书,她们都对纪录片怀有理想和热情,想借这个机会学点做纪录片的手艺。之所以选择以工厂青年作为拍摄对象,郭熙志说,他希望能以纪录片为媒介,回应曾经发生在富士康工厂里“十四连跳”的残酷现实,追问那些年轻人在自杀前究竟承受了多大的工作与心理压力。
富士康惨案发生的2010年,世界经济依旧处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阴影之中,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则加速了从实体经济向互联网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步伐。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和区域化竞争当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世界工厂的定义也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而悄然改变。在这一背景之下,新生代的中国工人群体开始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尽管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的境遇和命运不乏讨论,但在很多时候,这些讨论乃至其讨论的对象本身,依然湮没或遮蔽在以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主流的话语逻辑里面。[注] 其中,美国《美国》时代杂志将2009年的年度人物选定为“中国工人”,无疑最具符号意味;而国内在2017年末,对于所谓“低端人口”的“治理”也与外来务工人员、新生代工人群体相关,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郭熙志的摄影镜头所聚焦的,便是这样一群流水线上的工厂青年,而对他们精神困境的探寻和呈现,则赋予了这部纪录片更为丰富且独特的价值。
郭熙志将自己拍摄《工厂青年》的方法称作“不作为美学”,整个拍摄过程既没脚本也无计划,唯一事先确定的仅仅是,要让参与这次拍摄的两名女大学生也亲自进入工厂车间,按照产线工人的作息和管理要求,在流水线上工作一个月。由此,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三位拍摄者不仅为我们记录了世界工厂里的生产情形,还跟随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一同过年返乡,一同感受他们家乡的变化及其与父辈间的隔膜,同时还留存了一份颇为难得的工厂影像日记,也正是通过这种日记形式的影像档案,观众得以窥探到当代青年内心世界的隐秘一角。这些多声部的素材经过了近两年的剪辑,最终以“工厂”“青年”“故乡”和“日记”四个部分,被有机地组织到了三个多小时的成片当中——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导演剪辑版里,“工厂”和“青年”两个部分则用更丰富的素材分别扩展成了两个章节:“工厂(上)”“工厂(下)”和“男青年”“女青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内部对于仓储与配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慕思捷表示,随着大城市的购买力愈发旺盛,物流业对设备的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这给整个物流业都带来了挑战,使从业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在电商还没有崛起的时候,他们不会遇到用智能手机下单,然后要求24小时内送达的消费者,而随着移动互联和电商的发展,这种购买方式已经逐渐成为常态。因此,解决在庞大需求的背景下产生的供应链新需求,是我们现在最为关注的事情。”
可以说,这样的拍摄安排和叙事结构,将物质与精神、生产与消费、城市与乡村、中国与世界等维度一同纳入了我们的观察视野,为锚定、追踪工厂青年的生存轨迹和内心起伏提供了更具纵深性的社会坐标。不仅如此,这部纪录片还让车间里的工厂青年和更为人们熟知的知识青年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对照,作为拍摄对象的工厂青年不再是外在化、他者化的存在,而与大学生群体构成了一组密切的镜像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纪录片《工厂青年》确实“标志着一种重新整体化意识的觉醒,为我们重新理解现实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1]而当我们借由这部纪录作品尝试着推开现实之门,我们或许首先要追问的是,今天中国的新生代工人群体,是如何被“嵌入”到世界工厂当中的,他们遭遇着怎样的外部处境和内在困境;而同样置身于这一结构里的知识青年们,又面对着什么样的危机和难题?
一位高个子男孩抱怨道:“我说世界太不公平。”他左手边黄色头发的女孩立刻接话说:“世界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世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高个子好像对这种成功学的说法很不屑,忍不住骂了句脏话。他右手边的男生帮忙反驳道:“那为什么女的化妆,男的不化妆?”另一位女孩这时也加入了谈话,她说:“自己心里不公平,才会觉得世界不公平。”他们接着说起现在到哪里工作都不好找。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于自身处境和现状的不满,让“不公平的世界”成了他们最直接、最切身的感受,但从上面简单的对话中我们发现,大家在基本一致的现实判断面前,却有着不太相同的态度和反应,并且更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当他们试图言说这一严酷现实,话题很快就滑入了性别差异的层面。黄发女孩接着刚才的对话继续说道:“那以后,女的养男的怎么样?”这个问题显然引起了他们更大的兴趣,一番“辩论”之后,两个男生都认为男女平等根本是在扯淡,高个子继续举例说道:“就好像女的进厂去干活,永远都不会太累。”黄发女孩则说女的一样有压力啊,没有重活的压力,也有心理的压力。这回轮到高个子说,“那是你们承受能力太低了”,“你们插个卡,合个盒子有压力吗?”
一、世界工厂的空间与时间
在三小时版的《工厂青年》[注]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由于三小时版和五小时版均共享了基本一致的结构框架,只是在素材的丰富程度上略有差别,因此这部纪录片的两个版本将一同纳入我们的讨论。 里,影片开场是一个将近六分钟的镜头,令人印象尤为深刻。这个漫长的开场镜头之所以让人难忘,并非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信息或展现了什么独特视角,相反,这个镜头仅仅是用了一种平缓而单调的方式拍下了空无一人的工厂车间:拍摄者从车间的最右侧一直横扫到最左侧,接着再以同样的节奏和方式折返回来,其间除了依次排开的七条流水线之外,别无他物。这可以是任何一家制造业工厂里的任何一个车间,既无美感也不抒情,而数以亿计的流水线上的青年们,正是在无数个与之类似的地方,完成着每天超负荷的工作。这种机械性的往返运动和漫长的时间过程,营造出的无疑是某种压迫式的观看体验,夹杂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噪音,对观众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这种折磨是双重性的,既来自最本能的生理反应,同时也来自这样一个令人倍感困惑的疑问:世界工厂,究竟是机器的工厂,还是人的工厂?进一步说,当我们试图在今天讨论工厂青年,青年们在工厂里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世界工厂里的时间与自然时间并不相同,在纪录片的镜头里,观众往往难以察觉这种时间的流动。工厂车间永远灯火通明,光洁的地面也总是倒映着天花板上的灯光,这让我们只能借助窗外光线的变化勉强分辨眼前的场景是在白天还是夜晚,以至于时常会忘记自己看到的很多工作其实是在“加班”中完成。“加班”是工厂青年们自觉不自觉间最常提到的一个词,但依照这家手机制造厂的规定,直到每天夜晚八点半甚至九点前的工作,全部都是“义务”的。拍摄者阿涵在她第十八天的“工厂日记”里提到了两个新来的女工,起初她们觉得“只要愿意给钱,就愿意加班”,但阿涵补充道,“可能她们刚来,也根本不了解什么叫义务加班,总之听到今天晚上加班没有钱的时候,两个人都委屈地说,那我不来了。”阿涵在这里陷入了很长时间的停顿,不知是出于一天工作的疲惫还是因为自己想到了别的什么,随后她才继续说道,“但是晚上她俩还是来了。”义务加班当然不是这个厂的发明,比如“义务劳动”,但“义务”二字包涵着个人与集体/共同体超越了利益的另一种关系,包涵着个人对集体/共同体的认同,因为这一认同而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然而,在劳动力/劳动已经成为商品的今天,当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成为一种身不由己的义务和规定时,世界工厂的时间性再次体现出了特定空间及制度上的合谋。直接地说,工厂车间里的时间是由可以不用停歇的机器所主导的,并且决定着工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全部时间。
事实上,我们鲜少能够看到真正的管理者也即领导层在车间里现身。在五小时版的《工厂青年》里,领导唯一一次视察流水线,他们谈笑风生地说到了对工厂未来的“美好畅想”,那是在利润推动下的更高程度的“自动化”,几乎可以不用工人就能完成生产。而在这个未来还没实现之前,当前更为重要的则是产品的“策划与包装化”,是像罗永浩[注] 罗永浩,锤子科技创始人,曾先后在互联网、教育培训等领域创业。2012年初,罗永浩开始进入智能手机行业,因擅长利用手机研发、产品发布等环节制造各类话题,一度引发大众的广泛关注与质疑。 那样去炒作。同样是在五小时版当中,有一个刚刚工作了两个月的小女孩不知为何想要申请辞职,她拿到了一堆表格并被告知要找不同部门的领导签字。镜头中的她显得茫然无措,既搞不清楚表格上的“离职”和“辞退”的区别,也弄不明白每份表格究竟要找谁批准。尽管有老员工告诉了她各个主管的姓名,但她显然无法把那些名字和人对上号,只能在一间间办公室门口小心翼翼地徘徊,在好几次无功而返后,她显得很不耐烦,想要干脆直接走人。辞职女孩的经历和领导考察的段落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不仅为我们进一步扩展了工厂的空间,让我们看到现代企业制度下所谓世界工厂的等级结构,同时也再次反证了工厂青年与生产车间彼此绑定的位置关系。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世界便是由宿舍到车间的两点一线所构成。他们在手机生产的流水线上进行着插卡、贴标、检测、拆机等重复劳动,然而这些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无法和市场营销相提并论,并且即将甚至正在被更为自动化的机器完全取代。
第十二天的影像日记长达16分钟,几乎是整部纪录片中最长的段落。阿涵的这次爆发,可以看成是这些天来超负荷工作和情绪压抑的结果,因此她对着镜头几次哽咽道“我觉得好累啊……我感觉心好累啊……”但联系之前的日记来看,似乎还有某些别的因素在一起发酵酝酿。比如,她曾提到有位年轻的女工做了一个奇怪的恶梦,梦见自己一生过得特别惨,这让阿涵觉得“有时候跟她们聊,感觉挺替她们未来担心的”,她自己虽然念了大学,但对未来“也是很迷茫,也不知道这辈子究竟该以一个什么方式走下去”(第五天)。换句话说,这次特殊的拍摄经历似乎让阿涵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并且在身体感觉和情感体验上,都与以往大不相同。她狼狈不堪地来到一个陌生的位置,还来不及或许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整理这些新鲜的经验,而曾经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正在渐渐离她远去。我们注意到,在阿涵工厂宿舍的床头有一本灰色封皮的书,这本书名为《理想主义的困惑》,是对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精神足迹的追寻。阿涵此时就深陷于某种困惑当中。她在这天的日记里,说起了自己对纪录片的热爱,说起了自己进大学后如何萌生出要拍纪录片的想法,但她现在却产生了一丝怀疑:
除了整齐划一的宿舍和食堂,我们在《工厂青年》有关“工厂”的章节里,可以看到大量直接表现工厂空间的镜头:进入车间前的打卡处、离开车间前的安检口、白帜灯下的流水线、存放工作服的更衣间、大门紧闭的办公室,以及无处不在的监视探头……如此种种,和我们曾经从媒体上零星得到的关于现代化工厂的认知别无二致,只不过此时此刻,当这些空间一起出现在观众面前,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些现代化的世界工厂仿佛有着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它们不仅自行监控着工厂里的一切运转,同时还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散发出气味——导演郭熙志特别在某个细节里提到了流水线上刺鼻难闻的味道。在这样一个工厂空间里,各种机器发出的声响很容易将流水线上年轻工人们的说话声压盖下去。与此同时,这些年轻人的面目是模糊的,甚至在他们之间也更习惯用各种工种的名称来称呼彼此,如:QC(质检员)、工艺员、线长等等。他们穿着统一的防尘服、戴着同样的防尘帽,唯一的区别在于,不同级别、岗位的制服颜色不同:绝大部分工人是白色、线长一级是蓝色或黄色、考察来访的领导及外宾则是粉红色。
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职位的业务工作是文献整理、编辑与出版,其职责之一是编制专题书目和索引,以服务于学术研究。例如王重民编《国学论文索引》(中华图书馆协会1929年出版)、赵万里编《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出版)、孙楷第编《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出版)等。其职责之二是参与编辑馆刊和杂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读书月刊》《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以及《图书季刊》(中、英文两版)等。赵万里、向达、王庸、贺昌群等青年编纂都曾参与上述馆刊和杂志的编辑事务。其职责之三是进行文献整理与研究,发表学术文章。
到了这部纪录片的“青年”章节,我们终于能够听清那些年轻人在车间里的闲聊,但他们的谈话总会被手头上的工作打断。一位小伙问他隔壁工位的年轻女孩,“在宿舍孤独的时候,你会想起谁?”从接下来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小伙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听说这女孩有次一个人在宿舍感到心里特别难受,而他对她显然很有好感,想要找机会表现自己的关心。当女孩听出小伙的意图之后,她连忙否认说自己“很少孤独,孤独的时候就会听歌”。这段有点青春偶像剧味道的对话,发生在流水线上。事实上,小伙和女孩聊天的同时,两人都没停下手里的工作,并且在整个谈话中,他们也几乎没有任何视线的交流,女孩一直埋头看着手上的电路板,小伙则一边扫描着什么原件一边盯着面前的显示屏。小伙的工作显得熟练很多,因此他有更多时间说话,而女孩似乎无力分心,不一会儿她便抱怨“堆机了”——前面工位的机器堆积到了她的工位——小伙只得说:“好,先不说了。”类似的情形在这部纪录片里还出现过很多次,且几乎无一不是以“堆机”作为聊天的结束。如果说“加班”“义务加班”显现的是工厂时间对自然时间的强制延长,那么“堆机”无疑是前者对后者的某种无形挤压。也是在这样一些地方,我们反复体会到了机器的时间带给工人们的胁迫感。
换言之,工厂青年们正置身于一个边界更为模糊、疆域更为辽阔的“世界工厂”之中,他们一面在流水线上生产着智能手机,一面又透过手里的各种电子屏幕生产着本不属于他们的政治经济位置的文化逻辑和话语现实。对他们而言,这或许是一种新的感觉结构。由此,他们在过年回家面对父辈、故乡和土地的时候,始终感到隔膜。就像我们在这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样,乡土的风物与风景,仿佛已经成了这代工厂青年手机摄像头里的数码景观,父母一辈的奋斗经历和坎坷心酸好像也并不比游戏中的打打杀杀、电视里的恩怨情仇更有感染力。这显然不只是从乡村出走到城市的工厂青年所特有的感觉结构,作为拍摄者的两位女大学生,或者说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的知识青年群体,就同样身处其中。
尽管我们说机器的时间构成了世界工厂时间性的主导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全部。世界工厂的时间还与产品发布的周期有关,与世界贸易和全球竞争有关。并且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种时间更与其相应的等级化的空间结构、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一起,共同形成了今天工厂青年们生存发展的最主要的外部环境。那么,他们在生产之外的个人生活与精神世界又是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纪录片中有关“青年”和“故乡”的两个章节。
二、生产之外的再生产
对式(21)求导,用作为控制u3,k的标准二维双积分系统替换式(16).然后,用式(17)~式(21)求解未知的关节位置和速度,求解非奇异系统得到关节加速度为
于是对女神展开夏季攻势,又展开秋季攻势、冬季攻势和春季攻势,却收效甚微。楚墨的所谓攻势仅限于上前搭讪,“你好”“你好吗”“你 好啊”“你 好 哇 ”“ 你 好噻”“你好不好”等等,至多配合上他拙劣的摘帽、点头、弯腰、鞠躬甚至单膝跪地。他造作并且夸张的表演非但毫无浪漫可言,简直让人厌恶透顶。
如果没有摄影机郑重地记录下这些片段,我们或许不太可能聆听到工厂青年的声音,即便有机会听到,大概也只会把它当成是工人们打发枯燥劳动的闲聊,或者年轻人间无意义的斗嘴。但这其中实际上潜伏着一层更为隐秘的话语逻辑,值得我们去做更细致的讨论和推敲。首先自然是以性别的差异去谈论,甚至可以说是替换社会结构的差异,因此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公平变成了男女间的不平等。其次,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为什么不公平的命题也就很容易被打发、被搁置,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尽管可感可知,但如今俨然成为了一种前提,我们只能用机会主义、成功学、或心灵鸡汤的方式来寻求慰藉。不仅如此,当大家试图以个人的现实感、肉身感继续这一话题时,谈话的内容毫不意外地再次回到并被局限在了世界工厂的结构和流水线的时空当中,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其他的生命经验和资源可供支撑或打开这样严肃的讨论。在做上述分析时,我没有以工厂青年为特定的主语,这既为了避免引发对这一群体有所苛责的误解,更重要的是想说明,这样的言说方式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的大众媒体和各种话语生产中随处可见,而他们有关“世界不公平”的闲聊不过是这个同心圆中的一环罢了。如果这个同心圆的结构,可以粗糙理解成是当代主导性意识形态询唤的结果,那么就不难发现,工厂青年在其生产劳动之外,同时还进行着这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在他们关于许立志诗歌的聊天里,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得到了更为清晰的显现,但其中又似乎包裹着更为复杂而暧昧的面向。许立志1990年出生于广东省揭东县,高中毕业后开始在珠三角打工,并于2011年进入到深圳富士康工厂——这些经历和我们在纪录片看到的工厂青年们的经历极其相似。然而,就在这部纪录片开拍的两个多月前,被车间工作折磨到身心俱疲的许立志,从深圳市区的一座高楼上纵身跳落,他在打工期间写下的大量诗歌,也终于化成了一声声“绝望的回响”。解读青年许立志的自杀,无疑内在于导演郭熙志的创作冲动之中,因此当他将镜头对准同样一群工厂青年时,导演有意将一本在许立志身后出版的诗集拿到了他们面前。几位女工围拢在流水线上念起了许立志留下的诗句: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我被它们治得服服帖帖/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不会控诉,不会埋怨/……/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拒绝迟到,拒绝早退/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我就那样站着入睡》,女工们念出来的诗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对她们生活的直接描述,同时让她们格外兴奋的,是其中提到了“灰色的薪资单”,但她们没做任何隐喻性的解读,仅仅是将富士康的工资单和自己工资单的颜色比对了一番。当得知许立志已经去世之后,一位站着的女工迫不及待地往后翻阅起诗集,想要“看一下,他后面是怎么死的”。她像侦探一样搜寻着线索,她发现有些字不认识,而当她看到像“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阿嬷的弥留之际》)这样的诗句时,她说自己也会写,而“世界之窗/欢乐谷/东部华侨城/海洋世界/大小梅沙/仙湖植物园”(《深圳深圳》),好多地方她都还没有去过。然后,她找到了一些和死亡相关的诗句:“想死/你就去写诗”(《有题》),“锤下这最后一钉,我就可以安息了/……/母亲呵,我就要回到您的子宫”(《重生》),“可是这些我都办不到了/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我弥留之际》)——从她们挑选出的字句中,女工们一再确认许立志死亡的结局,可仍旧无法找到任何具体的原因或直接的解释,那位站着的女工为此显得有些失望和着急,她问道:“他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跳楼,谁能跟我解释一下?”
毫无疑问,对许立志诗歌的解读,在这里是以一种颇为戏剧化、通俗剧式的方式展开的。将许立志的命运转译成充满悬念的探案故事,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他远远没有走完的一生。但从文化循环的角度看,女工的这种“转译”所表征的或许正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大众文化创作与传播的主导机制,从曾经的流行歌曲、影视剧,到时下的网游、手游等等,概莫能外。我们没有更多的篇幅进行大众文化批判,并且简单的批判逻辑也很难说明今天的大众文化是否蕴含了某些积极的能量、调动了些许异质性的传统,从而让裹挟其中的工厂青年们没有那么轻易地走向许立志式的宿命。这里试图强调的,依然是当下的工厂青年在生产劳动之外,在他们的闲暇时间里,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中;而这恐怕正是消费主义的发展诉求和城市中产式的文化政治,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扩展自身的必然要求。如果不首先厘清这一层现实关系,对于工厂青年们在纪录片里展现的种种生活方式(如到影楼去补拍婚纱照,公司年会上的旗袍秀)、自己的奋斗目标(有房有车才结婚)、内心的欲望和想象(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将来自立门户做点小生意就能自由),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产生真切的体认、同情、理解。
有四个年轻工人在生产线上偶然谈起了“世界的不公平”。他们背对镜头,忙碌的身影连成一排,虽然看不清他们长什么样子,却能让我们从中把握到这个群体某种共通的感觉结构。
应计盈余管理。虚拟变量。采用修正琼斯模型 (Dechow等,1995[26]) 计算操控性应计,应计盈余管理的计算模型如下,先将模型 (1)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再将估计出来的回归系数带入模型 (2)。
三、理想主义的困惑
这部纪录片里有一段字幕特别提示我们,阿涵和阿婵被导演郭熙志要求在这家工厂的组装车间工作一个月,并且“她们的工作量与作息时间要同流水线上的工人保持一致”。事实上,要在结束每天的工作之后,继续录下一份影像档案,对于两位大学生来说并不轻松,起码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在五小时版纪录片的“日记”章节里,观众一共看到了22天较为完整的记录,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阿涵;除了极少时候是在产线上拍摄之外,几乎都是在更加私密的空间或宿舍里完成。头一周的日记里面,提到最多的便是几乎难以承受的工作和疲惫不堪的身体。甚至在第二天下午,阿涵就“感觉都做不下去了,然后挺烦躁的,不想加班,想回来睡觉”,而她之前以为这份工作“不会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累,反正都是坐着,然后就不停地做呗”。第六天是星期天,阿涵仍穿着工作服,一直没有抬头看摄影机,她显得非常疲倦,声音很轻:“今天加班。最近好像已经习惯了,觉得没什么”,可接着她就陷入了长时间的停顿,在说了句“今天不想再说了”之后便起身关掉了镜头。接下来的几天,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阿涵在“每次堆机的时候,就会感觉很慌……希望自己能像一个机器一样”(第七天),即便有时没那么忙,但“可能插了十天卡,每天都在做一样的工作……还是会觉得挺疲惫的。感觉最近睡得也挺早,但是好像每天都不怎么打得起精神”(第十天)。终于,在第十二天的时候,阿涵独自面对镜头,情绪出现了彻底的崩溃。
在每天的工作正式开始之前,全部工人都会被召集到车间门口,背诵一段口号:“……我们正直坦诚,我们实干进取,在变革中成长,在创新中超越,奉献精致产品,引领美妙生活……”[注] 本文对纪录片中出现的对话、采访等内容,均参考原片字幕进行直接援引,仅在个别地方修正或省略了某些过于口语化的表达,下不赘述,特此说明。 这种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在今天早已司空见惯,然而,口号里的“成长”“超越”“精致产品”“美妙生活”似乎都与流水线上年轻的工人们无关,即便在这部纪录片的全部章节里,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在这二者之间存在过任何实质性的关联。当每天重复而机械的工作告一段落,线长们也会被安排集体训话。一名线长负责人对他的同事强调着,大家现在的底薪已经从原来的2300元涨到了2700元甚至2900元,他希望大家的工作能够对得起这份底薪,同时在最后提醒大家记住两个字:意识。这位负责人没有在镜头里说明究竟是什么“意识”便宣告解散,我们大致可以猜想,恐怕他自己也无法说清其中含义或具体所指,似乎也没考虑过底薪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物价攀升间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训话以及在同事中建立起来的那种威严。实际上,拍摄者如实记录下的这两个片段,是我们在三小时版纪录片的“工厂”章节里,难得能够听清的由工人们发出的声音。但与其说这是工人们自己的声音,不如说这是作为某种有机体的现代工厂,透过一具具年轻的身体赤裸又神秘地显露着自身的意志。而从开工前的口号直到下班时的训话,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时间”。
“一路走来,我总觉得,拍片子还有做片子,还有看片子,看这些真实的影像,有时会找到一些对自己处境,包括自己心态的一些安慰……一直在努力去贴近更多人的生活,去跟更多的人接触,然后去获得一些爱和力量。可是我发现,现在,我很困惑,因为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在感受到一些爱和力量的同时,又能感觉到一些恶意和伤害。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里感受到的这些爱还有力量,在那一瞬间是很强大很温暖,可是在我心里停留的时间会很短暂,会变得很轻。而那些恶意和伤害,就会在我心里萦绕不去,挥不去。”
从后面的讲述中我们得知,阿涵这里提到的“恶意和伤害”,主要是指前一天去拍工友结婚时摄影机被抢的遭遇,以及拍摄回来路上一位女工开玩笑说的话,“我感觉你们像狗仔队一样,就是整天跟在别人后面拍来拍去”。直到这里,阿涵的整个语调都还显得比较平静。又或者说,尽管困惑于为什么“爱和力量”总是短暂且轻,而“恶意和伤害”萦绕不去,但拍摄过程中发生的这类挫折,毕竟是她能够面对和有所预料的。真正让阿涵情绪崩溃,失声痛哭的,是她“拍到现在,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快乐了”,而且,
“我好像更难去向一个具体的个体,一个人,去谈心,像过去那样,我向他讲述我心中一些特别压抑的东西,一些特别慌张、特别恐惧的感受。我讲不出来了。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困住了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阿涵没有补充说明自己曾经拍摄的纪录片都是以哪些人物作为对象,抑或是在处理什么样的主题,我们只知道她对纪录片的热情,是和一群同样喜欢电影的人,在小酒吧的沙龙里放映电影时被点燃的——但无疑,在导演安排下对工厂青年的拍摄和关注,让阿涵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某种与他人彼此交流时的困难和隔阂,甚至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而当她努力地寻找言说的对象、拼命地克服失语的焦虑时,她接着说道:“我现在跟我爸妈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有时候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镜头里的阿涵这时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和真正的孤独,她开始泣不成声:“我不知道该给谁说了,我觉得别人不理解我……”最终,她只感到无力,“康佳给我开绿灯开了好多,拍什么都行,可是这两天的拍摄让我觉得特别脆弱,让我觉得特别无力。我有时候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说不上来,我好难受……”
尽管这整段自白好几次被失声痛哭给打断,但从困惑到绝望到无力,阿涵的所有感受都是如此真实。对阿涵来说,那种“像被困住了一样”的孤独者的处境,无疑才是让她崩溃的真正原因。它来自于这样一个或许连她都还没有意识到的事实——阿涵无法内在地理解她镜头中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工厂青年们——阿涵不是没有理解他人的能力或意愿,但是,当她的理解对象这次不再能够仅从个体的层面加以把握,当她无法再用惯常的那套语言和生活经验与之交流,当她试图以这样的对象反观自身却发现自己不被认可的时候,她只能感到深深的困惑与隔阂。她本能地想向家人求助,却又知道父母在这里起不了任何作用,于是她彻彻底底“不知该给谁说了”。换言之,在无法理解眼前的对象和现实时,阿涵有意无意间,又将这一对象和现实屏蔽在了自己的视线之外。这就像是,她陷入了深谷,却又在四周竖立起无形的高墙,只会让自己更加绝望。现在唯一能够支撑她的,或许只有对于纪录片的热爱了吧。阿涵明白自己必须完成这部纪录片,关于纪录片的理想似乎还没有完全熄灭,但当难得的拍摄机会摆在面前,她好像仍在有意无意间,背转了身去,陷入到自责和脆弱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一幅孤立无援的青年肖像,于是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
综上可见,针对预防接种儿童,在接种疫苗、常规护理措施干预的同时,实施优质护理进行干预,可明显提高预防接种儿童的依从性,效果满意,故值得进一步推广。
这个孤独者是阿涵,同时也让我们回想起那个在宿舍独自听歌、心里难过委屈的年轻女工,或许还有我们自己。不妨说,是这种孤独的个体处境,构成了当代青年共同遭遇的深层困境。如何打破个人主义的迷思,如何让知识青年们走出由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所划定的自我认知的高墙,如何让工厂青年们拓展出更为丰富的文化想象和身份认同,如何让这样两个群体在共通的感觉结构和共同的现实困局中重新整合起来,便成了我们今天所有人的问题。也许,这些问题,暂时还没办法在阿涵们身上得到解答,但我们从中看到的“理想主义”的微光,哪怕是“理想主义的困惑”,却是珍贵的。因为,它能让我们在眼前消费主义的“流水线”和发展主义的“世界工厂”之外,依稀看见一些更有价值因而也更久远的东西,进而想象一些不一样的未来。
其二,上述界定没有揭示我国现行土地管制权最本质的内涵。毋庸置疑,概念是对一事物本质属性的揭示,“本质”代表了某一“概念”的核心部分,只有对“概念”之核心部分的“本质”有所了解,才能对其作出合理、妥当的界定。对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的科学界定亦同样离不开对这一权力本质的揭示。
参考文献 :
[1]郭春林.看见与再现——记录片《工厂青年》的意义[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3).
Plights and Outlets of Youth in “World Factory ”
Cai Bo
Abstract :Factory Youth (2016), a documentary directed by GUO Xizhi, focuses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workers in the current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observes the youth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y youth/educated youth, production/consumption, city/village and China/world in its four chapters: Factory, Youth, Hometown and Diary. Through the detailed presentation of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spiritual plight of contemporary yout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clarify that today’s factory youth not only bear the overloaded production labor in the factory workshops, but also place themselves in the re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dominant ideology. Educated youth and factory youth both face the same ideological structure while being separated by it at the same time. How to break the division and the myth of individualism and consumerism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hat we must rethink and face together today.
Keywords :Factory Youth;world factory;educated youth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947(2019)01-33-07
①[基金项目] 南京晓庄学院校级青年课题: 论 “新时期 ”中国电影的现代性与主体性问题 ,
项目编号: 2017NXY36。
②[作者简介] 蔡博,男,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新时期中国电影历史与美学、当代电影批评及文化研究。
(编辑: 邓 蕾)
标签:《工厂青年》论文; 世界工厂论文; 知识青年论文; 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