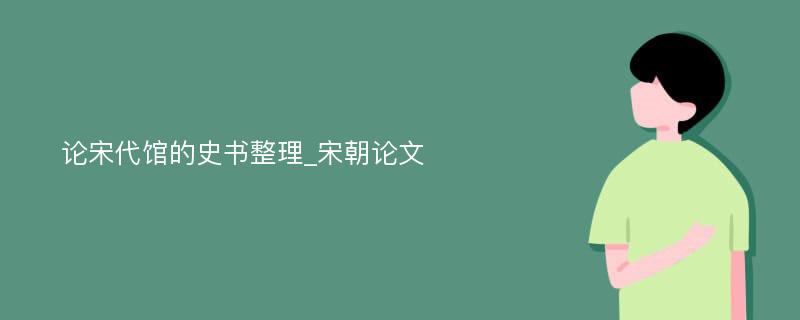
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书论文,论两宋馆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1)01-0056-10
近年来研究北宋官府校勘状况的论文已有数篇,研讨南宋馆阁校勘的则很少见,本文专门探究宋代史部书校勘方面的特色和成就。
本文所述之校勘活动,主要是朝廷中以校勘史书为主要目的的文献整理活动。两宋曾多次综校四部之书,其中当然也包括史书,然因其目的不是专门校史书,故本文不计算在内。
一
两宋馆阁校勘史书共计21次,其中北宋12次,南宋9次。
北宋校勘始于“前三史”:“太宗淳化五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崇文院检讨兼秘阁校理杜镐、秘阁校理舒雅、吴淑、直秘阁潘慎修校《史记》,朱昂再校;直昭文馆陈充、史馆检讨阮思道、直昭文馆尹少连、直史馆赵况、直集贤院赵安仁、直史馆孙何校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注:《宋会要辑稿·崇儒》(以下略作《崇儒》,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四之一。原文“阮思道”之“阮”作“院”,“孙何”之“何”缺,据《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12月版)卷四三改、补。又见《麟台故事》(以下略作《麟台》,上海涵芬楼影印之《四部丛刊续编》本)卷二。)这次校勘参加人数颇多,校后立即“镂板”。
第二次为真宗朝之复校《史记》:“咸平,真宗谓宰臣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未精,当再刊正。’乃命直史馆陈尧佐、周起、直集贤院孙仅、丁逊复校《史记》。寻而尧佐出知寿州,起任三司判官,又以直集贤院任随领之。”(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此次校勘,始于“咸平中”(注:《玉海》卷四三“淳化校三史”条下。又见《麟台》卷二。),至“景德元年正月丙午”(注:《玉海》卷四三“淳化校三史”条下。又见《麟台》卷二。)“校毕”,(注:《崇儒》四之一。)“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并刊误文字五卷,赐帛(注:《麟台》卷二。)”。这次校勘是由真宗亲自发起的,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将“刊误文字”另编为五卷上进。
第三次是校《三国志》等:“咸平三年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以直秘阁黄夷简、钱惟演、直史馆刘蒙叟、崇文院检讨直秘阁杜镐、直集贤院宋皋、秘阁校理戚纶校《三国志》,又命镐、纶与史馆检讨董元亨、直史馆刘锴详校。直昭文馆许衮、陈充校《晋书》,黄夷简续预焉,而镐、纶、锴详校如前。”(注:《崇儒》四之二。又见《玉海》卷四三、《麟台》卷二、《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版《四库全书》,前言为1987年8月)卷五六。)“直昭文馆安德裕、……勾中正、……直集贤院范贻永、……直史馆王希逸洎董元亨、刘锴同校勘《唐书》,宫苑使刘承圭领其事,内侍刘崇超同之。五年,校毕,送国子监镂板。校勘官赐银帛有差,锴特赐绯鱼袋。”(注:《麟台》卷二。)这次校勘,仅上述所记之参加者已有十数人,历时一年有余,且校后立即“镂板”,“惟《唐书》以浅谬疏略,且将命官别修,故不令刊板。”(注:《崇儒》四之二。又见《玉海》卷四三、《麟台》卷二、《长编》卷五六。)此处之《唐书》,显然是指后晋刘昫等所撰之《旧唐书》。
第四次在景德元年:“(正月)丁未,命刁衍、晁迥、丁逊复校前、后《汉书》。”(注:《玉海》卷四三。)至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汉书》历代名贤竞为注释,其得失相参,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错。除无可考据外,博访群书,遍观诸本校定。”(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刁衍所言之“博访群书”“校定”,当是陈垣先生四校法中的“他核”,而“遍观诸本核定”显然是“对校”了。此次校勘历时一年半。其结果为:“(校正文字)凡三百四十九签,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即赐器币有差。”(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仅在两部史书中便校正了三千余字,可谓效果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校勘亦将校勘结果集结成册“以进”。
第五次为校《后汉书》中的志书:“乾兴元年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言:‘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乞令校勘,雕印颁行。’从之。命本监直讲马龟符、王式、贾昌朝、黄鉴、张维翰、公孙觉、崇文院检讨王宗道为校勘,奭洎龙图阁直学士冯元详校。天圣二年,送本监镂版。”(注:《崇儒》四之五,四之六。其中刘昭《补注后汉志》原作《注补……》,据《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下同)卷二○三《艺文志》改。)
《后汉志》仅三十卷,校勘时参加者至少九人,且分校勘、详校两个步骤,又费时一年有余,可见亦是一次相当认真的校勘。
第六次为校《天和殿御览》:“仁宗尝谓辅臣曰:‘《天和殿御览》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注:《玉海》卷五四。)《天和殿御览》是《册府元龟》之精华:“乾兴初……于《册府元龟》中掇其善美事,得其要者四十卷……名曰《天和殿御览》。”(注:《玉海》卷五四。)至“天圣二年五月甲寅,内出《天和殿御览》四十卷……下秘阁镂板。”(注:《玉海》卷五四。)
《册府元龟》本为类书,但“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注:《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65年6月版,下同)卷一三五。),其原名为《历代君臣事迹》,显然偏重于史;此次摘录为《天和殿御览》,仁宗也将它视为史书(注:《玉海》卷五四。),因此本文将它归入史书类。且《册府元龟》“引书近二千多种”(注:见刘乃和:《〈册府元龟〉新探·序》,中州书画社1983年4月版。),因而此次“校定”当以他校为主,而非止简单的校对。本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为:发起者是仁宗;所校为当代之书。
第七次是校《南、北史》、《隋书》:“仁宗天圣二年六月,诏直史馆张观、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悫、李淑、秘阁校理陈诂、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勘《南、北史》、《隋书》,及令知制诰宋绶、龙图阁待制刘烨提举之……又奏国子监直讲黄鉴预其事。”(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仅此处所载,参与者就已达十人之多。至“(天圣)三年十月,(《隋书》)版成。四年十二月,《南、北史》校毕以献。各赐器币有差。”(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
仁宗以前,已校勘了正史中的前四史、《晋书》、《唐书》等,本次校勘,显然是校勘正史的继续。其中《南、北史》后又复校之:“景祐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注:《玉海》卷四三。)
第八次为复校:“(景祐元年)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注:《玉海》卷四三。)。其中较为突出者是校《汉书》:“会秘书丞余靖进言:‘《前汉书》官本谬误,请行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注:《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宋史·艺文志》中亦明载:“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参加者还有:“详定官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注:《麟台》卷二。又见《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
这次校勘,对《汉书》已至少是第三次复校了,结果又校出三十卷刊误文字。对一部史书,在约四十年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雠校,且校正文字达三十余卷,这在我国两千余年校勘史上亦不多见。而至“神宗熙宁二年八月六日,参知政事赵抃进新校《汉书》印本五十册,及陈绎所著《是正文字》七卷。”(注:《崇儒》四之十。)即又校出不少错谬,由此亦可见校勘工作是何等艰辛。
第九次校《国语》则是与校子书同时进行的:“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言:‘……《国语》、《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注:《崇儒》四之七。)本次校勘是为考试出题之需。
第十次为“嘉祐校七史”:“六年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全者访求之。”(注:《玉海》卷四三。)至“嘉祐七年十二月,诏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国子监镂板颁行。”(注:《玉海》卷四三。又见《崇儒》四之十九。)其中《陈书》稍迟:“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注:《元丰类稿》(引自《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卷十一《陈书目录序》。《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载:嘉祐所校七史,“政和中始皆毕。”此说与《元丰类稿》卷十一、《玉海》卷四三、卷五二所载皆异,恐误,本文不取。)
本次校勘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为校勘而搜求书籍,从《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元丰类稿》卷十一等书中可看出:当时为校勘而求书,时间上长达一年多,范围远及州县。
第十一次为校《后汉书》:“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字皆作‘恳’字,使侍中传诏中书,使刊正之。(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为一书云。”(注:《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著录有:“《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右……刘攽所撰也。”《宋史》中亦载:“(刘)攽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注:《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此《刊误》进呈时间为:“治平三年四月……刘攽上。”(注:宋版《东汉刊误》卷一,转引自曾贻芬:《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这次校勘的发起者又是仁宗。
第十二次为校《资治通鉴》:“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重行校定。”(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书后之《奖谕诏书》。)《资治通鉴进书表》标明进呈时间为“元丰七年十一月”,即成书后不到一年就进行“校定”。后至“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十九日,宰臣司马光言:‘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欲令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并从之。”(注:《崇儒》四之十。)《通鉴》引书数百种,此处之“校定”,当是以他校为主。而《通鉴》付梓的时间为:“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注:《资治通鉴》书后之《奖谕诏书》。)由此可见,本次校勘的目的就是为刻印之需。
由编纂者亲自上书、要求校定刚刚编纂之书,这在我国校勘史上颇为罕见。
对史书的校勘在南宋仍占有重要地位,达9次之多。
第一次始于绍兴元年:“七月七日,监行在都进奏院章效上欧阳修纂《太常因革礼》一百……仍令秘书省逐旋借本校勘、抄录,藏于本省。”(注:《崇儒》五之三○。这段史料中,“令秘书省”前之“仍”字颇耐人寻味:似表示在这次校勘之前已有先例。然笔者迄今尚未发现此前有南宋馆阁校勘的记载,尚待来日。)此书书名为英宗所赐。(注:《四库全书总目》书后之附录。)本次校勘后仅为“抄录”,而未镂板。
第二次始于绍兴三年:“七月六日,秘书少监曾统等言:‘伏闻前任本省官洪楫有《神宗皇帝朱墨本实录》、神宗、哲宗《两朝国史》、《哲宗实录》、国朝典章故事文字,望取索名件,官给纸札,借本缮写各一部,仍选差官校对,赴本省收藏。’从之。”(注:《崇儒》四之二三。)至“七月十三日,诏:‘昨曾统所进《神宗皇帝实录》……仍专令胡珵、李弥正等校勘。’”(注:《崇儒》四之十三。这段史料在“七月”前尚有“七月”二字,然未载是何年。但诏中有“昨曾统所进《神宗皇帝实录》……”,可见此诏距曾统进《神宗实录》之日甚近,因此本文将其附于曾统上言之后。)
此处所言之“朱墨本实录”,《玉海》中载之颇详:“(范)冲言《神宗实录》自绍圣中已命官重修,既经删改,虑他日无所质证,今为考异,追记绍圣重修本末——朱字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世号‘朱墨史’。)”(注:《玉海》卷四八。括号中原文为小字。)
这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为:神、哲实录后又重修,其中《神录》成于绍兴“六年正月癸未”,“凡二百卷”;《哲录》成于绍兴“八年……九月甲午”,共“一百五十卷,先后进呈。”(注:《玉海》卷四八。)
第三次在绍兴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起居舍人王鉌言:‘窃见《国朝会要》……比经兵火之余,公私所藏类皆散逸,深虑岁月既久,渐成湮坠。望诏秘书省,令访求善本,精加雠校。’从之。”(注:《崇儒》四之二五。)下诏则在九月:“四日,诏秘书省官雠校《国朝会要》,逐官每月添给茶汤钱二十贯文。”(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二七。)
此处之《国朝会要》,显为北宋所修者。北宋年间曾三次纂会要,即仁宗朝所修之《庆历国朝会要》150卷、神宗朝“元丰增修”之会要300卷(注:《玉海》卷五一。)和“政和末,有司独上帝系、后妃、吉礼三类,总一百一十卷”。(注:《通考》卷二○一。)其中后两种会要于绍兴元年、三年分别有人上进(注:《崇儒》四之二一、二三。),可能即为本次所校者。
以上三次,所校皆为北宋官修史书,且皆在绍兴年间。
第四次为校《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略作《长编》),李焘之《进书表》中明确记载:“臣先于去年(指乾道三年)八月……奉圣旨依敷文阁直学士汪应辰奏,取臣所著《续资治通鉴》,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缮写校勘,藏之秘阁……”(注:《四库》本《长编》前之李焘《进书表》,又见《崇儒》四之十四、五之三七。)《长编》最终成书在淳熙十年三月六日(注:《玉海》卷四七。),即在上述校勘之十五年后。
本次校勘与撰写穿插进行,这显然与《长编》本身卷帙浩繁有关,故不待完书便进行校勘。焘之《长编》引书甚众,因而此次校勘当以他校为主。
乾道五年,又对《徽宗实录》进行整理:“(李)焘又言:‘……近所修《徽宗实录》……疏舛特甚……乞……将《徽宗实录》重加(刑)[删]修,……仔细看详,是则存之,非则去之,阙则补之,误则改之……”。(注:《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五,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藏本。)
此处李焘所言之《徽宗实录》,为“绍兴七年诏修,八年秋即史馆开实录院”,后“(逾二十年乃成)。”而此书虽“(再加增润)”,但仍“(犹多疏略)”(注:《玉海》卷四八。括号中原文为小字。),此次“重加删修”中之“阙则补之,误则改之”,显然属于校勘范畴。更为重要的是:乾道七年校勘北宋实录时,不再校勘《徽宗实录》,故而本文将其计为一次校勘。
第六次为校六朝实录:“(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秘书省修写太祖、太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皇帝实录,精加雠校,逐旋进呈。”(注:《崇儒》四之十四。)
本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在于:雠校前搜求到不少相关资料,如绍兴元年“九月十三日,将仕郎黄濛上《太祖皇帝(五)[实]录》五十卷,《太宗皇帝实录》八十卷,《真宗皇帝实录》一百五十卷,《仁宗皇帝实录》二百卷,《英宗皇帝实录》三十卷,《天圣南郊卤簿册记》一十册”(注:《崇儒》四之二一。);绍兴三年“五月一日,承奉郎林俨上家藏……祖宗实录、国朝会要、国史等,及古文文籍二千一百二十二卷”(注:《崇儒》四之二三。),等等。在上述这些官方、私家所藏丰富文献基础之上所进行的校勘,称之为“精加雠校”,自非虚言了。
第七次为刊正《宁宗玉牒》:“嘉泰四年八月九日进,五十卷。嘉定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刊正辩诬之书上之。”(注:《玉海》卷五一。)而《宁宗玉牒》的最终完成则在淳祐二年(注:《玉海》卷五一。又见《宋史》卷四二《宋理宗本纪》。),即约29年之后。可见本次校勘亦穿插于纂修过程之中,并产生“刊正辩诬”的专书。
最后两次均在理宗朝:“(孝宗)淳熙三年,秘书监李焘编次成(《太上日历》)一千卷”,“淳祐八年,秘书省校雠缮写上之。”(注:《玉海》卷四七。又见《宋史》卷四三《宋理宗本纪》。)另一次为《孝宗日历》:“(光宗)绍熙元年八月戊戌进《日历》二千卷,……淳祐十一年,秘省校雠补写上之。”(注:《玉海》卷四七。)这两次所校皆为前朝之日历,均亡佚已久。史书中虽未载参加校勘的人员,然从数量上看,两次校勘达三千卷之多,亦可见其规模。
二
对两宋馆阁校勘史书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便可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
首先,从校勘的次数上看,北宋九朝校书之总次数近60次,而史部为12次,约占五分之一;南宋共校书18次,却有9次为史书,占二分之一,故其比重大为增加。
然若将两朝校史书的次数与年数相比照,则北宋167年中,平均约14年校史书一次;而南宋的152年中,约17年才校一次。因此从校勘的密度上看,北宋仍略胜南宋一筹。而南宋校史书比重的增大,不是因校史书的绝对数值增加,而只是因对其它部类书籍校勘次数的减少而显得突出了。
再观察一下各朝的状况。为观察之便,特列表如下:
北宋各朝:
太祖
0次
仁宗
7次
哲宗
1次
太宗
1次
英宗
0次
徽宗
0次
真宗
3次
神宗
0次
钦宗
0次
南宋各朝:
高宗
3次
光宗
0次
理宗
2次
孝宗
3次
宁宗
1次
度宗
0次
从上表中可明显看出:北宋之校史书,高度集中于真、仁两朝,特别是仁宗一朝的次数,超过了其余八朝的总和(其原因见下文)。南宋则相对集中于高、孝、理宗三朝。除这三朝本身的跨度较大以外,高孝两朝恰是封建史家誉为“中兴”的时期;理宗朝也是南宋政局相对稳定的阶段。
其次,从所校史书的体裁看,北宋的12次中,9次为正史,即纪传体;其余三次,分属编年体和杂史,合计仅三种史体。而当时史部书的门类已颇多,如《新唐书·艺文志》的史部中,就有故事、职官、地理等十三大类。
北宋校史书范围的狭窄,鲜明体现出“资治”的色彩:正史本身就是“以帝王本纪为纲”的史书(注:《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版)“正史”条下。),记录着每个王朝的盛衰荣辱,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其它三次中,校《国语》是为考试出题之需,可不论;其余两部则都有明确的资治目的:《资治通鉴》自不必赘言,《天和殿御览》亦如是——仁宗摘编此书的目的,就是为“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监[鉴]戒。”(注:《玉海》卷五四。)
南宋所校史书中,国史为纪传体,《长编》、日历、实录皆属编年体,玉牒为官修的“帝王族谱”,“以编年体叙帝系而记其历数。”(注:《辞源》“玉牒”条下。)会要和《太常因革礼》则为典志体,合计亦为三种史体。因此从校勘史书的范围上讲,南宋与北宋难分伯仲。而南宋所校之官修史书,皆为后世纂修正史的取材之所,因此他们的校勘,恰是为后世正史之修奠定基础,可见其校史书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资治”。
第三,从校勘对象的重要性观察,北宋的12次中,有9次是校正史。正史是封建社会史籍中最重要的一种体裁,今天一提到中国史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二十四史。所校其它书中的《资治通鉴》,又是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自《春秋》、三传之后,我国的编年体史书一直处于低潮;而《通鉴》问世后,编年体大兴,继踵者不绝如缕,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资治通鉴》、《明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等;我国的三大史体之一——纪事本末体,也由此而诞生;注释、研究《通鉴》之书亦层出不穷,乃至后世形成了专门之学——通鉴学。因此可以说,北宋所校史书,大多为当时最重要的史籍。
南宋校史虽亦有9次,然多为实录、会要、日历等,对成于北宋的三部正史——旧、新《五代史》、《新唐书》却未予刊正,所以其重要性自与北宋所校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是校当代之书。北宋仁宗乾兴年间所摘编之《天和殿御览》,至天圣二年就已校毕镂板;对《资治通鉴》的校勘距进呈时间还不到一年。南宋对《太上日历》、《孝宗日历》的校勘亦与成书上进的时间相去不远,与北宋情况相仿;而南宋在这方面又有发展——修书未毕便进行校勘,如李焘的《长编》和其后的《宁宗玉牒》皆属此种情况。这也是宋代校勘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
第五是校勘的计划性。北宋校正史表现出很强的计划性:第一次即校前三史,第三次为《三国志》、《晋书》、《唐书》,第七次校《南、北史》、《隋书》,第十次为南北朝之“七史”,其余几次复校穿插其中。从而在数十年内,系统校勘了成于北宋之前的全部十六史。
而南宋的情况却显得颇为凌乱:从实录方面看,第二次所校为神宗、哲宗实录,第五次为徽宗实录,第六次才校太祖、太宗等六朝的,而真宗朝的却始终未校;以国史论,仅校神、哲两朝,而未及其它;就日历而言,北宋已有日历,却从南宋高宗校起;从玉牒看,更是仅校宁宗一朝。因此,南宋之校史书可谓是毫无计划性。
特别要指出的是《神宗实录》等不断重修,已经不是“校勘”所能概括的,它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的政治斗争的反映。
第六,在将校勘成果汇编成书方面,两宋亦相差甚远。从上文不难看出,北宋校史书12次,汇编校记的就有4次,即:第二次复校《史记》时,产生“刊误文字五卷”;第四次复校前、后《汉书》时,将校正的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第八次复校前四史之后,余靖“上《汉书刊误》三十卷”;第十一次复校《后汉书》时,又产生《东汉刊误》一卷。
而南宋的9次中,仅在校《宁宗玉牒》时,产生“刊正辩诬之书”(其中之“辩诬”还可能不是校勘,而是对历史事实的纠谬)。
北宋的4次校记汇编,皆产生于复校之时,其原因何在?
《宋会要辑稿》中,在上文第四次刊正前、后《汉书》之后,有一句很容易被忽略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答疑的线索:“今之行者,止是淳化中定本。后虽再校,既已刻板,刊改殊少。”(注:《崇儒》四之一。)就是说:因前、后《汉书》已刻板,所以这次复校的结果,只有“殊少”的一小部分能反映在书板上。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将校勘结果集结为专书,则绝大部分成果都很难保存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就无法向皇帝汇报校勘的全部成果,因此很有必要将所校正的文字汇编成册。其余三次亦如是。可见,校勘记专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而南宋馆阁鲜有复校,故而没有必要将校勘成果编为专书。
而如果刊正的字数非常之多时,即便是集结成册之后,仍要在书板上改正,这就是第八次的情况:“……(余靖)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版,以从新校。”(注:《麟台》卷二。)
第七,在史书的复校方面,南宋远不及北宋。北宋馆阁除上述的四次复校外,在第七次校《南、北史》之后,于景祐年间又复校之。即在全部12次校勘中,有5次复校。而南宋的9次校史书,仅第二次所校众多史籍中的《神宗实录》,于乾道七年又随其它5种实录复校之。这种状况充分反映出南宋的校勘远不及北宋那样从容不迫,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复校。
第八为刻印情况,在这方面两宋相差亦很悬殊。北宋的12次中,校后立即“镂板”、“刊行”的有第一、三、五、六、七、九、十、十二共8次,而未刻板的4次均为复校,即校勘已刻印之书。实际上,北宋的多次校勘,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刻印。
南宋的9次校勘之后,却无一次提及“镂板”,仅为“缮写”、“抄录”而已。这主要是因为:日历、实录、会要等官修史书,大多具有官方档案的性质,日历甚至为机密档案,“在一定时期内,除编修官以外,其他人不能阅看。”(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六章。)而且这些官修史书的卷帙多颇浩繁,如北宋所修三次会要,就有五百余卷;而高、孝两朝日历,更多达三千卷,因此这类官修史书在北宋时就未付梓,南宋则沿袭其例。
上述八个方面之中,所校史书的重要性、校勘的计划性、将校勘成果汇编成书、复校的次数及刻印情况等五个方面充分说明:北宋的史书校勘远胜于南宋。究其原因,主要是北宋政局较为稳定,经济高度发展,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情况下,政府才有可能在校勘史书方面投入大量精力、物力。特别是真宗、仁宗两朝,国泰民安,君臣于治理国家之余,尚可追思历史,取鉴前朝,正如仁宗所言:“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鉴戒。”(注:《玉海》卷五四。)宋代21次校史书中,仅有3次是由皇帝亲自发动的,而3次均在真、仁二朝,这充分表明当时帝王对校勘事业直接关注的程度。在这些条件下,北宋之校史书才会高度集中于真、仁二朝。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宋仅残存半壁河山,金朝、蒙古大军时时压境,又怎么可能花费很多精力去校勘史书呢?绍兴十四年的一段君臣对话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上曰:‘崇儒尚文,治世急务。’李文会曰:‘若非干戈偃息,此事亦未是举也。’”(注:《崇儒》四之二七。)故而南宋君臣也只有在“干戈偃息”的间隙中才能去“崇儒尚文”。
三
纵观宋以前千余年官府校勘的历史,自刘向、歆父子雠校群书后,历代多为对四部书的综合校理,如东汉安帝时“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卷八○《刘珍传》。);西晋武帝时校理著名的汲冢竹书(注:《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卷五一《束皙传》,卷三九《荀勖传》。);刘宋年间谢灵运“整理秘阁书”(注:《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卷六七《谢灵运传》。);北齐宣武帝命樊逊等校定群书(注:《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版)卷四五《樊逊传》。)。至唐代,仅《玉海》(卷四三)所载,综校四部之书就已达5次。历代亦曾多次校定经书,如镌刻熹平石经、正始石经、晋石经、开成石经、后蜀石经之前,即多有刊正。然而在校史书方面,前代却甚少建树。
我国在汉代已出现了专门整理史书的活动,如“永平十五年……(马严)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但史书在汉代尚未成为独立部类(详见下文),因此雠校史书的次数自不会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统治者亦无暇经常校正史书。至唐代,史学高度发展,“唐修八史”等成就为宋代校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在史书校勘方面,唐代也仅是偶尔为之,如“太和五年,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奏曰:‘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注:《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卷六四。)这次校勘的起因是:韩愈所作的《顺宗实录》直书禁中之事,结果“内官恶之,于上前屡言不实,故令刊正也。”(注:《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卷六四。)
综合前文所述,宋代馆阁之校勘史书,至少在如下五方面超越前代:
一为校史书的频率。两宋合计319年,共校史书21次,平均约15年一次。这种频率实为前代所无。
二为北宋校理史书的高度计划性,也是前所未见的。北宋校正史始于太宗淳化五年,终于仁宗嘉祐八年,仅历时69年、主要经四次校勘即毕其功。隋以前尚少有专门校史书的活动,所以根本谈不到计划性。唐以前已修成7种正史,然唐代并未有计划地刊正之。
三是将校勘成果汇编成专书的作法,两宋共有5次,而宋以前却从未出现过。对此已有论述,本文不赘。(注:见拙作《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刊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
四是对史书的复校。两宋复校共达6次,而宋以前对经书有过复校,却罕见复校史书者。
五为刻印情况。北宋校史书后立即镂板刊行者达8次之多,亦远胜前代。
宋代校史书盛况空前,其原因除上述之“国泰民安”外,尚有如下三点:
其一,史部书自身的发展是宋代史书校勘成就辉煌之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我国自先秦至西汉前期,史书的门类、数量皆远不及经、子之书,因此至东汉班固修《汉书·艺文志》时,仍沿《七略》之例,不立史部。自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史书大兴,故而至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首将史书独辟一部,然尚在经部、子部之后。至东晋李充之《晋元帝四部书目》,史部才位列第二。隋唐时期,史部书继续发展,成为拥有十三部类的泱泱大国;宋以前的十六部正史中,有八部纂修于唐代——这一切都为宋代的史书校勘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推动宋代校勘事业空前发展的最直接原因是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唐以前印刷术尚未问世,因而宋以前之多次校雠皆无条件付梓,至多不过是将经书镌于石上,供人传抄而已。至唐代,印刷术虽已发明,然尚未普遍运用。五代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为宋代的刻书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宋代已具备了大量刊印书籍的各种条件,而镂板之前自然希望尽量减少书籍中的错讹之处,由是校勘事业大为兴盛。
其三是“会通”思潮的影响。我国史学至唐宋年间空前发展,史家已不满足于断代为史,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纵观上下几千年的变化——唐中叶《通典》问世,北宋年间《资治通鉴》付梓,南宋期间《通志》诞生,宋末元初《通考》修纂——这四部巨著皆“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能同天下之文”,“能极古今之变”(注:《通志·总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它们生动反映出唐宋时期“大矣哉”的“会通”思潮。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初年编纂的“四大部书”,即《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与《册府元龟》(总计达三千五百卷),同样是“包括群书,指掌千古”(注:宋太宗为《太平御览》所下之诏,见《玉海》卷五四。)的会通之作。四部书中前三部均修于太宗朝,《册府元龟》纂于真宗朝;而宋代之校正史,恰始于太宗朝,而终于仁宗朝。由此可见,正是在当时编纂会通巨帙蔚然成风的氛围之中,北宋馆阁校勘了全部正史,从而在校勘史书的领域里,成就了空前的会通之作。
[收稿日期]2000-06-12
标签:宋朝论文; 北宋皇帝论文; 郡斋读书志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书籍论文; 读书论文; 史记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册府元龟论文; 南宋论文; 汉书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西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