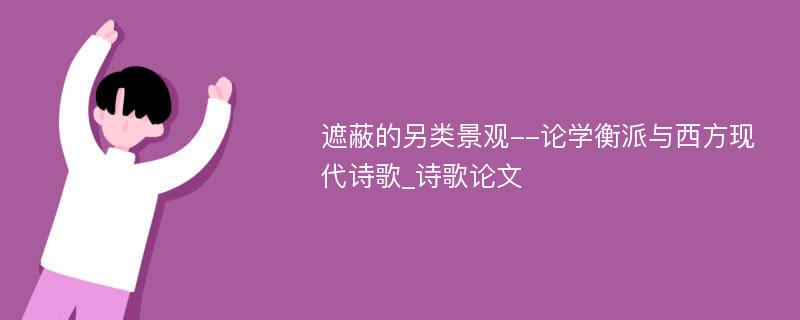
被遮蔽的另面景观——论学衡派与西方现代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观论文,现代诗歌论文,论学衡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3)04-0025-06
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学衡派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人们一改 过去将它置为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视为封建复古反动势力的立场和看法,由批判否定 转向分析肯定,甚至不乏理想化的提升和倾诉。其实问题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学衡派具有保守主义的特征,但还有一些其它文化选择和诉求。学衡派对新诗的批评, 是与五四新文化派论争交锋的火力点,而学衡派的批评,常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特别 是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相联系。学衡派对同为西方现代诗歌的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 ,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对前者拒斥、否定,对后者接受、肯定。本文试图在清理学衡 派诗歌观的基础上,重新检讨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探讨和分析学衡派过去一直 为人们所忽视和遮蔽的另面独特文学景观。
一
意象派是本世纪初一些英美青年诗人因不满维多利亚诗风而兴起的诗歌流派。这个时 期控制英美诗坛的诗歌逃避现实,冗长散漫,充满耳提面命式的说教气味和无病呻吟的 感伤情调。意象派强调诗人捕捉、创造意象,要求以意象客观呈现个人的瞬间感受,主 张诗歌凝练明确、硬朗清新,创造新韵律,以平易明白的口语写自由体诗。这不仅给当 时泛情滥理,矫揉造作的诗坛吹进了一股清风,而且为英美诗歌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路 径。这股诗风亦吹到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意象派的影响主要不在诗艺和意象创 新方面,而在于创造新韵律,以平易口语写自由体诗的主张和反传统精神。胡适留美期 间曾关注意象主义运动,特意将《纽约时报》书评版的“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剪贴 在自己的留学日记上,并认为“此派所主张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1]。胡适的《文学 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主张,受到意象派理论启发。《谈新诗》则引用意象派宣言, 提出写“具体性”、“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形式自由的新诗。余冠英曾指出“胡 先生提倡新文学运动的时候,本以清楚明白、能懂为文学的标准之一。他的文学主张是 很受印象派影响,朦胧本是印象派所不取的”[2]。胡适的新诗创作也受到意象派的影 响。文学革命和初期白话诗创作与西方意象派存在事实关系。
学衡派对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主张受到意象派影响这一点早有洞察。美国留学期间, 在讨论诗歌革命时,梅光迪就提示胡适“若以为Imagist poetry(意象派诗歌,笔者注) 及各种美术上新潮流,以其新出必能胜过古人,或与之敌,则稍治美术、文学者,闻之 必哑然失笑也。”[3]梅光迪显然鄙视美国时兴的自由诗和意象主义运动,将之斥为颓 废堕落文艺。在绮色佳与胡适论辩时,他认为胡适被欧美“新潮流”所感,尝试白话诗 ,误入歧途。梅光迪认为白话诗“只为诗之一种”,并且“非诗之正规,此等诗人断不 能为上乘”。他说:“今之Vers Liber(自由诗,笔者注)有康布利基女诗人Amy Lowell (即艾米罗威尔,意象派主将,笔者注)为之雄,其源肇于法,亦Decadents(颓废派,笔 者注)之一种。一般浅识之报章,多录其诗,为之输扬。然其诗非诗也。”[3](P144~1 45)但胡适不听梅光迪的“最后忠告”,一意孤行。他不仅倡导文学革命运动,而且身 体力行,发表第一部个人新诗集《尝试集》。梅光迪在《学衡》撰文批评新文学运动倡 导者非创造家乃模仿家,指摘新文学运动者“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特别强调 “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Verse Libre)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imagism)之余唾。 ”[4]这是他在美国与胡适讨论文学革命败北后的一次公开强劲反击。吴宓则从诗学理 论上批评意象诗派。吴宓认为,凡艺术各有其专用之媒质(medium),“不可以此美术之 媒质强用之于彼媒质”,否则“乱其畛域而灭其本质”。诗的本质是文字,而“形象派 imagists以作画之法作诗”,故“谬误百出,尤不宜效其法也”[5]。暴露白话诗麒麟 下的马脚,撩起新文学运动倡导者“数典忘祖”、“拾洋人余唾”这条不光彩的尾巴以 现其丑,是学衡派论战的刹手锏。
胡先骕的《评尝试集》一文更有代表性。这篇文章长达29页,2万多字,在《学 衡》第1、2期连载。该文首次引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用于中国文学批评。胡先骕拿 胡适的白话诗和中国古典诗歌及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诗歌作分析比较,很有说服力地论定 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新诗实在是糟粕。而胡适新诗尝试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拾西方意象主 义余唾。胡先骕批评意象主义是浪漫主义萎靡不振的末流,说它的最大的劣点是 “不能以物质表现精神,但窃取精神之外貌以粉饰物质”;前期英国浪漫主义有“高格 ”,“实为诗中之要素”,后期演变成意象主义则全是“下品”,“但求感官之快乐, 不求精神之骞举”。他将19世纪初英国浪漫诗派和意象派对比,认为华滋华斯的《水仙 吟》和《致杜鹃》“不但曲状自然界之美,且深解人生之意义”,指出:
同为咏物之作,然寄托之遥远,又岂印像派诗人Richard Aldington所作之The poplar 所能比拟。同一言情爱也,白朗宁夫人之Sonnets from portugese乃纯洁高尚若冰雪, 至D·H Lawrence之Fircflies in the corn则近似男女戏谑之辞矣。夫悼亡悲逝,诗人 最易见好之题目也,然Amy Lowell之Paterns何如丁尼逊之Home they brought her warrior dead与波Edgar Allan poe之The raven,而D·H Lawrence之A woman and her dead husband则品格尤为卑下。(注:胡先骕这篇长文,论及美国意象派和新诗 运动之诗人诗作,皆只提英文,不用中文译出。也许他认为,一文不值,尽写劣诗的意 象派根本不配享受中文译出这种礼遇。胡文此处论及意象派诗人诗作分别是:阿尔丁顿 Richad Aldington的《白杨》poplar,劳伦斯DH Lawrenc的《玉米中的萤》fireflies in the corn、《女人和她的亡夫》woman and her dead husband,罗威尔Amy Lowell 的《花样》patterns。)
胡先骕批评贬斥意象派,锋芒逼向白话新诗。他抨击“窃取精神之外貌以粉饰物 质”的艺术观时指出:“在欧美则有印象主义(imagism),在中国则近日报章所刊登模 仿塔果儿(A·Tagore)之作,与胡适君尝试集中‘蔚蓝的天’之诗,皆此类也。”这种 一箭双雕、一鞭抽二羊的技法运用得颇为娴熟、频繁。譬如他批评“不问事物之美恶尽 以入诗”的流弊时说:“在欧美有Edar Lee masters所著spoon river anthology与
Carl Sandberg之Chicago poems等劣诗,在中国则有胡君之‘权威’,‘你莫忘记’, 沈尹默‘鸽子’,陈独秀‘相隔一层纸’等劣诗。”(注:此处论及诗人诗作为:马斯 特斯Edar Lee Masters的《匙河诗选》spoon river anthology,桑德堡Carl Sandberg 的《芝加哥诗抄》Chicago poems。另外,《相隔一层纸》作者应为刘半农,胡先骕误为陈独秀。)胡先骕指摘意象派品格卑下,批评胡适的诗“卤莽灭裂”,“必 死必朽”,认定“《尝试集》之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胡适的新诗模仿颓废派,走的 是绝路,这使“入迷途少年,或能憬悟主张偏激之非而知中道之可贵,洞悉溃决于一切 法度之学说之谬妄,而知韵文自有其天然之规律”。
学衡派对意象派和五四白话新诗的批评,显示了他们的古典审美立场。这种诗学视点 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痕迹,更融入文化追求和生命体验。学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 、胡先骕等留学美国,做过白壁德(Irving Babbitt)的门徒,接受白氏新人文主 义理论。新人文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场亘古未有的浩劫 造成西方世界整体性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传统信仰、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丧失。新 人文主义试图通过复活一种以孔子和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代人文精神、重建一种“人的 法则”来解救危机,那就是用自己的理性来对个人的冲动和欲望加以“内在的控制”。 白壁德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新文化运动新旧之争,对“完全抛弃中国古昔之经籍, 而趋向欧西极端卢骚派之作者”表示警惕,指出“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 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6]在文艺思想上,白壁德追求、捍卫一种和谐 的古典审美理想,推崇、倡导理性原则,注重文艺作品的伦理道德意义。白壁德文艺批 评的最基本努力就是批判古典主义以降的西方近现代文艺。当时,英美意象主义运动正 兴始发展。但大胆反传统、勇于创新的意象主义运动,只是为青年人接受,距离普遍性 承认还很远。学院派批评家大多鄙视在野的意象派,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更是把它视作邪 派、异端。留美的学衡诸子鼻孔出的是洋师爷的气,加上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自 然对意象派“傲慢无礼”。更要命的是,中国五四新诗运动“使固有的文化受无妄之攻 击”,且误入歧途,模仿效法西方的堕落派,这是学衡派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集中 火力攻击意象派这个“双重”敌人。学衡派的批评抓住文学革命倡导者们的“根基”和 “要害”,以致胡适一直不敢承认受意象派的影响。在《尝试集》自序中他甚至否认, 说“我所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并没有 关系。”当时,美国新诗人,如意象派的庞德(Ezra pound)、罗威尔等的地位和价值还 没有被肯定,学院派批评家多将他们挡在大学门外,胡适因此不能借他们来支撑门面。 于是,他看风转舵,企图以历史眼光来寻找文学改良的藉口和理由。新加坡南洋大学王 润华注意到胡适的“不承认”问题,认为这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运动的“聪明策略”[7 ]。
二
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先河和渊源,具有世界意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由传统向 现代转型过程当中,象征主义是现代汉语诗歌接受西方多元影响格局中重要的一员。象 征主义对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追求和现代诗学建构产生深远影响。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象 征主义就被大量引介到中国,《新青年》、《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小说月报 》等发表不少评介文章和诗歌译作。周作人、沈尹默、鲁迅等创作出被当时的评论界视 为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作品,显示了新文学的新气象。1925年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出 版,标志着中国象征诗派诞生。而信奉新人文主义审美原则、对新文学持批评态度的学 衡派,也对象征主义表示兴趣和关注,在接受和译介象征主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虽然 象征主义和意象主义在审美方式和表现方法上存在区别,但二者的反传统精神和现代性 特征是相近的,意象派兴起时还不可避免受到当时执西方诗坛牛耳的象征主义影响。不 象对意象派一味贬斥和否定,学衡派对象征主义倾注了热情和理性分析。
1916年梅光迪和胡适在美国讨论新诗问题、表示对“新潮流”怀疑时,就提及象征主 义,称“法之Verlaine,Bardelaire(即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仑、波德莱尔,笔者注) 为颓废派”,并认为美国的新诗运动和意象主义“其源肇于法”[3](P144~145)。这是 学衡派较早对象征主义的论述。但这种“怀疑”态度后来转变为“关心”。1925年9月 《学衡》第45期发表顾谦吉翻译的美国诗人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诗《鹏鸟吟 》(The Raven)。此诗胡先骕《评尝试集》一文曾论及,甚为推崇。爱伦·坡对象 征主义影响很大,被视为此派鼻祖。编者附记和译者前言都称爱伦·坡为唐代诗人李长 吉,诗文有仙才,多鬼气。顾谦吉肯定这首悼亡诗“悲戚缠绵,情深语重”,并着重分 析了情景交融和韵律方面的特色。1925年11月《学衡》第47期发表李思纯翻译的法兰西 诗选《仙河集》,“所选为中古时代以及于现存之诗人”,其中有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 莱尔(Charles Baudelaire)诗10首,凡莱恩(Paul Verlaine)(即魏尔仑)诗4首。这是法 国象征派诗人在中国较早的集中译介。诗选还对诗人创作作了评介,说波德莱尔是“象 征派(Symbolism)之中坚也”,他的诗“崇拜丑历,歌颂罪恶,描写兽性,刻画污秽, 使人读之,若感麻醉,若中狂疾”;魏尔仑“其诗托想奇诡,短句变化,若有回音,甚 富于象征之思。论者谓其所作,能引诗歌入于音乐之境界。”这些评述还是比较中肯精 到的。另外,吴宓还在《学衡》上对法国后期象征主义重要诗人、理论家瓦雷里(Paul Valery)的诗学进行介绍:《韦拉里论理智之危机》译介瓦雷里诗学的理智心性追求, 《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译介瓦雷里的纯诗论和音乐性问题(注:分别载1928年6月 《学衡》第62期,1928年10月《学衡》第63期。)。学衡派确实抓住了象征主义的一些 内在和本质的东西,并且这些译介和论述要早于新文学阵营,甚至就所论方面而言较后 者深入和精到。
学衡派在接受象征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偏离。在诗歌艺术上,反叛性是象征主义的 特征。象征主义既反对浪漫主义那种过于感伤、夸饰和直陈其事,又反对当时巴那斯派 (Parnassiens)的“泛泛而谈的说教手法”以及自然主义对现实的如实摹写。莫雷亚斯( Jean Moréas)指出:“象征主义诗歌作为‘教诲、朗读技巧、不真实的感受力和客观 的描述’的敌人”[8]。在审美方式、艺术手法、表现主题等方面,象征主义都勇于创 新,反叛传统。这也是象征主义对后来的形形色色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迪借鉴之处。象征 主义注重神秘与未知,心灵与未来的关系,这给传统抒写自然、爱的诗歌以全新开拓[9 ]。而这一点学衡派闭口不提。象征主义将“未知”带入诗歌,构成晦涩、神秘的美学 追求,重暗示、通感等的艺术手法,学衡派也置若罔闻。他们看重象征主义的形式论和 音乐性,欣赏他们对诗歌韵律的追求。但象征主义诗人致力现代意义的自由诗创作,他 们努力探索反映潜意识“未知”冲动的新的诗歌艺术形式,这与学衡派所理解并信奉的 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诗律有深层差异。如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é)认为,诗 歌的音乐性在于词与词音之间的和谐,一种偶然撞击的火花的轨迹。诗人不是控制语言 ,理性地寻求诗的音乐性,而是把创造性还原给语言本身[9](P397)。在诗性音乐和语 言本体论上,学衡派是拒绝接受的,并提出批评。学衡派持传统诗歌音韵本位立场。吴 宓在《诗韵问题之我见》中提出“诗韵不特有其演进之历史,且有其当保存之价值”[1 0],他对黄遵宪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推崇备至[11];而在论及象征主义的音乐性时 ,吴宓指出,“象征派Symbolism则以作乐之法作诗,故谬误层出”,强调诗的媒质是 文字,“诗附丽于文字,每种文字之形声规律皆足以定诗之性质”[12]。瓦雷里的诗歌 创作,特别是在后期,确实呈现纯粹性、甚至古典化倾向。但正如莫雷亚斯所言,象征 主义“探索的是:赋予思想一种敏感的形式,但这形式又并非是探索的目的,它既有助 于表达思想,又从属于思想”,这种形式本体论诗学观与中国言志缘情、文以载道的内 容形式二元论诗学不同。
有意味的是,学衡派翻译象征派诗,全用中国古体诗形式。李思纯分析说,在马君武 近体式、苏玄瑛古体式、胡适白话直译式三种译式中他遵苏式,认为“马式过重汉文格 律,而轻视欧文辞义。胡式过重欧文辞义,而轻视汉文格律。惟苏式译诗,格律较疏, 则原作之辞义皆达”[13]。譬如魏尔仑的那首著名短诗《秋歌》(Chanson d'automne) ,李思纯译为:
秋日梵阿铃,呜咽哀声长。单调疲弱,心摇摇而悲伤。吾偶闻此哀音,面惨无神,喉 哽无声。忽旧梦之上心,颊泪已零零。微躯恍惚狂风吹,飘摇复凄悲,似彼死叶,随风 何所之。
但读着这些“古体象征主义诗”,仿佛穿长袍马褂的蓝眼高鼻洋人,我们很难寻觅到 那种本来的风貌和神韵,体会不到象征诗的自由洒脱和灵动神秘。
学衡派对象征主义的接受和偏离,与他们的古典审美趣味相关,同时也与对白话新诗 批评和对新文化的想象联系。吴宓在论述瓦雷里关于诗歌韵律问题时认为,理智是一切 伟大文学作品构成的基础,即使描写梦幻和疯狂,也不能纵任情感和想象。这是文学创 作的规律。学衡派推崇、捍卫和谐、理性的古典主义审美原则,对瓦雷里后期转向理智冥想,追求澄明大为赞叹,并认为是消除各种“浪漫派之末流”的唯一有效途径[14]。 吴宓特别指出:
今世之无韵自由诗,但求破坏规律,脱除束缚,直与作诗之正法背道而驰,所得者不 能谓之诗也云云。今节译韦拉里氏此篇中所论关于原理之处,以资考镜,吾国之效颦西 方自然的创作及无韵自由诗者,亦可废然返矣。[15]
由此可见,学衡派译介象征主义,是有其较强的功利性。殊途同归,又是借象征派之 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着眼点还是在于匡正纠偏中国新诗的弊端。吴宓认为:“吾惟渴 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故于今之新文化运动有所訾评耳。”[16]这就是说,眼下进 行的新文学运动,不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新文学。他们所批评的,正是这种造成现成这种 运动的倡导者和方式。除了言论,学衡派还以具体文学创作参与新文学建设,阐述理想 。《学衡》共推出三篇白话小说,其中一篇乃吴宓所作(笔名王志雄)。学衡派坚持旧诗 词创作的同时,也有在文白合一、韵律革新方面的尝试,如当时蜚声文坛的吴芳吉歌行 体叙事诗《婉容词》就获得新诗界好评。
三
学衡派视野开阔,融化新知,但并未全面深入把握或接受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精髓, 只是借用来反对白话新诗,为自己心中的诗学寻求新的合理性和现实注脚。中国新诗的 “新化”与“西化”相关,五四新诗变革采取反叛中国传统诗学,通过破旧立新、学习 西方这样一些激进策略和手段来实现文学的根本转变。而学衡派在强调对传统的利用和 延续的同时,也是以西方为资源为参照对象来反对新诗,并且接受的是最先锋激进的西 方现代主义诗歌。这给文学革命带来很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与孔教会、国粹派等复古主义不同,学衡派没有政治诉求和盲目自大,他们大多受过 新式教育,留学海外,洞悉西学,具有20世纪新的知识结构,对西方文学有系统深入的 了解和认识。学衡派与梁启超、张君劢等研究系也有区别。一些论者将学衡派的文化守 成态度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引用一位法国人的话“西方文化已经破产,正要等到 中国的文化来救我们”相联系,实际上在眼界和知识谱系上二者存在差别。学衡派的“ 昌明国粹”是与“融化新知”联系在一起的,汤用彤当时就对常“仰承外人鼻息”,又 对西方文化存在一定隔膜的“主张保守旧文化者”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提出深刻的批评[1 7]。这样看来,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有相近之处,他们都在思考并企图解决转型期的 文化问题,即如何对待传统、引介西方、建设新文化,无意鸵鸟似地把头埋在昨日的沙 地,沉浸于复古主义的梦幻,而把探寻的眼光投向西方。
新文化主流派对西方文学显示开放姿态和恢宏气度的同时,也表现出热情有余而理性 反思不足,存在径直急取甚至盲从的倾向。梅光迪曾讥笑新文化运动“以西洋学术思想 号于众者”大抵为“速成之留东学生,与夫亡命之徒”,“未受训练之眼光以为观察” ,他强调必须先打破这些“野狐禅”及其“谬种流传”,而后才能言西洋之学术[18]。 胡稷咸郑重指出当时学界西化倾向造成中国学术“为西洋文明之奴隶”,毫无独立自主 意识,并且助长民族虚无主义[19]。学衡派并不排外,而是维护传统,追求客观公正, 在历史创造中寻求中西文化发展的切合点,主张对异域文化进行慎重选择,这确实是对 新文学主流派的一种矫枉和补充。
学衡派对意象主义的批评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是对称摆动的两端,其核心是新人文 主义思想和古典诗学观。学衡派延续、维护传统诗学,认定有一种超历史的审美标准存 在。学衡派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认为长期积淀下来的理性和智慧远胜过个人瞬间偶然创 造,主张借鉴和维护历史资源来融合并参与现实建设,否认断裂和突变。他们对近世堕 落派文学如意象主义的“倾斜”和“断裂”持居高临下的不信任态度;发现象征主义某 些方面流露出“古典情趣”,表现出惊讶和理解。批评意象主义是学衡派的外攻,接受 象征主义是他们的内守。
但为什么学衡派拿意象派为外攻的对象,靠象征派内守,而不是相反?这里主要有时代 背景和审美追求两方面原因。学衡派对意象主义的批评,是进行时式的,当时正处于文 学革命激烈交锋之际。学衡诸子和胡适在美国留学,就开始关于“新潮”的论争;五四 新诗运动,这种论争公开和白热化。所以,对意象派的批评,就是对新诗的批评。意象 派主张诗歌用日常通俗的语言,胡适认为新诗“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不避俗字俗语 ”;意象派要求用词贴切,胡适强调“务去烂调套语”;意象派大胆革新传统诗律,提 出以句子和词组而不是词作意义单位,以音节作为韵律的基础,胡适主张诗不讲对仗, 破除旧律;意象派追求诗歌硬朗、清晰,胡适强调不作无病呻吟、不用典、须言之有物 等等。梁实秋指出意象派“在美国最盛的时候,我们中国留美的学生一定不免要受到其 影响。——影象主义者的宣言列有六条戒条,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几乎 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20]。学衡派对意象派的批评是与自己的文 化追求相联系的。而对象征派的接受,主要是在文学革命之后,是未来时式的,其时不 是要不要进行诗歌革命的新旧之争问题,而是进行怎样的新诗建设发展问题。初期新诗 存在平实直露、随意走笔等弊端,学衡派引介象征派的音乐化、理智性和纯诗理论,是 有积极意义的。可惜影响太小,被人忽视。另外,意象派和象征派呈现的诗歌审美特征 ,也是学衡派褒贬选择的原因。意象派主将庞德说“象征派诗是音乐一样强使自己成为 清晰的语言,而意象派诗则是象雕塑绘画一样使自身成为词汇”。他又打比喻:对象征 派诗歌来说,现实是一团泥,可以在诗人手中随心所欲地塑造;而对意象派诗歌来说, 现实则是一块石头,它抗拒雕刻家手中的刀刃[21]。这里庞德给意象派和象征派作了音 乐性与绘画美、神秘性与硬朗、质感和力度美等三方面的区别。象征派诗歌的音乐美、 理智性、内涵深等,与学衡派骨子里的古典诗歌审美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契合。而意象派 偏重形式上反传统的新潮面孔,特别是革新韵律、以口语写自由体诗等激进主张得不到 学衡派青睐。其实,在最初,比如梅光迪的文章里,对象征主义的颓废等“新潮”倾向 也是表示过批评和怀疑的。
收稿日期:2003-03-11
标签:诗歌论文; 胡适论文; 象征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读书论文; 尝试集论文; 梅光迪论文; 胡先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