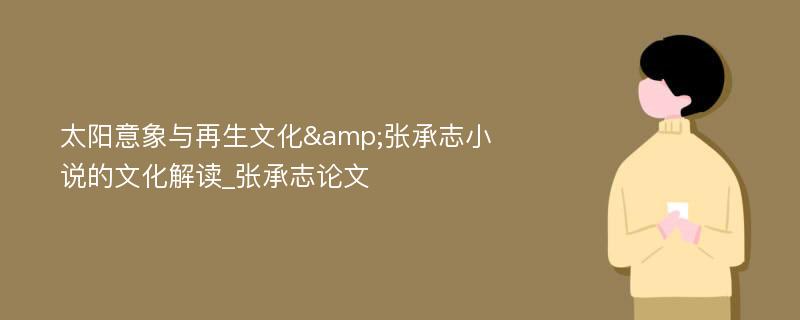
太阳意象与再生文化——对张承志小说的文化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意象论文,太阳论文,小说论文,张承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张承志小说中的太阳意象,蕴含着作家深刻的人生思考和文化选择。太阳意象在表层的象征意义上包蕴着三个方面的内涵:追求意识,孤独感,理性精神。进而由作品的呈现模式体现出了张承志的文化选择——对文化的混交与再生的期冀。不管是对原始生命强力的张扬,还是对原罪感、圣洁感、生命信仰的追寻,都鲜明地体现了边地文化对汉民族文化的不无益处的补充和矫正,包含了一种“重新铸造”的努力,以及寻找真实、永恒、超历史、超地域的价值的可能的意向。
关键词 张承志 小说 文化解析
一
正象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出张承志在新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一样,我们也很难用几句话来涵盖张承志作品中的太阳意象的丰富象征意义及文化蕴含。毕竟,“意象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出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①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择出大量富有代表性的意象群。除了草原、戈壁、黄土、大河等是作为作品背景而出现的以外,太阳、暗夜、火光、歪骑着马的男人等意象都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解析的重要凭证。其中,太阳意象的频频出现,应该视为作者的刻意为之。在这一古老而又新鲜的意象中,蕴含着作家深刻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思考。
架扬起《黑骏马》的不仅是那首悠长深情的古歌,还有不可让人忽视的那个贯穿性意象的太阳。太阳伴随着回忆、爱情,伴随着独行、愁思。主人公音乐般流动着的激情与日出、日落等和谐对应,人类的感官经验和生命意义投射在自然物象中,从而透露出了太阳意象在人类心灵深处共通的原型意义。《北方的河》里,条条大河都是在阳光下展示在主人公视野中的,并与黄土、戈壁、高原等相衬相谐,烘托出生命、力度、深静……大河上的太阳,作为充满自然气息的景观照耀着北方的河,也照亮了诗意纵横的作品。就连张承志本人一直不感兴趣的现代都市,他也为它洒满金色阳光。《黄泥小屋》通篇都给人一种压抑、窒闷、沉重的感受。唯有黄土地上的太阳仍然高高地悬挂在天空,且以炙人的热度和超常的亮度照耀着那片干涸、贫瘠、坚硬的大地,以不可抵挡的光芒驱逐着阴森、黑暗与残暴,温暖着焦渴、执着的心灵,使人永不丢弃心中的那一份“念想”。长篇小说《心灵史》、《金牧场》中,血雨腥风、风沙弥漫的黄土高原上,太阳仍不断出现,虽然近乎失血而略显苍白,但仍不可忽视地存在着。
意象“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系统的一部分。”②张承志的象征系统的构筑,很少离开太阳意象,这里,体现着新文学中的一种迥异于古代中国文学的全新精神追求。中国古代文人多爱歌咏夜月而少赞颂太阳,新文学却不吝笔墨和歌喉地进行太阳礼赞,是与整个民族昂扬向上、进取不止的青春精神息息相关的。无论是郭沫若、艾青诗中的太阳意象,还是新时代文学中的“西部太阳”,无不体现着青春追求意识与理性精神。
张承志的太阳意象主要包蕴着三方面的象征意义:
1.追求意识
太阳意象所象征的追求意识始于神话中那位逐日的夸父。这里,太阳并非象“后羿射日”中的太阳那样仅是作为人们的对立物出现的,而是与人们的理想、意志与希望紧密相连的。当夸父追上了太阳,也就是人们拥抱太阳、拥抱理想、实现追求和梦想的辉煌时刻。但夸父没有追上太阳,只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千古遗憾和叹惋,人们似乎还发现:夸父逐日几乎成为一代代不甘平庸者的人生象征。
太阳意象在张承志作品中的出现,始终伴随着主人公的上下求索。或是对冰大坂的征服、对老桥的跨越,或者是久别草原后回转去重寻年轻时失落的亲情与爱情,或者是为报考研究生而考察北方大河,在人生路上划下奋斗、思索、选择的轨迹,或者是为了追寻安身立命的黄泥小屋,为一颗躁动不安的心灵苦苦地寻找精神家园。无论是在草原沙漠,还是在黄土高原,都有这样一个狂躁不安的男子汉形象。“冷冷的男性的面容”背后掩藏着的,应该是人生中的缺憾。有缺憾就有追求、有创造。年轻的躯体内奔腾着激情,青春的心灵充满喧响,一如那个大河之子对北方的河的深情:“我就是我,我的北方的河应当是幻想的河、热情的河,青春的河。”这是青春的追求,青春的创造,执着坚韧,无怨无悔,一如逐日的夸父。
2.孤独感
自从后羿张弓射去了天空的九个太阳后,浩浩长空中只剩下一轮太阳,孤独地、形单影只地重复它那亿万年不变的行程。其唯一和遥远,其永恒和不可接近,在代代人心中产生一种苍凉、悲壮的感觉,直至积淀为一种共通的心理感受——孤独。这里,太阳的孤独象征意义是在“一种两极对称结构”中显现出来的,它“呈现一种肯定与否定、失去与获得、黑暗与光明的韵律”③,正是在此“韵律”中流露出深深的孤独感。此中潜含着上古神话中的“英雄——太阳”模式,即这是为英雄所有的孤独:英雄是孤独的英雄,孤独是英雄的孤独。
张承志的孤独长旅开始已久。由孤独而流浪,由流浪而追求,由追求、体验进而消解孤独,总有这样一个男人在不安分地寻求着什么。在其精神漫游中,他首先塑造了一组母亲形象群,她们勤劳坚韧,至诚至善,闪烁着伟大的母性光芒。母乳哺育了他,母爱温暖了他,却不能使其本分、平静。这颗心灵仍躁动不安。《北方的河》中,主人公理想中的那个姑娘又在哪里?因此,几乎是同时,漂泊中的张承志又在一系列孤独的男人身上寻找自己。他征服冰大坂,跨越老桥,漫游北方大河,扑向黄土高原……但《山之峰》中的铁木尔终于没有越过山之峰,《亮雪》中歪骑着马的男人满怀希望得到的仅仅是雪原上的刚刚出生的一匹小马驹而已。《残月》竟不可多见地以残月为原型意象,只有寺庙里射出的黄黄的、暖暖的光芒一扫现实与人心中的黑暗,弥补了只能由太阳意象才能传达出的意义,那位老汉正是在宗教的抚慰下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张承志本人也直到皈依哲合忍耶教,才为自己找到了苦苦寻求的精神家园。
3.理性精神
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掌管青春、医药、畜牧、诗歌、音乐、神谕等,“他是所有造型力量的神,代表规范、数量、界限和使一切野蛮或未开化的东西就范的力量”④,这是青春之神,是艺术之神,是理性之神。新文学对太阳的礼赞,引入了太阳代表的这种强烈的理性精神。
张承志的太阳意象,深蕴着作家对历史、对文化的研究与思考。当太阳的理性光芒照彻张承志赖以安身立命的新疆内陆、内蒙古草原、黄土高原这三大板块的时候,由此升腾起的关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思考便不仅仅只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它理所当然地包含了重构——以边地民族文化为参照对民族精神的重构。在青春与理性的光照下,重新构筑的民族精神应该是更加健全的。我认为,太阳的理性象征意义,是张承志文化选择意向的一个最重要因素。而这种理性精神,并不与张承志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相悖。恰恰相反,理性精神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正是在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这一层面上相契合的。在浪漫主义那里,生命激情正是被作为一种理性根据而奉持的。
二
既然理性精神被看作太阳意象的重要象征意义,理性支配下的价值取向与文化选择便成为我们要关注的内容。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部分作品呈现出的一种相似模式:《绿夜》、《黑骏马》是一个在草原上生活过的青年进了城,却厌倦城市生活的杂乱琐屑、喧闹刻板而希图再回到草原去寻找心灵深处的某些东西,重温那令人梦回萦绕的古歌;《北方的河》、《老桥》、《大坂》是高层知识分子在大自然中的游历,大河与老桥分明流淌着和连接着“一种水土”“一种血统”。主人公的奔波历程无疑体现着作为精神漫游者的张承志的心路历程,潜含着作为学者的张承志的文化选择的意向。
其次,不管是上述在草原上寻找古歌,还是那种“水土”“血统”,都鲜明地标示着一种文化混交倾向,而混交的目的和结果,便是文化的再生。即使作品中的落日和晚霞意象,都不妨看作一种再生的象征:留恋落日不是出于对黑夜的恐惧,而是对自然、生命再生的期待,所以把张承志的文化选择概括为混交——再生文化倾向,并无太多的不恰当。在白音宝力格对草原边地文化进行痛苦地认同时,我们看到草原人民也正力所能及地摆脱着愚昧和贫穷,艰难地向文明迈进;跨越老桥者标示着对两片不同天地、两种文化的有意连接;《北方的河》中黄河的刚健,额尔齐斯河的坚贞,湟水的忍耐,永定河的宁静,黑龙江的不驯都作为种种文化因子渗入了主人公的血脉,张承志希望“这个母体里含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这是汉民族文化与边地文化的融合与混交,这是中间地带文化的弘扬与再生。如果说这种混交——再生文化结构在其前期作品中还体现为一种具有浓厚象征寓意的相似叙事模式的话,那么,在后期作品中则直接表现为与汉民族文化比较下对边地民族文化中的某些优秀特质的接受、推崇和张扬。对一种文化类型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类型中的某些特质的必然排斥,在此意义上,张承志的价值取向并非非此即彼的一种极端追求,而是作为一名学者在对各民族文化进行深刻研究思考的基础上,有意用边地文化对汉民族文化进行的不无益处的补充和矫正。正象本尼迪克特所说:“研究不太复杂的群体中的有组织思想和行为,我们可以得到某些启迪,所有这些启迪都是我们需要的。”⑥
对原始生命强力的追求是张承志几乎所有作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主题。“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传统儒家文化用伦常、礼教和禁欲为人们构造了心狱,道家以清静、淡泊、无为为人们展示了太虚幻境,都极大地摧残与限制了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使人变得软弱卑微甚至病态。
与此不同,张承志则展示了另外一种图景:主人公在同严酷的大自然,同社会的猛烈搏斗中铸造出一种无畏强悍、热爱自由、敢恨敢爱、豪迈奔放的气概,连大自然都响彻着野性的声音。这是一种少受外部文明冲击的自然状态,它拉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更鲜明地凸现了人的自然风格,显露了人的自然本性中健康舒展的一面。这种充满原始质感的文化无疑是对中国正统文化中否定人性、窒息人的生命力的负面价值的反动和冲撞。
对人道与人性的呼唤包含着张承志所追求的一系列传统文化中少有以至缺乏甚至为现代人都难以接受的文化内容——对原罪感、圣洁感、漂泊感及宗教意识的追求。
张承志所追求的原罪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中面对上帝的原罪。它是面对横流的人欲、污秽的社会、沦丧的人性所发现的一种忏悔感。对自身罪恶根性的清除和忏悔无非是能让人更清醒更圣洁地把握自身,它是建立在自信与希望而非绝望不可求赎的基础上的。原罪感引发的不是人的自弃,而是走向个体生命中的神圣的一面,从而把个体生命与超绝的神性意义联系起来,使人意识到自身的自然状态在价值形态上的非自足性,在超越中体认到生命的意义。忏悔感则被看作是心灵的自我治疗形式,是灵魂重新获得力量的必由之路。
由原罪和忏悔感又引发出救赎层面上的圣洁感——伊斯兰文化的重要一面,张承志如是分析和理解。为了心灵的圣洁、念想的纯粹,为了“人心里最薄软的地方”免遭践踏,他们宁愿受冻挨饿、贫苦劳累,甚至从容赴死。张承志所张扬的充满原始质感的文化显明透露着一种英雄主义,而心灵的自由和圣洁乃是英雄内涵的第一要义。在这里,太阳意象经由自然循环呈现了其在最初层面上的“英雄——太阳”模式。正是这种英雄精神凝聚成了一种无所畏惧、不可摧毁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它构成了张承志所理解的人道主义的一面。传统文化没有对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罪恶和欠缺的认识,更缺乏原罪感及忏悔意识。于是,强权造就非人,非人又强化了社会的病态和污秽,长此以往,麻木不仁。边地文化对原罪感、忏悔意识和圣洁感的追求,无疑给灰黄色的文化点染了一丝炼狱火光般的鲜红。
漂泊感作为躁动不安的张承志的一种心态借助伊斯兰文化得以张扬和鼓吹。这种漂泊感和无家可归感并非指完全意义上的西方现代人的生存焦虑和窘境,更多地,它带有西方古典心态的面影。《圣经》中的伊斯梅尔是一个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人,所以《白鲸》一书开头便写道:“你们就叫我伊斯梅尔吧。”甚至爱因斯坦也发出过这种慨叹:“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漂泊感和无家可归感首先意味着一种心灵的孤独。但漂泊中的怀疑与否定意向并不意味着对孤独的否定和逃避,相反,它是对孤独的接受和肯定。漂泊感诉诸外部行为表现为形体流浪。个体以流浪去解除打破对自身的束缚从而使人获得自由。它使人们在寻求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张扬个体生命,充分展示自身的力量,让人在一种悲剧情境中创造出人生的辉煌。而素来讲究中庸保守的传统文化只讲究“父母在,不远游”等,仅有的一丝游子之情、漂泊意绪都化为一种哀怨的乡愁,进而被挥洒到青楼酒肆、山水园林之间。由此,行为的被动和保守带来精神的滞塞,也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民族的开拓精神、追寻视野和否定意识。
于是,宗教在张承志这里便成为一种生命信仰。当人们在全盘性的反传统中平静下来,才发现心中虚空一片,一无所有。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都已崩溃甚至薄弱,而新的观念和信仰与模糊而浮泛,甚至连个体生命都找寻不到了。边地文化中的这种生命信仰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无论是体现在作品中的宗教意识,还是张承志本身对宗教的皈依,我们从中体悟到的,都是这种文化选择意向中所包含的对自我生命的虔敬的信仰,以及由这种信仰所形成的圣洁和真诚。毕竟,宗教来源于人们对生命的信仰,而生命的信仰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前进的精神支柱。
既有象征意义上的表层契合,又有理性精神对文化选择的深层光照,非理性的叙事形态和感性形象中蕴含的是充满理性精神的文化混交与再生的期冀。“二十世纪是文化重建的时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它乃是人类的末日,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脱一次重新铸造的时代。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心态在外来文化的煎逼下显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它被迫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既不忍离弃自己的根,又不能安于自己的根。”⑦张承志的文化选择无疑包含着上述“重新铸造”的努力,以及寻找真实、永恒、超历史、超地域的价值的可能的意向。
当然,选择与探索中的偏颇是难免的,但混交中的再生却令人充满希望。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文化的再生尽管不会那么快,但民族精神的健全和文化的进步却是必然的。
收稿日期:1994年5月19日
注释:
①②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2、204页。
③④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0、234页。
⑤张承志:《黑骏马》,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⑥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
⑦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标签:张承志论文; 文化论文; 太阳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北方的河论文; 黑骏马论文; 原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