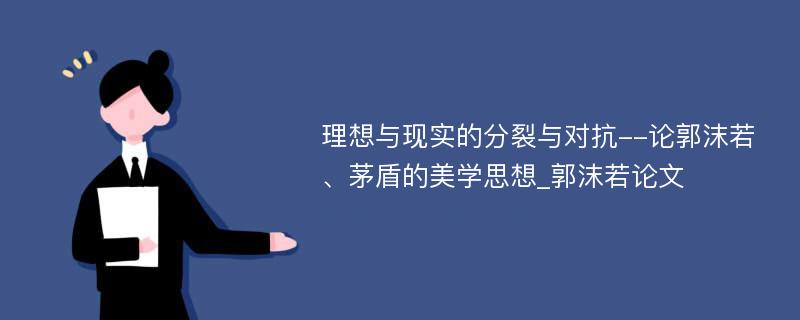
理想与现实的分裂和对抗——论郭沫若、茅盾的美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美学论文,茅盾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20—40年代,有两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不但通过自己的文学创造在人们的审美生活中放出光彩,而且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美学主张,并广泛、强烈地影响了人们的审美意识,在中国20世纪中期的美学理论构建中,深深地留下了他们的印痕。这两个人物就是郭沫若和茅盾。
中国古典美学强调情景交融,注重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郭沫若和茅盾,可以说是它最终实现现代分裂的最好体现。在这些矛盾分裂与对立中,他们两人各执一端,在数十年里进行了长期的理论较量,为现代美学在现实与理想两极的片面深入乃至极端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郭沫若的美学思想可以分为两期,日本留学期和投身革命期。当然这个分期只有一方面的意义,即看出郭沫若在对待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上的变化。前期他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后期主张文艺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但是郭沫若所坚持的强调主观、个性、表情、天才的文艺美学思想却一直没有变。变与不变的统一,构成了郭沫若独特的美学个性。变,是社会审美的变化使然,不变,又是郭沫若自己的特殊的气质和个性决定的,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我们先看他变化的一面。
郭沫若前期的美学思想是超功利的。尚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虽然怀抱一腔爱国热情,对国家民族的危亡极为关切,但他毕竟远离国内具体的政治运动,至少,他暂时还没有参与政治运动的客观条件。而且,《女神》的巨大成功,使得这位年轻的文学才子仿佛感到自己真的就只归属于纯洁超然的文学女神了。他当时需要总结反思《女神》的成功,满脑子所想的,就是“生命”,“生命的能量。”他认为:“生命与文学不是判然两物。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1〕很显然,郭沫若心里的“生命”是没有任何规定、羁绊乃是抽象的。他认为只要蕴积了生命的能量,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任何因素,象一个未被社会陶染的婴儿,就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他说:“创造生命文学的人当破除一切的虚伪、顾忌、希图、因袭,当绝对地纯真、鲠直、淡泊、自主。一个伟大的婴儿。”〔2〕很显然, 一个文学家,如果要使创作与社会人生相联系,他必然有所顾忌,有所希图,那就会妨碍他的纯真与淡泊,使他不能完全自主,从而使文学创作堕落。他说得很明白:“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文艺的精神太远了。”〔3 〕他坦率地承认:“我不反对艺术的功利性,但我对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是有所抵触的。”〔4〕
但是1923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态度明显改变了。他毕竟是一个关心国家兴亡的热血青年。面对国家衰败受辱的局面,他不可能再沉迷在艺术的冰宫里造自己的象牙塔。《女神》早已显示,他不是沈从文,不是丰子恺更不是李叔同。既然国内政治斗争风起云涌,他必然会投身进去。他开始考虑把文学作为为革命呐喊助威的工具。在1923年9月4日发表的《艺术家与革命家》一文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转变。他说:“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我们不能论议他宣传革命的可不可,我们只能论他所借以宣传的是不是艺术。即使他宣传的工具确是艺术的作品,那他自然是个艺术家。”〔5〕这只是一个过渡, 到1926年,全身心投入了救国救民的政治洪流的郭沫若,燃烧起的已经是政治激情多于文学激情了。他说:“一个超贫富,超阶级的彻底自由的世界还没有到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除此以外的文艺都已经是过去的了。包括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过去了。过去了的自然有它历史上的价值,但是和我们现代不生关系。我们现在不是玩赏骨董的时代。”〔6〕从这个时候起,在以后的岁月里, 郭沫若始终把文学创作与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并且在理论上总是对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文学表示呼唤和鼓励。这是特定时代中国的审美大场所决定的。在民生多艰,战火飞扬的岁月里,尚能静下心来玩弄“超阶级”的、“纯”的艺术的人不但日益减少,而且这样的人也不会有大出息,更不会产生大影响。1943年,郭沫若几乎是带着深深的愤慨为文学为革命斗争服务表示辩护。他说:“国家临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受着了空前未有的浩劫,一切都应该为了前线。作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多数是动员起来了。虽然在初期也有少数人倡导‘与抗战无关’论,但为大势所迫,不久也就销声匿迹。近来如沈从文有‘反对作家从政’的见解,这在平时可以说不成问题的议论,但在战时却可大成问题,而且把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认为‘从政’,那便是超过了误解范围的诬蔑。”〔7〕
毫无疑问,郭沫若的这种转变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家美学思想的转变。真正心无帝鹜地在搞艺术的人已少得可怜。这也许是一个民族的解放与振兴必然要付出的精神财富的代价——在这个时期的文艺创作中,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作品确实太少了。但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危难关头的唯一选择,忍让大量的精神贵族去悠哉游哉炮制高雅的纯文学,这不但是民族在求生的路上负担不起的奢侈,而且整个民族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就作家个人而言,也是其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的一种选择。邹华说得一针见血:“矛看的产生即根源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的贵族精神和英雄主义。……当社会一旦提供了治国平天下的机遇,他们就会……以轻视的态度利用文艺,夸大艺术的社会功用并不意味着对艺术的看重,……因为艺术被夸大的原因不是艺术本身的价值,而是它的载道之功。”〔8〕中国的文学艺术就在文艺家们这种选择中艰难地前进。 每个文学艺术家都只活一回,选择是他的权利。不论这种选择于民族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都无法回避,这种选择在当时普遍存在,而且明显影响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的进程。
郭沫若美学思想基本保持不变的是他对个性、想象、情感、天才等的肯定与张扬。
一、肯定天才。郭沫若相信,做诗作文是要讲天才的。他对于康德的“天才”论很欣赏。他说“天才是人,绝不是人以外的什么怪物。他与凡人的区别只有数量的相差,而没有品质的悬异。”〔9 〕但他认为,仅靠“天赋独厚”不能成为天才,还需要适宜天才成长的土壤。强调天才,也是创造社一个共同的倾向。在天才论遭到茅盾等人的一再否定之后,他仍然坚持。1939年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的确是才天”》,借一个日本作家的话予以强调。
二、强调情感的抒发。他认为,生命是文学的本质,生命中最高级的成分是精神,而精神是大脑里面能量(Energy)的交流。“Energy底发散便是创造,便是广义的文学。”〔10〕创造文学的人要做的事就是储积能量。“Energy愈充足,精神愈健全,文学愈有生命,愈真、愈善、愈美。”〔11〕所以郭沫若一生都在蓄积能量,以求喷射而出。他直率地说:“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回顾我所走过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12〕因此郭沫若为诗为文创作戏剧,都要酝酿或者等待一种情感的冲动。没有冲动他就不写。
三、反对再现。他认为:“艺术是从内部发生的。它的受精是内部与外部的结合,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它的营养也是仰诸外界,但它不是外界原样的素材。蚕子啮桑柘而成丝,丝虽是植物的丝维所成,但它不是桑柘的原叶。”〔13〕所以他很瞧不上那种直接模写再现现实的作品。他说:“提着一个照像机向无论什么对象便摄取一张,提起一支笔把自己周围的东西看见什么就记在帐薄里,这种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艺术。由内部发生的艺术,表现的艺术,无论如何从受精以至于分娩,总得有一定的怀胎期间。”〔14〕
所以他对“典型”理论时有微辞。1939年他在《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中就说:“中国文坛对于俄国文坛的应声,有时我觉得过于敏捷了一点。例如‘典型论’被一部分的批评家叫得高唱入云,其实典型的制造不必是文学的唯一的要务,而那制造过程并不是任何文学家都可以胜任的,欧洲的大作家要制造一个或一些典型,往往要费毕生之力。”〔15〕‘认为,典型创造,只适合于与造形艺术相近的小说。“但有人认之为‘艺术的本质’,那似乎有点‘逐鹿而不见山’。”〔16〕
总体上说,郭沫若的美学思想偏向于浪漫主义。精神上与世纪初鲁迅在《魔罗斯力说》中对浪漫主义的呼唤是衔接的。说他“偏向于”,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中还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因素。对悲剧的重视,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郭沫若认为,在处理题材的时候,“取着悲剧的形式,或者写来更能够动人。”〔17〕他觉得,“一般的说来,悲剧的教育意义比喜剧的更强。促进社会发展的方生力量尚未足够壮大,而拖延社会发展的将死力量也未十分衰弱,在这时候便有悲剧的诞生。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18〕
对悲剧的重视,不光是对悲剧的本质,美感特征及其社会意义有较清醒的认识,还在于郭沫若清醒的感觉到,悲剧是这个时代审美风格的集中体现和最高的审美要求。他说:“革命时期是容易产生悲剧的时候,被压迫阶级与压迫者反抗,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一切的反抗是容易归于失败的。阶级的反抗无论由个人所代表,或者是由团体爆发,这种个人的失败史,或者团体的失败史,表现成为文章就是一篇悲剧。而悲剧在文学的作品上是有最高级的价值的,革命时期中容易产生悲剧,这也就是革命时期中自会有一个黄金时代的第二个原因了。”〔19〕
基于这种认识,他自己创造了好几出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悲剧,《屈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出。即令如此,他的悲剧不是再现而是表现的,不是拘泥于史实而是满足于内心愤懑爆发的需要的。他自己就说:“《屈原》是抒情的,然而是壮美而非优美。”〔20〕
二
与郭沫若正好相反,茅盾的美学思想偏重客观,再现,社会和后天努力。
茅盾的气质属于认真、谨慎、踏实、勤奋的苦干型,遇事冷静,理论分析能力较强,但想象力却不够丰富。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以写小说为主,没有鲁迅深刻,也没有巴金的激情。主张“主题先行”,作品在那个白话小说本来就少的年代,仍然领了几多风骚。他的真正影响,是在他的文学批评和对于文学运动的组织与推动上。从他的履历可以看出,他的审美意识也是与中国社会的起伏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美学思想,可以说与郭沫若正好相反,如果说郭沫若是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代表的话,他却是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的前期代表。他的美学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郭沫若强调天才,茅盾这里坚决反对天才和灵感。他说:“我们并不以为文艺是什么艺术之神的神庙里的神秘的东西,我们也不承认什么创作家一定有他的天才或灵感一类的鬼话。”〔21〕他告诫青年作者:“慎勿轻率!慎勿认为作家的一篇作品是产生于一时的‘灵感’!绝对不是的!没有什么神妙的灵感,只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深湛的理解和精密的分析!”〔22〕否定了“天才”与“灵感”,创作靠什么呢?靠知识,靠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分析。那就是说,对社会你认识清楚了,你也就写得出来了。这个方子对所有想从事文学创作而又天分不高的人都是有诱惑力的。
但是,许多人努力地认识了社会,却还是写不出作品,这是怎么回事。茅盾认为,这是没有真正认清社会的本质。要想真正认识清楚社会,必须具备许多方面的社会科学知识,因此他劝告大家,为了写出好作品,要先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没有社会科学的基础,你就不知道怎样去思索,然而对于社会科学倘只一知半解,你就永远只能机械地——死板地去思索;不会思索的人去‘搜集形象’只是瞎子摸死蟹。”〔23〕所以茅盾总是不厌其烦地劝说文学家,要多学习社会科学知识。
二,郭沫若强调情感的酝酿与抒发,茅盾却主张对客观现实生活的观察、搜集、分析整理后再现之。他说:“文艺……应该是社会现象通过了作家的意识经过分析整理的再现;”或者“说是‘反映’罢。”〔24〕这样,他也就主张文学要塑造“典型”,“各人一个身份,各人是一个‘典型’,不但各人的形容思想各如其人,连各人的‘用语’也很富于“典型”的色调”。〔25〕茅盾强调典型,是因为他了解到不只文学反映生活,社会科学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只是与文学相比,各有不同。“社会科学家所取以为研究资料者,是那些错综的已然现象,文学作家的却是造成那些现象的活生生的人。”〔26〕
人物“典型”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并受“环境”所支配。写人物必须写出环境。环境支配人,又被人所改造。“环境当然是广义的。这是指一特定地区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立于支配地位的特权阶层以及被支配的阶级,在一方面是武器而在另一方面是镣铐的文化教育的组织以及风尚习惯等等。”〔27〕环境应该在与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被写出来。
在这里,不由我们不想起恩格斯1888年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对“现实主义”下的那个著名定义:“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8〕很显然,茅盾通过苏联的文艺理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这个观点,与他自己的创造实际一拍即合,深得他的认同。
三,茅盾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和社会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是他组织文学研究会后一直与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互相指责的核心话题。1929年他在反思这段争论时心理还愤愤不平。他说:“为什么伟大的‘五四’不能产生表现时代的文学作品呢?……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文坛上发生了一派忽视文艺的时代性,反对文艺的社会化,而高唱‘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这样的入了歧途!”他甚至指名道姓:“这就是当时的创造社诸君。即使人们善忘,总还记得当时创造诸君的中坚郭沫若和成仿吾曾经力诋和他们反对的被第三者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的一部分人的文学须有时代性和社会化的主张,为功利主义。”〔29〕虽然有些偏激和简单化,但仍反映出茅盾关注时代风云,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美学观。
基于这一点,他自己不但紧扣悲剧时代创作出一系列悲剧性作品,而且对于别人创造的悲剧作品也表示欣赏和鼓励。这一点,他和郭沫若是一致的。他说:“在我看来,写一个无可疵议的人物给大家做榜样,自然很好,但如果写一些‘平凡’者的悲剧的或暗澹的结局,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30〕对鲁迅写的一系列小人物的悲剧,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引述别人的评论说:“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他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31〕
不过,总起来看,不论是茅盾,还是郭沫若,其美学思想都并不怎么深刻,而且往往显得零乱,缺少系统性,他们谈出来的许多美学观点听起来有理却都不是他们所创造。他们之所以还值得提出来讨论,是居于这样三点理由:
第一,他们在中国20—40年代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审美生活中都是影响巨大的人物。可以说他们一直伴随着中国人民争独立求解放这股洪流的潮头,用他们的创作、理论、全部的智慧与激情乃至生命,引领着人们审美活动的发展曲线。美学的历史无法回避他们的存在。
第二,他们两人所代表的两种美学思想的对立与斗争,显示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矛盾对立统一的最后分裂,主观与客观的分裂,表现与再现的分裂,个人与社会的分裂。从和谐统一走向分裂对抗,正是崇高美学期的典型表现。这种分裂对抗,在茅盾与郭沫若之间表现得尖税而又分明。离开他们两人,这个变化不能得到简要又充分的说明。
第三,他们两人美学观点的消长,暗示了深层次的美学思想由朱光潜向蔡仪变化的发展趋势,他们是朱光潜到蔡仪的中介。如果说郭沫若的表现美学思想更倾向于朱光潜的话,茅盾的再现美学思想则更相似于蔡仪。在郭沫若与茅盾多年的理论较量中,最终是茅盾借助时代审美场的需要占据了优势,这个现象预示了蔡仪美学的必然崛起。
注释:
〔1〕〔2〕〔10〕〔11〕郭沫若《生命底文学》,1920年2月23 日《学灯》。
〔3〕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转引自李泽厚、汝信主编《美学百科全书》,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 页。
〔4〕《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沫若文集》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5〕〔6〕〔7〕《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17页,第24—25页,第82—83页。
〔8〕邹华《和谐与崇高的历史转换》,敦煌文艺出版社1992 年版第285页。
〔9〕《天才与教育》,《沫若文集》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64页。
〔12〕《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沫若文集》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5—106页。
〔13〕、〔14〕、〔15〕《文艺的产生过程》,《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第10页,第40页。
〔16〕《从典型说起》,《沫若文集》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4页。
〔17〕、〔18〕、〔19〕、〔20〕《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第427页,第33—34页,第391页。
〔22〕《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第425页。
〔23〕《思想与经验》,《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33—434页。
〔24〕《谈题材的选择》,同上书第444页。
〔25〕《西柳集》同上书第302页。
〔26〕《创作的准备》,同上书第466页。
〔27〕同上第470页。
〔28〕《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29〕《读〈倪焕之〉》,《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29—230页。
〔30〕《写在〈野蔷薇〉的前面》,同上书第50页。
〔31〕《鲁迅论》同上书第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