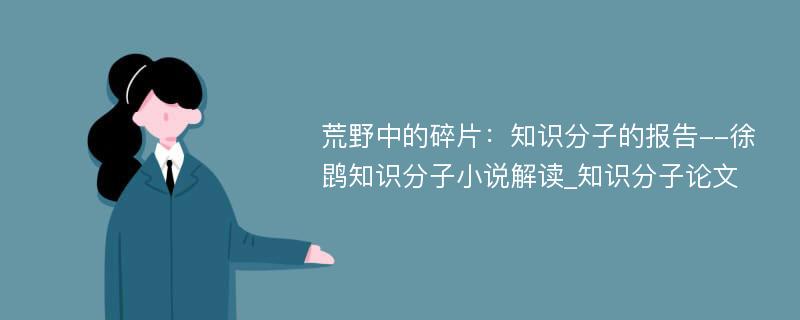
旷野上的碎片: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读徐坤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旷野论文,碎片论文,题材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坤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活画像。这一代知识分子大约是六十年代生人,现在三十岁左右,其童年或少年时代赶上一个“文化革命”的尾巴(当然,这是就徐坤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的主体以及他们的主导特点而言,也有个别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属于这个年龄段)。从知识分子社会学(the sociologe ofintellectuals)的角度(这是本文的主要分析角度)说,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是没有传统的一代,也是没有完整历史的一代。既没有中国的古典传统,也没有“五四”的启蒙传统、延安的革命传统,当然更不懂西方的传统。甚至于“文化大革命”的传统、红卫兵的传统、知青的传统,对他们而言也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至多是破碎的记忆与小说中捡得的“故事”。这一知识的背景使得他们不但不同于“五四”的一代,延安的一代,甚至也不同于老三届、红卫兵的一代。正如《斯人》中的那位诗人说的:“历史到我这里已经断代了”,“我只能看见我自己”。他们的童年是“营养不良的”,是在背诵“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中渡过的,他们的传统只能“上溯到毛主席那里”,因而他们“最伟大的理想是当毛主席或者当爸”(《斯人》)。历史给予他们的只是残缺的碎片,在他们少不更事的时候,曾经被人灌输过信仰,但还没等到这种信仰深入骨髓(这一点使之不同于老三届,老三届对于红色的革命乌托邦曾有过虔诚的信仰)他们就跟着别人大呼“上当受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都是迷途的羔羊”。
没有传统与历史、没有精神上的“教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爷爷那会儿人爱造神/我爸爸那会儿人造人/我们都是可怜的试管婴儿/也不知道精卵是他妈的谁的”(《游行》,《钟山》1995年第6期),而他们的出生年月又注定他们只能属于九十年代,只有其中的个别赶上过八十年代的尾巴。徐坤作品中展示的主要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诗人、学者)在九十年代的境遇。活跃于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两类,一是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然后又在八十年代再现辉煌的“重放的鲜花”们,另一类是粉碎“四人帮”后回城的下乡知青。前者在今天大多已届“耳顺”之年(虽然实际上牢骚满腹),后者也已过“不惑”,正走向“知天命”(虽然惑莫大焉,遑论知天命)。他们在八十年代加入了拨乱反正的浪潮,成为思想解放的主力军,积极清算极左路线,控诉专制主义给个人与民族带来的灾难,诉说自己被耽误、被荒废的青春岁月。这些人虽然没有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也不曾想要入得西方文化的大门,但是却虔诚地信奉过解放后的红色乌托邦,并参加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神运动。也许正因为他们有过信仰,而且是事关民族存亡、国家发展、世界趋势的大信仰,而不只是个人的灵魂安顿的小信仰,所以他们身上有强烈的“平治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以及“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领袖意识,这种过高的自我期待与社会承当使他们无法适应九十年代杂语喧哗与中心散乱的“后现代”局面。他们可以反思批判过去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但是他们不能不要任何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不能习惯于无中心。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信仰就没有生命,虽生犹死。即使是批判过去的意识形态,他们也将之视作一项严肃神圣的政治使命、文化使命,绝做不到以游戏的态度调侃与嬉戏之。他们本身就是那段历史的产物,反思历史、清算历史、批判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反思自己、算清自己、批判自己,因而他们的批判不能不是痛苦的。
徐坤以及徐坤笔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可就不同了。“造神”与“上山下乡”对他们而言同样是遥远的“故事”,至于反右运动简直就像是恍如隔世的历史碎片,他们对于那个时代、那个红色的乌托邦神话,既无切肤之爱,亦无切肤之痛。所以他们可以以无可无不可的潇洒态度后着那个时代,后着革命的神话,后红卫兵、后上山下乡、后毛泽东以及他的“最高指示”。在他们看来,这与后屈原、后鲁迅或后王朔、后流行歌曲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们本来就不知社会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为何物,更遑论丧失它们。在他们刚刚想要懂得使命、扛起责任的时候,支撑这种责任与使命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商业化的浪潮正在使一切悲剧都成为喜剧,一切正剧都成为滑稽剧,这对于本来就不曾导演或参与过悲剧、正剧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么?也正因为这样,在不谈“使命”、消解“责任”、躲避“崇高”的九十年代,他们除了“玩就玩它个天翻地覆”以外,还能干什么呢?于是他们迅速地潇洒起来,而这种潇洒是“右派”大伯和知青大哥所望尘莫及的,后者想潇洒也潇洒不起来啊!
因而他们变得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无所谓。他们比中国历史上任何其它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更无信仰的牵累和制约,但是也比任何一代的知识分子更加缺乏创造的未来指向以及反叛的明确目的。他们的反叛就是为反叛而反叛,为了快感而反叛,为了剩余的力比多的发泄而反叛,就是“在营养过剩却精神贫瘠的年月举行起义”。他们没有完整的传统,所以也就没有沉重的负担,他们无论调侃什么都显得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痛快淋漓,乃至于还带有些许的破罐破摔、自我嘲弄。是啊,玩就玩它个天翻地覆!闹就闹它个天昏地暗!甚至当他们自称为“迷途的羔羊”时,也带着自我调侃与自嘲的语气。他们颠覆传统就像“颠覆一朵花”,他们包装一个人就像“包装一朵花”(《游行》)。至于为什么要叛逆却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正像《游行》中名为“叛逆”的摇滚乐队所唱的:“那我可就管不着了/我没有办法叛逆墙/我空怀着叛逆的愿望/假如我要对墙妥协/那我还活着干什么/还不如干脆死了算了。”对他们而言,“但凡正常的就被鉴定为老古董,一切反常的都能成为反英雄。艺术的瞎眼儿,口吃,秃顶,脚气,吊儿浪当,流里流气,全都成为一种个性的象征”(《先锋》)。这就是中国的先锋艺术的命运,这就是中国最富革命性与反叛精神的艺术家的性格。他们的代表作产生于洗脚与拉屎之后,他们的灵感来自脚臭味和排泄的快感(《斯人》)。
这种为了反叛而反叛的方式,就是肆意地调侃、嘲弄,就是把在旷野上捡到的历史与文化碎片加以随意的拼贴与戏仿。于是,我们有了《先锋》中那些先锋艺术家的代表作:
《存在》:作者撒旦。画展一进门处,用一堆砖头支起来一个金属画框,一个四方形的巨大空框。从框里往外望去,能看到前来观展的人正鱼贯而入,人流熙熙攘攘。脑袋探进框子里的角度不同,进入视野里的物体也各不统一。往低处看,是大大小小的脚,往高处看,是奇奇怪怪的脸,往平处看,是粗粗细细的腰。背景则共同是灰灰蒙蒙幽深莫测的一片废墟。
作者题跋:一切的虚无皆是存在。一切的存在皆是虚无。
《我的红卫兵时代》:“作者鸡皮。鸡皮从废墟里掘来许多烂泥,一把一把掼到画布上。然后他骑上画框,撒了一泡很长很长的浊尿。一滩浓黄悄无声息地洇过画布,漫延流漓出很大很不规则的图形,很醇,也很臊。
《人或者牛》:作者鸭皮。这是鸭皮熬了几天几夜,用电脑绘制出的杰作。他把维摩诘的人像及毕加索的死牛一股脑儿地输入磁盘,结果机器里就吐出一幅牛身人面图。
就这样,他们凭借拼贴与戏仿“后”着一切,把孔子、老子、耶稣基督、释迦牟尼拼贴在一个平面上,让它们和平共处。所谓先锋也罢、反叛也罢、创新也罢,都是废墟上的狂舞而已。这里,最值得指出的是,知识分子的反叛总是与其精神上的压迫感联系在一起的,压迫的对象就是反叛的对象。而由于没有传统,也没有明确的占优势的压迫感,没有最主要的、第一位的“敌人”,所以,徐坤笔下的知识分子的反叛常常没有明确一贯的目标,甚至根本不加选择(我们可以比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压迫感主要来自封建礼教,所以他们常常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反叛对象,如鲁迅与他的“狂人”;革命知识分子的压迫感来自国民党的专制,所以其反叛对象是国民党的党文化;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压迫感则来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所以他们的反叛对象则是极左路线)。
与反叛的盲目性及由此带来的目标的模糊性紧密相关的,他们的所谓“创新”是没有未来向度的,也是缺乏文化资源的;或者说其资源不过是在废墟上捡得的一些文化与历史的碎片(试与“五四”知识分子相比较,后者有系统的中、西方文化教育与知识承传)。他们的创新只是其反叛的力比多的随意挥洒与宣泄,把随手捡来的文化碎片知识碎片痛痛快快地后它一遍,然后又把这些后过的碎片加以拼贴、戏仿、改造: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咱家园。”(后汤显祖)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全靠我们自己。”(后《国际歌》)
“梅花欢喜满天雪,浑身是胆雄赳赳。”(后毛泽东诗词和样板戏)
“去留肝胆两昆仑,我以我血荐轩辕。”(后谭嗣同与鲁迅)
“自古英雄谁无死,我是屁特我怕谁。”(后王朔)
——以上见《先锋》
“你要是打我左脸,我非把你右脸扇。”(后基督教)
“你哟,其实不懂我的心。”
“你这个样子让我很失望很伤心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后流行歌曲)
——以上见《斯人》
此外,他们还后着“三言”“二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后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后着《红梅花儿开》,一直到后《爱你没商量》(以上见《热狗》)。总而言之是古今中外,无所不后。你惊异于他们的拼贴智慧与戏仿才能,你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能指的狂欢”(巴尔特先生的这个著名的说法你以前总是半懂不懂);同时也惊异于他们的无所顾忌,他们的无所选择的乱砍乱抡,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是不可以亵渎的。
一个无所不后的人,如果再加上聪明过人,智慧超群,那么,他们的拼贴与戏仿才能就会令人惊叹,他们的语言游戏产生的效果就会神奇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徐坤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在徐坤的小说文本中,古人的语言与今人的语言、领袖的语言与痞子的语言、政治的语言与商业的语言、文学的语言与性的语言、体育医药用语与文化艺术用语、神圣的语言与亵渎的语言、圣人的语言与痞子的语言,以及庄严的语言与滑稽的语言,全都可以自由地拼贴在一起,可以处在同一个平面上,除刚刚所举的那些例句,让我们再选择其中的几个片断共同欣赏吧:
先锋者,积极要求进步,积极靠近组织,刻苦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又红又专,热爱劳动,积极主动和同志们打成一片之知识分子是也。
……
话题就给引到了球场上。小脑十分发达的运动员们纷纷发表了看法。不仅原来就踢前锋的人对此有意见,就连原来不踢前锋也没打算踢前锋,以及原来不踢前锋但一直想踢前锋却总也踢不上的也都有意见了。
……
先锋就是国产特效消炎药,头孢氨卡糖衣片,Ⅰ号Ⅱ号Ⅲ号Ⅳ号Ⅴ号Ⅵ号,败火去痰。
……
先锋就是赛场上永远打前场的。我想操谁就操谁。
(以上引自《先锋》。引者按:这里巧妙地利用了汉语的同音多义词。先锋既然什么都是,也就什么都不是。同样的技巧还见于同篇小说中的“撒旦”与“傻蛋”等几位艺术家的大名;《斯人》中的“斯人”—“诗人”—“死人”—“是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华大百科全书 文艺卷 F类》:
F:废;废都;废墟;废墟画派: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撒旦、鸡皮、鸭皮、屁特。代表作《存在》、《我的红卫兵时代》、《人或者牛》、《行走》。影响或贡献:唱念做打俱佳,呈前卫状,做先锋科。在纯洁绘画语言方面开创了中国后现代艺术的先河。
(以上引自《先锋》。引者按:这里混合运用体育用语、艺术用语以及戏剧用语,并对辞书文体进行了滑稽模仿,消解其宏大话语。)
鸿雁很快回信,鼓励我发扬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精神,还说杂志社有他的铁哥儿们,到时候自然会帮着批判我,把我批倒批臭,直批到我被公认为学术界横刺里杀出的一头麋鹿。信的最后说,跳好了我便成为英雄,摔下来我便是烈士,横竖都是光荣一回。……
……
什么非理性啊,先锋啊,前卫啊,现代啊,没有什么深奥玄妙的,全是故弄玄虚,在理性之光的照射下一切全都迎刃而解。资本主义早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审美意识越超前,不就离社会主义越近了吗?让我们共同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吧!
(以上引自《呓语》。引者按:这是对政治话语、宏大话语的滑稽模仿。领袖的最高指示与荒诞派戏剧语言的拼贴,不但解构了宏大话语的宏大性,而且使得卑微话语平添滑稽色彩。在徐坤的小说中,此类大话小说,小话大说,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政治性话语商业性地说,商业性话语政治性地说,崇高的话语卑琐地说,神圣的话语亵渎地说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结果是不同类型的话语、不同风格的话语全都被肆意拼贴,话语与语境分离,说话者与话语分离,从而造成了意义的变形,打破了指义的单向性。政治性话语失去了政治性,商业性话语的意义超出商业性,等等,效果神奇。)
在昨晚的世界杯小组预选赛中,中国队在一片“傻×”声中痛失出线权。究其原因,绝不是中国队的体质较之其它国家差,而是其射的欲望不甚强烈。
众所周知,中国是孔夫子的国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告诉他们,要“发乎情,止乎礼仪”,许多一触即发的机会他们不能够很好地把握,该射不射,使劲憋着,勃起的机能遭到抑制,在临门一射的紧要关头,还在四平八稳地调整体位。压抑的结果不是猛烈的怒射,而是软绵的流淌,最后当然也就无法过瘾。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引自《斯人》。引者按:此为德国佬看了足球赛以后写的通讯稿。其中充满了性的隐语,其性说足球的工夫堪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不。凭良心说黑茂还是很能干的,他腰间悬挂着一只尖锐无比似乎能够荡涤一切的巨笔,能够肆意挥洒出白露琼浆花言巧语柔情蜜意,这让林格感到十分满意。黑茂常常会出其不意从前后左右杀无所不在的方向杀将出来,……已经年届不惑了却仍在狼奔豕突东撞西撞的不好好定位,这让林格思忖着恐怕他直干到八十岁也不会有什么更年期。尽管他的多数动作从史的方面来说没有楔入多大的深度,但他的带球过人招数却有着极其巨大的方法论革新意义。他能够一刻不停地奔突交叉跳跃,从文艺批评转向社会政治学,又从文化民俗学转向后现代主义,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头顶背飞倒勾斜传,偶尔还能踢出一些莫名其妙十分出格的主义和动作,一时谁也弄不大清楚他隔多长时间会从哪个方位射。社科竞技场上一时间被他四蹄腾飞扬起的灰尘给蒙蔽了,动作全部跟着失范,也看不清什么比赛规则了。
(以上选自《游行》。引者按:这里使用了笔与生殖器的双向隐喻,对文学批评的性心理分析。文艺批评术语、性术语与体育术语的混合使用。此一“性说文学批评”的“伎俩”与“性说足球”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一代所谓“后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也正是存在于他们无所顾忌、不加选择的乱砍乱抡中(尽管这种革命性因其不加选择的砍、抡而大打折扣)。即使在他们最为荒唐的所谓“胡闹台”中,不也时时可以体会到一些思想的深刻与批判的锋芒么?更不要说智慧的出色表演与文字的神奇游戏了。不信你听听:
“那岳母刺字现象也值得推敲,把‘精忠报国’刺在岳飞背上毫无道理,老太太若真想赠给儿子一个座名铭,干嘛不刺在她儿子能瞧得见的地方,譬如前胸、胳膊或大腿根儿什么的,刺在背上给谁看?岳飞若照镜子那字儿还是反的呢,你说岳老太太有多虚伪,她哪里是在鼓励岳飞呀,这不明摆着是要为儿子日后加官进爵铺一条路,以向人表明其家教良好吗?”(《呓语》)
“我们要学习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为了求取真经,舍弃自家性命不要,不怕饥寒交迫,不怕政府通缉,不怕土匪打劫,不怕美女妖惑,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他西去留学。”(《梵歌》)
“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两点连成一线,建成玄奘旅游经济开发区,增设一日五游景点,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做贡献。”(《梵歌》。引者按:据徐坤小姐介绍,阿梵铃博士在论文答辩会上的此一出色答辩,被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法海大师记录在案,准备补充进政协提案中去。)
难道在这些“胡闹台”中,不是有深意藏焉么?在那场韩愈大战薛怀义的“闹剧”中,薛主持的一番话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赶走了佛,我们还怎么尊称您及您之后慈禧太后为老佛爷呢?这种人(指韩愈之类的精英知识分子),专爱与政府作对,用不得,信不得啊!”而韩愈先生的义愤之词当然也有相当强的针对性:“可恨那些社科院的考古学家们,慑于佛教势力的强大,不敢坚持真理讲真话,只会一味奉迎随声附合拍佛马屁。”就连那位似乎没一点正经的玩主王晓明的玩世不恭的言论中不也深藏着深意与锋芒么:“韩愈啊玄奘啊,说了归齐,也不过就是当朝者手里的一杆枪,需要儒的时候就祭孔,重用韩愈,需要佛的时候就推玄奘,供释迦牟尼。比方说你我,学问做得越大,越摆脱不了将来当枪的命运”;“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和尚也太聪明了”;“要传播点什么思想,必须献媚国王,巴结商人,勾搭妓女”;“当年玄奘译经的时候,政府给高额岗位津贴,给安排宏大的译场,有卫兵把门,指派民政部高级官员负责后勤事务,把全国最有学问的外文好的、中文底子厚的和尚全部抽调到译场给玄奘当助手,这一切我们今天都无法比啊”。是针砭时弊?是指桑骂槐?是隐射现实?你们自己去体会吧,恕在下就此打住了。
徐坤是犀利的,也是无情的,她对于当前学术界、知识界的各色丑剧、闹剧、喜剧、悲喜剧、滑稽剧,对于知识与权力、知识与金钱、知识与性等等的勾连同谋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暴露与讽刺,她作品中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或主动自觉或被动不自觉地自己陷入、参与到这种勾连与同谋的关系网络之中,从而揭示出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中的状况与命运。《梵歌》中的学术会议与论文答辩会议,整个就是以知识面目出现的权力的角逐,无论是学术会上德国汉学家克林斯顿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较量,还是论文答辩会上空空大师与不空大师之间的较量,以及阿梵铃对于他们的闹剧式的回击,从学术的角度讲完全是一场胡闹,一场丑剧,而从权力的争夺上讲又是太真实了,可以说是把我们并不陌生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把知识活动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得入木三分。学术争论不过是精心掩盖过的权力之争罢了。
乍一看,似乎徐坤笔下的知识分子极像是王朔笔下的玩主,只不过是其身份不同罢了,他们是些地道的知识分子,甚至高级知识分子(如画家、艺术家、诗人,或国家级社会科学院的高级专门研究人才)。然而如果就此断言他们只是一些玩主,只有不正经而全然没有正经的时候,只有游戏的时候而没有真诚的时候,只有轻松的时候而没有沉重的时候,那就只看到了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实这些所谓的“玩主”都是些小人物,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也有玩不动的时候,有牵动真情的伤心一刻。而且他们不管多么的没有传统,也不信仰革命,多么地缺少拯救中国乃至世界、重塑信念、重构价值规范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毕竟受过较多的教育,并从事精神生产,其支离破碎的知识也足以使他们比一般的痞子更多一点精神的重负。《白话》中的那帮硕士博士们似乎只是些练嘴皮子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正经也潇洒地很,只剩下了调侃,彼此彼此,无悲无喜。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至少是不那么简单绝对。譬如他们在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是那么的专注与投入,“被片子巨大的魅力震慑住了”,“人类心灵的痛苦竟可以用如此生动的电影语言来表达”,“我们都觉得自己的语言很笨拙,很庸俗,觉得在这之前的一切文人的有关痛苦的描述都变得很笨拙很庸俗了”。直至第二遍看的时候,“看着看着,博士哭了”。还有小林与“我”分手前看照片的情境以及一群人在博士蒙冤之际的挺身而出,都是相当感人的,同时也是让人感到沉重的,绝非潇洒轻松的游戏。《热狗》中的陈维高与《梵歌》中的阿梵铃都不乏小人物的悲哀,陈维高虽然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地交了一个短命的桃花运,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碰壁,活得极其艰难。无论是单位的大小领导还是家中的小舅子,都可以随便地欺负他一把。阿梵铃在论文答辩时的遭遇,充分说明知识界后生小辈周旋于各级“大师”之间是多么艰难。
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先锋》、《斯人》、《游行》中的三位主人公的结局。这三位主人公都经历了从奋斗探索(无论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局限,这种奋斗探索多么浅薄)到幻灭的精神发展历程,而且最后的结局都是因为精神的绝望而自己选择了自杀身亡(不是因为物质的困乏,也不是外力压迫所致)。《先锋》描写了撒旦以及他的先锋艺术从八十年代中期的辉煌到九十年代初期的沦落,再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戏剧性“再度辉煌”的经历,而这个经历被接合到他从虚妄的反叛到迷惘,再到寻根归隐,直至彻底绝望的精神历程之中,但是两者并不完全吻合,而是在最后呈现出深刻的断裂。撒旦在第一次失败之后开始了他痛苦的精神探索。已经充分商业化的田园与佛门都不能使它的灵魂真正得到拯救,倒是商业性的炒作以及变相卖身行为使他神奇地“东山再起”,但是这并没有使撒旦获得灵魂的再生,相反使之陷入绝望的深渊。他在废墟上的仿古乐园中的经历是有象征性的,在这个彻底堕落的世界上,撒旦绝望地呼唤“影子啊,快回到我的身体里来吧”,而后自己解开了身上的安全带。“诗人”的经历是由回归传统的悲剧、现实的悲剧、爱情的悲剧等部分组成。传统对于诗人来说已经是地底下发着阴气的“木片上的灰尘”,其功能只是戕杀诗人的生命力。写在竹片上的所谓“诗”只不过是和尚(“断绝了欲念”的人)的语言(诗=寺+言或言+寺)。被传统阉割一次之后好不容易挣脱出来的诗人,又一头跌入了现实的灾难,再次遭受现实的阉割,这双重的阉割使得诗人成了历史;但是诗人与他的第一位情人绿不同的是,他不安于当这样的历史,不安于用“总得活下去”来作为与现实妥协的借口。于是他组建了名为“蚯蚓”的摇滚乐队,所谓“蚯蚓”“就是那种随便给剁掉哪一截都还能继续生存下去的东西”;“而诗人却永远在心里记着自己只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什么他妈的蚯蚓”。如果说,蚯蚓的比喻使人想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萎缩与以投降为基础的“顽强”生命力;那么不甘当蚯蚓的诗人就是一个不甘于认同所谓“当下状态”的艺术家,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反抗性使得他不甘认同于传统(以高汉镛为代表),也不甘就范于现实(以女老姜为代表),而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当他真心爱着的小姜给了他最后的致命一击后,他彻底地绝望了。在尽情地调侃了一通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以后,他终于“涅了一把槃”,告别了这个他所憎恶而又无力改变的“当下”世界。是的,“这个世界只有斯人独憔悴,这个世界上诗人已经永远消失”。诗人终于以自己的死完成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反抗。与他的那些拼贴起来的作品相比,这更像是一首真正的诗。《游行》中的林格在经历了神(诗神以及代表程甲)的幻灭与性(散文及其代表黑茂)的幻灭以后,开始了“痞子化”的历程,着意包装一位名叫伊克的摇滚歌星。这种包装对于林格来讲只是她自绝于人世前对这个世界的疯狂的、恶作剧式报复。她明明知道伊克他们“焦急渴望得到的,无非是鲜花和掌声”。但是林格还是要包装他们,包装“这帮试管婴儿发芽窜红疯长”,有道是:“包装它,就像包装一朵花,包扎它,就像包扎一朵花。”由此,包装的完成之日势必也就是林格的灭亡之时,“用金的和银的丝绒,以及五彩斑斓的缨络,包扎它,把它扎制成璀璨绚烂的花圈,作为她在这个世俗最后一程探索的祭奠”。因而被她包装起来的他(伊克)唱的就是她(林格)自己的“挽歌”,自我送葬的挽歌。果然,在她的包装行为终于如愿以偿、超级凯旋之际,她完成了自己对于这个“乱纷纷闹嚷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世界的报复,以死结束了她精神探索的悲剧。
当然,这不是说徐坤在作品中把这些人物塑造成了与现实抗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英雄或精英。实际上,除了极少数例外,她对笔下的人物很少给予简单的褒贬,从而她作品中的人物几乎无法用正面或反面概括之,他们都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当今社会中知识、知识分子与金钱、与权力、与各种利益的关系之中,都参与了(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积极地还是消极地)知识分子的悲喜剧、滑稽剧以及闹剧、笑剧。可以说,他们都是“淤泥”中人。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于“淤泥”(他们生活的当下环境)的不满、抗争、无奈与幻灭。显然,徐坤感兴趣的是客观地呈示知识分子的原生态,不加提炼,甚至没有主题。这是徐坤的深刻处,也是她的冷漠处。所谓“从容不迫,心如止水”,其是之谓乎?
这就是徐坤为我们塑造的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群像。他们没有传统又失去了坚实的信仰,既无法完全适应,也难以彻底超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于是只好以乱砍乱抡的“后现代”方式游戏人生、调侃现实、嘲讽自我。徐坤以及她笔下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认同于或就范于他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也没有满足于所谓的“当下状态”。这是她的作品所以显得犀利甚至让一些人不舒服的原因。但徐坤对于现实的批判毕竟更多地采取一种调侃一切、戏拟一切的态度,这使得她的批判力度大为降低,甚至存在自行消解的趋势。无选择的调侃看似威力无穷,而实际上却分散了调侃的目标,从而也就消解了调侃的力量,四处出击的拳头必然是没有力量的,它的低命中率正是它无力的原因。可见,真正有力的反叛必然是有明确的未来指向与价值法则的,因此也必须是有明确的对象的。正因为这样,它才是建设性的而非消耗性的,是集中力量的而非随意出击的,是致命的而非虚张声势的。因而我以为,要使知识分子的反抗性不致陷入虚妄,要使他的解构真正富有建设性,必须明确反叛与解构的对象,而明确对象的前提必然是确立正面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