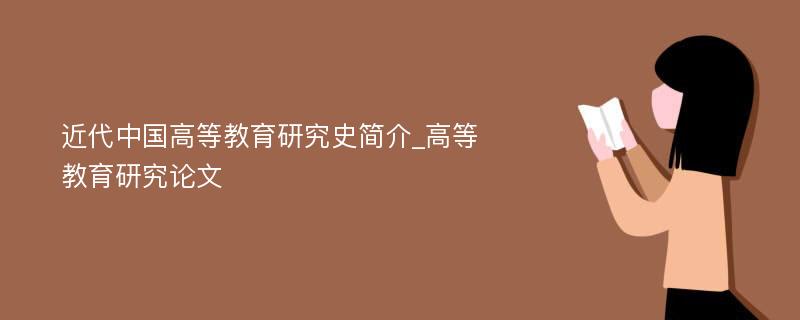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史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略论文,高等教育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4)01-0099-05
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虽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但早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针对当时高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了。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对于当前更好地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伴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而发轫,并伴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演进而得以逐步发展。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郭嵩涛、李风苞、黄遵宪、李善兰等官员和学者就介绍过英、德、日等国的高等教育,但这些介绍大多是只言片语或直观感性的描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许多学者开始对传统高等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张之洞的《劝学篇》、康有为的《请开学校折》和《大同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以及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都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提出了评论和建议,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设想。这些评论、建议和设想大多是建立在他们对中西高等教育理解的基础上,经过一定思考提出来的,体现了他们对高等教育不同的价值取向,已初步具备高教研究的特点,标志着中国近代高教研究的蹒跚起步。
宣统元年(1909年)创刊于上海的《教育杂志》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教育研究专业刊物之一。该刊创办之初,就很重视对外国大学教育的介绍,刊登过不少这类文章,如《美国大学之特长》、《美国之大学》、《德意志大学之特色》、《法国巴黎大学之模样》等,这些文章对当时人们了解西方高等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总体来看,清末的高教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当时高教研究并未受到关注,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文章寥寥无几,对高等教育的评论和思考也大多散见于论述其他教育的文章之中。其中康有为所著的《大同书》中的《大学院》一章,堪称清末高教研究的代表之作。在该章中,康有为对大同时代大学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分析了大学的含义,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其高等教育思想。
民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掀起,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逐步开展起来,一些在国外专攻教育的留学生也开始陆续归国,他们带来了国外高等教育的新理念、新信息,大大推动了高教研究的发展。
1919年,《新教育》创刊,由蒋梦麟担任主干(主编)。该刊物设立专门的高等教育编辑组,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郭秉文等当时高教界知名学者组成,张伯苓其后也加入进来,可谓阵容强大。虽然这些大学者在高教文章的编辑中是否发挥了实质性作用还难以考证,但至少说明高教研究已经开始在学术界得到重视。
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大会把高等教育专门列为第二组。参加高教组讨论的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等18人,大会提交的高等教育议案有14件,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多数是针对高校内部的教学和管理所提的具体建议。[1]这可能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研讨会。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随着近代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高教研究的成果也日益增多。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抗战前,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谢冰翻译的美国哈佛校长埃里奥特的《大学之行政》(1928年),郑若谷的论文集《明日之大学教育》(1929年)、董任坚的论文集《大学教育论丛》(1932年)、郑若谷翻译的美国教育家威尔铿斯的高等教育专著《大学教育新论》(1932年)、孟宪承的专著《大学教育》(1933年)等。其中孟宪承所著的《大学教育》是民国时期一部重要的高教研究专著。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两度出版,对民国时期高教研究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高教研究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不断涌现一批研究成果,其中很多是关于战时高等教育的研究。梁瓯第出版的《战时的大学》(1938年)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欧战时的美国的大学》(1940年)都是探讨战时高等教育的专著。王觉源编的《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1941年)和宋如海编写的《抗战中的学生》(1942年)等论文集,分别介绍了抗战时期各大学的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还创办了《高等教育季刊》,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高教研究刊物,只可惜仅仅维持了两年就停刊了。
抗战胜利以后,高教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战后高等教育的重建方面,并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制度的研究。胡适的论文《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1947年)、许孟瀛的译著《演变中之大学教育》(1945年)、社会大学同学会编写的《社会大学》论文集(1946年)、陶行知的《民族解放大学》论文集、檀仁梅的译著《美国大学课程的改造》(1948年)等都是当时的重要成果。
1949年3月,交通大学教授联谊会成立了高等教育制度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交大、复旦、同济等校的教授组成,是一个以研究高等教育制度为任务的高教研究组织。委员会拟订了研究大纲,计划研究高等教育的目标与任务、设校政策、学校行政制度、课程标准、教育方法、留学政策等11个方面的问题[2],并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因为战争等原因,该研究委员会存在时间不长,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同清末相比,民国时期高教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研究领域的拓展、专门研究组织和研究刊物的创办,使民国时期的高教研究朝着专门研究领域的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
二、中国近代高教研究的主要课题
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面,中国近代的学者已经对某些重要的高教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例如,对高等教育(大学教育)概念研究,从清末就开始了。康有为认为:“凡大学皆专门之学,实验之学。”并把大学界定为十五岁“于普通之学皆已通晓”基础上的专门之学。[3]同时,他还对中小学、专门学校和大学各自的含义进行了区分:“小学中学者,教所以为国民,以为己国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学也。高等专门学者,教人民之应用,以为执业者也。大学者,犹高等学也,磨之砻之,精之深之,以为长为师,为士大夫者也。”[4]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早在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就已经认识到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专门教育,并对专门学校和大学的培养目标分别进行了比较恰当的定位,实属难能可贵。
到了民国时期,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三类:一是指中学后所接受的更高一级教育。在1930年编辑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蔡元培把“大学教育”解释为:“大学教育者,学生于中学毕业以后,所受更进一级之教育者也。”二是指学术教育。傅斯年认为:“所谓高等教育者,大体指学术教育而言,即大学与其同列机关之教育。此中自然也包含些不关学术的事,例如大学学生人品之培养等,然而根本的作用是在学术中之取得、发展与应用的。”[5]三是从高等教育的功能出发来界定高等教育。最有代表性的是庄泽宣对高等教育的定义及性质的论述:“高等教育者,造就一国领袖人才之教育也”,“高等教育在中等教育之上,其性质为专门而非普通,入学者非智力高尚程度相当者无从得益也。”[6]在上述三种定义中,蔡元培的定义与今天的“中学后教育”比较相似,傅斯年的定义则突出了高等教育的学术性特征,他们都还没有把高等教育定位在“高等专业教育”这一层面。而庄泽宣作为一个教育理论研究专家,对高等教育的专门(专业)教育性质的认识更为准确,与当代有关理论已经相当接近了。
又如,近代不少学者对高等教育的意义和大学的社会职能进行了探讨。王国维是近代最早对高等教育意义进行阐述的学者。他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不立小学,不能立中学;不立中学,不能立大学”的观点,认为如果按照这个次序发展教育,“比其材之成,至少亦须俟诸十数年之后”。他举例说:欧洲“大学之立之先于中小学,专门教育之先于普通教育,此学校发达史上不可抗拒之事实也”。主张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做到“初等、中等、高等之教育,三者当并行,而不当偏废”。[7]并指出:“不兴高等教育,则中等及初等教育亦均无下手之处。”“不兴高等教育,则中学之教师又安从得乎?兴高等教育,则食其利者不独初等及中等教育,而二者实于是立其根柢。”[8]王国维在20世纪初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刚刚确立的时候,就能把高等教育放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来认识其深远意义,是很有远见的。
民国时期,近代高等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高等教育的意义及大学的社会职能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体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思想的多样化特色。蔡元培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等论断在当时的高教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雷沛鸿、孟宪承等学者则对大学职能做了更具体的研究。雷沛鸿把大学职能总结为三点:“其一,为研究高深学术、扩大复推进知识领域;其二,为培养专门学者及技术专材;其三,为传播智慧(科学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改善民主。”[9]孟宪承也把大学职能归纳为三点:一是研究,“大学既以智慧的创获,为最高的理想,当然就以研究为其最高任务”。二是教学,“这是凡有学校所共同的任务,大学也非例外”。三是推广,大学要“适应平民主义的要求,推广其知识于它的‘宫墙’之外,而有所谓‘大学到民间去’的运动”。[10]这些观点与今天我们熟知的高等学校“三职能说”已经较为相似了。
不过,近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是很薄弱的,不仅研究者寥寥无几,而且多数研究只是一些观点和看法,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较为少见。与此不同的是,对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并成为中国近代高教研究的重点。
在清末第一个近代学制颁布前,不少学者提出要建立新学堂、开展留学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张之洞建议:“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他还积极倡导留学教育,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11]康有为也曾提议:“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其省府能立专门高等学大学。”[12]而梁启超在他制订的一份“教育制度表”中设想,未来大学制度包括:最高是大学院(自由研究,不拘年限),在大学院之下分设理、工、农、商、文、法、医七科大学,同时设与大学院平行的师范大学和与分科大学平行的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大众高等实业学校。[13]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新学制颁布前后,学者议论的重点则是高等教育的学制问题。当时的《新教育》杂志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例如汪懋祖认为,新学制把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划分为两大系统是不合理的,因为这对于高等专门学校,尤其对高等师范学校的发展是不利的。[14]而陶孟和在《论学制系统》一文中则建议:“废止专门学校,统称大学,依学科的繁简,定毕业年限……除去法学医学两科须延长外,其余各科皆可定为三年至四年。”[15]
从1927年到1937年,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高教界讨论的问题更加广泛。例如,针对当时高等学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现状,高教界对高等学校的地理布局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学者主张通盘策划,从宏观上考虑,重新改组、合并设置大学。[16]有的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目前大学地点的不合理布局和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局面是一致的。[17]又如,关于大学是培养通才还是专才的问题,在30年代也曾有过热烈的争论。有的学者主张大学应该培养专才,重视专门知识技能的训练。王文俊认为:“今日之大学必为造就专才之所,具备专识之后,然后以之为中心而向各方面发展接触,以取得各方之常识,进可以为通人,退仍不失为专才。”而有的学者则主张大学应是通才教育。钱穆认为:“今日中国大学之弊,在培植专才而不知注意通才……如此以往,在彼以为专门绝技,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人。”[18]这些讨论,对3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战爆发以后,教育界曾对战时高等教育方针进行了争论。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服务抗战,调整学科,开设军事课,有的甚至主张“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19]。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战时高等教育持不同的见解。胡庶华认为:“现代战争是参加国整个民族知识的比赛和科学的测验,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截了当改为军事学校。”[20]根据当时的争论,教育部经过考虑后,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21]。
可见,中国近代高教研究的课题与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现实针对性,有的观点对当今的高教研究和高教改革仍有一定借鉴价值。
除了上述的争论和评论之外,在当时的高教研究成果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高等教育现状的批评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近乎“尖酸刻薄”。
如孙晓楼批评当时的大学教育太偏重理论,忽略了人格的训练:“我看到很多的大学教授,有的于畜牧学的理论研究得很高深,然养不大一只猪,有的于园艺学的理论研究得很高深,然而种不活一颗花……大学教育里完全讲职业,讲功利,讲学分,讲文凭,置礼义廉耻做人的方法于不顾,纯以外国功利主义的教育方法来训练现代的中国青年,这是‘相率而为盗’,中国社会的总崩溃,其病因即在于此。”[22]
又如,郑若谷对当时大学教育的批评:“当今的最高学府,只不过是几所红顶高楼,几十位日暮途穷的老朽,几种理化工程的仪器,和几百个学生,当局者且以为校门外高挂大学专门的字样,外表堂皇,大学教育之能事毕矣。而其内容腐败,尽人皆知:先生讲,学生听,先生为谋生而教书,学生为头衔而来说……如果这样新式的大学教育,再继续存在人间,恐怕现代文化马上就要破产。”[23]
对高等教育的这类批评,在近代的高教论文中屡见不鲜,这与当今高教研究相对平和的文风大相径庭。
三、对中国近代高教研究的简要评论
通过回顾中国近代高教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课题,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高教研究并非有的学者提及这段历史时所说的那样“近乎空白”,还是开展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是中国近代高教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几乎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和微观领域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目前高教研究的不少问题,在近代都已经有所研究,还产生了一批颇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如对高等教育概念、高等教育意义和大学职能的理论研究与当今高教理论的有关论述比较接近;对高等教育制度、大学培养目标等问题的研究针对性较强,对当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等教育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是中国近代高教研究的队伍层次较高,不少知名学者和大学校长同时也是高教研究的专家。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雷沛鸿、孟宪承、郑若谷、庄泽宣等都发表了不少关于高等教育的名篇佳作,为近代高教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民国时期几次全国性的教育会议,高等教育组也都是名家云集、群贤毕至。
三是中国近代的不少学术刊物都对高教问题比较关注,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以及《独立评论》等都为高等教育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一席之地,对高教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是中国近代高教研究的论文大都针对时事,切中时弊,崇尚简捷和务实的文风。许多文章篇幅不长,但观点鲜明,开门见山,言简意赅,用词精妙,文笔清新流畅。这值得今天不少高教研究者学习。
尽管中国近代高教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来看,仍然处于一个比较薄弱的状态。
同西方近代高教研究相比,中国近代高教研究还相当落后。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学者就已经陆续撰写了一些学术水平较高、理论性较强的高教研究著作,如费希特的《大学的理念与构想》(1817年)、休伯的《英国大学》(1843年)、纽曼的《大学的理想》(1852年)、赫胥黎的《科学与教育》(1892年)等。法国于1880年就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会(Societe de Lenseignement Superieur),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高教研究组织。但中国近代高教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研究成果多数属于感悟或介绍性质的,欠缺理性思维和系统阐述。如清末代表性的成果康有为的《大学院》,除个别观点外,多数只是充满着浪漫色彩的、理想化的臆想;民国时期的代表作孟宪承的《大学教育》也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全书分为“现代大学的理想和组织”、“中国大学的发展”和“大学的问题”三章,更像一部论文集,其中的理论部分大都直接借用了外国已有的理论和材料。[24]此外,在高等教育管理等研究领域,成果基本上都以翻译外国的理论和资料为主,国内学者几乎没有多少自己的研究。
同中国近代教育学研究相比,中国近代高教研究也相对不受重视,一直没有形成专门领域或学科。从清末引进日本的教育学开始,中国近代的教育学研究一直比较繁荣,各种西方教育思潮和教育理论纷纷登陆中国,各种教育实验也非常活跃,教育学教材和著作更是层出不穷,仅民国时期出版的教育学教材和著作就达到几十种之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高教研究则一直没有形成专门的领域,没有专职的研究人员,甚至还没有“高等教育研究”这一概念。虽然曾经办过《高等教育季刊》,也建立过“高等教育制度研究委员会”,但作为仅有的个案,它们存在时间短,影响有限,并不能作为中国近代高教研究形成专门领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