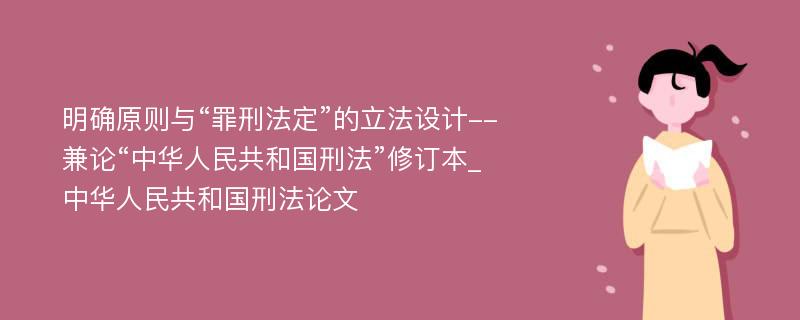
明确性原则与“罪刑法定”的立法化设计——兼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确性论文,刑法论文,原则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是近现代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长期以来,由于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我国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大多致力于对原则的渊源、历史演变和发展的考察,注重是否将罪刑法定原则予以立法化的问题,其直接的成果便是立法者审时度势,以法律条文明示的方式将罪刑法定原则在修订后的刑法中加以确立,并在诸多问题上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在理论研讨中,人们对“罪刑法定”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原则基本特征的概括;在总结司法经验时,对其归纳又大多集中于原则的基本形式,从而无暇顾及罪刑法定原则对各类刑法规范的直接指导意义及其具体量化的内容。随着修订后刑法的施行,诸如刑法是否应当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以及是否应当废除类推等的争论已经成为纯学理的问题,在新的基础上所产生的量变,其坐标应落脚于怎样把握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内容,如何把握其在刑事一体化中的形式,以及又怎样把握其对具体刑法规范的指导意义。就这些角度审视,人们便会发现,修订后刑法的某些内容及其规定方式,仍具有一定的不周延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仍然存在着距离。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和立法取得了长足发展,使得它日渐成为一项国际性的通用准则。相对于刑罚权而言,刑法保障机能的呼声复归,对罪刑法定的研究正侧重于对其派生原则进行的修正和从形式要求开始引申为对其实质的领会。为此,各国学者相继提出了不同的立论,以不同的分类依据对原则内容进行归纳整合(注:具体观点可参见(日)内田文昭著:《刑法总论》,青林书院新社1997年版,第44页;(日)中山研一著:《现代刑法讲座》第1卷,成文堂1980年版,第85、88页。),然而,不可否认,新生的一些原则内容已经不再拘泥于禁止类推、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等几个规范的基线,而是融合于整个刑法的实体之中。明确性原则、同等保护原则、刑罚法规正当原则等,均对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全面的规制。本文以下仅就争议较小的明确性原则结合我国修订后的刑法进行一些论证。
明确性原则,又称避免含糊性原则(Void-of-Yagueness Principle),主要是指立法者必须明确规定刑法法规,使普通公民对法律充分明晰,使司法官员充分理解,防止适用法律的任意性(注:Joel·Samaha"Criminal Law",1993,Fourth Edition,P43.)。目前,多数学者已经认同其构成罪刑法定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其代表人物包括威尔哲尔、内藤谦等刑法学家,尤其是内藤谦教授将罪刑法定原则区分为形式性原则和实质性原则。将明确性作为罪刑法定的实质性内容,这是尤其可取的。此外,对于明确性原则的认识在法律实务中也成为有据可证之事。美国Lan Zetta v.New jersey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人们不应当承担财产、生命、自由受损的危险去臆测法律的内涵,刑法应当明确使人们有效地加以理解,否则即违反正当程序的实质(注:Lan Zetta v.New jersey 306U.S.451,453,51s.ct.618,83L.Ed888(1939).)。
明确性原则在我国已经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有些学者已在刑法教科书中提出类似的观点(注:该教科书指出:“此一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在具体内容上的宽与严、绝对与相对的程度上有过一些争论和变化,其实质是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具体论述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但就整体分析,由于我国1979年刑法奉行“宜粗不宜细”、“宁疏勿密、宁简勿繁”的立法思想。因此,原刑法内容的不确定性相对较为突出,而刑法理论研究的重心在于解决基本立法问题,对明确性原则的认识和论证明显相对不足。尽管修订后刑法有所改观,条文更为明确和细密,笼统的个罪也开始加以分解,但毋庸讳言,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修订后刑法也存在着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方面(注:参见杨春洗:《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化》,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2期。)。
一、罪的明确性
罪刑法定原则开宗明义要求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我国刑法第3条中,不仅重述了立法规定之罪的要义,更从定罪这一动态过程阐述、深化了这一原则(注:对此,有学者认为,修订后刑法第3条表述方法立异实无必要,但我们认为,不论其是否是“标新”之处,在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同时,着重定罪和量刑角度加以解析,至少有利于人们注意在定罪量刑过程中强化罪刑法定原则。)。但就刑法设立的罪的某些制度、范畴而言,仍不免有可圈之处。
1.罪名明确化、法定化问题
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尽管罪名问题颇多,法定化的呼声较高,但立法上终究未加解决。其直接后果是将立法成本转化成了司法成本,即通过司法解释加以界定。由于司法解释本身的痼疾(如解释主体的多样性等),有可能导致罪名偏差(注:参见游伟:《罪刑法定与立法权、司法权的划分》,载《法学前沿》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168页。)。不仅如此,罪名明确化、法定化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其能够直接引起犯罪构成要件的明晰,对定罪产生直接影响。立法中忽视了这一问题,不仅导致实际确定罪名的困难(一些解释而来的罪名亦颇有可议之处),而且不利于变相“口袋罪”的分解。如刑法第217条有关侵犯著作权的犯罪,早在单行刑法实施期间,关于其罪名的争论即已形成,现在仍然认同为“侵犯著作权罪”。这里虽有如何区分“侵权”与“违法”界限的问题,但“侵犯著作权罪”毋庸置疑地应当是包括刑法第218条在内的一个小类罪名。如果当初考虑罪名立法问题,不仅纷争将息,而且第217条的规定也不会如此繁杂。
2.罪名法定的意义问题
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刑法的某些罪名也随之产生了价值问题。如刑法规定了多种证券犯罪,作为一种法定犯罪,其基石是相应的证券法律,但在证券法及相关法规未及颁布或者尚不完善的条件下,罪名存在的价值及其司法规制程度便成为待证之事。另一类罪名如聚众“打砸抢”罪,这里且不论其概念的规范性和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承传意义,单就第289条条文本身分析,犯此罪只能够按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或抢劫罪定罪处罚,原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条款亦被取消,罪刑的对应性被打破了,其罪名基本上已无实际意义。此中规定或许略有立法技术上的价值,但落实到该条条文的现实性意义上,这种技术价值仍不见有多少可取之处。
3.犯罪构成不确定性问题
犯罪构成在立法上有多种表述方式,如果表述不够明了,对其理解便会染上浓重的主观臆测性。在刑法第257条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2款和第60条虐待罪第2款中均规定了“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致使”的主观心态是仅指过失抑或可以包括故意?从1979年刑法规定为“引起”以及法定刑的具体期限看,“致使”的主观罪过似乎只能是过失。但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在多数条文中,“致使”不包括主观故意或者不包括间接故意显然与法理不合,如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中“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以发现,这里包含的主观罪过与上述条文有质的或程度上的差异。其至少应包括间接故意在内。此外,刑法分则条文中还有一种与其相类似的罪过形式。如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第234条、第232条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这里的主观罪过显然也应包括故意在内。
同时,修订后刑法分则条文对某些客观行为的规定也带有不确定性,如针对刑法第270条第2款所规定的将他人遗忘物占为己有的行为,一些人提出疑问,将他人的丢失物占为己有能否以此处理(即遗忘物是否包括丢失物)。这与美国刑法中的流浪罪(The Crime of Vagrancy)的特点引发的争议颇相类似(注:对于流浪罪的认定,首先要认定什么是流浪者(the tramp),什么是游手好闲(idleness for perse)。由于法律含混不清,后来在Papachriston v.City of Jacksonville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采用了上述原则,但《模范刑法典》将这一“口袋罪”加以分解。参见American Law Institute,Model Penal Code,tentative draft no.13(1961),P.61。)。详加分析,我国刑法第270条中的规范疏漏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便发生了对条文的理解问题。我们认为,对“遗忘”的理解不应局限于从受害人的角度去进行判断,而应将其理解为侵害人侵占财物时的认知状态,即不论受害人遗失的主观情况如何,就侵害人认知状态来看,均将犯罪对象认定为他人遗忘物。当然,此种论证仍与明确性原则有所逆悖,但却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补足方法。
二、刑的明确性与均衡性
首先是明确性问题。法国学者保曼认为,罪刑法定要求在明示可罚的行为类型的同时,更要求刑罚的种类、分量,明示可罚性的程度。在我们看来,刑罚的明确化、规格化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刑法对刑罚体系乃至对个罪的法定刑都进行了较大的变革,个罪中较为典型的便是诬告陷害罪的法定刑的变迁。在1979年刑法第138条中,此罪判罚的尺度是“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并无独立确定的法定刑。修订后的刑法明确将其法定刑分设两档,分别以情节轻重作为裁量分档的标准,体现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视与贯彻。然而,刑的不确定性遗迹犹存。譬如,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即是如此。修订后刑法第49条删除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死刑条款,明确规定不得对其适用死刑(包括死缓),也就是说,最高刑只能判至无期徒刑,但第17条又明文规定,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现在的问题是:对其从宽是建立在完全刑事责任的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第49条的基础之上?如是前者,则犯罪人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如是后者,则至多只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立法精神显然指向前者,但以此推论,第49条的有关规定又无必要了。
其次是均衡性问题。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日本的一些学者对此持赞同观点。我国学者一般也承认罪刑关系的法定客观性,并指出除了考虑社会危害性大小决定刑罚轻重外,还应考虑犯罪性质决定刑种(注:马克昌:《罪刑法定主义比较研究》,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事实上,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内涵,罪刑均衡的基础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客观性,即不是主观危险性的大小,而是刑罚惩罚的不可避免性。因此,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减弱或灭失,不宜被过分夸大。否则,必将影响罪刑的均衡性,导致罪刑法定原则基础的破坏。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犯罪自首后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们认为,此处立法过分夸大了包括悔罪在内的主观情节,这种规定使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受到抑制,动摇了罪刑的均衡关系,其后果有可能导致犯罪行为人故意规避法律。同时,由于自首和立功的概念仍不够确定,在适用法律时又可能致使司法权的进一步扩张。这是值得引起警觉的。
三、定罪标准的法定化
如果以上所阐述的两大问题是在刑罚静态立法的形态下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那么实际立法以及刑法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定罪与量刑。在这种动态过程中如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这需要倾注更多的关心。然而,与此相反,我国1979年刑法、单行刑法却一直未加重视,1997年颁布实施的现行刑法同样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
就定罪角度而言,在定罪过程中,修订后刑法废止了1979年刑法第79条的类推制度,最为有效地维护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规范层面上的完整性。然而,定罪过程中的痼疾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对牵连犯的定罪问题上,是作为处断上的一罪还是按照数罪并罚进行处置,立法未予说明,由此形成了并罚说、从一重处断说、折衷说等观点。司法实践曾一度承认从一重处断说,即作为处断上的一罪处理。但尔后通过的一些单行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又明文规定,对牵连犯可以实行数罪并罚。这种状况的产生与当时的刑法理论和立法水平一脉相承。然而颇为遗憾的是,修订后的刑法似乎承袭了这些定罪标准的不统一性,使得对牵连犯的一罪和数罪的定论难以维护原则所要求的明确化和法定化。其中最为明显的规定是刑法的第241条。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的犯罪,若有该条第2款、第3款的行为,则与第1款构成数罪,如存在第4款行为的,则一律按照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处理,而不论各个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有牵连关系。由此,可以反证该条第3款、第4款均应包括牵连犯在内。既然包括牵连犯,其定罪的方式、标准却迥然相异,这就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难以落实。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实行着多元标准,其基准是折衷说,其目的在于不轻纵罪犯。多种方法交合并用,又以定罪量刑较重者优先为原则(注: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页。)。我们认为,在定罪过程中处理一罪和数罪关系,如何才能有效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主要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牵连犯的罪数及处罚原则一个在立法上需要加以明确的问题,应写入刑法典的总则规范,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刑法中也是有例可循的(如台湾刑法第56条);其二,对于牵连犯无论是从一重处断,还是作为数罪并罚,都应采用划一的标准,不应适用多元标准,更不应以重刑制裁为出发点。
对于共同犯罪(尤其是有特殊身份主体参加的共同犯罪)如何定罪,尽管刑法第25条至第29条作了总则性规定,但分则条文中的某些规定却使罪刑法定原则所体现的罪刑均衡性受到了严重挑战,其主要表现是:首先,依据原刑法总则规定,共同犯罪是应当作为相同一罪处理的,但近年颁布的许多单行刑法却实际上造成了分别定罪的现实。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分别定罪的实际判案(注:参见孙万怀:《关于共同犯罪的修改》,载《东吴法学内刊》1997年第4期。)。而修订后刑法只是将单行刑法的个罪依据客体的不同进行了归类规定,并未对共同犯罪定罪标准加以实质性更动;其次,即使在作为一罪处理时,其定性标准仍然不十分明确,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只能基于实行犯身分定罪。如共同强奸罪的定性只能依据男子的性别身份定罪;其二,以法定主体的特殊身份定罪。如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伙同贪污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在此,就不完全以实行犯身分或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其三,以实行犯的实行行为为标准。如刑法第156条、第198条规定的保险诈骗等罪;其四,以共同犯罪行为人的实际作用或分工(总则性规定)为标准。我们认为,对有特殊身分主体参加的共同犯罪,由于其身分、行为及其他构成条件的复杂性,适用单一标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注:关于共同犯罪的定性,理论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以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为标准,一种主张以实行行为的性质确定。详文可参见游伟主编:《刑事立法与司法适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定性标准的多元化并非不可考虑和研究的,关键是对其分类适用应有合理依据,标准应该法定化,从而减少其中更多的任意性因素。
四、量刑情节的法定化和明确化
由于量刑情节直接决定宣告刑的轻重,直接反映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因此,多数国家均对其进行了严格限定。在立法者看来,量刑幅度之内的从轻或从重处刑,完全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份内的事,刑法只注重于那些超越量刑幅度的减轻、加重或者只作有罪宣告而免除其刑罚之类足以使刑罚轻重发生质变的情节确定,并同时制定了减轻、加重裁量的严格幅度,不致使宣告刑与基本刑相去甚远。在这方面,诸如德国、意大利、法国刑法的规定就较为典型。
修订后的我国现行刑法比较重视量刑情节的法定化,在总则和分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努力,进行了条文设计上较大的修改,以求与量刑法定原则相适应。然而细加研究,其不足之处仍然十分明显。首先,对基础刑期的设定还不够明确。对此,理论上虽曾提出过多种模式,但它们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极为有限;其次,对减轻情节的实际运用,没有确定下限。这样,便导致了诸多原本没有必要的理论争论。由于争论犹在,实践中可能形成司法裁量权的任意扩张,从根本上动摇罪刑法定原则。如何加以修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纯属立法方式上的问题(注:详文参见游伟、孙万怀:《新刑法与量刑情节》,载《上海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至于具体量刑情节的设置,同样应当充分贯彻明确化的要求。例如修订后刑法在法定情节方面首次增设了“立功”,但是何谓“立功”,尤其是何谓“重大立功”,刑法规定却不甚明确,只是在刑法第78条减刑制度中,吸收了1996年《监狱法》的立法成果,列举了重大立功的6种表现,但从第78条的角度进行分析,则又显然被限定在服刑期间的立功表现了,范围显得过窄。所以,刑法第68条的“重大立功”与第78条相比,是不同阶段上的立功,其内容自然相异。由于立功范围的确定会对量刑产生极大的影响,意义重大,因此,新刑法中未作详尽界定,同样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不相切合。
笔者认为,我国社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我国现行刑法也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周延。从刑法修订前后的比较以及我国刑法发展的进程分析,我们同样认为,1997年刚刚修订的我国刑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这一特征所显示的诸多不足,其形成原因是多元性的,有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文化背景,有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的一般性局限,也有刑法自身运行机制的制约,等等。与此相适应,刑法不足的表现也是多层面的。有的表现在立法过程中,有的表现在司法活动上(如司法解释中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不切合性);有些表现为实体的静态方式,有些又表现于运行中的动态过程。所有这些都昭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化及其全面贯彻并非一蹴而就,仍然需要我们在立法尤其是司法活动中付诸艰苦的努力。我们坚信,只要我们达成共识,积极推进立法的发展和司法的进步,“罪刑法定”就一定会从“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化设计,并最终形成一种普遍的法治思想,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