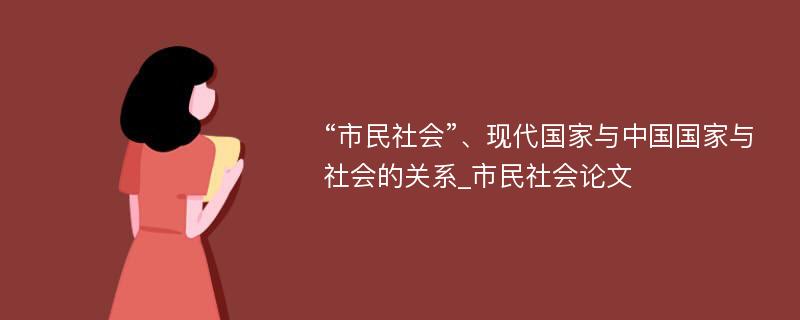
“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国家论文,中国论文,市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的简略考察,指出独立于和外在于国家的所谓“市民社会”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时期的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它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要求人们探索一种能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与主动精神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这方面探索的成功将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关键词 国家 社会 市民社会 现代化 “强国家—强社会”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这里,国家指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通过合法垄断暴力的使用权而对其居民进行强制性管理的各种组织机构及其体现的强制性等级制关系的总体;社会则相应地指在该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居民及其群体的非国家组织与关系的总和。两者的关系的调整,也就是对国家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以及某一社会共同体中强制性等级制关系与其他关系(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血缘的等等)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比重的调整。在西方,人们习惯于将国家行政性关系之外的那一大部分社会生活称为“市民社会”。自由主义传统的理论家则向来把“市民社会”的存在视为公民自由和社会发展的保证。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全面改革之后,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在苏联、东欧寻找“市民社会”的因素,视之为这些国家社会变迁的主要表征。苏东剧变之后,他们继而把“市民社会”的发育看作是“自由民主制度”在那里得以巩固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当然也有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①]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也展开了一场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目标同样是建构一个“市民社会”[②]。这种主张是否适宜,在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调整,这就是本文试图探索的问题。
一、“市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演变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西方是一个渊源久远但其内涵又不断变化的概念。最初的civil society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拉丁文中“市民社会”(societas civilis)这个词就来自于古希腊文。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开篇即使用了这个词,用来指城邦作为一种根据宪法建立起来的独立自足的社会团体的性质。[③]在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civil society的概念获得了一个新的含义,用以反映与“自然状态”相对的社会状态。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结束彼此敌对的自然状态,通过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而结成“市民社会”[④]。其他社会契约论者,如洛克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civil society一词。[⑤]自启蒙时期以后,人们还用civil society来指称社会中世俗的公共生活,与宗教社会相区别。从17、18世纪开始出现的“市民社会”的现代含义,指的则是当时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之外萌发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它意味着一种经济的、私人的社会活动领域,与政治的、公共的社会领域相对。首先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一词的是苏格兰思想家亚当·福格森。福格森看到了近代国家向以前属于私人的社会领域不断扩张的趋势,并且就这一趋势对于“市民美德”的侵蚀感到担忧。[⑥]这样,在他那里,“市民社会”与国家就被放到了对立的两极。
一般认为,福格森的《论市民社会的历史》一书被译为德文以后,对德国思想界,尤其是黑格尔产生了较大影响。[⑦]德文中把civil society称为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更加强化了福格森给这个词赋予的含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与福格森不同,黑格尔对于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侵蚀没有任何不安;相反,他把“市民社会”作为理念发展的前国家阶段。理念只有从“市民社会”提升到国家,才算是实现了它的本质。[⑧]当时的德国迫切需要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扶植,这种理论当然也就是社会现实的反映。黑格尔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看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矛盾统一的关系,但在他之后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则一般都秉承福格森的传统,强调两者相互对立的一面。澳大利亚学者里吉比认为:“市民社会包括了这样一些结构与过程,通过它们,个人与群体在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能够独立于国家的控制结构而相互作用。”[⑨]英国学者格雷也认为,“市民社会,……指自愿团体、市场交换,以及私人结构的领域,在其中并且通过它们,具有不同的意识以及不同的而且通常是相互竞争的目标的个人能够和平共存。”[⑩]
自由主义传统能够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明确的区分,其历史根据就是封建社会中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在西欧封建庄园的海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它们通过向封建主纳税而换取或者干脆一次性地花钱买下自己的“自治”。这种自治城市拥有自己独立的立法、行政与司法系统以及财政和防御体系,城墙就是封建主权力的最后边界,所以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经济逐步演化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从而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经济上与封建社会旧有的秩序相对立。另一方面,“公”与“私”、国家与社会的严格区分在西欧的政治法律思想和实践中本来也就有悠久的传统。罗马法曾对男性公民的公共义务及其作为一家之长的私人角色进行了区分,并且界定了有关私有财产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这样一种“公”“私”之分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思想家当中再次得到反映,他们一般都把私有财产当作国家行为不能轻易涉足并且应予保护的对象。即使像让·布丹那样的绝对君权论者也承认,主权者没有公正合理的理由而侵犯臣民的财产的行为是对自然法的一种违抗。
总起来说,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中,“市民社会”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意味着一种独立于与对立于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其次,它也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一种法律上的界限。当然,两者并不是始终吻合的。近代欧洲的城市相对于封建国家而言可称为“市民社会”;而城市内部的私人领域相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则又是一种“市民社会”。不过,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国家行政权力之外的社会联系与社会生活的理论上的抽象基本上还是合适的。以色列社会学家什洛克·阿维内里对“市民社会”的含义与实质进行了如下的概括:“出现于中世纪晚期并最终导致资产阶级世界与工业化兴起的,是一种活动范围的缓慢分化,由此导致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作为自主领域的合法化,从此不再受到封建制度在伦理上、宗教上和政治上种种约束的阻碍。”(11)他并且认为,西欧的现代化就是“市民社会”“从政治—宗教领域分化出来的结果”。(12)
“市民社会”被认为构成了国家行政权力之外的具有自身联系的社会实体,其中的关键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化工业发展所包含的内在逻辑。杜尔克海姆着重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劳动分工的专门化越少,社会整合越要依赖有效的规范制度。然而,在工业化社会中这种强制力量逐渐被各种关系代替。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和可信赖的法律系统。高度发达和专门化的劳动分工使社会成员相互依赖,也使有机的团结得到固定。杜尔克海姆相应地把行政性的联系称为机械的联系,而把工业化发展和社会分工导致的联系称为“有机的”联系。“市民社会”正是这种有机联系的总体。他断言,“新的社会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凝聚在一起”(13)。这是“市民社会”的社会学含义。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
与自由主义理论家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市民社会”恰恰是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基础。马克思曾经总结性地指出:“我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黑格尔根据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4)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反对对国家和对“市民社会”的崇拜。马克思明确宣布,无产阶级要“为消灭(Aufhehung)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15)。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对“市民社会”的问题有较多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葛兰西。葛兰西不同于他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处是他提出了上层建筑的两个层面的思想——“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统治’或指挥的职能是通过国家和‘合法的政府’来执行的。”(16)换言之,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只是统治阶级行使其统治权的一种间接的工具。因此,他反对把国家与“市民社会”强行分开的企图,认为国家已经包含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也是‘国家’,并且不仅如此,市民社会恰好构成国家”(17)。
葛兰西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是因为他看到了自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国家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它不断向“市民社会”渗透与扩张的过程。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已经牢固地统治了“市民社会”的一切领域并使之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基础。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也承认,“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这只是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才能成立。”(18)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统一的行政、司法、税收和常备军体制的建立,恰恰是一个把原先独立于封建秩序的“市民社会”再度纳入国家的过程。与此相伴随,近代国家在广泛的领土范围内首次建立了可以不经任何中介而直接作用于它的每一个成员的强制机制。与封建国家相比,这显然是一种极度扩展了的国家。正是这样一种国家及其成员之间直接的强制性联系,为以后国家社会职能的扩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现代西方国家社会职能扩展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控和干预。凯恩斯在1926年宣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自由主义经济假说并没有根据(19),也就是说,仅仅依靠非国家的市场力量,经济并不能自动达到平衡。此后,西方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不断扩展。它不仅成为平衡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而且在战后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的规划、保护和干预已经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现代国家社会职能扩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福利国家的建设。福利国家乃是国家以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的身份,试图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矫正社会自身所固有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的趋向,并以此作为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一种手段的结果。福利国家的建设遍及西方世界,所差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这是就较早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而言的。对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来说,国家在其社会职能方面还表现出以下的特点:第一,国家维持了高水平的社会稳定与社会整合;第二,国家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大量扶持与保护;第三,国家不仅制定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而且通过产业计划乃至行业计划和对个别企业的指导以促进经济发展。这类国家中较为典型的是日本和韩国,一些西方学者因而相应地称之为“强国家”,因为它们可以“独立于特定的团体之外制定政策目标”,“可以改变团体和阶级的行为,并且可以改变社会的结构”。(20)从“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不是社会独立于国家,反而是国家在一定的程度上独立于社会。国家强有力地约束着社会的行为,创建并且保护国内的市场,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不少学者认为,这种模式不仅对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且也对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提出了挑战。(21)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指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者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22)所谓的“竞赛规则”的作用包括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各种所有权主体的法律地位的确定,以及对社会经济行为的规范等等,它们是市场经济顺利有效地运行的前提和保证。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规则”中,除了少部分是国家对市场原则——如公平竞争的原则——的强制性保持之外,其余的大部分却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构成部分。它们可以被看成是政治与经济的接合部,是政治的终点和经济的起点。这些规则是对市场的约束与限定,它们反映着某个社会共同体基本的价值取向及其对社会共同生活的认识。像对所有权的地位、劳动时间、劳动条件与强度、用工制度以及税收制度等等的规定都属此类。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与经济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作为不同关系形态体现者的“国家”与“社会”也并不是两个泾渭分明、完全彼此独立的实体。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因而指出:“‘经济’是指这么一种行为,它有可能也是政治行为,只是要求以特殊的方式实行。”“我们之所以把这些过程称之为经济的过程,仅仅是因为还有一个假设:我们从它们那里可以见到一种价值的提取。”(23)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哪些过程被视为经济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当国家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者从事某些生产活动,或者对一定数额的个人收入课以高额累进税时,这些因素的经济过程即告结束。布坎南也同样认为:“强调作为社会过程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另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按照此处的公式,‘经济’完全被包含在‘政治’之内,经济是一个解决不同的个人利益之间的潜在冲突的过程。……在制定规则或立宪阶段,政治可以给市场分派任务,使市场能够避免广泛的公开冲突并促进社会相互作用的顺利进行。”(24)
总起来说,在现代社会,国家的作用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孤立地谈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已经毫无疑义。无论就国家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而言,还是就国家必须行使其广泛的社会职能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西方不仅仅只是历史上的特例,而且也只能是一种理论的抽象。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现代国家职能的扩展而认定“市民社会”的理论在现代西方国家纯属虚幻。正如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所指出的,“市民社会”虽然并不能与国家相分离,但它毕竟又是一种间接的、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社会协调与控制手段。它表明了那些不应该或者不适宜由国家直接或广泛介入的社会领域。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传统则对于国家的行为提供了某种不能替代的约束。它对于防止国家的专断行为,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葛兰西等人指出:“市民社会”的存在及其机制,的确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同时也使这种统治能够显得比较持久和稳定。
三、“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
看起来,无论就现代国家发展的一般趋势,还是就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的经验而言,认为在中国应该通过构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以实现现代化的观点都是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的,而在实践上,这样的观点则可能是有害的。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的确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状况,但这毕竟不能等同于在国家之外形成一个独立于国家又能向它施加压力的“社会活动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这首先是因为现代国家的职能必然要求它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领域,其次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的特点要求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强有力的推动。对于那种独立于国家又与国家相对抗的“市民社会”的容让与支持只能导致经济的混乱乃至政治的动荡。
1979年以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较大的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国家的社会控制幅度明显收缩,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的相对量和绝对量都已经大大减少。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全民所有制所占比重显著下降,集体、个体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成分迅速上升。第二,国家的社会控制手段渐趋多样化,改变了以往几乎完全依靠行政命令与计划指令的状况,经济、法律等其他社会控制方式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三,国家自身的权力结构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地方、部门、企业乃至个人占有与处置社会资源的自主权不断扩大。由此可见,改革中限制国家的社会职能范围,扩大各种社会经济组织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同时扩大各种非国家的社会联系方式在社会中的控制与协调作用的趋势是十分强劲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应该对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进行全面压缩。正确的方向应该是在总体上缩减国家的社会控制幅度的同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国家职能进行科学的调整,并且不排斥在某些方面强化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和扩展其职能范围的可能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职能的界定必须同时遵循三个方面的标准,即现代国家的一般要求、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这就是说,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与控制的“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与社会之间主要是不对立和冲突,而是一种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的有机统一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的“合作主义”理论可以给我们带来若干的启示。
“合作主义”理论最初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其代表人物是德国人卡尔·施密特。施密特认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国家与人民之间对立冲突的基础之上的:一方是拥有自己受到宪法保证的权利的“人民”,另一方则是拥有自己权力范围的“国家”。然而,只要在这两者之间引入一个调解性的中间因素,即“运动”,那么这种传统的冲突就可以得到解决。(25)但是,由于“合作主义”理论曾被德国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所采用,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时间内,人们不再提及这个概念,直到60—70年代,一些学者在对西北欧国家的研究中才又重新指出,这些国家中存在着“合作主义”的因素——在那里,社会与政府的关系表现出一种有规则、有秩序的特点。代表社会的一方一般是“由国家组织的”,“在各相关领域享有代表权”的群体,它们与政府各部门就工资、物价和投资政策等问题进行定期的谈判。(26)有学者认为,这一政策形成的模式与具有较强竞争性团体的模式(如美国)相比,能带来更大的社会稳定、较慢但持续的经济增长、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27)
这种重新出现的“合作主义”理论又被称为“新合作主义”,其代表人物美国政治学家菲利浦·施密特认为,“合作主义”模式尤其适合于“后自由主义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和有组织的民主的福利国家”(28)。他对该模式进行了如下描述,即它是“一种利益代表机制,在其中选民团体组织成为有限数目的、单一目标的、强制性的、等级制的和功能分化的不同范畴,通过国家的再组织或认定(如果不是创造的话),并由国家为其保证在各相关领域的特殊的代表权的垄断地位。作为交换,这些组织在其领袖的选择和需求与支持的活动方面遵循(国家)的某种控制。”(29)
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界,新合作主义并未取得主导地位,但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种合作的关系,但并不否定各种社会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强调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对国家的控制、监督与参与,同时也强调国家对各种社会组织的保护与促进。因此,我们认为合作主义对于当代的社会政治过程具有较好的解释与规范功能,而经过改造之后,这种理论也可以为中国未来“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作为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改革目标的“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首先要求社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各种非国家的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较为广阔的自主活动领域,国家行政性联系之外的其他社会联系方式在社会生活的协调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下,国家吃掉了社会,国家的行政性等级制关系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各种社会组织和群体都作为国家的附属物而存在。实践已经证明,这样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既容易产生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也容易导致社会总体效率的次优化,因而改变这种模式是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与提高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的必由之路。
“强国家—强社会”的目标模式其次要求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在尊重社会及其各种组织法律上的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过程,对后者的活动进行多种形式的协调与引导、或者为它们创造出适宜的活动环境与条件。对于社会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环境保护、社会公正、国民教育等等,国家则必须主动地予以解决。
“强国家—强社会”的目标模式最后要求建立国家与社会,尤其是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种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在这种模式中,各种社会组织自然不能作为国家的一级行政单位而存在,它们应该是具有确定的法律地位、独立于国家的行政控制的实体。在这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协商制度和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都体现了正确的方向。以后的任务是使这些制度进一步完善和法制化,并扩大协商与对话的范围。
如果说在“市民社会”的模式之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视为一种双方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则,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零和博弈”的话,那么“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则强调在国家与社会这两者之间进行沟通与协作,从而实现一种“非零和博弈”。也就是说,没有必要把国家的所得视为社会的所失,或者相反。实际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方面来看,都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求得社会与国家、个人与整体的利益的协调发展。波兰社会学家奥索斯基对于当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区分,认为存在三种模式,即第一,集体理解的模式,即建立在传统习俗之上的社会生活;第二,多元化模式,它是由于相互作用的“自然法则”而获得的社会均衡,在遵循某些竞赛规则的情况下,是各个不协调的决策的结果;第三,一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决策规定社会生活,主要决策都由一个机构制定并且监督实施。奥索斯基认为,由此尚可演绎出第四种模式,“第四种社会制度的概念是——尽管旧式的自由主义者反对——把社会生活的多元特征与合理的计划系统协调起来,这向现代人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里,它是一个多元社会中的范围最广的计划性合作的方法论问题,是解决整体趋势与多元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之间的冲突的问题。”(30)
除去奥索斯基的特殊用语不论,他提出的第四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与“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在人类社会的现阶段发展水平上,人们除了把国家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者之外尚无别的选择,这是两种模式沟通的基础。对于我们来说,“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能够体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规范性特征,中国也具备建设这种模式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事实上,也只有通过探索出一种全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中国的改革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注释:
① 参见:Stephen White,John Gardner,George Schoplin and Tony Saich,et al.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London:MacMilln,1990:Ellen Frankel Paul,ed.Totalitarianism at the Crossroad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h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Center and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0,以及Robert F.Miller,ed.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Communist Systems.Sidney:Allen and Unwin Publishing LTD,1992等。
② 参见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号,第61页。
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
④ 霍克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1—132页。
⑤ 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8—76页,128页。
⑥ Adam Ferguson.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Edinburg:University Press,1966,pp.136ff.,John Keane,ed.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New European Perspective.London:Verso,1988,p.43.
⑦ Norberto Bobbio.Democracy and Dictatorsthip-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English translation by Peter Kennedy.Cambridge:Policy Press,1989,p.37.
⑧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7页。
⑨ Robert F.Miller.op cit.,p.11.
⑩ Ellen Paul.op cit.,p.100.
(11) 什洛克·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12) 同上,第11页。
(13) 参见[美]W·C·珀杜等著:《西方社会学——人物·学派·思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1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15) 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8页。
(16) 葛兰西:《狱中杂记》,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页。
(17) 同上,第222页。
(18) David Held.Political Theories and the Modern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p.169.
(19) 见罗志如、范家骥、厉以宁、胡代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20) 戴约等著:《东亚模式的启示——亚洲四小龙政治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21) 同上,第141页。
(22) 弗里德蔓:《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6页。
(23)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体制》,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11页。
(24)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3页。
(25)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95页。
(26) Robert Kavaik.Interest Groups in Norwegian Politics.Oslo:University Press,1976;Philip Schimitt and G.Leobrum.et al.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California:SAGE.,1984.
(27) John Goldthop.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Cambride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28) Schmitt Philip."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Politics Review,January 1974,p.105.
(29) Schmitt Philip.op cit.,pp.93-94.
(30) Stanislav Ossowski:On the Peculiarity of the Social Science.Warsaw,1962,p.86.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